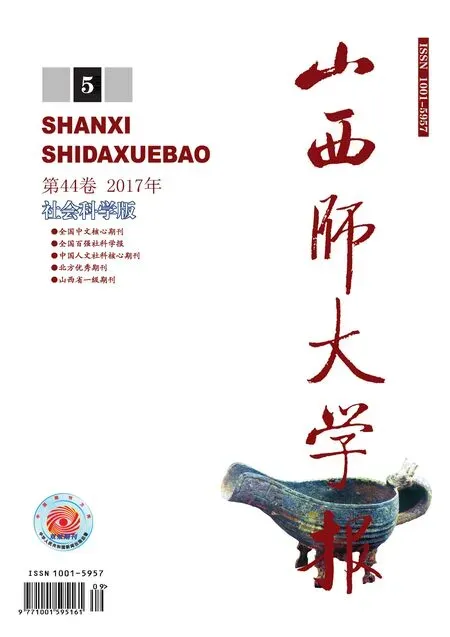重返戈夫曼的拟剧论与自我分析
——一种社会批判的路径
王 晴 锋
(中央民族大学 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以《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为国内外学者所熟知,该著作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拟剧论与关于自我的阐释。人们通常关注的是拟剧论及其转喻意义,也即莎士比亚那句名言——“世界是一个大舞台,人人都是演员”——的社会学隐喻,而较少解读其深层的结构性意涵。有些社会理论家对戈夫曼的自我观提出批评,认为它缺乏能动性、关于自我的实证主义解释与自我呈现和印象管理的论述不一致[1],无法实现的自我[2],过于极端的情境化自我观念[3]79以及自我沦为没有使用价值的“纯粹商品”[4]383,等等。事实上,这些批评仅是针对拟剧论中自我的某种形式,它或凸显情境化的自我,或将矛头指向作为能动者的自我,未能辨析戈夫曼自我观的复杂性而以全景式视角加以讨论。本文不再重复读者早已耳熟能详的拟剧论措辞,而是透过戈夫曼的戏剧表演语汇,理解它背后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性意义,试图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探讨戈夫曼的拟剧论以及关于自我的阐释,从而更好地理解拟剧论与自我分析蕴含的丰富意涵。
一、拟剧论与印象管理
在拟剧论中,戈夫曼以自我呈现和印象管理来表达莎士比亚的世界观:“世界是一个大舞台,人人皆是演员。”日常情境中的个体运用各种技巧在他人面前塑造或维持某种印象,并应对在该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偶然性。舞台行为受个体扮演和想象的自我形象的型塑,同时也受剧本化的角色规范制约。戈夫曼详细论述了个体向他人呈现自身及其活动的方式,引导和控制他人形成关于他的印象的手段以及他在维持表演时的各种行为选择。在面对面的互动过程中,个体试图通过各种信息源和信息载体,诸如举手投足、外表、过往经历与记忆、言语、文案记载、心理特征等方式获取或调动关于共同在场者的信息以进行情境定义,理解并预期其当下与将来的行为。个体关于自身的观念是其投射出的情境定义之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的表意性或沟通行为涉及两种不同类型的符号活动,即“给予式”表达与“流露式”表达。前者指个体明确使用特定的言语符号及其替代物传达附着于这些符号的信息;后者包含了被他人视为行动者征兆表现的各种行动,并假设行动展演的真实理由不同于以这种方式传达出来的信息。互动过程中的观众附和、配合表演者的印象管理,这也是观众自我印象管理的方式,以显示他们是表演的合格参与者。在面对面的互动情境中,一方面,共同在场者的行为具有“约定性特征”[5]2,若要沟通行为转化为道德行为,他人必须不加怀疑地接纳个体并给予适当的回应,这种约定性的承诺表明,面对面的互动参与者之间必须保持“相敬如宾”的仪式性姿态,即个体呈现的印象蕴含着具有道德特征的各种宣称和承诺。另一方面,个体通过操控印象管理和情境定义来实现支配他人行为的意图,有时个体会以缜密算计的方式向在场的他人呈现某种预想的自我。个体甚至未能意识到其审慎的算计行为,因为它可能是社会地位、传统习惯或角色要求使然。因此,行动者既表现得文质彬彬、礼让谦和,又工于心计、老谋深算。共同在场者会抑制其真实的需求和感受,形成互动的“临时协定”(modus vivendi)[5]9,从而达成情境定义的表面一致性,防止面对面互动的社会系统出现崩溃和失范。
戈夫曼将这种一致同意以避免对情境定义的公开冲突称作“运作共识”(working consensus)[5]10,它通常是基于君子协定。不同互动情境中运作共识的内容千差万别,但其一般形式是相同的。无意姿态、不合时宜的侵入、失态和闹剧等是表演崩溃的主要形式,也是尴尬和情境失调的来源,表演崩溃会对人格(自我)、互动和社会结构三个不同的层面产生作用。尤其是在个体层面,由于个体会将他的自我意识认同于特定的角色、机构或群体以及他的自我观念(此时他没有打破社会互动,也没有损害依赖这种互动的社会单元的威信),当产生互动崩溃时,可能会对围绕着他的人格而建立的自我观念产生怀疑。也就是说,行动者投射的“前台”与“真实的自我”之间可能出现矛盾与断裂,这也是实际呈现的自我与理想状态的自我之间的矛盾。这些不一致导致的慌乱和尴尬被行动者感知之后又将进一步破坏和削弱由表演维持的现实,因为这些紧张的迹象是角色扮演者本身而非所扮演角色的表征,它迫使观众接受面具背后的形象。为了防止出现各种意外以及由此导致的尴尬,就需要互动的所有参与者具备某些属性,并为维持表演而运用相应的实践,包括防御性实践、保护性实践以及表演者对观众和局外人的圆滑给予适当的配合。戈夫曼用印象管理和自我呈现研究社会机构内发生的互动,它包含了前台、后台和剧班等概念,表演者之间相互配合在观众面前呈现出既定的情境定义,礼貌和得体的规则维持着互动伦理的假定,并使印象管理的各种技术得以可能。由这些特征和要素构成的框架体现了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面对面互动的基本特性。
拟剧论揭示了隐含在社会生活中的戏剧成分,但是,拟剧论仅是一种类比、修辞或策略。戈夫曼真正关心的是社会交往的结构,当社会生活中的人们彼此共同在场时,便呈现出这些实体性结构,该过程的关键性要素是维持一致的情境定义。剧场的角色表演固然不是真的,通常也不会产生真实的效果,但舞台表演中虚构的人物却采用了真实的互动技术,它与日常生活中人们为了维持他们真实的社会情境而采用的技术是一样的。因此,在剧场舞台上进行面对面互动的演员必须符合真实情境中的要求,他们必须表意性地维持共同的情境定义。
二、拟剧论的极端形式
拟剧论将社会世界看作一个剧场,社会行动者扮演着多重角色,他们创造自我形象、表达自我身份,并建构理想的自我。他人(观众)将面对面互动中的表意行为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行动者容易控制和操纵的;另一部分则是行动者无暇顾及或无法操控的,他人往往利用这种无法管控和约束的表意行为来检视和验证那些可管控行为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因此,人际沟通过程中表现出一种基本的非对称性,个体关注行为的可控方面,即给予的信息,而他人则同时关注给予的信息和流露的信息,并且通过后者来矫正前者的偏离度。但是,如果个体一旦意识到这种信息交换的非对称性,那么他可能会及时采取适当的举措,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对称性。在日常生活的面对面互动中,人人都试图利用各种机会捕捉那些尚未被观察对象意识到、未经修饰的行为表露。在互动场域里,人人都是精通各种舞台表演技艺的行家,而对方又竭力摆脱这种信息追捕并想方设法进行反控制。这是一场信息狩猎的游戏,一个充斥着隐瞒、发现、虚假显露和重新发现的无止境的循环。[5]8
在戈夫曼那里,自我并非衍生自其拥有者,而是来自个体展演行为的整个场景,观众通过特定的舞台设置与场景表演赋予某个展演的角色以自我,但是“这种自我是它得以展现的场景之产物,并不是其原因。因此,作为表演角色的自我,它不是具有特定位置的有机体”[5]252。而常识性的错误观念是将一个人的自我与他所表现出来的特征相等同,认为自我“寄宿于其所有者的身体之内,尤其是它的上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格特征的精神生物学之结点”[5]252。戈夫曼认为,个体及其身体“仅仅提供了挂钩,在它上面协作性的产品能够悬挂一段时间。而生产与维持自我的方式并不存在于挂钩之内”[5]253。事实上,这些方式通常固定在社会设置之中。也就是说,戈夫曼的自我并非如弗洛伊德的自我那样寄居于个体之内。自我的首要特征是社会或社会过程的产物。
综观其论述,戈夫曼区分了情境化自我和作为能动者的自我。在拟剧论中,关于作为能动者的自我,戈夫曼更多是从舞台表演的角度进行阐述,这种自我还可以从不同的维度进行细分,诸如道德性的自我和非道德性的自我,等等。拟剧论的许多批评者往往只关注非道德性维度,这主要体现在面对面互动过程中行动者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两面三刀,诸如此类。对他人的深度怀疑同时也导致自我的分裂与疏离,精神病人甚至还可能遭遇亲人与专家之间达成的共谋。[6]在这里,戈夫曼为我们惟妙惟肖地描绘了一幅现代性条件下个体主义的浮世绘:人人都在隐藏、掩饰自己,让别人琢磨不透,因此,每一张社会面具的背后是另一张面具,如此层层叠叠。这种自我的构型犹如俄罗斯套娃或西方人所说的“中国盒子”:一个自我紧紧套链着另一个自我。在日常生活中,这些面具时刻处于不断地生成、被抛弃或转换的过程。只要表演仍在持续,这些面具游戏就永无止境。倘若将这种拟剧论和自我观推向极致,那么不只是行动者的面具背后还有面具,而且在层层剥离完面具之后,这些个体/表演者甚至根本没有肉脸。或者说,在无穷尽的面具背后,脸已经成为了面具本身。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戈夫曼对现代“化妆舞会式”社会和人际互动模式进行着极其尖锐的批判。互动的主体是华丽而又空洞的面具,而不是人;面具已然成为更“真实”的自我,人难以获得深刻的日常体验。在这种极端的个体主义理论中,每一个作为行动者的个体都极其孤独,他们独自面对自己的他者。对此,戈夫曼生动地描述道:
无论扮演的角色是庄重肃穆的还是逍遥自在的,无论身份贵贱,扮演角色的个体都是忧心苦恼地倾注于其作品的孤独表演者。在诸多面具与角色背后,每一位表演者都呈现出孤寂的神情,一种赤裸的、未社会化的神情,一种专注的神情,这种神情表明他正秘密地卷入在艰难的、背叛性的任务之中。[5]235
因此,美国知名的社会理论家和文化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曾断言,戈夫曼的行动者不仅是个体性的,而且“他们的真正自我永远不能被实现”。[2]172拟剧论中自我的极端形式表现为它自行消解于角色扮演,面具之下的肉脸已荡然无存。个人成为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集或面具丛,并在这些角色和面具之林中片断地、间隙性地呈现着他的社会属性与自我。换句话说,现代生活中的个体并不具有完整的自我性,他们通过各种碎片权宜性地拼凑出特定时间与空间里需要的自我。“持久性的自我是个人感知的一种幻象,是常识与心理的一种虚构”[1]178,尽管这种自我由相对稳固的社会设置与关系支撑着。在探讨作为展演性角色的自我时,戈夫曼悬置了“是否存在真实的自我”这个问题。在戈夫曼看来,“有没有实质性的自我”“戴着面具的人究竟是谁”之类的本质主义问题并非关键所在,他更多讨论的是“自我呈现”,而不是“自我实现”。因此,在戈夫曼的行动者模式假定中,要弄清楚一个人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毫无意义。[7]653单个的、自然状态下的自我存在与互动状态下的社会存在并不一样,人不仅仅是作为个体而存在,更是作为社会角色而存在,行为产生于戏剧性的互动过程。在作为角色的自我之层次上,不管是阐述能动性还是强调场景,重要的是关系、表演和体验,而不是本质或主客体的任何一方。
三、对阶序格局的否定与底层抗争
美国左翼评论家和社会学家阿尔文·古尔德纳认为,戈夫曼的拟剧论呈现的现实缺乏一种“关于阶序的形而上学”。[4]379在他看来,拟剧表演和表象模糊了所有的文化等级及其高下之分,典雅与庸俗、高贵与低贱、真诚与欺诈、专业与外行等之间的固有差异不复存在了。这表明拟剧论既反对美国社会既存的阶序等级体系,也反对因这种固有的阶序等级而获得优势和支配地位的利益群体。由此,戈夫曼关于日常生活中的拟剧表演和印象管理的论述也获得了强烈的社会批判意味。对此,古尔德纳作了这样的精辟解读:
拟剧论模型反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该世界里,中产阶级不再相信努力工作是有用的,或者成功取决于勤勉专注。在这个新世界里,个人成就和回报大小、实际贡献与社会声望之间的关系存在一种强烈的非理性的感觉。这是身价不菲的好莱坞明星和股票市场的世界,他们的价格与其收益并没有多大关系。拟剧论标志着从旧有的以生产为中心的经济向新的以大众营销和宣传推广——包括自我营销——为中心的经济的转变。[4]381
拟剧论隐射出西方社会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变,它是对个体主义的实现困境作出的理论反应。拟剧论生动形象地展现了美国新中产阶级“白领”的社会价值观和阶级表征,同时也宣告了旧式资产阶级道德伦理的死亡。“呈现性自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因为科层制系统中的行动者时刻受到监控并根据他们的工作表现进行绩效评估,正是由于对外表的迷信导致了前所未有地强调印象管理。[8]这种科层制体系和商品化社会的自我呈现逐渐走向异化,也导致了目的与手段、实质与虚质之间颠倒的悖谬性后果。原本作为印象管理、保护真实自我之手段的自我呈现却成为目的本身,行动者必须竭尽全力维护他们所呈现的各种自我,甚至不惜以扭曲、压制真实的自我为代价。最终,虚假取代了真实,表演取代了生活,面具取代了脸面。更为甚者,这种展演性自我能够脱离其拥有者而获得自主的生命。
然而,古尔德纳将戈夫曼对阶序的拒斥理解为是规避社会分层和权力差异的结果。在古尔德纳看来,拟剧表演和印象管理是个体对既有权力设置进行调适的手段,它实际上起着维护和巩固既有社会秩序之功能。正因这种内生性的矛盾和张力,拟剧论丧失了其潜在的激进性和革命性。古尔德纳从宏观社会的视角对拟剧论进行了独到的解读,并将拟剧论的理解推进到新的高度,但他认为戈夫曼对社会等级的排斥是以忽略权力为代价的观点值得商榷。戈夫曼并没有完全忽略权力,他实际上是从资源(尤其是信息控制)的角度看待权力,并且正是对社会生活中以互动为导向的意向性(包含自我意识和算计过程)的关注使戈夫曼将权力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9]88此外,拟剧论的批判性也不仅仅表现为它对现实社会等级秩序的否定。古尔德纳迷恋常规政治中的权力,而且他对戈夫曼的解读过于强调拟剧论中互动操控、博弈和功利主义的色彩。作为左翼知识分子,古尔德纳寻求宏大的激进式社会变革,以期系统性地改变或颠覆社会和组织系统的结构。从这种立场出发,他批评戈夫曼理论的保守性,因为拟剧论中的行动者人人自危,只求在现有的体制下明哲保身,无意于尝试制度性的颠覆行动,这种批评确实不无道理。但是,个体的反抗并不一定是武装革命和暴力战争,它也可以是日常生活中细微的、非正式的和隐蔽的抵制与反叛。无权群体的日常反抗形式可以是消极不服从、暗中破坏、逃避和欺骗等。在公开顺从掩护下的反抗中,对象征性秩序的遵从和认可是为了使实际遵从最小化。这种日常而琐碎的反抗形式远非微不足道,相反,它们体现了“在强制背景下进行日常的经济与政治斗争的真正基础”[10]355。而且,此类反抗很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社会变革与文化变迁。在这方面,戈夫曼本人亦是明证。他对美国精神病院和住院治疗制度的批评推动了西方精神病医疗的“去制度化”运动,最终促成国家层面的结构性变革。
四、全控机构中的自我救赎
归根结底,拟剧论仅是一种社会分析工具,它并非现实本身,更无法取代现实。戈夫曼的理论关怀并不在于舞台和表演,而是社会结构。一方面,戈夫曼警惕全控机构对自我进行的极端羞辱和攻击;另一方面,他提醒人们,个体对社会机构的完全投入将导致自我的沦丧,这在现代科层制体系下表现得尤为明显。情境化自我的观念表明,作为个人的感受来自被卷入其中的更广泛的社会单元。如果没有所属物作为支撑,人们就无法形成稳定的自我。然而,“对任何社会单元的彻底投入和依附则意味着某种无自我性”。[6]320拟剧论表明,互动秩序的建立不是基于完全真诚的动机,它并不反映普遍的价值体系。秩序的建立是以压制个体内心的真实情感作为代价的。在以此建构的互动秩序中,自我是被压抑的,它无法在日常生活中自由地进行表达。自我是未充分完成的,它是一个社会化过程。戈夫曼关于污名以及精神病院之类的全控机构的研究,都可以被视为是对这种禁锢性自我的进一步揭示。
病人在进入精神病院之后,其自我形象开始不断地遭到攻击,承认自己是“不正常”的是回归“正常”的必要前提。在《框架分析》中,戈夫曼再次回到《精神病院》中曾经探讨的这个主题,他将个体的某种经验称为“负感经验”或“消极体验”,即主体失去对情境、信息以及关系的控制,并经受自我暴露和新关系的重塑。[11]这种经验不仅存在于类似精神病院的强制性情境中,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同样会不同程度地遭遇这种经历。人们已经看到,当角色理论和情境化的自我走向极致时,其尽头是一个灰暗、压抑和虚无的世界。当然,人们在讨论戈夫曼的社会学思想时,不应该过于强调冷漠无情、自私自利的舞台表演技术,拟剧论并不乏道德性和仪式感,但就本文所要探讨的社会批判性意味而言,这种道德性反而削弱了它的力度。如果人们看到拟剧论中作为行动者的能动性,就能够发现戈夫曼并不是一位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在拟剧论中,戈夫曼强调人是反思性的存在者,“能够监控他们的行动,因此能够控制他们周围的环境”。[12]127尽管作为个人的身份感通常存在于缝隙之中,但是人们自我性的感受产生自抵制这种拉力的各种细微的方式。[6]也就是说,个体虽然处于情境的偶然性与社会结构的必然性之中,但反抗仍是自我的基本构成。即使在全控机构中,个体仍然能够进行各种形式的抵抗与自我保护。
戈夫曼探讨了精神病院里个体的各种应对策略,其中一种是建构“伪自我”,以过滤和防御对真正自我的攻击;另一种保护自我的方式是创造“隐秘生活”,[6]171这也是主体对压迫性情境的应对策略。由此,管理人员与精神病人之间形成新的互动形式,它是自主和自发的,并最终产生新的社会秩序。在这里,戈夫曼描述了个体在遭遇强大的非人化的制度时的命运,并探讨主动干预世界动态的自我。通过这种抗争形式,全控机构中的个体得以抵制异质性制度的肆意侵入与干扰。因此,在戈夫曼那里,自我从未完全被社会框架化,在某些情境中,个体会积极地抵制被贬抑的自我之认同。个体一旦意识到在剥离自我支撑物的环境里难以继续坚持公民社会中的自我,他会暂时将自我撤离,从而免受自我被彻底征服而产生的痛楚与羞辱。由此,底层的社会行动者以各种公共或私人的方式维持着积极的自我感。
五、商品化世界中人的境况之剖析
戈夫曼展示了日益原子化和商品化世界中个体的生存遭际。在消费社会里,商品的逻辑将所有功能和需求具体化为利益话语,而且被戏剧化,即被呈现、编排为可消费的形象和符号。[13]197现代社会的无深度感前所未有地凸显出外表和感官的重要性,在符号和形象之丰沛、精致以及奢华的表象下则是结构性的匮乏、空洞与做作。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其实并无多少具有实质性差异的选择,仅由不同的风格支撑着自由选择的假象。通过肉体的规训和灵魂的科层制化过程,个体不由自主地戴上各类行为的面具,在既定的场合表现出同质性的行为。拟剧表演取消了真实与想象之间的差异,使现实消融、坍塌在各种表征之中。在这里,戈夫曼事实上描述了拟像与仿真社会的雏形,即在米歇尔·福柯宣布主体死亡和让·鲍德里亚提出仿真概念之前,戈夫曼已表明自我的呈现是一种拟像,他更加栩栩如生地向人们展示了社会生活中的模拟/扮演过程。[14]320同时,戈夫曼对自我的分析抨击了西方社会的个体主义,揭示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内在紧张。戈夫曼对弥漫式专制体制的批判,是以民主社会中个体尊严的名义进行的,[15]355尤其是精神病人被如同物体般加以对待,精神病院和监狱等全控机构成为现代专制体制的集中体现。从这种意义上讲,戈夫曼社会学是一种社会诊断学。
拟剧论也是研究社会心理学的重要分析工具。由于强调印象管理、情景定义和相互合作(“运作共识”),并关注责任与道德,戈夫曼对自我的拟剧分析为阐释人们如何感知和理解他人的行为(即归因判断)提供了新的研究框架。[16]通过对自我的社会性生产、呈现和结构的精巧剖析,戈夫曼实现了对现代性条件下的个体与制度的批判。作为表演者的个体,他是“过于人性”的存在,这体现出戈夫曼的人性观以及对商品化世界里人的境况的深刻思索。正如约翰·洛弗兰德所说,戈夫曼早期的研究“可被视为寻找人之所以为人的条件”,这些研究详尽透彻地刻画了生活在当下世界的个体之各种经验特性,它们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存在主义的社会学”。[17]48一言以蔽之,拟剧论呈现的多重自我既是对现代性条件下的自我状态和人性图景的详细描绘和剖析,也是对它的深刻反思和批判。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拟剧论和自我分析成为戈夫曼批判现代社会的切入视角。
综上所述,欧文·戈夫曼对拟剧论和自我的详尽论述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剖析与批判。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的序言中明确地指出,该书是作为“某种指导手册”,旨在详细阐述一种可用于研究社会生活的社会学视角。“人生如戏”的隐喻早已是老生常谈,对此,戈夫曼毫不讳言。但他意在提出一种能够运用于任何具体社会设置(无论是家庭的、工业的或商业的)的解释性框架,这种视角便是戏剧表演,其原理源自舞台表演艺术。戈夫曼关于自我呈现、尴尬等的研究反映了艾森豪威尔时代冷战思维的多疑、猜忌以及都市中产阶级不断增长的社会怨恨。[18]戈夫曼提醒读者在他们身处的社会结构中存在深刻的紧张和荒谬;但同时他似乎也相信,美国社会有能力遏制各种社会问题。
戈夫曼的社会批判与他自身的性格以及他在美国社会学圈中的边缘地位可能存在一定关联。一方面由于他的犹太人身份,另一方面当时关于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的研究占据着主流的位置,微观的面对面互动研究似乎难登“大雅之堂”。戈夫曼直到60岁(1982年)才当选为美国社会学协会的主席,也正是在这一年,戈夫曼溘然长逝。最后应该指出的是,作为社会分析范式的拟剧论是一种理论工具(戈夫曼认为其他四种分析范式分别为技术的、政治的、结构的和文化的),是为了理解现实世界而临时搭建的“脚手架”。这种脚手架“是为了建造其他事物,在它被竖起来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它将被拆卸”。[5]254然而,正是通过拟剧论,戈夫曼对现代性条件下的人及其生存境遇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和冷峻严厉的批判。而自我既是这种批判的具体对象,同时也是它必不可缺的重要载体。
[1] Thomas Miller. Goffman, Positivism and the Self.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1986,16(2).
[2] (美)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M].贾春增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3] (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M]. 邱泽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4] Alvin Gouldner.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5] 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Y.: Anchor, 1959.
[6] Erving Goffman.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1961.
[7] (美)刘易斯·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M]. 石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8] John Welsh.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capitalist Society: Bureaucratic Visibility as a Social Source of Impression Management. Humanity and Society, 1984,8(3).
[9] Mary Rogers. Goffman on Power.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1977,12(4).
[10] (美)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M]. 郑广怀,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11] Erving Goffman.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12] (美)帕特里克·贝尔特,(葡)菲利佩·卡雷拉·达·席尔瓦.二十世纪以来的社会理论[M].瞿铁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13]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 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4] Heinz-Günter Vester. Erving Goffman's Sociology as a Semiotics of Postmodern Culture. In Gary Alan Fine & Gregory Smith eds., Erving Goffman, Vol. 4. Sage publications, 2000.
[15] (法)达尼洛·马尔图切利.现代性社会学:二十世纪的历程[M].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7.
[16] Mary Babcock. The Dramaturgic Perspective: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Person Perception. European Journal Social Psychology, 1989,19(4).
[17] John Lofland. Early Goffman: Style, Structure, Substance, Soul. In J. Ditton eds., The View from Goffman. London: Macmillan, 1980.
[18] Charles Lemert. Goffman. In C. Lemert and A. Branaman ed. The Goffman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