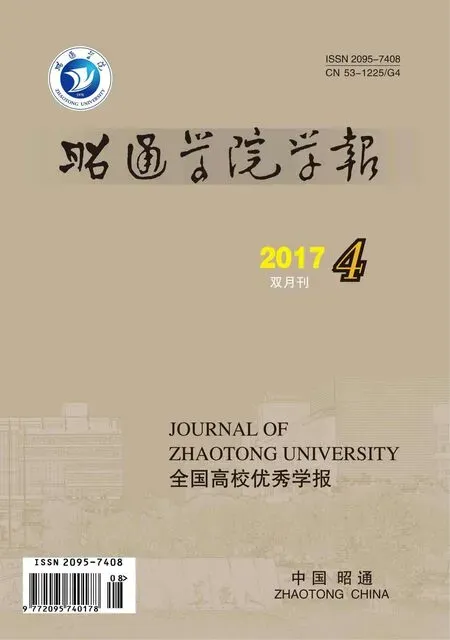《棋王》:不能承受的历史之重
党渊博
(新疆师范大学 文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文学研究
《棋王》:不能承受的历史之重
党渊博
(新疆师范大学 文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从《棋王》中的两个主题“吃”和“棋”出发,结合作家及其所处时代等主客观因素进行解读,最终发现,《棋王》是作家成功放大了的个人记忆和时代印记。只不过恰逢其时,其个人记忆被放大、上升为民族寻根的高度,成为不能承受的历史之重。
物质性; 世俗化; 历史之重
作家阿城的短篇小说《棋王》于1984年发表以来,众多评论者都是从寻找民族生存之根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并认为其一部经典的“寻根文学”作品,很少从文本中成功构建起王一生这一经典形象的两个最主要的事物“吃”和“棋”为基础进行分析,而汪曾祺则清醒地认为“《棋王》写的是什么?我以为写的就是关于吃和下棋的故事”。[1]再结合作家阿城的生平和所处时代,便会发现“吃”和“棋”清晰而明了地反映了作者阿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所做出的极为理智而无奈的选择。以“吃”和“棋”构建起来的“棋王”形象,是作者成功放大了的个人记忆和时代印记。只不过恰逢其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的时代和文学要求,个人的记忆被放大,进一步上升到了民族寻根的高度,成为不能承受的历史之重。
一、“吃”:物质性的追求
小说虽然将“棋王”作为题目,但作者却没有急于写主人公的棋艺如何,而是通过对“吃”的描写抓人眼球。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很少有作品是专门描写“吃”的,因为在作家的观念里,专门写“吃”,是一件十分不雅致的事,难登文学的大雅之堂,先贤孟子都曾有“君子远庖厨”之说。但阿城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吃认作是人生最大的事进行书写。
小说中对主人公王一生在火车上吃饭的动作,进行了细致而又精彩地描写:“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 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 ……他对吃是虔诚的,而且很精细。”[2]27由此可见,王一生对“吃”这件事是多么认真而又虔诚,在他的意识里存在着一种极其彻底的朴素唯物主义,即吃饱是福。“吃”作为人类生存的基础,即使在“文革”期间,一切让位于政治的环境中,“吃”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也始终且必须放在首位。所以,“吃”对当时的主人公王一生和作者本人来说,是为了维持最基本生存需要,不可或缺也不能或缺。因此,王一生对“饿”与“馋”作了极其严格地划分,对菜里的油、书、电影等超出他生存要求的东西并不在意,只求通过“吃”来求得“活”。
与其他作家一直以来不屑于描写的“吃”不同,阿城在其文章中却大费笔墨对其进行描写,似乎有意凸显王一生身上的烟火气、世俗气,并期望以此来解救当时政治高压下被禁锢的思想。阿城曾道:“我是非常实际的人、非常入世的人,没有出世的时候”。[3]“《棋王》可能很有趣。一个普通人的故事能有趣,很不容易。我于是是冒了一个想法,怀一种俗念,即赚些稿费,买烟来吸。……等我写多了,用那稿费搞一个冰棍基金会,让孩子们在伏天都能吃一点凉东西,消一身细汗”。[4]阿城后来在很多场合都喜欢渲染其自身及作品的世俗性,说其写作并没有什么远大的意图,但却通过其文本,极其生动而准确地还原了人通过“吃”,从而对“生”的执着追求。由此可以推断,作家阿城通过对“吃”生动、刻骨而又真实的描写,展示了作者本人在当年极为特殊的饥饿年代中所滋生的一种深刻个人记忆,并将其生动表现和有意扩大,从而诠释了其自然朴素的生存意识,即民以食为天。
二、“棋”:世俗化的追求
小说通过对主人公王一生“吃”的细致描写,既表现了个体为了生存对物质的迫切关注,更生动表现了对“生”的执着追求。但小说以 《棋王》命名,可见“棋”乃文中关键意象。小说中王一生的第一句话就是“下棋吗?”[2]21由此便奠定了“棋”在其生命进程中的核心地位。
“棋”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其具有极强的竞技性质,以输赢论英雄。有一个极为耐人寻味的场景,当时王一生偶遇一个棋艺高超的老头儿,回忆道:“老头儿说,棋运不可悖,但每局的势要自己造。棋运和势既有,那可就无所不为了……我说,可这下棋,千变万化,怎么才能准赢呢?”[2]31其提问中的一个“准”字,生动表现了其一开始便毫不掩饰地对胜利的急切渴望。而当棋赛结束后,王一生说:“妈,儿今天 ……妈—— ”。[2]61从其话语中,能领会到其喜欢下棋并逐渐沉迷其中的原因,王一生从一开始便清晰明了下棋的胜负特征本身具有极强的竞技特性,而这种特性所带有的世俗功利性,使得王一生能通过赢棋的方式来带给母亲荣耀,从而进一步获得自我满足、认同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对于王一生来说,在“文革”那样的社会环境下,只能通过类似下棋的方式才可能完成对自我的确认。王一生曾说:“何以解不痛快?唯有象棋”。[2]26可见,王一生在特殊年代找到了一种实现自我认同的合理方式。等到了九局连环车轮大战时,王一生的“棋王”荣耀到达顶峰:“棋开始了。 上千人不再出声。 ……再没人动一下 ……”。[2]57而王一生则“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2]60以一对九的棋赛中,好似一人面对千军万马,场面十分宏大。然而,面对这种场景时,王一生一开始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兴奋感。以至于事情结束之后,王一生没有继续走上其辉煌灿烂的“人生巅峰”,而是继续过他的普通生活,波澜不惊、风平浪静。
在“文革”那样的环境下,“下棋”作为一项充满胜负性质的竞技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因为王一生出众的棋艺,让其通过这项活动实现了自我价值的确认;但在大环境的束缚下,作为无权、无势的平民,却无法真正获得实现人生价值的公平机会。因此,“下棋”对王一生来说,是一个极其无奈的选择。
三、寻根的本质:扩大的记忆
对“吃”和“棋”生动而深刻地描写,反映了作家阿城在大环境下的一种生存智慧,既能生存下去,又不至于对人生彻底绝望。因为适应了当时的思想潮流,《棋王》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作是寻根文学的优秀代表,但究其实质,则是个人记忆的无限扩大化而已。
《棋王》以主人公王一生学棋的经历,展示了棋王的成长,充满了武侠小说的色彩,尤其是对下棋经过的描写上,好像充满了道家的智慧。但透过表象,对整部小说进行整体研究,则会发现,《棋王》实质上所写的是作为知青的这一代人的记忆。作者阿城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自小生活条件优渥。但在中学尚未毕业时,遭遇“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使其度过了较长时间的艰辛生活。除了时常食不果腹,面临生存的极大威胁;其才智也难以施展,面临深重的精神折磨。因此,作家才对“吃”,如此重视;对“棋”如此执着。“文革”时期,需要“上山下乡”的都是处于青春期的知识青年,年轻、活力、斗志昂扬,渴望建功立业。但当他们发现所有上升的路途几乎都被阻断时,便产生了极大的焦虑。因此,当时他们最大的焦虑就来源于能否被政治上认可,但被认可的条件由家庭出身决定,因此,出身的限制使得阿城难以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所接受,同时也导致其难以排解的焦虑,如难以得到父亲认同般无助而焦虑。因而,《棋王》的书写,其实是对一代人精神创伤的书写,是隐藏在作者内心深处的强烈焦虑的表现,是其知青记忆的无限扩大化。
《棋王》之所以被认作“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只不过是一桩历史的偶然事件,如福柯所言,历史分析会将偶然事件划分成必然,从而将本没有联系的诸多事件联系在一起,即“如何求取两个孤立事件的关联?如何建立其因果关系?它们具有什么样的连续性及整体意义?”[5]文学也如此,《棋王》于1984年发表,恰逢当时改革开放开始,大量的西方思想、观念、文学理论等涌进中国,使得当时众多文艺界人士对中国的民族传统进行重新思考。在1985年,韩少功发表的近似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写道:“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6]以此理论为指导,作家开始进行与之相关的创作,如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等一系列文章,因此文学界便将他们称为“寻根派”,一系列相关作品称为“寻根文学”。而《棋王》一经推出,便在当时文坛引起极大轰动和诸多评论,如从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态度出发,认为“王一生的棋道并不仅仅是道家文化的体现,其中又含着现代的精神,是一种东西方精神互相交融渗透而成的道”。[7]或认为“阿城的小说《棋王》蕴含的文化意蕴不仅仅表现在儒道互渗的统一体中,同时在潜层次上还表现为一种世俗文化中的游侠的精神,一种与传统道德规范相冲突的精神,一种与寻根文学相联系的精神”。[8]而这些评价主要结合当时“寻根文学”的潮流,认为此小说的主题与当时所倡导的“寻根文学”的主旨不谋而合,便将其认作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
虽然《棋王》一发表就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而被掀起广泛讨论,但本文以《棋王》中的两个主题“吃”和“棋”出发,并结合作家及其所处时代等主客观因素进行解读,最终发现,《棋王》并没有特殊的文化寻根意味和诉求,只是作家对个人、特殊时代记忆的扩大化。只不过恰逢其时,从而上升到民族寻根的高度,成为不能承受的历史之重。
[1]汪曾祺. 汪曾祺说阿城小说《棋王》[J]. 名作欣赏,2005(1):1-2+34.
[2]阿 城. 阿城精选集[M].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3]施叔青. 与《棋王》作者阿城的对话. 文艺理论研究[J]. 1987(2):47—53.
[4]阿 城. 一些话[J]. 中篇小说选刊,1984(6).
[5][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的考掘[M]. 王德威 译,台湾:麦田出版,1993:69-70.
[6]韩少功. 文学的“根”[J]. 作家,1985(4):2-3.
[7]胡河清. 论阿城、马原、张炜:道家文化智慧的沿革[J]. 文学评论,1989(2):71-80.
[8]李 蕾. 浅谈《棋王》中的游侠精神[J].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1):71-73.
King of Chinese Chess: The Unbearable Weight of History
DANG Yuan-bo
(College of Liberal Arts,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Wulumuqi 830017,China)
A Cheng’s the King of Chinese Ches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novel in Chinese Literature, whose used to be considered as a representative novel of the Root Seek Literature and was defined from that point of view. Now, this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the protagonist of eating and chess, the paper appeals that the novel is based on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memories of A Cheng and make them enlargement.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Root Seek Literature.
eating; chess; personal experiences
I207.42
A
2095-7408(2017)04-0092-03
2017-05-03
党渊博(1989- ),女,陕西渭南人,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