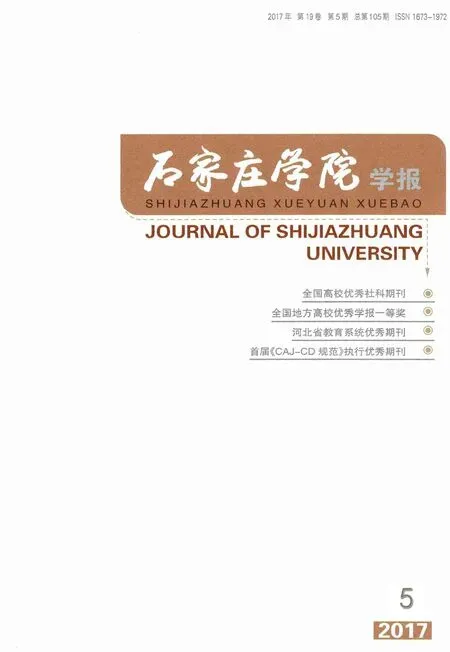《伤逝》研究90年综述
朱郁文
(佛山市艺术创作院 文化与文艺理论研究部,广东 佛山 528000)
《伤逝》研究90年综述
朱郁文
(佛山市艺术创作院 文化与文艺理论研究部,广东 佛山 528000)
鲁迅的小说《伤逝》诞生90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批评家特别的关注,对它的解读、评价和争议一直存在。以1930年代中期和1980年代中期为界,可将《伤逝》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评论数量虽少却个性鲜明;第二个阶段由于时代氛围与政治环境的影响,研究模式相对比较单一;而第三阶段在政治环境松动与西方理论思潮输入双重因素助推下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多元化局面。三个阶段各有特色,充分体现了社会思潮、政治动向和个人主观动机等因素对文学批评的复杂影响。
鲁迅;《伤逝》研究;90年
任何一个经典文本的经典性,就在于它有着无限丰富的可解读与可阐释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讲,鲁迅先生的小说《伤逝》的经典性应该是无须质疑的。它自1925年10月诞生之日起,至今已经历90余年时光之流的淘洗。后人对它的阅读、欣赏、评价和解读在年复一年地进行,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不断更新。当然,其中不乏争议。纵览这些研究文字,我们可以看出,文学批评这一行为并非单纯地对文学文本进行解读,其背后隐藏着社会思潮、政治动向、个人主观动机等各种因素的作用。
一、个性鲜明的早期评论 (1920年代中期-1930年代中期)
笔者所看到的最早评论《伤逝》的文章是李荐侬的《读〈伤逝〉的共鸣》①李荐侬《读〈伤逝〉的共鸣》原载于1926年9月27、28日《世界日报副刊》。,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篇文章剥离时代背景和人物性格方面的因素,从人类共有的命运来分析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认为“这不但是他们俩的悲哀,实在是全人类的苦痛”。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印证:首先,“面包问题”即经济状况影响“纯洁的爱情”;其次,爱情因年龄和经历而变,开始比较冲动和盲目,而后就比较现实,人往往弄不清楚爱情;再者,爱情不能跟同居或结婚混为一谈。[1]125-127
茅盾写于1927年的《鲁迅论》是极为有名的一篇作家论。他在1920-1930年代写了数篇作家论,对后来的文学批评以及作家论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尽管有论者指出,其30年代的作家论中存在着“左倾机械论”“贴政治标签”等缺点②参见常江虹《论人是否知己?——评茅盾左翼思潮时期的八篇“作家论”》,载《惠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周兴华《茅盾作家论的盲视之域》,载《南方文坛》2005年第1期;谢丽《从〈鲁迅论〉到〈落花生论〉——论左翼文艺思潮对茅盾作家论的影响》,载《山东文学》2008年第8期。,但《鲁迅论》③茅盾《鲁迅论》原载于1927年11月10日版《小说月报》18卷11号,署名方璧。显露出论者独到的审美眼光和敏锐的艺术感知力。文章在谈到《伤逝》时,首先指出主人公的幻灭主要原因是经济压迫,而后从主人公的性格入手,认为“涓生是一个神经质的狷介冷僻的青年,而他的对手子君也似乎是一个忧悒性的女子”,认为《伤逝》的意义“或者是在说明一个脆弱的灵魂(子君)于苦闷和绝望的挣扎之后死于无爱的人们的面前”,文章对子君表达了更多的喜爱和同情,而对涓生给予了委婉的批评,认为他并不了解子君的“寂寞”和“委婉的悲哀的女性的心理”。[1]125-12720年代还有一篇谈及《伤逝》的文章,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率先对《伤逝》提出批评,认为它是“一篇平凡的作品”,“象打花拳的拳师,手脚虽然动得花巧,而没有一记真实的工夫”,“是在玩弄几个名词的概念”。文章认为,小说写得逼真的地方是“因生活上经济的压迫而在爱情上有了变化,和以后的逐渐变动”以及“细细地”写出了“种种生活上的琐事”。第二,对鲁迅采用男主人公第一人称的叙事策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不是一种贤明的处置”,而应该“用客观的叙述加上心理解剖,用一种冷冷的态度”,用涓生的自述是“很不相称”“极不和协”的。[1]459后一点显示出叙事学分析的意味。
1930年代,张文焯《子君和涓生——子君走后的涓生》①张文焯《子君和涓生——子君走后的涓生》原载于1935年5月25日《国文学会特刊》第3期。是最早鲜明地站在女性即子君的立场来评论《伤逝》的,他的文章从女性的社会地位、子君的“无畏”和“毫无依赖习性”、涓生的自私自利和“不肯负责”等方面来分析两位主人公的恋爱关系,对涓生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判。[1]1107-1110初步的女性主义色彩在文中得到彰显。写于1935年出版于1936年的《鲁迅批判》一书,使年轻的李长之颇负盛名。该书作为唯一经过鲁迅批阅的批评鲁迅的专著,历来受到鲁迅研究专家和广大读者的青睐。该书提到,《伤逝》是“更纯粹的抒情文字”,“可以代表鲁迅的一切抒情的制作”。并将涓生与鲁迅等同,认为“这篇托名为涓生的手记,就是作者自己,因为,那个性,是明确的鲁迅的个性故。他一种多疑、孤傲、倔强和深文周纳的本色,表现于字里行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小说中多次出现此类的话,表明了“鲁迅的中心思想”,即“生物学的人生观”;涓生心理上的矛盾和困惑也流露出“鲁迅在情绪上和理智上的冲突”。李长之还认为,《伤逝》“有对于女性最深切的了解”,即“女性在理智上,意志上的脆弱”。[3]83-90
以上五篇对《伤逝》的评论文字,笔者认为都有着极其鲜明的个性和独到之处,就影响而言,当然是茅盾的《鲁迅论》和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无人能比。不过在笔者看来,它们在价值上并无高下之分,此五文都属于印象式批评,里面渗透着批评主体强烈的审美意识和独立品格,在感性的情感体验之中不乏理性的深度。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些文章依然熠熠生辉,乏有超越者。
二、时代氛围与政治环境决定下的单一批评模式(1930年代中期-1970年代末)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国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文艺界状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学批评也较多地带上了时代的烙印。身为共产党员的何干之以“须旅”之名发表的《一出悲壮剧——一九二五年的〈伤逝〉》②何干之《一出悲壮剧——一九二五年的〈伤逝〉》原载于萧军编《鲁迅研究丛刊》,鲁迅文化出版社1941年版。,非常明显地带有阶级论色彩。文章站在统观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各阶层和阶级变化的高度,大而化之地分析《伤逝》中的悲剧。文章认为,封建家庭长大的子君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炸弹”——“自由恋爱”——的惊醒,无畏地走出旧家庭,她的勇敢“表现了中国‘现代式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层’的急进的气质”。她的理想是“爱”,她认为“爱”便是一切,是生活的整个内容。这“委实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阶层的特质:资产阶级没有她这样勇敢,而无产阶级则不似她这般架空”。相对于子君身上残留的旧思想的束缚,涓生“具有着比子君优胜的品质”,“具有比子君更进一步的觉悟,他明白当时社会生活的客观的局限性,而对此不乏精神上的准备”。他经过痛楚的路程,“肯定了生活的第一义”并“生发着新的理想”,而子君“已经成为无勇的庸俗的人了”,于是乎涓生“便只能奋身孤往了”。文章还认为,“鲁迅现实地创造了这个悲壮剧”,“子君表现了‘悲’的一面,涓生表现了‘壮’的一面”,“再没有谁比鲁迅更深刻地体验了当时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阶层的苦闷了的。这涓生的苦闷,和子君的灭亡,一样是中国现代式小资产阶级知识阶层参加革命以前的真实的纪程碑……”[4]何干之这篇文章首先明显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知识阶层的矛盾和局限性;其次明显地站在涓生的立场,批判了子君的落后和软弱性。在笔者看来,在《伤逝》研究历史上,它既开了阶级论分析之先河,又开了男性中心主义批评之先河,尽管后人较少提到它,但其在《伤逝》批评史上的意义不应忽视。在另外一本小书《鲁迅思想研究》中,何干之从女性经济权的角度分析,认为子君的爱是勇敢的、无畏的,但这是无物质保障的。她不附丽于父亲而逃出家庭,但又附丽于丈夫,结果是回去、灭亡。所以,“经济权不革命,女子的解放是没有可靠的保障的”[5]141。作者的这个观点已经表露出中国的妇女解放反父权不反男权的思想,这是很难得的。欧阳凡海《鲁迅的书》③欧阳凡海《鲁迅的书》,文献出版社1942年版。“《彷徨》中的最后四篇小说”一节中,将《伤逝》与当时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蒋光慈等人的恋爱小说作比较,认为只有鲁迅的《伤逝》用“深沉的理性”对自由恋爱进行冷静反思、提出批判。文章依然站在批判子君的角度,认为她的灭亡只是为她自己的盲目、麻木和怯懦负责,为的是两个人不一同灭亡。[6]986-987默涵①默涵在1942年6月2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两个悲剧——读书杂记》一文。认为,鲁迅的《祝福》和《伤逝》写出了两个“伟大的悲剧”,一个是演出在农村,一个是演出在城市,两个悲剧的主角都是女性。在城市的子君在“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的口号下有了个性的自觉,要求自己的解放。她胜利了,但最终又失败了,原因是“经济的基石,并未变动”。“曾经给了她勇气与温暖的爱情,已被现实的磐石压得粉碎,而她却又找不到更新的理想来支持自己,她就只好使自己的心身随着这破碎的爱情一同破碎。”她的个人主义“完全被淹没在封建势力的大声的嘲笑中”。子君死了,但“这件事却告训了同行者和后来者,使她们去另寻更加宽阔的道路,而且是终于寻到了”。[6]1020-1021作者并没有明确这道路是什么,但是很明显,其时身在解放区的默涵像无数转变了的知识分子一样知道这条路,那就是加入到无产阶级大众的行列,在中共的领导下翻身做主人。京派作家李广田40年代写过一篇《鲁迅小说中的妇女问题》②李广田《鲁迅小说中的妇女问题》原载于 1946年10月1日《文艺复兴》第2卷第3期。,认为子君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反动思想、假道学、流氓和土豪劣绅,“乃是生活问题,而生活问题乃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妇女解放运动和整个的政治运动——目前是民主运动——是不可分的。真正的妇女解放之成功,必须是真正的政治民主化之后,而政治民主运动中也必须同时有妇女运动这一支流。”[5]277-281文章认为,在其时的环境中,子君只有和人民大众合成一体,争取应有的一切权利,在整个民主运动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此外,巴淑的《恋爱与结婚》③巴淑《恋爱与结婚——再读〈伤逝〉》原载于1948年1月12日《大公报》。从理想与现实关系的角度,认为涓生和子君的悲剧“不能责备子君,也无理由责备涓生,应该责备的是不太合理的经济环境”[5]598-599。
1950年代直至“文革”结束,在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中,文艺界也缺少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局面,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立场和作家身份的影响。在此种情况下,《伤逝》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大同小异,批评者多从反映论、认识论的角度剖析《伤逝》,往往从内外两方面来分析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外因无外乎社会各种反动势力的压迫和经济打击,内因无外乎主人公性格弱点和阶级局限性,并且几乎都把更多的责任推给子君,对涓生则相对宽容,认为他比子君更觉醒。在此基础上,批评者得出结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丑恶的、吃人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个人的解放必须同全体人民的解放运动结合起来,知识分子应该投身于更广大的社会斗争中去。论者对主人公的态度往往既同情又批判。④参见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呐喊〉与〈彷徨〉研究之一》,出自汪晖、钱理群等著《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论鲁迅(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7页,原载《人民文学》1954年第11期;冯雪峰《鲁迅的文学道路·伤逝》,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3-199页,原载《新中国妇女》1955年第12号;王西彦《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1956年)、《关于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1956年)、《诗篇〈伤逝〉》(1956年)、《有关鲁迅初期小说作品的两三问题》(1950-1956)等文收入《第一块基石》,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高瞻《试谈“伤逝”》,载《人民文学》1956年第12期;王士菁《鲁迅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第149-152页。这种思路在“十七年”后期尤其是“文革”中发展到极端,即认为鲁迅在《伤逝》中对个性解放思想作了彻底批判,鲁迅的思想开始由进化论转向历史唯物主义,并向共产主义道路迈进。⑤详见吴中杰、高云著《论鲁迅的小说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14-15、81-86页。本书写于1960年代初。值得一提的是,作家兼出版家、鲁迅的同时代人曹聚仁50年代在香港出过一本《鲁迅评传》,以其行文中立客观、内容翔实、能真实地逼近鲁迅而大受关注。该书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但在论及《伤逝》时并无独到创新之处,似有照搬茅盾《鲁迅论》之嫌疑。⑥详见曹聚仁著《鲁迅评传》,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66-267页。
“文革”结束以后,文艺界有所松动,但仍在相当程度上延续着此前的批评模式。对《伤逝》的评论并无本质上的变化,仍然强调鲁迅对个性主义的怀疑和否定,强调资产阶级的个性自由思想斗不过封建思想和宗法制度,强调个性解放、婚姻自由与社会解放的一致性以及知识分子与群众结合的必要性。⑦如林志浩《“五四”节前读〈伤逝〉》,载《工人日报》1979年5月4日第4版;李希凡《幻想·破灭·求生——论〈伤逝〉的时代意义和子君的悲剧形象》,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严家炎《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收入《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陈鸣树《论〈伤逝〉的主题思想》收入《鲁迅的思想和艺术》,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8-236页;林志浩《鲁迅传》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156-157页;唐弢《妇女解放的道路》收入《鲁迅研究》(第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30页;王瑶《谈〈呐喊〉与〈彷徨〉》收入《鲁迅作品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115页;杨义《鲁迅小说综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60、194-195页;刘扬烈《鲁迅小说三题》收入《鲁迅研究》(第1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216页。所不同的是,言辞上已不再像此前那样过激和偏颇,对主人公的态度也有所缓和。有的论者如李希凡、陈鸣树等对此前过多责怪子君的论点有所纠正。由于政治环境的决定性因素,“十七年”和“文革”十年的批评思路和模式在新时期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旧发挥着作用,只是影响和威力在渐渐减弱。时至今日,仍有论者坚持着这样的立场和观点。与此同时,不同的声音开始悄悄浮出冰面,尤其是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对《伤逝》的批评和研究渐成繁荣之势,各种不同的观点相继出现并发生碰撞。
三、政治环境松动与西方思潮输入下的百家争鸣局面(1980年代初-1990年代末)
(一)个性解放语境下的再讨论
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人对《伤逝》提出批评,支克坚从“人的文学”和个性主义思潮产生的意义出发,认为五四以后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否定了个性主义改造社会的可能性,否定了人的个性解放和发展,把人的问题简单化了,而鲁迅的《伤逝》正是这种简单化形成的标志。[8]康林从《伤逝》产生的时代背景着眼,通过与同时期其他作家的作品相比较,对此前有些论者刻意把鲁迅与其他作家区别开来、拔高鲁迅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伤逝》的出现和存在,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把自由恋爱的‘胜利’,小家庭的建立当作进一步探索的起点的作家绝不止鲁迅一人”。这样理解《伤逝》并不是要把它与同期同类作品完全等同起来,而是要“全面地把握它与社会思潮,与同类作品之间的这种广泛联系”[9]315-322。张永泉《〈伤逝〉与个性解放》一文,首先批评了此前诸多论述把《伤逝》的主题“拔高到‘批判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高度”的倾向,认为这“给鲁迅的作品招来不应有的灾难”。“灾难”之一就是贬低《伤逝》的价值,认为它否定了个性解放,把人的问题简单化,如前面提到的支克坚的文章。作者认为,《伤逝》并没有批判、否定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而是“要通过涓生和子君的悲剧,对广大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争取个性解放斗争的经验教训做一个总结,从而帮助他们从涓生和子君陷进的泥沼走出来”,把悲剧的责任无论推给子君还是涓生,甚或个性解放的欺骗,都是“脱离作品实际的主观臆断”。鲁迅没有批判主人公的个性解放思想,而是批判他们个性解放思想的不成熟、不彻底。[10]217-242同样,此前陈安湖的《论〈伤逝〉》①陈安湖《论〈伤逝〉》原载于《文艺研究》1981年第5期。一文也认为,鲁迅“并不是为了证明资产阶级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的理想和信念的破产,而恰恰是为了证明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存在着先天不足的情况,亟需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的思想武装,把他们引导到更完全、更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道路上来,引导到广阔的社会斗争中来,以便把中国的反封建的革命事业推向前进”[11]315-340。赵晓笛、冯奇的文章认为,此前出现的几种对《伤逝》主题的理解,即对个性解放思想的批判、简单化人的问题以及对此后的文学产生不良影响,不是批判而是肯定了个性解放,这说明对《伤逝》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文章认为,《伤逝》展示了两个方面的主题思想:一方面,“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社会对青年的迫害,从而肯定了个性解放思想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批判了子君和涓生的爱情至上主义、狭隘的自我中心意识、以及软弱的性格”。文章还联系时代背景,认为辛亥革命失败之后,鲁迅对个性解放思想开始“从乐观逐渐产生怀疑”。作者总结说:“鲁迅对个性解放思想是有批判的,但这批判不是简单的全面否定,而是在肯定它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的基础上,对其软弱性和狭隘性给予了恰当的批判。他是有肯定有否定,在肯定大方向的前提下,又否定了它的不足和局限。”[12]347-359不难看出,作者的观点相当折中。有论者从艺术形象和美学价值的角度,将子君同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茅盾《蚀》三部曲等作品中的“新女性”形象一起,看作是对现代文学女性形象的丰富和发展,她们的美学价值不容忽视。[13]334-350在80年代众多探讨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个人与众数关系的文章中,王富仁的观点对以上的研究具有矫正性的批判,他认为,《伤逝》《孤独者》等鲁迅作品的“基本价值尺度不是用‘社会群众’的思想眼光批判其中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站在‘孤立的个人’的思想立场上抨击整个社会的思想、批判‘群众’‘多数’的愚昧和落后”,“物质力量的缺乏必须用精神力量的充实来支持,群众基础的不足必须由个人意志的坚毅来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涓生和子君在没有被压垮之前身上所有的“傲视世俗封建思想势力的个性主义精神”无疑是值得高度赞扬的。[14]212这一观点颇具胡风提出的“主观战斗精神”之遗风,在一味强调“集体”“群众”“大我”的80年代和既往言论中,这不能不令人振奋。
(二)索隐式研究
在《伤逝》的研究当中,有一部分重考证的“索隐式”研究。研究者将《伤逝》与鲁迅的私人生活联系起来考察其主题及背后的意蕴。尽管鲁迅对这种思维方式曾明确给予了否定①鲁迅1926年底曾致信韦素园说:“我还听说一种传说,说《伤逝》是我自己的事,因为没有经验,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哈哈,做人真愈做愈难了。”见《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0页。,但仍有喜好探幽掘微之人,将《伤逝》与鲁迅的婚恋生活联系起来而津津乐道。虽然有些言论有哗众取宠、吸引眼球之嫌,但还是有部分文字不无道理。周作人曾就《伤逝》作过不同的表述,1953年他说:“‘伤逝’这篇小说大概全是写的空想,因为事实与人物我一点都找不出什么模型或依据。”[15]136可几年之后他又说:“《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借假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16]486不管有没有确凿的证据,周作人既然有影射兄弟失和的说法,一定有他自己的确信,同时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参考价值。将《伤逝》看作是对兄弟失和的影射意味着并不把《伤逝》看作一篇爱情小说。周楠本也认为,小说不过假借了爱情的形式,“这篇忏悔式的作品,并非宣泄和倾诉性爱的愁苦,它只是主人公因为过错产生罪恶感,因为前途渺茫感到惶惑,因之而引起内心的不宁和骚动,爱情小说的分子其实是很少的”[17]。涓生的“忏悔”里隐藏着鲁迅思想的变化和矛盾复杂的心理感受。同样是突破爱情小说的解读模式,赵敬立认为,《伤逝》主题是作者的“自我伤悼”,“涓生”与“子君”是作者的两个不同侧面的化身与变体,“鲁迅假借了恋爱的形式,对自我从思想到人生道路进行深刻而痛苦的反省、探索、总结与调整”,这也是鲁迅“彷徨期”心路历程艺术化的反映。[18]此文可看作是对周楠本观点的发展。21世纪初,谢菊的一篇《〈伤逝〉解读》,从小说的副标题、小说没有公开发表、周作人的回忆、“子君”这一名字等细节入手,认为鲁迅是“借助小说这种虚构的形式”,将兄弟失和这件事以及给自己带来的“内心深处难言的隐痛”表达出来。[19]该文算是时隔几十年之后对周作人说法的呼应。当然,这种观点得到了部分人的赞同,同时也引来了激烈的反驳。谢世洋就撰文对周作人和谢菊的观点表示否定,认为这有损《伤逝》的社会意义。他从鲁迅“全人”、小说“全篇”及写作背景三个方面进行论证,并对谢菊一文的论据一一加以反驳,以此证明《伤逝》“非凡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20]。
新时期以来,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鲁迅逐渐被拉下“神坛”返回“人间”,有研究者开始撇开不必要的忌讳,从私生活上来探讨《伤逝》与鲁迅或多或少的关联,或认为涓生和子君的恋爱有着鲁迅婚恋生活的影子,或认为鲁迅将对婚恋生活和自我人生的思考投注到了《伤逝》中。朱正在《鲁迅传略》②该书由作家出版社初版于1956年,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修订版。中用详细的文字来分析涓生和子君的恋爱过程及心理变化,以考证《伤逝》流露出的一些细节和情绪可能是鲁迅和许广平二人相恋的精神写照。殷国明从两性关系的角度认为,如果过多地注重作品的社会认识意义而忽视“鲁迅本身思想的变迁”,忽视鲁迅“面对两性关系所做的选择及其含义”,那会是一个很大的失误。“鲁迅与许广平的恋爱过程充满着心理冲突”,解读《伤逝》如果“不考虑鲁迅这段时期特殊的心理状态显然是不明智的”。③详见殷国明《〈伤逝〉:两性的冲突与和解——兼谈与〈娜拉走后怎样〉的关系》,宋庆龄基金会、西北大学合编《鲁迅研究年刊》(1990年号),中国和平出版社1990年版。作者显然认为《伤逝》的创作与鲁、许二人的恋爱有着内在的联系。周棉的文章独辟蹊径,从人们“一直避而不谈”的鲁迅与朱安的婚姻入手,认为这一悲剧婚姻给鲁迅的思想和性格造成很大影响。随着心境的变化,到1925年,鲁迅“开始重视审视自己长期以来对包办婚姻的态度和认识上的偏颇”,这可以他的杂文《寡妇主义》和小说《伤逝》为标志。周棉认为,“如果鲁迅没有与朱安的痛苦婚姻和许广平的友谊,实在难以写出至今令人震惊的感受”,鲁迅的“悔恨”和“悲哀”都因与朱安的婚姻而起,所以,“研究鲁迅思想而回避与他纠缠了三十年之久的封建婚姻,无视思想家的鲁迅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变化,这种研究是欠全面欠深刻的”[21]285-297。同样,李允经也强调说:“《伤逝》并不是鲁迅婚恋生活的传记……只不过有着鲁迅婚恋生活的某些投影和折光。”[22]214-232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在鲁迅内心消长起伏相互纠结,使鲁迅郁积于胸,于是写下《伤逝》,吐出心中块垒,这预示着鲁迅要与“朱安”即旧式的包办婚姻告别。文章还认为,《伤逝》“就思想意义而言,它是要通过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展示一种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的深刻矛盾”[22]232。李允经的说法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坚持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矛盾说”这一对《伤逝》主题的解释。蓝棣之倾向于认为鲁迅写《伤逝》的初衷,是要提出妇女解放的经济条件,是想批评“诗人式的爱情方式”,然而,在小说展开过程中,作者无意之中把自己投射了进去,与许广平的恋爱使鲁迅有了很多思考,成为“小说文本的无意识结构”,因而《伤逝》文本里出现了“更多的声音,更深的意蕴”。[23]林贤治在鲁迅的生命体验这个层次上认为,《伤逝》“发端于自我,又超越了自我。借涓生的自剖,鲁迅表白了内心深挚的爱情,但同时又一次照见自己身上的‘毒气’和‘鬼气’。作为对个人前途的预想,他不无疑惧,但作为对同代人的命运的启示,却又是相当明确的:不要耽于‘自由、平等、独立’一类洋鬼子的学说,任何高妙的理想,都必须同中国的现实社会联系起来。自由成为自觉的追求者和奋斗者,才可能在环境的严酷的压迫下,开辟出新的生路”[24]584。王晓明在《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里,也认为《伤逝》表现出鲁迅对他与许广平之间关系的忧虑,“他把涓生和子君的结局描绘得那么绝望,把他们承受不住社会压力,爱情逐渐变质的过程表现得那么可信,你就能知道他的疑虑有多深,思绪也是怎样地偏于悲观了”[25]116。同样是把《伤逝》与鲁迅本人的婚恋生活联系起来,但陈留生却认为,将它看作起因于跟朱安的婚姻或者缘于跟许广平的相恋都有“致命的漏洞”,因为它跟另外一个女性许羡苏有关。鲁迅在与许广平共同迈向新生活的同时,“感到有愧于许羡苏,因此就虚拟自己若果真与她结合了,其结局必然会像涓生与子君那样,以悲剧告终,既然如此,还不如不结合。这样,鲁迅悬着的心终可平衡了”[26]。此种见解评论界极少见,可谓别出心裁。宗先鸿通过对人物“原型”的分析以及“变形”“镜像”等理论的运用,认为《伤逝》是鲁迅对自己与朱安的“无爱”婚姻的记录,涓生与子君的“隔膜”正是鲁迅与朱安的写照,涓生忏悔时的复杂心态也正是鲁迅心理的真实折射,只不过在小说中,鲁迅对人物原型进行了“艺术变形”,所以不能简单地把人物形象与原型等同起来。[27]作为对宗文的反驳,贾蕾从现代性的角度认为这种索隐式的探究无助于创造性地理解《伤逝》,并且可能将读者引入歧途。《伤逝》是“鲁迅借助传统小说‘始乱终弃’的叙述模式,灌注进现代的个性思想与忏悔意识,使之成为传统文学向现代转型的范本”,“鲁迅用一个‘始乱终弃’的结构模式讲述了现代的爱情和由此而来的隔膜,他的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精神在涓生的叙述中起伏着”[28]。
(三)中西比较视野下的研究
众所周知,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在1980年代逐渐复苏并呈现繁荣局面,原因除了前述政治环境的松动之外,西方哲学思潮和文艺理论的输入无疑是关键因素。其时相继出现的“方法热”“文化热”给文学批评注入了新鲜血液,于是文学批评实践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刘再复把这种变化称为包含两项内容的“文体革命”:一项改变了文学批评的语言符号系统,开辟了新的概念范畴体系;另一项是改变了基本思维方式,包括思维结构、研究方法和批评的基本思路等。[29]统观当时的文艺界,除了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和道德伦理批评,文艺心理学批评、原型批评、叙事学批评、系统论批评、比较文学批评、形式主义批评、接受美学等各种文学批评方法争奇斗艳、颉颃并进,一个百家争鸣、多元共存的局面由此展开。具体到《伤逝》的批评和研究中,同样出现了由于新方法、新思路、新视角的运用而带来的新成果。上述索隐式的研究很多就涉及到文艺心理学和原型批评。
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伤逝》的文章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出现,如吴茂生《从〈伤逝〉与〈工人绥惠略夫〉比较看鲁迅小说技巧的借鉴和创新》①吴茂生《从〈伤逝〉与〈工人绥惠略夫〉比较看鲁迅小说技巧的借鉴和创新》,载《鲁迅研究月刊》1986年第1期。、宋凤英《〈玩偶之家〉和〈伤逝〉的比较分析》②宋凤英《〈玩偶之家〉和〈伤逝〉的比较分析》,载《曲靖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康林《借鉴与超越——〈伤逝〉与〈玩偶之间〉的比较》③康林《借鉴与超越——〈伤逝〉与〈玩偶之间〉的比较》,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9年第5期。、马瑞瑜《纪伯伦的〈折断的翅膀〉和鲁迅的〈伤逝〉之比较》④马瑞瑜《纪伯伦的〈折断的翅膀〉和鲁迅的〈伤逝〉之比较》,载《阿拉伯世界》1993年第3期。、许淑娟《中国的“娜拉”和挪威的“娜拉”──比较鲁迅和易卜生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探索》⑤许淑娟《中国的“娜拉”和挪威的“娜拉”──比较鲁迅和易卜生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探索》,载《妇女研究论丛》1994年第3期。等,这些文章多是从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技巧、叙述方式、表现手法等方面将《伤逝》与外国作品相比较,来说明鲁迅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以及对之的超越,论述的层次相对浅显。21世纪前后至今的比较文学研究深度有所增加,蔡春华通过考察子君和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笔下的四位女性的爱情追求历程,探讨中日女性在历史转型期及女性自我觉醒初期走向悲剧的过程中所具有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进一步理清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30]马以鑫将视点放在俄罗斯文学和东欧文学对鲁迅的影响之中,结合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特别关注及所受的深刻影响,认为陀氏的《地下室手记》与《伤逝》在思想叙述与表现形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二者对于灵魂的刻画与描绘成为“至今活着的一代人的一个代表”,令人回味无穷。刘立善从“渊源学”和主题学的角度,对《伤逝》和有岛武郎的小说《一个女人》中的反封建、争自我的女性形象以及人物悲剧的个性原因与社会原因进行探索,认为二者在思想主题、人物设定和悲剧的终场上,都有诸多相似之处。[32]季源、季海洋《男权统治下的牺牲品》一文,从男权统治和中西文化入手,将《伤逝》与《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作对比研究,归结出正是男权统治下的人类基本情感的扭曲导致了女性的悲剧。[33]此外,还有许多文章将《伤逝》同鲁迅的其他作品或其他作家的作品放在一起作比较分析,这一类的研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研究,有些篇目在其他类别的《伤逝》研究作了概括,故略去不述。
从文化角度研究《伤逝》的文章相对不多,但体现出人们开始在更深广的层次上挖掘《伤逝》的内涵。徐越化和沙水从中西文化冲突的角度进行了阐释,前者认为,“《伤逝》是鲁迅吸收外来文化并继承中国传统的产物”,是鲁迅借用西方文化来启蒙民智以唤醒人的自觉,这也使得小说具有“鲜明的启蒙主义色彩”[34];后者认为,“鲁迅的深刻处便在于,他并没有像通常描写个性解放的小说那样,把重点放在人物与环境的外在冲突上,而是着力于表现人物在‘安宁和幸福’的环境中的内心冲突即文化心理冲突”,“《伤逝》对中国传统以儿童式的‘赤诚’为基础的爱情、‘纯情’的反思,是鲁迅极其深刻地看穿了中国文化的本质并领会了西方的拜伦、雪莱、易卜生等人的‘摩罗诗力’精神的产物,是中、西爱情观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碰撞”[35]。王兆胜从家庭文化角度将《伤逝》和钱锺书的《围城》进行对比阅读,一窥二者不同的家庭观念和创作个性,并追踪中国现代文学的流变与态势。[36]李之鼎从父权制文化积淀着眼,认为《伤逝》隐含作者受到“强大的、具有几千年堕力的男性中心化的文化及历史无意识”的操控,使得小说文本呈现出男性中心主义的色彩,这最突出地体现在“第一人称男性主人公内聚焦(内视角)的叙述方式”上。“男性权威叙事剥夺了她(指子君,笔者注)的话语权,使她成为一个失语的、暗哑的女性形象。”“隐含作者所以从主观的性别关怀滑入客观的性别歧视,可说是男性中心化文化所具有的巨大的、命运般的历史无意识力量施逞威风的结果。”[37]李文可以说是运用叙事学理论从性别文化角度解读《伤逝》的典型个案。
(四)性别视阈下的研究
自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性别理论在1980-1990年代陆续传入中国以后,中国本土的文学批评实践开始大量涌现,作为鲁迅“唯一的爱情小说”,《伤逝》必然受到青睐。于是就有很多文章从性别视角、女性主体性或者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来分析解读《伤逝》,此类文章在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大量出现,前述李之鼎的文章即是一例。周玉宁从性别角色的冲突、人生的寂寞和孤独两个层面对主人公的悲剧原因作了分析,一方面是“现实生存关系的匮乏”,另一方面是“男女间的隔膜与厌弃”,而“子君自身的惰性因袭,她的较平凡的个性是造成她悲剧的主要原因”[38]。不难看出,该文依然把过多的责任推给子君。李继凯从“异化”的观念出发,从“人的异化”和“女性的异化”两方面分析鲁迅笔下承受着“异化力量”的女性的命运,“借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方法,来揭示鲁迅对女性异化的深刻的艺术把握”[39]。冯奇的《服从与献身》一文,认为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早已被制度化,这种制度化了的性别压迫深刻影响着妇女的心理、精神、欲望、情感和身体,以至女性丧失了自身的性别意识而不自知。子君正是在这种状况中找不到自己的恰当位置,“从一种形式的束缚走向另一种形式的羁绊”[40],悲剧是必然的。缪启昆站在女性的立场对子君给予了高度赞赏,认为《伤逝》中的子君,无论是涓生的“怒其不争”还是鲁迅的“哀其不幸”,都是被潜在的男性主体意识扭曲了的误解:涓生将她的“奉献”曲解成“索取”,鲁迅则把她的“刚强”当成是“柔弱”。[41]杨剑龙将《伤逝》与《倪焕之》放在一起解读,认为二者“有一种明显的男性视阈”。女性在矛盾冲突中的心理和行为“都被男性主人公视作变为粗俗庸俗的表现”,“女性形象从天使向妖妇转变的趋势,多少隐藏着男性父权制社会观念对女性的苛求与歪曲”[42]。与对《伤逝》作者和叙述者的批判立场相反,曹建玲则认为,鲁迅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男性视角和意识,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43]。《伤逝》中涓生的忏悔、辩解和自我剖析是“几千年来男性对男女关系中的自我的一次冷静的审视和否定”,是真诚和真实的,其自我批判的意义也相当丰富,“表现了男性视角的偏移,男性意识霸权倾向的式微”,而“男性角色的自剖,也是作家对男性的解剖,其间透着历史文化的厚重感”[43]。同样是肯定鲁迅的女性主义思想,杨联芬从叙述的修辞性角度,将鲁迅与郁达夫、茅盾等同时期其他男性作家区别开来,认为后者的作品拟想读者是同时代的男性而不是女性,男性的经验、欲望、道德及审美期待,支配着他们对女性的塑造与想象,也限制了他们对女性处境的真切关怀;而《伤逝》拟想的读者不是男性而是女性,是那些在启蒙思潮鼓动下追求自由,却又无法超越传统女性宿命的女性,作品表现了鲁迅独特而深刻的女性主义思想观念。[44]贾振勇将西方“现代性”理论与性别文化相结合,认为《伤逝》“从寓言的意义上,展示了以‘娜拉出走’为代表的现代性价值理念在当时历史境遇中的两难处境,批判了它的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功能和虚拟的乌托邦色彩”[45]。该文由于现代性理论和术语的运用而颇具理论思辨色彩,当然也对读者的理论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李玲从社会事业和日常生活的关系中切入性别压迫,认为“中国现代男性叙事在批评女性落后的时候,往往以社会事业简单地否定家庭日常生活,以既有的男性生命尺度简单地否定既有的女性生存方式”,《伤逝》“隐含作者显然是操纵话语霸权的男性人物涓生的同谋。而在婚姻生活中,把社会事业与日常生活置于价值绝对对立状态,以前者否认后者的价值,便是隐含作者、叙事者、男性人物共同倚仗的价值霸权。涓生借忏悔之名把爱情夭折的责任一味推卸给子君,这就造成了《伤逝》文本关于爱情‘更新,生长,创造’理念在特定语境中的偏颇与狭隘”[46]。这一探讨将《伤逝》的性别分析引入深层。王璐认为,子君在开始高扬了一种女性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性代表了一大批五四时代觉醒的青年,同时也是“涓生和子君恋爱的基础”,但这种主体意识在二人同居后却渐渐失去,这种丧失“可以说是传统文化对女性的遮蔽”,那么“女性通过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争取到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权利之后,如何成为爱情和婚姻的主体?”[47]鲁迅正是通过子君形象表达了这一忧思。赖翅萍、翟永明则从身体叙事、叙事结构等角度认为,子君主体性的沉默与丧失与叙述者及隐含作者的男性集体无意识和性别歧视有关。①参见赖翅萍《身体叙事与女性困境》,载《中国女性主义》2005年秋冬卷,第200-202页;翟永明《启蒙中的两性关系——从〈伤逝〉谈起》,载《中国女性主义》2005年秋冬卷,第204-205页。这几篇文章主要是从女性主体性的角度来解读《伤逝》,探讨女性与传统文化、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男权意识与性别歧视之间的关系。林丹娅超越现有的从“小说者说”出发的研究方法,将《伤逝》置放在从古典到现代众多经典的文学文本当中,梳理出其内在的一致性——“私奔”模式,在《伤逝》的叙事破绽及意图悖谬中,解读出其所蕴含的中国现代男性文化精英的性政治观、话语类型、两性关系与女性解放进程的真实形态,从而使《伤逝》显示出远不止于现有研究层面、价值的文本意义。[48]
从上述文章可以看出三种明显的性别立场,第一种是对《伤逝》的男主人公及作者给予女性主义批判,认为小说的叙事策略或者他们的潜意识中隐藏着男权思想;第二种是相反的观点,肯定了作者对女性的关怀及对男性中心文化的反思与批判;第三种则是站在相对客观的角度和中性立场,对鲁迅及其作品给予比较公允的性别视角上的评价。针对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现状,王富仁曾给予客观冷静的审视,他反对将男女两性文学截然划开的做法,反对用“定义性的抽象本质代替活生生的、复杂多变的研究对象”,在谈到鲁迅时,他认为,“鲁迅将子君、祥林嫂等女性形象置于‘被看’的位置上,固然反映了男性作家所不能没有的局限性,但其目的却是为了加强读者对女性生活命运的感受力和对女性内心精神痛苦的想象力,从而突破男性主观体验的狭隘性而进入到对女性生命体验的精神空间之中去,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男女两性的精神沟通”[49]。这一认识对当代性别文化研究和女性文学批评不无参考和借鉴意义。
(五)形而上层面的解读
为了挖掘《伤逝》形而上的深层意义,有论者从哲学层面或人(类)的普遍性角度来解读《伤逝》。李怡的文章较早地尝试了这种方法,认为完全从弱小个人与强大社会的对立这一角度还不能说明这篇小说,“鲁迅所着力渲染的并不是社会如何一步一步桎梏、干涸涓生、子君的感情,而是涓生、子君之间的内部感情变化的必然过程。社会环境在小说中始终处于背景状态,它对子君、涓生的内在影响也是触发式的,而不是决定式的。《伤逝》的这一艺术角度启发我们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来理解其悲剧意义:这是新时代难以避免的两性悲剧。也正是从这个更深的意义出发,《伤逝》涵盖了一种更为广阔的现代世界的悲哀”[50]。刘起林、易瑛二人认为《伤逝》的主题内核是“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求”。涓生对子君始爱终弃,“与他对生命最高意义的追求紧密相连”,两人的悲剧“对涓生来说,实际是一曲生命终极意义追求的悲歌”,鲁迅采用“涓生手记”的形式正是为了强调其中“所包含的这种形而上层面的意蕴”[51]。此种阐释看似深刻,但有为涓生开脱之嫌。张宁借助柏拉图故事的寓意,从“爱”和“自由”两个主题着手,认为《伤逝》蕴含着两个基本问题,即“自由与意志的悖论”问题和“爱的悖论”问题,前者表现在“自由的爱与爱中的自由意志的冲突”,后者表现在“让情侣充当神祇的企图和情侣担当不起神祇的重量之间的矛盾”,从而宣告了“浪漫主义出路”的终结。[52]袁桂娥认为,在涓生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他“关于爱情本体及爱情与生活关系”和“生命终极意义”的思考,这其中实际上蕴含着叙述主体鲁迅对人生的感悟和体验,《伤逝》同《野草》一样“体现了鲁迅的人生哲学”——“个体生命存在的无奈和悲剧性”[53]。同样是将《伤逝》与《野草》联系起来,汪晖的形而上解读最为典型。他认为,《伤逝》“爱情故事的叙述过程与《野草》人生哲学的表达方式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在对爱情的追忆、失望和哀悼的表层叙述背后,始终纠缠着对希望、绝望与虚妄三者关系的心灵搏斗”,“小说中的‘虚空’主题自始至终伴随着‘真实’对于一切与‘希望’相联系的精神现象的否定,换言之,‘虚空’是对一切乐观主义人生期待的深刻怀疑,是对现实无可希望或绝望状况的证实”[54]。对“虚空”的自觉,逼使涓生陷入“荒诞的局面”并不得不作出选择,而这种选择只能是“反抗绝望”[54]。简单来说,汪晖认为包括《伤逝》在内的文学世界是鲁迅“反抗绝望”人生哲学的体现。钱理群则认为,《伤逝》“有强烈的知识分子的自忏自省性,而且也充满了对人生的生存困境的追问”,它与《在酒楼上》《孤独者》等一样是“最具鲁迅气氛”的小说,都是“鲁迅在‘真实’与‘说谎’之间苦苦挣扎的产物”[55]59-79。如果补上缺席了的子君的视角,以平等的态度看待男女主人公,就能破解“小说背后蕴藏的人生之谜”——《伤逝》的悲剧“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悲剧和庸常的人生悲剧,而触及了人生之根本,展示了人与人永恒隔膜的悲剧状态”[56]。与上述几篇稍有不同,罗华撇开精神性问题,而从物质性的角度审视鲁迅的《孤独者》《伤逝》和《弟兄》三篇小说,认为:“借助这三篇小说,鲁迅有意识地凸现了物质性问题,分别叙述了人的生存方式、情爱关系、血亲关系是如何在物质的制约下呈现出‘虚弱’,并由此营构人物在自我悖论和自我诉讼过程中的伦理诉求,探究人物的道德心性和人性能力。”[57]同样是将《伤逝》与《孤独者》并置阅读,安文军从小说文本之外的三个方面:“病”“爱”“生计及其他”进入《伤逝》,揭示出“20年代中期鲁迅的惨淡人生和小说创作之间最深切的内在联系”,此种解读的形而上意味虽有所弱化,但却为我们“敞开了一个更丰富、更广阔的鲁迅小说的意义空间”[58]。
不难看出,上述各文多是从存在论的高度给予了《伤逝》新的解读,使读者对人的存在本质和人与人的关系本质有了更深的思考。
(六)启蒙语境及其他研究
由于鲁迅作品所具有的强烈启蒙色彩,有些研究者从“启蒙”这一关键词对《伤逝》进行了解读。张岚从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出走”现象切入并指出,与其他作家所展示给女性启蒙对象的幸福光明前景不同,鲁迅的独特性在于他的“悲观启蒙”,即女性的“出走”并非抵达理想之境的坦途,仅仅指向一种“虚妄”,这种“虚妄”跟鲁迅对女性社会历史地位的思考及鲁迅个体生命与女性复杂的互动关系等有着深层联系,而“悲观启蒙”正是鲁迅“绝望的抗战”精神的体现。[59]申朝晖、李继凯认为《伤逝》的主题已远远超越了20世纪“妇女解放”的社会问题,文本内外呈现出的是涓生与鲁迅,包括隐含的作者这些男性启蒙思想家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痛苦、复杂而隐晦的人生体验,是他们对自身所矢志追求的“启蒙”行为的深刻怀疑,是“启蒙者”在叙述中不自觉地蜕变为“被启蒙者”这一具有深邃哲学内涵的“悖反”式主题。[60]与此相似,马敏在对《伤逝》的解读中发现了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中男女两性关系存在着“导师与学生”的模式,《伤逝》中男女主角的关系就再现了这种模式中“启蒙与被启蒙、召唤与跟随”的情形;但由于双方“性别和个体的天然隔膜”,最终造成启蒙的失败,鲁迅借助这一悲剧表达了对于以导师自居的启蒙主义者行为结果的反思。[61]刘俊从“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出发,提出一个疑问:相对于“被启蒙者”,“启蒙者”“具有一种不证自明的先进性、正义性和正确性”,但“启蒙者”的权力来自何处,“启蒙者”的身份应不应该受到质疑?文章认为,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启蒙者”的深刻反思从一个方面丰富了鲁迅深刻的思想:当同时代的“启蒙者”们专注于向“蒙昧”宣战的时候,鲁迅已经开始了对“启蒙者”自身的“解剖”。《伤逝》就是鲁迅“除魅”“启蒙者”的一个结果,鲁迅通过对涓生这一“启蒙者”形象的塑造,对“启蒙者”自身的缺陷进行了深刻反省 ,对笼罩在“启蒙者”身上的正义和正确光环进行了去魅。[62]朱郁文联系“呐喊”和“彷徨”两个时期鲁迅的不同思想状态,从对启蒙者的反思、对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关系的反思、对启蒙本身的反思三个层面就《伤逝》中鲁迅对启蒙的反思作了分析,认为鲁迅在“呐喊”时期对启蒙的力量是确信的,而到“彷徨”时期就开始质疑和反思了。[63]
除了上述几类研究,还有一些文章从各自的角度对《伤逝》的主题作了新阐释。吕俊华《〈伤逝〉别解》一文:“用距离说分析两人情感的消长,说明距离与美感的关系,即有距离即有美感。”①转自刘再复《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载《读书》1985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1985年4月,第11-19页。陈瑞林从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视角,将《伤逝》与《狂人日记》《孤独者》《在酒楼上》等其他小说放在一起来解读主人公们内心的恐惧意识,这种恐惧意识缘于“觉醒者”对“吃人”的历史环境以及毁灭“先觉者”的各种外在的和内在的力量的省察,这些作品塑造的一系列具有内在精神联系的觉醒知识分子形象,显然是鲁迅精神人格多层次的具象外化,也就是说这种恐惧意识是主人公所具有的,也是作者自己所具有的。[64]344-355冯金红抓住“涓生的手记”这一形式所寓含的反讽性,来认识涓生形象的忏悔者内涵及子君所处的叙述缺席的位置。文章认为,涓生和子君“各自所爱的都只是自己主观制造的对方的幻象”,涓生自认为是启蒙者,把子君当作“被拯救的对象”,而子君骨子里却没有多少现代性可言,只不过是当时流行观念的产物。文章借助弗洛伊德的“超我”与“本我”理论分析了“既矛盾分裂又统一谐和”的涓生形象。[65]罗小茗的文章表达了相似的意思,认为涓生选择的并不是一个现实中活生生的子君,而是子君身上“被额外赋予了光明意味”、被抽象了的某个部分,并把它扩展为她的全部意义,涓生确立了自己启蒙者的地位,却无力承担启蒙的后果。[66]郜元宝从“自由”与“自由的条件”的关系着眼,认为《伤逝》的主题是:“自由”是不讲“条件”的,而现实偏偏给它设置种种必须正视的“条件”;《伤逝》并非要谴责涓生,也无关乎“男权”和“女权”,而是叹息“自由的条件”太多,且这些条件偏偏附在争自由的新女性身上。[67]吴成年认为,鲁迅的《祝福》《离婚》和《伤逝》“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女性的三种生存困境:祥林嫂受封建道德习俗奴役,在救赎自己的道德罪过无望中悲惨离世;爱姑受陈腐的权威蒙蔽,将是否离婚的决定权交给了七大人;子君受爱情束缚,退守于爱的小巢,将命运交付给所爱的人涓生。她们共同的悲剧都是将决定自己命运的主动权交给了外在于己的对象”[68]。作者的这种分析对于女性当下的生存状态以及人生选择仍具有很强的警示意义。
(七)独辟蹊径的内部研究
如果按照雷纳·韦勒克(Rene Wellek)关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两分法,那么以上所谈到的研究《伤逝》的文章几乎都属于“外部研究”。与阵容强大的“外部研究”相比,《伤逝》的“内部研究”则相对薄弱,正因其“弱势”,更显示了论述这种研究的必要性。早在80年代,就有少数文章突破主题研究的拘囿,或从小说语言的叙述,或从小说富含的诗性语言和韵味来阅读《伤逝》,不过这些文章多是立意于肯定小说的艺术性,算不上地道的文本批评。随着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日深,《伤逝》的“内部研究”也日见起色。
谢会昌的《圆形:鲁迅小说的突出结构》一文,以结构主义审视鲁迅小说,发现无论人物的行径还是人物思想感情变化的轨迹,大都有一个“圆形”结构,即从原点出发,绕了个圈子,又回到了原点。《伤逝》里的子君或涓生甚至小狗阿随身上都体现了这一点。[69]同样是认为《伤逝》具有圆形结构,但胡德才主要不是从人物的命运而是全篇着眼,认为文本以涓生写“手记”始,写完“手记”终,是一个严密的“封套”即“圆”,且封套中有封套,大圆中有小圆。无论是小说首尾的呼应衔接,还是爱情悲剧本身,抑或故事发生的时间都是圆形结构,封闭的圆形寓意为通往希望的路途被封闭,这就是《伤逝》圆形结构所潜藏的内涵。[70]从“圆形”结构解释“希望”之为“虚妄”不失为一个新颖的角度。汪卫东将“叙事学本文解读”与“作家主体存在论解读”相结合,揭示出“《伤逝》本文的分裂正来自鲁迅主体的分裂,本文危机正反映了鲁迅潜意识中自我意识的危机”[71]。张箭飞从形式方式(显性重复和隐性重复)、结构作用(交响诗般的丰富的简洁)、效果(音乐性)三个方面来分析“诗性节奏”在《伤逝》里的表现,以证实其“实现了小说和诗的重合”[72]。同样是探讨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党秀芬则运用结构主义的元语言、对象语言、联想关系、符号学等来解析出文本的深层语义结构,并反其道认为“子君才是实践中的行动上的启蒙者”[73]。马丽蓉运用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等人的小说“空间化”理论,从叙事学的视角切入,发现在叙述基调和叙述方法的显示与运用中,“空间化”成了《伤逝》鲜明的叙述特征,即“将历时性的情节作了空间化的处理”,“这不仅为我们传达出了一个有机的现实全景,还令我们必须改变以往因果线型的单向度接受思维,力求在多向度的立体阅读中更深入领会鲁迅小说的深刻与独到”[74]。
有论者从修辞学的角度,或从“反讽”和“隐喻”两方面认为《伤逝》具有反讽语义结构,涓生“忏悔”的反讽情境可以解构整个独白话语的权威和真实性;“吉兆胡同”是鲁迅写作《伤逝》时所面对的北京段氏反动统治的一个极佳代称,它有着隐喻意义。[75]或从“象征”方面说明《伤逝》是一篇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高度融合的艺术作品,“家”和“夜”象征着人类的生存困境;“爱”象征着人类精神追求中世俗的牵绊和情感的重负;“花与动物”“谈天、读书、散步”与“家务”象征了脱俗与世俗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子君”象征了一种虚无的存在,“涓生”象征着不可征服的生命;“走”是他的原型,是他反抗死亡与空虚,获得生命永恒意义与价值的方式。[76]也有人以苏珊·朗格(Susanne K Langer)的符号论美学来解读《伤逝》的语言艺术特色,认为它有符号的节奏美、符号的形象美和符号的个性美。[77]谭君强专门从叙事学的角度对鲁迅的小说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他认为,“《伤逝》的叙述者不是一个与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相一致的可信的叙述者,而是一个不可信的叙述者”,叙述者的冠冕堂皇、理直气壮、自欺欺人与读者对故事的推测和理解之间形成了很大的张力,这“使读者增强了对叙述者道德审判的力度”[78]86-87。郜元宝在《〈伤逝〉讲解》中认为,由于作者“将涓生摆在既是实际的小说角色又是唯一的叙述者以特殊位置”,那么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之间、叙述者涓生与完全处于被叙述地位的子君之间以及复数(不同时态和语境中)的涓生相互之间这三方面的不和谐,就是阅读小说的关键。[79]63-64
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一时也成为解读《伤逝》的有力工具。严家炎认为,鲁迅的小说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而使作品呈现出“复调”色彩,《伤逝》中叙事技巧的圆熟使小说中同时回响着多重的声音,具有多声部特点。[80]吴晓东认为,鲁迅第一人称小说中的叙事者“我”与人物之间构成了一种对话与潜对话的关系模式,这种关系模式既是处理小说中不同的甚至彼此冲突的声音的方式,也使小说中的对话性与辩难性得以“形式化”,其中蕴涵了一种第一人称叙事的复调诗学,《伤逝》即是典型的一例。[81]冷桂军运用西方接受美学理论,探讨《伤逝》召唤结构的生成与对读者期待视野的反拔和读者的接受过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以及读者接受情感的发展、演进历程。[82]张春泉运用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认为《伤逝》其实描述的是普遍语用学背景下基于主体交互性的对话的“伤逝”,它表明语言和谐是交往理性的基本要义,“没有控制的交往”是人际和谐的一种表现形式,“对话”是化解交往危机的必要途径,交往理性是合理性对话的基本动因。①参见张春泉《人际和谐与交往理性——鲁迅〈伤逝〉的文本意义新解》,载《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第129-131页;《语言和谐:交往理性的基本要义——鲁迅〈伤逝〉主题的新诠释》,载《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第126-127页;《交往理性的“伤逝”——〈伤逝〉的主体交互性解读》,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07年第1期,第137-140页。
以上关于《伤逝》“内部研究”的文章大多产生于19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
四、新世纪以来的零星突破
近年来,关于《伤逝》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前人在不同理论背景下的多层面多视角阐释,在为《伤逝》研究添砖加瓦的同时也对后来的学者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在研究中寻求突破和创新已非易事。此种情况下,在2015年,即《伤逝》诞生整整90年之际出现的几篇论文倒是值得一提。其中,有学者从三个层面——“即表层‘五四’式恋爱悲剧;深层的启蒙理性谋害日常生活正当性的隐喻以及悬浮在两者之上的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摆脱不了的梦魇般存在的虚空感何以将时间空间化并最终使第一人称叙事者消极地确立了自己的存在感”[83]——对《伤逝》进行了讨论,并从叙事学的角度对《伤逝》文本中暗含的现代性命题作了深度解读。有学者从进化论与近代女性解放之关系切入,在宏观视域下对子君悲剧成因及中国女性解放的悖论处境作了更深层次的分析。[84]有学者藉《伤逝》文本考察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实践,重点讨论了鲁迅对“造人”神话的反省、对“伪士”形象的批判以及对“日常生活的辩证法”的强调。[85]有学者从对《伤逝》中女性身体叙事的考察,将《伤逝》看作一个与古代才子佳人小说“始乱终弃”故事类型在叙事形态上具有同构性的文本,认为鲁迅“借助传统故事叙事的现代转型”,寄托“对五四个性解放与女性解放问题的反思,由此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制造的似乎坚不可摧的现代启蒙神话”[86]。这些研究成果都在以一种超越单纯性别视角的分析来寻求《伤逝》研究的新突破。
五、《伤逝》研究的阶段性特点
《伤逝》的诞生及对它的研究已有90年的历史,综上所述,就中国大陆的研究而言,如果以1930年代中期和1980年代中期为界,把《伤逝》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突出的特点:首先,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这两个时期是相对比较自由和多元的,前者产生的批评文章虽然较少,却极富个性,有很强的可读性和感染力。其次,第一阶段的《伤逝》批评多属印象式,重体验,批评主体的独立性较强;第二阶段的《伤逝》批评较为统一,解读模式比较单一,批评主体的独立性较弱;第三个阶段的《伤逝》研究,多样化色彩明显,成果丰富,批评主体的自主性也逐渐增加。第三,从理论色彩来看,三个阶段也呈现出递增的趋势,原因在于,第一个阶段世界范围内的文学批评理论尚未形成多样多元共存的局面,传入国内的就少之又少,所以此时的文学批评更多的还是受到传统感悟式、体验式、印象式批评的影响;第二阶段虽有了理论基础,但基本来自俄国(及苏联)的革命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比较单一,别的理论即便有,也处于被压抑状态;第三个阶段就大不相同,西方在相当长时间内产生的理论派别和方法几乎同时传入中国,为贫瘠的文学批评注入了充沛的活力,上述几个层面,如文化批评、性别批评、哲学批评及内部研究等研究成果几乎全部产生在90年代以后就足以说明问题。第四,我们可以发现,用不同的思路或方法解读《伤逝》,可以得出大致相同的观点,而用相同的批评模式或方法却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充分说明了批评主体在文学批评中的独立性和能动作用;或者可以说一个人的立场不取决于它所用的理论方法和工具,而更多地受限于他的主体性和他所处的政治环境。另外,从数量上看,第一个阶段很少,第二个阶段明显增多,而第三阶段远远超过了前两个阶段之和,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除了《伤逝》的读者受众和批评者越来越多之外,也跟国内的学术评价体制有关——由于发表论文的硬性规定,各高校和其他单位以及身在其中的师生和研究人员必须完成一定的指标,才能完成学术评估、晋级、拿学位证、评奖学金、评职称等,这在促进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就拿《伤逝》研究来说,21世纪以来近十年的时间里,《伤逝》以及与之有关的评论文章数量大大超过了以前,且呈现逐年递增之势,尽管其中不乏新论,但很多文章重复了此前的研究成果,不客气地说都属于“垃圾论文”。这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需要说明的是,90年来,《伤逝》研究的专文数量粗略算来不下500篇,如果加上将《伤逝》与其他作品相比较的研究以及涉及到《伤逝》的专著和文章,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本文作为对《伤逝》研究的综述性分析考察,不可能也不必要涉及所有的文章,但囊括了比较典型的、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从这些研究当中,也许不同的人能发现不同的东西,这有待进一步探讨。总之,鲁迅及鲁迅的文字远未过时,对其经典性的作品《伤逝》的研究也是一个“未完成”的课题。
[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1913-1936[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2]茅盾.鲁迅论[M]//李何林.鲁迅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3]李长之.鲁迅批判[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4]何干之.一出悲壮剧——一九二五年的《伤逝》[M]//鲁迅作品研究:中国和中国人的镜子.上海:新新出版社,1946.
[5]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1946-1949[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
[6]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1940-1945[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
[7]吴中杰,高云.论鲁迅的小说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
[8]支克坚.一个被简单化了的主题——关于鲁迅小说及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发展中的个性主义问题[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3):7-25.
[9]康林.应当全面把握《伤逝》的创作背景[M]//鲁迅研究:第9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0]张永泉.《伤逝》与个性解放[M]//鲁迅研究:第 10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11]陈安湖.鲁迅研究三十年 [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12]赵晓笛,冯奇.论《伤逝》和个性解放问题[M]//鲁迅研究:第1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13]陆文采.从子君到莎菲——浅谈“新女性”的艺术形象及其美学价值[M]//鲁迅研究:第1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4]王富仁.《呐喊》《彷徨》综论[M]//汪晖,钱理群.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论鲁迅: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5]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16]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7]周楠本.谈涓生的忏悔 [J].鲁迅研究月刊,1995,(3):22-29.
[18]赵敬立.唱歌一般的哭声,给旧我送葬——《伤逝》新解[J].鲁迅研究月刊,1996,(11):16-24.
[19]谢菊.《伤逝》解读[J].鲁迅研究月刊,2001,(11):56-61.
[20]谢世洋.是“兄弟情”之哀还是“国民性”之叹?——《伤逝》主题辩[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110-114.
[21]周棉.从与朱安的悲剧婚姻看鲁迅的思想演变 [M]//江苏省鲁迅研究学会.鲁迅与中外文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22]李允经.向朱安告别——《伤逝》新探[M]//李允经.鲁迅的情感世界——婚恋生活及其投影.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6.
[23]蓝棣之.万不可做将来的梦——论《伤逝》[J].鲁迅研究月刊,1998,(10):34-36.
[24]林贤治.人间鲁迅[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
[25]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26]陈留生.《伤逝》创作动因新探[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115-120.
[27]宗先鸿.论《伤逝》的创作意图与人物原型[J].鲁迅研究月刊,2005,(11):41-45.
[28]贾蕾.《伤逝》:传统乐章的现代变奏与升华——兼与宗先鸿先生商榷[J].鲁迅研究月刊,2006,(3):52-56.
[29]刘再复.论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革命 [J].文学评论,1989,(1):5-22.
[30]蔡春华.走向悲剧:中日女性的爱情幻灭之路——鲁迅《伤逝》与夏目漱石“爱情三部曲”比较[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78-81.
[31]马以鑫.“至今活着的一代人的一个代表”——《地下室手记》与《伤逝》比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33-35.
[32]刘立善.有岛武郎《一个女人》与鲁迅《伤逝》之比较[J].日本研究,2005,(4):66-71.
[33]季源,季海洋.男权统治下的牺牲品——对《伤逝》和《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的女性主义解读[J].文教资料,2009,(11):28-29.
[34]徐越化.东西方文化激荡中的《伤逝》[J].湖州师专学报,1992,(2):52-58.
[35]沙水.《伤逝》中的文化冲突试析[J].鲁迅研究月刊,1994,(5):26-29.
[36]王兆胜.伤惋与漂移——从家庭文化角度解读《伤逝》和《围城》[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4):86-90.
[37]李之鼎.《伤逝》:无意识性别叙事话语[J].鲁迅研究月刊,1996,(5):29-33.
[38]周玉宁.性别冲突下的灵魂悲歌——《伤逝》解读[J].江苏社会科学,1994,(2):119-123.
[39]李继凯.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异化 [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5,(1):71-78.
[40]冯奇.服从与献身——鲁迅对中国女性身份的批判性考察[J].鲁迅研究月刊,1997,(10):27-33.
[41]缪启昆.子君——男性主体言说下扭曲的女性形象——《伤逝》散论之三[J].职大学报,2003,(1):43-46.
[42]杨剑龙.男性视阈中的女性观照——读鲁迅的《伤逝》、叶圣陶的《倪焕之》[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34-39.
[43]曹建玲.超性别书写——鲁迅作品的女性主义立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3):122-126.
[44]杨联芬.叙述的修辞性与鲁迅的女性观——以《伤逝》为例[J].鲁迅研究月刊,2005,(3):22-27.
[45]贾振勇.娜拉出走:现代性的女性神话——鲁迅小说《伤逝》再诠释[J].鲁迅研究月刊,2001,(3):23-27.
[46]李玲.生命的超越性追求与女性日常人生——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落后于男性的女性 [J].文艺争鸣,2002,(6):64-67.
[47]王璐.鲁迅小说中女性人物的主体意识 [J].鲁迅研究月刊,2006,(8):32-35.
[48]林丹娅.“私奔”套中的鲁迅:《伤逝》之辨疑[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54-60.
[49]王富仁.一个男性眼中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究[J].文艺争鸣,2007,(9):6-14.
[50]李怡.《伤逝》与现代世界的悲哀[J].名作欣赏,1988,(2):55-60.
[51]刘起林,易瑛.《伤逝》主题内核: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求[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4):106-109.
[52]张宁.“浪漫主义出路”的终结——从《伤逝》中引出的几个问题[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6):9-14.
[53]袁桂娥.两难,个体生命存在的无奈——《伤逝》意蕴阐释[J].语文学刊,1997,(3):19-22.
[54]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54]钱理群.“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读《在酒楼上》《孤独者》及其他[M]//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5]吴露.存在之殇:《伤逝》主题意蕴别解[J].鲁迅研究月刊,2004,(11):76-78.
[56]罗华.物质制约下的伦理诉求——以《孤独者》《伤逝》《弟兄》为中心 [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5):131-145.
[57]安文军.病、爱、生计及其他——《孤独者》与《伤逝》的幷置阅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6):52-68.
[58]张岚.虚妄的圣殿坍塌之后——论鲁迅小说的女性“出走”[J].浙江社会科学,2003,(1):171-174.
[59]申朝晖,李继凯.不同叙述层面“启蒙”与“被启蒙”的相互转换——《伤逝》主题论[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S1):220-222.
[60]马敏.鲁迅《伤逝》的新解读[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6):120-123.
[61]刘俊.对“启蒙者”的反思和除魅——鲁迅《伤逝》新论{J].文艺争鸣,2007,(3):110-113.
[62]朱郁文.从《伤逝》看鲁迅对启蒙的反思[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133-135.
[64]陈瑞林.试论鲁迅小说中的恐惧意识 [M]//鲁迅研究年刊(1991-1992年合刊).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2.
[65]冯金红.忏悔的“迷宫”——对《伤逝》中涓生形象的分析[J].鲁迅研究月刊,1994,(5):21-25.
[66]罗小茗.涓生的思路——《伤逝》重读[J].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3):211-222.
[67]郜元宝.再谈鲁迅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 [J].鲁迅研究月刊,2000,(11):17-26.
[68]吴成年.论鲁迅小说中女性的三种生存困境[J].妇女研究论丛,2001,(4):56-61.
[69]谢会昌.圆形:鲁迅小说的突出结构[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3):59-65.
[70]胡德才.《伤逝》的圆形结构[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5,(2):1-4.
[71]汪卫东.错综迷离的忏悔世界——《伤逝》重读[J].鲁迅研究月刊,1998,(10):37-46.
[72]张箭飞.论《伤逝》的诗性节奏[J].鲁迅研究月刊,1998,(10):47-53.
[73]党秀芬.由《伤逝》看男性启蒙与被启蒙——《伤逝》的结构主义解读[J].新学术,2008,(2):166-170.
[74]马丽蓉.在空间维度上叙述——《伤逝》新解[J].鲁迅研究月刊,2001,(9):59-62.
[75]梁伟峰,许静.“为了忘却的记念”——论《伤逝》[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66-68.
[76]王兵.人生终极意义的永恒追求——《野草》为参照看《伤逝》的象征意义[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2,(3):39-42.[77]杨凌云.情感与符号——《伤逝》的语言艺术赏析[J].台州学院学报,2003,(5):45-48.
[78]谭君强.叙述的力量——鲁迅小说叙事研究[M].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79]郜元宝.鲁迅精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80]严家炎.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3):1-20.
[81]吴晓东.鲁迅第一人称小说的复调问题 [J].文学评论,2004,(4):137-148.
[82]冷桂军.重读《伤逝》——《伤逝》的接受美学分析[J].张家口师专学报,2003,(2):37-39.
[83]国家玮.“空间”的现代性:论《伤逝》的第一人称叙事[J].鲁迅研究月刊,2015,(5):4-22.
[84]岁涵.进化论与女权——重读《伤逝》[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5):14-25.
[85]金理.造人·“伪士”·日常生活——重读《伤逝》,兼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J].南方文坛,2015,(5):5-14.
[86]程亚丽.“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伤逝》中子君身体叙事的多重解读[J].鲁迅研究月刊,2015,(11):26-35.
A Review of Studies about Lu Xun's Novel Regret for the Past in the Past 90 Years
ZHU Yu-wen
(Department of Cultural&Artistic Theory,Foshan Art Institute,Foshan,Guangdong 528000,China)
Since it was created,Lu Xun's novel Regret for the Past has always drawn attention of readers and critics.Its interpretation,evaluation and controversy have always existed in the past 90 years.The studies of Regret for the Pas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In the first stage,the number of reviews is small but distinctive;in the second,reviews are relatively monotonou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n atmosphere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in the third,under the influences of the loos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he input of Western theories of thought,the studies are much diversified.The three stages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which fully reflect the complex influences of social trends,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individual subjective motives on literary criticism.
Lu Xun;studies of Regret for the Past;90 years
I210.97
A
1673-1972(2017)05-0098-14
2017-08-20
朱郁文(1981-),男,河南淮阳人,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
(责任编辑 周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