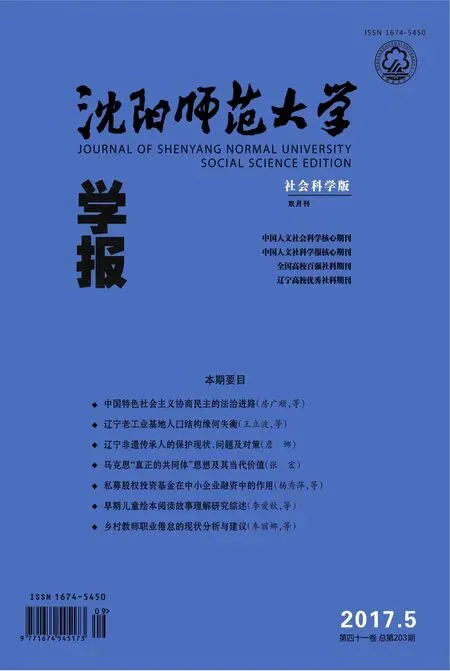清末民初文言小说的传统与新变
陈迪强
(大连外国语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
文学综论
清末民初文言小说的传统与新变
陈迪强
(大连外国语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
随着小说界革命的势力减弱,清末至五四之前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文言小说大繁荣。宏观上看,这批小说仍在继承着古典文言小说的艺术规范,沿袭着文言书面语的传统修辞。但同时,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了新变:文言翻译小说、变异骈体小说、文言章回体小说增多。与古典文言小说表现个人情怀及神怪、传奇不同,此期的文言小说包容更加广阔的社会时事内容,语言也呈现浅白化、驳杂化、新词汇涌现等新特性。
清末民初;文言小说;传统;新变
一、清末民初文言小说的兴盛及其原因
随着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展开,小说成为“新民”之利器,白话小说繁荣一时。但是在民元前后(1910年至1916年之间),文言小说却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有学者甚至称这是一个“谜”“尽管白话文运动日见发展,提倡白话小说者也日见增多,可文言小说不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大行其时,甚至可以说揭开了文言小说发展史上最后但也是最辉煌的一页。这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谜。”[1]笔者通过统计清末至“五四”之前的小说杂志,也证实了这一结论,仅以贯穿清末民初的小说杂志《小说月报》《小说时报》为例,《小说月报》在1912—1917年共发表小说506部(包括长篇和短篇),其中文言小说460部,白话小说46部;《小说时报》在1912—1917年间共发表小说111部,其中文言小说85部,白话小说26部[2]。更不用提在民初创刊的那些几乎全部发表文言小说的杂志,如《小说海》《小说大观》等。仅从数量而言,在整个中国小说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文言小说有清末民初这样繁盛。为什么在小说界革命蓬勃地开展起来的同时,文言小说却有一个回光返照的繁荣期呢?综合来看,无非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小说界革命是建立在“新民”的功利主义基础上,白话只是写给普通民众的,在其他场合用文言更方便。梁启超在翻译《十五小豪杰》时说:“原拟依《水浒》《红楼》等书体裁,纯用俗话,但翻译之时,甚为困难。参用文言,劳半功倍”[2]47。鲁迅在1903年译《月界旅行》时开始也“初拟译以俗语”,可又觉得“纯用俗语,复嫌冗繁”[3],最后还是用文言译出。白话小说和文言小说是平行的两条大道,这和五四时“二选一”的思路不一样,如1915年《小说大观》的选稿标准就是“无论文言俗语,一以兴味为主”[4],文言小说的大道始终是通畅的。因此,小说界革命及白话文运动的浪潮减速时,文言小说就出现反弹。在1909年前后,以《小说时报》(1909年创刊)、《小说月报》(1910年创刊)为代表的第二波小说期刊取代了清末的“四大小说期刊”,至1912到1915年间鸳鸯蝴蝶派崛起之时,文言小说风行程度达到顶峰。
第二,新型作者群、读者群与小说市场的形成。晚清小说创作者和读者大部分是“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1905年科举废除,传统文人的仕途之路阻断,出现大量既无法进入新式学堂,又不能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的“文化游民”,文字可为“稻粱谋”,办刊、办报、写稿赚取稿费就成为他们中间大部分人的事业。所以晚清小说的生产、流通及消费主要是浸淫旧学而对新学也有兴趣的文人阶层。《小说林》杂志社在调查了小说行销状况之后说:“就今日实际上观之,则文言小说之销行,较之白话小说为优”“余约计今之购小说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其真受学校教育,而有思想、有才力、欢迎新小说者,未知满百分之一否也?所以林纾先生,今世小说界之泰斗也,问何以崇拜之者众?则以遣词缀句,胎息史汉,其笔墨古朴顽艳,足占文学界一席而无愧也。”他进而提醒“产销”双方注意:“夫文言小说,所谓通行者既如彼,而白话小说,其不甚通行者又若是,此发行者与著译者,所均宜注意者也”[5]。在白话小说倡行的同时,文言小说的道路始终没有阻断,当遇上蓬勃的市场需求,再加上特定的社会思潮,就会以更加蓬勃的势头发展起来。
第三,文言小说兴盛与民元前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兴起有关。1905年,邓实、黄节、刘师培等人创办了国粹派的代表刊物《国粹学报》。1906年,清廷规定“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教育宗旨,并进而提出“保存国粹”的口号。1907年,张之洞上书说现在“道微文敝,世变愈危”,只有“存国粹”才是“息乱源”的最好方法:“若中国之经史废,则中国之道德废,中国之文理词章废,则中国之经史废……正学既衰,人伦亦废。为国家计,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为世道计,则不啻有洪水猛兽之忧。”[6]这篇奏疏颇受清廷赏识,被“上谕嘉勉”。“保存国粹”思潮不仅在保皇派那里滋长,也得到革命派青睐,但目的与依赖资源不同,他们通过复兴古学唤起人们反清“热肠”。国粹学派的精神领袖章太炎1906年出狱后一到日本就对革命党人提出两大任务,之一便是“以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7]。不久又成立了国学振起社,自任社长,而他主编的《民报》自第20期始,风格大变,讲革命减少,讲国粹增多,征集“宋季、明季杂史下及诗歌、小说之属”,而这里的小说也主要是文言小说。不少革命派刊物也以“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作为发刊词。显然,在各种力量的交织下,辛亥革命前几年,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复古思潮。
千年帝制的崩塌,满清政府的倒台,民国的建立,革命目标一夜之间实现。旋即又有帝制复辟。曹聚仁曾回忆说:“民初的人,不免陷于绝望与焦灼的情结,大家都好似从手掌中溜走了什么似的,虽说整个世界的变动已在开始,我们却雾里看花,既看不出近景,也看不出远景来的。《甲寅》杂志记者的文字,从开头到结束,弥漫着绝望的气息。我还记得章士钊写给陈独秀的信中,就用了‘折简寄愁人,相逢只说愁’的话”[8]。帝制坍塌,袁氏当国,乱象纷呈,新旧文人均产生幻灭情绪。沉浸到儿女情长,花前月下的“鸳蝴”世界,结撰文人雅集,用骈文、古文作小说一时成为趋势。
第四,在此背景下,林纾、徐枕亚这样的畅销书作家的榜样力量不可小视。林纾的文言译著小说自不必说,成为各小说期刊的压卷产品。近代学者王无为在为张静庐著《中国小说史大纲》所作之序言中指出“:逊清末叶,林纾以瑰之姿,用文言译《茶花女遗事》一书,是为西方小说输入吾国之始,亦启长篇小说用文言之端,于是小说界之趋势,为之一变。”[9]包天笑谈到林译小说时也说“:这时候写小说,以文言为尚,尤其是译文,那个风气,可算是林琴翁开的。林翁深于史汉,出笔高古而又风华,大家以为很好,靡然成风地学他的笔调”[10]。而徐枕亚的《玉梨魂》自1912年初版,其发行量更是惊人,据范烟桥说,其发行总数当在几十万册[11]。同时,徐枕亚主编或主笔的刊物也在这期间创刊,如《民权素》《小说丛报》《小说旬报》《小说季报》等,李定夷、吴双热、许啸天、许指严等“鸳蝴派”作家常在这些小说刊物上发表小说,互相推介,形成一个庞大的文言小说创作群体。
从数量、形式多样性及作者队伍的庞大来说,这一时期文言小说大繁荣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道奇观。那么,其艺术内涵及语言美学在文言小说大传统中有何继承和变化呢?
二、清末民初文言小说语言的传统性
总体来说,民元前后的文言小说是处于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大传统之中。文言小说家对小说文体的自我认同、审美想象、艺术手法均以传统文言小说作为参照。但是在这种大繁荣背后,小说的生产方式、表现内容、语言美学都有了新的时代气息。
清末民初文言小说多以古代经典文本为楷模,在传奇、笔记、轶事小说等各类别上均有较为优秀的作品。
传奇体小说,无疑代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最高水平,无论是唐传奇还是清代的《聊斋志异》,其语言上的特点历来为人所称道,鲁迅概括为“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其“文采”主要是体现在语言层面:富丽精工,“叙述宛转,文辞华艳”[12]。民初的文言小说有许多承接了这种华丽婉转的语言特点,仅仿《聊斋》笔法的小说就有许多。
林纾是深得古文笔法的小说家,无论是翻译还是创作,都以清雅的古文笔法出之。这里仅以他的自创小说为例。他曾创作了许多神怪小说,明显延续唐传奇和《聊斋》的风格。如《吴生》写一个狐女爱上一个美俊书生,为接近他而伪装成邻女,循循善诱,终于与吴生结为夫妇。从题目到内容都看到《聊斋》的影响,作者本人亦在篇末称:“此事大类《聊斋》所述之宦娘”[13]。还有一篇《薛五小姐》与此类似。这些小说往往文辞典雅绚烂,结构上富于变化,而意境、人物神韵方面,也深得唐传奇和《聊斋》三昧。体例上以纪传体例为主,常以“某生者”开篇,语言雅正丰赡,加之伏脉、接笋、结穴等古文笔法,使得小说别有一番风味。比如,在《吴生》中写吴生第一次见到邻女,如此写道:
生自在阴中,已见女郎,然亦惊叹其美,亦不解其所以然。既归对烛冥想,初无淫靡之思,似女之秀色能扑人使之丧失所守者。久之忽曰:“吾又废时刻也。奈何为无为之思,抛我正业?”乃复吟诵。
一个可笑、迂腐而又不失可爱的书生跃然纸上,笔致简洁有力。
《小说月报》6卷9期署名为盟鸥榭的《函髻记》,是颇受好评的一篇传奇小说,恽铁樵的评价是“笔墨雅饰,音节入古,今人所不能到,全在声光色韵之间”[14]。其中词句明显有传奇之风:
俄而觥爵交错,丝管杂陈,诸妓以次奏艺。序及行云,揽衣而起,立于筵前,抗声曼歌,众目惊视。歌词之意,横挑欧阳,神情流注,逸姿艳态,殆非人世所见。行周属目倾耳,久之,谓将军曰:“此其申行云也耶?异乎佳人,何为属意于我哉?”歌既阕,欧阳生乃移座而前,顾行云而语曰:“深悉微意,然申君何自而知鄙人?”行云对曰:“妾得《怀忠赋》、《栈道铭》、《曲江池积》,读之年余,略皆上口,与君岂不深耶?”欧阳骇异,以广坐不能久语,遂怅然而归。
当时以骈体作小说的文人更是以唐传奇为尚。仅举徐枕亚的《箫史》(《小说月报》4卷第6号)为例,小说中夹杂诗词,使作品的抒情气氛十分浓郁,篇首小序有议论的成分,作品在整体风格上可以看出对“可见史才、诗笔、议论”的“文备众体”的唐传奇的效仿痕迹。从整体来看,此篇有唐传奇之名篇《虬髯客传》之风。相类似的还有《小说月报》2卷7期《莲娘小史》,写到主人公莲娘揽镜自照时语言华丽抒情,有《李娃传》《霍小玉传》的影子。
与传奇体小说不同,也有一些文言小说大有六朝笔记小说的“粗陈梗概”和“隽永玄妙”的特点。清末民初的小说杂志,刊登有许多传统意义上的笔记小说,有些从现代小说观念来看,不能称小说,这也反映出清末民初混杂的小说分类,栏目名称通常叫野乘、辨订、箴规、谐趣等。如《新小说》刊载的“记小说”《啸天庐拾异》《月月小说》的《新庵译萃》和《新庵随笔》(第2号),《小说丛报》第5期的“笔记”一栏有《雏伏室记》《铁佛庵笔记》《临碧轩笔记》,等等。林纾发表《技击余闻》之后,形成“续”“补”之风,如钱基博的《技击余闻补》(《小说月报》第5卷),江山渊的《续技击余闻》(《小说月报》第7卷),朱鸿寿的《技击余闻补》(《小说新报》第1、2卷)。这些笔记虽然不合现代小说理念,但与古典的笔记、轶事小说则是一脉相承,自有其价值。江山渊说:“林子畏庐,善为古文辞,声播四方。其撰《技击余闻》,虽寥寥短篇,实足以淬民气而厉懦风,其文复典雅渊懿,直逼庄周司马迁,不能徒以小说读也。余窃私其意,博取所见所闻者,撮而录之,以续林子之书”(《小说月报》7卷11号)。这种“博取所见所闻者,撮而录之”的精神正是古代轶事小说如《博物志》《拾遗记》的路数。这些笔记小说的语言简洁、不重铺排,而讲情趣,体现了古典文言小说的语言传统。
三、清末民初文言小说语言的新变
如果对清末民初文言小说进行整体观照的话,我们应该看到,将传统文言小说的语言特色能够发扬光大的还是占少数。这一时段值得注意的是文言小说在体制和语言上有了新变化。
文言小说初期,如魏晋时期的志人志怪小说,甚至唐传奇,均没有长篇大制,清代的《聊斋志异》也是短篇故事的合集,笔记小说更是以短篇为主,而晚清以来的文言小说出现长篇文言小说的繁荣。文言是雅正的书面语,文言的句式及语法有特定的规定性,仅能顺畅地阅读就需要多年的专业训练,而阅读几十万字的文言章回小说,很难说是通俗和消遣。钱基博在论梁启超文章时说:“古人以万言书为希罕之称,而在启超无书不万言,习见不鲜也。”[15]这对于文言小说来说也同样如此。清初的屠绅用文言写过二十万言的小说《史》,这使文言小说史家很难界定,因为他们认为“就‘文言小说’一语的约定俗成的含义来看,通常是不包括长篇在内的。”“我们所说的文言小说,其外延包括传奇小说和笔记小说,以短篇为主,中篇为辅”[16]。按这种界定梳理到清末民初就会很棘手,因为清末民初长篇文言小说成为常态,每一种小说期刊都开辟有长篇小说专栏,文言长篇占多数。林纾自1897年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以后,用文言大量翻译西方小说。有人统计自1897年至1919年前后20年间,林纾翻译了181种小说,“且其中的多数均是长篇或中篇”[17]。如果说1909年以前的小说界是以白话的“四大谴责小说”为主流的话,那么,1909年至五四之间则是以林纾、徐枕亚、苏曼殊的文言小说为主流的,而且在民国初年,文言长篇小说更是大量涌现,《小说大观》是包天笑主办的小说杂志,他苦于其他杂志连载使人阅读不畅,便每期一次登完,往往厚厚一大本只能登一篇文言小说。这是清末民初小说界一个明显的变化。
而小说语言上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浅文言的大量涌现,二是文言的驳杂化,三是用文言叙述现代生活。
随着读者群的扩大,小说杂志的出版,改变了传统文言小说小圈子内的互赠传抄方式,因此,文言小说首先要面临市场化、市民化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吸纳白话的词汇和句法,形成浅白的文言。所谓“浅近文言,就是用典用得少,很少用古字难字,不讲究音调对仗,语法也比较随便,接近于白话,比较容易理解。”[18]这在清末民初的小说期刊中很明显。陈景韩的《路毙》(《新新小说》第2期)是一篇写中国人之间冷漠的短篇小说,塑造了各种“看客”,它的语言就是浅文言:
老病污秽,有一路毙,倒于城厢之内,十字街之路侧。年约七十至八十,骨格(骼)饱受风霜辛苦,容貌极委顿,迫于饥寒疾病,目闭口开,手足卷(蜷)缩不动,然尚有气息。
词句虽保留了文言四字基本句式,但通俗平白。再如徐卓呆的《温泉浴》(《小说林》第7期,1907年)中的描写:
乃而入浴。有顷,见日本女子二人,亦来洗浴,脱裤入水。时某之面,宜嗔宜喜,现不可思议状,两颧色深红,涎涕交下,呆坐水中,目不转睛,钉住二女子雪白的肉身上。及余出浴,二女子亦去。回顾会长某,则仍坐水中,不敢稍动。
全篇基本是文言句式,但亦夹杂着“雪白的肉身”这样的白话句子。在一篇讨论看《月月小说》益处的文章中,作者在谈历史家为何应看小说时说:“将正史一概演成白话,使人家一目了然。”“《八宝匣》和《美国独立别裁史》是记事体的,这两种虽不是白话,文法不甚深,易得要领”[19]。这里提到的两部小说其实都是文言小说,也纳入到白话小说的“通俗”“新民”的轨道中来。
此期文言小说浅白化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长篇文言小说相对短篇来说更多采用浅文言。“长篇小说”是现代概念,旧称通俗小说、演义等,普遍篇幅较长,用白话创作。而当用文言创作长篇小说时,它除了保留文言的句式以外,也要考虑到它的传播效果和“讲故事”模式,所以在写法上会部分采用白话章回体的写法,比如,分章回,并加上对仗的回目,可以称为文言小说的“话本化”。传统的文言小说大多不分章回,因为都比较短,而长篇文言小说如果不分章,就给人冗长的感觉,甚至有的洋洋上万言不分段落,排山倒海的文字扑面而来,让人不能卒读。
此期文言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驳杂化。一篇小说之内,文白夹杂,汉英夹杂。文白夹杂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其一,正文用文言的,而人物对话用白话的。典型的如包天笑、徐卓呆的短篇小说《无线电话》(《小说时报》第9号),模拟死去的丈夫与活着的妻子通电话谈家庭的未来规划。叙述用文言,而打电话的内容则全用白话,很能体现作者对模拟人物声口的艺术追求。其二,正文用白话,而书信、日记、文告用文言的。如《泰西历史演义》(洗红庵主演说,1903年5-10月载于《绣像小说》)中有的人物对话用文言:
华盛顿先到演武场中,整齐队伍,仿佛凯旋的模样,然后登坛设誓,对着众人道:“此后一切,必揆诸道义,而后施行,愿天降佑,俾称厥职。”
及至到了议会里,又对着众人道:“今幸承诸君推荐,辱此重任,然藐躬不肖,恐不能相称,愿诸君想与提挈,幸甚幸甚!”(第26回)
而他母亲的话又用白话:
(华盛顿将做大总统的话,告诉他母亲。)他的母亲非但不喜,倒反潸然泪下,说:“我的年纪一天老一天了,况且多病,以后你担了这样大的责任,不能时常回来,恐怕我始终不能见你一面了。”(第26回)
另外,日记、书信用文言,正文用白话的例子更多。如徐枕亚的《毒》(《中华小说界》第1年第6期),正文用白话,书信用文言;远生的《海外孤鸿》(《小说时报》第18号)引言用白话,书信的内容用文言。这些都反映出当时作者对文言白话的不同美学意义还没有清楚的认识。
还有一种很难分清文言白话的混用情况,如《扫迷帚》(壮者著,载《绣像小说》第43期至52期,1905年)第一回中的一段:
某年七月上浣,忽然买舟往访,到岸时日已西沉,相遇之下,略叙寒暄,即请出嫂氏相见,不免治馔款待。那资生平日见他书信来往,诸多迷惘,思趁此多留几日,慢慢的(地)把他开导。岂知心斋之来,也怀着一种意见,他不晓自己不通透,反笑资生狂妄,变欲乘机问难,以折其心,一闻挽留,正中下怀。
这些都说明文言白话的应用在小说作者那里开始互相渗透,成为一种过渡的状态。这种混杂状态连当时的有些小说家都很不满意,有人评论《月月小说》刊载的《柳非烟》(天虚我生著)时说:“最特别者为名《柳非烟》之一种,体例则章回不成章回,笔记不成笔记,词句则文言不文言,白话不白话”[20]。他批评的现象并非特例,这也反映了保守的小说家对传统小说文体及语言传统的坚守。
正文用白话,前言、后记用文言的比比皆是,如《爆烈弹》(冷,《月月小说》第16号),《放河灯》(非非国争著,《月月小说》第19号),《泪》(胡寄尘,《小说月报》9卷2号),《断弦》(拜兰译,《小说月报》9卷3号),《面包》(周鹃译,《小说月报》9卷9号),《纪念画》(雏,《小说月报》10卷8号),等等。
清末民初的文言小说也要表现现代生活内容。立宪、戒烟、新学堂,自由恋爱、华工的苦难,官场的腐败以及洋人的骄奢跋扈等,成为小说家最喜欢涉足的题材。传统文言小说以言情、史传、神怪见长,表现超现实的内容较多,即使有反映现实的也以象征、以神怪狐鬼出之。而清末民初的文言小说表现时事内容时出现了新变化。这方面,林纾的长篇文言小说也是很好的例证,郑振铎就有精到的论述:“中国小说叙述时事而能有价值的极少;我们所见的这一类的书,大都充满了假造的事实,只有林琴南的《京华碧血录》《金陵秋》,及《官场新现形记》等叙庚子义和团,南京革命及袁氏称帝之事较翔实;而《京华碧血录》尤足供给讲近代史者以参考的资料。”[21]当然,这种趋势并不是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民初至五四前夕,由于鸳鸯蝴蝶派的兴盛,文言小说言情一派蔚为大观,但即使言情,亦穿插较多时事及革命内容,《玉梨魂》写何梦霞参加武昌起义即是明证。
这种反映现实的文言小说以旧瓶装新酒,使文言小说的语言状况发生一些改变。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新词汇的增加,这里举吴趼人的《预备立宪》为例。作者加了说明,故意让人以为是翻译小说,“恒见译本小说,以吾国文字,务吻合西国文字,其词句触于眼目者,觉别具一种姿态。”“偶为此篇,欲令读者疑我为译本也。呵呵”[22]。作者沾沾自喜的正是其新词汇(“西国文字”)较多,在短短两千字的小说中粗略统计就有如下新词:预备、趣味、真相、光明、国民、下午二点半、朦胧、天文台报告、超越、数百磅之铁锤、脑筋、思想之能力、问题、思想力、记忆力、敏捷、幸福、精神、鸦片原料制成之药品、海滨、吸受新鲜空气、商招(商店招牌的意思)、各种器具、示意、购买、头彩之希望、开彩、买彩票、举动、乘汽车、习惯、被选及选举之章程、政体、纳税、国家、选举权、投票、资格、议员、购置、经营、事业、势力、目的、投身均贫富党扩张社会主义、命运、见解、代表、全体、知识,等等。这样以新词为时髦的小说很普遍,这一方面是出于追新的心理,另一方面也适应表现新生活的现实需要。刘半农在1916年创作的文言小说《我矛我盾》,叙述两件外国的事情,也出现诸如雪茄烟、面包、牛酪、新闻纸、广告牌等新式事物名称。
当然,文言小说语言的这些新变有其积极的一面。首先,文言的浅白化,可以丰富白话的书面语言,事实上,有许多文言语汇融入现代汉语之中。其次,部分文言小说注重艺术性,文采斐然,继承了古典小说的清雅之气,这对白话小说向现代小说转型有借鉴作用。但是,大量低水平重复,失去了传统的“雅”,又不能尽“俗”,随着时代变迁的步伐日益加快,文言小说由于其自身的语言特点,已不能适应现代生活变革的脚步了,这种大繁荣,注定只是一种回光返照,成为中国小说古典时代的最后回声。
参考文献:
[1]陈迪强.“五四”文学革命之前的小说语言状况考论——以1914—1916年的小说杂志为中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9):37-45.
[2]严家炎.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3.
[3]鲁迅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64.
[4]包天笑.小说大观·例言[J].小说大观,1915(1):3.
[5]徐念慈.余之小说观六[J].小说林,1908(10):1-5.
[6]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折[G]//张之洞全集(三).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1766.
[7]章太炎.演说录[G]//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02.
[8]曹聚仁.文坛五十年[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7:97.
[9]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M].上海:上海泰东图书局,1920:2.
[10]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M].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25.
[11]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G]//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174.
[12]鲁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73.
[13]林纾.林纾选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40.
[14]恽铁樵.《李芳树传》评语[J].小说月报,1917(7):56.
[15]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290.
[16]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3.
[17]韩洪举.林译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52.
[18]袁进.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65.
[19]报癖.论看《月月小说》之益处[J].月月小说,1908(13):12-18.
[20]新楼.月刊小说评议[J].小说新报,1915(5):6-8.
[21]郑振铎.林琴南先生[J].小说月报,1924(11):1-10.
[22]吴趼人.预备立宪[J].月月小说,1906(2):181-189.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Chen Diqiang
(College of Culture Communication,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Dalian Liaoning 116044)
With the weakening of Novel Reform,the unprecedented boom of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appeared before late Qing Dynasty to May 4th.Macrocosmically,these novels still inherit artistic criterion and follow traditional rhetoric.Meanwhile,new changes appeared.For example,classical translation novels,parallel novels,and classical serial novels have increased.Different from the expressions of personal feelings and legends in the past,this period of novels contain much broader social affairs,and languages present new features including superficiality,intricacy and new words.
the Late-Qing-Early-ROC Period;classical Chinese novels;inheritance;innovation
I242
A
1674-5450(2017)05-0089-06
【责任编辑:赵 践 责任校对:王凤娥】
2017-06-03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5YJC751003)
陈迪强,男,湖北襄阳人,大连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