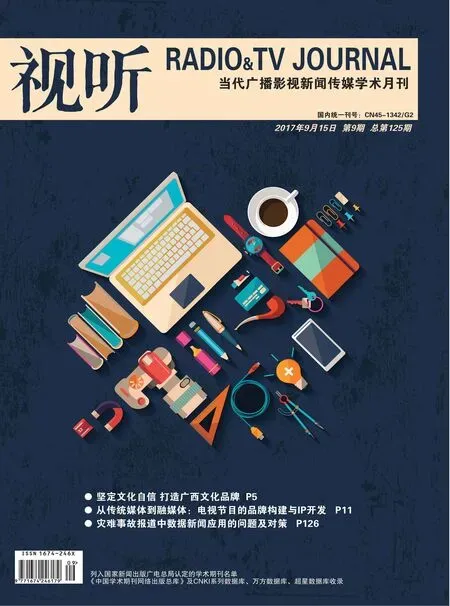浅谈朗诵中情声气的驾驭艺术
□布艺鹏
浅谈朗诵中情声气的驾驭艺术
□布艺鹏
本文从播音主持和艺术概论的理论体系出发,对朗诵活动的语言驾驭艺术进行了三个方面的论述:即情声气的和谐运用、内容和情感如何统一、坚持恰切的态度立场。
朗诵;情声气;具体感受;态度立场
朗诵通过适宜的声音语言、身势语言、表情语言和背景音乐等的综合表现,用典型化和艺术化的手法来集中和表现特定的主题和情感。这个过程中我们主要从情声气的关系和恰切的态度立场着手,以达到再现丰满形象、创造优秀朗诵作品的目的。
一、情感、语气和气息
在语言艺术的操作过程中,情、声、气三者密不可分。所谓“气随情动,声随情出,气生于情而融于声”,这就是情声气之间的关系。在语言艺术创作中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只有情、声、气结合起来,才能使朗诵者更好地传情达意,受众更加清晰地感觉到朗诵者要表达的感情。《经典诵读》是广西电台文艺广播FM950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要求下,在2016年底创办的一档诗词鉴赏精品栏目,本人在其中既是主持人,也是诵读者。两种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要求。主持人的角色,主要是起到串联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作为主持人,主要是要做到平实、亲切、自然,说人话,接地气。比如在第一期中,有这样一段主持词:1884年,泰戈尔离开城市来到农村,开始了关于自然和故土的创作。作为一个诗人,泰戈尔崇尚纯真和简朴,企望自己的生命“简单、正直像一枝苇笛”。这是对泰戈尔一段生活的描述,既是平常的,也有诗人不平常的理想。如何体现这种平常中的不平常?笔者特别注意首先要控制语速,这是因为《经典诵读》是一档夜间节目,如果语速过快,就会给听众造成紧迫感。第二,要控制情感,不能过于高涨,这样容易让听众觉得主持人是在端着,造成高高在上的印象。尤其是印度诗人泰戈尔是一位著名的诗人,更要表现出他普通的一面,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觉。第三,气息要平稳、流畅。主持过程中要控制好气息的强弱,不能忽大忽小,给听众造成急促感。
二、从“触景生情”到“声随情出”
朗诵文本创作和朗诵操作的过程中情感的作用至关重要。首先,在文本创作中创作主体“触景生情”,产生出带有强烈情绪色彩的感受,从而为文本创作产生心理定势和情感动机。其次,当朗诵者面对现成的朗诵文本时,如果受到情境的感染也会产生相应的心理感受,从而影响到朗诵操作的效果。再次,情感朗诵是语言驾驭过程中的必要情感准备。最后,情感不能逾越内容,而应该有所控制,要让情感服务于所要创作和表现的内容。优秀的语言艺术创作者要致力于“声随情出”,实现情感与内容的有机统一。
2016年,FM950创作的广播剧《父爱如歌》获得了广西人民政府颁发的文艺创作最高奖——广西铜鼓奖。本人在剧中担任演员及配音工作,扮演的角色是一位对老父亲学开车没有耐心的儿子。比如:有句台词是:“爸,我们再来一次!”短短的一句台词,既要表现儿子对父亲的惭愧,又要表现对于父爱的向往。这就要求做到“融情于景,触景生情”,真切地感知其中的情感变化,然后将语言充分融入其中,自然流畅地表达出来。
三、坚持恰切的态度立场——既要体现时代感,又要把握分寸感
播音语言的特点可概括为“三性”“三感”六个特点,即规范性、庄重性、鼓动性和时代感、分寸感、亲切感。作为语言艺术的朗诵活动,其语言特征也符合上述“三性”“三感”,其中,朗诵艺术要尤其注意做到紧随时代特色和坚守态度分寸:一方面,时代感是指创作主体对于所处时代的精神和氛围的认知和把握;另一方面,时代感要求朗诵创造者胸襟开阔,应和时代的脉搏,高扬主旋律。作为新时期的语言艺术,在内容上朗诵更应体现时代精神,充满人文关怀。
2016年,本人的播音作品《一个将军的远征》获得了广西新闻奖一等奖。这是一篇弘扬主旋律的作品。在播音过程中要将语言和播讲状态富有代入感,同时又要把握好分寸。不能一味地进行“宣读式”的高声赞美,更不能从头到尾地进行阐述。要讲究情感的合理分配,根据具体内容进行表达,做到“该扬的时候扬,该抑的时候抑”,使整个作品富有层次感。以戴安澜将军的《七绝·远征》为例:万里旌旗耀眼开,王师出境岛夷摧。扬鞭遥指花如许,诸葛前身今又来。策马奔车走八荒,远征功业迈秦皇。澄清宇宙安黎庶,先挽长弓射夕阳。
戴安澜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的抗战将领。本人作为朗诵者,既要传达出戴将军视死如归的抗战决心,又要照顾到当代人的收听习惯,不能一味地讲究高亢激昂,而主要体现出将军作为一个爱国志士的深切情怀,突出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情感的表达。在朗诵过程中,要融入强烈的爱国情怀,流露的是必胜的信念,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每一句的处理上,要干净利落,不能拖泥带水。
四、结语
总之,在朗诵活动中,语言驾驭艺术分解为朗诵文本创作和朗诵行为操作两个步骤,其中前者体现的是语言艺术的表现性,应该同时把握塑造丰满的形象、运用厚积爆发的情感和把握恰切的态度立场三个方面;后者体现的是朗诵艺术的表演性,应该着重把握运用厚积薄发的情感和把握恰切的态度立场。我们通过对播音主持和艺术概论的学习掌握,可以迁移运用到朗诵艺术之中,用以指导朗诵的语言驾驭之道。
(作者单位:广西人民广播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