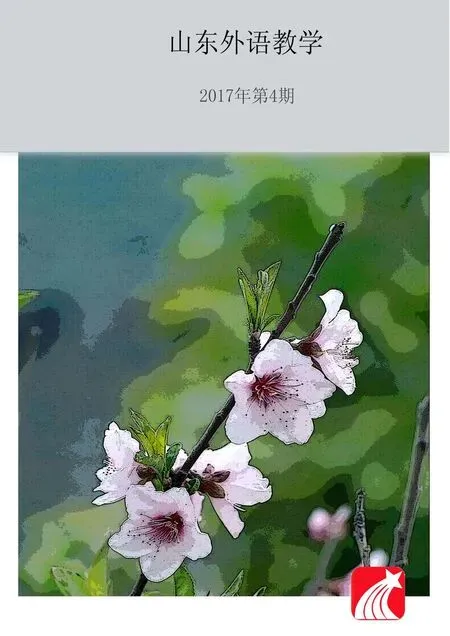中国科技典籍出版“走出去”的路径探索
——以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为考察中心
李伟荣, 刘湘苹
(湖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410082)
中国科技典籍出版“走出去”的路径探索
——以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为考察中心
李伟荣, 刘湘苹
(湖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410082)
李约瑟主持编纂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在中外科技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自出版后得到多方面的研究,却鲜少从出版视角来探析这一巨著。本文从选题缘起与规划进展、编辑出版特色、出版的现实意义与海内外传播影响及其局限性、对出版“走出去”的启示等四个方面对李约瑟这一著作进行了详尽剖析,为中国科技典籍出版“走出去”的路径进行了有效探索。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出版;科技典籍;中国文化“走出去”
如果说中国古代科技在20世纪才真正走向世界,国际著名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的首创之功不可忽视。自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导论》1954年出版以来,全世界的学者纷纷关注并从各种视角探析李约瑟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成就,不过鲜有学者从出版的角度来探讨这套著作的重要意义。而且,论者在讨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路径时一般都强调文学因素,可喜的是有论者已经注意到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非文学思维(韩子满,2015:77-83),这种思路跟本文的初衷可谓不谋而合。本文尝试以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为考察中心,探索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走出去”的有效路径。
1.0 选题缘起与规划进展
1.1 选题缘起
李约瑟选择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庞大的项目,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早期,他是一位成功的生物化学家和胚胎学家,热衷于收集并研究这方面的文献和历史,并于1931年和1942年分别出版三卷《化学胚胎学》(ChemicalEmbryology)和《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BiochemistryandMorphogenesis),这种专业训练和研究无疑锻炼了李约瑟的科技史思维。外因主要是他接触到中国文化并与欧洲科学发展史进行对比,便产生了很多疑问,他想通过研究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解答这些疑问(潘吉星,1999:300-301),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1)鲁桂珍向李约瑟介绍中国古代医药成就,李约瑟由此对中国科技史发生兴趣,并开始学中文,阅读各种有关中国的著作,注意到中国古代有些科学发明和发现长期领先于西方(潘吉星,2003:113-114)。(2)跟时任剑桥大学汉语教授哈隆(Gustav Haloun,1898~1951)学习《管子》。《管子》中谈到某些海洋动物受到月亮周期的影响,其大小随着月亮的盈亏而增大或缩小,李约瑟发现这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完全相同(王钱国忠、钟守华,2012:88)。因此,他在接受英国政府的邀请去重庆参加文化与科学合作代表团之前不久,对于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计划已经有了一个大体的轮廓。(3)1942年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他主持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工作期间与我国科学界各领域的杰出人士(如竺可桢、郭沫若、傅斯年、华罗庚、闻一多和钱宝琮等)进行了密切接触,并得到他们的帮助,又在中国各地进行实地科学考察(Needham,1954:11-14)。
1942~1946年李约瑟在中国工作期间,开始了解中国文化和文明,认识到有许多关于中国文明的东西需要学习,也有机会时刻四处向中国数学家、医务人员、化学家、工程师和物理学家们学习。这一切使他能够了解有关文献,为编写一部中国科学史、技术史和医学史等的系统专著提供了充足条件。
1.2 规划进展
最初,李约瑟认为只需要写一本薄薄的书。1948年5月15日李约瑟致函剑桥大学出版社编辑罗伯特(S. C. Roberts),提交自己写作并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计划。因为出版社强调这种书不能超过一卷,所以李约瑟原计划此书的篇幅在600至800页之间。同时,李约瑟介绍并说明自己在科研工作经验、科学思想史知识背景、中文阅读水平和中国生活经历等多方面都具备这一撰写工作所需要的能力。5月22日,出版社复函李约瑟,接受了他研究和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计划(Winchester,2008:170-173)。
然而,一旦开展工作,他们便发现这一工作与其初衷大不相同,因为一本薄薄的小书根本无法涵盖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全部内容。因此,李约瑟后来将《中国科学技术史》从最初计划的1卷扩展为7卷,每一卷视具体情况再分几部分,用比较方法讨论中国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Winchester,2008:172)。第一卷大体为概论,以便让读者熟悉由科学、技术和医学所构成的一个完整文化体系;第二卷至第五卷主要涉及中国哲学、数学、天文学、气象学、地球科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科学等诸多科学领域;第七卷主要从东西方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出发尝试回答两个主要问题:(1)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西方所谓科学革命中才彗星般起飞?(2)1到5世纪间,在取得有关自然的知识并在多方面用之以造福人群这一点上,为什么东亚文化比欧洲更为有效?(李约瑟,1999:419-421)这两个问题,世称“李约瑟命题”(Needham Thesis)。
自1954年到2008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共7卷大部分已出版。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原定计划出版7卷共28分册,目前除《军事技术:射击武器和骑兵》(第5卷第8分册)、《纺织技术:织布和织机》(第5卷第10分册)、《盐业、墨、漆、颜料、染料和胶粘剂》(第5卷14分册)以及《园艺和植物技术(植物学续编)》(第6卷第4分册)未出版外,其他著作均已出版。
由于读者使用该丛书不方便,本书的主体部分由李约瑟委托科林·罗南(Colin A. Ronan)改编成一套6册的简编本,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简编》(TheShorter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李约瑟,1999:427)。这一套简编本已译为中文,书名定为《中华科学文明史》,200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 编辑出版特色
2.1 海量而翔实可靠的资料支撑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完成首先仰赖于资料的穷尽式收集。如果没有详实而可靠的资料,这一著作的重要性就会大打折扣。李约瑟收集的资料既有直接资料,也有间接资料。直接资料主要来自中国的原始资料,由于中国印刷术的出现远远早于欧洲,所以极大一部分是已经印成书的,但偶尔也有抄件,例如在敦煌发现的道教和医学的残卷、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汉代书籍、在福建发现的造船手册等。间接资料则指那些已写成的某一门科学的发展史的书籍,这些几乎都是用汉语写的,而且涵盖的学科不多,只有数学、天文学、昆虫学和医学等的发展史著作,而几乎没有机械工程、植物学、动物学或药物学之类的发展史著作(李约瑟,1999:423)。鲁桂珍曾赞扬李约瑟似醉似痴地力求完全,不遗余力地到处搜寻资料和线索,例如在生物学方面,往往最冷门的刊物中会刊有很有价值的论文,须予注意;在科学史方面,又常常能从最想不到的书籍、论文,甚至诗歌、民谣中得到启发(鲁桂珍,2012:20)。
李约瑟也指出,典籍远非唯一的资料来源。另一个很大的来源是图像、图片,或是刻在坟墓或庙宇的石碑上,或描绘在画梁上,或作为书中的木刻插图,或其他翻刻的图片等等。还有一个来源是保留下来的传统,这些传统必须现在仍然通行,否则,单凭书上的记载,有不少在今天已无法了解。此外,与非中国典籍平行的,还有人种学这一无限广阔的天地,包括旅行家的游记(李约瑟,1999:423-424)。
根据潘吉星(1983)的记述,剑桥大学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不仅仅是欧洲最大的有关中国科学史著作的藏书中心,而且还是欧洲最大的有关中国科学史研究中心。除李约瑟和鲁桂珍外,常在此工作的人员还有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其他合作者,如罗宾逊(Kenneth Robinson)、白馥兰(Fransisco Bray)、司马克(Michael Salt)和卜鲁(Gregory Blue)等(潘吉星,1983:175)。
2.2 运用比较研究的撰写原则
李约瑟认为科学史有多种写法:有初级的、有逸话式的、书目式的、详尽介绍式的和社会背景叙述式的。不过,李约瑟认为这些方法都不适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而认为布律内(Brunet)和米里(Mieli)所著《科学史》、辛格(Charles Singer)论草本植物和光学的专著以及卡特(T. F. Carter)所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等书最接近于他理想的撰写模式(Needham,1954:7-8)。因此,李约瑟在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时主要采用比较研究法。因为,当《中国的科学与技术》一卷卷编下去的时候,他发现孤立地研究中国的科学技术显然是行不通的,必须在每一阶段都同所有其他民族文化中所发现的东西进行比较,包括更早的、较晚的(一般是较晚的)和差不多同时的。例如当我们考虑计时器中的擒纵器(escapement device)的发明时,只知道它由僧一行和梁令瓒于720年左右创制,并由苏颂和韩公廉于1085年左右完善还不够,还应该知道欧洲到1320年左右但丁时代才开始用机械来计时(鲁桂珍,2012:20)。
2.3 跨国军团式的作者队伍
既然这一项目如此庞大,那么仅靠李约瑟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李约瑟本人确定《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著计划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集体合作的事业,因为在他看来,任何学者单靠个人是不可能精通中文和西文的有关专业文献的。当写作计划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开始实施时,不仅王铃,而且何丙郁(Ping-Yoke Ho,1926~)、罗宾逊(Kenneth G. Robinson)和鲁桂珍等都发挥了重大作用。特别是鲁桂珍于1957年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返回剑桥协助他工作。李约瑟后来明显感到,写作的内容十分繁复,以致这个小组不堪负担,因此吸收了更多的合作撰稿人,并分工负责剩余各卷的工作。统计而言,全世界共有29位国际知名且学有专长的合作者参加了这一卷轶浩繁而任务繁重的写作计划。
具体而言,王铃在中国史学研究的专业训练、中国文献的英译、原始资料的发掘以及各种索引和编目等繁琐的图书馆工作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李约瑟认为,如果没有王铃合作,那么这部书的出版可能会推迟很久,而且会出现更多错误(Needham,1954:14-15)。
而何丙郁的贡献则与此不同。他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为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积累了丰富而有价值的资料,也不仅在于为《中国科学技术史》撰写了著作(刘兵,2003:34,40-41,71,88-89),而更在于他出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以来为李约瑟研究所筹集的款项。这些款项主要用于:一、为研究所运行以及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提供经费,二、资助中国内地从事科技史研究的学者到剑桥攻读博士学位或进行访问,三、资助和推行“龙腾”计划(何丙郁,2007:127-162)。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李约瑟年事已高,无法亲自撰写每一分册,所以从第5卷开始邀请全球各学科领域的顶尖学者按李约瑟设计的总的指导思想及体例进行写作,再由李约瑟审定。除了李约瑟与鲁桂珍分别为该丛书的正副主编之外,邀请撰写的专家分别有王铃、钱存训、何丙郁、黄仁宇、黄兴宗、郭郛、李家治、席文、白诗朗(John Berthrong)、傅汉思(Hans Vogal,1916~2003)、卜正民(Timothy Brook)和罗宾逊等人。因此,这是实实在在由英、中、美、德、法、加等不同国籍学者组成的“跨国军团”,正是这一“跨国军团”才保证了该丛书的高质量。
3.0 出版的现实意义、海内外传播影响及其局限性
3.1 出版的现实意义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撰出版具有非常巨大的现实意义。第一,这套著作成功地向世人证明,在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兴起之前,中国早有了自成体系的科学技术,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影响巨大;第二,这套著作通过详尽的比较分析,非常全面地向世人尤其是西方人展示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也详细阐明了它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互相理解,从而推动了国际范围内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第三,李约瑟通过史料的开掘、整理、研究与利用,创造性地把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中国思想发展史、社会经济发展史等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将中国科学技术史提到了认识论的高度来阐发。可以说,这套著作的编撰出版,让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本来知之甚少的知识领域即中国科学技术史有了较为完全的理解,各国之间与各民族之间从而能够通过交流在科技领域相互促进,全球科技因融汇了各国各民族间的精华而得到发展和创新,从而得到进步。
3.2 海内外传播影响
这套丛书自出版以来,就在全球不断发挥着广泛、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如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1894~1986)、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ammel,1884~1975)和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等纷纷撰文对李约瑟这一著作表示赞赏。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在伦敦的《观察家报》(TheObserver)如此评价这部书:“这是一部打动人心的多卷本综合性著作……作者用西方术语翻译了中国人的思想,而他或者是唯一一位在世的各种资格胜任这项极其艰难工作的学者。李约瑟博士著作的实际重要性,正如它的学术价值一样巨大。”叶企孙(1898~1977)则在《科学通报》上指出“全球的学术界将通过这部书而对于中国的古代科技得到全面的清楚了解”(王钱国忠、钟守华,2012:158-161)。可以说,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极大地改变了西方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局面。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1卷《导论》出版后,毛泽东主席曾说:“我们中国人应感到惭愧。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知识那么丰富,包括对世界有巨大影响的三大发明,我们中国人自己不写,让英国人来写,而且写得那么好!”(汪德耀,1993:25)因为这部巨著非常重要,所以出版后也受到中国科技界的重视,在国家层面组织力量对其进行翻译,并于1975年由科学出版社以7分册的形式将原著第1、3卷翻译成中文而得以出版。台湾地区也翻译出版了这套著作。李约瑟倡导在全世界召开国际中国科技史讨论会,从1982年开始先后在比利时、香港、北京、澳大利亚、美国、英国、深圳、德国、哈尔滨、南宁、北京等地成功举办了11届(徐昕,2007:37)。
由于《中国科学技术史》后来出版的每一卷和每一分册越来越精彩,所以每一分册一出版,各国竞相翻译,目前已有10余种语言(汉、法、德、日、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和丹麦语等)的译本或节译本,由此可见这一套著作在全世界是多么受重视。
3.3 编撰的局限性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著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他基于生化学家的立场设计并撰写该著作,自诩为唯物论者、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笃信宗教,宗教信仰使他的唯物观念在某些地方相互抵牾,不过这是李约瑟思想的两大支柱。李约瑟由此展开他的全套研究计划,因而其研究计划带有先天性的缺陷,由此招致了杨联陞、何炳棣、李济、郝大维(David L. Hall)和安乐哲(Roger T. Ames)等学者的批评(王钱国忠、钟守华,2012:160-169)。另一方面,李约瑟采用西方对自然、应用科学的分界原则与纲领作为自己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指导原则,他完全用西方科学的分类来研究中国的学问,遭到席文(Nathan Sivin)的激烈批评(Nakayama & Sivin,1973:xix-xxv)。何丙郁指出,如果要讨论中国的传统科技史,那么首先需要考虑中国古人所理解的自然界问题,也要充分考虑中国古人是如何利用他们对自然界的理解的,例如宋代理学家张载、邵雍、朱熹等对于自然现象,他们都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来对自然现象进行解析(何丙郁,2007:105-106)。
4.0 对出版“走出去”的启示
何丙郁提到一个事实,李约瑟并非中国科技史的先驱者,因为20世纪20、30 年代,一些中国科学界老前辈和外国科学史家在这方面已有相当的贡献。可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出版前,一切中国科技史研究成果并未唤起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科技史的注意。而相反的是,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书,连第一卷尚未出版,就已受到国际,尤其是英国科学界和汉学家们的注意(何丙郁,1996:94-95)。综合而言,关于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撰写、出版与影响的考察,对于我国古代科技典籍出版“走出去”有如下五点启示:
4.1 选题策划立足创新、视野宽广、沟通古今中西
《中国科学技术史》这套著作之所以在全球具有巨大的影响,跟这部书立足创新、视野宽广、沟通古今中西的特点是分不开的。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在世界上首次以令人信服的海量史料和证据对四千年来中国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全面的历史总结(潘吉星,1999:306)。到目前为止我国学者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视野还没有人能超越李约瑟,因为李约瑟的著作以比较方法向世人展现出了东西方文明的广阔历史背景(何丙郁,2001:63)。因此可以说,《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出版对国内科技史的研究有启发意义,在当今全球化发展背景下,沟通古今中西的翻译出版精品,在文明互鉴与文化交流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4.2 明确读者定位、由世界一流出版社出版
李约瑟坦率承认,《中国科学技术史》不是为汉学家也不是为一般读者而写,其目标读者是一切受过一定教育的人,他们对全人类文明史有关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与技术发展史,尤其是对欧亚两洲的文明比较感兴趣(Needham,1954:8)。也就是说,《中国科学技术史》不是单纯的学术著作,而是有关中国科学的教育普及性读物,读者范围较为广泛,这有利于科技文明的传播和交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书是由世界一流学术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该出版社在整个西方学界名闻遐迩且深受重视,经过该社出版的书可说是一登龙门,身价可望大大提高。20世纪50 年代剑桥大学的物理和生物两个学科在世界上遥遥领先,更提高了该出版社科技出版物的品牌身价(何丙郁,1996:94-95)。
4.3 加强中外学者、译者的团队合作
李约瑟兼具科学家和编辑的双重身份,他有一定的科学素养,熟悉欧洲科学史,体验过中国人的生活并且有机会以科学家的身份在中国各地旅行和考察,得到了大量中国科学家和学者的指导,在研究和撰写过程中得到几十位亲密合作者的帮助(Needham,1954:6-8)。正如前文所说,李约瑟的重要合作者,包括王铃、钱存训、何丙郁、黄仁宇、黄兴宗、郭郛、李家治、席文、白诗朗(John Berthrong)、傅汉思(Hans Vogal,1916~2003)、卜正民(Timothy Brook)和罗兵逊等众多学者,他们在收集积累一手资料、承担各章翻译撰稿任务、提供出版经费等方面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4.4 利用考古新发现、融汇科技与人文,充实和拓展我国古代科技典籍的研究与出版内容
近几十年来中国大陆考古学的出土文物已经引起国内外科学史研究者的注意。李约瑟非常重视考古学的新发现。他每次访问大陆,务必跑去北京考古研究所,探听新出土文物的最新介绍。今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也该与考古学的新发现共同迈进。何丙郁认为,具备科学的根底和人文的素养都可以研究科技史。目前,中国科学对东亚各国的影响、东西方交流等论题仍乏人问津,所以还有研究空间,新进学者可多方开拓领域(何丙郁,1999:372-394)。我们应该将人文和科技融会贯通,利用新的考古发现,充分拓展我国古代科技典籍的研究范围和方法,进而推动我国古代科技典籍的国际出版。
4.5 通过各种途径筹集出版经费,推动中国科技典籍的海外出版
像《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的大型丛书,持续时间长,参与撰写的专家多,而且牵涉到几十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世界级专家,充足的出版经费无疑是它能够成功的重要保障。为此,李约瑟从一开始便在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到社会上筹措出版经费,包括剑桥大学出版社本身的投入和各大财团(例如剑桥东亚科学史信托会和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等)以及合作学者的慷慨解囊。何丙郁接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后,其主要任务也是为丛书的出版多方筹措经费。因此,中国科技典籍的翻译出版需要寻求政府主管部门的政策支持,借助于国内外知名出版社和社会民间力量(协会、基金会等)以及学者个体的资金资助和版权合作,通过多主体、多元化的合作方式积极推动中国科技典籍的海外出版。
5.0 结语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出版后,对我国学者影响很大,让我国学者认识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有着充分的世界性意义,这无疑会激发我国学者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上的研究。我们已将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直接翻译过来,在此基础上,我国学者还组织撰写并出版了多套系列著作,大都是国家重大出版工程项目,并约请各相关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和著名专家撰写,然后由国内外知名出版社出版,例如卢嘉锡主持的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的29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杜石然等编著的2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江晓原主持的5卷本《中国科学技术通史》以及郭金彬和徐梦秋主持的20卷本《中国科学思想研究文库》;同时也有类似的著作在海外知名出版社出版,例如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Verlag)出版的由路甬祥担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AHistoryofChineseScienceandTechnology)。这些著作的出版说明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一点,那就是,尽管李约瑟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始于20世纪中期,而且有着其自身的不足,但是全世界依然还没有哪一套著作能够超越并取代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该套著作的全球性视野和比较研究方法在撰写中的应用。
目前,中国文化正处于全面“走出去”的大好局面。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科技典籍“走出去”一方面能够让世人认识到中国科技文化的精深与博大,另一方面则通过比较的方法让中国人自己认识中国古代科技的优长与劣势,从而客观认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世界性意义。笔者认为,中国典籍走出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形成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合力(李伟荣,2016:73)。中国科技典籍走出去无疑也得如此,方能取得最佳效果。
李约瑟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自从1954年第1卷出版至今,60多年过去了,其优点我们当然无法忽视,但因为新发现层出不穷,新材料、新视角也不断出现,所以我们应该借鉴李约瑟的长处,吸取目前世界科学技术史的最新方法,结合考古的新发现,立足世界,聚焦中国,策划并出版超越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著作,让中国科技典籍更好地“走出去”。
[1] Nakayama, S. & N. Sivin (eds.).ChineseScience:ExplorationsofanAncientTradition[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73.
[2] Needham, J.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VolumeOne.IntroductoryOrientation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3] Winchester, S.TheManWhoLovedChina:TheFantasticStoryoftheEccentricScientistWhoUnlockedtheMysteriesoftheMiddleKingdom[M].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8.
[4] 韩子满.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非文学思维[J]. 山东外语教学,2015,(6):77-83.
[5] 何丙郁. 如何正视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研究[J].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6,(2):94-95.
[6] 何丙郁. 李约瑟研究所与中国科技史研究[A]. 王钱国忠编. 李约瑟文献50年(1942~1992)(上、下)[C].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389-394.
[7] 何丙郁. 民国以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李约瑟与中国科技史. 何丙郁中国科技史论集[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8] 何丙郁. 学思历程的回忆:科学、人文、李约瑟[M].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7.
[9] 李伟荣. 20世纪以来中国典籍出版走出去的回顾与思考[J]. 中国出版,2016,(23):70-73.
[10] 李约瑟. 中国的科学与文化[A]. 王钱国忠编. 李约瑟文献50年(1942~1992)(上、下)[C].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416-428.
[11] 刘兵. 若干西方学者关于李约瑟工作的评述——论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编史学问题[J]. 自然科学史研究,2003,(1):69-82.
[12] 鲁桂珍. 李约瑟的前半生[A]. 王钱国忠,钟守华编著. 李约瑟大典(上、下)[C].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16-42.
[13] 潘吉星. 英国剑桥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访问记[J]. 中国科技史料,1983,(2):75-76.
[14] 潘吉星. 李约瑟——沟通东西方各民族与科学文化的桥梁建筑师[A]. 王钱国忠编. 李约瑟文献50年(1942~1992)》(上、下)[C].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289-313.
[15] 潘吉星. 李约瑟博士如何研究中国科学史[J]. 世界汉学,2003,(2):113-119.
[16] 汪德耀. 我所认识的李约瑟博士——兼谈中国科技史重要性[A]. 周济主编. 八闽科学技术史迹[C].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16-29.
[17] 王钱国忠,钟守华编著. 李约瑟大典(上、下)[M].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18] 徐昕. 第11届中国科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4):37-41.
(责任编辑:陈幸子)
Approaches to “Going out” of the Public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Classic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cusing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Joseph Needham’s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Series
LI Wei-rong, LIU Xiang-p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410082, China)
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Series, coauthored and coedited by Joseph Needham, has been a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oth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t has been investigated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since its publication, but rarely research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shing. This essay scrutinizes it from four aspects: the origin of the project and its plan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diting and publishing;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publication; the influence both in China and in other countries; and its inspiration to “going out” of the public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classic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aim is to provide effecitve approaches to publication which hepls Chinese anci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lassics to “go out”.
Joseph Needham;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Series; publish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ooks; Chinese culture “going out”
10.16482/j.sdwy37-1026.2017-04-012
2017-05-28
本文为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李约瑟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5YBA093)和中国翻译研究院2015-2016年度重点“中国传统经典文化对外翻译与国际传播调研报告”(项目编号:2016B12)的阶段性成果。
李伟荣(1973-),男,湖南攸县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比较文学、西方易学研究、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刘湘苹(1994-),女,湖南衡阳人,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2016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
H159
A
1002-2643(2017)04-009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