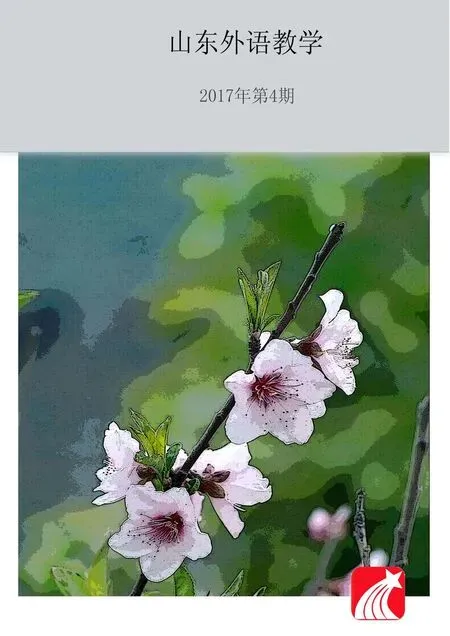文化旅行视域下的《道德经》英译图景剖析
辛红娟
(宁波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文化旅行视域下的《道德经》英译图景剖析
辛红娟
(宁波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出现旅行文化研究的趋向,学者们除了对“旅行”进行哲学上的阐发,还从文化接触的角度研究旅行中文化“接触地带”所彰显的文化固守、文化冲击和文化认同。典籍文献翻译中文化内核语词的翻译,常常成为异质文化交锋的“抗争之场”。本文从文化固守、文化冲击以及文化认同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典籍《道德经》在英语世界一百五十年来的译介与传播情况,希望此类典型个案文本的溯源性研究能够为当下大热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启迪与思考。
《道德经》;文化旅行;翻译研究
《诗》《易》将“旅”定义为“行旅、商旅”,《尔雅》中有“旅,途也”,从这些早期的定义中不难看出,“旅”字最初即有“距离跨越”的意味。后来,“旅”字在历史使用过程中又引申出“客”、“客居”等意。《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羁旅之臣,幸若获宥……所获多矣。”杜预注:“旅,客也。”《说苑·辨物》文“不群居,不旅行”中最早将“旅”、“行”作为一个词语使用,意思是“不要与众同行”(“旅”是“众多”、“众人”的意思)。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旅行”一词,直到《礼记·曾子问》才出现:“孔子曰:三年之丧练,不群立,不旅行”。“旅行”即“到外地出行做客或游历”,也即“失其本居,而寄他方”(宋代朱熹,《易·旅卦疏》)。至此,“跨越”、“从众”与“客居”始成为“旅行”的题中之义,本文对翻译的文本旅行、文化旅行的剖析,对典籍文本的跨文化旅行的梳理,正是基于这一定义展开的。
1.0 旅行作为文化“抗争之场”
旅行广泛地存在于人类历史中,并在一些特定的时期和阶段对历史中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产生了重要而独特的影响。世界上几大主要文明的产生与发展,均得益于因旅行而生的与其他文明的广泛交流。近世以来,旅游、旅行研究学者多从社会学和经济学意义上探讨旅游概念,分析旅游系统中诸多要素、属性、对象或过程。这些发生学意义上的阐释,是文化学者对旅行概念进行引申探讨的根基,文化学意义上的旅行是其发生学意义上的“喻词”表达法,共享发生学意义上的几乎所有特质。
在文化转向的学术视域下,学者们开始注意到旅行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并开始从形而上层面入手分析旅行之于民族性格和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关系。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学者逐渐拓宽对旅行概念的界定,旅行文化研究出现新的视点。Rojek & Urry(1997:1)认为,旅行成为一个问题的重要原因是,它的含义源自他者,而作为他者的人、文化和文化产物无时无刻不在迁移,因而,旅行的含义也是飘忽不定、变化无常的。C. T. Williams(1998:xii)更是从宏观的高度指出,“人类历史是一个旅行者的故事,一个奥德赛。”当代文化旅行学者郭少棠(2005:35-36)在对中国古代丰富的旅行文化研究的基础之上,将人类的旅行分为三个层次:旅游、行游和神游,其中后两个层次的旅行是形而上层面的距离变迁,促进了人类文化的转化和价值变迁,促生不同的文学想像。人在文化中旅行,而文化和文化产物自身也不断移动,因此,旅行不是简单的空间置换或延伸,而是人类文化进程中复杂而具渗透性的光谱,成为包含文化意味的位移活动,被喻为“穿过另类现代的道路”(郭少棠,2005:5)。在此意义上看来,把中国文化作品按照本土的观念译成外文传递给西方读者,只是旅游(位置转移);西方译者经过自己文化的渗透,添加一些非中国的元素,使之成为易于被本土读者接受的“新质”,才算得上达到“行游”甚至“神游”的境界。“文化意义上的旅行,是旅行主体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中,通过物理世界或形而上世界的迁移而进行的一种目的十分明确的实践活动,在此过程中,旅行主体通过主观的选择、接受或拒斥,在接触中形成对他者文化的想象,融汇出新的文化视野,达成新的文化创造”(辛红娟,2009:149)。
西方旅行哲学认为,人类的“奥德赛情结”使人类始终处于一种“在途中”的状态。人类的这种“在途中”的状态,不断地拓展了人类的想象力,成为文学创作和文化积累的源泉。旅行因而“被提升到哲学的、形而上的高度,成为人类思想的喻词”(辛红娟,2009:150)。旅行,由于跨越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地带”,在带动文化迁移的同时,必定会加剧现实和想象或物质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性张力,成为不同文明、文化之间因文化接触而生成的文化固守、文化冲击的“抗争之场”和主体寻求文化认同的通道(辛红娟,2007:157)。文明交流中的“接触地带”可以是现实世界中的地理空间,也可以是承载着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场域”或精神文化产品。历史上,中国典籍的域外传播和西方文献的汉译与汉传,无不体现着东西方两大文明的冲突、对话和融通。本文拟结合旅行的文化概念,阐释《道德经》在英语世界一百五十年来的译介历史,揭示在各个不同历史文化时期,译者通过翻译选择所彰显的本族文化固守(cultural adherence)、文化冲击(cultural encounters and conflicts)以及由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所达致的文化对话与交融。
2.0 《道德经》英译藏匿文化固守
“旅者,客寄之名,羁旅之称;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谓之为旅”(朱熹《易·旅卦疏》)。对于旅者而言,去往他乡,意味着与本土的疏离,这种疏离造成旅行者困苦劳顿之时倍感精神上的孤独,这种精神上的不适应常常体现在对原有文化的顽强固守。“人类本能遵循着祖先遗传下来的生活和行为模式,储藏着心灵初始生长演化的原始意象,这种集体无意识或原始意象,蛰伏在人类的内心深处,一伺离别故土,去往他乡,这种集体无意识便会以明显的文化固守的方式表现出来”(辛红娟,2007:157) 。
《道德经》在往英语世界的旅行中,造成文本旅行的介质是译者。这些译者总的来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西方到中国的行游者或中国到西方的行游者,如明末清初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和二十世纪上半叶旅居国外的华人学者;另一类是西方向中国的神游者(包括从未到过中国或曾经到中国短期逗留的西方学者)或中国向西方的神游者(较少国外生活经历的中国本土学者),他们也许有短期到异域的旅行经验,但对异文化的感受多来源于文学阅读等精神层面的活动。译者在物理世界的旅行或在精神领域的思想流动,是站在文化认同与反思的高度,对他者文化的观望。作为一种主动的文化切入,他们对异域他乡文本的解读,是一种有态度的“凝视”。时空的转换并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他们只着意体认时空转换所展示的文化价值、所宣泄的文化认同抑或文化批判。译者作为文本旅行的推助者,力图通过翻译和传播“他者”文化,改变历史与现实的不尽如人意,并在个人所属的世界里予以再造和重组,以获得新的审视与评价。从人类文明交往的角度看,对异文化典籍的翻译,不仅有助于本民族文化质量的提高,也有助于人类整体文化价值的开掘与提升。
文化固守是一个相对于文化变迁而提出的相对较新的学术概念,是指“在社会与文化不可逆转的变迁过程中,作为文化拥有者的民族或者族群成员对他们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传统知识、信仰、道德、艺术、法律、习俗和群体成员所必需的各种基本能力和惯习的坚守与保持”(王希辉,2014:54)。在彼此隔膜的文化交流之初,一方的文化固守往往表现为对异文化的非难和贬斥。落实到精神文化层面,在本文探讨的文化典籍翻译中,这种“非难”和“贬斥”往往会以较为隐性的方式存在。译者通过主体选择、概念置换来实现对本民族文化的提升或对他者文化的贬抑。《道德经》英译初期,译者主体多是西方来华传教士,他们在翻译中以修辞巧渡的方式藏匿本土的基督教情怀。由于人类的文化价值经过蒸馏,会在宗教的位格上沉淀下来,因而固守宗教信仰成为传教士固守文化的一种有效方式。《道德经》英译初期的文化固守,主要表现为对中国之“道”的牵强比附和对“圣人”形象的扭曲。
“道”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蕴涵深厚,先秦诸子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对“道”进行阐发,诸子百家各有其道,中国哲学也可以说就是研究道的诸多方面(李晨阳,2005:2)。“道”是老子哲学的中心概念。《道德经》中反复出现的“道”字,虽然语言符号同一,但义涵却各自不同,可以归纳成三个相互贯通的层面:形而上的实存者;一种规律;人生的一种准则、指标或典范(陈鼓应,2003:23-48)。“道”的“不可道”特质和“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形体存在给了西方学者极大的阐释空间,使“道”的翻译成为西方译者拒斥汉语文化因子、藏匿其民族文化的“避难所”。
1895年版亚历山大(George Gardiner Alexander)《道德经》译本中将“道”译为God,认为“道”的内涵类同于西方哲学中的“第一因”(infinite First Cause),并以“he”这个人称代词来指涉“道”,将老子的形上之“道”转变为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有意志和位格的造物主(王剑凡,2002:120-122)。亚历山大通过转换“道”的形象,固守了基督教文化基因,获得广大西方读者的认同。他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德经》第一章)译为:
God (the great everlasting infinite First Cause from whom all things in heaven and earth proceed) can neither be defined nor named.
For the God which can be defined or named is but the Creator; the Great Mother of all those things of which our senses have cognizance.
Now he who would gain a knowledge of the nature and attributes of the nameless and undefinable God, must first set himself free from all earthly desires, for unless he can do this, he will be unable to penetrate the material veil which interposes between him and those spiritual conditions into which he would obtain in insight.
Yet the spiritual and the material, though known to us under different names, are similar in origin and issue from the same source, and the same obscurity belongs to both, for deep indeed is the darkness which enshrouds the portals through which we have to pass, in order to gain a knowledge of these mysteries. (Alexander, 1895)
通过将“道”与创生万物的造物主相比附,以其熟悉的基督文化格义陌生的东方哲学,一则是认识新事物的必要程序,犹如脚手架或跳板。但同时,译者也借中国老子之口宣扬了基督耶稣是东西方共认的唯一神的思想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即将赴华传教的传教士对其本土宗教传统的荣耀感和使命感。出于文化固守,译者在他者文化中的主要目标并非寻异,而是求同。通过对文化接触地带的语言操纵,译者固守了其本土的文化因子——基督教信仰和教义,这一固守不仅获得本民族读者的普遍认同[亚历山大的译本,因其语言简明易懂,具有浓厚的基督教意味,是当时最受一般读者爱戴的英译本],也为基督教福音书传入中国铺平了道路。
3.0 《道德经》英译调和文化冲击
在旅行中,人不可避免地要用固有的“文化拐杖”处理自己所遭遇的文化间距。旅行是一种遭遇,一种他者眼光与陌生现实的遭遇,是越出本土的囿限,看外部世界的人类体验(周宪,2000:115)。在旅行过程中,时空差异使得旅行者形成“陌生地看”与“去看陌生”的体验方式,这种体验方式必定会给旅行者带来冲击。空间的转变同时意味着文化的转变,“当人们从一个熟悉的文化环境转到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总会有一种文化失落的感觉。人在文化空间脱离本土的感觉,就像一株植物被从正在生长着的土壤里拔出来一样。虽然,他也许能在另一种文化环境里成活,但必定要经历一番为时不短的九死一生的痛苦” (辛红娟,2007:157),这种由文化转移引发的动荡和伤筋动骨,就是异质文化(heterogeneous culture)接触中的文化冲突现象。良性文化冲击可以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交流,一旦异质文化间的不可调和性引发文化冲突,便会阻滞文明的进程。
一般说来,物质文化产品常会给旅行者带来新奇、愉悦的感觉或是特殊的奇趣。相比之下,文化内核部分的接触由于旅行者的文化固守常导致文化冲突和文化抵抗。旅行者由于采取对立的文化身份,常会将对异质文化内核的体验扭曲、变形为一种自以为是的独白话语。为了顺利地传播福音书的思想,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传教士采取“学术传教”的文化调适政策。他们把汉服、汉儒等外在形式的儒家文化当成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全部,拒绝触及儒家文化的深层义理,诸如敬祖之礼、祭孔之礼和祭天之礼等,从而引起中西交往史上的极端文化冲突——“礼仪之争”。文化冲突是文化冲击的极端状态,常常可以通过接触双方的妥协来实现向良性交往的转化。传教士在选择和使用中国文化时无法避免自己的基督教及西方文化本位立场,面对中西文化之间的各种隔膜、抵触和扞格不入,传教士一改“礼仪之争”时期的极端做法,但也并不一味妥协,而是对其中的重要范畴与命题进行直接或间接、委婉或直白的辩论、重释,以西方的内涵对其加以置换,直至做出完全的否定(刘耘华,2005:119)。
在中西文化接触中,双方都将形而上层面的旅行(语词接触或文本翻译)看作是一部基于自己文化倾向的自我上演的戏剧。戏剧的脚本早已写好,旅行者只需在旅行开始时将其角色一一对应而已(郭少棠,2005:67)。与《道德经》英译同步,传教士开始了《圣经》汉译工作,为便利基督教教义的传播,他们选择使用中国典籍中的“上帝”或“帝”对译God,用中国典籍中的术语来表述基督教义理。这一做法的结果,并不会消解基督教传统对其本土宗教的认知,却会由于强势文化的推进,造成基督教义理对中国概念语词原有意蕴的置换,加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事实上,这一概念置换下的基督教,其本真样态也发生了变化,是基督教在中国文化域中的重新定位,是面对异质东方文化冲击下的文化转换。要妥善解决这种文化冲击,顺利实现文化转换,首先要求作为文化行游者(旅行者)的传教士也实现转换。文化旅行者在精神域的转换,是在不失其文化固守的基础之上与异质文化的协商和谈判,一方面固守本源文化基因,一方面抱着“允执其中”的态度去感悟他者文化的精要。不可否认的是,文化冲击虽然往往会给接触的双方造成文化阵痛,但也常会化生为一种正面的力量,使人类文化朝着健康有益的方向发展。长达一百年的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是中西文化因人类在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旅行而导致的正面的冲突和抵抗,这一文化冲击是中国思想输入欧洲的良好时机,给欧洲思想界以一大刺激并因而促进了欧洲“哲学时代”的到来(朱谦之,1985:128)。
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开始有了自己的《道德经》英译文本。此后,不少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中国学者也投入《道德经》的翻译事业。这些生于中国,浸濡儒道文化的海外华人学者,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这种外化为乡土情结的文化固守在他们的海外旅行生涯中与西方文化相遇,受到激化,促使他们致力于中国古代典籍在西方社会的传播。站在中西方哲学的交汇地带,这些学者的《道德经》文本翻译活动本身是应对文化冲击的外来表现形式。他们的翻译体现了本源文化在面对文化冲击时的姿态和立场,他们在文本旅行过程中的修辞选择彰显了文化冲击的良性结果,为中华典籍和思想体系在西方的传播立下不朽功勋,改变了英语世界对于《道德经》的独自言说的局面。
4.0 《道德经》英译达致文化认同
“旅行既体现着以文化吸收为主的对异质文化的认同,又体现着以文化身份确认为目的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指旅行者在经受文化冲击后,理性地吸收目的地文化。而文化认同则是指旅行者通过旅行确认自己的文化,既是旅行者的一种主观心理认同,也是主方文化在接触客方文化时的主体认同”(辛红娟,2007:157)。文化在历史积淀中,成为一个国家的集体行为模式和心理特征,构成国家的思想风貌,凝聚着民族的精神智慧,而典籍文本则全面、生动、深层次地体现了这种风貌和智慧。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国家精神载体,典籍文本中蕴藏着民族的、社会的、历史的乃至文化的全部奥秘。由翻译沟通的典籍文本的去往他乡、他国,是不同文化在彼此接触中“凝视”他者文化、寻求并彰显自我文化认同的场域。
文化态度的转换是旅行者/译者对异质文化实现认同的先决条件。如果因为隔膜或误解,旅行者/译者对异质文化产生拒斥,这种他异的文化无论多么新奇,多么具有先进意义和价值,都不会被旅行者/译者纳入自己的文化体验和经验中去。只有当旅行者/译者文化态度发生转变,异质文化的价值才能获得认同,进而被纳入旅行者/译者的文化架构。旅行中的迁移推动人类知识的增量,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由于对异质文化的认同而带来的文化吸收和文化融合。亚瑟·韦利(1999)用Way翻译《道德经》中的“道”,被认为是“除了希腊语源的logos,在英语里恐怕再也找不出比Way与‘道’更对等的词”(姚小平,1994:13)。其实,用Way译“道”,本身就暗含着一种民族集体无意识,是西方学者内心储藏着的心灵初始生长演化的原始意象在文本解读层面的投射。《道德经》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和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这两处表述高度概括了“道”的存在,亚瑟·韦利对中国之“道”的认同,却是通过西方民族的宗教无意识“Way”来外化,实则展现的是融汇了中国道体意涵的中西融通之“道”的形象:
The Way that can be told of is not an Unvarying Way;
The names that can be named are not unvarying names.(第一章)
There was something formless yet complete,
That existed before heaven and earth;
Without sound, without substance,
Dependent on nothing, unchanging,
All pervading, unfailing.
One may think of it as the mother of all things under heaven.
Its true name we do not know;
“Way” the by-name that we give it.
Were I forced to say to what class of things it belongs
I should call it Great (ta).(第二十五章)
依据商务印书馆《辞源》(1983:3073),“道”的基本含义有:①道路;②方法、技艺;③规律、事理;④思想、学说;⑤说;⑥道象之简称;⑦祭路神;⑧疏通;⑨引导。陆沉(1999:48)说,作为名词的道,如果是由动词演变而来,则此动词最有可能是引导意义上的道。而作为“说”动词意义上的道是后来引申的意义。韦利在对老子其人其书进行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将“道”译为“Way”,不仅改变了早期传教士的强暴比附,而且在某些层面与汉语中的“道”有暗合之处。但参照《圣经》,我们不难发现,韦氏选择Way来翻译“道”,一方面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同时,也是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反观基督教文明。
《新约·约翰福音书》第十四章记录了耶稣与使徒的一段对话:
4 “And you know the way where I am going.”
5 Thomas said to him, “Lord, we do not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how can we know the way?”
6 Jesus said to him, “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but by me.”
译文如下:
4 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5多马对他说,主阿!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6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耶稣所昭示的 way,是通向彼岸世界的光明大道,而老子的“道”是世俗的人间正道,如“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第五十三章);“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第八十一章)等。二者表面对应,内涵却迥然不同,但较之于早期译者将“道”比附为唯一神——天主或上帝,这一修辞替代较为含蓄、隐性,是一种在异质文化中寻求双重文化认同的举措。
事实上,从传教士接触道家经典以来,一种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文化优越论思想桎梏的将“道”译为“Tao”的翻译努力一直未曾中断过。目前,Tao已经作为英语语言的一个词条收入词典,专指中国老子之道。这种翻译努力,体现了新的文化语境下,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终于趋向中立而至尊重,也体现了译者们逼向“道”之本原的学术努力。将“道”译为God,体现了强势文化在与弱势的异质文化接触时的一种扭曲、错误而变形的想像;将“道”译为Way,虽有简单化的感觉,却体现了良性文化冲击下的一种文化协商;将“道”对应为Tao甚或Dao,这一陌生的音译或“笨拙的”译法(宇文所安,2003:14),使西方读者先有一个概念,意识到这是中国文化的独特范畴,给予读者揣摩、想像的余地,避免了理解的偏差和文化的失落。从“道”的翻译变迁和《道德经》文本形象的变化可以看出一个多世纪以来,《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行旅中经历的西方文化固守、中西方文化冲击和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是一个由霸权而渐至理性的良性发展过程。西方译者走出了对《道德经》进行意义侵吞、意象扭曲和文本变形的独语的修辞操纵阶段,在对话的过程中建构了一个多面的《道德经》历史文本形象。
旅行中的文化认证是一个辩证、动态,甚至是曲折的过程,是对自我和异质文化的双重确认。异质文化如同本源文化的一种镜像。旅行者/译者在认同异质文化的同时,其实是在重新体认其本民族文化,通过文本解读和文化想像提升了自身民族文化的位置,又通过对异质文化的认同改变了旅行者/译者原有的进入文本之前持有的单一文化身份。经由译者一系列心理、文化转换而实现的文本跨文化旅行,因此能够在文本和文化层面推动双方文化的认同与提升,从而生成一种有益于人类文明的新的文化智识,是对遇合双方文明的一种“有益的补充”。“不同文化间交流与互动,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而译介与传播,是一种文化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焦鹏帅、颜海峰,2017:92)。20世纪后期,英语世界对《道德经》的接受,走出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泥潭,不再仅仅择取有利于基督教义理阐发的个别词汇或命题,进行为我所用式的引申和比配。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意识到道家哲学是一种追求和谐、遵循宇宙和组织理性的哲学,在《道德经》文本翻译中明确体现出对于道家思想和道家文化的认同。英语世界对于《道德经》的解读和翻译,走出与《圣经》进行强行比附的泥沼,更多地采取一种比较文化、比较哲学的眼光看待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哲学文学文本。
[1] Alexander, G. G.Lao-Tsze,theGreatThinkerwithaTranslationofHisThoughtsonNatureandManifestationsofGod[M]. London: Trubner & Co., 1895.
[2] Rojek, C. & J. Urry.TouringCultures:TransformationofTravelandTheory[M]. London: Routledge, 1997.
[3] Williams, C. T.TravelCulture:EssaysonWhatMakesUsGo[M]. Westport: Praeger, 1998.
[4] 陈鼓应. 老子今注今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 郭少棠. 旅行:跨文化想像[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 焦鹏帅,颜海峰. 内涵·误区·路径——中国文化“走出去”再思考[J]. 山东外语教学,2017,(3):92-98.
[7] 李晨阳. 道与西方的相遇:中西比较哲学重要问题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8] 刘耘华. 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其本土回应[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9] 陆沉. 老子的“道”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之异同[J]. 天府新论,1999,(6):48-51.
[10] 王剑凡. 中心与边缘——初探《道德经》早期英译概况[J]. 中外文学,2002,(3):114-132.
[11] 王希辉. 论文化人类学文化固守理论的初步构建[J]. 广西民族研究,2014,(1):53-60.
[12] 辛红娟. 旅行的文化研究及其对翻译学的启示[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156-160.
[13] 辛红娟. 旅行与文学翻译的象似性研究[J]. 社会科学家,2009,(1):149-152.
[14] 亚瑟·韦利英译. 陈鼓应今译. 傅惠生校注. 老子:汉英对照[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15] 姚小平. “道”的英译和《圣经》中的“道”[J]. 外语与翻译,1994,(2):12-15.
[16] 宇文所安. 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M]. 王柏华,陶庆梅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17] 周宪. 旅行者的眼光与现代性体验——从近代游记文学看现代性体验的形成[J]. 社会科学战线,2000,(6):115-120.
[18] 朱谦之. 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杨彬)
Tracing the English Versions ofTaoTeChing: A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ravelling
XIN Hong-juan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Many scholars have come to realize that the “contact zone”, being a place of cultural clinging, cultural shock and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sometimes reveals the radically asymmetrical relations of power when two different cultures encounter.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translation ofTaoTeChingin the past centuries from this new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ravelling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map ofTaoTeChingtranslating and the conception of Tao manifest different cultural attitudes of the translators and hence brought new edification to the recipient culture.
TaoTeChing; cultural travelling; translation studies
10.16482/j.sdwy37-1026.2017-04-011
2017-05-28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道德经》在美国的译介与接受研究”(项目编号:14BYY025)、“钱江学者”人才工程项目的部分成果。
辛红娟(1972-),女,江苏徐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典籍英译。
H159
A
1002-2643(2017)04-009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