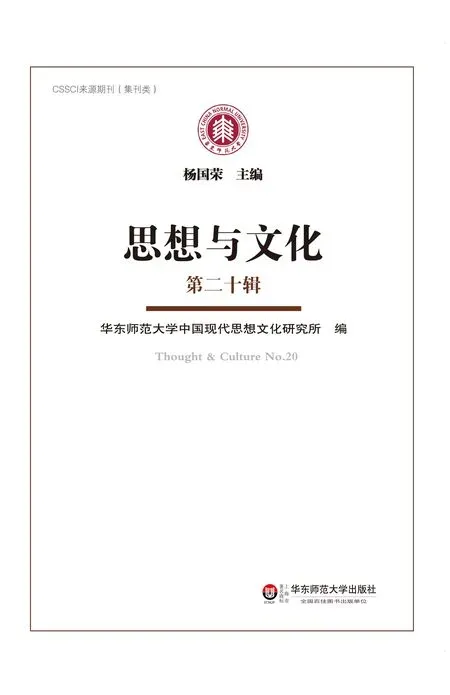试论王柏思想的入世倾向*
●
古代印度哲学一向有以绝对的空为宇宙本原的观念,此观念化为中国禅宗“无一物可得是为见道”、“说似一物即不中”等思想并在中古时期盛行于中华大地。而后起的宋代理学——尤其程颢、程颐与朱熹的理论却是对此虚无主义与神秘主义的理智地远离。程朱等理学思想家将目光由味淡声稀之处重新转回现世人伦之间,在哲学的、近乎宗教的沉思中返回了先秦儒家“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王守仁: 《王阳明全集》(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91页。的旨趣。而且,理学思想家认为,此超世间的人生观比出世间的更高。
宋代理学是道禅思想洗礼过的儒家,是儒、释、道三教大融合的产物,兼具内省与外应、出世与入世双重因素并相济无间。然而,理学在由中古时期向近古时期传播时,却发生了悄悄但显著的变化。朱熹生前,理学被当作“伪学”打击,宋理宗统治时期,理学才被立为国学,历经元、明、清三朝,始终作为官方的学术存在,影响持续将近千年。在此传承中,号称北山四子的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起了重要作用。由朱熹女婿黄榦传给北山何基,何基再传给鲁斋王柏,王柏再传给仁山金履祥,金履祥再传给白云许谦的金华一脉衔接了宋元之际的朱学,并成为元朝朱子理学的核心和明朝朱子理学的主要倡导者。近古时期在我国大地上流传最多的儒学都是北山四先生的余脉,他们也一度被视为最醇正的朱学。但他们虽以嫡传自命,对朱学的继承却主要表现于对道统论的维护、对《四书》的尊崇、扩展儒家道德判断到文学、史学乃至一切学术领域等外在方面,朱学的精华处、微妙处、生命气息已散去,如一枝花被制成了标本。
作者认为,这是由于理学在传播后期,向外、入世的因素高于了出世的、内省的、关注生命本身的因素、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和谐被打破所致。作者试以理学从中古向近古转变的关键人物——北山四子之一的王柏为例,对这个问题做简单分析。
一
《复斋记》有云:“物无终困之理。圣人之彖: 复,于以见天地之心焉。盖万物必有大剥落,然后有大发生。”*王柏: 《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五,《续金华丛书》,民国十三年(1924年),永康胡氏梦选楼刊本,第254页。《周易》中的复卦,王柏认为是天地之心的呈现。王柏诗意地指出,当朔风怒号之时,看似天地闭塞而成冬,实则浮游般的生气已在槁木死灰下潜动,因而复道反善之意既是天地生物之仁。这种奇思也感染了他的后人——金履祥与许谦,王柏、金履祥、许谦的诗文中都出现过许多梅花的意象和对梅花物态的描写,他们钟爱梅花,因为梅花是复卦的化身,天寒地冻之中开出几朵零星的梅花正像群阴之中露出一点阳,而菊花、瑞香、兰草等手植的和野生的花木也都是造化阴阳之流屈伸的瞬息之兆。纷纷落英、怡怡华萼、木石藤蔓、幽谷流泉、冰壶秋月之于王柏等人,无不是元元继无息的发露。
这万象春融的物态原也是程颢、程颐和朱熹眼中、心上的天地的本相。但对于程朱,宇宙又多了一层含义——程朱认为永恒生化中的实际世界之上还有一个亘古长存的理世界。如果说,前一种生生不息的实际世界的观念是程朱从儒家、从中国哲学的传统中继承来的,后一种观念——万物之上还有不变的真谛之光的观念便来自印度哲学。印度哲学一向主张,在此可见、可触、可思的有形世界之上还有无形的大梵,与大梵相比,有形世界中的一切都无实体性,都是大梵的变幻。这种古老思想在佛教中变成了神识生万物的学说,理学产生时深受佛学影响,这种思想通过佛教进入程朱理学中,化为理所形成的世界大于、高于气所形成的世界的见解。终极实在即有人间的万物之魂的一面,也有超人间的神的一面。在理学发生、发展的前期、中期,这两方面是相对持平的,但理学走向后期时,理学形上学中超世间的意味渐渐弱化、消失,而世间的意味却日益丰厚,仅示以王柏思想中一二概念便可说明:
(一) 理
王柏的老师何基认为理是事物的“恰好处”,孔子的“一贯”、《大学》的“至善”都是此意。这影响了王柏,王柏也认为理是事物的“中”或“则”,《研几图》道:“为是物必有当然之则”*王柏: 《研几图》(《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六册),济南: 齐鲁书社,1997年,第6页。,而这当然之则便是“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程子所谓天然自有之中”*王柏: 《研几图》,第6页。,也就是理。王柏的“理”与朱熹既有相似又有不同,《朱子语类》云:“理是有条理,有文路子。文路子当从那里去,自家也从那里去,文路子不从那里去,自家也不从那里去。”*钱穆: 《朱子新学案》(一),北京: 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72页。朱熹对理的这种看法类似先秦时期人们对理的看法,何基、王柏等传人所继承的主要也是这种定义。但朱熹对于“理”还有另一种观点:“形而上者是理。才有作用,便是形而下者。”*钱穆: 《朱子新学案》(一),第270页。“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钱穆: 《朱子新学案》(一),第269页。朱熹在形形色色的物世界之上又造出一个亘古长存的理世界,一物未生,其理已具,一物即灭,其理不亡。总之,理是先验的存在。这种观点在王柏的哲学中却较少显现。
南宋后期——尤其庆元党禁之后——由于政治上的高压,学术团体内部的团结加强,朱学、陆学、浙学三大学派逐渐趋于合流。王应麟、黄震、北山学派等浙江学者都在接受朱学的同时也秉承了永康学、永嘉学、婺学的渊源。作为北山学派学者之一的王柏也或隐或显地表现出陈亮、吕祖谦等人的思想痕迹。对于道,陈亮认为:“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陈亮: 《龙川文集》,北京: 中华书局,1985年,第92页。道不离器,道不是脱离于实际世界之外的、不受实际世界影响的存在,拒斥道的绝对性与超验性是事功学派一如既往的观点。陈亮指出,道的实在性要在具体事物的运动变化中展现,“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途万辙,因事作则”。*陈亮: 《龙川文集》,第219页。王柏的理是“则”,实际上是受到浙学作用的变异的理学观念,而他们对理的这种立场又导致了他们对理与气的关系的看法的改变。
“某窃谓理气未尝相离,先儒不相沿袭,虽言不同,而未尝相悖。言气者,是以气为道之体,理已在其中。言理者,是以理必乘气而出,气亦在其中。”*王柏: 《鲁斋王文宪公文集》,第278页。虽然王柏和朱熹一样认为理是气运行的“则”,但他抹杀了理的先验性,把理与气的不可分变成了二者的同等。朱熹哲学始终以理为主导、气为附属,理气不分只是在实际世界中,在终极层面,理高于气。但王柏对理、气的看法已经近乎二元论,他不仅认为在实际世界中理与气是无法分开的,在本体论上也几乎承认了气与理的同等地位。王柏削弱了程朱学说的空灵色彩,力争将无形的意义消除,从他对“理一分殊”命题的辨析也可以发现。
王柏曾讲:
子知万物之荣枯乎?此阴阳升降之大节也。然逐枝逐叶自有一荣枯,盖各有一乾坤也。”藻曰:“物物各有一消长也,亦不外乎一大消长。此理一分殊之谓乎?”夫子莞尔而笑曰:“藻也,始可与言道也矣。”*王柏: 《鲁斋王文宪公文集》,第331页。
在此,王柏指出天地万物看似各个相异,却是生自同一根源的哲理,好像朱熹的名句“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 《朱子全书》(第二十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85页。所表达的寓意一样。然而,朱熹的“理一分殊”是从华严宗月印万川理念而来,始终充满真元又遍在宇宙间每一事物中,而每一事物中的真元都是真元本身的秘奥意味。王柏的“理一分殊”却更像是“理一份殊”,也就是说,个别的“理”与理的全体之间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王柏的“理一份殊”实际上是受陈亮的影响产生的,陈亮在注解张载《西铭》时曾言:“一物而有阙,岂惟不比乎义,而理固不完矣。故理一所以为分殊也,非理一而分则殊也。苟能使吾生之所固有者各当其定分而不乱,是其所以为理一也。”*陈亮: 《龙川文集》,第149页。一个部分受损就会使整体起变化,同样,所有部分安然,整体就会完好地运行,这就是“理一份殊”,这又是将抽象的、理论的变成实有的、具体的表现。
(二) 太极
盖周子欲为此图以示人也,而太极无形无象,本不可以成图,然非图则造化之渊微又难于模写,不得已画为图象,拟天之形,指为太极,又若有形有象,故于《图说》首发此一语,不过先释太极之本无此图象也。*王柏: 《鲁斋集附录补遗》,北京: 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第136页。
王柏本欲凭借自己一贯的疑经精神指出《太极图说》起首原没有“无极而太极”这句话,是后人窜入,但又觉得不太可能,便认为“无形而有理”的意思是没有“太极图”的图像、“太极图”的图像是为方便而设。
在朱熹的理论中,太极无声无息:“是以自其著者而观之,则动静不同时,阴阳不同位,而太极无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观之,则冲漠无朕,而动静阴阳之理,已悉具于其中矣。”*周敦颐: 《周敦颐集》,北京: 中华书局,1990年,第4页。太极始终存在于动静化生的两仪、阴阳所化的五行与四时、五行所化的万物之中。“至其所以为阴阳者,则又无适而非太极之本然也,夫岂有所亏欠间隔哉!”*周敦颐: 《周敦颐集》,第5页。太极的存在与阴阳五行的存在是共时的,没有形而下世界中的先后关系。举天下无以加此、究极而无可名,所以称为太极,以“无极”冠于“太极”之前是指“太极”并不是一事物,它无形象无方所。
王柏的“太极”却似乎回到了两汉黄老哲学太易、太初、太始、太素的内涵,又明显有邵雍《皇极经世》的影子。他用一种近乎图画的方式演绎了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五行生万物。王柏效仿邵雍《观物内篇》设立元、会、运、世等概念。元是王柏所定的最大的时间,相当于佛教中的一劫,一元分为十二会,其中第一会,王柏说:“此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复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之时也。”*王柏: 《鲁斋王文宪公文集》,第329页。这个阶段是从天地混沌走向有形有色的开始。一元中的第二会:“此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之时。”*王柏: 《鲁斋王文宪公文集》,第329页。起初只有太极,然后太极向阴阳分化。一元中的第三会:“此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之时。”*王柏: 《鲁斋王文宪公文集》,第330页。就像细胞分裂那样,阴阳分开之后,化为五行,又从五行产生出四时、万物。王柏认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太极图》是时空中的宇宙发生论,打破了朱熹本体上的、逻辑上的太极。总之,王柏将朱熹哲学中所有光影一般的词语都做了拖泥带水的解释。
从对上述两个哲学问题的简单分析可知,王柏看似继承了朱熹哲学的本体论,实际上,已经对其进行了深度改造。他将从二程、朱熹那里继承来的立体的、纵深的、复杂的结构变成简单的、平面的结构,将奥妙的形上学化为对经验世界中现象的概括。这显示出形上学——理学曾经的高峰之学,此时,已中止了向上发展,而趋于停滞。形上学的这些变化开始影响认识论——理学的另外一个领域。
二
王柏与继其后的金履祥、许谦等人对《诗集传》、《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书集传》等前人著作做了许多上及星辰、下及山河、中及花鸟草木的补古今名物之略的考证。然而,在这些考证中难以发现朱熹注释《四书》时闪耀的新哲学的光辉,却有汉儒疏不破注的原则在起作用。北山四子的知识论中,多是对以往儒学思想家所提出的概念、命题的说明、补充,而少见开拓性的格局。这标志着朱学创造力的衰弱——理学的思想家已经从规范的创造者变成了规范的恪守者,就像一位大师的弟子只是不断临摹他留下的原作。在后期理学中,时时有死的形式反噬活的精神,程朱思想中诗性的特征已褪色,留下散文味儿的拼凑,这在王柏对知识本身的性质和知识的作用的观点上有明显的表现。
(一) 体知的碎裂
真正的知识应当是“体知”,对于这种“体知”,程颢、程颐、朱熹有许多叙述。《河南程氏遗书》言:“如读《论语》,旧时未读是这个人,及读了后又只是这个人,便是不曾读也。”*程颢、程颐: 《二程集》,北京: 中华书局,1981年,第261页。《朱子语类》道:“圣人之道,如饥食渴饮。”*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北京: 中华书局,1986年,第129页。学问之养人要像饮食之养人,如无体知,求学者就只是一个道的谈论者,却不会见道、悟道。《大学章句》“格物补传”条云: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北京: 中华书局,1983年,第6—7页。
知识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始终与终极实在相关、是通向终极实在的桥梁。无论在外界做多少繁琐的格物,最终都要回归本性中的太极,体知的妙用是以外在的光明点燃内心的光明。
然而,王柏认为“致知”是上对下的教化,《大学沿革后论》云:
致者,上之所以教也。知者,下之所以学也。“知”字即重,不可不授之以致之之方,盖致知只在格物之中,穷物之理所以致吾之知也。*王柏: 《鲁斋集附录补遗》,第20页。
王柏将“致知”中原有的恢复澄明良知的含义掩盖,正如他认为“明明德”是要秉承“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第4页。的原则、使天下人的言行都符合名教那样。由于在本体论中,王柏认为理是事物的恰好处,所以在认识论中,王柏也认为“知至”所至之“知”是指万物的“止”——“诚能知其所当止,则思虑不杂、意向不偏、气质不得而胜、物欲不得而迁,此所谓定也。”*王柏: 《鲁斋集附录补遗》,第21页。此“止”便是至善,大学之道所要实现的至善就是这“止”。“致知”的教化也是要学习者明了“止”,并在齐家、治国等活动中将“止”实现。王柏的“知”已经没有了真知、体知的意蕴,而像是一种头脑的知识,他的知识是一种外在的要求。实际上,他又回到了知识的实用性之中,这种实用性在于维护社会秩序。
王柏的思想会有如此的特点是由于浙东事功学派功利主义的作用,而将经验世界中的社会人事的认识当成知识本身、将实践中的有效性当成检验知识价值的标准的缘故,正如在本体论中,他排斥了先验的存在,在认识论中,他也排斥了关于超验本体的纯粹的知识。经验知识是知识的全部,经验的有效性是知识的最后目的。吕祖谦在《大学策问》中讲:“所以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也。盖尝论,立心不实为学者百病之源。”*吕祖谦: 《吕祖谦全集》,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4页。实用、实然、实理、实见是读书讲明义理的目的。叶适曾言:“且物格而后知至,是其在卓然之中与吾接而不能去者也。”*叶适: 《叶适集》,北京: 中华书局,1961年,第731页。叶适抹去了格物中联结此岸与彼岸的通心作用,从以物用而不以己用的准则出发,认为格物是对事物的客观反映,并不能穷理尽性,也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叶适、陈亮等浙学思想家没有对理学认识论的指导思想做理论上的分析,而是一开始就舍弃了不能干预实际世界的“玩心于形之表”的知识。王柏虽然是朱熹的传人,但年少时极有经世之志,他自号“长啸”,也是陈亮豪迈不羁性格的表现,中年以后,他因明了家学渊源而师事何基,逐渐有了醇儒气象,然而,早期学以致用的思想从未改变,他讲:“某窃谓吾儒之学,有体有用,其体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氏之书,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要;其用则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王柏: 《鲁斋集附录补遗》,第120页。所有隐藏的体都要由用来开显,他删去了认识的宗教性、出世性、高严性、纯粹性,代之以世俗的、经验主义的风格,而这种趋势还有另一种表现。
(二) 下学与上达
理学在与佛教,尤其禅宗思想的斗争中逐步完善起来,印度哲学,尤其大乘中观宗将对实际事物的知识视为“法缚”的观念一开始就受到理学家的排斥。理学家将对实际事物的知识本身看成通向终极的道路,认为具体知识对最高真理的洞见不是阻碍而是不可缺少的辅助。《朱子语类》云:“吾儒心虽虚而理则实,若释氏则一向归空寂去了。”*钱穆: 《朱子新学案》(三),第527页。,“释氏唯务上达而无下学,然则其上达处岂有是邪?”*钱穆: 《朱子新学案》(三),第541页。同时,理学也排斥了禅宗最高真理不可言说、言说就会落入第二意的说法。朱熹讲:“知,只有个真与不真分别,如说有一项不可言底知,便是释氏之误。”*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第159页。总之,理学是要事事从低处着手。
王柏作为朱熹的传人,也继承了这种平实的求知精神。金履祥曾就读《论语》时“得于集注言意之外者”*王柏: 《鲁斋王文宪公文集》,第288页。求教于王柏,王柏回答:“于言意之内尚未能得其仿佛,而欲求于言意之外,可乎?”*王柏: 《鲁斋王文宪公文集》,第288页。王柏从儒家哲学传统的中庸之道出发,摒弃了一切幽远玄虚之说。他认为上乘的“知”只应如布帛蔬粟一般,使人终日食用而不忘:“学不见于事,是玄虚之学耳。以己未知效前人之已知,以己未能效前人之已能,是谓师古,是先之以为学之实也。”*王柏: 《书疑》,《金华丛书》,清同治胡凤丹辑刊本,第15页。圣贤所有之知仍是常人之知、所做之事仍是常人之事,只是境界不同,如人初学写字是写字、成为书家也还是写字,这也就是从下学到上达的变化。
然而,在王柏的学说中,下学之味已经过于浓厚,乃至淹没了上达,这也是他——一个朱熹三传弟子、一个后期理学思想家——的哲学向着形下世界下落的表现。由于陈亮义利双行、王霸并用意识的影响,王柏将富国、强兵、理财等世俗事物都视为儒家学者的职责。《大学》中的“絜矩”之道,王柏认为,是均天下之财的最好方式,《大学》本身,王柏也视为处天下以方正均一、以避免民贫国弱的书。宋代道学固有的浓厚的心性修养论色调在王柏手中逐渐褪化,随之而现的是对可见世界的关注。因此,王柏的“上达”变成了致君泽民,一个非常具体的概念,不再有朱熹的玄秘韵味。“夫致君泽民,固儒者之事业,亦朋友以是期君也。自上而下言之,能致君则泽民在其中矣;自下而上言之,能泽民乃致君也。”*王柏: 《鲁斋王文宪公文集》,第243页。王柏的上达实际上是朱熹的下学,朱熹等前辈学者认为,凡可以教授、可以以言语告知的都是下学,上达要靠心悟,这是形上形下之分在认识论中的表现,王柏将其抹杀。与此同时,王柏的下学也发生了变化——知识的范围在萎缩。王柏在谈及赵明诚《金石录》时道:“谓之博古可也,论之学,则进德修业之士有所未暇。”*王柏: 《鲁斋王文宪公文集》,第243页。王柏将天文、地理、律历、碑帖鼎彝等离圣贤功业较远的学问都视为有玩物丧志之嫌的癖好,惟有“考圣贤之成法,而后识事理之当然”*王柏: 《鲁斋王文宪公文集》,第243页。才是士之常业,其他知识都是小节,这和朱熹一物不格缺了一物之理的做法已经有了很远的距离。
与朱熹等前辈理学家相比,王柏的“下学而上达”是在缩小,一方面削去了前辈理学家在佛道等宗教思想中获得的通天气息,另一方面削去了他们从“格物”引发的探求客观外界的科学精神,又返回了先秦儒家的“学而优则仕”,变成了从义理文章到以明明德化天下。这是王柏本人的写照,也是他之后许多儒家学者的写照。
三
儒家哲学的目的始终在于经世致用,从朱熹起,理学家所关心的就已经不是纯粹的学术,而是如何将书斋内的讨论化为人心世道的整治。而在王柏与北山四子,对人心世道的关注变得更加突出,也更加有具体的、形象化的色彩。思想变成文化、蔓延的集体无意识取代实践主体的自我意识,这是后期理学伦理学衍化的特点。如同先秦儒家哲学持有共同人性的观点一样,宋代儒学“一个根本的目标是要使被确立了的观念具有普遍性,进而使之超越个体的相对性而具有确定性”。*何俊: 《南宋儒学建构》,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页。北山四子之一的王柏致力于将这种个体之上的普遍性化为个体本身,而将不属于这种普遍性的特征都作为相对性排斥。
(一) 道统论的强化
圣人崇拜在王柏的思想中比在二程、朱熹的思想中更加强烈,而且,有了一种不寻常的专断意味。朱熹等前人对儒家哲学视为圣人的人物的崇拜还是理性主义的,王柏则将此看成一种不需要任何论证的大前提,所有其他见解都要从这个大前提上建立,而大前提本身却是不容置喙的。王柏批判苏辙所著古史时说:“至于《孔子传》,叙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母讳之不以告其父之墓。此又何为轻信也?书圣人之家世而不典,如此何以谓之学者?”*王柏: 《鲁斋王文宪公文集》,第281页。王柏一向将从儒家伦理来的道德判断放在一切其他见解前面,因此,史学家表明圣人在道德上有瑕疵就足以否定他的史学成果,无需过多讨论。在王柏看来,儒家哲学的义理是不需要穷究史实、再从史实中得出的,因为这些义理是自明的、不容怀疑的,应用这些义理去修正史书中的史料,如果史料与义理不符,错误一定在于史料,因为义理是不会错的。陈亮曾指出,并没有三代大同盛世,过去的黄金时代和尧舜禹等圣人都是儒家学者在整理文献时造出的。但在这个问题上,王柏却没有效法陈亮,而是坚定不移地追随朱熹并在朱熹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王柏希望为历代儒家圣贤建立一个类似帝王世系的谱系,而将儒家之外的学说当成异端列于次要位置。他盛赞与他讨论史学的陈天瑞能顺应朱熹之意:
今足下乃用朱子之意,削其世次,益以事实,黜秦伯而不污其世纪;降三晋、田齐,而不作世家;增虞、夏、商、周名臣于列传,而春秋战国之贤亦与焉;别立孔子及其弟子传,止于孟轲;斥老子荀卿于异端。其立意凛然、其用力甚勇,其地步阔而又阔;复加以正其门户,正而又正,复济之以阔,岂非欲推本于经、折衷以理邪?*王柏: 《鲁斋王文宪公文集》,第280页。
用朱熹的理学去统摄史书,王柏认为,并不是格物而致知,而是推此理于经史,是从上到下,不是从下到上。
王柏进一步从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角度再次巩固了儒家道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他在为车玉峰的道统录所做跋语中说——
立天之道者,阴阳也;立地之道者,刚柔也。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此非天地之道统乎?圣人以仁义设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所以继绝学而开太平,此则圣人之道统也。*王柏: 《鲁斋王文宪公文集》,第300页。
王柏指出,道统的存在就像天地的存在一样长久,儒家圣人在人间设立道统只是效法造化的秩序。虽然“道统”是韩愈时才提出的,但王柏却认为道统自上古时期一直存在,只是没有这个名号。道统的作用便是“大一统”、便是将所有思想都归于儒家圣人的旗帜之下。统一思想从来都是自命为正统的儒家的做法,先秦时期,荀子就义正词严地表态:“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辩说也。”*杨倞注: 《荀子》,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66页。儒家思想家最希望的是用行政的、法律的手段消灭“异端之学”,与“异端之学”辩论、在学理上打败它们只是没有掌握权力时的不得已的做法。王柏自己也曾说:“君子达而在上,立法定制,品节禁戒,其为教也,顺而易。君子隐而在下,著书立言,开导劝世,其为教也,逆而难。”*王柏: 《鲁斋王文宪公文集》,第249页。犹如应以立法控制人们的行为那样,应以道统控制人们的思想。
(二) 家族伦理的延伸
此心之仁,即父母生育之仁也;父母生育之仁,即天地生物之心也。*王柏: 《鲁斋集附录补遗》,第128页。
王柏对仁的解释并不符合朱熹的思想,朱子云:“谓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第48页。王柏的观念的形成仍是婺学的作用所致,吕祖谦曾讲:“人爱其父母,则必推其生我父母者,祖也。又推而上之,求其生我祖者,则又曾祖也。尊其所自来,则敬宗。儒者之道,必始于亲。”*吕祖谦: 《吕祖谦全集》,第284页。由于在本体论中削弱了纯粹思辨,在伦理学中,王柏也离开了二程与朱熹所推进的形上风格,却在浙学的实用观念中返回了近于原始儒家的推己及人。“爱莫大于爱亲,此本其所由生也,其次则仁民而爱物,此推其所并生也。吾儒所谓理一而分殊者,爱有等差如此。”*王柏: 《鲁斋王文宪公文集》,第249页。亲子之爱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家族关系又成了仁的根,王柏认为德行的根源都在于亲子之爱,是家族的温床养育了德行,因而,牢牢把握儒家孝道就成了王柏的伦理思想的核心。“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惧亏其体、惧辱其亲也。”*王柏: 《鲁斋王文宪公文集》,第257页。中国家庭宗族伦理在此被提到本体的位置上,不再是美德的表现,却是美德的根源。
将形而上的空灵思辨化为可见可触的有形事物是王柏一贯的做法,在此,他也以家族的复杂的“礼”替代了程朱的庞大的理的体系,又用宗族中的感情代替了抽象的“仁”,维护宗族法度、秩序在他看来就是淳化世风、正人心的关键。“自后世宗法不立,而尊尊之义、亲亲之恩,几至于晦蚀泯灭而不存。岂秉彝好德之良心,不如古人哉?亦以观感服习之未至,此正父兄之责也。”*王柏: 《鲁斋集附录补遗》,第75页。因此,宗族之内冠婚丧祭、序拜聚会、上冢受胙等仪轨和这些仪轨所承载的人文信息就成为一人心、定名分、培植根本的无比重要的内容。按照王柏的立场,一个崇高圣洁的人、一个可做榜样的君子总是一个具有孝、悌、慈、义、节等大家族所需的品德的人。内心仅信奉儒家道统,外在最好地践履家族伦理是王柏及北山四子理想的人格模式。
(三) 理想人格
朱熹曾为一位吕姓女人写过墓志铭:“未笄,失其母,剑浦俾治家事,抚弟妹如成人。寻以归邵武饶君伟,事舅姑,甚得其欢心。余年生子干,甫晬而寡。夫人誓志秉节,毅然不可夺。”*朱熹: 《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第4205—4206页。得到朱熹赞赏的人物一般都是严正地履行了家庭中责任的、“一践其庭,礼容肃穆,纤悉中度”*朱熹: 《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第4189页。的人。这些人一旦听到佛学等“异端之说”,决不会相信,只会见其诐淫邪遁。这是朱熹的伦理学所要塑造的人、完全符合新儒家模式的人。
王柏亦讲:
礼者,尊卑贵贱、等级隆杀之品也,因其叙而与之,以其所当得者谓之秩。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王柏: 《鲁斋王文宪公文集》,第285页。
王柏认为君臣父子等礼就是人心中的“德”,而修身是要像淘漉清水、磨拭明镜一样,让这号称是道在局部的显现的“德”越来越亮并将不属于它的成分——这些被视为人欲之私——克去。这种旨在以观念的普遍性超越个体的相对性的思想本是王柏从他的老师何基、间接地从朱熹继承来的,却由于王柏加强了道统的权威、提高了家族伦理的重要性而变得更加明显。他不仅要在思想上将一切不属于儒学的些微之识泯灭,也要在言语、行动上如此。在王柏为自己的同乡、好友、长辈所写的行状、祭文、墓志中,常能看到这些语句:“岂特一家之佳子弟,实为吾党之良友朋也。”*王柏: 《鲁斋王文宪公文集》,第360页。“公天性至孝,自丧父终身不衣华侈,遗文片词必宝藏。”*王柏: 《鲁斋王文宪公文集》,第365页。入则孝、出则义、仁民爱物被王柏视为贤人的共性,而贤人也有相近的气象——端庄严肃又温煦敦厚,“张拱徐趋兮,俨乎其若思。动有则兮神定,澹无欲兮心夷”。*王柏: 《鲁斋王文宪公文集》,第354页。这种看似玉雕般完美的理想人格模式意在凸显共同人性,而一切将在此模式中变得中规中矩——这正是王柏所希望的。翻开王柏的人物谱,不难发现所有他树碑立传的人都是相似的、无一不符合他从朱熹继承来、又被他自己固化了的标准。
伦理是最高寄托,甚至有通天的功能,即使治国之术也不过是这些据说从未变过、也不应当改变的宗族伦理的放大,“至于家,势虽与国悬殊,其理则一而已”。*金履祥: 《仁山集》,北京: 中华书局,1985年,第7页。既然在形上学中,王柏已否定了出世间的本体的存在,在伦理学中,道德境界的尽伦尽性就会成为唯一寄托。
儒家道术从日用开始,终究察乎天地,也就是说,寄宗教性的意义于最普通的事物之中。西周时期,我国就盛行对道德性的天的崇拜,而这种崇拜又是在宗法社会中实现的,因而,夫妇、父子、兄弟等家庭关系确为宗教精神的起始。对有意志、有道德的天的信仰是儒家哲学中超世一面的代表,正因如此,儒家哲学才能成为人终极的精神皈依而不仅仅是处理治国、理家等现世问题。宋代理学家在建立“天理”这个概念和相应的体系时,是以高度逻辑化、理性化的方式又一次说出了先秦儒家对天道的信仰。世间固是世间,但不能执着于世间,只有在超世间的情怀中,世间才得到最好的维护。是相反的事物维系了看似与它对立的一切,一旦这种相反的力量不存在,事物本身就要分裂。由于宗教性因素在王柏等人思想中的退化,伦理本身就取代了宗教,不再是对宗法制之上的至上存在的关注,却是宗法制本身成了他们的终极寄托。
结语
黑格尔曾经指出:“思想是一种结果,是被产生出来的,思想同时是生命力、自身产生其自身的活动力。这种活动力包含有否定性这一主要环节,因为产生也是消灭。”*黑格尔著,贺麟等译: 《哲学史讲演录》,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4—55页。一种思潮在流传的过程中,往往会被重新解释,会被延伸,会被扭曲,会面目全非,甚至会与创立者的宗旨背道而驰。理学便是如此,产生在宋元之际的王柏及金华四子的学说实际上已经偏离了理学泰斗朱熹的初衷,而距离北宋时期理学家们的思想更加遥远。宋代道学的产生本是以佛教为代表、以出世为导向的印度文化和以入世为导向的中国早期儒家文化合流所致,它完美地体现了中国文化固有的和谐——让对立的因素相溶相济、相辅相成地共存于同一整体中——无需到六合之外,入世即是出世。二程和朱熹的思想是此超世观念达到的高峰,是此和谐的金瓯无缺之态。然而,程朱理学在向南宋后期发展时,和谐被破坏、不和谐再次出现,曾经一体共存的两极再次变得对立。宋元之际,理学中入世的倾向逐渐加强、盖过了出世的倾向,二者原本的统一已不复存在。
王柏及其所代表的北山学派使形而下的因素越过了形而上的因素,拆散了朱熹等前辈学者苦心塑造的整体。朱熹等前辈道学家让大地与天道相接而生气灌注,王柏等后辈学者却使人间向着人间下沉。所有现实的、具体的、有限的事物脱离了无限赋予它们的诗性,再次变成散文式的存在。北山学派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创造力的枯竭与走向没落,王柏、许谦等人都在维护朱熹及其他儒家学者留下的金科玉律便是证明。伟大的思想家是规范的创造者,无创造力的时代才会维护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