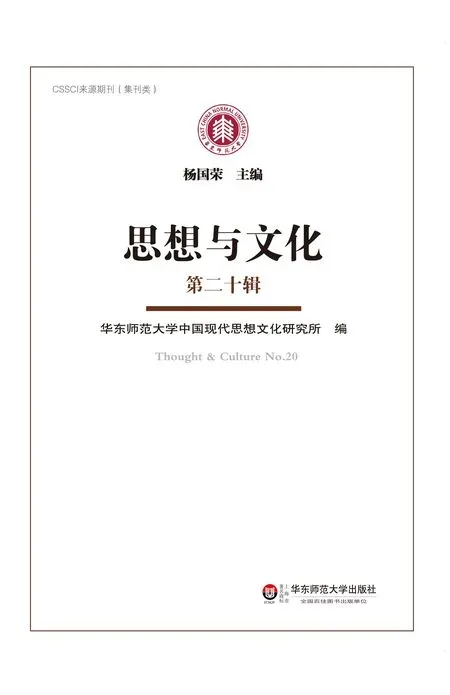仿行宪政与礼法调适*
——清末修律宗旨演变考论
●
中国传统史学讲究察势观风。近代中国之大势就是由外在入侵导致自身的一系列调整。不同于以往,此次入侵者比我们文明程度更高。*时人康有为尝言:“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正是对这一时势的体认。参康有为1898年4月在保国会的演说。新政上谕的发布,是清廷官方对这一变局认同的表示。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清末新政的实行,“使得长期以来在此问题上的激烈社会冲突集中到了体制内部”。*关晓红: 《晚清学部研究》,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绪论第4—5页。新政的下一步就是立宪,在朝野一浪高过一浪的立宪呼声下,1905年7月16日,上谕派戴鸿慈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故宫博物院编: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北京: 中华书局,1979年,第1页。舆论亦以为“五大臣此次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预备,其关系于中国前途最重且大”,“可以定变法维新之国是”。*分别见于《时报》1905年9月25日、1905年7月18日。转引自侯宜杰: 《清末立宪运动史: 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4页。戴鸿慈随后即联系梁启超起草有关立宪的考察报告。8月25日,戴鸿慈、端方联名奏请依日本例改定官制。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上谕,正式决定“仿行宪政”:
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定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故宫博物院编: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3—44页。
随即,1906年9月2日,朝廷即派载泽、奕劻、张之洞、端方、袁世凯等重臣会议改革官制。且不说其实际修改了多少,如此牵连重大之事,清廷仅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就改定了中央官制,其释放的改革信号不可谓不大。
接下来就是法律了。
一、 修律: 宪政始基
“宣统建元,宪政颁布,庶政维新。而与宪法最关切者尤莫如法律一项。”*吉同钧: 《乐素堂文集》卷五,北京: 韩城吉氏印行,国家图书馆藏1932年铅印本,第15页。及至1909年2月16日(宣统元年正月二十六日),法部尚书戴鸿慈上奏请求催收关于新订刑律草案的签注意见,清廷随即下旨催收,并于上谕中正式提出“法律为宪政始基”*故宫博物院编: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857页。一语,更是明白点出了修律与宪政的关联。
按计划,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中有关刑律的规定如下: 光绪三十四年,修改新刑律,由修订法律大臣、法部同办。第二年,颁布法院编制法,由宪政编查馆、修订法律大臣同办。第三年,颁布新刑律,由宪政编查馆、修订法律大臣同办。第四年,核定民律、商律、刑事民事诉讼律等法典,由宪政编查馆办。第六年,实行新刑律。第九年,宣布宪法,由宪政编查馆办。*《宪政编查馆资政院会奏宪法大纲暨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及逐年筹备事宜折附清单》,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初一日,见《清末筹备立宪史料》上册,第54页。
官方给出的时间表如此,民间更是急迫。在戴鸿慈、端方回京路经天津时,8万余名学生上书提出“奏颁宪法,更改官制,复为法律”。*《中华报》1906年8月20日;《汇报》1906年8月15日。转引自侯宜杰: 《清末立宪运动史: 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51页。按: 此处所言学生数目过于庞大,似有夸张。可见无论是清廷还是当时接受新知的读书人观念中,宪政-官制-法律亦已渐成为一个整体性有待引入的制度架构。
1907年8月13日,奕劻等奏请将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同日奉旨俞允。该馆与资政院之关系“一司编纂,一主赞定”,故其职责之一即“考核法律馆所订法典草案”*故宫博物院编: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8页。,事实上成为修订法律馆的上级机构,从而确立了修订法律事业附属于宪政框架的制度形式。
其后,对这一制度框架具有礼教意义冲击的,是有奏倡议礼学馆专派大臣与法律馆汇同商订法律。礼学馆之设肇端于两广总督岑春煊,但开办以来该馆形同虚设,“未见进一草案”,御史史履晋上折称,“今日欧风美俗渐染日深,衿缨之士不读礼经之子竞谈新学,以逾闲荡检为自由,以尊己卑人为平等,以犯上作乱为民权”,所以他提议修订法律之事必要“博通古今洞明中外之才不足以成”,也即礼学馆的人员参与。*史履晋: 《奏为礼学馆宜专派大臣官吏与法律馆汇同商订以维礼教而正人心折》,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十九日,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此折后刊于《大公报》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第3版。上谕此折发会议政务处议奏,颇值玩味的是,精通礼学且身在礼学馆的曹元忠拟《遵议礼学馆宜专派大臣管理与法律馆汇同商订疏》,称此议“揆诸情事,似多窒碍”。*曹元忠: 《笺经室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90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77页。此次议论结果是礼学馆的人仅在民律制定中得以参与,刑律则没有。
二、 修律宗旨的确立与礼教争议的由来
虽然有修律从属于宪政进程的意识与制度安排,但是清廷却并未将其视作脱离礼教的过程,尤其是在预备立宪之前的所谓修律,主要是“整理旧律”,“刑以弼教”尚为《大清律例》当然的指导思想。
清末新政前期(至预备立宪),刑律问题并未成为改革中心。早在张之洞主导的著名的《江楚会奏三折》中,即对新政中的刑律修订有过明确意见,“整顿中法”折中专列“恤刑狱”一条,但其中并未涉及《大清律例》条文本身的修改。在“采西法”折中,涉及律例方面的内容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谓:“至刑律,中外迥异,猝难改定。然交涉之案,华民、西人所办之罪,轻重不同,审讯之法亦多偏重。除重大教案,新约已有专条,无从更定外,此外尚有交涉杂案,及教堂尚未酿大事者,亦宜酌定一交涉刑律,令民心稍平,后患稍减,则亦不无小补。”*张之洞: 《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初五日,见《张之洞全集》第4册,武汉: 武汉出版社,2008年,第32页。可知,张之洞等人心目中修改刑律的原因为“驱民入教之患可渐除”这一由中外交涉而来的问题,而其采取的办法并非修改《大清律例》本身,而是用传统的慎刑明狱之法来整顿狱事,就刑律条文来说,其意见仅是补一“交涉刑律”。
李细珠先生认为,《江楚三折》可以作为清末新政第一阶段的总纲领。三折奏上后不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初二日,政务处奏《请改律例折》提出修改律例的办法,“应与公法参订互证,以办民教交涉之案,而商律附焉”。并指出改革法制之“大纲”,“一则旧章本善,奉行既久,积弊丛生,法当规复先制,认真整理;一则中法所无,宜参用西法以期渐致富强,屏除成见,择善而从,每举一事宜悉心考求”。*《政务处条议》,《申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十九日,第2版。《续政务处条议》,《申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日,第2版。
随即,清廷发布修律上谕:
中国律例,自汉唐以来,代有增改。我朝《大清律例》一书,折衷至当,备极精详。惟是为治之道,尤贵因时制宜。今昔情势不同,非参酌适中,不能推行尽善。况近来地利日兴,商务日广,如矿律、路律、商律等类,皆应妥议专条。著各出使大臣,查取各国通行律例,咨送外务部,并著责成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来京,听候简派,开馆编纂,请旨审定颁发。总期切实平允,中外通行。*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8册,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6—37页。
开馆编纂,即开设法律馆。清代本有律例馆,专司修订法律之事。开始是独立机构,其后归入刑部。此次开设法律馆,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草创,起初即用律例馆旧址,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正式开馆,中间经过官制改革冲击一度停顿,其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重新开馆。这一修律上谕将人员简派任务交给主导新政的三位重臣,最终三人商定选派沈家本与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三人意见中,尤以张之洞为主。其中沈家本久在秋曹,熟悉中律,且据董康言,沈家本与张之洞属“葭莩之亲”,也即关系较为疏远的亲戚,被举在情理中。而伍廷芳亦早年即进入张之洞、袁世凯视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二十三日张之洞奏,“查使美伍大臣熟谙外国律法,深通交涉”,后折又以“深幸得人”许伍氏交涉成果,*张之洞: 《请调伍廷芳、袁世凯协助议约致军机处、外务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二十三日;另有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请电饬伍廷芳迅速回国致军机处、外务部》一折,系袁世凯领衔,张之洞联名会奏。以上均见《张之洞全集》,武汉: 武汉出版社,2008年,第539—540页。关于三位大臣的商议过程,参见李细珠: 《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261页。二人一中一西搭配,得到三位举荐人的一致认可。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六日(1902年5月13日)上谕:
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俟修定呈览,候旨颁行。*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8册,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5页。另,中英《马凯条约》,有“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弃其治外法权”条款,见王铁崖编: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北京: 三联书店,1959年,第109页。诸多学者把这一条约看成晚清修律的起因,高汉成则考证《马凯条约》之签订实在清廷修律上谕之后。我们认为,不能仅仅以文本签订时间来考虑事件的内在逻辑,而且具体的开端原因对本文来说也不重要,其实中外交通以来,修律是必然的,引起争论也是必然的。
上谕指出须“参酌各国法律”。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意识到这一指示背后,并未有明确的修律宗旨。苏亦工先生即已指出:“所谓‘参酌各国法律’,‘务期中外通行’之类措词,微言大义,不过是个总体目标,并未提出一个明确的宗旨,令人不知底里。”*苏亦工: 《明清律典与条例》,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54页。据《邸抄》显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上半年,沈家本亦连续请假达五十余日,闭门不朝。*佚名: 《邸抄》,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905年伍廷芳、沈家本上《删除律例内重法折》即于翻译外国律典之外委婉地抱怨到,“现在各国法律既已得其大凡,即应分类编纂,以期克日成书。而该馆员等佥谓宗旨不定,则编纂无从措手”,并请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俾天下晓然于朝廷宗旨之所在”。对沈家本的犹豫,《大公报》的观察一语中的:“律例亟应大改,自不待言。惟沈、伍之才,虽能任其事而不能任其责。此事重大,非加派极有名望之王大臣,恐无人敢办。”*《时事要闻》,《大公报》1902年8月3日。大改王朝律典,兹事体大,沈家本断不敢自作主张。
这种情况下,沈家本等人的工作,只是接续清朝的修律定例,所以,在没有新的修律宗旨前提下,沈家本等提议先编订一部《大清现行刑律》以为过渡之用。大清律例自有定本之后,渐渐形成了修订定例。在沈氏上奏的《奏请编订现行刑律以立推行新律基础折》中云及此例:“伏查乾隆年间定章,修律年限,五年小修一次,又五年大修一次。”“然历届修订,仅就《条例》删改增纂,罕及于律文。”*董康: 《前清法制概要》,《董康法学文集》,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8页。事实上,俞江先生即已指出,“律文修纂事关重大,修订之后,各朝皆有不得妄议律条的规定。清代乾隆六年定制,律文再不得改动,例则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彻底堵死了律文随时损益的可能性,律不能随时代变迁而调整。”*俞江: 《倾听保守者的声音》,《读书》2002年第4期。至同治九年,“原有律文凡四百三十六条,例文凡一千八百九十二条”。*修订法律馆: 《钦定大清现行新律例》凡例,《续修四库全书》864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页。自此之后,则连大修小修之例亦停止,这也成为薛允升等职司西曹者念兹在兹的事业。所以,沈家本提议编订《大清现行刑律》,形式上是接续这一修订定例,而这完全是旧有体制内的应有之义。
可见,江楚三折对新刑律的意见确为新政前期的修律进程所遵从,即“只欲略采西法,修而不改”。*《时事要闻》,《大公报》1902年8月3日。在这种情况下,修律并不会引起礼教问题。然而从沈家本等人反复请求清廷“定宗旨”一事即可看出,这一保守的意见绝非他们所能满足。显然,如果他们还完全认同刑以弼教的旧律宗旨的话,就不必汲汲于请求另定宗旨。
相较大修律典,以沈氏之资历尚显人微言轻。所以尽管现有材料无法确知内情,不过我推测引起礼教问题的最根本原因,是“预备立宪”之后,以奕劻为首的在中枢推进宪政改革的主导者,倡导礼与宪不兼容,*早有学者指出,不宜过高估计沈家本在清末修律中的作用,在整个改律进程中,他很可能只是扮演执行者的角色而已。沈家本背后真正的决策者很可能是奕劻。高汉成先生已经注意到,在礼教派的攻击下,奕劻屡屡起到重要作用,并指出:“他对沈家本主持起草的《大清刑律》草案的公开支持和赞成,是《大清刑律》最终通过的关键性因素。”参高汉成: 《签注视野下的大清刑律草案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54页。由此引发以张之洞为首的儒臣集团的不满,对这一修律进程加以驳斥。只有中枢大员的鼎力支持,才可能让修订法律馆在上谕并无明定宗旨的情况下,采用最激进的刑律草案: 尽用西法,并且起草权都完全托付给延聘的日本人。
修订法律馆成立以来“三阅寒暑,初则专力翻译,继则派员调查”,因“各法之中,尤以刑法为切要,乃先从事编辑”。*沈家本: 《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刑律草案告成分期缮单呈览并陈修订大旨折》,故宫博物院编: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北京: 中华书局,1979年,第845页。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间,法律学堂开课,延聘日本法学博士冈田朝太郎主讲刑法,并成为新刑律修订过程中事实上的主导人员。冈田氏起草的《新刑律草案》,真正导致了传统中国律典的断裂。*据胡思敬云,新定法律草案即出自冈田之手,其引证历朝沿革,则取之薛允升稿本,法部郎中董康主笔。见胡思敬: 《国闻备乘》,北京: 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2页。按照冈田的记载,清末的刑法草案有六案之多: 第一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脱稿,此即法律馆具奏本;第二案为法律馆会同法部根据中外各衙门督抚对于第一案的签注意见修改而成,并于宣统元年(1909年)十二月具奏;第三案乃宪政编查馆根据第一案加以修正者;第四案为宣统二年(1910年)之冬,资政院法典股股员对第三案的修正本;第五案为经资政院三读通过的总则而分则未经议论完毕部分暂从第四案者合并而成;第六案为对于第五案,以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谕裁可军机大臣之修正案者,此即清廷最后颁布的新刑律定本。*冈田朝太郎: 《论中国之改正刑律草案》,此文系留庵译自日本《法学协会杂志》第29卷第3号,见《法政杂志》1912年第1卷第2期。亦参以冈田朝太郎: 《论〈大清新刑律〉重视礼教》,《法学会杂志》1901年第1卷第1期。冈田朝太郎(1868—1936): 日本东京大学法学教授,系清末修律中延聘的日本法学专家,专门负责刑法一门的起草。其中,第四案、第五案仅有相关人员的讨论可资研究,并没有形成正式法典文本。
六案底本都是冈田氏起草的第一案。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新成立法律馆,但《新刑律草案》已经由冈田朝太郎赶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设立的修订法律馆关闭之前大致起草完毕,冈田朝太郎介绍说:“法律馆将于明治四十年(1907年)被关闭,刑律草案虽有可能完成,然刑事诉讼法及其他附属法的编纂到底不能完成。我当时彻夜把管写作,到七月中旬右腋下起了鸡卵大的肿物,日日疼痛,其困难可想而知。由于日期紧迫,不可有一刻延误,用布包冰块敷在痛处,到八月上旬,条文和理由书终于脱稿,并交付委员长。”*据章宗祥:“修订法律馆最初成立时……新派尚无甚势力,提调数人皆刑部旧法律家”,不过此后由于沈家本好延用留日学生,尤其是新法律馆中新派分子渐多,这也是这一案得以顺利在法律馆内部通过的原因。参章宗祥: 《新刑律颁布之经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34页。及至新法律馆重新开馆,馆中同仁再行议处,“刑法一门不日即可脱稿”。*《修改法律之内容》,《神州日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月二十二日。
光绪三十四年(1907年)十一月,由修订法律馆所拟之《大清新刑律草案》告成,并由修订法律大臣将总则分则各条分别进呈。是年八月二十六日,沈家本即上《刑律草案告成分期缮单呈览并陈修订大旨折》,在公开的上疏中,*据传,董康与章宗祥曾于1905年起草过一部刑法草案,经冈田朝太郎审阅后,认为主要系参考日本《旧刑法》(1887年)而成,应修、应改之处甚多,乃建议重新起草法案。董章二人起草的《刑律草案》由孙家红先生发现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图书馆,整理本收于黄源盛主编《晚清民国刑法史料辑注》上册,台北: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笔者未见此草案,如按照孙家红先生考证所云,则至少董康等留日学生即早下定决心全袭日本刑法,不过其主张是否得到修订法律馆同仁一致意见仍存疑,且本文此处重在整个清廷公开层面的修律宗旨,故以沈家本此折为结点。沈家本也已经完成从“请定修律宗旨”到“陈修订大旨”的改变,沈家本奏称:“臣审查现时之民俗,默验大局之将来,综复同异,絜校短长,窃以为旧律之宜变通者,厥有五端。”其列举到: 一曰更定刑名,二曰酌减死罪,三曰死刑唯一,四曰删除比附,五曰惩治教育。*《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刑律草案告成分期缮单呈览并陈修订大旨折》,故宫博物院编: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北京: 中华书局,1979年,第845页。此处相关问题,可参李贵连编著: 《沈家本年谱长编》,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97页。
议礼与议律,向为历朝聚讼大端。熟谙旧律的沈氏恐怕比谁都明白,此案一出,必引起礼教争论,所以此奏新刑律的大旨,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了礼教问题。但纸终究包不住火。沈家本等进呈刑律草案之后,清廷谕旨将刑律草案“下宪政编查馆知之”。此后由宪政编查馆分咨京外讨论参考签注,由于此案基本乃是移植自日本法律*黄源盛先生早即指出:“如果细察整部大清新刑律正文的内容,几乎什九的条文都是有来历的,不是照张誊录日本、德国等国刑律,便是略加增减。”见黄源盛: 《大清新刑律礼法争议的历史及时代意义》,《中国法制现代化之回顾与前瞻: 纪念沈家本诞生一百五十二周年》,台北: 三民书局,1993年。,故而,此案一经公布即引起廷议一片哗然,“经宪政编查馆奏交部院及疆臣核议,签驳者伙”。*赵尔巽等: 《清史稿》,北京: 中华书局,2003年,第4190页。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七日,张之洞以“大学士、管理学部事务大臣”身份对新刑律草案加以发难。*关于此折前后史实,李欣荣先生有更详细的考辨可参,见李欣荣: 《如何实践“中体西用”: 张之洞与清末新刑律的修订》,《学术研究》2010年第9期。大旨如下,据许宝蘅日记:“今日学部奏驳修律大臣所定刑律草案一折。此事初发难于陈仁先,于南皮枢相前极论之,南皮遂嘱属稿。”陈氏“大旨谓新律于中国礼教大相反背,于君臣、父子、夫妇、男女、长幼之礼皆行减弃,且改律之意注重收回治外法权,而收回与否视乎国之实力,非改律足以箝其口,拟请另派大臣会同修律大臣将旧律之繁而不切者改,即将新律之增出者并入,南皮颇以为然”。不过同在学部的“严范孙、宝瑞臣两侍郎向来依附新学,崇拜日本,以此草案出于日本游学生之手,不愿加驳”,只因“此稿所驳诸条又关乎君臣、父子大伦,又不敢以为非,初有不愿会衔之意。二十六日会议于学部公所,南皮席间言诸君若不列衔,我当单衔具奏,严、宝不敢立异”。后“蒙古相国亦与南皮同意,于是严、宝乃输情于项城,欲为阻挠,后经蒙古将原稿略为修改,严、宝遂勉强附名”。据董康回忆,学部副大臣宗室宝熙亦参与修改此折,同时董氏记载宝熙改定之理由亦与许宝蘅所记不同,宝熙初不愿联署的原因是他看到张折之后,见此折因草案对“内乱罪”不处惟一死刑,“指为袒庇党人,欲与大狱”,因“大惊”问张之洞曰:“公与沈某有仇耶?此折朝上,沈某暨一干纂修夕诏狱矣!”张之洞回道:“绝无此决,沈某学问道德,素所钦佩,且属葭莩戚也。”宝熙又说:“然则此稿宜论立法之当否,不宜对于起草者加以指摘。”最后,此折“由宝改定入奏”。综合看来,董康此后多次提到有赖宝熙“规劝之力”才使得沈家本与自己的修律事业没被张之洞参劾,他的记载应更为可信。除开张之洞的儒臣立场外,促使张之洞于要员中首先发难的理由,还有一因,即官制改革之后,“臣部(引按: 指学部)职司教化,明刑弼教,理本相因”。故而,张氏“数月以来,悉心考核,查此次所改新律与我国礼教实有相妨之处,因成书过速,大都据日本起草员所拟原文。故于中国情形不能适合”。
在张氏看来,我国立法之本,为经典上规定的教之核心,“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书》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王制》曰:“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故此,“我国以三纲立教,故无礼于君父者罪罚至重;西国以平等为教,故父子可以同罪叛逆可以不死,此各国其政教习俗而异,万不能以强合者也”。洋洋洒洒,此签注总则开始即明确阐释中国礼教的内涵,也即表明西律之不适合中国处:
一、 中国即制刑以明君臣之伦,故旧律于谋反大逆者不问,首从凌迟处死。新律草案则于颠覆政府僭窃土地者为首魁或不处死刑,凡侵入太庙宫殿等处射箭放弹者或科以一百圆以上之罚金,此皆罪重法轻与君为臣纲之义大相刺谬者也。
一、 中国即制刑以明父子之伦,故旧律凡殴祖父母父母者死,殴杀子孙者杖。新律草案则凡伤害尊亲属因而致死或笃疾者,或不科以死刑,是祖父母与路人无异,与父为子纲之义大相刺谬者也。
一、 中国即制刑以明夫妇之伦,故旧律妻妾殴夫者杖,夫殴妾者非折伤勿论。妾殴杀夫者斩,夫殴妻者绞。而条例中妇人有犯罪坐夫男者独多,是责备男子之意尤重于妇人,法意极为精微。新律草案则并无妻妾殴夫之条,等之于凡人之例,是与夫为妻纲之义大相刺谬者也。
一、 中国即制刑以明男女之别,故旧律犯奸者杖,行强者死。新律草案则亲属相奸与平人无别,于对未满十二岁以下之男女为猥亵之行为者或处以三十元以上之罚金,行强者或处以二等以下有期徒刑,且曰奸非之罪与汲饮消眠同例,非刑罚所能为力,即无刑罚裁制此种非行亦未必因是增加,是业以破坏男女之别而有余也。
一、 中国即制刑以明尊卑长幼之序,故旧律凡殴尊长者加凡人一等或数等,殴杀卑幼者减凡人一等或数等。干君犯义诸条立法尤为严密,新律草案则并无尊长殴杀卑幼之条,等之于凡人之例,是以破坏尊卑长幼之序而有余也。*以上所引张之洞议论,均见《奏为新定刑律草案多与中国礼教有妨》折,佚名: 《刑律草案签注》(油印本)第1册,1910年,国家图书馆藏,原书无页码。
可见,张之洞对新刑律的意见,是以明刑弼教观念观察新刑律的典型。刑以弼教,教之所重,在刑中亦以轻重相体现。据许宝蘅云:“南皮请令会同法部按旧日刑律,以名律居首,实与中国伦常礼教互为经纬,若改从外国刑律,非先改亲族法不可,不然终不能合符。”*许宝蘅: 《巢云簃日记》,《近代史资料》总第115号,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4页。这其实也代表了当时很多督抚的意见。
前文已及,对于大清律例由中外交涉而来的律文之变化,儒臣张之洞可以接受,但很明显,张之洞的意见还是以明刑弼教为出发点,且未因清廷立宪进程的展开而改变。然而,沈家本主持的修律,却在事实上将宪政的要求指向了刑律中的礼教内容。
回想新政的修律上谕,并无礼教明文。壬寅年上谕著派沈家本、伍廷芳修律亦未提及礼教的问题。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当时清廷上下未曾料及修律会触及礼教的问题。等到《刑事诉讼律》与《新刑律草案》修成,以张之洞为代表,签注意见纷纷集中于其中的礼教问题,促使清政府做出回应。张之洞等人从礼教的角度反对新法之举引起了清廷的注意。稍后,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五日(1907年10月11日),清廷谕令修律大臣沈家本等人修订法律要“参考各国成法,体察中国礼教民情,会通参酌,妥慎修订”。*《清实录》第8册,北京: 中华书局,1987年,第661页。此时,清廷已经在原来的修律宗旨“参酌各国法律”之后再加上一条“体察中国礼教民情”了。*李细珠: 《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271—272页。但此时,修律大臣已经完成了《新刑律草案》的起草工作,并于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1907年10月3日)和十一月二十六日(12月30日)先后将总则与分则上奏朝廷。1907年,张之洞等人对《刑事诉讼法草案》的批驳之后,上谕下达:“各国从无以破坏纲纪干犯名义为立宪者,况中国从来敦崇礼教名分谨严。采列邦之良规,仍宜存本国之礼教等因钦此。”*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初六日上谕,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5册,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805页。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二十七日,又有一道上谕《修改新刑律不可变革义关伦常各条谕》:
惟是刑法之源,本乎礼教,中外各国礼教不同,故刑法亦因之而异。中国素重纲常,故于干犯名义之条,立法特为严重。良以三纲五常,阐自唐虞,圣帝明王,兢兢保守,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今寰海大通,国际每多交涉,固不宜墨守故常,致失通变宜民之意,但只可采彼所长,益我所短,凡我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庶以维天理民彝于不敝,该大臣务本此意,以为修改宗旨,是为至要。*故宫博物院编: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858页。
礼教的争议,逼着清廷表态了。*当然,只是说公开地成为廷议热点,毫不意外,真实情况是自制定新刑律起,就一定会伴随着礼教的争论。据吉同钧回忆:“当时馆员十余人列座公议,鄙人首以不适实用,面相争论,并上书斥驳,无如口众我寡,势力不敌。随即刷印散布,外而各省督抚,内而六部九卿,群相攻击,举国哗然。”可见,尽管参与修律诸公在以后总是说修律时他们处于劣势,但是,或许在修律的圈子里,真正处于劣势的恰恰是守旧一方。否则,《大清新刑律》的草案就很难出台。另外,虽然吉本人没说,但以吉同钧为首的法部“守旧者”对新刑律草案的礼教发难,有着某种重要的作用。因为,律例乃专门之学,非治律出生根本无从置喙。各省各部能立生反应,言之凿凿,群狺汹汹,其中必有所恃,而所恃者,要么律学专家,要么法政留学生。见俞江: 《倾听保守者的声音》,《读书》2002年第4期。这样,汇集于华夏律典中的礼法关系问题再次被激活。与古代中国不同的是,这次礼法关系再度被提出,乃是基于礼教原则面临被根本抛弃的危险。这也是近代之变在律中的体现。在立宪的前提下,围绕修订刑律的争论,区分只在于是否抛弃刑律中的礼教因素来引入宪政原则。
三、 清廷支持《新刑律草案》的有限礼教化
按许宝蘅日记记载,张折所上日期为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七日,“两宫览后发下”,核以《刑律草案签注》所云“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七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可知此折乃上奏当日随即旨交军机大臣,“庆邸遂命拟交旨片,仍著修律大臣再详细修改”*《许宝蘅日记》第1册,北京: 中华书局,2010年,第184—185页。。
1908年5月,法律大臣会同法部据签注意见修改刑律草案,1909年12月修正案告成,复由法律大臣会同法部上呈。这是新律草案的第一次修正,主要变动是草案正文外增入有关礼教的五条附则。对这一改动,法部尚书廷杰与沈家本联名上疏说明:“惟中外礼教不同,为收回治外法权起见,自应采取各国通行常例,其有施之外国不能再为加严,至背修订本旨,然揆诸中国名教,必宜永远奉行勿替者,亦不宜因此致令纲纪荡然,均拟别辑单行法,籍示保存,是以增入《附则》五条,庶几沟通新旧,彼此遵守,不致有扞格之虞也。每条仍加具按语,而于各签注质疑之处,分别签覆。”*廷杰、沈家本: 《上〈修正刑律草案〉疏》,转引自李贵连: 《沈家本年谱长编》,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7页。短短的五项附则,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对未加附则的《新刑律草案》,持旧派立场的刘锦藻云:“此编全系剽窃日本成法,并未将中国民情风俗法令源流通筹熟计酌量变通。”而对于法部加上附则的提议,刘氏则大为赞赏,认为这是“补救之计”。*刘锦藻: 《清朝续文献通考》,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9918页。
当然这一针对尽采西法的《新刑律草案》的礼教化改变非常微弱,甚至并非正文的改动。所以,礼教条文是否应该进入刑律正文,成为下一阶段争执的重点。《修正刑律草案》的附则第二条内有云:“中国宗教遵孔,向以纲常礼教为重……况奉上谕再三告诫,自应恪为遵守,如大清律中十恶、亲属容隐、干名犯义、存留养亲以及亲属相奸相盗相殴并发冢犯奸各条,均有关于伦纪礼教,未便蔑弃,如中国人有犯以上各罪,仍照旧律办法另辑单行法以昭惩创。”*故宫博物院编: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887页。
对此,有醇儒之誉的劳乃宣针锋相对:“子孙违反教令之条均有关于伦纪礼教,为中国人所不可蔑弃者,应修入刑律正文之内。”*劳乃宣辑: 《桐乡劳先生(乃宣)遗稿》,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357册,台北: 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915页。其附则中所谓“中国人另辑单行法”的说法更让劳乃宣恼火:“窃维修订新刑律本为筹备立宪统一法权之计,凡中国人及在中国居住之外国人皆应服从同一法律,是以此法律本当以治中国人为主,特外国人亦在其内,不能异视耳,非专为外国人设也。今乃按照旧律另辑中国人单行法,是视此新刑律专为外国人设矣,本末倒置莫此为甚!”*劳乃宣辑: 《桐乡劳先生(乃宣)遗稿》,第887页。
劳氏的义愤不为无见,刑律乃一国之重典,而主持修律之人居然有如此看法,清末中国在宪政旗帜下的制度引进之虚弱不堪可见一斑。问题是,荒谬以至于此的立法逻辑,如何就轻而易举地获得当时中国人,甚至是如沈家本等精研旧律学者的高度认同?
从思想层面上,沈家本在法家与西方法律学之间有意识地对接,为有旧学根底的他提供了接受西学的入口。中国古代只有律家、律学、律治而无法家、法学、法治。信奉礼教的儒生,严礼法之辩,以礼治无刑为盛世理想。比如吉同钧即云:“士人束发入学,即读四书五经,志在圣贤;谈及刑律,薄为申韩之学,辄鄙夷而不屑为。”*吉同钧作为律学大家薛允升的嫡传弟子,其中律造诣世所公认。见吉同钧: 《刑法为治国之一端若偏重刑法反致国乱议》,吉同钧: 《乐素堂文集》,国家图书馆藏,北平: 中华印书局,1932年,第15页。沈家本于《法学会杂志序》对此状况有强烈的批评:“举凡法家言,非名隶秋曹者,无人问津。名公巨卿方且以为无足轻重之书,屏弃勿录,甚至有目为不祥之物,远而避之者,大可怪也。”沈家本: 《历代刑法考·寄簃文存》第4册,北京: 中华书局,1985年,第2244页。而沈家本等人的对接则使传统“流于苛刻”的申韩之学得到发掘。*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一肯定法家申韩之术的思路,并非仅由知识引进活动而来,比如传统中人汪士铎曾言:“管商申韩孙吴,后人所唾骂,而儒者尤不屑置齿颊。要而论之,百世不能废,儒者亦阴用其术而阳斥其人尔。盖二叔之时已不能纯用道德,而谓方今之世,欲以儒林道学两传中人,遂能登三咸五,拨乱世而反之治也,不亦梦寐之呓言乎!”见萧穆: 《汪梅村先生别传》,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资料丛刊》第43辑,台北: 文海出版社,第581页。沈家本的名篇《法学盛衰说》以呼吁传统“法家”申韩之学“由衰而盛,庶几天下之士群知讨论,将人人有法学之思想,一法立而天下共守之,而世局亦随法学为转移”*沈家本: 《法学盛衰说》,《历代刑法考·寄簃文存》,北京: 中华书局,1985年,第2143—2144页。,正是道出了传统“法家”在转型时代争夺自身话语权的要求。时人对此亦多有体认,“清之季年,朝野上下鉴于环球法学日进精微,瞿然知墨守故步之不可为治,于是申韩坠绪渐有发明,而泰东西之成宪英美大陆之学说,益复竞相纂述粲然著于国内。”*王树荣: 《考察各国司法制度报告书提要》,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藏太原监狱石印本,1914年。在这一背景中,礼学已经无法以传统时代兼括言说道德与制度的方式容身。换言之,基于经典的礼学研究再也无法为“出礼入刑”的全面治理模式提供无可置疑的学术基础。
无疑,处于西方文明的强势入侵之下,沈家本的考虑更具有应时的色彩。庚子年清廷迭经国变而无奈西狩,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二月初五日,沈家本一路颠簸前往西安,途经郑州时专门谒子产墓并赋诗一首,末句为:“小学邻强交有道,此人端为救时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沈家本就修民商法上疏,即有“救目前危亡之祸”一语。当初郑子产不顾旧贵族之责毅然变旧礼制而铸刑鼎,沈家本在清末面临的亦为新的内外交迫。此时作为律学大家的他心中一定想到了子产在郑国的艰难改革。
而更为微妙的原因恐怕是沈家本内心对旧体制的彻底失望。民国元年元旦,沈家本日记载:“元旦,晨阴午晴。未出门。今日本应诣皇极殿行朝贺礼,因服色不便未去,同人相约如此。呈递如意两柄,仍赏还。”*《沈家本日记》,《沈家本全集》第7册,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56页。语气之淡然令人吃惊,辛亥鼎革,如此大员对先朝文物制度毫无半点留恋,可见,在沈氏的心里早对这一体制丧失信心。二千年来,由儒生设想的以礼教制约秦制的思路随着传统中国制度的一步步转衰而毫无实现的可能,并使得整个制度体系及其社会结构日益僵化,在这一制度形式裹挟之下,郡县制中国以礼乐为虚文的一面展露无遗。*当然,亦有另一批读书人抱持如张之洞一般的谨守礼教立场。比如,虽然旧体制积重难返,但针对刑律中礼教原则的退隐,汪穰卿等人仍力言“宜慎”,因为其所关绝非刑律而已。其云即使法律大臣本意“非果敢于变国教”,但事实的情况是“未有刑律废之而礼教能存之也”,所以在律典中礼教存废之事,甚至重于“立宪”本身,故而力诫其“慎行”。见汪康年: 《痛论颁行新刑律之宜慎》,《汪穰卿遗著》,上海图书馆藏钱塘汪氏铅印本,1920年,第5—8页。
在晚清中西思想与制度的剧烈交锋中,这一对旧体制的失望情绪极易促成一股礼宪对立的思潮,并演化成为政治实践中的直接移植西法,不过由于郡县制时代皇权礼教治天下的压力在,这股思潮终于没有完全得势。
皇权既需要礼教这一温情脉脉的外衣,一批批抱持儒学理想的士子即以礼教来制约皇权,此为郡县制时代礼教与皇权关系的另一面。以此再返观前引张之洞奏折,张氏如此执着于律典中存续礼教原则的苦心方得更进一步的展现。作为朝廷重臣,张折更近于礼教宣言而非仅关注于律中之礼。就文本来说,张此处所奏与劝学篇中论述几乎完全一致,《劝学篇上·明纲第三》云:“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张之洞全集》第12册,武汉: 武汉出版社,2008年,第163页。现有研究者多囿于“保守”这一现代社会科学话语来对张折及其后清廷这一维护礼教上谕进行解读,进而据此认为是礼教派的胜利云云,恐怕未能洞悉传统礼律关系的精微之处。在传统语境中,天子宣示认同礼教,其最大意义首先不在于所谓保守,而在于承认自己接受礼教之制约。也许在这一脉络下观察张之洞以礼教为旗帜反对新刑律草案的“尽弃”礼教,其真正意义才得以彰显,传统礼律关系的一大关节是礼教可以形成对君权的制约而律典不能,儒学名臣张之洞不可能不了解其中的隐微,惟此为廷议,无法亦不必明言。
关于这一点,在张之洞、郭嵩焘等一批批儒学名臣以礼教“尊尊亲亲”原则而对慈禧以光绪、宣统入继大统相规制的努力中得到展现。今即以宣统承继大统为例以见一斑。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帝崩,无子,故而大统承继问题再成疑议。据《慈禧外纪》载:“太后初定嗣位,世续、张之洞皆以宜立长君为请,太后怒斥之,始定议。”遗诏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嗣皇帝承继穆宗为子,兼承大行皇帝之祧”,亦即承继穆宗,兼祧光绪。据张寿安先生的研究,这里,世续与张之洞请立长君,与当年文祥请立“溥伦”一样,都是从礼制的立嫡、立长、昭穆次序上维持帝脉的独立性。对此,张寿安先生评论:“立国本有定制,脱却制度,纵恣权欲,岂能恒长?”所谓“礼者,其为政之舆”,此评正是在肯定张之洞等礼学名臣以礼义维系政治的苦心。*张寿安: 《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整》,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2页。这点,也正是此谕的首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前引《修改新刑律不可变革义关伦常各条谕》亦在元年元月公布,距离光绪帝崩还不满百日,也即距离由宣统入继大统而来的礼教争论时日无多。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张之洞心里肯定是将二事联系起来考虑的,在他看来,一旦从律典打开了礼教对制度形式制约的缺口,那么后果可能是礼教被整体性的抛弃,皇权亦无从约束。
结语
诸种合力,造成清廷官方自始至终都谨守礼教底线。除开前引光宣两朝明令修律不得更改伦常上谕外,在沈家本去职一事上,更可见清廷在最后的时日仍未抛弃修律的礼教宗旨。宣统三年(1911年),沈家本提出辞去修订法律大臣和资政院副总裁两项职务的请求。二月二十二日,清廷下谕:“以大学士世续为资政院总裁,学部右侍郎李家驹为资政院副总裁。”*《宣统政纪》,《清实录(附宣统政纪)》第60册,北京: 中华书局,1987年,第886页。金毓黼系之二月二十二日,金毓黼辑本: 《宣统政纪》卷三二,辽海书社,1934年,第9页。注意,此处沈家本的替代者,即一贯重礼,当年与张之洞一起请立长君的大学士世续。又谕:“命法部左侍郎沈家本回任,以大理院少卿刘若曾为修订法律大臣。”*《宣统政纪》,《清实录(附宣统政纪)》第60册,北京: 中华书局,1987年,第886页。沈氏所谓请辞,恐怕只是一种政治操作。实际的情况更可能是沈氏遭到奏劾,笔者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查到奏折一封,其谓:“查法律馆初设即派沈家本充修订法律大臣,原以其中律尚精必能审慎无弊,乃自任事以来,一切任馆员主持,宗旨谬误,以致所订法律动与礼教背驰,显违谕旨,今奉旨改派刘若曾,是沈家本修律不善为圣明所深悉。刘若曾学术素优,应请饬其持正宗旨,毋蹈沈家本故辙,致负委任。”*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奏请饬派江宁提学使劳乃宣帮同修订法律事》,档案号04-01-01-1114-006。此折既无具奏人又无具奏时间,但其背后毛笔行书写有“奏折原缺宣统三年十二月”字样。考此折后面推荐“帮同修订”法律之人,专门提到劳乃宣,且又说到:“上年十二月十八日宪政编查馆奏请饬劳乃宣赴任,称该员研究律学,新旧贯通,请派该员为该馆一等资议官。”查此折提到劳乃宣赴江宁提学使本任之折,应为宪政编查馆大臣奕劻等《奏为馆员劳乃宣经手事竣请饬赴江宁提学使新任并派充本馆资议官事》一折,这一奏折奏劳乃宣有事拖延,内中提到:“惟该员研究律学,颇能新旧贯通,明年为臣馆复核民律之期,拟派该员充臣馆一等资议官,届时遇有讨论此项民律须免为咨询者并拟电调其暂行来京,同臣馆在事各员悉心审议,俾昭详慎恭候。”正是上折所谓“研究律学新旧贯通”之折,奕劻此折所奏时间为“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则此折时间认定为宣统三年十二月应为大致不误。小小的一个错误是,此折误以为奕劻一折的上奏时间为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实际应为十二月二十八日。见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由此可知,此时清廷确实已经否定沈家本一任引入西律的修律宗旨。饶是奕劻弼护,在宣统二年上奏中称新刑律“与现行刑律宗旨相同”,也即合于旧律礼教,亦难以挽回清廷意识到沈氏新刑律尽弃礼教的事实,或者沈家本成了奕劻的替罪羊也未可知。见奕劻等宣统二年: 《奏为新刑律分则并暂行章程未经资政院议决应否遵限颁布折》,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宪政编查馆录副奏折,档案号3-152-7474-72。此时新刑律业已颁布,清廷是否真要恢复旧律不得而知,历史留给大清王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仅仅从历史的偶然性来说,张之洞在世时,由于其巨大的影响力,可以使伍廷芳主导的英式刑事诉讼法直接被否决,其后沈家本主导的大陆法系色彩浓厚的新刑律草案却历经清末多次争论及辛亥之变而阴差阳错得以颁行后世,良可一慨!可见至少沈氏去职的原因之一,即是与清廷所定“修律宗旨”相违背,由此可知直至清亡前夜,清廷对修律宗旨仍始终坚持礼教的旗帜。*甚至清廷最高统治者还刻意在礼教与宪政之间建立关联。宣统元年(1909年)上谕内阁各部院衙门拟奏慈禧尊谥时,论及其文治武功有云:“比者颁布立宪年限,薄海欢呼。此实远绍唐虞三代好恶同民之心传,一洗秦汉以来权术杂霸之治体。”《宣统政纪》,《清实录(附宣统政纪)》第60册,北京: 中华书局,1987年,第15页。这里涉及问题非本文主旨,拟另文详述。
故此,针对尽用西法的《新刑律草案》的有限礼教化修订才成为可能,亦在某种程度上是郡县制时代直接移植西方律典之必然。其后这五条附则历经删修,既未如醇儒所想加入正文,亦未便完全删去,而终于以《暂行章程》形式发布*《暂行章程》与附则五条大旨相同而微异,具体区分可参陈新宇: 《〈钦定大清刑律〉新研究》,《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新刑律草案》最终以这一形式体现礼教。这一有限礼教化的刑律草案最终在资政院部分得以通过*李启成点校: 《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上海: 三联书店,2011年,第589—681页。,并由奕劻主持的宪政编查馆定下颁布日期。*虽然争执依然存在,对此有限的存续礼教,旧派自然不满足,而在新派看来,“有此暂行章程,而新律之精神尽失”。江庸: 《五十年来中国之法制》,上海申报馆编: 《最近之五十年》,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正由于礼教原则与君权有直接关联,所以礼教原则在刑律中的彻底消退,必定要等到皇权消失之后。这一步障碍的扫除,由辛亥革命所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