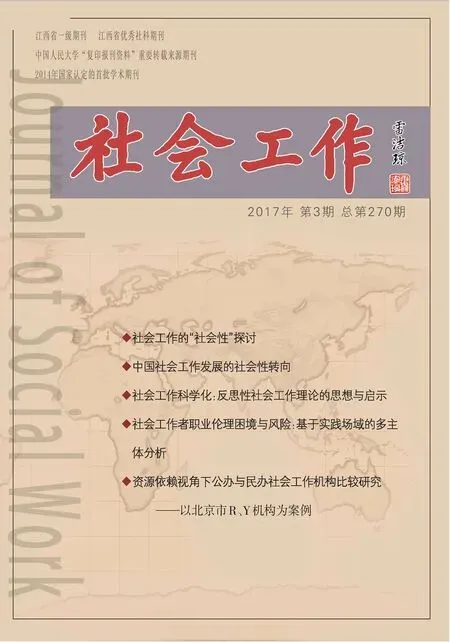社会工作的“社会性”探讨
陈锋 陈涛
社会工作的“社会性”探讨
陈锋 陈涛
在一些社会工作的理解与实践中,存在着片面而错误地强调专业性而缺失社会性的偏向。也有一些论者在对社会工作之社会性的认识上有偏颇,从而将其与专业性对立起来。本文力求从社会学、社会理论及社会心理学等关于社会性的论述出发,辨析确认社会性的全面准确意涵;进而寻求更好地理解把握社会工作的社会性含义。本文提出,社会性最基本的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联系性,而社会工作之社会性即是贯注这种人与人交往联系的视角,以之为目的和手段。同时,社会工作的社会性也正是其专业性之所在,其专业性与社会性之间并无矛盾,而恰恰是统一的。
社会工作 社会性 “社会的”工作
陈 锋,社会学博士,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文化艺术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讲师(成都 610103);陈 涛,社会学博士、社会工作文学硕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主任(北京 100089)。
本文关注社会工作的“社会性”,尝试分析探讨此种“社会性”的含义,回答社会工作为何被称作“社会的”工作(socialwork)。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工作的实践在世界上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在中国,所谓现代的、专业的社会工作也已有数十年的发展。就中国的情形来看,人们在发展和实践这种社会工作时,愈益强调其专业性,强调其是一种“专业的”工作,并因而要追求相应的工作品质和职业地位。
在许多具体的实务当中,社会工作专业性的要求常被引向对社会工作者工作的技术水平的要求,意味着社会工作者在开展工作时要尽可能展现特定而明晰的程序、方法与技巧,并最好能熟练使用各种细化的技术工具(像测评表格之类)。在此,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被转喻为它的“技术性”;并且经常地,使社会工作者的实务活动越来越多地卷入各种文字工作和技术处理工作中。老实说,社会工作者在沦为“写工”的同时,其基本社会属性——与服务对象的社会交往——也大大减弱。这种情况当然与现行的社会工作服务体制有关,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很多地方在实行“项目制”的社会工作服务时对项目的各种管理要求造成的,但是,它也源于前述的对“专业性”的那种强调,而且是有很大误识的强调。
从更宽广的角度视之,社会工作因缺失社会性而引人质疑,还有更多的表现。这一点无论是对尚处发展初期阶段的中国社会工作还是对相对较为成熟的西方社会工作而言,都有类似之处。西方早就有业内业外的人士指出日趋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或隐或显地持有病理学视角,实际上采用了“医学模式”来处理社会工作服务对象与其环境的问题,偏重个案工作的聚焦也限制了其对社会目标的关注和社会变革的承担,甚至于导致“责怪受害者”(Ryan,1976)、背弃了自己应有的使命(Specht&Courtney,1994)。在中国,我们同样可以观察到种种表现:制度化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首重个案,将心理辅导或治疗混同于社会工作的服务,不少社会工作者只关注和处理“个人的问题”(personalproblems)而很少展现改变环境的潜力、更遑论实现社会结构性的改善。在某些场合,以“学校社会工作”为例,不难见到这样的情形:“学校社会工作”变成了“学生社会工作”,进而再变成了“学生工作”,而其中的“社会性”不说荡然无存,至少已经失落很多了。
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工作?它为何被称作“社会工作”而不是别的什么工作或者仅仅是“工作”?它的“社会”涵义究竟是指什么?它如何才能展现出如它名字所示的“社会性”?虽然看起来也许不少人认为社会工作是什么的问题早已经解决(那么多的教科书已给出了定义),但追根溯源,回答它为何被称作“社会工作”而不是别的名称,它的“社会性”到底是指什么,这件事并不简单,却又常常受到忽视。而若不能很好地回答这问题,那么,对社会工作的认识与把握还会有许多偏差,在实务中,就可能做得越多,离它的本质属性和目标越远。
在这一点上,香港社会工作学者甘炳光有同样的担忧与关切。几年前,他在审视香港以及某些西方社会工作的现状时,指出存在着一种“去社会化”的偏向,因而提出“社会工作的‘社会’涵义——重拾社会工作中的社会本质”(甘炳光,2010)。他指出,香港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社会工作实务愈来愈着重个人辅导工作及专注于临床治疗理论与技巧的发展,也就是有一种“去社会化”的情况。对此,他提问道:社会工作是被称为“社会工作”,而不是“治疗工作”、“辅导工作”或“个人照顾工作”,那么怎样才能体现其“社会”的涵义与本质呢?甘炳光认为,社会工作之“社会”涵义有六项:社会关怀及意识、社会的弱势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建构个人问题、社会改变、社会公义。为了更好地体现社会工作的“社会”涵义,他认同社会工作更准确的名称或应叫做“社会公义工作”或“临床社会公义实践”或“公义治疗”。有趣的是,他还提到有论者认为:愈专业的社会工作可能就愈远离社会(殷妙仲,2009)。如此,似乎在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与“社会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对立或紧张。是不是这样呢?笔者正在此点上,在基本同意甘炳光呼吁重拾社会工作中的社会本质这一立场的同时,也意欲就此“社会本质”或“社会性”究为何所指与之做出讨论,并对此种“社会性”与其“专业性”之间到底是何关系提出不同的看法和结论。当然,在笔者看来,各个问题的逻辑关系是先关于社会工作的“社会”涵义是什么,其“社会性”究竟何所指,再是关于这种“社会”涵义和“社会性”与其“专业性”的关系为何种。因此,本文将先就社会工作的“社会”涵义或“社会性”之意味,尝试从更多、更充分的角度加以探讨。
在社会学中,20世纪即有论者谈论“社会的消失”(Gouldner,1971)。这样的论点是说,随着数字技术等现代科技的发展,还加上其他因素如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结果,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互相全人投入、有密切联系的“社会性”交往愈趋消失,而作为整体的“社会”也不复存在。因之社会学这门研究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的学科亦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机。可以合理地推想一下,倘若这立论成立,无论是指作为一个曾经想象为有机整体的“社会”(society)之消失,还是指人与人之间那种“社会的”(social)交往和联系之终结,则不独社会学将失去其学科赖以立足的根基,社会工作亦然,因而亦无讨论其“社会”涵义或“社会性”意味的基本前提。是故,换言之,对社会工作之“社会”涵义和“社会性”有关问题的探讨,值得将之放诸社会学乃至一般社会理论的更大视野中进行,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它。
二、理解“社会性”的不同角度
如前已述,本文关注的是社会工作为何是被称为“社会的”(social)?这种“社会性”(socialness)究竟意味着什么?除了其他角度(如甘炳光的角度),笔者首先尝试从一些更一般性的理论层面来进行探究,也就是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理论(甚至社会哲学)等关于“社会的(social)”之义的探讨与论述开始。
在社会学中,什么是“社会的(social)”、何谓“社会性(socialness)”?是绕不开的话题。就算是偏重宏观、整体取向的社会学,它可能更关注整个“社会(society)”,也仍然要论说人的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人们的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hip),或者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这其中始终有对于“社会的”或“社会性”的或明或暗的认识。不过,对这些认识观点做详尽而复杂的分析并非本文的重点。仅从简单的解读来说,偏重宏观整体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其或认为,“社会的”基本涵义就是指人和人之间的互动或交互行为;再简单地说,就是指人相互有各种交往(而不论交往的基础和内容是什么)。而“社会性”之所谓,也就是指这种交往的普遍性与基本性——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人一定要跟他人来往,这种相互来往就是“社会性”,而不管它们是出于什么原因、为了什么目的等等。应当指出,实证主义社会学一般假定了作为整体的“社会(society)”之实体存在,的确其更关注大社会层面的问题与认识,而对“社会的(social)”之探讨和论述并不是其重点。
与实证主义社会学有所不同,人文主义的社会学对什么是“社会的”或“社会性”有更为细致的讨论,也显示了其不同的人性与社会(society)假设。以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克斯·韦伯为例,其核心的关注在人的“社会行动(socialaction)”。他指出这里“社会的(social)”的涵义是意味着行动者的行动赋有主观意义、同时并且是指向他人的。他还主张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或社会唯名论,认为有意义的行动的上限是如前所述的个体的社会行动者,也就是说,只有个人才能视为社会行动分析的主体,而像“民族”、“国家”诸如此类的集体只是个人社会行动的复合概念(马克斯·韦伯,1998)。同样比较简单地归结来说,人文主义社会学或认为,当说到某些人与人的关系是“社会的”、具有“社会性”,或当我们在任何场合用“社会的”这个形容词来指称某事某物时,它不仅仅是指人们之间有来往(且可能是较持续稳定的),更区别于说它是“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或“文化的”。换言之,“社会的(social)”和“社会性(socialness)”是有着特别的涵义所指。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之间存在各种交往和关系、他们的共同生活中也有各式各样的活动,但其中只有某一些是可以称为“社会的”、具有“社会性”,另外一些则得称为“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或者“文化的”。如此,也才使得社会学(sociology)或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的研究领域能够区分于诸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等而有其独立的价值。更进而言之,人文主义的社会学或社会理论多半会将“交互主体性”界定为此种“社会性”。其倾向于认为,当人与人是以各自作为有着主观意义或想法的“主体”(subject)存在而发生相互的交往关系时,这种交往和关系才可称之为是“社会的”而具有“社会性”。反之,任何缺乏“主体性”(subjectivity)特别是“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的交往和关系都不能称之为“社会的”,也不具备“社会性”。比如,它们可以称为动物性的交往(本能反应、生理活动),个体自身的心理活动,纯粹受利益支配的经济交往与关系,只受权力驱使的政治活动及关系等等。简言之,在人文主义的社会学者或社会理论家那里,“社会的”和“社会性”是有所特指的涵义,较严格持这种立场的看法认为,它是指一种“交互主体性”,意味着人与人要各自作为主体而又相互投入、相互渗透和影响。
当然,不那么严格的人文主义社会学或社会理论,以及其他社会学或社会理论,还可能对如何理解“社会的”及“社会性”提供更多的观点意见。例如,或者可以把人看作是更复杂多面的一种存在,因而,当他们发生交往、形成关系时,其中既可蕴藏着动物的本能、心理的活动,还可夹杂着主观意义、客观利益乃至权力因素等诸多东西,而“社会的”可以包含所有这些成分内涵,正是意指这样一种综合的、交融的状况;而“社会性”之所指,则不限定于指“交互主体性”,亦容纳了其中的经济性、政治性、规范性、象征性等方方面面,是指所有这些性质的融合或结合。换言之,凡涉及人际和关系的层面,恰恰是反映此种交往与关系之属人的而又多面多维度的综融性质,皆可以“社会的”一词以统摄之,而“社会性”也就是与“个体性”和“单一性”相对的属性。
概言之,在社会学或社会理论(乃至一些哲学)中,关于“社会的(social)”及“社会性(socialness)”之理解,有三种不同层次:最一般的指人与人的交往和联系性,对应区别于“个体性”;处于中间的指人和人交往联系的“综融性”,有别于“单一性”(如某种纯经济交往关系、纯政治权力关系、甚至纯文化象征性的关系等);最后在严格人文主义的理解中指的是“交互主体性”,一种人与人相互投入且交流主观意义的交往联系状态及属性——或者类似哈贝马斯有关“沟通理论”的论说(哈贝马斯,2004)。
除了社会学或社会理论,在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以及所谓一般的关于“人类成长”的理论中,“社会的”涵义则以个人作为焦点,常常是相对于个体之“生理的”(physical)、“心理的”(psychological),或有时还有“道德的”(moral)方面来谈论。在此,“社会的(social)”是个人在如上那些维度或方面之外的一个存在与运作的维度或方面,实即意指其与他人交往和联系的维度或方面。因此,我们可以分别地讨论一个人在不同阶段的生理发展、心理发展、社会(性)发展乃至道德发展的情况;而其中,“社会(性)发展”指向与他人交往的范围、水平、程度等状况之变动(通常应当是提升的)以及有关能力的变化(增长与增强)。在静态上,我们也可以考察一个人或不同人表现出的“社会性”功能运作的状况及水平等,例如,与他人交往联系是频繁顺畅还是相反,等等。那么,以此推之,在这里“社会性”归结地说也就是指个人与他人有效交往联系的特性。
三、认识社会工作的“社会性”
梳理并综合以往一些理论或论述的相关含义,笔者认为,中文里关于社会工作之“社会”涵义的讨论,可能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具体所指:一是指形容词“社会的”,对应于英文之“social”;另一指的是名词“社会”,对应于英文之“society”。这其实与社会学或社会理论中本身也混杂了对大“社会”和“社会的”之关切与讨论的情形相似。但它也正是造成某些讨论陷入某种混乱或至少是紧张的原因之一。
无论如何,在形容词“社会的”之涵义上,在与它相关联的“社会性”(socialness)之意味上,已有的理论分析可以说明,其基本之义就是“与他人的交往和联系”。关于社会工作之“社会”涵义或其“社会性”之意味,另一重讨论实际上对准的是名词的“社会”及与之相连的大社会视角,或甚是“全社会性”(societalness)问题。如甘炳光所阐论的,社会工作欲成为一种站得住的实践,不能缺乏对大社会环境的关注,不能须臾或忘它对个人处境的影响,也不能不致力于在实务活动中谋求更大的社会目标、促进“社会(society)”的进步改变。
不过问题在于,若社会工作真的为了上述的考虑而更应当成为“社会公义工作”,或者它原来的英文名字也得改为“societalwork”又或是“sociologicalwork”,社会工作者的主要干预层面是在宏观制度结构上、工作的对象似应变为社会制度政策或“大的社会”等,这是否又合于其本意与本义?这还是“社会工作”(socialwork)吗?
此外,侧重主张从大社会角度理解社会工作之社会取向或社会性(scoietalness)的论述,多少采取了反对“专业性”的立场,将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与“社会性”一定程度上对立起来,可能给这个领域带来内部紧张甚至是某种分裂。但是,这似乎轻忽了多年社会工作发展历史中包含的合理追求之意义。也就是说,社会工作强调专业性不应该被简单地否定。问题的关键可能还在于对“专业性”的理解上,而它恰恰关联着对“社会性”的准确完整涵义之把握。
实际上,本文认为,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与其社会性并不矛盾,对“社会性”的两重理解(一重是指socialness,一重是指societalness)甚至更多重的理解之间,也同样可以兼容,而关键的关键在于“社会的”(social)这词。
“社会的”意味着“与他人交往和联系”,而最根本的“社会性”所指也就是人和人这种交往和联系的属性品质。人们投入相互的交往和联系,就意味着发生了“社会的”现象,而若社会工作促进了这种人与人相互交往和联系的增强与增进,也就是促进了人们的社会性,本身也就体现了它自己的“社会性”。它的这种促进可以小到在两个个人之间,中到不同规模的群体至组织层面,直到大至于整个社会的制度或结构。因为这一切不过是不同规模或层次、不同形态的“与他人的交往和联系”,贯穿其中的都是一种“社会的”性质或“社会性”(socialness,不拘它是人与人直接接触的微观社会性、是间接接触的中观社会性,抑或是更间接的有些‘抽离’的社会性)。并且,所谓“全社会性(societalness)”如果不能体现出这种在“与(具体)他人的交往和联系”中——且还不说在与他人“交互主体性”的交往和联系中——来把握与对待,一样有可能变成危险,并偏离了社会工作之恰当的“社会性”之谓。
在实际工作中,何时社会工作偏离了促进人与人交往联系——不管是在哪个层面、何种规模上——的目标,何时缺少了将人的处境与问题也放在人与人交往联系的视野中来看待和处理,它也就缺失了自己的“社会性”,也就没有很好地把握住“社会工作”的特有本质属性;其实,此时它也就丧失了自己的“专业性”。还要指出,这种偏离、缺失与丧落,既可能表现为过分关注微观、社会工作者单向地以技术理性对待所服务的那些人,也同样可能表现为过分关注与强调宏大而抽离的制度或结构、不注重具体的过程中的对话与人们之间实在的交往联系。凡此种种,都同样是有违社会工作的“社会性”本质意涵的,可以被合理地批评未能很好地掌握这个专业之精神。
倘若如此理解“社会性”或“社会”的涵义,并如此去把握住社会工作的“社会”涵义与“社会性”,则掌握了其独具的“专业性”。因而恰恰要说,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与其“社会性”毫无矛盾,倒恰是相互支撑、彼此促进的。甚至可以说,社会工作的“社会性”即是其“专业性”之所在,而其“专业性”也正在于它的“社会性”。说社会工作的“社会性”也就是说它的“专业性”;反过来,强调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也就是强调它的“社会性”。
正因如此,彰显出了社会工作不同于生理学、医学,不同于心理学、某些教育学,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科学,不同于社会政策与行政等等的意义所在。一言以蔽之,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就在于它的社会性,在它长于从人与人的各种交往与联系入手、并促进这种交往与联系的能力。这种能力既由它特有的一些方法技术所构成,也来自其一系列理论知识的支撑,更源自其鲜明的价值伦理。可以看到,社会工作全部的专业知识,围绕着“人与人交往联系”这个中心,对之着重关注、关切与强调和追求,构成了其知识的价值与使命的意义。若就价值观而论,以全美社工人员协会(NASW)伦理守则所阐述的为例,其六大核心价值——服务、社会公正、个人尊严与价值、人类关系的重要性、诚信、能力,无一不反映了对“社会性”涵义的前述理解。无论是对服务的崇尚、对社会正义的看重、对个人尊严与价值的珍重、对人类关系重要性的强调,以及对自身诚信与胜任的要求,都是为了带来更好的人与人的交往联系,促进它在各个层面尽可能的实现。于此,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与社会性实现了统一:其专业性即等于社会性,而其社会性也就是其专业性。
四、开放的结论
在较成熟地方的社会工作界,关于社会工作的核心目标和其独特的专业作用,共识性的说法是它聚焦人的“社会功能运作”(social functioning),采用各种有效的方法以恢复和提升这种社会功能运作(Chan Yuk-chung etl.,1995)。在具体的实务中,甚至已经发展出一些可量化的指标来测度此种功能运作水平及其变化。例如,为一位独居老人的社会工作服务,无论用怎样的手法技巧,最终可以看看,这老人家与其他人各种方式的接触交流是否增多了,增多到何种频率与规模,以及这些接触交流带给其本身的满足感是如何变化的。而当其这种接触和交流在量上和质上都有积极良好的改变,基本上可以说就是其社会功能运作得到了提升。当然,衡量一个人社会功能运作的状况还可有更加丰富的内容角度,而就不同人群层次或更大社会来说,人们的社会功能运作是否获得改善或改善到什么程度,也有更多要讨论的地方。但是,社会工作基本的方向和目标便在此,实质就是促进人的社会性和更大社会的社会性提升。同时,社会工作也就如其名称所宣示的那样,展示出了其“社会性”,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社会工作”。
相信这样一些理解,与素来人们强调社会工作是“助人自助”亦是相通一致的。而另外,要考虑到之所以有时候突出重视“全社会性”的含义,要求更好地认识大社会环境对于个体和微观社会交往与联系的影响,而倡导宏观视角和取向的社会工作,这一要求也具有合理性,尤其是更针对了当下常见的某些偏颇。因此,可以再做一个综合,将合理的社会工作具体定义为:服务人群以改善社会,或改善人们的社会功能运作与改善社会体系交互促进。希望这一定义,能够更好地体现社会工作的全部之义,即它是在所有实践中“贯注‘社会性’的工作”。
此外,在关注社会性的同时,如果社会工作能够更好地采纳“发展性”的视角、甚至明确地践行“发展性社会工作”(developmentalsocialwork),把握社会工作者在与服务对象的关系角色中顺序经历从“照顾者”到“陪伴者”直到“同行者”的完整过程,或许能更好地将“社会性”贯彻到底,也打通由微观个人社会功能改善直至整体社会功能运作提升的途径,从而真正做到“服务人群以改善社会,改善人们的社会功能运作与改善社会体系交互促进”(陈涛,2012a;2012b)。社会工作者从关注人的需要出发,将自身作为与人交往联系的一个部分,进入对服务对象的照顾关系中,这本身并不与其社会性抵触,反而是适当的社会性表达。但是,社会工作者不可停留于单向的照顾关系中,而要拓展人们之间更多更好的交往联系,并使自身与所服务者迈入双向陪伴的关系。最终,他们要一起走向互相给予力量、为共同的美好社会目标同行奋斗的关系。这或许就应是符合其本义、该有的那种“社会工作”。
[1]陈涛,2012,《重构社会工作专业的使命》,《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八辑,王思斌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陈涛,2012,《发展性社会工作的探索与思考》,《公益研究》第1辑,朱健刚、赖伟军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甘炳光,2010,《社会工作的“社会”涵义——重拾社会工作中的社会本质》,The Hong Kong Journal ofSocial Work,Vol.44,No.1(Summer2010)。
[4]【德】尤尔根·哈贝马斯,2004,《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5]【德】马克斯·韦伯,1998,《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6]殷妙仲,2009,《从专业说起》,《微光处处——28位社会工作者的心路历程》,曾家达等主编,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7]Chan Yuk-chung,1995,Chun Ping-kitand Chung kim-wah,SocialWork Practice I(Diploma in SocialWork),Volume1.Hong Kong: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8]Gouldner,A.,1971,The Coming CrisisofWestern Sociology.London:Heinemann.
[9]Ryan,W.,1976,Blaming the Victim.New York:Vintage Books.
[10]Specht,H.&Courtney,M.E.,1994,Unfaithful Angels:How SocialWork Has Abandoned ItsMission.New York: Free Press.
编辑/程激清
C916
A
1672-4828(2017)03-0003-06
10.3969/j.issn.1672-4828.2017.03.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