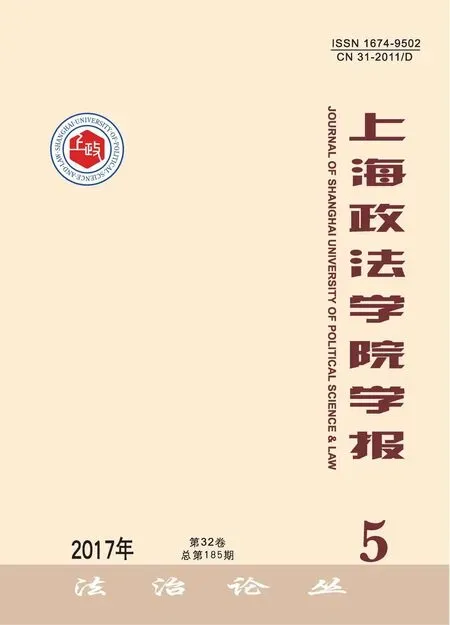占有说理论:竞合质疑、禁止损失扩大与类型区分
庄绪龙 何向东
占有说理论:竞合质疑、禁止损失扩大与类型区分
庄绪龙 何向东
占有说及其折中说主张突破所有权范围,将财产罪法益保护触角延伸到非法占有的主张,契合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在整体上基本处于财产罪法益保护的通说地位。占有说在形式上貌似制造了财产罪与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的竞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从一重处罚”原则下后者适用的荒芜,相反,这恰恰诠释了刑法法定刑幅度精密设计的合理梯度;财物利益本身与财物被非法占有后经由“化学反应”所衍生的新利益之区别客观存在,对此基础事实应当予以明确和尊重,绝对化的“本权对抗占有”论点忽视了私力救济可能引起的损失扩大危险,其正当性值得怀疑;犯罪所侵害之法益存在国家法益与非国家法益的类型区分,在国家法益遭受侵害的情形中,占有说所依据的“暂时性占有”“可还原为原权利人法益”的论证并无实践支撑,也不具有理论上的解释力,应当支持本权说作为此类法益侵害犯罪的必要补充。
占有说;竞合解释;基础事实;损失扩大;类型区分
在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学说史上,从先验思维角度出发,本权说无疑具有正当性,而且这种正当性永远处于最明显的地位,现今德、日刑法学界以及我国大多数刑法学者,不管是本权论者还是占有说论者,还是以占有说甚或本权说为基础的各类折中说论者,都承认本权之于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优先地位。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本权说的观点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趋势。这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所有权部分权能与作为整体的所有权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发生分离。这种分离既可能给所有人带来相应的经济价值,也会给占有、使用该财产的非所有人带来经济利益,对于此种相对独立的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权能,刑法当然应当保护。①参见张明楷:《骗取自己所有但由他人合法占有的财物构成诈骗罪》,《人民检察》2004年第10期。后来,人们在承认占有权能及其利益保护的基础上,也逐渐认识到纯粹的占有说可能会过分扩大刑罚的处罚范围:保护一切赤裸裸的非法占有,完全禁止力所能及且正当必要的私力救济。例如,纯粹的占有说会导致“连盗窃罪的被害人窃回自己所有的被盗窃财物的行为在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实质判断阶段也要认定为盗窃,只是在违法性阶段考虑是否属于自救行为之类的违法性阻却事由”。②需要说明的是,在此种情形中对于本权者而言,采用私力救济手段维护自身权利无疑具有正当性。但是,由于私力救济事实的过程性和复杂性,并非所有的私力救济都符合利益保护的原则,可能会引起损失扩大的不当后果,需要慎重。有关分析详见下文论述。就整体而言,就目前的理论观点来看,财产罪法益保护理论中的占有说(包括以占有说为基准的折中说、中间说)获得了较多的支持,基本处于通说的地位,而本权说(尤其是纯粹本权说)则全面萎缩,只有极少数学者仍然“据理力争”。①参见徐光华:《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应坚持所有权说——以取回自己所有而被他人占有的财物为例》,《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3期;高翼飞:《侵犯财产罪保护法益再探究——为本权说辩护》,《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7期。
现阶段,刑法理论界关于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占有问题,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需要澄清的问题:一是占有说是否人为制造了刑法竞合问题,进而导致有关刑法分则条文的废弃;二是“本权对抗占有”绝对性立场有无例外问题;三是占有说理论在类型区分视域是否全部适用等,本文将对上述几个存在争议的问题进行归纳和研究。
一、占有说制造所谓“竞合质疑”的疑问及其解释
(一)占有说制造“财产犯罪与非法处置、扣押、冻结的财产罪”竞合困境的观点
财产所有权人对于他人合法占有而行侵犯行为的情形,占有说(包括基于占有说的折中说)认为,合法的占有可以对抗本权,故本权人无权擅自将已为他人合法占有的财物取回,否则就会侵犯他人对该财产的占有。比如,债务人擅自取回质押物、留置物的行为就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利。这是因为,根据物权法的基本原理,担保物权的效力优先于所有权,债务人将其财产出质或者留置,其所有权的权能行使就应当受到担保物权的限制。具体言之,担保物权是所有权人担负债务的他物权形式,所有权人将本权的占有权能让渡,存在先在的债务抑或对他人债务的担保承诺,该担保承诺能够因质押物、留置物的占有权能而取得法律上的债权优先保护效果。因而,虽然质押物、抵押物的所有权人依然存在,但是由于担保承诺以及所有权上占有权能的让渡,该权利人的所有权已然成为优先保护债权人债权实现的法律保障。在民法比较法的视野内,大陆法系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民法典中明确规定(比如德国民法典第863条、日本民法典第202条,韩国民法典第208条等),或者在司法实践中坚持(如我国台湾地区)占有之诉不依赖于本权的原则,对于占有之诉,当事人不得直接以本权作为抗辩,法院亦不得以本权作为裁判的依据。当事人如欲以本权进行抗辩,应该反诉或者另行起诉。②参见Vgl.Dieter Medicus,Grundwissen Zum Burgerlichen Recht,S.154ff. 王泽鉴:《民法物权(二)》,台湾三民书局2005年版,第172页。均转引自章正璋:《我国民法上的占有保护——基于人民法院占有保护案例的实证分析》,《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依据现代民法中占有理论“维系社会和平与物之秩序”的目的,财产罪法益保护理论中的占有说观点基本上得到了理论认同。不仅如此,刑法规范文本也持相同态度,如我国《刑法》第91条第2款规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
但问题是,如果所有权人对于国家机关合法占有的、拟制性认定为公共财物的私人财产进行盗窃、骗取的,在以占有说为理论基调成立财产犯罪的同时,是否也同时触犯了《刑法》第314条非法处置、扣押、冻结的财产罪,如果在盗窃、骗取既遂后故意毁坏的,是否同时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对于这个问题,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均存在较大争议。③有学者对最高人民法院主编的《刑事审判参考》刊登的4个典型案例“王彬故意杀人案”“陆惠忠等非法处置扣押的财产案”“江世田等妨害公务案”“叶文言、叶文语等盗窃案”进行了系统研究,得出:在他人合法占有的情况下,本人采用非法手段取回自己的财物,如果没有借此索赔等后续行为,则不构成相应的财产犯罪,但是取回财产的手段行为构成其他犯罪的,按照其他犯罪处理。参见于志刚、郭旭强:《财产罪法益中的所有权说与占有说之对抗与选择》,《法学》2010年第8期。对此司法实践中的观点,有学者找到了不同的案例进行反证,如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滁刑终字第7号判决书、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厦刑终字第120号刑事判决书,等等。足见司法实践中关于此类案件定性的混乱。参见陈洪兵:《财产犯罪之间的界限与竞合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有观点认为,对于此类情形,如果是所有权人窃取他人占有的本人之物,则不能仅仅因有窃取行为就构成犯罪,还要看事后有无索赔的行为。之所以强调只有具备事后索赔的情形才成立盗窃罪,主要是因为这种窃取处在他人保管之下的本人财物的行为,如果只是将财物窃回,但并不向他人索赔,则他人财产不可能遭受损失,这表明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①参见陈兴良:《判例刑法学(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1-282页。张明楷教授对于“事后索赔才成立盗窃罪说”观点系统地阐述了不同意见。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972-973页。还有人这样解释,盗窃是偷别人的东西,自己的东西不存在偷的问题。处于他人合法保管之下的财产,所有权并未从此发生改变,因而盗窃在他人保管之下的本人财物的行为,如果没有以作为形式积极主动索赔或者以不作为形式默认、间接接受保管人赔偿的,不构成盗窃罪。②参见沈志民:《对盗窃在他人保管之下的本人财物行为的刑法评价》,《北方法学》2012年第2期;高翼飞:《侵犯财产罪保护法益再探究——为本权说辩护》,《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7期。对此争议,张明楷教授认为,根据《刑法》第91条第2款的规定,司法机关查封、扣押的财产属于公共财物,行为人(包括财产的所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非法变卖等方式取得财产,或者故意毁坏该财产的,实际上也符合侵犯财产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由于侵犯财产罪的法定刑重于非法处置扣押的财产罪的法定刑,故实施非法处置扣押财产的行为,同时符合侵犯财产罪的构成要件的,属于想象竞合犯,应当从一重处罚。③张明楷教授对于行为人转移、变卖已被司法机关扣押的在民法上属于自己所有的财产的行为,司法机关一概认定为非法处置扣押财产罪的司法处理方式指出了其中的不协调之处,难以契合解释论上的自洽。参见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7页。
张明楷教授所主张的“想象竞合说”观点,虽然明确了两类罪刑关系的处理原则,但也可能面临如此质疑:想象竞合说的理念及其处理方式脱胎于占有说,按照占有说的观点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擅自取回或者毁损司法机关扣押、查封财物的行为,同时构成侵犯财产罪(盗窃罪、诈骗罪或者故意毁坏财物罪)和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侵犯财产罪与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和冻结财产罪之间形成“想象竞合”。④此种疑问,同样适用于《刑法》第307条第2款所规定的“帮助毁灭证据、伪造证据罪”,相关结论与《刑法》第314条规定的“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基本一致,本文不再就此展开分析。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的法定最高刑为3年有期徒刑,而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法定最高刑为7年有期徒刑,盗窃罪、诈骗罪等侵犯财产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侵犯财产罪的法定刑显然更重,在“从一重处罚”的原则下,最终对于这种“想象竞合犯”的情形只能选择适用侵犯财产罪。这也就意味着,在“占有说”所制造的侵犯财产罪与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和冻结财产罪之间形成“想象竞合”的情形下,将直接导致《刑法》第314条规定的非法处置、查封、扣押的罪名无用武之地,进而使得该条的部分规定失去存在价值。①参见高翼飞:《侵犯财产罪保护法益再探究——为本权说辩护》,《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7期。
(二)体系解释视角下的正本清源
上述观点对《刑法》第314条所承载的法条价值抑或“命运”的担忧在形式上貌似存有道理,但就此以其质疑占有说作为财产罪法益保护理论的论证却未免过于武断。就其所指出的竞合问题所导致的“非法处置、查封、扣押的罪名无用武之地”的论断,笔者不能认同。事实上,在全面考察刑法分则法条规定的基础上并结合体系解释的科学方法,就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占有说支撑下的财产罪与非法处置、查封、扣押罪之间的竞合问题非但不会制造上述观点所认为的“非法处置、查封、扣押的罪名无用武之地”的后果,反而会合理解释两类罪刑关系的合理位阶。
刑法分则体系中的类罪与个罪之间、普通法条与特殊法条之间存在大量的包容和交叉,罪名中包含与被包含、交叉与融合的情形比比皆是,并且包容性竞合与交叉性竞合的竞合性质也并不确定,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的区分在理论上还是必要的,毕竟涉及到后续的量刑标准选择的问题,到底是“从一重处罚”还是“特别法优先”则是比较关键的问题,需要分情况讨论。比如,寻衅滋事罪与抢劫罪之间是想象竞合还是法条竞合,由于寻衅滋事罪的行为类型多样,可能还要具体分析。有观点认为,对于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行为与抢劫罪之间的交叉关系是由于法条用语本身造成的,因而属于法条竞合,而其他类型的寻衅滋事行为,如随意殴打他人或者追逐、拦截、辱骂他人等,与抢劫罪之间,则可能是想象竞合或者牵连犯的关系。②参见付立庆:《论抢劫罪与强拿硬要型寻衅滋事罪之间的关系》,《法学》2015年第4期。在竞合关系区分复杂化的客观情形下,“越是所谓界限模糊的犯罪,越不宜讨论此罪与彼罪之间的界限。因为越是界限模糊,越表明两罪之间的关系复杂、难以区分”。③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3页。因而,充分尊重刑法分则体系的竞合现象,采取有效的解释方法解决“法条弃用论”的理论担忧抑或质疑才是科学的思路。
想象竞合犯作为真正竞合犯,在事实上只有一个行为,但是这个行为在成立A罪的同时,法官完全可以宣告其成立B罪,只不过要按照处罚重的罪来定罪量刑。④参见周光权:《法条竞合的特别关系研究》,《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想象竞合犯的基本原理,在于行为人的一个行为该当两个犯罪构成要件,亦即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既符合A罪的构成要件,又符合与A罪完全不同的B罪的构成要件。在想象竞合犯的理论思维中,只要承认刑法的规范评价功能,就可以从不同规范目的出发,运用多个犯罪构成,对一个自然意义上的行为进行多重评价。⑤参见丁慧敏:《想象竞合犯的功能及其存在根据》,《现代法学》2013年第3期。行为人将自我所有但处于他人合法占有状态下的财物予以窃回、骗回的情形,一方面,按照占有说的观点,当然侵犯了财产犯的保护法益,成立相关的财产犯罪也是理所当然;另一方面,这种行为可能客观上会妨害司法秩序,因而也同时符合《刑法》第314条规定的非法处置、扣押、冻结的财产罪。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能够认定为相关财产犯罪,如盗窃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由于想象竞合犯从一重处罚的原则,《刑法》第314条所规定的非法处置、扣押、冻结的财产罪由于法定最高刑低于故意毁坏财物、盗窃罪的法定刑,当然要在罪名选择上让位于处罚较重的罪名。
但即便如此,也并未出现某些学者所担忧的现象,即将《刑法》第314条的规定“打入冷宫”,成为“无用武之地”的禁区。笔者认为,上述想象竞合的法律适用问题,完全可以在体系解释的思维中得到合理的解答。体系解释要求根据刑法条文在整个刑法中的地位,联系相关法条的含义,阐明其规范意旨。①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1页。按照体系解释的基本理论,刑法分则中的条文并非单独存在、孤立适用,其有效准确适用的合理性在于将条文纳入所有条文的整体中去,才能明晰该条文的真实含义与适用范围。事实上,我国刑法中关于盗窃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侵犯财产罪的立法有效遵循了“定性与定量”的二元立法规律,亦即并非所有的侵犯财产罪保护法益的行为都要纳入到财产罪治理的体系。比如,盗窃一个苹果,摔坏一支普通的花瓶,由于实体层面的经济价值微弱,别说难以用刑法规制,恐怕连民事侵权及其权利维护的必要性都难以在程序上启动。从这个角度而言,财产所有权人将被国家机关抑或他人合法占有的财物窃回、骗回的情形,可能存在由于财产的经济价值微弱,在侵犯财产犯罪的视域按照《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亦可出现视为无罪的情形。②虽然财物本身经济价值微弱,但在性质上却仍属财产犯法益保护的范畴。但所不同的是,经济价值微弱之物,除却实体上的经济价值本身,并非是毫无价值存在,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下完全可以成为《刑法》第314条非法处置、扣押、冻结的财产罪中的犯罪对象。这是因为,非法处置、扣押、冻结的财产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司法秩序,只要行为人的非法处置、扣押、冻结财产的行为,哪怕非法处置、扣押、冻结的对象只是一支带有指纹的廉价钢笔、一件沾有血迹的旧衣服、一笔根本达不到包括盗窃罪、诈骗罪等在内的所有财产犯罪的起刑点且根据“但书”规定不可能成立财产犯罪的资金等等,但客观上盗窃、毁坏的行为只要阻碍司法程序顺利进行,就完全有可能造成破坏司法秩序“情节严重”的情形,因而也就完全可以成立非法处置、扣押、冻结的财产罪。这是因为,由司法秩序的性质分析,非法处置、扣押、冻结的财产罪中“情节严重”的情形,并不侧重财产犯法益保护中的财产价值而更注重是否严重影响司法程序的有序推进。
概言之,在“想象竞合说”的理念下,行为人将处于司法机关控制之下的财产抑或其他财产性利益非法处置、扣押、冻结的,侵犯财产罪与第314条非法处置、扣押、冻结的财产罪之间的竞合及其法条适用并不存在绝对的冲突,也不存在重罪完全架空轻罪的情况,《刑法》第314条非法处置、扣押、冻结的财产罪成为“无用武之地”禁区的标签式判断经不起推敲。实际上,在法定刑的配置中,盗取经济价值微弱财物的情形虽然被排除在财产罪的范围之外,但如果符合非法处置、扣押、冻结的财产罪中“情节严重”的条件,则完全可以按照《刑法》第314条的规定处理。另外,还需要充分正视的是,《刑法》第314条中规定的犯罪对象,也可能是数额巨大的财产,比如司法机关扣押的价值巨大的精密仪器设备,如果在行为人窃取、骗取或者非法处置、扣押后,必然对该财物的原权利人承担债务责任,如果仍以《刑法》第314条的法定刑量化,恐怕对于刑法分则的法定刑体系造成威胁。这样一来可能就会释放一个信号:盗窃、非法处置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中扣押、管理的财产,不管数额多大,法定刑不会超过有期徒刑3年。恐怕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错误思路,因而,刑法分则财产犯罪与非法处置、扣押、冻结的财产罪的罪刑体系解释与法定刑安排上,并不存在不科学之处,想象竞合的理论非但没有架空刑法相关条文的适用,而且还比较科学、注重层次性地解决了财产犯罪与侵害司法秩序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换言之,刑法分则中关于财产犯罪与非法处置、扣押、冻结的财产犯罪中法定刑设定的镶嵌式、互补性的立法构架及其解释对于竞合理论有效适用的原则预留了合理空间。
二、损失扩大禁止:“本权对抗占有”的绝对性之反思
(一)“本权对抗占有”的绝对性理论
在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理论选择上,以占有说为理论蓝本进行修正和补充的占有折中说已日渐成为国内外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通说观点。现阶段,大多数日本学者都以“占有说”为理论蓝本进行修正和折中。如平野龙一教授主张“平稳占有说”,即在法律关系需要通过民事诉讼强制恢复的场合,一方对财物的占有应当作为平稳的占有而被刑法保护;①参见[日]平野龙一:《盗窃罪的被害法益》,载平野龙一等编《判例演习·刑法各论》,有斐阁1961年版,第191页。西原春夫教授基于占有说理论也作了修正,将自己的学术观点描述为“大体平稳的占有说”。该说认为,占有说在财产罪法益保护的选择上是妥当的,但所有人在紧急情况下取回被盗财物时,如果仍然保护单纯的占有,则与本权优先的财产法益宗旨相违背,为了使这种行为不可罚,应认为从一般人或行为人的立场来看属于大体平稳的占有,是财产犯所保护的法益;②转引自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8页。西田典之教授针对自救行为不能为占有说所赦免的不合理性提出了“合理理由占有说”,即在被害人与行为人关系上,如果一眼就能明白并非值得保护的占有,就应该否认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该当性。③参见[日]西田典之:《刑法各论》,弘文堂2012年版,第155页。我国学者对此也有类似表述,例如,张红昌博士将修正的占有说表述为“合理对抗本权的占有”,即在所有的占有中仅仅排除不能合理对抗本权的占有。所谓“不能合理对抗本权的占有”,是指行为人具有比占有人更高的地位和利益,此种情形仅仅存在于权利人从非法占有人那里取回赃物的场合。④参见张红昌:《财产罪中的占有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页。
不管是日本学者主张的“平稳占有说”“大体平稳占有说”“合理理由占有说”还是我国学者主张的“合理对抗本权的占有”等论断,在语义涵摄与具体指向上可谓是一脉相承。它们均以占有说为基础进行理论折中并完成自洽,并在占有说的整体安排下,通过修正补充、限定排除的形式将诸如盗窃罪的被害人盗窃自我“赃物”等近似于自救行为的情形排除在犯罪圈之外,实现刑法对于财产秩序稳定以及对本权法益的优先保护。
可以明确的是,在上述各修正的占有说主张中,“行为人”免责的唯一例外便是:“行为人”作为财物的本权人,其本权优先的地位可以完全对抗实际占有人的非法占有。例如,张红昌博士认为,在侵夺他人非法取得占有的场合,必须将侵害者与占有者进行实质的利益比较与衡量。刑法虽然应当保护非法占有,但是占有保护不能与权利保护相冲突,在侵害非法占有的全部场合,只需将权利者取回财物的情形排除在外即可。①参见张红昌:《财产罪中的占有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0页。这种观点可以归纳为,在非法占有的语境下,就本权者而言,其本权地位绝对优先于占有地位,本权利益可以绝对对抗占有利益。换言之,在非法占有的情形中,原权利人对于本权地位和利益的恢复,完全可以采用私力救济的手段而不必求助于公力救济。
(二)损失扩大禁止的基础事实
上述“合理对抗本权的占有”作为修正占有说的基本表述,其“合理性”的标准是什么?亦即,在非法占有的情形中,权利人的本权恢复行为(即私力救济)有无限制?这在上述修正的占有说观点中,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是因为,正如上述论者所阐述的那样,行为人(即原权利人)比占有人(即非法占有人)具有更高的地位和利益。这里,所谓“更高的地位和利益”是价值判断还是事实判断,显然,上述论断属于价值判断。在价值判断的视野中,利益受损者对于确定的侵权人而言,自然具备权利恢复的原始动力和情感动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事实判断的视角下,价值判断虽然具备先验的原始情感动机,但却并不能完全经得起实践检验。本权绝对对抗占有的价值判断只有与事实判断完全重合,才具备天然的正当性。在具体的事实考量中,如果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之间存在位阶甚或罅隙,就难以证明价值判断的绝对优先性。
比如,A的妻子B系尿毒症患者,长期需要血液透析维持生命。但是,A的经济条件支付不起长期巨额的透析费用。在此困境下,A采用伪造票据等手段将C医疗公司的透析机骗走供妻子使用。尔后,C医疗公司发现被骗,向A主张返还赃物。但是,此时透析机已经被用于B的血液透析,C公司能否不顾B的生命危险而强行通过私力救济手段取走机器?换言之,C公司强行取走透析机而导致B的死亡后果,是否应当在财产罪的范畴内承担刑事责任?②该举例改编自“廖丹诈骗罪”,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2/12/08/238143.html,新京报网,2016年10月19日访问。显然,“本权对抗占有”的立场,并不能科学回答。
一般而言,在非法占有的场合,本权者当然取得私力救济权限,本权对抗占有的立场并不违反任何法理。但是,这种对抗的绝对性和完全性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条件之上,即损失扩大禁止。所谓损失扩大禁止,是指本权者在通过私力救济手段对抗占有的过程中,不得造成占有者占有利益丧失之外的其他利益损失。事实上,财产罪中的法益自所有权与占有分离后,占有权能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出了所有的权能。财物占有作为一种事实形态,必然会为占有者带来由此所衍生的利益。比如,行为人盗窃他人1万元用于经营,获利10万元,那么其在对1万元占有的过程中就衍生了额外的利益。由此可以认为,发轫于财物本身的占有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极有可能与其他生产资料要素或者利益结合,进而衍生成新的利益。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财物所有人对于财物的所有权,在他人占有持续的过程中往往已经发生质变,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本权者的权利原型。新的权利抑或利益,往往凝结了占有人的自身权益,亦即非法占有的利益可能与自身的利益密切结合进而发生了“化学反应”,成为一种新的、相较于本权者的利益原型更具刑法保护意义的利益。此时,如果固执地坚持“本权地位高于占有”的观点,可能就难以契合事实判断的标准。因此,在“本权地位高于占有”的修正占有说判断中,损失扩大禁止的事实考量必不可少,而“本权地位高于占有”的价值判断也必须接受事实判断的检验。
笔者认为,在非法占有的场合,如果放任损失扩大禁止的限制性条件,忽视本权对抗占有的条件性限制,恐怕会人为地制造混乱。日本学者牧野英一教授正确地指出,“倘若以本权为名而允许他人侵害,则是允许无秩序的私斗”。①[日]牧野英一:《刑法各论》(下卷),有斐阁1951年版,第594页。转引自黎宏:《论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人民检察》2008年第23期。大冢仁教授也指出,所有权人及其他本权人在盗窃犯的犯行之后立即从盗窃犯那里取回被盗的财物等,在本权与占有相互对立时,只有占有者一方不存在能够与本权者相抗衡的合理理由,其占有在刑法上就不应受到保护。②参见[日]大冢仁:《刑法概说》(各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185页。“不存在能够与本权者相抗衡的合理理由”到底为何,大塚仁教授并没有进一步明确。笔者认为,损失扩大禁止应当成为这里的“合理理由”。
(三)初步结论
归纳而言,对于非法占有情形中所谓“本权对抗占有”的观点应当慎重。具体言之,在非法占有的情形中,主张“本权对抗占有”的观点,无疑是为了恢复本权者已被侵害的财产权利,只不过恢复的手段是本权者发起的私力救济。自人类文明社会以来,私力救济始终被法律所禁止,取而代之的是以程序公开、操作透明、措施公正、处理科学的公力救济措施。在非法占有情形中,学界为何众口铄金地主张“本权对抗占有”的绝对性,且变相的承认、鼓励私力救济而忽视私力救济可能会造成的占有者利益损失扩大的危险,着实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必须明确的是,在纠纷解决、利益恢复的救济模式上,公力救济显然是最优的基本措施,私力救济由于救济方式、救济手段以及救济所衍生的“副作用”等无法把控,因而不适合作为利益保障和恢复的措施,尤其是不适合作为刑事领域的救济措施。③对此问题,意大利刑法对于“本权对抗占有”绝对性的理论颇具启示。《意大利刑法典》第392条规定了“擅自采用对物的暴力自行其是”:以行使自己所主张的权利为目的,在能够诉诸法官的情况下擅自通过对物的暴力自行其是的,经被害人告诉,处以516欧元以下的罚金;第393条规定了“擅自采用对人的暴力自行其是”:为了前条列举的目的,在能够诉诸法官的情况下擅自通过对人身的暴力或者威胁自行其是的,经被害人告诉,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在实施行为中也采用了对物的暴力,除有期徒刑外,并处206欧元以下罚金。如果对人身的暴力或威胁是使用武器实施的,刑罚予以增加。参见《意大利刑法典》,黄风译著,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142页。笔者主张,倡导公力救济方式而非私力救济应当作为刑法理论需要承担的责任而不是相反。遗憾的是,现阶段大多数观点都无一例外地承认非法占有情形下“本权对抗占有”的完全性和绝对性,这对于司法实践而言无疑是值得警惕的。
三、国家法益侵害的类型区分:占有说的“学说想象”
(一)“小偷反腐”现象的启示
2014年7月8日,陕西女子房云云由于在江苏常州盗窃作案6起,盗得财物22万余元,被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2014年8月上旬,房云云向媒体举报称,她在调查审讯过程中交代了8起案件,但最后被判刑时,只追究了其中的6起案件,被遗漏的2起案件是她在合肥盗窃了安徽省两副厅级官员家,盗得财物、购物卡约200万元。④参见刘炜:《“小偷反腐”十年十案》,《民主与法制时报》2012年1月2日。
对于房云云等“侠盗”以盗窃罪定罪量刑基本没有什么争议。在理论上,对于非法占有予以刑法保护的动机基本都以“禁止私力救济”“财产秩序维护”为解释理由,这是占有说在非法占有情形中的诠释。对于以“财产秩序维护”为根本目的的占有说根据的解释,周光权教授认为,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还没有完全确立,财产权利关系难以理清的情况并不少见,趁机获取各种财产上不法利益的犯罪有增无减。因此,对于所有权相分离的财物的占有、持有本身暂时予以保护,对及时恢复财产秩序、最终有效保护个人财产具有重要意义……占有说不是要最终保护违法的占有,而是强调必须依据适法的手续剥夺违法占有者的占有权,防止违法占有财产在经合法手续交还原所有权人以前处于可以任意夺取的状态。①参见周光权:《刑法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7页。
笔者发现,周光权教授关于刑法保护“非法占有”的合理解释限定了两个条件:一是非法占有的“暂时性”;二是非法占有的“可还原性”。虽然,“无权占有仅仅对于确定占有的发生及其权源具有意义,无权占有并不必然意味着该占有不受法律保护”,②章正璋:《我国民法上的占有保护——基于人民法院占有保护案例的实证分析》,《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无权占有内部却存在是否属于暂时占有、是否能够还原为原权利人法益的限定性条件而具体地存在两种不同占有性质的基础事实和类型区分。
上述两个限定性条件的界定,一方面对于非法占有情形中占有说观点的适用奠定了解释的视角,另一方面也对非法占有情形的类型化与区别性思维具有启示。由此而言,由于非法占有情形在客观上依据是否属于暂时非法占有、是否能够还原为原权利人法益的区别,因而存在类型化思维判断与解释的空间。故而,对于非法占有状态无限期的存在或者不可能还原为公民个人权利的问题不能弥合于占有说的解释与观点,那么维护既定的公民财产权利和社会财产秩序的目的恐怕只能是一句空话,刑法上这种标榜财产秩序维护的占有说在类型化思维的视野中可能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
(二)以“暂时性”与“可还原性”为论证依据的占有说在国家法益侵害情形中的“学说想象”
在类型化思维的前提下,非法占有状态背后的法益侵害对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法益,比如贪污、受贿犯罪所侵害的法益无疑是国家法益;另外一类则是与国家法益相对应的非国家法益,包括个人法益与单位法益。如果非法占有状态背后的法益侵害对象为笼统的国家,周光权教授上述所限定的条件及其解释恐怕不存在实践依据。
首先,“暂时性”的理由假设性痕迹明显。在“小偷反腐”事件中,小偷因为盗窃官员案发后所牵带出来的贪腐事件,正如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所言,毕竟是小概率的事件,小偷不到万不得已、黔驴技穷时一般也不会告发贪官腐败,毕竟小偷或者有组织的盗窃团伙在专门从事偷官员行当中获取最大利益的前提就是利用官员害怕揭发的心理而甘愿自认倒霉,从而大致形成一种“(贪)官匪制约平衡”的态势。而贪官被落网的小偷告发后,这种平衡自然也就旋即失去,小偷、有组织的盗窃团伙的利益攫取目的也就失去了源泉。所以,在制度反腐尚未形成刚性约束机制的社会背景下,贪腐官员经由贪污受贿等非法手段聚积的大量财产“暂时占有”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而长期占有甚至通过洗钱手段转变为形式上合法资产的可能性却比较大。①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中将洗钱的范围扩展至包括贪污贿赂罪等7种犯罪,也从侧面说明贪官通过贪腐犯罪所得“暂时占有”的理论假设并不合理。
其次,“可还原性”的法益保护目的并无实践根据。占有说的观点在解释盗窃犯对赃物的非法占有时认为可以作为财产罪法益保护的根基是维护稳定的社会财产秩序,而根据周光权教授的解释,在经济交往社会中,以稳定财产秩序为价值追求的非法占有刑法保护,不是为了保护非法占有本身,而是为了“防止违法占有财产在经合法手续交还原所有权人以前处于可以任意夺取的状态”。日本的相关判例也认为,对于赃物的刑法保护,主要是基于被害人的返还请求权,刑法对赃物罪科以制裁是为了防止赃物被转移,以保护被害人之返还请求权。②大判大正4·6·2刑录21辑721页。转引自[日]山口厚:《从新判例看刑法》,付立庆、刘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8页。这种理论倾向和目的本身没有瑕疵。但是,需要明确的是,稳定的社会财产秩序不是抽象、空洞的,而是具体、鲜活的,社会生活中因犯罪遭受财产损失的被害人必须能够还原为具体的个人、单位,否则稳定的社会财产秩序则无价值可言。在“小偷反腐”事件中,贪官通过贪污受贿所得的赃物,在本质上属于国家法益侵害,在性质上并不属于任何具体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因而也就无法还原为原所有权人,这与其他普通财产犯罪侵犯具体被害人财产权,被害人得以行使返还请求权的情况存在本质差异。
(三)本权说的解释路径
如上分析,占有说的观点对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财产秩序而言在整体上是合适的,但是对于诸如“小偷反腐”现象中赃物占有和侵害国家法益的类型解释却不能自圆其说,“暂时性占有”与“可还原性”的论证支撑并不科学,将其纳入占有说的范畴存在明显的实践漏洞。因而可以认为,对于类似于“小偷反腐”现象这种无法评价为暂时占有、不能还原为具体权利人利益维护的赃物犯罪的刑法保护,占有说的观点及其解释原则并不适格。
那么,是否意味着对于贪官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手段所占有的财产就可以任由小偷抑或其他任何人任意窃取,换言之,贪官非法占有的财产是否不需要在刑法的角度予以保护,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么,对于贪官非法占有的财产如若予以刑法保护,亦即在小偷等行为人以盗窃、骗取等手段取得属于国家法益性质的赃物后,应当在理论上采取何种解释原则予以自洽?
笔者认为,在占有说无法解释抑或至少不能与其自我标榜的解释理由相吻合的情形下,本权说可以作为补充,并给出合理的解释结论。事实上,贪官通过贪污受贿等手段聚敛的赃款,虽然不能还原为具体的原权利人,但不能否认赃款应当属于国家所有的性质。传统理论大都认为,财产犯罪侵犯的法益是“国家、集体或者公民个人的合法财产所有权”。显然,贪官所贪污的赃款原本就属于国家所有的合法财产,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等作为国家事务的具体管理单位、经营单位当然也具有民事主体的地位,当然享有合法的财产权;贪官所非法占有的受贿赃款,虽然原本属于行贿人个人、行贿单位的合法财产,但是该行贿赃款的主要效用在于与贪官掌握的公权力进行交易和置换,在本质上行贿者的合法财物在与受贿贪官的权钱交易后已经质变为非法运用公权力谋取个人私利的对价。可以认为,由于公权力的国家性质,决定了非法谋取、营运公权力的赃款在归属上也应当回归于公权力的应然主体,即代表人民管理社会事务的国家。
然而,我国学者对于“国家对他人非法占有的财物具有所有权”的观点持否定态度,指出:就“国家对他人非法占有的财物具有所有权”的说法而言,实际上也就是说国家对违禁品享受所有权。但是财产所有权是民事主体权利的一项民事权利,作为所有权客体的物,首先必须能够成为民事权利的客体,而违禁品是法律上禁止任何人(包括国家)持有之物,其性质本身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民事权利的客体,说国家对违禁品享有所有权,岂不是很荒谬吗?而且,所有权的所得,以具体的交付为标准,违禁品在其产生之后,至其案发被没收之前,国家根本不知道其存在,也就不能对其加以处置,又怎能说国家对该物享有所有权呢。①参见黎宏:《论财产罪的保护法益》,《人民检察》2008年第23期。
笔者认为,“国家对他人非法占有的财物具有所有权”中的“他人非法占有的财物”既包括违禁物,也当然包括赃物(不能够还原为具体权利人占有的赃物,如贪官非法占有的赃物,即本文所归纳的国家法益),这里该学者虽然没有针对不能还原为具体权利人占有的赃物属于国家的结论提出质疑而仅仅针对违禁物属于国家所有的观点提出异议,这种论述我们同样也不能认同。
首先,财产所有权是否能够成为民事权利的客体,亦即能否认定为民法交易中的物,与违禁物属于国家所有的观念没有直接关系。确实,在民事交易活动中,民事权利主体用以交换、买卖的权利客体必须具有合法性,但这仅仅是民事交易秩序维护讨论的范畴,并不能得出违禁物不属于“物”的结论。有观点指出,违禁品不是一个内涵清楚的刑法概念,它的种类很多,法律对其禁止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判断一个物品是否属于违禁品更多的是依据行政法上的规定。例如,管制刀具不禁止持有,但禁止携带进入公共场所,淫秽物品不禁止持有,但禁止传播,枪支、弹药、爆炸物、毒品、假币等则禁止持有,因此对于管制刀具、淫秽物品这一类不禁止持有的违禁品,应当认为是有主物,可以纳入权利客体的范畴。②参见高翼飞:《侵犯财产罪保护法益再探究——为本权说辩护》,《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7期。违禁物作为“物”的一种,其客观存在性不容否认,不能因为其地位特殊就否定抑或忽视其客观存在,不管我们怎么否定抨击,违禁品作为“物”的客观存在性不会因为法律上的否定而自行消失。事实上,正如“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一样,违禁品在性质上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仅仅是不具有民事权利客体自由交易的属性,国家对于违禁品规范、限制的是持有主体的身份和地位。换言之,社会上普通公民对于违禁物的持有抑或使用当然有损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安宁,但是国家作为资源整合的责任主体,严格配置相应的持有限度、持有范围,使得违禁品严格限制在特定的范围,非但不会有损于社会秩序,还有助于社会整体法益的增加与保护。③比如,毒品如果在社会中自由流通势必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但是将其应用于医疗目的(比如杜冷丁),减免恶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延长其生命,则可以扬长避短,毒品也不再是单纯的毒品,而是带有特殊功效的药品。在这个角度上看,似乎否定国家对于违禁物的所有权属就显得过于武断。
其次,以具体交付为标准的所有权取得,同样只是民事交易活动的基础性事实,并不能否定违禁物国家所有权属的关系。比较而言,违禁物的性质、法律规定与国家对文物的管理规定类似。我国《文物保护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第74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会同公安机关追缴文物;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一)发现文物隐匿不报或者拒不上交的。根据法律规定,对于不能明确其所有者、继承者的文物,在出土发现之前就已经被拟制性的认为属于国家,任何个人不得私自藏有、占有,否则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由此观之,文物在出土发现之前,国家也不可能知晓其存在,难道就不属于国家所有吗?显然不是。同样道理,以“国家根本不知道”违禁物存在的理由否定国家对其权属的性质界定,显然也缺乏说服力。
四、结 语
在整体上,占有说及其中间说理论由于契合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要求,正成为大多数学者所提倡的财产犯罪刑法法益保护的务实态度,①参见尹晓静:《论作为财产犯罪保护法益的占有说》,《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而本权说在财产法益理论的整体范畴中逐渐式微的命运也愈来愈明显。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财产罪法益保护的理论选择上,占有说虽然在整体上占据了有力地位,但是从来没有否定本权说的基础性,“财产犯的法益首先是财产权及其他本权,其次是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改变现状(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的表述已经明显说明了这个事实。②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38页。占有说与本权说之间的矛盾在于,对于他人合法占有状态下的本人之物,本权者擅自取回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按照占有说的观点,本权者成立财产犯罪,而按照本权说则不构成犯罪。在当前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占有说显然更具生命力。但是,对于他人非法占有状态下的本人之物,本权者取回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占有说主张者无一例外地给出了绝对肯定性的回答,似乎又偏向了本权说的视域。对此主张,笔者认为需要足够慎重,应当考虑承认和尊重损失扩大禁止的基础事实,如果非法占有者本人合法利益与非法占有财物利益之间发生了“化学反应”衍生出了更高地位的利益,那么本权者恐怕也不能取得绝对的私力救济权力,而应该通过公力救济手段谋求利益之恢复。在国家法益侵害的类型区分中,支撑占有说观点的“暂时性占有”和“恢复至原权利人”的论据并无实践支撑,占有说对此并不能科学解释,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非法占有下的国家法益侵害救济更适合以本权说为支撑。概言之,对于不能还原为具体权利人权利恢复的赃物、违禁物等国家法益,占有说一方面在理论解说的层面不能涵盖全部范畴,贯彻始终;另一方面也难以处理司法实务中的矛盾。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财产罪法益保护的理论论辩中,本权说与占有说并不是学者之间所论战的针锋相对、格格不入的矛盾关系,而应当是一种补充关系。本权说虽然在整体上让位于占有说,但是在占有说不能完成其理论自洽时,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上也需要本权说的观点支撑。
(责任编辑:丁亚秋)
DF625
A
1674-9502(2017)05-102-12
作者:庄绪龙,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何向东,江苏居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