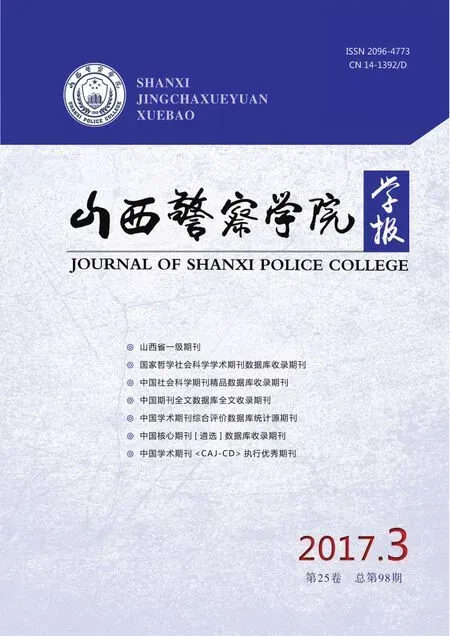古今维度下的死刑存废之争
——对唐律中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思考
□刘盈辛
(山西大学法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法学研究】
古今维度下的死刑存废之争
——对唐律中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思考
□刘盈辛
(山西大学法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危害统治安全和威胁皇帝安全等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是唐律重点打击的犯罪类型之一,在唐律中大多被规定为死罪,并且其在唐代死罪的数量上也占有较高比例。唐律之所以重惩此类犯罪原因在于封建社会中皇权至高无上的尊崇地位和统治者在大一统专制思想下对“国家”这一观念的重视。在当今国际死刑废除的浪潮之下,中国已在死刑废除与否以及具体实施步骤、程序、时间的问题上争辩许久,在具体罪名改革方面,我国死刑所占比例最高的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则是罪名改革的焦点之一。中国古典律法之最的唐律对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重惩,其背后蕴含的维护大一统理念以及强烈的天下国家观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代中国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保留死刑的必要性,及其在死刑改革的热浪之下部分死刑罪名保留的必要性。
唐律;危害国家安全罪;死刑存废;死刑制度改革
贝卡利亚说过:“在一个组织优良的社会里,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人们可以凭借怎样的权利来杀死自己的同类呢?”[1]43自1764年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首次明确提出了废除死刑的主张后,死刑的存废便成为一个旷日持久的话题,各方站在不同立场上提出了各式论证。然其不单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仅从学理上抽象论述颇难定论,“中国死刑存废的价值理念议题过于抽象,最终理论依据回到了道德、生命价值、人权等一系列更为抽象和宏观的概念中,而关于如何界定和解读这些概念,人类社会数千年来亦未能得出共识。同时,对于这些概念的不同解读,往往同时成为死刑存废争论双方的共同依据,例如,关于死刑存废是否尊重生命这一视角,似乎任何解读都有合理性。”[2]若是对于死刑存废一直专注于抽象层面的争辩恐是意义甚微,因此,应将视野更多地转向现实的改革策略上来。危害国家安全罪作为我国死刑罪名规定最多的一类犯罪理应是死刑制度改革中所需关注的重点之一。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在新时代随着国家安全观念的扩充和发展,对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重视程度也愈加深。对这样一个由来十分久远的犯罪自然需要用历史的眼光进行研究和改革,而唐律作为中华法系的集大成者,对此类犯罪的规定也是极其完善和缜密。那么,对当下死刑制度改革相关方面的探讨以唐律中具体规定为视角是很有意义的。
一、皇权思想下的唐代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
诗经有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古代君王地位的尊崇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在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般言论之下也是为了“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最终目的,“天子”、“王”、“帝”、“君”的尊崇地位自秦代始便又延续至皇帝,逐渐构成一个以皇帝、皇室为核心的政治社会组织,这个组织是以皇权至上的权力架构为基础的,国家是皇帝个人和“天下”构成的统一体,彼时的“国家”从政治层面也就意味着一个以皇帝为最高统领且具有统一疆土的庞大帝国。《唐律疏议》曰:“案《公羊传》云:‘君亲无将,将而必诛。’将有逆心,而害于君父者,则必诛之……王者居宸极之至尊,奉上天之宝命,同二仪之覆载,作兆庶之父母。为子为臣,惟忠惟孝。”(《唐律疏议·名例律·十恶》)可见君主被视为民与天交通的自然界之最高统领,民不尽自己应对君主所承担的义务,便是有违天命和天道,是对自然秩序的破坏。于此情况下,对于皇权、对统治者个人及其政权安全的侵犯即是对国家安全及统治秩序的破坏;唐律中对国家安全的保护亦是以保护皇帝个人、维护专制皇权和政权安全为重心。故而唐律对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的处罚甚重,大多罪至斩绞,这一点从沈家本对唐律死罪的考察中可窥得一斑:
(一)唐死罪中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以侵犯皇权罪为中心
1.侵犯皇帝人身安全及尊严的行为。皇帝个人的安全问题与国家安危息息相关,因此,唐律对侵犯皇帝本人的行为处罚是极重的。其中,一类是对皇帝个人人身安全的保护:唐律《卫禁》中对皇帝居所安全维护的规定,如“持杖及至御在所者”[3]573;“越殿垣者”[3]577;“奉敕夜开宫殿门,其不承敕而擅开闭者”[3]578;“宿卫人于御在所误拔刀子”[3]578等擅自进入皇帝宫殿以及宿卫人员违反宫廷守卫规定的行为,皆处以死刑;另有《职制》中对皇帝起居饮食安全维护的规定,如“主食者造御膳误犯食禁”[3]578;“工匠御幸舟船,误不牢固”[3]578等对皇帝服务过程中的失误行为。据唐大理少卿戴胄之解释:“臣子之于尊极,不得称误。准律云:‘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旧唐书·戴胄传》)。此类行为因具有对皇帝安全造成危险的可能性,为保障皇帝个人绝对安全,即便出于过失也构成死罪。若是故意,那便另当别论了。另一类是侵犯皇帝尊严而构成的死罪,如《职制》中“指斥承舆及对捍制使条”之规定“指斥乘舆,情理切害”[3]573;“对捍制使而无人臣之礼”[3]578以及《贼盗》、《诈伪》中的“盗御宝”[3]580;“伪造皇帝八宝”[3]576;“盗皇帝八宝封用”[3]576;“弃毁御宝”[3]584,这皆是一些当面斥责皇帝(斥责中有“欲杀”“欲反”字眼则构成谋反罪)、违背皇命或是偷盗、伪造皇帝御宝、符节等直接或间接侵犯皇帝或皇室尊严和权威的行为。甚至一些情况下,律中未明文规定为死罪,出于维护皇帝信息的私密性和个人权威也被处以死刑,足见对于皇权维护之谨慎和严苛。
2.侵犯专制皇权及政权安全的行为。其中,最重的是反逆类犯罪:倘若危害皇帝本人的犯罪行为只是间接上可能造成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后果,那么,谋反、谋大逆、谋叛则是对皇权的直接挑衅和对国家安全的直接危害,是古代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的主要形式。所谓谋反,即为子为臣“将起逆心,规反天常,悖逆人理”的行为;所谓谋大逆,即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的行为;所谓谋叛,则是“谋背国从伪装”等投奔他国或投降与唐统治者政权相敌对势力的行为。《贼盗》所规定的死罪中,“三谋”重罪被列置于首位,“谋反大逆条”及“谋叛条”规定有谋反、谋叛、谋大逆及亡命山泽“抗拒将吏”[3]574;“不从追唤”[3]579(古代亡命山泽可能被认定为谋叛)即为死罪,而谋反之罪即便未能为害,然而犯意既起、行动已施的“谋”字成立都可处斩。此外,对于此类犯罪见知不告不举的行为也处以重罪。甚至,对于诬告谋反及大逆的行为,为首者要处斩,从犯也要处以绞刑。足可见统治者对此类犯罪行为惩罚之严厉,更可见其对于皇权稳固、政权安全的危害之大。
除反逆类犯罪外,还有一些诸如巫术、邪教等通过思想言论的传播来动摇统治者执政地位、颠覆政权等对封建国家安全造成危害的妖妄犯罪。《贼盗》中“造妖书妖言”条对“诸造妖书及妖言者;传用以惑众者”[3]580规定处以绞刑。还有些妖妄犯罪与谋反谋大逆等结合,造妖言谋为反逆,如此例:贞观十三年,道士秦英、韦灵符与还俗道士朱灵感,“惑乱东宫,结谋大逆”,后秦英等并被诛斩,私宅财物及妻子并配人官,便是散播妖言化而为谋逆类犯罪。[4]这些妖邪行为、异端邪说对社会稳定具有严重的现实危害,且大多政治意图明显,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出于加强社会控制、维护统治安全之目的,此类犯罪也是唐律重点打击的危害国家安全类的犯罪之一。
3.危害国防、军事安全的行为。此类犯罪行为更为直接地危及国家安全,与统治阶级的政权安全关系密切。唐死罪中也有诸多关于此的规定,《职责》《卫禁》中“诸漏泄大事*“大事”指“潜谋讨袭及收捕谋叛之类”,参见胡兴东《中国古代死刑制度史》。应密者”[3]578;“密有征讨而告贼消息者”[3]573等泄露国家重要事项的行为皆至死罪。而一些军事类犯罪,诸如主将守城弃去、临阵先退等情况下也可能构成死罪,如《卫禁》中对“连接寇贼,被谴斥侯,不觉贼来,以故有覆败者”[3]573是处斩的。还有一些诸如“越度沿边关塞,私与禁兵器”[3]578等违反边防警卫制度以至威胁到边防安全的行为也会构成死罪而处以绞刑。
(二)唐代重惩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之原因:统一国家下的政治整合力
1.观念与结构:统一国家的建构
探讨唐代重惩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的原因,就不得不提及统一国家观念与形态的建构,而这观念与制度的源起则是大一统的思想。“大一统”一词最早出现于《春秋公羊传》,《公羊传·隐公元年》中有记载:“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 先言王而后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之王正月?大一统也。” 在春秋战国时已有所发展:如孟子对梁襄王“天下恶乎定”的发问所作“定于一”的回答(《孟子·梁惠王上》);荀子“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则天下归之,若蝉之归明火也”(《荀子·致士》)的说法;老子“抱一为天下式”(《道德经》),李斯“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史记·李斯列传》),其间都可见到统一的思想。然此时“一”的思想还仅是基于渴望结束当时分裂局势的现实期盼,那么秦汉以后“一”的思想则真正转化为政治治国理念。秦代据此建立了疆域上具有政治统一体特征的大一统封建专制国家,至于汉代,董仲舒则有过更为系统化的论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5]也就是从思想、法律、制度上都遵循“大一”,这与早前单纯谈统一的内涵有所不同,在“一”与“统”之下萌生了天下国家观念,“中国古代先哲之思维,皆以‘天下’为立足点,而不是以‘国、家’等一部分自画,此乃百家所公同”[6],事实上,作为转义的社会概念,“天下”已由本义转而指代时人所能认识到的国土范围,其含义在春秋战国以后是与“国家”基本一致的,“天下一统”可能只是无法界定的空泛的想象,然而,在此基础上的统一国家的概念轮廓却日益清晰,并进一步加深为维护疆域、思想、制度统一等国家秩序方面的重要内容,大一统”思想是中国古人在国家观念上的奠基性规则和牢牢奉行的传统。
“一统”之下,维系王朝和庞大帝国统治成为重中之重。自秦建立的“六国毕,四海一”的中华帝国在经历了南北朝三百多年分裂后于公元七世纪的唐代复兴,秦的统一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及社会规模延续至唐代,进一步主导着唐代“统一体”的国家意识的发展,并成为统治者意识形态的核心,“天下一统”、“太平盛世”成为统治秩序得以维护的外在表征,“万世一系”更是统治者建基在统一国家上的美好愿景。 历史学家费正清言:“中国自唐代以来一直是一个牢不可破的政治统一体”,“‘五代’时期的混乱只持续了50年左右,这与六朝时期长达350年的分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7]大一统的天下国家观使得唐代国家意识内化于具体的政治统治中并不断加深。
2.皇权下的国家安全:与统治相关
大一统思想中的具体构建原则有二,一则制度统一;二则权力集中。因此,中国古代的大一统专制国家是建立在皇权(君权)唯一性基础之上的集权国家,皇帝是皇权的拥有者,“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封建社会下整个国家是由一个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所掌控,这个集团对国家具有强大的控制力,而皇帝则是这个集团中的绝对权威。皇权至上而国家权力集中于皇帝,皇帝与专制化为一体,在某种程度上皇帝即是国家,梁启超曾说过君主是“既攘国家为己一家之私产矣”,国家是在皇帝私有化王朝的控制中的,那么又可以说,王朝即为国家,王朝与国家的一体使得统治集团内部对国家安全的重视形成一致的集体认同。统治集团尤其是集权者皇帝本人,为了保证自己所有的王朝安全存在,就必须承担对国家安全的保护,故唐代统治者对国家安全的构建是站在维护自己的统治秩序的立场下的。有学者指出,唐代的“中国”就有指向政权之含义*据《旧唐书·宗楚客传》载,唐朝宰相宗楚客因受西突厥阿史那忠节的重赂,发兵攻突骑施首领娑葛,监察御史崔琬劾奏楚客称:“今娑葛反叛,边鄙不宁,由此贼臣,取怨中国。”这里的“中国”便是政治权力机构的概念,指朝廷或中央政府。因为突骑施臣属于唐朝,此处称突骑施首领要葛为“贼臣”,即承认他是唐朝的臣子,他所怨恨的“中国”,当然是发兵攻伐他的朝廷或中央政府。参见李方:《试论唐朝的“中国”与“天下”》,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然而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中国”代表的政治共同体越来越具有国家含义,国家安全自然与政权安全密不可分。还有学者认为,即便是“中国”的“中”字,也包含一种“以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8],这个“我”自然指向的是统治阶级,尤指皇帝,那么国家则限缩为成为一个皇权下的王朝和政治实体,统治集团的政权安全和皇帝私有的王朝的利益便混同于国家利益。于此而言,对古代国家安全维护的价值取向则趋同于对于统治者及其政权安危的维护,皇帝维护自己政权安危之迫切心理随之转化为对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的重惩上来。
二、危害国家安全罪于当代
(一)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和1963年《刑法草案(第33稿)》基础之上于1979年刑法中正式确立了反革命罪,并在刑法分则第一章做了明确规定,第90条对反革命罪下了严格的定义:“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罪。”具体而言有13个罪名*这13个罪名为:第91条“勾结外国、阴谋危害祖国罪”;第92条“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第93条“策动投敌叛变或叛乱罪”;第94条“投敌叛变罪”;第94条“投敌叛变罪”;第95条“持械聚众叛乱罪”;第96条“聚众劫狱、组织越狱罪”;第97条“间谍、资敌罪”;第98条“反革命集团罪”;第99条“组织、利用封建迷信、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罪”;第100条“反革命破坏罪”;第101条“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第102条“反革命煽动罪”。,其中可判处死刑的罪名有10个*除第98条、第99条、第102条外,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判处死刑。。此时反革命罪的涵盖范围较为广泛,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而设立的罪名,对于当时打击反革命分子和维系新生政权安全是有很大意义的。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经济、政治、社会情况都有所不同,立法价值取向和刑事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基于现实情况对反革命罪的具体条文进行了增删、调整,并于1997年刑法正式确立了现行刑法中具有实在的法律概念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仍然置其于刑法分则第一章,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反革命罪”自此成为历史。而后经历次补充、修正,我国现行刑法中关于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章的条文规定有12条,包含12个具体罪名*这12个罪名为:第102条背叛国家罪、第103条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第104条武装叛乱、暴乱罪、第105条颠覆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第107条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第108条投敌叛变罪、第109条叛逃罪、第110条间谍罪、第111条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第112条资敌罪。,其中,死刑罪名有7个*根据《刑法》第113条规定,第一章上述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中,除第103条第2款、第105条、第107条、第109条外,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是构成死刑罪名所占比例最高的一章。也就是作为古代打击最为严厉的犯罪,即便制裁的立场和所保护利益有所差别,其危害性仍是最为严重的,对其惩罚也是最严厉的。有学者为危害国家安全罪所下定义为:“故意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利益及安全之行为。”[9]也有学者认为危害国家安全罪是:“违反我国刑法的规定,故意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应受到刑罚惩罚的行为。”[10]还有学者认为是:“损害国体、政体及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国防和其他安全利益的犯罪。”[11]然不论诸具体含义的差异如何,都体现了一个中心内涵,即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国”之利益的维护,而非仅仅维护政权、出于阶级斗争的目的打击“敌人”,正如我国刑法对危害国家安全罪客体之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和利益。”这既摒弃了刑法所规定的客体中的政治色彩,且又表述得更加全面和准确了。[12]
(二)观念之变:当代国家安全观的新血液——“政治安全”到“国民安全”
早前学界对国家安全的概念曾做过一些探讨,譬如:“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防止境外间谍、敌特势力进行渗透和破坏的专门能力与措施之和”[13]、“国家安全是指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制度不受外来势力的侵害”[14]、是“维护主权国家存在和保障其根本利益的各种要素的总和”[15]等,均是立足于旨在维护国家主权、领土、政权等具有政治意义的“政治安全”的立场,很大程度上与唐代或者说是中国古代对于国家安全的观念有一脉相承之感,只是具体的利益指向有所不同;现代国家安全的范围则随着“人的安全”观念的兴起有所扩大,可以说,“人的安全”概念之兴起可以看作是对仅以国家为中心且片面以军事手段为主的传统安全观的补充,是对新历史条件下的各类新型安全威胁的直接反应。联合国1994年度首个《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现代人们对于安全(事实上是宏观层面上的安全)的理解过于狭隘,仅仅停留在例如免受外来侵略的领土安全、对外政策中的国家利益保护或者免遭核浩劫的全球安全等,而“对于在日常生活中寻求安全的普通民众的合理关切则被遗忘了”[16]。尽管这种理解不免存在“泛安全化”倾向,但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说,当代意义上国家安全之概念应很大程度包含整体的国民利益,或者更进一步讲,国家安全只是手段,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罪之规定的落脚点是为了保护一国之下的国民安全。
因此,随着当代社会国家逐渐被赋予更多道德价值,停留在狭义上“国家安全”的传统国家安全观也随之变化。与唐代所不同的是,国家安全的重心由封建时代侧重皇族、皇权安全向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国民安全转变。国家是国民的集合体,相较于唐代完全在于对皇室一家以姓氏统治和政权等具有政治意义的保护,当代国家安全观除包含本身的政治属性外还具有国民安全的内容,在价值取向上显然更具有进步意义。
三、存与废的艰难抉择:当代中国死刑改革的特殊性
(一)“死刑废除热”——西方死刑废除思潮的侵入
在相当长时期内,死刑作为威慑犯罪的武器,其地位本是无可撼动的。而至18世纪,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否认了死刑的威吓作用并率先强烈地谴责了死刑:“用死刑来向人们证明法律的严峻是没有用处的”。如果说,欲望和战争的要求纵容人类流血的话,那么,法律作为人们行为的约束者,看来不应扩大这种残暴的事例。随着人们用专门的研究和手续使越来越多的死亡合法化,这种事例就更加有害了。体现公共意志的法律憎恶并惩罚谋杀行为,而自己却在做这种事情:他阻止公民去做杀人犯,却安排一个公共的杀人犯。”[1]47此后,学界对死刑的质疑和反对声便从未停止。随着源起欧洲的死刑废除运动陆续取得成效和国际人权运动的兴起,20世纪国际死刑废除运动风起云涌,并进一步推进了理论上死刑废除论的发展。各方纷纷从报应观、人权、正义观、功利主义、威慑主义的角度更加强烈地抨击死刑,自此高举人权和生命价值旗号的死刑废除论便占领了国际舆论的高地。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国际死刑废除思潮亦对我国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国际交往的需要和维护国家形象的压力之下,起源于欧洲的死刑废除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的死刑制度改革。
(二)死刑不应完全废除,部分罪名不放弃适用死刑
在废除死刑的热浪冲击下我们要时刻保持思维的清醒,死刑仍有其巨大功用,即便是死刑废除的支持者贝卡利亚,也对某种特定情况下死刑的必要性表示支持:“其一,某人在被剥夺自由之后仍然有某种联系和某种力量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安全,或者他的存在可能会在既定的政府体制中引起危险的动乱。其二,当一个国家正在恢复自由的时候,当一个国家的自由己经消失或者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时候,这时候混乱取代了法律,因而,处死某些公民就变得必要了。”[1]47这就是说死刑作为手段在某种情况下仍为法律所需要,全面废除死刑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主张,在相当一部分国家是行不通的。国际死刑废除的大浪潮也时有倒退和反复:譬如美国 1972 废除死刑后于1976 再次恢复死刑。可见,即使死刑的完全废除在理论上已进行过十分成功的论证,诸多情形下基于实际情况也不得不恢复。就如日本学者正田满三郎说:“我认为死刑作为理念是应该废除的,然而抽象地论述死刑是应该废除还是保留没有多大意义,关键在于重视历史的社会现实,根据该社会的现状,文化水平的高下等决定之。”[17]在死刑的废除问题上,社会的实际需要是更需要考量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中国的死刑制度改革应立足国情。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急剧转型变动期,国际社会的各方博弈和动荡局势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压力和潜在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死刑作为保障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利器具有了更加现实化的功利效用。现阶段死刑改革在对部分罪名削减死刑的同时,也要针对部分罪名的死刑有所保留,有些罪名甚至不可放弃死刑。笔者认为,危害国家安全此一类犯罪因其一旦出现可能造成的严重破坏性,即便其中大多死刑罪名长期设而未用,也并非虚设,更不应废除。唐代法律设置的经验和当代的新变化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首先,只要有国家存在,此类罪就必然存在。任何一个阶级夺取政权确立统治地位之后,都会借助法律这个工具,威慑打击企图否定、推翻自己统治的行为。唐代将危害政权稳定和统治秩序的犯罪、危害皇帝人身安全和个人尊严的犯罪都视作危害国家安全一类的犯罪,其中规定又极其细密,三谋重罪以外更多诸如思想言论类犯罪、军事类甚至经济类犯罪都可归为危害统治秩序和威胁皇权之中。而另一方面,“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土长期保持统一且未被分裂,文化传统古老且未能割断的国度,在世界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18],这样,由统一国家建构之下的国家实体和国家观念所衍生出的国家利益无疑会对制度施以强大的作用力。故唐代的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是唐律所规定死刑罪名最为集中的地方之一,也是统治阶级用死刑来维系统治和政权安危的手段,唐律中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的规定即是法律,或者说是刑法的政治工具属性的体现,其中有关死刑的设置所具有的工具主义性质则更为明显。而当代法律的工具性作用也未曾弱化,执政者仍需强化政权意识,利用法律来维护国家政权稳定,用死刑来惩治恶意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危害的行为。即使国家利益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有其差异性,那么建基在统一国家之下的国家观念和认同感也是不变的。在国家利益和国家观念都存续的情境下,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的死刑继续使用就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在统一国家观念和国家安全利益的支配下的国家行为取向理应一以贯之地对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予以严厉制裁,作为对政权稳定和国家秩序具有严重危害性的犯罪,其死刑罪名不可废除,以彰显国家维护稳定的决心。
其次,在国家安全概念新内涵下对危害国家安全罪保留死刑更符合死刑的有利性要求*这里谈到死刑的有利性不得不提及死刑的价值性:“死刑的价值性是指死刑的收益必须大于死刑的代价,即死刑所保护的权益应大于其所剥夺的权益的价值。当死刑被分配于所侵犯的权益的价值高于人的生命价值的犯罪时,死刑所保护的权益的价值绝对大于其所剥夺的权益的价值,即生命,因而绝对具有有利性。当死刑被分配于所侵犯的权益的价值低于人的生命的价值的犯罪时,死刑所保护的权益的价值绝对小于其所剥夺的权益的价值,即生命,因而绝对不具有有利性。所以,死刑是否具有有利性,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看死刑被分配于哪些犯罪。对危害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安全的有关犯罪所分配的死刑具有绝对的有利性,对故意杀人罪所分配的死刑也具有有利性,而对其他犯罪分配死刑则绝对不具有有利性。”参见王亚贤《中国语境下的死刑存废》,吉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4页。。唐律中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的惩罚及建国后反革命罪的规定更多是以维护“政治安全”为目的,现代意义的国家安全观虽包含有政治安全的意味,但更多地融入了对“人”的重视,国家对国民的服务功能强化,政治安全逐渐转向国民安全。若要维护国民安全,重点仍是对国家安全的保护,国家安全是国民利益得以保障的前提,一国内部的安定状况直接影响着国民的安全利益,国家安全和国民安全是相互包含的,国家安全之内涵是兼具“国家”与“国民”双重利益的。因此,在当代对危害国家安全罪规定死刑仍有其正当性。从抽象的等价观来看,剥夺人生命的死刑在所保护的法益不小于被死刑所剥夺的法益是合乎公正性理念的。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其所造成的国家和国民安全(包括国民生命)的损害远远大于因死刑所被剥夺的个体生命损害。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死刑构成条件“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的规定,也体现了其是在造成严重法益侵害的情况下才适用的。所以,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死刑适用也是有一个较高标准的,要做的是明确具体标准,而不是对其直接废除。
最后,国内外严峻的犯罪态势要求我们亦当对危害国家稳定和统一、危害国家安全等此类对国家、国民利益造成严重侵犯的犯罪行为的制裁不放松。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矛盾和部分地区动荡局势下,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势力日益猖獗,这些犯罪行为都以危害国土安定统一、国民安全等方式严重威胁着一国安全。与此同时,国内外反动分裂势力对政权正虎视眈眈,对社会主义制度蓄意颠覆和破坏,我国国家统一与安全正面临巨大威胁。唐代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打击范围较窄,或者说其不安全因素来源单一,仅仅是威胁皇权和个人统治,其后果无非是一家一姓之更迭,与当代所面对的多样化威胁因素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不同。然唐律中危害国家安全罪的规定,在以惩治谋反、谋叛、谋大逆之罪为重点的表征下,其所蕴藏的对古时作为“天下”的“国家”本身和统一国家观念中认同感在现今也应发挥其内在历史延续性,这是在任何时代任何阶段的语境之下都不可摒弃的。在如今藏独、疆独势力威胁加大的情况下,鉴于对国家统一与生存安危之利益的保护,危害国家安全罪死刑不应弃用。
“不审势则宽严皆误”[19],研究死刑的存废问题要结合我国法律传统和现实情况,才能对死刑制度的改革做出更良效和有针对性的建议,才能“不误宽严”。
四、结语
死刑废除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不能片面地谈存废去留,对其改革也要从复杂漫长的历史里、从民族法律传统中寻求借鉴。中国的死刑制度改革最终还需从中国本土中找到解决办法,传统文化亦是十分重要经验。尽管封建时代已逝于历史中,中华法系也已瓦解,然而,灿烂辉煌的文明铸就的历史不可抛弃,其间的法律制度耐人回味,作为中华法系的集大成者的唐律更是凝练了前代统治者治理经验之精华。从传统制度、文化的经验中参考、总结、吸收为当下所需,对现代制度改革,具体地说对死刑制度的改革是大有裨益的。
[1]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3.
[2]于志刚.死刑存废之争的三重冲突和解决之路[J].比较法研究,2014(6):77-95.
[3]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上)[C].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4]陈 玺.唐代惩治妖妄犯罪规则之现代省思[J].法学,2015(4):151-159.
[5]班 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523.
[6]江 湄.北宋诸家《春秋》学的“王道”论述及其论辩关系[J].哲学研究,2007(7):27-35.
[7]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2:133.
[8]陈玉屏.略论中国古代的“天下”、“国家”和“中国”观[J].民族研究,2005(1):67-71.
[9]陈兴良.刑法疏议[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210.
[10]于志刚.危害国家安全罪[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26.
[11]魏平雄,赵宝成,王顺安.犯罪学教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515.
[12]张明楷.刑法学(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541.
[13]李 敏,吴 为.国家安全法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230.
[14]胡锦光,王 锴.论我国宪法中“公共利益”的界定[J].中国法学,2005(1):18-27.
[15]刘卫东.论国家安全的概念及其特点[J].世界地理研究,2002(2):1-7.
[16]石 斌.“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国际政治视角的伦理论辩与政策选择[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2):85-110.
[17]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844.
[18]田卫疆.关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原因的探索[J].新疆社会科学,2004,(6):92.
[19]张崇琛.“后来治蜀要深思”:成都武侯祠一副对联的解读[J].档案,2004(1):17-19.
ControversyofExistenceandAbolishmentofDeathPenaltyinViewofAncientandPresentTimes——Thinking on the crime of endangering state security in Tang Law
LIU Ying-xin
(SchoolofLaw,ShanxiUniversity,Taiyuan030006,China)
Crime of endangering state security such as endangering reign security and threatening the emperor’s security is one of the crimes that were stricken severely and more sentenced to death and taken a high proportion in death penalty in the law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severe punishment of this kind of crime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peak of feudal legal development, was that the idea of the supremacy of the emperor and the unification of the country was emphasized much in feudal society. In the modern society, the abolishment of the death penalty tends to be popular and there have also been the disputes about whether death penalty should be abolished, concrete application steps, procedures and time in China. In the reform of crime name, the crime of endangering state security, taking the highest proportion in death penalty in China, is one of the focuses of crime name reform. The ideas of unification and strong domination in the severe punishment to the crime of endangering state security in Tang Dynasty Law showed the necessity of reserving death penalty to endangering state security in China and reserving some crime name for death penalt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death penalty reform.
Tang Dynasty Law; crime of endangering state security; abolishment of death penalty; death penalty system reform
2017-03-05
刘盈辛(1994-),女,山西运城人,山西大学法学院2016级法律硕士研究生。
D929
A
1671-685X(2017)03-0037-07
(责任编辑:黄长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