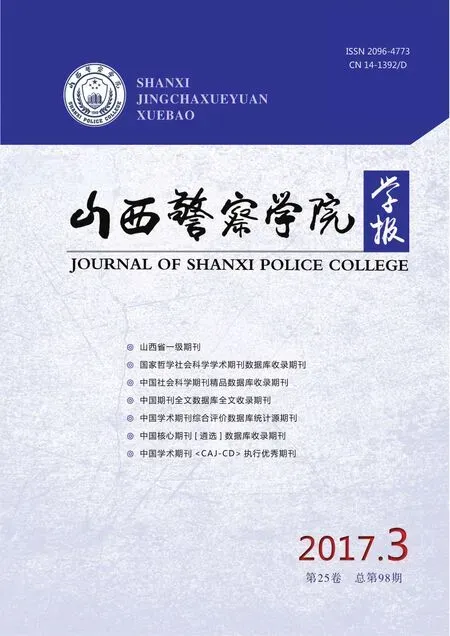细化刑事裁判文书说理要求的现实路径
——基于于欢案一审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申 巍
(山西警察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1)
【法学研究】
细化刑事裁判文书说理要求的现实路径
——基于于欢案一审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申 巍
(山西警察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1)
细化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要求,是当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当前通用的刑事裁判文书在事实部分的制作中存在问题,亟须纠正。建议增加对关键事实、证据的评判内容,落实质证过程。
错案;裁判文书;说理;以审判为中心;于欢案
裁判权是审判权的核心,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依法裁判的重要表现形式。为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越来越多的裁判文书于各级司法机关的官网上公开,这不仅实现了公众的知情权,更重要的是起到了民众监督法律实施的作用。在公开的裁判文书中,民众希望看到定性准确、结构完整、论证有力的说理过程。而司法实践中的刑事错案或引发热议的刑事案件,其裁判文书中事实部分内容往往是当事人双方争执的焦点所在。因此,改变事实论证不充分,法律推理不到位的现状,成为细化裁判文书说理的重要初衷之一。为方便起见,下面以时下一起热点案件的一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书展开讨论。
一、于欢案一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书中的核心认定
2017年3月26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于欢案的一审判决书在网上热传。[1]这是一起引起网民热议的有关正当防卫认定的案件。正当防卫是国家提倡、刑法认可的私力救济途径之一。但近些年的法院判例显示,此制度往往被推入法律和民意对立的尴尬境地:是法律制度太严苛,还是民意太任性?细究该案的一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书,①见其核心争议为:
“关于被告人于欢的辩护人提出于欢有正当防卫的情节,系防卫过当,要求减轻处罚的意见。审理认为,被告人于欢持尖刀捅刺多名被害人腹背部,虽然当时其人身自由权利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辱骂和侮辱,但对方均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和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犯的现实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所以于欢持尖刀捅刺被害人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的不法侵害前提,辩护人认为于欢系防卫过当以此要求减轻处罚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这是法院对该案所引发争议的问题的分析、认证,恰恰是这一段文字表述,引发了社会各方的争议。
二、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性,不是加害行为
我国刑法典第20条对正当防卫作了明文规定。张明楷教授从刑法教义学角度对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即防卫意图、防卫起因、防卫时间、防卫对象、防卫限度等五个方面予以了细致的阐释和界定,成为学界的通识。在此基础上联系于欢案,笔者认为被告人于欢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需要从上述五个方面详加分析。
(一)防卫意图
防卫意图的合法性是彰显行为的正当性的首要条件,我国刑法典第20条第1款对此作了明文规定。于欢案中,法院在判决书的“本院认为”部分曾有这样的认定:“本案系在被害人一方纠集多人,采取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秩序,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侮辱谩骂他人的不当方式讨债引发,被害人具有过错。”这一法律认定能否构成于欢的防卫意图?即,当警察出警到达现场后,进行了言语制止,正待转身离开中心现场——接待室时,于欢紧随其后也想出去,但是立即遭到了讨债一方的多人阻挡。这时,于欢能否为了维护自己和母亲的人身自由不再遭受非法限制和随时可能继续的侮辱谩骂、为了恢复企业正常经营秩序,而实施防卫行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能跟着警察离开现场,于欢本人及其母的人身自由权和人格权,以及企业正常的经营秩序都有很大可能得以恢复。警察未出警之前,这些法益已经遭受损害,当警察已经亲临现场,难道于欢不能借机来保护这些权益吗?
(二)防卫起因
防卫起因表明正当防卫是被动发生的行为,其实施的前提是必须有不法侵害实际发生和客观存在。而且,不法侵害发生与存在在先,正当防卫实施在后,即二者有时间上的顺序要求。那么,在于欢持尖刀捅刺被害人之前,可否有不法侵害已经发生?这需要从该案的判决书中寻找经过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才能予以证明。故此罗列有不法侵害已经发生和客观存在的事实如下:
“经审理查明,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负责人苏银霞向赵荣荣借款100万元,双方口头约定月息10%”;“2016年4月14日16时许”到“约21时50分”,“杜志浩等多人来到苏银霞和其子于欢所在的办公楼一楼接待室内催要欠款,并对二人有侮辱言行”;“被告人于欢欲离开接待室被阻止,与杜志浩、郭彦刚、程学贺、严建军等人发生冲突……”。
综上,首先,杜志浩等人在案发当日催要的债款属于非法所得。众所周知,高利贷是法律禁止的行为。苏银霞前期借款100万元,至案发之前,已经还款152.5万元。对于民间借贷,超出法律许可范围的利息不受法律保护,而10%的月息已经大大超过国家规定的合法年息36%的上限。其次,非法拘禁罪是持续犯,自案发当日16时许至21时50分许(民警未出警之前),于欢及其母因拖欠不被法律保护的高利贷而被讨债者非法拘禁长达5小时左右。最后,即使民警朱秀明等人赶到现场并有处警行为,但是没有将于欢及其母从非法拘禁的不法状态下解救出来。事后,经聊城市纪委、市委政法委牵头的联合工作组调查,认为出警民警在警情处置过程中存在处警不力、对现场处置严重失责等失职行为,并明确指出:“民警朱秀明等人在多名讨债人员阻止于欢、苏银霞离开接待室的情况下,未采取有效措施。”[2]上述事实表明非法拘禁的不法侵害不仅存在,而且始终持续进行。除此之外,于欢及其母还伴有被侮辱、殴打的事实存在。有基于此,被告人于欢具备防卫的起因条件。
(三)防卫时间
我国刑法典第20条第1款对防卫时间的规范表述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通说认为,所谓“正在进行”是指不法侵害正处于已经开始、尚未结束的进行阶段。仔细揣摩于欢案一审判决书,不难看出其认定于欢不具有防卫紧迫性源于两个理由:一是对方“未使用工具”,二是“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犯的现实危险性较小”。对此,笔者反驳如下:
首先,这里的“工具”,是通常意义的脱离人身体之外的工具。网民热议此案,其中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就是:当着一个儿子和众人的面,以故意暴露下体的方式侮辱这个儿子的母亲,即使不属于通常意义的“使用工具”,但其行为的卑劣恶性,也已经超过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严重挑战了公众的道德认知。“使用工具”是反映不法侵害的恶劣性的具体表现,而不是要求所有的不法侵害都必须“使用工具”。一审判决词在此的逻辑推理是本末倒置的。
其次,一审判决书似乎认为只有在不法侵害人“使用工具”的前提下,防卫人才有防卫的紧迫性,这种认识缺乏合理依据。
再次,民警的出警行为并未起到实质意义,没有达到法律所期待的效果。民警在接待室主要说了一句话:“要账可以,不能打架”,然后转身室外去“进一步了解情况”。这对室内被非法拘禁的于欢及其母来说,讨债人没有因此主动散伙,于欢及其母也没有因此顺利脱身。严格地说这是一种不完全不作为行政行为,民警处警之后案情向恶性方向持续发展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最后,于欢亮出水果刀后,并没有使对方停止不法侵害。于欢及其母欲跟从警察以摆脱非法拘禁被阻之后,绝望之际亮出了水果刀,但是讨债者并未就此离去。说明于欢持刀在手,也没能制止住不法侵害的继续进行,至少非法拘禁的状态仍在持续。
(四)防卫对象
正当防卫只能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施。于欢案中,于欢捅刺的对象都是讨债人员,因此符合该要求。
(五)防卫限度
正当防卫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如果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就构成防卫过当。由于我国刑法没有对“必要限度”作出明确判断标准,因此学界主要存在“必需说”、“基本适应说”和“相当说”等三种观点。张明楷教授认为,“相当说”是“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原则界限与具体判断标准的有机结合。”[3]基于此说衡量于欢的捅刺行为,仅以目前一审判决书提供的信息,笔者无法断定该行为是否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理由如下:
首先,“相当说”认为必要限度以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但是防卫强度常常不好判断,尤其是在侵害方的人数远远大于防卫方的人数时。于欢案中,从结果看于欢情绪激动之下连续捅刺四人,且每人腹部、背部各一刀。究竟捅刺到第几刀就是制止不法侵害的必要限度,事实上并不好准确判断,而且事后的冷静分析也不能替代当时特殊情境之下防卫人的认识和意志。判决书中现有的证人证言和被告人供述均不能明确解释这个问题。
其次,不能以存在重大损害结果就推定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从刑法典第20条第2款的字面意思理解,“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造成重大损害”之间的关系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种,二者是并列关系,即构成防卫过当必须要求行为既要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还要造成重大损害的结果。第二种,二者是因果关系,即因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所以致使重大危害结果的发生。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更为合理。第一,这种解释更符合社会相当性理论。赵秉志教授认为,刑法典第20条第2款的规定运用了社会相当性理论。也就是说,“只有正当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才成立防卫过当;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不能成立防卫过当;虽然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但没有造成重大损害的,同样不能成立防卫过当。”[4]第二,从因果关系判断,容易导致一种误解,以为重大损害结果都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制导致的,因此往往以是否具有重大损害结果来判断是否超过必要限度。有重大损害,就认为是超过必要限度;反之,则没有超过。这显然有客观归罪的嫌疑。从于欢捅刺讨债人的最终后果来看,确实造成了一人死亡、二人重伤、一人轻伤的重大损害结果。但不能因此就推断于欢捅刺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再次,加害行为往往缺乏自我约束,但是判决书称:“审理认为被告人于欢被围困后,在接待室较小范围内持尖刀对四被害人腹、背各捅刺一刀,并没有表现出对某一被害人连续捅刺致其死亡的行为,也没有对离其较远的对方其他人捅刺……”说明于欢的防卫行为还是有一定节制的。
最后,认定于欢的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证据不足。1.判决书在此关键认定中,有语焉不详之处。据判决书中被害人郭彦刚、严建军和程学贺三人陈述,于欢没有预先警告就直接捅刺他们三人,加害性质明显。这一证据与被告人于欢的供述有明显不符。于欢的供述意在说明其捅刺的行为完全是被动为之。而支持于欢说法的竟是讨债方的幺传行的证言证词。显然,在于欢持刀捅刺之前是否有被殴打的行为,以及于欢持刀后是否有警告言语这两个关键细节上,被害人陈述与被告人供述是有很大出入的。而判决书在罗列上述证人证言后,并未厘清上述的是非问题,仅以一句“上述证据已经开庭质证,本院予以认证”作结语,究竟哪一方哪一人哪一句言辞被认证或采纳,为什么被认证,法官自由心证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判决书没有明确写出。2.判决书对重要细节有缺漏。比如,于欢为何在讨债者百般凌辱其母时未持刀反抗,却在警察出警到达现场并即将离开之际亮出凶器?此种做法有悖常理,但是判决书不仅在“经本院查明”的内容之下没有提及,而且将警察的出警行为作为了于欢不具有“正当防卫意义上的不法侵害前提”的理由之一。
综上,首先于欢的行为不是加害行为;其次,由于判决书中关键细节缺失,导致无法准确判定其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排除制作者个人水平等主体因素外,笔者认为检析刑事裁判文书的格式与制作要求,可能会有更有意义的发现。
三、对刑事裁判文书在制作要求上的检析与设计
我国刑事裁判文书依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制作,在格式上由首部、事实、理由、判决结果和尾部五个部分组成。其中,事实是裁判的基础,理由是裁判的灵魂。不讲清楚事实、不对裁判理由进行充分的阐释和说明就径直作出裁决,无疑有司法专横之嫌。因此,在不断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背景之下,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细化裁判文书的说理过程和要求就成为必然趋势。
当下刑事裁判文书的事实部分主要包括三个内容,一是检察院的指控,二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供述和辩称,三是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尤其是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部分,对最终裁判结果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以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一审公诉案件使用普通程序)为例,现行通用文书格式要求,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部分,首先写明经庭审查明的事实;其次写明经举证、质证定案的证据及其来源;最后对控辩双方有异议的事实、证据进行分析、认证。[5]15理由部分的“核心内容是针对案情特点,运用法律规定、政策精神与犯罪构成理论,阐述公诉机关的指控是否成立,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犯的什么罪,依法应当如何处理,为判决结果打下基础。”[5]7
基于上述对于欢案的一审判决书的实证分析,笔者认为该判决书在事实部分的写作中存在下面两个问题:
(一)事实陈述模糊不清
对于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部分的写作,要求之一是对控辩双方有异议的事实、证据进行分析、认证,但没有要求对控辩某一方不一致的事实、证据进行分析、认证。比如,当被告方是共同犯罪,或被害人、证人为多人时,各人对同一事实的表述、同一证据的表现存在不一致时,判决书缺乏相应的评判内容。而这部分内容必须予以补充,因为它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以于欢案的一审判决书为例,该判决书在事实部分依照证据的种类,分门别类地进行了详细的列举。从形式看似乎证据厚实,但是仔细分析就发现存在不少模糊不清之处。比如,被害人郭彦刚、严建军、程学贺与证人幺传行同是讨债一方,利益比较趋同,但前者的陈述与后者的证言在关键情节上却存在不一致之处,如果不对它们进行分析、鉴别、厘定,不但不能与被告人于欢的供述及辩解进行清晰比对,进而无法有理有据地指出哪个证据更有证明力因而被认证,而且使得下文的理由部分的论述显得基础薄弱、底气不足、连贯性不强,因而影响正确的行为定性和量刑。因此,不是只有控辩双方有异议的事实、证据才有必要分析、认证。只要是对认定行为的性质、构成犯罪、影响量刑等有重要意义的事实、证据,都应当加以评判。
(二)事实部分的某些写作要求在实际制作中没有贯彻落实
对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部分,文书格式要求在写明经庭审查明的事实之后,必须写明经举证、质证定案的证据及其来源。但是这一要求在实际制作时没有得到严格的落实。以于欢案的判决书为例,法官在写完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之后,另起一段只罗列控辩双方的举证情况,但是缺乏质证定案的过程,没有对证据、事实进行评判、认证。文书结构呈现“证据罗列→抽象概括→定性定量”的特征,而且证据罗列部分占比较大。证据罗列并非不重要,但是不能以罗列证据替代对证据的分析、认证。从庞大的罗列证据到瘦小的“本院认为”部分的抽象概括,仿佛一个身形不均称的人站立在我们面前。它导致了判决书的理由部分的某些论断站不住脚,由此容易引发诉讼内外的争议,一定程度上可能损毁司法的权威。
解决上述两个问题的可行性方案是:在事实部分,建议细化“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的要求,增加对关键事实、证据的评判内容,其中包括对控辩双方有异议的事实、证据进行分析、认证。文书格式上具体表述如下:
“对……一事,鉴于XXX证据、XXX证据与XXX证据存在冲突(或不一致),本院评判如下:
……”
四、细化说理要求的现实路径探索
刑事裁判文书在载明案件事实、证据、法庭认证和裁判结果的同时,还直观反映了行为的性质认定和刑罚裁量是否严格遵循刑法、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等法律规范,体现了刑事司法活动的公正性。制作刑事裁判文书,只有把理说好才能避免错案的发生,得到民众认同。上述笔者提出的可行性方案的实质正是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细化说理要求。尽管这一精神已经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但将其真正贯彻落实却需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现行刑事裁判文书样式颁布于1999年,“当时对其修改的重点在于强化判决事实的认定和证据的分析、认证,增强判决的说理性。”[6]主要是基于当时的刑事裁判文书忽视事实认定的论证辩驳和 “对证据和事实上有疑难之处,应当重点说明”的要求。[7]但至2014年,还有学者指责当时大量判决书90%以上的内容是罗列证据,不到10%的部分是分析定案理由的结论。[8]证据的罗列固然重要,但是不能因此代替质证定案的过程,罗列出来的证据难免有内容冲突、不一致的地方,尤其涉及死刑、死缓、无期徒刑等重刑惩处的案件,法官最终经过自由心证采纳哪个证据、哪一方的证据,理应给被告人一个清楚的阐释和说明。2015年熟谙文书写作现状的司法实务者进一步从制作者角度指出,文书说理不明确与政治制度传统、公民社会养成、法治思维信仰等有关,但更接近现实的两个原因是:法官“累”和“怕”。[9]“累”使法官无暇说理,“怕”使法官不敢说理。2016年有学者更为理性地提出了围绕对质权保障来展开庭审程序及相关制度的改革的思路,其中明确建议:“被告人、被害人、证人在侦査机关所作的庭外陈述和笔录,原则上不具有证据能力”。[10]那么,沿着这个思路下去,笔者认为在刑事裁判文书的改革上,可以具体细化为:在事实部分,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及证据具有证据能力,但前提是必须书面写出分析、评判和最终的认证过程。当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证据存在矛盾的时候,或“案卷笔录与被告人当庭供述、证人当庭证言以及其他书面证据存在矛盾之时,法官不能在无明确理由并进行充分说理的情况下认可前者,相应的理由应当在裁判文书中明确记载。”[10]
在此研究过程中,不少学者都注意到了细化说理要求与繁简分流之关系。细化说理要求与繁简分流不是矛盾关系。繁简分流是根据程序的不同、案情的必要,该繁就繁,该简就简;细化说理要求的目的并不是要一味增加法官制作文书的负担,而是在公诉普通程序等“该繁”的程序和文书部分不厌其繁地分析、评判,最后予以认证,对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等该“简”的程序和文书部分则简洁陈述事实、概括列举证据,以作到繁简得当、合理配置司法资源。
[1]重磅!聊城“辱母杀人案”一审判决书全文披露[EB/OL].山东频道_凤凰网.[2017-03-26].http://sd.ifeng.com/a/20170326/5498177_0.shtml.
[2]搜狐网.[2017-04-07].http://mt.sohu.com/20170404/n486488074.shtml
[3]张明楷.刑法学[M].7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35
[4]赵秉志,刘志伟.正当防卫理论若干争议问题研究[J].法律科学,2001(2):66-79.
[5]吴在存,刘玉民,马军.最新法院诉讼文书格式样式[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3:15.
[6]李 敏.诉讼文书修改的目标:访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冉丹法官[J].中国审判,2015(19):40-42.
[7]龙宗智.刑事判决应加强判决理由[J].现代法学,1999(2):35-41.
[8]周光权.判决充分说理与刑事指导案例制度[J].法律适用,2014(6):2-9.
[9]庄绪龙.裁判文书“说理难”的现实语境与制度理性[J].法律适用,2015(11):83-92.
[10]胡 铭.审判中心、庭审实质化于刑事司法改革[J].法学家,2016(4):16-27.
PracticalWayofDetailingArgumentRequirementsinCriminalJudgmentManuscripts——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written judgment of the first trial of YU Huan case
SHEN Wei
(ShanxiPoliceCollege,Taiyuan030021,China)
Detailing argument requirements in criminal judgment manuscripts is one of the key tasks of current lawsuit system reform with trial as center. There are several problems in the making of facts part in our general-purpose criminal judgment manuscripts, which should be corrected. It is suggested to increase the key facts, judging contents of evidence and the process of questioning the evidence.
false case; judgment manuscripts; argument; with trial as center; Yu Huan
2017-04-11
申 巍(1973-),女,山西长治人,山西警察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刑法。
D926.13
A
1671-685X(2017)03-0026-05
(责任编辑:王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