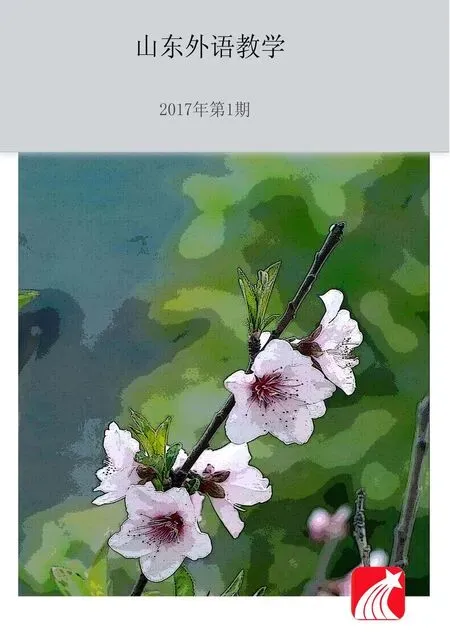后现代视域下的“死亡之诗”
——韦尔登·基斯诗歌中的末世情结
却俊, 彭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191)
后现代视域下的“死亡之诗”
——韦尔登·基斯诗歌中的末世情结
却俊, 彭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191)
韦尔登·基斯的诗歌带有浓郁的自传性色彩,糅合了一种独特的末世情结和幻灭心理。他采用镜头式的语言,深刻的反讽方式,以及现实与梦魇相结合的手法,将美国后现代社会中纷繁复杂的人物与事件粘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在整体的背后呈现出一个充满破坏性、摧毁性暴力的末日世界。基斯拒绝接受基督教的救赎观念,断言从末世到救赎的生命轮回的不可能性以及人无可逃遁的死亡结局。最终,末世阴霾下的诗人放弃了文化主体的自我救赎和更高意义上的社会救赎,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淖中自杀身亡。
韦尔登·基斯; 末世情结; 救赎;虚无主义; 自杀
1.0 引言
美国诗人韦尔登·基斯(Weldon Kees,1914—1955)的诗歌创作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其诗歌深受艾略特、奥登、叶芝等现代派诗人的影响,却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反映与揭示了后现代文明碎片化、视觉化、多元化和荒诞化的特质。基斯不以社会“改造者”或“改良者”自居,他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所谓的历史与真实,从社会边缘人的视角平缓、冷峻地描述空洞浮躁的美国都市生活,以荒诞不经的形式和反讽式的语言揭露这个可怖而悲剧的世界。基斯认为后现代文明已经陷入末世的崩倾,人类工业文明使得美国日益粗鄙化,机器的肆意扩张造就了一个可怕的文化荒漠,人性更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死气沉沉,柔弱无力、自我禁闭的美国人“如博物馆藏品般霉烂枯朽。”(Kees,1975:19)生存在巨大社会灾难中的个人无疑具有末世心理和悲剧色彩,这种末世情结构成了后现代美国诗歌的主基调,成为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大卫·伊格内托(David Ignatow)、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W.S.默温(William Stanley Merwin)等一批后现代诗人的终极关怀。他们的诗中充斥着毒品、暴力、自杀、战争、政治腐化、文化堕落、道德沦丧、生态破坏和被罪恶、失败、孤独湮灭的美国梦,并将美国社会岌岌可危的厄运衍化为普世性的末日悲剧。基斯死前不久曾在《新共和国周刊》(NewRepublic)上发表文章批判“我们当今社会欺诈、暴力和非理性的氛围,成千上万的人正在自杀——无论是真实性的还是象征性的”。(转引自Siedell,2003:168)最终,末世阴霾下的诗人放弃了文化主体的自我救赎和更高意义上的社会救赎,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淖中自杀身亡。
2.0 末世的阴影:末日世界的影像化呈现
著名诗人兼评论家肯尼斯·雷克思罗斯(Kenneth Rexroth)认为,“基斯生活在一个永久性的、无可救药的末日世界”。(转引自Buckley,2011:24)基斯的末世情结源自于他对战争和人性本身的反思、对美国工业化发展的洞察和对后现代社会文化价值衰萎的体悟。这一体悟使基斯致力于呈现一个“噩梦般的末日时代”。(Kees,1975:104)基斯采用了一种影视化的手法——镜头推进法来展现后现代文明的末世景况,诗中的镜头景别往往从狭小视像空间中的单个物质客体(包括人物、物品等)出发,逐渐延展至“塔楼”式的全景敞视下人类社会的悲剧视像和末世视像。如他的第一部诗集《最后一个人》(TheLastMan,1943)中的《派对》(TheParty)一诗,诗人开篇从派对宾客们凝视水晶球这样一个小场景切入:“淫荡的女主人,在厅内踏着碎步,将宾客们聚到水晶球周围。/真是激动人心的时刻;/独眼的勒费夫尔夫人屏息凝视;/一个友善的肚子摩擦着另一个人的背;/‘有意思’,只听一个胖家伙叹道。”(同上:20)这短短一节诗几乎包含了基斯诗歌所有的标志性元素,如对病态、畸形或不协调的人物形象的刻画(“淫荡的女主人”、“独眼的勒费夫尔夫人”、“胖家伙”)、暗示性描写以表现现代人的性压抑和性焦虑(“一个友善的肚子摩擦着另一个人的背”),以及以调侃的情趣写无趣之人和无聊之事的戏谑诗风(“真是激动人心的时刻”)。最后一节诗人从室内的狭窄视像迅速切换到死亡和战争的宏大视像:“我们的眼睛/盯着一架架飞机塞满鼓胀的地球,/蓝色的烟;血,被子弹撕裂的脸。/忽然,鼓声咚咚震响,一直传到我们这里:/死亡,还是死亡,还有一切的战争/正欲袭来。”(同上)诗人以科幻片式的描述呈现出战争中世界满目疮痍的末日景象,内部世界的享乐和外部世界的倾毁之间的强烈反差迫使读者从混混沌沌、声色犬马的迷幻氛围中抽离,进入宏阔浩荡的外部空间和野蛮骇人的死亡想象,在战争的宏大视像与末日劫音般的鼓声的强烈震撼中感受置身末日世界那种令人窒息的沉重。《春分》(Equinox)也是一首影像化风格的末世诗,全诗聚焦于一位女性人物,她是“人类最后的幸存者”(同上:146),诗人将一种荒谬感、恐怖感融汇入想象的末世景象中,镜头在物体之间快速切换,展现出末日背景下多幅连续、诡异的画面:“黑色鞋带下白秃秃的头骨闪着光,点着头,/一只瓜在冬日里成熟,/赤裸,泛黄,装饰在爪球式底脚凳上,/向北哀悼/冰冻的窗和海湾……/死鱼堆满数英里的海岸。/猩红的眼/从皮肉中猛地睁开,模糊地望向/湿答答的水龙头和最后几罐/在架子上腐烂的/意大利面和豆子。”(同上:146-147)对“头骨”、“瓜”、“死鱼”等物象的绘染传达的是诗人沉重、压抑、扭曲的末世心理和绝望情绪而非其实体意义,诗人虚构的末世景观通过电影画面式的呈现和“蒙太奇”的组接方法被赋予了可触可嗅的具象性,同时又蒙上了一层超现实主义的虚幻色彩。
3.0 美国梦的幻灭与文化的衰亡:后现代文明中的社会危机
随着工业技术的泛滥,美国后现代社会中的人建构起一种扭曲变异的、以物质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产生了精神上的空虚和百无聊赖。(Daniel,1976:131)而基斯与这种已趋于枯燥、无趣、异化的后现代生活之间出现了错位,他在《北美之旅》(TravelsinNorthAmerica)一诗中同样以影视化的手法再现了美国后现代文明的各种繁杂景象,揭露整个社会日益程式化、符号化、复制化和商品化的现象,以及这种现象导致的人的主体性的消解与美国梦的幻灭。《北美之旅》共110行,堪称一部“美国纪录片”,诗中基斯的足迹遍及全美,勾勒出后现代商业文明视域下美国城市发展的真实现状。《北美之旅》继承的是美国文学经久不衰的一个创作母题——公路文学(The Open Road Literature),“在路上”之于美国人有着异常丰富的内涵,它包括美国梦的追寻、实现和拥有。(廖永清,2008:62)惠特曼是美国公路文学的领路人,他的《草叶集》(LeavesofGrass,1892)中有许多讴歌上路旅行或将美国各地浪漫化、崇高化的例子。而在《北美之旅》中穿越美国的基斯一反惠特曼的昂扬与虔敬,他笔下的旅行充斥着失望、恐惧、烦闷和错失的机遇,诗人感受到的是这个国家令人震惊的荒瘠、生命力的衰减和无法解释的混乱与疯狂,赤裸裸地揭示了一代美国人逐梦之旅的破灭。诗的开篇就以几个特写与远景交互切换的镜头呈现出美国城市颓败的全貌:一个叫做“六翼天使”的汽车旅馆里“粘在墙上的肥硕蛾子飞出来迎接我们”(Kees,1975:114);圣巴巴拉的海岸边“一只古老的海鸥/在绵绵细雨中颤抖着飞落”(同上);著名饭店里的海鲜大餐散发着“一股经典的锡的气味”(同上);圣达菲的夜空“迷浊、老旧,奶色的薄雾中/本色尽失”。(同上:115)诗人镜头下的美国城镇不仅缺乏生机,而且具有一种可怕的同质性,毫无历史人文感与地域特色可言。惠特曼将上路旅行视作自由和追求美国梦的美好隐喻,而基斯的旅行却包含着实现美国梦的可能性的阙如,上路旅行根本实现不了美国梦,反而变成个人精神上的自我放逐,指向一种悲剧性的生命虚无体验——“你已经忘了为什么离开,为什么来这,/走了哪些路,/或期盼什么东西。”(同上:117)
基斯不仅与美国商业化和工业化体制之间存在着对立,他对美国社会衰落的另一方面——流行文化的泛化和经典文化的衰亡,同样进行了深刻的讽刺。美国发达的工业文明推动了流行文化的崛起,进而形成了以报刊、畅销书、无线电、电影、电视等工业技术构成的后现代文化体制。(刘怀光,2008:43)法兰克福学派把流行文化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关联看做是文化衰落的象征,这与基斯的观点不谋而合。他在《新闻工作者的难题》(Problems of A Journalist)一诗中便强调现代社会中经典文化的困境,揭露与讽刺了流行文化覆盖下现代人生活的低俗性。诗中迅速扩张的城市建设正在侵蚀宁静的乡村(“郊区的黄昏里/条条道路通往乡村如裂开的丝巾”(Kees,1975:126);D·H·劳伦斯诗歌中浴火重生的神鸟“凤凰”褪化成了一只聒噪的“鹅”(“然而火焰咆哮后熄灭,凤凰像鹅‘轧轧’乱叫”;两位杂志编辑反复对自己的同行说:“我要逃到一个地方,重读普鲁斯特”,却“在冬天来到小镇时,/在欧文广场咖啡店里,读着晚报。”(同上)作为社会上文化修养和知识阶层较高的杂志编辑甚至都懒于阅读经典名著,可见诗人所处社会日渐浅薄的文化氛围和文化空气,浮华喧嚣的文化工业时代里人早已迷失于流行文化铺天盖地的席卷之中,失去了内心的纯粹与高尚。在《图书馆的末日》(TheEndoftheLibrary)一诗中,诗人以极端荒诞的手法表现经典文化曾经的独尊和强势地位在现代文化中的日渐衰微。诗中“我”将英国小说家布尔沃-李顿(Robert Bulwer-Lytton)、司各特(Walter Scott)、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法国作家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诗人波多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希腊悲剧以及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集投入火炉以温暖冰冷的身躯。这些名家之作在各自所处文明时代的经典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文化权威的象征,而令人匪夷所思的“烧书”象征着经典文化遭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同时也反映出后现代文明中精英级读者的匮缺。《给歌剧的炸药》(DynamiteforOperas)一诗中,诗人对现代歌剧这一市民化的通俗艺术极为鄙夷,认为它无非是博人一笑的“小丑”,在审美深度和个性强度上与代表了贵族审美趋向的古典歌剧有着天壤之别。这些无意义的流行歌剧不仅不关注人的存在境遇,还试图掩饰后现代社会中真实而巨大的痛苦以及不可避免的死亡:“腐朽闹剧里的兼职演员/让人在更衣室发出怪笑的一刻,/很难触动死亡。/我从不在这里微笑。”(同上:62)当代美国思想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TheCulturalContradictionsofCapitalism,1976)一书中指出,“传统文化中心是人的生存意义问题,通过艺术表现人类生存困境中诸如悲剧与死亡等不可立喻性问题,而流行文化则偏离了这一中心,鼓励人们讲求物质享受与奢侈的享乐主义。”(Daniel,1976:205)基斯清醒地意识到流行文化麻醉了现代人感受生存痛苦的能力,他们变成时代迷惘气氛中了无方向的随波逐流者,在肤浅无聊的人生中没入精神之死,而诗人虽挣脱了后现代文化体制的羁留,却无力化解个人生存意义的危机,只能在被文明掩盖、压抑的虚无中安顿痛苦的灵魂:“别了,崇高的同事们!/我问候吹落街头的流行报纸,/我太了解它们了。/有种空虚比它们的空虚来得丰富。/太丰富了,我因此不喜欢。/脑袋在冰冷的风景里发紧。”(Kees,1975:62)
4.0 分裂的自我:末世中的个人精神危机
梦魇般的后现代文明使基斯坠入了无边的精神苦境,在对这个可怖而荒诞的末世景象事无巨细的描绘中,他的内心世界同样已畸变为地狱般的末日世界,敏感柔弱的心灵因不堪叠加的思想文化重负而产生自我身份的困惑,进而引发了严重的个人精神危机。基斯“深层的精神分裂感”在他成就最高的一组(共四首)以“罗宾逊”为主题的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罗宾逊”是诗的主人公,他是一个典型的西方现代人,外表光鲜、彬彬有礼,却深受噩梦、白日梦和潜意识中闪现的恐惧、迷惘等消极念头的折磨,他是飘荡在美国这片无上帝、无信仰的文明荒野上的现代版“鲁滨逊”。第一首诗《罗宾逊》(Robinson)开篇就以一种铅灰的冷色调渲染了主人公死气沉沉、令人窒息的生活环境:“罗宾逊走后听不到犬吠。/他的动作结束了。这是个灰暗的世界,/并非没有暴力,他在钢琴下一阵乱踢,/噩梦紧追不舍。”(Kees,1975:59)罗宾逊的一生只是“灰暗、暴力如噩梦般的世界里”的一个“动作”,足见其存在的卑微,显示出他是一个毫无作为、自我迷失、不合时宜的现代人,但他也有一种意欲突破束缚的冲动和愤懑(“他在钢琴下一阵乱踢”),让人想起了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的《梦歌》(TheDreamSongs,1969)中那个怒气冲冲而又敏感怯弱的主人公亨利。第二诗节中诗人以超现实主义的画面勾勒出罗宾逊荒诞化的人物轮廓:“贴在墙上的墨西哥镜子,/照不出任何东西。玻璃是黑的。/罗宾逊一人映出罗宾逊式的形象。”(同上)“泛黄的相片”、“空白的书”、“盒中的雪茄”、“无人接听的电话”等室内物品的特写镜头也透露着神秘与诡异,让这幅令人压抑的画面蒙上了一层更为沉重的死寂感。诗的最后一节里诗人将镜头由居室的内部空间转向外部世界,以极快的速度捕捉光影变化,凝固瞬间印象,描绘出一幅颇具印象派风格的末日图景:“外面,白色建筑在太阳中泛黄。/外面,鸟儿低旋不已。/树是真实的,不眠不休。”(同上)读者似乎能感到,基斯一直隐匿在罗宾逊的房间一隅,观察着这个末日世界,体会存在的孤独感、疏离感以及虚无感。第二首诗《罗宾逊的各方面》(AspectsofRobinson)中,罗宾逊游荡于灯红酒绿的纽约城中,他打牌、喝酒、买报、逛酒吧、嗑药、偷情,始终处于一种百无聊赖、如醉如狂的状态下。此诗的发展过程是罗宾逊逐渐从中心被抛到边缘最后自我解体的过程,随着主人公的名字被一次次唤起(他的名字共出现了16次),他内心的绝望感以及个人存在的非真实感也愈发强烈,直至跌入幻灭而悲痛的谷底,渴望在死亡中求得精神的解脱——“罗宾逊穿着花式泳裤,望向/飞溅的海浪……/他悲伤而平凡的心,如冬天里的一片孤叶”。(Daniel,1976:129)《罗宾逊在家》(RobinsonatHome)一诗记录了罗宾逊经历的一场荒唐的噩梦,他在梦中低喃:“我象征着这个疯人院里的某样东西——/这个城市——噩梦——黑色——”(Kees,1975:136),梦呓般的语言启示出对本质和存在的沉思,他痛苦地意识到世界是一个荒诞的、精神分裂的存在,而自己只是其中的一个疯子。结尾的几行诗透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寒意:“罗宾逊在惨怖的月光中醒来,/满身是汗”,他周围的世界“似乎是安静的”,却又传来了“伸出屋檐的电线的嗡嗡声”,“电线”无疑是人类工业文明的产物,基斯藉此影射无孔不入的工业文明对私人空间的侵扰与碾压。最后一首诗《关于罗宾逊》(RelatingtoRobinson)中基斯试图接近罗宾逊,与之产生精神和情感上的互动,全诗在一种亦真亦幻的情境中展开:“切尔西市某地,初夏;/暮色中我走向码头,/我似乎看到罗宾逊在前面。”(同上:148)在这种模糊不明的环境(“切尔西市某地”、“码头”)和象征性的时令(“初夏暮色中”)的铺陈中,人物也随之模糊化、碎片化,呈现出一种扭曲性与人格分裂的倾向。诗人声称自己在“雪茄广告牌下”(同上)看到了罗宾逊,但被笼罩在“薄暮中由红变绿的灯光里”(同上)的主人公仍然扑朔迷离、虚实难辨,这一系列模糊化的语词与形象指涉在读者脑中造成了一个根本性的犹疑。诗人看到罗宾逊“停下,凝视商店橱窗里/一座维纳斯石膏像……/望着向东的车流”,他忽然意识到此人并非罗宾逊:“但我知道,罗宾逊出城了”。(同上)既然明知罗宾逊早已出城,为何还将陌生人误认作罗宾逊?显然诗人的意识存在裂痕,出现了间歇性的失忆,他浸没于精神分裂式的思维中,感知的世界是零散、无序、错乱的,他眼里的世界正是以这样一种不连贯的、糅合了幻觉与现实的生活碎片穿缀而成的,这种精神分裂的视角为同代人呈现了一个分裂的矛盾重重的自我镜像,映现出诗人所处时代的特征与现代人心灵深处的混乱、困惑、疯狂和乖谬。
5.0 结语
基斯在诗歌中细致入微地描绘出后现代文明崩溃的悲惨景象,凸显出后现代社会末世的窒息性和毁灭性,末世镜像中苦难与死亡如梦魇般挥之不去。在永恒的精神苦役中,基斯以敏感的知觉省视个体存在境况,对现代人的生存遭遇、存在状态和精神家园展开了终极性的思考。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巴洛维(James Barlowe)指出,“基斯的诗歌展示了一位锲而不舍、兼容并包的艺术家对文明与人性的深刻剖析。”(Barlowe,1994-1995)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人身陷巨大的精神危机之中,而基斯以决绝的勇气承担起一位末世诗人的使命——他要书写这个分裂、罪恶、黑暗、野蛮的“荒原”社会,然而诗人身陷主体救赎的困境,内心无法承受的压迫性恐惧将他推向毁灭。(Reidel,2007:195)当我们跟随基斯的行踪穿梭于诗中的末日世界时,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矛盾、痛苦与悲抑,感受到诗人对生命情感无归宿的喟叹以及对世界未来命运的焦虑与关注,他的末世诗无疑包涵着深切的精神隐喻,激发出读者强烈的时代危机感和社会责任感。
[1] Barlowe, J. Weldon Kees: Loathed All Roses[J].NorthDakotaQuarterly, 1994-1995,(3):193-195.
[2] Buckley, C.AspectsofRobinson:HomagetoWeldonKees[M]. Omaha: The Backwaters Press, 2011.
[3] Daniel, A. B.TheCulturalContradictionsofCapitalism[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4] Kees, W.TheCollectedPoemsofWeldonKees[C]. D. Justice (ed.).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75.
[5] Reidel, J.VanishedAct:TheLifeandArtofWeldonKees[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7.
[6] Siedell, D. A.WeldonKeesandtheArtsatMidcentury[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3.
[7] 廖永清. 美国文学中的旅行与美国梦[J]. 外语教学, 2008,(4):62-65.
[8] 刘怀光. 流行文化及其对经典文化表达方式的颠覆[J]. 理论学刊, 2008,(6):43-49.
“Death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Modernism: The Doomsday Complex in the Poetry of Weldon Kees
QUE Jun, PENG Y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Writing with a strong autobiographical tone, Weldon Kees integrates a distinctive doomsday complex and disillusionment into his poetry. Via his unique “visual rhetoric”, a profound sense of irony, and the unparalleled technique of fusing reality with nightmare, he pieces together a miscellaneous collection of people and events in the post-modern American society into an organic whole, and reveals a violent doomed world looming behind. Kees rejects the Christian concept of redemption. Instead, he deems it impossible to go through a glorious transition from doomsday to salvation and prophesies the inevitable death of humanity. Having forsaken all hopes of self-salvation and salvation for the society, he soon precipitates into nihilism, and finally commits suicide.
Weldon Kees, doomsday complex, redemption, nihilism, suicide
10.16482/j.sdwy37-1026.2017-01-008
2016-03-3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幻觉型诗人研究”(项目批号:13BWW052)的成果之一。
却俊(1988-),男,江苏宜兴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诗歌。 彭予,男(1956-),河南信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大学英语》杂志副主编。研究方向:美国诗歌。
I106
A
1002-2643(2017)01-0063-05
——被大自然接管的精神病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