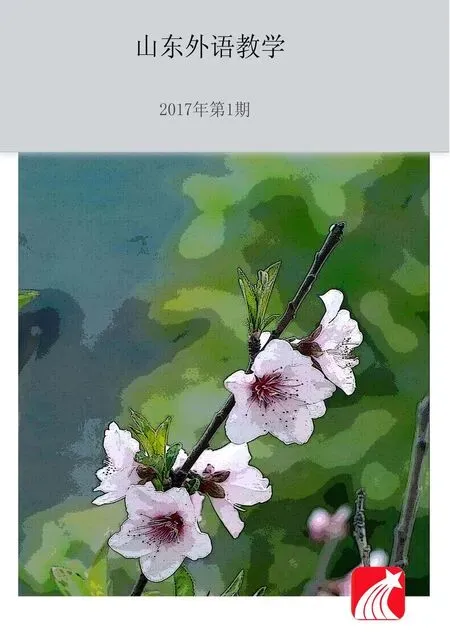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理论辨析
王影君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 上海 200093)
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理论辨析
王影君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 上海 200093)
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当今全球热点的批评话语之一,其批评理论呈现驳杂之态。它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生态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并在80年代形成批评话语潮流,90年代以来成为后女性主义批评的显要流派,融合了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的差异合理、他者主体话语权、多元中心主义等批评策略。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虽众声喧嚣,但总体以女性为批评视角,以解决生态危机为己任,以“爱”、“平等”和“生态正义”的主张为理论核心,对西方父权社会的菲勒斯中心主义展开文化批判。其实践目的在于号召全世界女性行动起来反对生态危机,维护女性与自然母亲的生存权力。
生态女性主义;菲勒斯中心主义;他者;爱;平等;生态正义
1.0 “生态女性主义”之诞生
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运动和女权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又是这一理念在批评实践中的发展和运用。1962年,美国作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发表,揭露了自然生态遭受人类经济活动惨烈迫害的灾难性后果,在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世界引起震动,人们纷纷投入到保护生态环境的实际行动中,西方生态主义运动大规模兴起。此时,正值欧美大陆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女性与自然在人类文化中共同的弱者地位,“女性历来比男性更接近自然,女性的心灵更适合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Merchant,1995:166),使女性主义者很快便捕捉到自身与生态主义在文化体位中的对等认同,找到了彼此理念上的结合点,即以女性自身的地位和遭遇,反思自然在人类历史中的境遇和遭遇,认为女性在人类社会中的遭遇正如自然母亲在人类社会中的遭遇一样,充满了父权文化的压迫和暴虐,于是女性主义者与自然生态自觉地结成一个弱者身份共同体联盟。
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Francoise d’Eaubonne)在“女性主义或死亡”(Le Feminisme ou la mort)一文中,最先使用了“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的概念,号召女性拯救地球母亲。正如批评家格里塔·伽德(Greta C Gaard)和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D Murphy)所阐述的那样:“生态女性主义是致力于社会变革的实践运动,兴起于女性维护自我,维护家庭,维护社区的斗争”(Gaard & Murphy, 1998:2),生态女性主义者在日常的生活中组织了许许多多的维护生态和维护女性利益的社会活动,因此生态女性主义具有现实的社会改革运动的特性。随后,女性主义者开始越来越多地以自然之母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生态批评上,呼吁人们关注环境污染、土壤退化、物种消失等生态问题,提倡女性以自身的立场和行动挽救日益恶化的地球生态环境。随之,在文学创作批评上,将女性主义思潮与生态运动的社会实践反应相结合,在70年代形成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2.0 后女性主义时代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随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兴起,它很快融入了后殖民女性主义、新历史女性主义等架构起的女性主义运动第三次浪潮的洪流,进入后女性主义①批评时代。后女性主义批评时代,以身份权力话语批评为其主要特色,以寻求他者话语权为其目标。其文化表征是关注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的他者的主体意识,努力替他者言说,以建立多元和谐的文化社会伦理秩序为己任,“自然”因其相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他者地位而成为后女性主义关注的伦理对象之一,自然界的生态问题亦成为后女性主义关注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
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结合绝非偶然。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二者都面临着祛除“他者”身份,向文化和社会进行中心位移,再塑主体自我的艰巨任务。为此,在文学批评中,她们直接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男性文化的中心意识形态——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即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文化形态,批判男性文化一元独霸的状态,强调多元文化,主张差异之合理,以此谋求后现代差异合理性基础上的他者主体话语权。对于菲勒斯中心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卡罗·毕歌伍德(Carol Bigwood)早在1993年的著作《地球缪斯:女性主义、自然和艺术》(EarthMuse:Feminism,NatureandArt)中, 就曾谈及过女性如何确证自身的问题。在谈及她的这本著作的创作意图时,卡罗明确指出“我将这本著作看作是一本谨慎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后现代的艺术哲学,我所专注的是西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形成,以及菲勒斯(phallus)是如何成为一种在场象征的(如表现着整体性、目的性、直线性和自我认同感),换而言之,就是男性身体的这一部分,是如何作为意识形态的象征物进入我们人类最重要的概念体系的。我试图追溯这种神秘勃起的开端,为的是瓦解和破坏专制关系,寻求开启新空间的道路,以期可以容纳差异的存在。然而,我实在无意于结果的诞生,以至于形成一种与其自身‘指向’相反的局面”。(Bigwood,1993:2)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对差异合理性的强调,以及一种只求批判时解构,不求批判后再进行同质建构的后现代思想。因为,为了实现女性“他者”身份的主体性转换,在传统女性主义那里,往往是一种男性一元中心主义的反向生成复制,即以女性中心主义代替男性中心主义。以一种中心主义代替另一种中心主义,即以一种不平等代替另一种不平等,显然会陷入一种男女两性会不断重复反向建构自身,本质上却一致的逻辑矛盾。
这种矛盾,同样蕴含着一种新的卡罗所谓的“整体性、目的性、直线性”的专制关系。因此,这种结果不断遭到来自于女性主义阵营内部的否定,后殖民女性主义者加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利落地将其批评为“倒本质主义”的策略。但是,她也只能是用解构主义方法将其不合理性进行解构,却找不到何去何从的现实出路。好在生态女性主义的加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实践机遇。显然,在后女性主义的阵营中,生态女性主义因兼具性别话语与生态话语的双重属性,裹夹着人际关系与自然关系,更具有兼容并包的张力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优势,尤其是其不计较结果而更重行动过程的进行性建构式的批评方式,使传统女性主义批评出现了战略转机,为她们冲出学院象牙塔提供了突围之路, 同时也是女性对男性社会文化认知的突围之路。
3.0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现实语境
建立在女性与自然相连接基础之上的生态女性主义,代表着女性主义理论的策略中心由两性关系批判,向更加广泛的多元社会现实关系批判的转向。进入21世纪,伴随着人类生态环境极度恶化的历史背景,生态女性主义成为后女性主义时代的生力军,虽然在理论建构方面它依然无法完全走出传统女性主义的困境,但是在批评方法和现实话语活力上确实可圈可点。在批评方法上,生态女性主义融和了后殖民和新历史主义等批评方法,极力揭示并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对自然他者的强权和压榨;在现实话语上,生态女性主义以生态的视角,女性主义者的身份,进行创作、批评和保护生态的各种文化政治活动。与整个生态运动和女性主义传统一样,文学批评成了生态女性主义运动不可缺少的思想阵地。
美国著名的生态主义文学批评家劳伦斯·布依尔(Lawrence Buell)在论及整个生态环境批评的时候指出:“环境批评是付诸于行动的事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并且“环境问题将成为今后文学创作的永久话语”。②(Buell,2005:vii)不难由此可以推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亦前途漫漫。在文学创作中,女性因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具有对自然进行书写的优势,自然写作成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阵地,对自然进行书写的最成功的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卡森。布依尔认为卡森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引起轰动,并流芳百世,和别的同类作品相比,她的优势就是除了书写自然的毁坏,更书写了自然的美丽,“要不是大力颂扬了自然的美丽,她的声音同样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Buell,2005:ix)正是自然的美丽激起了人们对现实生态危机的关爱。
事实上,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确实以其对自然的礼赞和关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效应,将生态文学批评的实践性品格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于,不但整个生态运动是以女性卡森的文学作品掀起,更以此后诸多的生态女性主义作家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将生态运动的迫切性与深远意义不断具象化,极好地推动了人们对生态环境与女性生存样态的双重关注,并促使现实中出现了如雨后春笋般的生态女性主义组织,在众多妇女的参与下开展着如火如荼的生态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尤其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担当了最理想的生态女性主义理念论辩与展示的舞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开始形成自己的批评理论的。
4.0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构成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如整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样,依然缺少严格完整的理论体系,时至今日它仍然处于开放着的建构中,但不同的是其具有其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缺少的,令人信服的属于当下社会的广泛而迫切的实践性。可以肯定地确认:实践性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最重要品格。这一具有无限优势的实践性品格来自于其“女性”与“生态”兼具的双重身分构成。事实上,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融入了女性视域下的生态整体意识,建立起了自己的生态伦理观,即关注生态正义,主张人际平等,注重代际公正等,寻求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整体和谐。这些都十分符合时代的需要,从而使它的现实实践品格格外突出。无论是现实运动③还是批评创作,“爱”、“正义”和“平等”都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追求的伦理核心。
4.1 理论基石自然之“爱”
自然之“爱”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石。“爱”(love)是西方文化中较为常见的理念,上帝曾告诫世人彼此关爱,亦包括“爱你的敌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也曾主张自由平等理念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博爱”。但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爱”在两个方面不同于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爱”。首先,出发点不同。传统文化意义上的“爱”是以宗教伦理和科学理性为基础,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和关系平衡为中心的。而生态女性主义所强调的“爱”则充满了感性体验,诉求的是万物达于和谐共生的自然状态。再有,性质不同。传统宗教意义上的“爱”是人之爱,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强调更为广泛的他者之爱——爱自然。对大自然的“爱”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石,从表面上看这块基石似乎是对西方关爱文化的一脉相承,但因其由传统的人之爱向非人的自然之爱的转向,实际上却是另起山头。所以,它既是伦理向度发生的新转向,又颠覆了西方文化传统的认识论根基。
我们知道,自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起,就开始高呼“人是万物的尺度”④,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的赞叹“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⑤,他们无一不认为:人是超越一切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衡量一切的尺度。自然界在这样一脉相承的横贯几千年人类文明史的认识论基础上,彻底沦落为人的附属物,遭受到肆无忌惮的索取与破坏。与这种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霸权意识上的传统认知理念截然不同,生态女性主义另辟道路,主张以对自然的“爱”为基准的尺度取代以人为中心的尺度,从对他者自然的“爱”出发,而不是从人的自我中心出发,来量度评判人类的一切活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将凝聚着感性、心性和情感意识的“爱”推致至高的位置,使“爱”成为人类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属地,是既具有情感投入又具有实践品格的“关爱”(love and care),这样的主张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上均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
在自然之“爱”的关注下,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土地、海洋、森林、沼泽、动植物以及女性自身等都呈现出了新的面貌,通常可以寻找到女性所特有的对自然母亲的爱心境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深层次的爱心依赖为纽带。蕾切尔·卡森在这方面独具贡献,她不但较早地在作品中展现了这种爱而且给出了明确阐述。她认为热爱我们生存的世界是科学发展必须具备的前提。尽管人们对自然界缺乏足够了解,但首先必须热爱它。(Diamond and Orenstein,1990:iii)在大海系列作品中,卡森形象地告诫人们,正是因为缺少爱,人类曾经鸟语花香的家园才变成了寂静的荒野。
尽管在此前,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olf),薇拉·凯瑟(Willa Cather)等生态女性主义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过对自然的热爱。但是,卡森的著作则被视为具有掀起革命式认知风暴的力作。因为,她明确地以自然之“爱”为尺度,不但改写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改写了自然界的他者地位;也改变了女性对自我的认知,改写了女性的他者地位。在人类的文明史上,男人一直被看作理性的、逻辑的、科学的物种,即所谓的“男性气质”;而女人则被看作感性的、混乱的、性情的,即所谓的“女性气质”。在卡森之前,女性主义者一直焦灼于对“女性气质”的批判。自女性主义运动的前驱起,就力求建立一种世界大同式的人类气质。早在18世纪末,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就在其著作中大力论述了女性具有与男性同样的美德,包括逻辑和理性,并呼吁给予占人类一半性别的女性以平等权,她说“我们的第一个崇高目标就是寻求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性格。”(Wollstonecraft,1996:5)然而,女性主义运动的历史早已证明,追求一种全人类大同的性格,无视性别的个性特征,不过是乌托邦色彩浓郁的美好想象。因为,若这一崇高目标果真实现,不可忽视的一个后果就是:“女性”相对于男性的独特性将被无意放逐或有意遮蔽,从而使女性自身存在的合法性面临挑战,那样女性将失去更多。
尽管如此,女性主义者在很长时期内无法走出追求大同性格的梦想。女性主义作家不断塑造出以男性气质的“理性”特征武装起来的女性形象,女性主义批评家也不失时机地对这些女性形象给予格外的关注和赞扬。女性主动亲近理性,疏离感性,成为女性积极塑造自我的标志,在这一过程中女性自我的天然感性被屈辱地流放,女性的情感自由也被理性幽禁和牵绊。卡森的批评策略跨越了这样的拘囿,她特别看重女性的感性能力,并给予充分赞扬和肯定,且上升到可以救世的高度。面对生态环境危机,她勇敢地告诫人们:首要的不是去求助科学理性,而是去热爱我们的世界,唯有充满爱心的对自然的关爱才能使人类获得永久的生存。
卡森对感性之“爱”的呼唤,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凯伦·沃伦(Karren J Warren)、罗斯玛丽·卢瑟(Rosemary Luther)、帕特里克·墨菲,马蒂·基尔(Marti Kheel)等人的著作中,不断得到回应,而且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清晰。最终对自然爱心的提倡,成为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石,其最深远的意义在于,它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向。因为有了对自然界的关爱,生态世界才成为彼此息息相关的有机体,才有了生命的尊严和地位。那么,自然界就不再是人的对立物、附属物或征服品。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不再是征服与被征服,利用与被利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了。爱心是广义的自然之爱,更具体到爱森林,爱草原,爱河流,爱土地,爱动物,直到爱任何弱小生命的行动之爱,亦成为一种有着女性主义生态文化信仰的精神之爱。在某种程度上,生态女性主义呼唤着自然母神的回归,使他们自身成为自然母亲的缩影和代言人,成为生态整体系统的一部分。生态女性主义者以爱心,修复着男性社会给人类文明带来的生存危机。
科学理性不再是圭臬,保护生态,关爱自然万物的爱心,才是人类自我繁衍生存的法宝。以爱心为纽带,把自然和人类文化重新相连。女性的超强感性与爱心,就这样经历了从19世纪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到20世纪的蕾切尔·卡森的海洋系列著作的不懈努力,终于上升到能够解决人类现实危机的高度。女性由此光明正大地确证自身的情感品性,男性社会千百年来因此对女性所进行的排挤和抨击,从此不再具有合法性,女性再也不必为此而极力改变自我的本性。由此出发,女性对自我的认知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历史进入到卡森时代,女性能够心平气和地正视两性差异了。正是对差异的认识,女性才真正开始有了自我认知,女性的主体意识才越发明确起来了,以男人为镜的时代结束了。
女性从此拥有了在自然界中的责任,也就拥有了生态系统中的一席位置。此后的生态主义运动向世人展现出了女性的这一自我主体意识的变化。诸多女性们在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充分地发扬着他们对世界,对子孙后代的真情爱心,挽救着人类行将毁灭的家园,并且成效卓著。总之,在卡森如何处理文明危机的问题上,女性的感性之“爱”成为策略首选,并被强烈召唤。“爱”,不但要成为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还要成为理解自然的前导。人类对自然母亲缺少“爱”的科学开发,结果只有毁灭性的灾难。此后,在苏珊·格里芬的《女性与自然》(WomanandNature)、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羚羊与秧鸡》(OryxandCrake)、凯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的《自然之死》(TheDeathofNature)中,同样清楚地看到了这种思想连续不断的文学链条。
4.2 理论核心:生态正义
“生态正义”(ecological justice)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核心。“生态正义”的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美国的环保运动中诞生的,最初是指“环境正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充分接受并广泛使用了“生态正义”的概念,为整个女性主义批评获得了社会意义上的法理支持。由此,女性主义由喃喃自语的性别权力欲求壮大为以人类生存为己任的生态关系批判。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在强调其崇高意义的同时,认为对“环境正义”的理解要具体到日常人生。
格里塔·伽德(Greta Garrd)指出:“环境正义”并不仅仅存在于蛮荒的野外,同样深入到我们生活、工作和娱乐的每个地方。这样的理解,使得“正义”的理念与现实行动能力亲密相连,吸引着大众的参与。最初的“环境正义”是指人们不分种族、肤色、国籍、贫富共同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力,并同时承担制定、遵守和执行有关环境的法律、规章和制度的义务。当人人都能够远离有害环境,享受着健康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环境的时候,环境正义就实现了。⑥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重塑人与自然之伦理关系的深度生态主义的出现,“环境正义”扩展为“生态正义”,主张生态圈中的各个物种不分高低贵贱,都有繁衍生息的权利,且彼此息息相关。人类不能因为自私自利而剥夺其他物种的生存权,从而影响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并最终影响到人类自身的生存。
生态女性主义者分别在各个时期加入了性别因素,认为女性与男性一样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力和维护环境的义务。并且,她们提出因为家务大多是通过女性打理的,女性通过日常的衣食起居,对生态环境变化更加敏感,所以女性更具有爱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健康的前沿意识。而且,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是由男性社会无休止的战争和经济活动造成的,所以在生态的问题上男性中心主义仍然是罪魁祸首。在对男性中心主义的生态批判中,女性被赋予维护生态的天然使命。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因为自身承担人类繁衍的角色,对自然世界的繁衍生息更具长远目光,因此苏珊·格里芬说道:“女性距离大地更近”,女性与大地同为卑贱的他者,因此更能体贴地球母亲的伤痛,理所当然地成为维护生态环境正义的最主要的天然合法力量。(Griffin,1978:4,7)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站在这样的觉悟高度上,对人类的战争和经济活动进行批判。女性的这些有关自然生态正义的主张,除了性别身份权力话语,更具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话语意识。至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全面打通了性别话语与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通道,祛除了仅仅为女性自身谋利益的狭隘色彩,也进一步消除了与男性的尖锐对立。在对生态环境和谐的强调中,自然也使男女两性关系走向和谐,并将两性关系融汇到更为广阔的自然伦理秩序体系。女性主义的话语空间一下子就敞开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就更具有了建设性的意义。“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的结合是文学研究‘向外转’的过程中找寻到的一条独特而明媚的道路。”(韦清琦,2006:19)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也越来越向人类社会整个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敞开。
随着生态伦理的深入人心,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进入21世纪,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地域上从西方蔓延到东方,与东方古老的自然思想结合并反过来影响着西方,且在特征上出现了与政治经济话语批判相结合的新趋势,如在生态正义的基础上,印度著名的生态女性主义大家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进一步提出“大地民主”(Earth Democracy)的主张,明确地将民主的正义理念延伸给大地,提出:“并非大地属于人而是人属于大地”(Shiva,2005:4),且大地拥有政治上的民主话语权,大地具有自身的存在方式,不能全凭人说了算;大地为人类提供食物,人类有责维护大地的平等权益,人与大地是合作关系,这就是自然伦理的正义所在。在人类日益蔓延的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增长不应挤压大地天然的民主权力,不能无视大地的生存权,让一个个小农场消亡,让一块块土地被污染。大地上的万物都享有自由安全的权力,包括食物链中的食物,都有平等生存的自由。大地民主的权力应该在正义、可持续发展和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得到保障。(Shiva,2007:37)席瓦的贡献在于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具有了政治经济批判的属性,这表征着生态女性主义已经成为目前最具活力的文学批评话语之一。
4.3 目标指向:平等
“平等”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目标指向。生态女性主义继承了传统女性主义对于男性一元中心主义的批判,除了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性别角度的批评,继续强调女性被男性社会压迫剥削的历史,更立足于整个生态视域,发掘出更多的种族、物种、自然资源等方方面面的不平等。具体来讲,除了女性,她们认为包括动物、植物、矿物、大气、水土等各个自然领域里,各种有机生命和无机物质都受到了这种一元中心主义的压迫盘剥。
历史上,无论是宗教教义,还是世俗法则,都把这些物种置于被人类统治的地位,由此产生了一种短视的人类功利主义。人们功利地认为,唯有人的生存才是最重要的,唯有人的利益才是最高的,因为人是世界的核心和尺度。基督教认为,上帝造万物是为了人类生存服务的;世俗法律认为,人有能力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为人类服务。但是,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万物都是由上帝创造的,包括人。所有的种属都是出于造物主的意愿,是彼此平等的,应该获得彼此的尊敬,正像一母所生的子女一样,本无高低贵贱的区分。万物因为平等而应该互相尊敬,因为尊敬而彼此和谐共存。显然,这是一种目的在于改变不公平秩序的论说。人类历史一直奉行的一元中心化的差序秩序,受到生态女性主义的强力批判。她们指出,男性不是女性的中心,人类也不是宇宙万物的中心。这与各种后现代理论中的多元思想是一致的,不同的是生态女性主义者明确提出了建立物属平等世界的诉求。
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通过对文学作品与作家的评判与分析,推进着生态女性主义者的主张,如苏珊·格里芬、玛丽·卢瑟等人的文学批评,无疑正在清醒地告诫人们:生态危机,导致了人类的文明危机,以一元为中心的差序等级世界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刻了,万物平等的多元等序世界才是解决文明危机的最好出路。虽然目前这种努力更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文学上的乌托邦理想,但是它所带来的冲击力无疑必将影响深远。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其更多地是通过反乌托邦文学(dystopia literature)来表现的。诸多的反乌托邦作品,如《羚羊与秧鸡》、《洪水之年》(TheYearoftheFlood)、《人之子》(TheChildrenofMan)等通过塑造一系列世界末日式的文学景观来警醒世人,如果继续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平等的生存秩序,那么最后人类必然在破坏生态之后,走向自我毁灭。如今生态危机更加严重恶化,气候变暖、土壤板结、河流断流、地震海啸频繁……人们心中形成一种末日将至的世纪恐慌,于是反乌托邦作品的创作越来越多,且催生了一些风靡全球的电影作品,像《后天》、《阿凡达》、《金刚》等。建立一种平等共存的新生态秩序,已经不仅仅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诉求,其正在成为整个人类生态文学的共识。
5.0 结论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当下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批评流派之一,几乎集中了女性批评的所有行动话语流派。他们主张以自然之“爱”、万物“平等”和生态“正义”为旗帜,组织着各种各样的女性生态保护运动,如动物保护生态女性运动、素食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绿色生态和平运动等,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们不但从事着理论批评、文学创作、媒体演讲,还不断走向街头,引领人们从我做起,从关爱身边的事物做起,呼唤人们热爱地球母亲、保护环境健康、赋予动物权力等等,承担起女性对生态保护的责任。所有这些都使得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具有极其强劲的现实实践品格,并以此引起世人越来越多的关注。
注释:
① 本文没有遵循postfeminism当下较多的译法,即后女权主义,而称为后女性主义。关于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孙绍先曾在《外国文学》上论述到:“女性主义涵盖并超越了两性的权力关系, ……女性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产物,是一种男女平等的信念和意识形态”,因为生态女性主义恰恰属于“(女性主义)旨在反对包括性别歧视在内的一切形式的不平等”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范畴,本文据此采用了后女性主义的译法。(孙绍先,2004:56)
② 布依尔喜用“环境”(environment),指代通常概念上的生态。
③ 从美国的妇女环境发展组织,妇女地球之声,女性主义动物权力组织、波士顿生态女性主义行动组织,到英国妇女环境网等许许多多的西方社群机构里,生态女性主义者关爱着整个生态伦理的健康发展。整个生态主义运动,也因为女性主义的加入变得更加实际和令人瞩目,展现出了极强的行动能力。
④ 参阅http://gretagaard.efoliomn.com[DB/OL].
⑤ 参阅http://www.epa.gov/environmentaljustice[DB/OL].
⑥ Environmental justice is the fair treatment and meaningful involvement of all people regardless of race, color, national origin, or income, with respect to the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environmental laws,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参见 https://www.epa.gov/environmentaljustice. [2016-01-11]
[1] Bigwood, C.EarthMuse:Feminism,NatureandArt[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 Buell, L.TheFutureofEnvironmentalCriticism:EnvironmentalCriticismandLiteraryImagination[M].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3] Diamond, I. & G. F. Orenstein.ReweavingTheWorld:TheEmergenceofEcofeminism[M]. San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1990.
[4] Gaard, G. C. & P. D. Murphy.EcofeministLiteraryCriticism:Theory,Interpretation,Pedagogy[M].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5] Griffin, S.WomanandNature[M].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8.
[6] Merchant, C.Earthcare:WomenandtheEnvironment[M].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7] Shiva, V.EarthDemocracy[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South End Press, 2005.
[8] Shiva, V.ManifestosontheFutureofFood&Seed[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South End Press, 2007.
[9] Wollstonecraft, M.AVindicationoftheRightsofWoman(2nd edition)[M].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96.
[10] 孙绍先. 女权主义[J]. 外国文学,2004,(5):48-56.
[11] 韦清琦.中国视角下的生态女性主义[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19-23.
On the Western 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WANG Ying-jun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s one of the critical discourses on power, the western 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is quite prominent at present in the world with its various faces. It buds up in the 1960s and blooms into tide in 1980s. It derives some criticism strategies from the postcolonialism and newhistoricism on “differences reasonable”, “other”, “subjective discourse” and “multi-centralism”. As a result, it becomes a brilliant big branch of the postfeminism named ecofeminism. At the perspectives of feminists, it also devotes to criticiz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patriarchal phallocentrism, but it advocates its core notions of “care”, “equality” and “ecojustice”. Ecofeminists call all the females worldwide up to fight against the ecocrisis to protect the living rights of women and Nature Mother.
ecofeminism; phallocentrism; other; care; equality; ecojustice
10.16482/j.sdwy37-1026.2017-01-009
2016-06-10
王影君(1973-),女,吉林省四平人,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后,上海理工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西方文论及中西文化比较。
I0-03
A
1002-2643(2017)01-006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