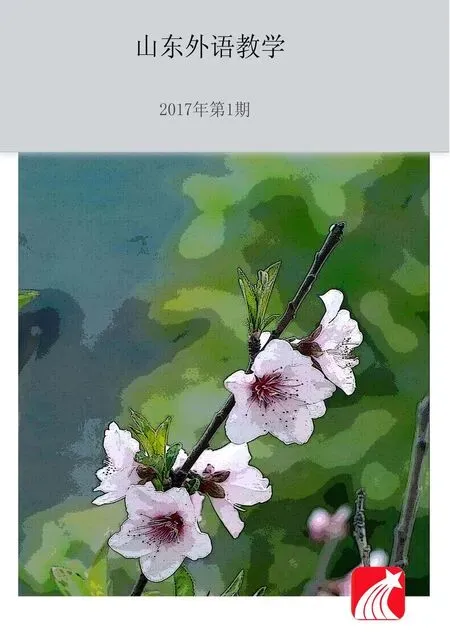语义的相对性和批评的反思性①
辛斌
(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语义的相对性和批评的反思性①
辛斌
(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后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关键的主题和概念,而葛兰姆西、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巴特等的各种后现代主义理论对霸权斗争、全球化、知识和权力、语言和权力、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制度和生活世界的分离、制度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以及各种对这种殖民的抵制与反抗等的阐释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一系列的理论和研究课题。批评话语分析产生于后现代的语境下,是对“后现代性”批评研究的一种贡献,其重点关注的是语言在后现代社会变化中的作用。本文旨在表明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批评话语分析的相对语义观和动态辩证的方法论。
后现代;批评话语分析;语义的相对性;批评的反思性
后现代转向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在知识领域摒弃了确定性。在启蒙主义思想中,我们对科学和知识的理解依赖于一个假定的真理和其表达媒介之间的对立,即客观真理独立存在于任何可能用以表达它的符号之外,理智的权威高于它自己的外在表达体系,“修辞的”与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真实相分离。但是,后现代主义者合并了真理和表述、信念和认识、理性和语言、表象和实在,以及意义和隐喻的二分体系,用一个修辞性的科学概念推翻了现代主义语言理论的权威:“知识被重新定位在符号建构的过程中,而不再被认为是由符号辅助传达的东西。关于社会实在的知识不仅仅被看成是客观的产物,而且也被看成是具有内在说服力的符号过程。”(布朗,2001:313-314)
1.0 语义的相对性
在后现代以前的三个多世纪中,“相对主义”(relativism)一直为欧洲哲学所深恶痛绝,任何人只要被怀疑没有与相对主义划清界限,就要被迫作出解释与辩护。然而,当人类迈入后现代社会时形势发生了翻转:“追求普遍标准的人们被要求去证明相对主义的罪恶本性究竟何在;正是这些人眼下不得已要去证明他们仇恨相对主义的行为为什么是正当的。” (鲍曼,2001:265)布朗(2001:318)指出,不同的民族建立起了全套的范畴体系,通过这些范畴现实的一些方面被固定、聚焦或禁止。这些方面被置于人们意识的前景,成为说话或知觉的经验,其背景是缄默无言的存在:“这个修辞性地建构的叙事整体为在特定符号背景或生活世界中的人们提供了认同的模型。”布朗的这一观点与早于他近半个世纪的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如出一辙,只不过沃尔夫强调的是语言在建立这些不同范畴体系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我们都按自己本族语所规定的框架去解剖大自然。我们在自然现象中分辨出来的范畴和种类,并不是因为它们用眼睛瞪着每一个观察者,才被发现在那里。恰恰相反,展示给我们的客观世界是个万花筒,是变化无穷的印象,必须由我们的大脑去组织这些印象,主要是用大脑中的语言系统去组织。”(Whorf,1956/2009:220)这就是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原则”(principle of linguistic relativity):“我们这样就知道了一条新的相对性原则,即并非所有的观察者都会由同样的确凿证据获得相同的关于宇宙的图画,除非他们的语言背景相似或者具有某种可比性。”(同上)经由语言建立起来的这些范畴体系不仅左右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与感知,它们也影响人们的思维(Whorf,1964:135)。
后现代主义的语义相对性思想并不局限于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层面,他们更关注同一种语言中具体文本的语义相对性。索绪尔坚持将差异局限在语言系统之内,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着一对一的关系,能指再现所指。德里达则认为语言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参照系统,各种因素在其中相互作用和变化,所有因素都互为“踪迹”(trace);各种在场和非在场的因素相互唤起、暗示、激发、延异和替补,生生不息,永无止境。德里达因此否定文本意义的确定性,主张文本意义的不自足性、相对性和多样性。以德里达、福柯、巴特等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关于文本意义的相对性的核心思想是:意义不是独立存在于文本中,而是在将经验转换为文本的过程中产生,当下文本与其他文本和语境处于对话的关系中(Todorov,1984:48);文本是一个互文网络,“某种接合点,在此其他文本、规范和价值相遇并相互作用。”(Iser,1987:219)因此,文本不再具有一个确定的意义,而是充满了许多意义和声音。
Halliday & Matthiessen(1999/2008)提到了关于语法和语义研究的两种观点,一是“本质主义”(essentialist)或者“符合论”(correspodence)的观点,二是“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的观点。前者认为意义先在于形式,形式编码意义,“语言或语法服务于一个已经存在的经验模式,一个事先已经被识解了的‘真实世界’”(同上);后者则认为我们借助语法本身来识解经验,语法为我们建构现实世界中的事件和物体对象:“现实是不可知的,我们所知道的只有我们对世界的识解,即意义。意义并非先在于实现它们的词语,它们形成于我们的意识与其环境之间的碰撞。”(同上)Halliday & Matthiessen(1999/2008)更倾向于建构主义的观点。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批评话语分析持建构主义的观点,认为任何语篇都以不同的方式解读,一个语篇并没有唯一正确的意义,批评话语分析的任务之一便是分析对语篇的各种可能的理解。批评话语分析对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关系的任意说做出了一定的修正,认为使用中的语言形式和其内容之间的关系不完全是任意的,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有其社会成因(Fairclough,1992:75)。语篇中出现的语言结构和过程是说话者从整个语言体系中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语境,说话者的立场观点和交际意图。某一结构孤立来看或许并不具有任何固定的社会意义,然而一旦用于特定的语境中,与其它结构相联系,它便可能产生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语篇的各个层次和各种结构都可能具有意识形态意义(见van Dijk,1995)。
2.0 批评的反思性
在后现代社会,“反思”(reflexivity)日益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关于实践的知识日益成为参与实践的重要一部分:“社会学……处理预先被解读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行为主体发展的意义实际上进入了那个世界的建构或生产”(Giddens,1993:170)。反思还有另外两个特征。首先,反思涉入了社会斗争。反思性应用的实践知识是有立场的知识,这些知识产生于实践内部或外部的特定立场,它们既是斗争的资源又是斗争的赌注。其次,实践的反思性意味着所有实践活动都有话语的一面,这不仅是因为所有的实践活动都或多或少地涉及语言的使用,也因为对实践的话语建构本身就是实践的一部分,而后者正是反思的真正意义所在。
启蒙主义者认为,调查者只有在情感、认知和道德上都变成一块白板,才能消除观察者的偏见。但伽达默尔认为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传统之中,传统是我们的一部分,由于时间和空间与记忆的相互作用,我们总是对存在的传统(历史性)产生着偏见,偏见构成了我们全部的体验。理解活动其实就是把自身置于传统的进程中并使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因此理解不仅以偏见为基础,它还会不断产生新的偏见。与伽达默尔一样,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真理、知识和意义都是相对的、不固定的、非最终的,它们是在各种我们身处其中并与之相适应的环境中不断被创造的:“离开了文化、传统、语言游戏等情境,任何知识都是不可评估的。……不存在任何一种可以‘在语境之外’自行证明其存在合法性的有效性标准。”(鲍曼,2001:262-263)“观念只有在它们帮助我们与我们经验的其他部分建立起满意的关系时才是正确的。”(James,1947:58)因此,社会批评家很少能成为超然的观察者,他们“根本就找不到一个阿基米德支点来使自己脱离社会关系和人类知识之间的相互限定。文化和它们‘已定位的主体’都带着权力,而权力反过来也是由文化形式定形的。”(罗萨尔多,2001:232)那么,社会批评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又来自何处?罗萨尔多(2001)认为我们应该采取一种与启蒙模型,即客观地分析社会现实的超然的观察者模型,相决裂的立场,而偏向于把社会知识视为与多种立场和视角相关的东西,看成是社会分析家与社会的内在联系,看成是利益和价值在产生知识中的作用,看成是知识和权力交织在一起的产物。罗萨尔多赞成基于具体的地方社团和传统的多元化的语言批评,并建议社会批评家们在选取他们的道德标准和视野时应该依靠所属的文化传统和社团:“领福利救济的母亲和警察局长对于国家权力的认识和感觉一定是不同的。”(同上:233)
Thompson(1984:130)指出,实践依赖于反思性的自我建构来维持支配关系,由于反思性的自我建构功能,我们将其称为意识形态。各种意识形态就是出于特定视角或立场的实践建构,因而是片面的,它们以符合支配者利益和目标的方式调停或消除实践中的矛盾、困境和对抗。现代的意识形态概念与现代社会的各种实践尤其是话语实践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一种社会实践的话语往往会“殖民”(colonize)或者“挪用”(appropriate)另一种。因此,意识形态就是攸关支配与控制的社会实践建构,这种建构取决于某一实践和其他实践之间具体的话语关系。例如当代教育及其管理的意识形态是参照其他相关实践,尤其是经济实践话语而建构的(Fairclough,1992,1995a)。另外,理论研究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实践,不可避免地与其他社会实践,例如政治、经济、文化实践形成关系网络,这种关系决定着其内部结构和意识形态效果。因此,理论实践者理应反思其理论实践的社会立场和可能导致的后果,尤其是其理论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和社会斗争是如何交叉又是如何由它们决定的。Habermas(1972)以“知识兴趣”(knowledge interests)来解释理论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之间的联系,指出批评社会科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对从僵化的意识形态依赖中获得解放的兴趣。
批评话语分析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分析和解释语言/话语、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关系。批评话语分析者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语言不单纯反映社会,它直接参与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的构成。因此他们力图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从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包括意识形态对语篇生成过程的影响,语篇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以及两者是如何源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又是如何为之服务的。就像其他批评社会科学一样,批评话语分析需要就自己的立场观点和一切与此相关的东西进行反思和自我批评:它如何进行研究,如何看待和展望自己的研究目的和结果,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是何种关系,甚至写的是什么书什么论文。批评话语分析从不隐瞒自己的立场和倾向性:“批评话语分析是对做学问的一种批评视角:因此它是‘持有态度’的话语分析。”(van Dijk,2001:96)批评话语分析总是站在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或被压迫者的立场上,反对和抵制滥用话语来合法化对权力的滥用。批评话语分析不像其它学问,它“并不否认,而是明确地界定和维护自己的社会政治立场。就是说,批评话语分析是带有偏见的并以此而自豪。”(同上)
鲍曼(2001)认为在后现代的条件下社会分析家应从“立法”的角色转向“解释”(interpretive) 的角色;他们应该成为不同社会阶层的调解人、外来文化的解释者以及特定道德观的倡导者。他把后现代的社会分析看成是一种解释学研究。批评话语分析与其他批评社会科学一样,其基本动机是帮助人们认识现状,认识它如何产生和将走向何方,以便人们能够安排并改变自己的生活。批评话语分析强调各种后现代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语言和话语的变化,后现代社会中的各种经济活动和组织结构无不受到话语的塑造和重塑,话语是社会现实的“构成”(constitutive)因素。批评话语分析从一开始就自视为一种“工具语言学” (instrumental linguistics),它着重分析人们生成的符号和他们交流的意义之间的关系。分析的目的是揭示语篇中含而不露的意识形态意义,尤其是那些被人们习以为常的偏见、歧视和对事实的歪曲,并解释其存在的社会条件和在权力斗争中的作用。批评话语分析的目的与Connerton所说的批评社会学的目的是一致的:“批评……旨在改变或者甚至消除被认为是导致不真实的或者歪曲的意识的条件……批评……使得此前被隐蔽的东西显现出来,并以此在个人或群体中开启一个反省过程,以获得从以往的压制和支配之下的解放。”(Connerton,转引自Fowler,1987:483)
3.0 动态辩证的批评话语分析
后结构主义认为词语和文本根本没有固定的或内在的意义,而且词语或文本与思想或事物之间也没有明确的联系,语言和世界之间并没有一一对应关系,因此任何文本或话语分析都应建立在对特定的历史意义和语境意义的分析之上。斯科特(2001:381-382)认为,这样的一种分析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是:“意义是怎样获得的?它是在怎样的语境下,在哪一个特定的民众团体中,通过那些文本的和社会的过程而获得的?更一般的问题是:意义是怎样变化的?一些意义如何变成标准的意义,而其它的意义又是如何丧失或者消失掉的?这些过程又解释了权力构成和运作过程的哪些方面?” 批评话语分析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时特别重视对话语“殖民”(colonisation)或“挪用”(appropriation)的分析。所谓“殖民”或“挪用”指的是话语或者话语体裁在社会实践的网络中从一种社会实践向另一社会实践的挪移。这种挪移可被视为一种实践殖民(因而支配)另一种,或者后者挪用前者。话语的“殖民”或“挪用”总是意味着一种话语或体裁在另一种里的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权力关系和语言“杂合”(hybrid)问题。批评话语分析的许多研究都属于这一类,例如话语的市场化(marketisation of discourse,Fairclough,1995a)、官僚话语(bureaucratic discourse)、企业话语(enterprise discourse)和技术话语(technocratic discourse)向其它领域的话语的蔓延(Fairclough,1995a;Lemke,1995;Sarangi & Slembrouck,1996),以及公共话语的“会话化”(conversationalisation,Keat,Whiteley & Abercrombie,1994)。
再语境化涉及对其他话语有选择性的挪用和排列,这是构成任何话语实践的基本条件:“社会实践的应用性知识,即作为特定实践参加者所拥有的如何行事的知识,是处于未被表征状态的知识。一旦这种实践被表征(被思考、被描述、被讨论),那它就是被再语境化了。”(van Leeuwen,1993:204-205) Bernstein(1990:183-184)甚至认为“教育话语”(pedagogic discourse)并非一种真正独立的话语,而是一种再语境化原则,这种原则把原本属于其它实践的话语挪移过来植入自己的实践。在再语境化的过程中,某些话语被抽离于其原来的社会基础和权力关系,然后“作为涉及想象主体的想象实践而被重植”(Chouliaraki & Fairclough,1999:109)。意识形态正是在这种再语境化的过程中发生着作用:“‘想象的’并非与‘真实的’相对照,而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实践或主体是如何通过再语境化而被意识形态地建构成了真实的东西;其建构方式通过伪装分类原则以及影响分类的再语境化实践的具体逻辑而掩盖了分类的任意性。”(同上)如果我们把话语视为意义潜势,那么再语境化意味着在分类话语的过程中对某种话语的一部分意义潜势的压制,并在不同的话语之间设置隔离。再语境化压制不同话语之间的矛盾,但是当不同的话语在具体的话语实践中相遇时,它们之间的这些矛盾又会涌现出来;批评话语分析对语篇的互文性和对话性的分析就是要探讨这种压制和再涌现的问题。
批评话语分析者对话语“殖民”和“挪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语篇或话语的互文性和对话性的考察分析(例如Fairclough,1992,1995a,1995b;van Dijk,1995);除此之外,他们也十分关注全球化与本土化现象,两者也是一种话语/文化殖民或挪用,例如欧美传媒模式对中国传媒的影响或者后者对前者的本土化或挪用(黄敏,2012)。全球化与本土化涉及强势国家或群体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蚀与支配问题。现代化开启了全球化,在全球化过程中,几乎每个国家都被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而且其国家认同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也面临着危机。目前的世界规则、主导性价值观念,主要源于西方。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全球化或本土化是否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或民族要想融入现代、融入世界就一定要丧失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尊严?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后现代社会,不同的国家或民族如何理性地继承传统,又理性地走向未来,这对包括批评话语分析在内的所有社会批评研究是一个十分严肃的理论命题。
后现代主义者指出了现代主义研究范式的两大缺陷,即西方中心论和刻板僵化的二分法。现代主义理论往往将西方的现代化作为参照系,建构起传统与现代、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二元对立模式。按照这种范式,非西方国家或民族只有追随西方的模式才能实现所谓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后现代语境下的批评话语分析就是要力图打破西方中心论,更多地关注非西方世界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建构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多元的语言/话语或文化研究范式:“后现代世界摒弃了普遍的标准,它的问题不是如何使优势文化得以全球化,而是如何确保不同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鲍曼,2001:262-263)
在后现代的社会中人们对自己的身份越来越困惑,而人们日益增强的反思意识,尤其是对话语实践和主体身份的反思以及他们试图确认或确立自己身份的斗争是后现代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后现代主义主张“主体已经死了”并不等于否定或完全抛弃“主体”这一概念,它真正寻求的是“主体的建构过程以及将主体作为理论的要求或前提的政治意义和后果”(巴特勒,2001:209)。因此,后现代主义对主体的解构“仅仅意味着我们终止所有对于那个术语所指之物的支持,并考虑它在巩固和掩盖权威中起的语言作用。解构并不是否定或是排除,而是对诸如‘主体’这样的术语提出质疑,或许最重要的是,开拓这样的术语,使它向先前没有被认可的新用法或新用途开放。”(同上:223)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主体总是处于被建构的过程中,它永远不会被完全构成,而是会一再被构成。批评话语分析尤其关注“主体”在话语中的“占位”(positioning)问题,这既涉及对具体社会群体和个人的身份和自我表征(如媒体对妇女、民族、种族等的表征),也涉及具体的体裁如何构建人们的话语位置或角色(如门诊中的医患角色),以及人们在动态的交际中如何建构自己的话语角色。
在身份和角色上的斗争也是在差异上的斗争。如何与他者对话或交往的问题就像“我是谁”或者“我们是谁”一样是包括批评话语分析在内的社会批评理论需要面对的后现代最紧迫的问题之一。Bourdieu(1990)认为,主体的社会性同时内在于“领域”(field)和个体“习性”(habitus)中,而且两者之间往往存在张力,尤其是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但是其理论并未阐释这种个体习性由何而来。Bernstein (1990)关于“声音”(voice)的理论有助于批评话语分析对主体身份和话语角色的研究。在他的理论中,声音与主体辨别区分话语实践的各种语境的能力有关:即何时何地说什么合适。正是基于这种能力主体才能参与具体的交往并表达具体的意思。Chouliaraki & Fairclough(1999)发展了Bernstein的“声音”理论,认为在批评话语分析中,“声音”可从主体所掌握的体裁和话语及其相互关系的具体“构型”(configuration)上加以理解。对于任何处于具体社会地位的主体,这些声音的话语构型都服从于其所参与的具体社会实践的权力关系和支配原则。Blommaert(2005:4-5)对“声音”的理解与Chouliaraki & Fairclough(1999)如出一辙,认为“声音代表人们设法表达自己或无法表达自己的方式。人们在表达自己时必须依赖和调用他们所掌握的话语手段,而且他们必须在具体的语境条件下使用这些手段。”
在进行具体的话语分析时,我们还有必要区分结构性的或者相对永久性的声音和在具体情况下领域、习性和声音的临时区分和搭配。Zimmerman(1992:87-91)区分主体的“话语身份”(discourse identities)、“情景身份”(situated identities)和“伴随身份”(transportable identities)。话语身份构成即时互动组织结构整体所需的身份,如发话者和受话者、提问者和答问者、修正发起者等;情景身份是特定情景中的临时身份,如求救电话中的求救者;伴随身份无论在何种交往情境中总是伴随着个体,如性别、种族等。在这三种声音中,伴随身份代表的是相对永久性的声音,而话语身份和情景身份则是在具体语境中产生的临时声音。批评话语分析对身份的定义和分类充分考虑到了言语交往的动态性。
后结构主义的语言或话语分析与差异概念密切有关。所谓“差异”是指意义通过或明或暗的对比而产生,对任何事物的正面定义都是以否定或压制其对立面为基础的。因此,“任何一个统一体的概念事实上都包含了被压制或被否定的事物;它就是在与另一个术语的明确对立中建立起来的。意义的分析包括了对于这些否定和对立的梳理以及弄清楚这些否定和对立怎样(以及是否)运行于特定的语境中。”(斯科特,2001:384) Minow(1984)提出了分析差异的进退两难困境,指出在处理从属群体时不考虑它们之间的差异,就会留下一种不完美的中间状态;但是如果老是盯着差异又会显得离经叛道。因此他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思考差异的新思路,这就是由于在每一个范畴中一切现象都被看做是相同的,这就掩盖了各范畴内部的差异。我们的分析目标应该是不仅要了解不同范畴之间的差异,而且也要了解这些差异如何掩盖了各个范畴内部的差异。系统功能语言学是批评话语分析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理论中各种话语实践之间的差异是通过“方言”(dialect)、“体裁”(genre)和“语域”(register)来阐释的,一种话语实践内部的差异通过“编码倾向”(coding orientation)来解释。社会成员身份差异对应着编码倾向差异,这种差异通过具体的“语义风格”(semantic styles)来实现。“编码倾向”决定着语义和词汇语法的选择,这样的选择会最终系统性地表现出特定的立场或态度的倾向性。因此“语义风格”与意识形态直接相关。不过系统功能语言学以语言和语篇分析见长,而社会实践分析不足,分析者往往过于关注社会实践的语言符号因素,关注阐释具体的语篇如何从语言系统的不同潜势中做出具体的选择,而或多或少地忽视社会实践的其他方面,因而常常难以解释语篇内部的体裁“杂合”或者互文现象。
语言具有无限的生成能力,但话语秩序的稳定性会通过限制某些联系来限制这种生成力。另外,话语秩序还具体说明各种话语实践之间的流动关系和不同话语和体裁之间的再语境化关系,这种关系导致了语篇类型和其具体特征在不同话语实践和不同语境之间的不同分布。Hasan(1994)用“可渗透性”(permeability)概念来解释杂合语篇,认为可以把来自其他语类或体裁的成分视为当下语篇的构成部分,是“次语篇”(subtexts),在功能上支持“主语篇”(main text)。不过,Hasan(1994)的做法其实是用“实例”(instantiation)来适应“系统”(system)。对话语实践进行整体分析可揭示其中各种因素的作用和相互关系并因此能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语言符号因素在其中的功能。批评话语分析应该既重视具体的话语实践如何受系统的约束和限制又重视话语实践如何生产和再生系统,这才能反映系统和实例之间的辩证关系。
4.0 结语
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形成了与话语和语言的不同关系,而这种关系也随着话语实践的不同而变化。关于话语的知识成为了社会斗争中争夺的资源,例如在话语技术化(technologisation of discourse)中,基于知识的技术培训和学习已经变成了社会组织管理的一部分,带有明确的工具性目的。批评话语分析的产生和迅速传播本身就标示着生活在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普遍提高了的语言反思意识和能力,当然它自己在发展和日渐壮大的过程中也应反思自身在基于知识的话语斗争中的立场和角色。强调话语反思的后现代社会似乎会削弱话语的意识形态功能,这当然只是一种假象,因为正如Volosinov所指出的,意识形态贯穿整个符号学领域或全部表义系统,“意识形态领域与符号领域相重合。它们相等同。凡是有符号的地方就有意识形态存在。凡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就具有符号价值。”(Volosinov,1973:9-10)不过,随着后现代社会人们的语言反思意识和能力的不断提高,话语要更好地完成其意识形态功能就需要更有效的话语建构策略,而这也会反过来对批评话语分析者提出更高的要求。
注释:
① 后现代语境下的批评话语分析之三
[1] Bernstein, B.TheStructuringofPedagogicDiscourse:ClassCodes&Control[M]. London: Routledge, 1990.
[2] Blommaert, J.Discourse:ACriticalIntroduction(KeyTopicsinSociolinguis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3] Bourdieu, P.InOtherWords:EssaysTowardaReflexiveSociolog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4] Chouliaraki, L. & N. Fairclough.DiscourseinLateModernity:Rethinking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5] Fairclough, N.DiscourseandSocialChang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6] Fairclough, N.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TheCriticalStudyofLanguage[M]. London: Longman, 1995a.
[7] Fairclough, N.MediaDiscourse[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5b.
[8] Fowler, R. Notes on critical linguistics[A]. In R. Steele & T. Threadgold (eds.).LanguageTopics:EssaysinHonourofMichaelHalliday[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87.481-486.
[9] Giddens, A.NewRulesofSociologicalMethod:APositiveCritiqueofInterpretativeSociologie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10] Habermas, J.KnowledgeandHumanInterest[M]. London: Heinemann, 1972.
[11] Halliday, M. A. K. & C. M. I. M. Matthiessen. 1999.ConstruingExperiencethroughMeaning:ALanguage-basedApproachtoCognition[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12] Hasan, R. Situation and the definition of genres[J]. In A. D. Grimshaw (ed.).What’sGoingonHere?ComplementaryStudiesofProfessionalTalk(vol. 2.) Norwood: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4.
[13] Iser, W. Representation: A performative act[A]. In Murray-Kreiger (ed.).TheAimsofRepresentation:Subject/Text/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217-232.
[14] James, W.Pragmaticism[M]. New York: Longman, Green & Co., 1947.
[15] Keat, R., N. Whiteley & N. Abercrombie (eds.).TheAuthorityoftheConsumer[C]. London: Routledge, 1994.
[16] Lemke, J.TextualPolitics,DiscourseandSocialDynamics[M]. London: Taylor & Francis, 1995.
[17] Minow, M. Learning to live with the dilemma of difference: Bilingual and special education[J].LawandContemporaryProblems, 1984,48(2):157-211.
[18] Sarangi, S. & S. Slembrouck.Language,BureaucracyandSocialControl[M]. London: Longman, 1996.
[19] Thompson, J.StudiesintheTheoryofIdeolog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
[20] Todorov, T.MikhailBakhtin:TheDialogicPrincipl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21] van Dijk, T. A. Discourse semantics and ideology[J].Discourse&Society, 1995,6(2):243-289.
[22] van Dijk, T. A. Multidisciplinary CDA: A plea for diversity[A]. In R. Wodak & M. Meyer (eds.).Methodsof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1.95-120.
[23] van Leeuwen, T. Genre and field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synopsis[J].DiscourseandSociety, 1993,4(2):193-223.
[24] Volosinov, V. N.MarxismandthePhilosophyofLanguage[M]. Translated by L. Matejka & I. R. Titunik. New York: Seminar Press, 1973.
[25] Whorf, B. L. 1956. Linguistic relativity[A]. 刘润清,崔刚编. 现代语言学名著选读[C].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214-223.
[26] Whorf, B. L.Language,ThoughtandReality[M]. Cambridge: MIT Press, 1964.
[27] Zimmerman, D. H. The interactional organization of calls for emergency assistance[A]. In P. Drew & J. Heritage (eds.).TalkatWork:InteractioninInstitutionalSettings[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418-469.
[28] 巴特勒. 不确定的基础: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问题[A]. 塞德曼. 后现代转向[C].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207-230.
[29] 鲍曼. 是否有一门后现代的社会学[A]. 塞德曼编. 后现代转向[C].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251-276.
[30] 布朗. 修辞性、文本性与社会学理论的后现代转向[A]. 塞德曼编. 后现代转向[C].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355-378.
[31] 黄敏. 新闻话语中的言语表征研究[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2] 罗萨尔多. 社会分析的主观性 [A]. 塞德曼编. 后现代转向[C].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231-250.
[33] 斯科特. 解构平等与差异的对立:或面向女权主义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运用[A]. 塞德曼编. 后现代转向[C].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379-401.
The Relative Nature of Meaning and the Reflexivity of Criticism
XIN B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The post modern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provides multiple themes and concepts fo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and social critical theorists such as Gramsci, Habermas, Foucault, Derrida and Barthes have cultivated a fertile soil for CDA with their theories of hegemony, globalization, knowledge and power, language and power, the life world and the public world, the colonization of the life world by system and the resistance to it, etc. On the other hand, critical discourse, with its focus on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the social change of the post modern era,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cal study of post modern socie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lative nature of discourse meaning and the dynamic and dialectic natur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postmodernism;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relative nature of meaning; reflexivity of criticism
10.16482/j.sdwy37-1026.2017-01-001
2016-09-10
辛斌(1959-),男,汉族,山东乳山市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用学、篇章语义学、批评语言学。
H030
A
1002-2643(2017)01-00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