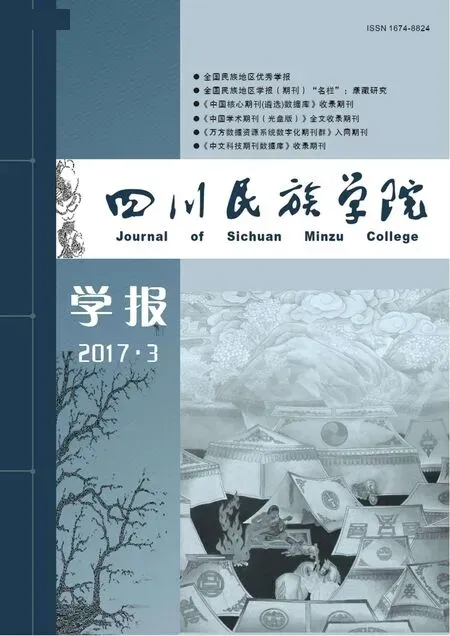从兴功惧暴到定分止争——关于甘孜藏区刑事纠纷解决模式的思考
刘树国
★法律研究★
从兴功惧暴到定分止争——关于甘孜藏区刑事纠纷解决模式的思考
刘树国
兴功惧暴和定分止争分别体现了法的阶级统治作用和执行公共事务的作用。刑事司法中,传统的刑事司法模式侧重于兴功惧暴,现代的刑事和解模式侧重于定分止争。在解决刑事纠纷时,应当处理好兴功惧暴与定分止争的关系,甘孜藏区的合作模式将法律、政策、习惯等因素有效地结合,更能充分发挥法的定分止争的作用,有利于实现兴功惧暴与定分止争的契合。
兴功惧暴; 定分止争; 刑事纠纷; 刑事和解
一、兴功惧暴与定分止争在刑事纠纷中的语义解读
兴功惧暴和定分止争语出《管子.七臣七主》,是一种常解常新的治国理念,契合了我国法律理论中的法的社会作用,按照其字面含义,兴功惧暴是指兴建功业、惧止暴行,与法的阶级统治作用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定分止争则可解释为确定名分、制止纷争,也就是解决纠纷,则与法执行公共事务的功能不谋而合。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学理念,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实现阶级统治的,然而,实现阶级统治是抽象的、概括的表述,其必然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具体职能的发挥即执行公共事务的职能来实现,各国家机关发挥法律职能的过程,也是各种法律纠纷解决的过程。只有通过各种纠纷的解决,才能建立和保障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从而真正实现法的阶级统治的作用。
在刑事纠纷解决的过程中,兴功惧暴与定分止争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强调兴功惧暴,在刑事司法中就会倾向于国家追诉主义模式,这种模式的刑法理念是一切犯罪均是对统治阶级秩序的破坏,刑罚是对破坏统治秩序行为的报复,在这种理念之下,国家通过严格的刑事司法程序发动刑罚权也就顺理成章了。强调定分止争,刑事司法中就会倾向于刑事和解等合作式司法模式,这种模式认为,每一个刑事案件背后都有一个待解决的刑事纠纷,刑事司法不仅要发挥刑法的威慑力,更重要的是还要通过犯罪人与被害人协商、赔偿等方式实现和解,从而避免刑事司法程序终结后,由于纠纷没有解决而产生的负面效应,如当事人不服司法处理结果而实施一些过激行为,甚至犯罪等。每一个刑事案件都涉及追究刑事责任和解决刑事纠纷两个方面,忽略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利于刑事案件的解决,所以在刑事司法中必须处理好兴功惧暴与定分止争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兴功惧暴与定分止争的关系?甘孜藏区的刑事纠纷解决模式对认识这一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二、甘孜藏区的刑事纠纷解决模式及简要分析
(一)私了模式
私了模式是指刑事纠纷发生后,双方当事人及近亲属等利害关系人直接“谈判”或通过第三方调解,通过赔偿的方式解决刑事纠纷的模式,实质上就是刑事行为民事化。以私了模式解决刑事纠纷不外乎两种原因,其一是习惯使然,在藏区社会,一直有通过“赔命价”、“赔血价”等赔偿的方式解决刑事纠纷的传统;其二是刑事纠纷当事人有意识地规避国家法律,之所以这样做,据调查了解,在当事人看来,认为这样解决刑事纠纷,更有利于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被害人一方看,“不报官”作为重要的筹码,可以在“谈判”中获得更多的赔偿,从犯罪人一方看,通过更多的赔偿换取对方“不报官”,从而避免国家的刑罚处罚。*本文关于甘孜藏区解决刑事纠纷时存在的各类情况,均为调查研究后的总结性表述。
不可否认私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解决刑事纠纷的作用,例如,对于由民间纠纷引起的轻伤害犯罪案件,牧区常见的盗窃牛马等情节较轻的盗窃案件等,这些案件大都属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自诉类案件,这类案件的私了,既解决了刑事纠纷,也节约了司法成本,与我国的刑事立法精神是一致的,即使私了也无可厚非。然而私了模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在私了模式解决的刑事纠纷中,不仅有属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自诉类犯罪,还有重伤害、杀人、抢劫等依法应当判处最低刑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的公诉类犯罪,公诉罪私了不仅违反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与现代的法治精神格格不入。其次,私了模式解决刑事纠纷会使国家制定法边缘化,甚至被排斥。有意识地规避国家法律而实施的私了或许并不可怕,因为规避的存在本身就表明规避者意识到国家制定法或一种权威的存在,当他们努力规避国家制定法时实际上也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国家法律的规则。[1]真正可怕的是习惯使然所进行的刑事私了,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心目中根本就没有国家制定法可言,也就是说,行为人在事实上排斥了国家制定法。再次,从解决刑事纠纷的效果看,私了模式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在私了时常用的“命价”“血价”赔偿根源于甘孜藏区特有的血亲复仇传统,如若私了不成则当事人双方或其家族就可能会出现报复性的伤害、杀人等行为,造成新的纠纷;刑事私了中赔偿标准的不确定性常常出现由于超出赔偿能力支付高额的赔偿金,造成部分犯罪人及家属债台高筑甚至倾家荡产的情况,而为了支付高额的赔偿金,犯罪人就有可能又实施新的违法犯罪行为,给社会治安带来隐患。基于私了模式的种种弊端,甘孜藏区司法行政机关对私了模式解决刑事纠纷一直是严格禁止的,加之以司法资源的不断充实,法律渗透力度的加大,近年来,甘孜藏区私了模式解决刑事纠纷的现象已经呈现下降的趋势。
(二)司法模式
司法模式是当前我国最主要的刑事诉讼模式,是指刑事案件发生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等国家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处理刑事案件的模式。司法模式强化了程序的正义性,强调刑罚的权威性,重在通过刑罚的适用解决刑事纠纷。然而,这种一元化解决刑事纠纷的模式,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矛盾,犯罪行为一旦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受现代国家追诉主义的影响,国家取代被害人成为与加害人在“台面上”对抗的主体,此时体现国家与加害人关系的刑事案件逐渐成为影响刑事司法程序进程的主线,刑事纠纷则逐渐隐去直至完全被处于显性状态的刑事案件遮蔽。[2]当加害人被判处刑罚尤其是重刑或死刑后,被害人的利益往往不能得到充分保护。虽然被害人或其家属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大都会予以支持,但是被告人及其家属要么由于生活困难没有能力赔偿,要么获悉了无法改变的重刑或死刑的判决结果而失去了赔偿的积极性,其最终结果是被害人的获赔率极低,心灵的创伤更加难以抚平。[3]这一矛盾,在甘孜藏区的司法实践中体现地尤为明显。从甘孜藏区人民法院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来看,对同类案件而言,法院判决的赔偿数额与私了方式解决刑事纠纷的赔偿数额差距较大,而且兑现和执行到位的难度相当大,有的案件执行的时间甚至长达数年。也由于判决赔偿的数额与私了赔偿的数额差距较大,加之以宗教、传统文化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在甘孜藏区,司法模式解决刑事纠纷的接受度并不是很高。
(三)合作模式
合作模式,是指刑事诉讼中的程序主体在充分考虑各自利益诉求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妥协协商和合作,形成纠纷解决共识的诉讼。[4]在甘孜藏区,合作模式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私了+司法模式,另一种情况是多元联动模式。私了+司法模式是指刑事案件发生后,当事人先通过民间调解或和解等方式就赔偿等问题达成协议,加害人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后到司法机关投案自首,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在得到满意的赔偿后向司法机关表示对加害人的刑事责任不再予以追究,也有的请求司法机关对加害人从宽处理,人民法院在判决中通常会把这些情况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据调查,近年来农牧区因民间纠纷引发的故意杀人、伤害案件的附带民事部分,在法院判决前绝大部分都通过民间调解方式达成了赔偿协议,并且也基本上能得到履行。*参见甘孜州X人民法院的调研报告述。民间调解所达成的赔偿协议很多时候是由嫌疑人的亲属甚至家庭代为履行且履行迅速,被害方既通过调解实现了自我需求上的正义,又能够得到较大额度的经济赔偿,有效消除了原始复仇行为。故这一模式解决纠纷普遍为农牧民群众所接受。
多元联动模式是甘孜藏区党政司法机关在社会治理中结合藏区社会生活的特点所常用的一种解决刑事纠纷的特有模式,其针对的主要是案情复杂、涉及人数众多的由民间纠纷引起的刑事纠纷,如由土地纠纷、草场纠纷引起的家族之间、村落之间的械斗等。这种模式的外在形式是在刑事纠纷发生后,相关国家机关迅速到场平息纠纷,进而对纠纷进行调解,*调解采用的是现场调解和非现场调解相结合的形式,甘孜藏区各县司法局均设有“大调解”室,现场调解不能及时结束的,再由大调解室继续进行调解。消除再次发生纠纷的隐患。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通过调解直接结案,无需再走司法程序;犯罪情节严重的,通过调解程序先行解决刑事纠纷,然后再按照司法程序处理,法院介入到调解程序中主要是了解案情,并不对调解结果发表实质性的意见。相对私了模式和司法模式解决刑事纠纷,多元联动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参与解决纠纷的主体更加广泛,从国家机关层面看,不仅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等传统刑事司法机关参与其中,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国家机关有时也参与其中,从社会层面看,不仅包括当事人及其近亲属,还包括其他亲属长者、基层群众组织成员、宗教界人士、德高望重者等。也就是说,多元联动模式是一种比刑事诉讼中的合作模式参与主体更为广泛的纠纷解决模式。
第二,多元联动模式融合了私了模式和司法模式的优势,克服了私了模式和司法模式的不足。以私了模式中常用的民间调解为例,藏族全民信仰佛教的现实使得民间调解具有较强的宗教色彩,寺庙、喇嘛、堪布等在民间调解中发挥着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多元联动模式有效地结合了这一特点,甘孜藏区有些高僧本身即为人大、政协领导,在各县司法局设立的大调解室中,一般均有当地的喇嘛、堪布等宗教界人士担任专职或兼职的调解员,在解决刑事纠纷时,由他们出面对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动之以情、晓之以法,往往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每一次刑事调解的过程,也是一次法律教育的过程,既解决了刑事纠纷,也避免了国家法律被边缘化的危险。再以草场纠纷为例,对当地农牧民群众而言,草场是生活中最重要的物质性权利之一,加之以虫草、菌类等草场资源价格的不断上涨,近年来草场纠纷成为藏区社会常见多发的民间纠纷。有些纠纷甚至引发家族之间、村落之间的械斗,在械斗中,死人、伤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果按照司法模式,解决这类刑事纠纷非常简单,即在械斗中没有造成重伤害或死亡结果的,按照聚众斗殴罪或者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造成重伤害或死亡结果的,按照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将首要分子、主要参与人员绳之以法,再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起诉、判决、执行。但是从刑事纠纷的解决效果看,这种方式并不理想。在斗殴中被绳之以法的首要分子和主要参与人往往是其中一方的领导者,是维护本方利益的“英雄”,在其他参与人或利益关系人看来,自己的“英雄”被处罚,难免心生怨气,这种怨气即便不直接发泄出来,却有可能成为社会治理中的不安因素,要么以新的违法犯罪行为发泄,要么再遇到类似行为时便有意识地绕开国家法律和相关国家机关而以私了模式解决之。多元联动模式在解决因草场纠纷引发的刑事纠纷时,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对纠纷双方说服教育,平息双方的怨气,化解双方的矛盾,促成双方和解,然后再进入司法程序,从而有效避免了刑事案件已结、刑事纠纷未止的情况。
综上所述,相比私了模式和司法模式,合作模式更加适合甘孜藏区社会的发展现状,是以在甘孜藏区得到了广泛应用。
三、甘孜藏区刑事纠纷解决模式的启示
(一)欲兴功惧暴,当先定分止争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私了模式下,处理刑事案件的主要依据是甘孜藏区当地的习惯,而非国家制定法,法律只是在私了“谈判”中用于讨价还价的筹码,由于法律并没有发挥其定分止争的作用,法律的兴功惧暴作用也就无从谈起。其最终结果是造成法律与社会生活两分离的状态。在司法模式下,处理刑事案件的依据主要是国家制定法,当地的习惯至多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固然法律兴功惧暴的作用在这一模式下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但其定分止争的作用却不甚理想。由于定分止争与兴功惧暴存在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也就使得法律的兴功惧暴功能大打折扣。合作模式则使法律的定分止争功能与兴功惧暴功能做到了有效结合。合作模式中的私了+司法模式,处理刑事案件的依据是习惯+国家制定法,即习惯侧重的是解决刑事纠纷,国家制定法侧重的是追究刑事责任,多元联动模式下,处理刑事案件的依据不仅包括国家制定法、民族习惯,还包括党的政策、国家政策等,总的来看,在合作模式下,刑事纠纷的解决是法律、政策、习惯等合力发挥作用的结果。从社会效应看,多元化的合作模式更有利于发挥法律的定分止争的作用,在甘孜藏区,只有解决好各种纠纷,才能够实现藏区社会的和谐稳定,有利于藏区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放眼我国法治建设的大局,一切法律兴功惧暴作用的落脚点都应当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所以,欲兴功惧暴,当先定分止争。
(二)需要解释的疑问:刑事制定法与习惯法的关系问题
甘孜藏区的合作式模式解决刑事纠纷,难免融入习惯法因素,关于习惯法处理刑事案件,一直不乏质疑之声,最为典型的观点就是罪刑法定原则与习惯法是排斥关系,用习惯法解决刑事纠纷会破坏刑法的稳定性、权威性等。那么事实真的是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是:
第一,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渊源看,罪刑法定原则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于民主、人权等思想为反对封建刑法的恣意性、残虐性、干涉性、身份性而建立的一种刑法理念,旨在通过对刑罚权的发动进行限制,实现人权保障的目的,时至今日,罪刑法定原则已经发展成为现代国家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的大宪章,罪刑法定原则是入罪加刑原则而非出罪减刑原则已经成为理论共识。根据我国刑法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法律规定只是定罪量刑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一个行为构成犯罪与否,如何承担刑事责任应当根据该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等综合判断。
第二,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看,罪刑法定原则具有形式和实质两个侧面,法律主义是罪刑法定原则形式侧面的核心内容,由此出发,必然得出排斥习惯法的结论。而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出发,则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要求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何种行为为不当罚的行为,法律的抽象性、概括性特点决定了其不可能被一一列举,只能依靠执法者、司法者在实践中根据法律的精神、法律的目的等去把握。例如,刑法中没有一条规定“在战场上打死敌人的行为是否属于犯罪行为”,之所以认定这种行为不属于犯罪行为是因为根据刑法的精神、刑罚的目的可以自然推出。在甘孜藏区,解决刑事纠纷时,何种行为入罪当罚,不仅需要考虑法律的规定,还需要考虑法律的精神和目的,考虑藏区社会建设和谐稳定的大局。具体到法律的作用层面,既要有利于兴功惧暴,还要有利于定分止争。那么,在出罪减刑时,就有可能吸收习惯法的因素,这不仅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恰恰符合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内涵,体现了司法行政机关在社会治理中的智慧。
第三,从法律解释上看,成文法的特点决定了刑法中可能包含有不当罚的行为,善良的人们总是希望一切应当以犯罪论处的行为在现实上都被论罪科刑,但成文法的局限性与罪刑法定原则使这一愿望难以实现。[5]所以,正确地适用刑法,必须对刑法作出合理的解释。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为吸收习惯法的合理成分解决刑事纠纷预留了解释空间。首先,刑法第90条明确赋予了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机关根据刑法的原则和规定结合自治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对刑法做出变通或补充规定的权力。尽管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大都未制定变通的或补充的刑事法规,但是刑法第90条的规定为民族地区适用习惯法解决刑事纠纷提供了可能性,因为习惯法本就是民族地区文化的一部分。其次,在没有刑法或变通法规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习惯法的适用也并非必然被排斥,根据我国刑法第61条,定罪量刑的依据是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性,在法律解释上,除了犯罪事实而外,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和社会危害性都存在较大的伸缩性。最高人民法院在《在审理故意杀人、伤害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中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指出犯罪情节多属酌定量刑情节,法律往往未作明确的规定,但犯罪情节是适用刑罚的基础,是具体案件决定从严或从宽处罚的基本依据。故对民族自治地方而言,即使没有成文法的规定,自治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也应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关于社会危害性的有无及大小问题,不仅需要依据法律的一般规定还要根据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性更要考虑民族地区和谐稳定的大局综合认定。如果说法律规定是我国的大传统,那么民族地方的习惯则是小传统。在民族地区,判断一种行为有无社会危害性以及危害性大小的问题不仅依据法律规定(大传统),还要依据习惯(小传统)。综上,刑事制定法和习惯法并非完全的排斥关系。
(三)必要的展开
“强行推进”一直是国家刑法在民族地区贯彻实施的主要方式,而且国家刑法从一开始就有改造民族刑事习惯法的冲动,[6]甘孜藏区的合作模式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同的面向,实践证明,法律、政策、习惯合力解决刑事案件不仅可行,而且社会效果明显。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设的刑事和解程序标志着我国的刑事司法在立法层面开始从兴功惧暴走向定分止争,刑事司法模式由最初单一的报应性司法演变为以报应性司法为基本司法模式,以协商性司法和恢复性司法为重要补充的多元刑事司法模式共存的现状。[7]法因世而迁,因时而易,世变法亦变,新生的刑事和解制度必然会对我国的法治秩序建设带来深刻变化。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结构特点和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现状决定了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还需要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有一番改革。[8]而法律思想的确立绝非朝夕之功,既需要自上而下的强力推行,还需要自下而上的自愿接受。所以,何种法律能及时有效地回应民众的需求,何种法律才会被人们真正的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加以接受。[9]而法律只有被人们真正地接受,其定分止争的作用才能更充分地发挥,进而实现兴功惧暴的目的。
[1]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p73
[2]何挺.解决刑事纠纷的双重方案:基于模型建构的分析[J].法商研究,2016年第1期,p43
[3]葛琳.刑事和解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
[4]谭世贵.论刑事诉讼模式及其中国转型[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3期,p113
[5]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p91
[6]苏永生.论罪刑法定原则与民族习惯法[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5期,p14
[7]王林林.多元刑事司法模式共存语境中的量刑基准研究[J].政法论坛,2016年第3期,p46
[8]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p58
[9]杜宇.作为间接法源的习惯法——刑法视域下习惯法立法机能之开辟》[J].现代法学,2004年第6期,p52
[责任编辑:陈光军]
From Intimidating Violence by Punishments to Ending Disputes by Identifying Responsibilities --Reflection on Solving the Criminal Disputes in Ganzi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LIU Shuguo
Intimidating violence by punishments and ending disputes by identifying responsibilities demonstrate the roles of a law played in classes governing and executing public affairs respectively.In criminal judicature, the traditional mode emphasizes on intimidating the violence by strong punishments, while the modern focuses on ending disputes by identifying responsibilities. When solving criminal disputes, th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ones must be well-balanced. In Ganzi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the cooperative mode that effectively combines law, policy, custom and other factors will allow the law a full play in ending disputes and benefit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intimidating violence by punishments and ending disputes by identifying responsibilities.
intimidating violence by punishments; ending disputes by identifying responsibilities; criminal disputes;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D920.5
A
1674-8824(2017)03-0052-05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藏区刑事和解制度研究——以甘孜藏区为例”,项目编号:14SB0268。)
刘树国,四川民族学院政法系讲师。(四川康定,邮编:626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