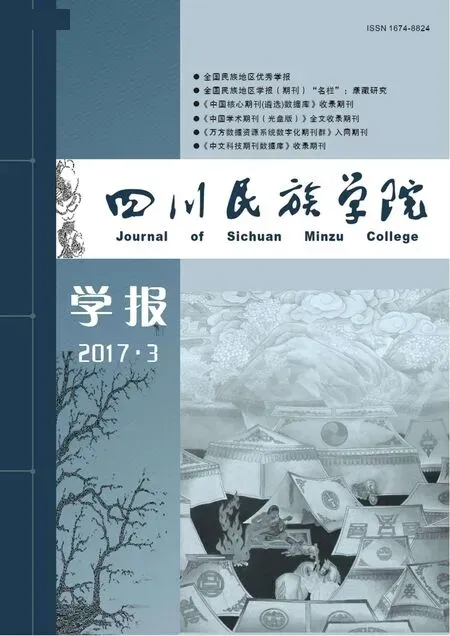浅谈民国时期西藏的宗和谿卡
刘永花
★康藏研究★
浅谈民国时期西藏的宗和谿卡
刘永花
宗与谿卡是西藏噶厦地方政府中出现较早,持续时间最长、职能最多的基层行政组织,也是推动其下属各基层机构正常运作的重要保证。西藏历史上,以宗、谿为基础形成的这套组织制度在其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通过梳理宗谿制度的形成及历史沿革,综合各类文献史料,对民国时期西藏的宗谿及其宗本、谿堆的任命、品级、主要职责,以及宗谿内主要管理人员的构成等内涵分析阐述之。
宗本;机构;制度
一
宗,即藏文“rdzong”的音译,本意为“堡垒、山寨、要塞”,实际上是自古代至近代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下各地大小酋长的驻地。当然,宗的治所一般是居高临下,置于地形险要、黎民百姓聚居地的要冲,包含了固守疆土、护卫要人的重要防御功能,旨在内防外患。例如,西藏历史上的第一座藏王宫殿——雍布拉康、日喀则桑珠孜宗堡、山南岗巴宗堡、拉鲁庄园的修建等等,均具有典型的这类特点。再如举世闻名、雄伟壮丽的历代达赖喇嘛的“冬宫”——布达拉宫亦是如此,不一枚举。
元代,中央政府在西藏设立的十三万户之一的帕竹万户的第八任万户长绛曲坚赞时期,帕竹家族势力逐渐强大,于至正十四年(1354)推翻了受元王室扶持的萨迦政权,建立了帕竹政权。14世纪后期,绛曲坚赞兼并了其他几个势力较弱的万户后,封赐家臣,开始推行宗谿制度。在广袤卫藏交通畅达的枢纽地方,如贡噶、乃乌、桑珠孜、仁蚌等处兴建了十三大宗,各宗设有宗本,任期为三年。从此,在西藏出现了以“宗”为单位的基层行政组织,并为后世所相沿,其地位相当于内地的县。宗本由帕竹政权的法王(“第悉”或称“第巴”)任命,采用流官制,此项措施推动了领主庄园制的发展和西藏地方的统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15世纪中叶,帕竹政权第五代法王扎巴坚赞将宗本流官制改为由主要的家臣世代掌管各宗的宗本世袭制,并赐给其属臣格尔·南喀坚赞世代担任仁蚌宗宗本的玉印,如此直接导致了地方贵族势力坐大、帕竹政权的势力日渐衰微,并最终由其属臣仁蚌巴窃取了帕竹政权对卫藏地区的统治权,此期宗谿制度的发展亦受阻。
到17世纪前期,蒙古和硕特部的军事力量帮助格鲁派排除了敌对势力、取得了西藏的统治权后,固始汗任命了五世达赖喇嘛的强佐索南饶丹为第一任第巴,行使对西藏世俗事务的管理权。康熙十八年(1679),桑结嘉措出任第五任第巴后,他在不遗余力建设“第巴政府”的过程中,分封各地各类领主时又恢复了绛曲坚赞时期设立的流官制度,并在各地设立了下属的宗、谿机构。此期,“甘丹颇章”政权政教合一的性质亦体现在各宗的宗本或宗堆、各谿的谿堆的基本职责中,如桑结嘉措在他当政两年后(1681)主持编纂的《法典明镜》二十一条的最后两条——“驻守各宗官员的工作”和“驻守各谿卡的工作”中,除了规定各宗谿官员的世俗职权和职责外,条例中还要求必须要保持格鲁派的主导地位等。康熙二十四年(1685)随着西藏与拉达克之间战争的结束,甘丹颇章政权又将宗谿制度引入了阿里地区,将噶厦政府对卫藏和阿里的管辖权归于一统。至此,西藏的宗谿制度基本确立下来,并一直延续到了近代。
谿卡,藏语称作“gzhis-ka”,意为采邑、庄园,其出现比宗更早。约在11世纪前期,古格首领拉德为了表彰大译师仁钦桑布修建寺院、翻译佛经等对于佛教在西藏再度复兴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将乍布朗附近的谢尔等三处分封给仁钦桑布,成为了他私有的三处谿卡。从此,谿卡以领主经营领地的形式,逐渐发展成为西藏的另一种基层组织。14世纪,帕竹法王在建立十三个宗的同时,将谿卡这一有效的基层管理办法向雅鲁藏布江中游各地推行。17世纪后期,甘丹颇章政权完成对卫藏、阿里各地区的统一后,谿卡作为西藏农业区社会基层组织的基本形式一步步地被落实,谿卡制度也逐渐定型。此时,按照西藏各领主实际掌有领地的大小、多寡不同,谿卡又被分为“雄谿”(gzhung- gzhis,政府庄园)、“格谿”(sku-gzhis,贵族庄园)和“却谿”(chos-gzhis,寺庙庄园)三类,即被后世称为的三大领主庄园。
二
宗,作为宗政府的驻地,由于历史上其首领兼管军民两事,因此它既是基层行政办事的衙门,也是宗本的军事指挥部所在地。直到近代,西藏各宗政府的公务及军务处理场所仍然保留在古老而坚固的城堡里,矗立在峻峭的山顶上,守卫着西藏的大小峡谷。是时,关于西藏宗谿之数目,由于部分大的谿卡规模与宗相仿,以及部分谿卡区域被当地寺院、法王所管辖等,因此难以准确统计。为阐明本文观点,笔者将以民国时期西藏主要的几个宗为例,分析论述其内部组织形式和管理人员的构成等。
——宗本的任命与品级。宗,作为基层行政单位,直接管辖着分属三大领主的庄园或部落(sde),其统治者——宗本(rtsong-dpon,类同今县长)是由噶厦地方政府直接任命的最低一级的地方官。乾隆十三年(1751),清廷在颁布的《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中规定:“补放宗谿头目等官,……众噶伦等务须秉公查办,共同禀报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酌定,俟奉钤印文书遵行。”[1]至民国时期,尽管西藏地方政府在宗之上设有“基巧”(spyi-khyab,类同今专区或州),但各“基巧堪布”(spyi-khyab-mkhana-po,类同今专员或州长)却无权任命辖区内的宗本。以昌都基巧中权力最大的昌都总管为例,其所辖的宗本仍由西藏地方政府任命,基巧总管仅行监督和指挥各宗工作之权。如民国六年(1917)在昌都类乌齐设立了宗一级政权机构,其宗本却由噶厦地方政府每四年选派一次。但也有部分属于寺属宗谿之宗本则由寺院直接委派,如清朝解体后,噶厦地方政府很快便将原直属驻藏大臣管辖的当雄宗赐封给色拉寺后,该宗宗本则由色拉寺委派。当然,为了便于基层管理,地方政府在宗之上设立了基巧,但各宗宗本的任命权却仍然掌握在当地政府、寺院和贵族手中,这无疑反映出在政教合一制度下的西藏封建农奴社会的管理体系中,对于一宗之内的土地、山川、河流、树木、牛羊、房屋、农奴等,以及为之效力的大小官弁之任免权都被牢牢掌控在三大领主手中。
关于宗本的出任,以俗官为例,一般贵族弟子在十几岁时可以通过培养俗官的“孜康”学校学习,经过若干年的学习和考试通过后,即可获得官职。最初几年往往任噶厦政府中的“噶仲”(bkav-drung,秘书或传令官)等职,任期满后,到二十几岁时便可以升任为某宗的宗本了。如现代著名藏学家恰白·次旦平措先生在他年青时便被任命为江孜宗宗本,这样的例子在《西藏的贵族与政府》一书中不胜枚举。但大多数时候宗本们并不驻宗政府办事,其职责由“涅巴”(gnyer-pa,管家)代为行使。如当雄宗宗本仅在每年六~八月向牧奴们征收差税时才赴宗政府“巡视”,中饱私囊后一走了之,其他的九个月,则由涅巴全权代理。又如民国三十三年(1944)秋天的“林周宗事件”,被色拉寺杰札仓的催债喇嘛打死的林周宗代理宗本,即为时任译仓中权势显赫的四大“仲译钦莫”(drung-yig-chen-mo,秘书长)之一的群培土登的胞弟,林周宗作为群培土登的俸禄领地,原本他是该宗的宗本。
通常对于宗本的人数与任期,意大利著名藏学家L·伯戴克(Luciano Petech,又译为毕达克)先生的观点就比较典型:“每宗由1至2名宗堆主管,每任为期3年。在两个宗哲(rdzong-sbrel,即两个宗本——笔者注)并列的情况下,可能两者皆是俗人,更通常的一为俗人,一为僧侣。”[2]对此,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实例来验证其言之有理的部分,也可以找到与此说法并不一致的地方。如恰白先生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出任江孜宗宗本时,与他共事的另一名宗本是彭康家族的公子衮波才仁(是年结婚),这说明当时江孜宗的两名宗本的确皆为俗官。此后三年(1943),噶厦政府将霍尔措划归为绛曲基巧下的六宗后,派僧俗官员各一人充任各宗的宗本。然而,宗本人选并非均如上所言,如从民国初年起,由色拉寺任命的当雄宗宗本为3人,分别是该寺三大“扎仓”(grwa-tshng,僧学院)中的一般上层喇嘛,任期为五年。由此看出,宗本的任期亦并不一定为三年。20世纪上半叶,随着阿里地区改则境内部落势力的不断壮大,改则宗本受封为四品世袭官,允其子嗣承袭。十余年后,当改则宗本在任上去世,其儿子索南班觉承袭了改则宗本一职。除此,宗本往往在各宗间相互调任,如,帕拉家族的平措南杰先后担任过江孜宗、定结宗和仁蚌宗的宗本;恰白先生亦曾担任过江孜和吉隆宗宗本。
另外,宗又视其面积大小、地势险要与否、事务繁闲和户口、收入之多少,分为边宗、大宗、中宗、小宗四种。早在乾隆五十七年(1793)清廷颁布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中就规定:“大宗及边总宗本之缺额,由小宗宗本中委任。……各边宗及小宗宗本之缺额,由普通职员中委任”。[3]可见,清廷法律条款中明确规定的贵族子弟一旦步入仕途,不久就能出任宗本职务。基于此,道光二十四年(1844)驻藏大臣琦善在任期内,在对上述章程详加考订的基础上,将中原内地依品擢职授权的官僚制度引进了西藏。直到民国时期,西藏的大宗与中宗一般设五品或六品僧俗宗本1~2人。据恰白先生著述坦言:江孜宗由于面积辽阔,吉隆宗的粮食产量高,算是广袤富裕的宗,所以当时他被定为(俗官)官秩五品,且该宗设宗本2人。除外,西藏小宗则设六品或七品宗本1人,如位于拉萨西北的东噶宗,因其面积狭小,宗本只有一人充任。至于边宗也有大小之分,并且这些边宗因多位居于国防边塞要地,战略地位在其它大宗之上。如卓木宗就是位于藏印交通孔道与国防门户,噶厦政府因此特设四品基巧堪布兼理卓木宗宗本,民国六年(1917)任四品俗官的卓木基巧堪布米介巴·齐米多吉即是一例。
——宗本的职责。赋税是土地所有者赖以从中盘剥农奴的重要手段,近代西藏的土地及农奴等被三大领主所占有:即由噶厦地方政府直接占有并经营着一部分;贵族、官僚们作为俸禄地掌握着一部分;还有一部分由政府分封给寺院,由活佛、高僧们操控着。因此,宗本作为由三大领主派出的在其辖区内管理各宗的代理人,必然要为其效劳。根据上一任宗本离任时向新任宗本交接的辖区内的户数以及具体差税事宜,现任宗本向辖区内的农奴摊派乌拉差税。孜康亦每年会往各宗谿派出一个“雍堆巴”(yong-sdud-pa,催收租税的官员)协助宗本审计收税。民国年间,十三达赖喇嘛曾屡次颁布文告,严厉告诫各宗谿头人“不得徇私偏袒、巧立名目征派新的差税,扰累欺压属民百姓……”[4]这亦从侧面反映出当时西藏诸多宗谿第巴、头人等任意敲诈勒索、鱼肉百姓,已然盛行成风。
宗本作为基层地方官与封建领主间相互沟通的媒介,其上传下达地方政府命令的作用不可小觑。如民国初年噶厦政府在“给里帕宗本的指令”中,要求宗本对其辖区内全体僧俗广泛深入宣传:自是年五月一日始,一年内要到银行去兑换清末地方政府铸造的三钱、五钱的银质“章嘎” 藏币和七分半、两分半的铜质章嘎事宜。另外,宗本在秉承领主的旨意告知辖区内百姓支差纳税义务的同时,还要及时向上秉报基层情况。如民国三十三年(1944)秋,林周宗农奴因无法偿还借贷利息乞求该宗代理宗本减轻他们的债务负担,这一请求被宗本呈报给了噶厦政府,随后进行了调查了解,事后也没有了下文。
除上述职责外,宗本对其辖区内的农奴还握有一定的生杀予夺的司法权,有权力对未按规定执行或违法的农奴依法进行惩处。民国年间,当雄宗就有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律,有一套封建制度的等级习规,宗内设有法庭、监狱以及刑具,其法权的一套体系基本上沿袭了噶厦政府的法规,但杀人等重大案件要上报噶厦政府处理。为此,十三世达赖喇嘛曾于任内颁布的文告中要求“各宗谿官员除依照法律轻微量刑外,不准为满足个人欲望以小事作由头进行处罚……”[4]然而,现实生活与上级指示或法律规定还是相去甚远,基层的农牧奴们哪怕只是家庭纠纷或农牧业生产矛盾也得贿赂宗本,具体需要送一头牛还是呈献一条哈达,视违法者家庭财产状况而定。
对于被派往边界要地的各宗宗本而言,镇守边关,保靖安民,征收商税,发展经济是其十分重要的职责。卓木宗地处西藏国防边陲最前沿,虽然辖地不广,但驻地位于藏印交通要道,所以由卓木基巧兼任的宗本主要负责征收出入两国之间的货物贸易及盐粮税收,并办理卫藏(西藏)、天竺(印度)、哲孟雄(锡金)、布鲁克巴(不丹)等各种边境事宜。而阿里日土宗宗本要负责征收当地百姓赋税,与国外以物易物的盐粮交换或征收官税。若遇战事,宗本还要负责筹划军粮、征发土兵,为国为民临阵指挥等等。如光绪十四年(1888)英帝国主义悍然对我国西藏发动第一次武装入侵战争时,“西藏(民众)扩大会议”则下令日喀则宗本担任定结、卡达哨所的总指挥。该宗本不辱使命,火速催派属地乌拉差役,调运辎重粮秣,并紧急修筑碉堡十多个,加强兵力,并按地段分兵布置,严防死守,做到责任到位。此次反侵略战争虽然最后以藏军的失利告终,但也彰显了宗本们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的坚定态度、顽强抗敌的决心和不屈的斗志。
对于处理本宗内部的事务,宗本们也常常会受到宗内较大寺院势力的“干政”和钳制。民国初年,地处金沙江上游的昌都西南部的硕般多寺“赤巴”(khri-pa,住持、方丈等)在当地拥有极大的权威,所有的世俗行政事务如征税、执法、官吏的任免等都要插手,连同宗政府一起办理。[5]这也反映出了在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大环境下,基层组织的性质亦存在政教联盟的特点,这一点与近代云南迪庆藏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松赞林寺的性质完全吻合。
——宗内其他管理人员的构成。关于宗政府内部人员构成,西藏各宗之间都存在着略微的差异。以东嘎宗和当雄宗为例,宗本之下一般设有“涅巴”(gnyer-pa,管家)1~2人,他们是经常驻宗的宗本代表,宗本不在时全权代理负责宗内事务,宗本驻宗办公时则作为其助手;“仲译”(drung-yig,秘书)2人,按照宗本或涅巴的命令,处理案件,检查派差,宗府召开会议时,2人都必须出席,如2人中有人缺席,会议便须改期召开。仲译任期较长,人选一般从宗所辖的谿卡内选出,若该谿卡属贵族领有,由贵族领主选出,上报噶厦则可以世袭。除外,按照地方政府的官吏相应待遇,为宗本还配有私佣6人,若是宗属某个寺院,以上人员则全部由寺院派出。宗政府还有信差2名,负责向最低一级的基层管理者“佐扎根布”(gtso-drag-rgan-po,庄头、头人或乡吏)传送宗本之命令,每位佐扎根布又分别负责管理着宗内的若干个农区或半农半牧的小谿卡,或牧区的“学卡”或“如瓦”(shog-kha,ru-ba,即部落)。如东嘎宗有大小72个谿卡,属6个根布管理,这些乡村官吏分别由他们隶属的谿卡或部落的领主派出。当然,宗本与这些基层乡吏有时也发生各种问题,这也是在所难免的。如民国前期,阿里日土宗的新任宗本与当地头人发生纠纷和冲突,因事态严重,最终被噶厦政府将其流放到了西藏南部的协噶尔宗苦度余生。
——谿卡及其内部管理人员构成。西藏的谿卡按其规模大小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宗一级的谿卡,“在卫藏有64个比一般谿卡大得多,被称为‘谿’的行政单位”。[6]这类谿历史悠久,如桑日宗的桑日谿是七世达赖喇嘛父亲的封地;隆子宗的加玉谿则是十四世达赖喇嘛母亲的封地。这类谿的规模与小宗相仿,所以,噶厦就地派六品或七品官前往担任相当于宗本的官职,称做“谿堆”(gzhis-sdod,领主之代理人或庄园头人)。其府邸内所设的管理人员及其职责也近似于宗,此处不再赘述。第二类谿卡则是规模比较小的普通谿卡,以山南基巧下扎囊宗囊色林谿卡为例,其内部管理者的主要构成为领主-涅巴-基根-定噶根布。涅巴是谿卡的总管家,是领主从大差巴家庭选出的能算会写的亲信,经管谿卡各方面的事宜,他不能任意处理谿卡的重大事情,要事要由领主出面解决。小谿卡下设2名文书和“基根”(spyi-rgan,农奴总管),基根是4位定噶根布的头目,定噶根布对上效忠涅巴、基根指示,对下催派监督“差巴”等贫苦农奴缴纳赋税、支纳乌拉差役等。
三
综上所述,宗与谿卡作为噶厦地方政府的基层行政组织,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至民国时期,其内部形成的一套稳定有序、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在为其主子——三大领主服务的同时,为推动地方各机构的正常运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清季十三世达赖喇嘛向西藏全体僧俗民众颁布的文告中所言:“所谓宗本谿堆者,乃是受本处委派,以收差执法为主要职责并将公事晓谕于各方者”。[7]他们集派差收税、上传下达、处理案件、调解纠纷和戍边守关等职责于一身,这无疑为地方政府分忧解难、管理黎民庶众及保一方水土之平安等,有效地提高了执政效率,也节省了大量的行政成本。可见,此期由“400~500名被授予全权的僧俗官员在管理着拥有至少100万居民(奴隶——笔者注)、领土几乎与西欧一样大的西藏就不足为怪了。”[8]
当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于古已有之的西藏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农奴对农奴主的依附关系,领主实际占有的领地与中世纪欧洲、沙俄和封建日本时代的采邑非常相似,而穷苦农奴赖以生存的耕地又被“政教合一”地方政府、贵族和寺院各占约三分之一,他们有任意封赐、没收或支配的权力;加之不置可否的由三大领主豢养的宗本、谿堆们,由于其蔑视、欺诈、贪婪的本性,他们往往依靠手中握有的些许权力,恣意压迫鱼肉普天下的农牧奴。而受剥削者既无生产资料又毫无人身权利,完全被农奴主占有、奴役和驱使,听天由命,这是西藏奴隶制社会的诟病根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代人类文明曙光的到来,最终腐朽、黑暗、野蛮、残酷的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
[1] 张羽新.清朝治藏典章研究[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p42
[2] 〔意〕毕达克著.沈卫荣、宋黎明译,西藏的贵族与政府[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p11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研所、中央民族大学藏学所合编.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p270
[4] 扎西旺都.西藏历史档案公文选·水晶明鉴[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p86、p67
[5] 西藏自治区政协法制民族宗教文史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23)[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p79
[6] 多杰才旦.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p203
[7]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西藏自治区历史档案馆.藏文史料译文集[M].1985年,p201
[8] 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年,p11
[责任编辑:林俊华]
Zong and Shiga of Tibet in the Chinese Republic
LIU Yong-hua
Zong (a distinctive style of fortress)and Shiga (estates) are the grass-roots level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that had early appearance, the longest existence and the most functions within the Tibet's political system. A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entire administrative system,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Tibet. By untangling the complex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Zong and Shiga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a variety of historical resources,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and articulate Zong and Shiga's sphere of responsibilities and how they functioned as a political body at the time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Zong Bong;institutions;system
K251
A
1674-8824(2017)03-0014-05
刘永花,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北京海淀,邮编: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