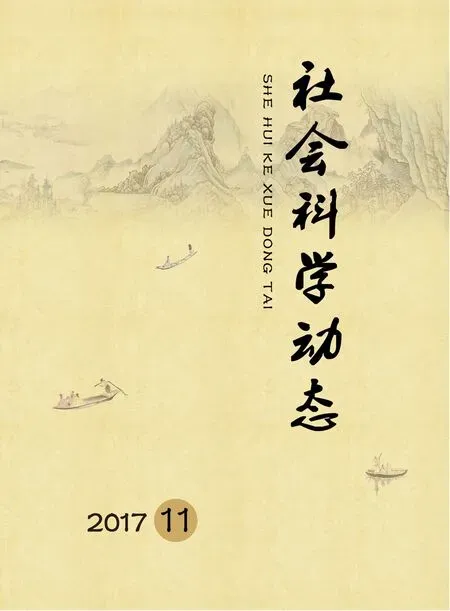论杨万里诗风多变及诚斋体形成的原因
龙珍华
论杨万里诗风多变及诚斋体形成的原因
龙珍华
杨万里诗风多变,缘于对诗歌本体的执着追寻,从而最终形成别开生面的“诚斋体”,在南宋诗坛独树一帜。诚斋秉持“矫天下之具”的诗教观,一方面强调诗歌作为现实批判工具的教育意义,另一方面又肯定了诗歌的抒情特征与审美价值,认为诗歌能“钩天下之至情”,让人产生“愧”的情感体验,从而达到“矫”不善者的目的。杨万里认为,诗之本体就存在于这种“去词去意”、微婉而讽的深味之中。“诗味说”体现出诚斋的诗美理想与追求,也是其于长期创作实践中不断思考与总结的结果。在漫长的诗歌本体追寻历程中,诚斋始学江西而终于走出江西,与吕本中的“活法”理论以及陈师道等江西前贤之影响密切相关;其遍参诸家,尤喜唐诗,并力推晚唐之“异味”,经长期积累,在诗歌艺术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从量变到质变,终于到达“至法无法”的自由创作境界。可以说,“诚斋体”的形成体现了一代宋儒对于诗学真谛的不懈探求,以及务实通变的理学精神。
杨万里;“变”;诗歌本体;“晚唐异味”
作为宋诗一代大家,杨万里诗歌数量极其丰富,在中兴四大诗人中,仅次于陆游,而其诗风更是多“变”,“变”几乎贯穿了杨万里一生诗歌创作的全过程。元代方回认为“杨诚斋诗一官一集,每一集必一变,……诗不变不进”①,历代论者对此几成定评。杨万里对自己诗风的多变也有说明,其《诚斋南海诗集序》云:“予生好为诗。初好之,既而厌之。至绍兴壬午,予诗始变;予乃喜,既而又厌之。至乾道庚寅,予诗又变。至淳熙丁酉,予诗又变。……嗟乎!予老矣。未知继今诗犹能变否?延之尝云予诗‘每变每进’,能变矣,未知犹进否?”②诚斋学诗刻苦卓绝,遍参诸家,其诗风转变的过程实为追寻诗歌本体的实践历程,即何为诗?诗存之于何处?何为真正的好诗?在寻求这些答案的过程中,诚斋诗风渐趋成熟。
一、何为诗
作为南宋重要理学家的杨万里,对于诗歌的认识深受理学影响,对于何为诗、何为好诗的问题,首先可从其有关“诗论”中寻求答案。
诚斋《心学论·诗论》曰:
《诗》也者,矫天下之具也。……盖圣人将有以矫天下,必先有以钩天下之至情,得其至情,而随以矫,夫安得不从?盖天下之至情,矫生于愧,愧生于议,议生于众。愧,非议则安;议,非众则私。安,则不愧其愧;私,则反议其议。圣人不使天下不愧其愧,反议其议也,于是举众以议之,举议以愧之,则天下之不善者不得不愧。愧斯矫,矫斯复,复斯善矣。
此《诗》之教也。
诚斋认为《诗经》是圣人矫正天下不善的工具。其虽然着论于狭义之“诗(《诗经》)”,且带有经世致用的理学色彩,但是这篇诗歌理论的纲领性文章却从宏观上指出了诗歌创作的本质和目的,即抒写人生之“至情”,通于至道而止于至善。一方面,诚斋强调诗歌作为现实批判工具的教育意义,似乎忽视了文学作品自身的艺术审美价值,但另一方面诚斋认为诗歌能“钩天下之至情”,让人产生“愧”的情感体验,从而达到“矫”不善者的目的,这与诗歌审美又相关联,肯定了诗歌的抒情特征与审美价值。
那么怎样的诗才是好诗?或者说怎样的诗歌才能“钩天下之至情”,从而起到矫不善者的目的呢?诚斋《颐庵诗稿序》云:
夫诗何为者也?尚其词而已矣;曰:善诗者去词。然则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诗者去意。然则去词去意则诗安在乎?曰:去词去意,而诗有在矣。然则诗果焉在?曰:尝食夫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暴公谮苏公,而苏公刺之,今求其诗,无刺之之词,亦不见刺之之意也。乃曰:“二人从行,谁为此祸?”使暴公闻之,未尝指我也,然非我其谁哉?外不敢怒,而其中愧死矣。《三百篇》之后,此味绝矣,惟晚唐诸子差近之。《寄边衣》曰:“寄到玉关应万里,戍人犹在玉关西。”《吊战场》曰:“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折杨柳》曰:“羌笛无须怨杨柳,春光不度玉门关。”《三百篇》之遗味,黯然犹存也。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予不足以知之,予敢言之哉?
此序中,诚斋不仅详细阐述了他对诗歌本体的认识,即诗之本体存在于“去词”、“去意”后的深“味”之中。诚斋用生动的比喻对此进行了解释。如糖与“荼”(茶)的给人的不同味觉感受,说明了诗歌艺术的魅力并不在于其文词的藻饰和意义的直达,而在于蕴含于词意之外的“味”。从诗歌创作的角度来说,诗不应像糖一般肤浅而了无回味,而应含蓄委婉地表现出味外之味、弦外之音,应像茶一样“苦未既,而不胜其甘”,才有令人回味无穷的魅力和美感。对于读者而言,诗之“味”如“荼”之味,并非停留在表层、浮面的外在形式,而是“词”与“意”所酿成的深沉之味,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须经反复涵咏玩味才可领略。故要领悟某首诗的妙处,就必须领会其词意之外的旨味,而不能仅从词意中去搜求。所谓“诗味”,就是包蕴在诗歌深层境界中的意蕴。这与诚斋“愧斯矫,矫斯复,复斯善”的诗教观趋于一致,诚斋主张微婉含蓄地讥刺批判,令不善者“愧”而“矫”,复于道,止于善,而非浅露急切的直接怨刺,正如《诗经·小雅·何人斯》一诗中周朝卿士苏公刺暴公那样,虽无刺之之词,亦不见刺之之意,却令暴公产生心理暗示:“未尝指我也,然非我其谁哉”,以致外不敢怒,而“其中愧死矣”。这种微而能显、婉而多讽的批判方式,使诚斋“矫天下之具”的诗教观并未将诗歌艺术沦为纯粹的教化工具,而使其对诗之本体的认识更趋于诗歌审美的高度。
同时,诚斋所谓“去词去意”,并非将作为诗之载体的语言艺术和思想内容都去掉,事实上,诚斋喜好文词如好美色,“至于好诗,又好文词中之尤者也”(《唐李推官披沙集序》),而且认为,“唐律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古今作者皆难之”③,可见诚斋强调的是,诗歌与其他文体的艺术审美形式有别,作诗不能像写其他文章那样直接道出,而应符合“微婉显晦,尽而不污”的美刺原则。这样的诗歌,才是符合风雅传统,能微婉而讽的“矫天下之具”,这样的诗歌才最有诗“味”,而富有这种“诗味”的诗才是真正的好诗,可惜《诗经》之后,这种“诗味”已绝,“惟晚唐诸子差近之”。
当然,“诗味说”并非诚斋首创,以“味”论诗在古代诗学中由来已久。“味”原指人的酸甜香臭之感,《左传》云:“天有六气,降生五味。”④《国语》曰:“和五味以调口。”⑤后来,“味”被引进文学批评领域,如王充以美味来比喻“尧舜之典”,“孔墨之籍”(《论衡·自纪》);陆机以“味”批评文章:“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以去滥,阙太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泛。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⑥。这样,“味”与人们的审美活动和审美感觉联系起来了。到刘勰、钟嵘诸人,“味”完全变成具有特定涵义的审美概念,“吟咏滋味,流于字句”⑦;“众作之有滋味者”⑧。唐人以味论诗者尤多,如刘禹锡、白居易、司空图等。在钟嵘和刘勰对诗味的理论加以阐述以后,司空图则把它提到突出的理论地位,形成了以“诗味说”为核心的美感形式论,所谓“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与李生论诗书》),在他看来,对于诗歌的领悟,必须注重“味”,从而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和“象外之象”的“三外”理论,要求诗歌之美不仅求诸文词之内,更须辨之于文词之外,即“味外之旨”。杨万里“诗味说”与司空图的意见颇为一致,但也明显有别。司空图之“味”所指主要为诗歌之风格,诚斋所考察的是诗歌之本体,其所谓诗之“味”是指诗歌言辞之外(“去词去意”)所暗含的情趣、意味才是诗歌真正寄寓之所在。诚斋《江西宗派诗序》云:“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江西之诗,世俗之作,知味者当能别之矣。”(《诚斋集》卷79)意思是说,江西诗人、江西之诗,之所以归于一派,是因其诗歌之本体具有一致性,而非江西之诗在词意等形式技巧上的共同之处,即“以味不以形也”。
以“味”论诗虽古已有之,但将“味”视为诗歌之本体所在,赋予风格以外的本体意义,当为诚斋之所独创。以前论者多将“味”用以形容诗歌之审美风格,而诚斋之“诗味说”更多地强调了诗歌自身的创作规律和特点,以及诗歌的审美感受与价值。
二、江西之“穷”与诚斋之“变”
至于诗之“味”从何而来,其“去词去意”后的“味外之味”如何觅得,诚斋“诗味说”的形成是在其诗歌创作实践中不断思考和总结的结果。其对诗之本体的追寻经历了漫长历程。其诗风之变是从其力图走出江西穷途困境开始的。
诚斋是位多产的诗人,除去其自云所烧掉的“少作千余篇”外,自36岁始存诗,至80岁去世,杨万里共有诗作4200余首,编成9个诗集,即《江湖集》、《荆溪集》、《西归集》、《南海集》、《朝天集》、《江西道院集》、《朝天续集》、《江东集》、《退休集》等。其“一官定一集”,几乎成为他人生经历的纪实写照,从总体上看,可大致反映其诗风转变的历程,亦即对于诗歌本体的追寻过程。而诚斋对于诗歌本体的拷问又是从其欲摆脱江西束缚开始的。
中国古典诗歌源于《诗》 《骚》,兴于汉魏而盛于唐。继唐诗高峰之后,宋诗要求得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在唐诗的基础上求新求变。宋诗在各个发展阶段中既有内在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变化。北宋中期以后,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对宋诗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当时,黄门弟子众多,到南宋,江西诗派的影响几乎笼盖了整个诗坛。而黄庭坚“脱胎换骨”、“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创作理论,导致江西诗派诗人误入故纸堆里觅诗句的歧途。在创作材料的选择上,常于佛经、语录、小说等杂书里去寻找冷僻的典故、罕见的字词,还有意造拗句、押险韵,往往导致作品内容的空虚而严重脱离现实。这个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自觉结成的诗歌流派,始于对西昆体诗风的否定和革新,可是又成为诗歌创作中新的形式主义,许多富有创新精神的诗人渐渐不满这种窠臼,而欲摆脱江西诗风的束缚,江西诗派最终走向末路势在必然。
与当时多数诗人一样,初入诗坛的杨万里也成为江西诗派中的一位“文艺青年”。诚斋青年时期是学习江西派的,其称“参透江西社,无灯眼亦明”(《和周仲容春日二律句》其二);又说“要知诗客参江西,政似禅客参曹溪。不到南华与修水,于何传法更传衣”(《送分宁主簿罗宏材秩满入京》),都说明了诚斋与江西诗派之渊源,但其最终又欲摆脱江西诗派的束缚。《诚斋江湖集序》云:
予少作有诗千余篇,至绍兴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体也。今所存曰《江湖集》者,盖学后山及半山及唐人者也。予尝举似旧诗数联于友人尤延之,如“露窠蛛恤纬,风语燕怀春”,如“立岸风大壮,还舟灯小明”,如“疏星煜煜沙贯日,绿云扰扰水舞苔”,如“坐忘日月三杯酒,卧护江湖一钓船”。延之慨然曰:“焚之可惜。”予亦无甚悔也。然焚之者无甚悔,存之者亦未至于无悔。
由于杨万里早年是江西诗派的忠实门徒,对江西前辈极度仰慕,使得其早期诗歌几成江西诗的刻意模仿之作。因受其师王庭珪不满江西诗派的影响,杨万里对江西诗派也显然不满,并有力证实了其摆脱江西诗派藩篱的强烈愿望,其绍兴焚诗行为便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绍兴焚诗一直被看成诚斋与江西诗派告别的宣言,但尽管其努力摆脱江西诗派的束缚,而自成一体,诚斋似乎始终与江西诗派难脱干系。钱钟书先生便认为:“他对黄庭坚、陈师道始终佩服,虽说把受江西诗派影响的‘少作千余’都烧掉了,江西派的习气也始终不曾除根,有机会就要发作。”⑨这种说法不无道理,诚斋晚年亦时念江西,犹在“足痛无聊块坐读江西诗”,对其学诗的初恋对象,实难忘怀。他的诗歌也确实时有江西之遗韵。但诚斋在学诗过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之后,随着对江西诗歌的渐渐参透,发现了江西诗派创作的弊端,意识到刻意模仿并非创作之正路,便喟然叹曰:“是得毋类韩子所谓俳优者之辞耶?”因而烧掉自己的江西诗,丢掉优孟衣冠式的诗歌创作方法,正是否定自己而重新创造的开始。
其实,杨万里作诗从江西入手,确是时代使然,在江西诗派的影响遍及整个南宋诗坛之际,“杨万里学江西派与背弃江西派,除个人创作的自觉与变化外,与当时的社会政治以及江西派自身地位的升降有关”⑩。诚斋登上诗坛之际正是江西诗派独领风骚之时,其代表诗人虽然大多已经去世,但他们的影响还广泛存在。江西诗派虽出唐诗之藩篱,力除五代绮靡柔弱之余风,而重构“宋调”之美学传统,但至南宋中后期,因其后继者天分不足,才学不济,江西诗派诸如炼字琢句的诗学主张因过于刻板凝滞而成为诗坛之痼疾。作为理学家的诚斋,既深知江西诗派之弊病,便秉持“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通思想,欲求新求变以突破江西诗派之穷途困厄。
《诚斋荆溪集序》云:
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学之愈力,作之愈寡。……戊戌三朝,时节赐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试令儿辈操笔,予口占数首,则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
在序言中,杨万里说明了自己学诗的经过,以及从艰涩“轧轧”到酣畅“浏浏”的创作发展历程。其诗之“变”有自觉,亦有不自觉。自觉为其对自己刻意努力结果的清醒认知,不自觉体现的是他创作实践经验积累的质变,如其《诚斋朝天续集序》所云:“昔岁自江西道院召归册府,未几而有迎劳使客之命,于是始得观涛江,历淮楚,尽见东南之奇观,如《渡扬子江》二诗,余大儿长孺举似于范石湖、尤梁溪二公间,皆以为余诗又变,余亦不自知也。”
根据自序,杨万里的诗歌创作主要经历了四次变化:一是绍兴壬午;二是乾道庚寅;三是淳熙丁酉、淳熙戊戌之间;四是绍熙元年前后。但由于诚斋诗集自序与诗歌创作的实际时间并不一致,有人认为这种时过境迁的自序并不十分可信⑪。钱钟书《宋诗选注》即云:“他把自己的创作讲得层次过于整齐划一,跟实际有点儿参差不合。”⑫结合杨万里诗歌的具体创作实际,学界一般将杨万里的诗歌创作分为四个时期:模仿期,即绍兴三十二年以前,主要学习江西体诗歌;过渡期,即模仿与创新的探索阶段,自绍兴三十二年至淳熙四年,学习陈师道五言律诗、王安石七绝和唐人绝句,间有独创风格之诗显现;形成期,淳熙丁酉、戊戌以后,“诚斋体”已趋成熟;发展变化期,即绍熙元年十一月以后,基本风格定型后的进一步拓展和新变期⑬。
关于杨万里诗歌转变的时间与分期一直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对于诗人自言学诗之经过,拙文认为应当是可信的。《诚斋荆溪集序》所叙应是诚斋诗歌创作心路历程的真实独白,其“学”与“不学”之间的抉择决非简单的取舍,而是一个对诗歌本体执著而艰难的追寻历程。
三、“活法”前贤之影响
有了强烈的诗歌革新的愿望,诚斋还转益多师,吸取前贤之经验,学习前辈之精华,尤其得益于吕本中、曾几的“活法”思想,于艰苦的创作实践历程中,深得“活法”之真谛,以此走出江西诗法之藩篱。
事实上,对于江西诗风的扬弃与否定,其根本动因在于作家内在的嬗变,也只有这种内在的动力,才能根本摆脱江西藩篱。可以说,杨万里应是这股嬗变力量中当之无愧的佼佼者。其之所以得以摆脱江西诗派束缚,与江西诗派本身内部的革新力量有关,特别是受到吕本中等人的“活法”理论的启迪,以及江西诗派“三宗”之一陈师道诗风的影响。
《江西诗社宗派图》作者吕本中,是江西派诗风继承与新变的关键人物,对于杨万里的诗歌理论及创作有着重要影响。吕本中被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列入江西诗派,更被南宋诗人赵蕃视为江西诗派的正宗。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认为其诗法出自黄庭坚。吕本中在南宋初地位就很高,刘克庄将他和陈与义一起并称为南渡初期诗坛的“大家数”。陆游云:“其诗文汪洋闳肆,兼备众体,间出新意,愈奇而愈浑厚,震耀耳目而不失高古,一时学士宗焉。”⑭在吕本中的诗集中,也常能见到一些颇近黄庭坚老健风调的诗歌,但他绝不是简单地模仿山谷,而是既学山谷的严密深邃,又学东坡的豪放达观及其行云流水般的语言,从而形成了轻快自然的独特诗风。江西派诗人谢逸曾说:“以居仁诗似老杜、山谷,非也。杜诗自是杜诗,黄诗自是黄诗,居仁诗自是居仁诗也。”⑮说明吕诗并未一味步山谷之后尘。
吕本中之所以首先打破了单纯模仿黄庭坚的诗歌风气,是因为他认识到江西诗歌艰涩的缺点,感到了江西诗歌弱点所带来的危机。他说:“《楚辞》、杜、黄,固法度所在,然若不遍考精取,悉为吾用,则姿态横出,不窘一律矣。如东坡、太白诗,虽规模广大,学者难依,然读之使人敢道,澡雪滞思,无穷苦艰难之状,亦一助也。”(《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这是他给江西诗人曾几的书信中所言,其告诫曾几要兼学苏黄,遍参诸家,不要偏废而使诗歌创作走入艰涩穷苦之狭路。可见,诚斋“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学李白、苏轼等,明显为受吕本中影响下的学诗之路。可以说,诚斋认识到江西诗歌的缺点,而敢于大胆去创新变革,吕本中给他的启示作用不容忽视。诚斋诗风多变与吕本中“活法”理论的影响不无关系。
关于“活法”说最早的完整表达,可见于吕本中为其友夏倪诗集所作的序言:
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谢玄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近世惟豫章黄公首变前作之弊,而后学者知所趣向,毕精尽知,左规右矩,庶几至于变化不测。然予区区浅末之论,皆汉魏以来有意于文者之法,而非无意于文者之法也。⑯
序言反映了吕本中对于自然平易诗风的倡导与追求,其欲融合苏、李与黄、杜,借助“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之所谓“真活法”,以及禅悟的思维方法,以救江西诗派之困,并希企进入诗歌创作的自由境界。吕本中曾批评黄庭坚诗歌“有太尖新、太巧处”(《童蒙诗训》),并且主张因兴而发,“惟不可凿空强作,出于牵强,如小儿就学,俯就课程耳”(《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
吕本中“活法”说的提出,标示着江西诗风出现了根本转机,说明他已经认识到律度法式与诗歌创作主体自由之间的关系,并论及主体创作的相对自由问题。一方面这是响应了南宋文学思想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江西诗派作家内在变革的结果,因此,“‘活法’后来在杨万里的时代成为时代的诗歌精神,也是宋诗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⑰。“活法”诗论影响范围之广,甚至波及豪放词家,比如辛弃疾就有“诗句得活法,日月有新功”的经验之谈,后又经曾几的发展而更趋完善,但真正体现这种“活法”精神的却是杨万里。诚斋无疑是对吕本中“活法”理论实践得最好,体现得最为充分的诗人,但诚斋“活法”与吕本中“活法”并不完全一样⑱。也许因为吕本中一直被当作江西派诗人,杨万里并未明确表示要学习吕本中,但其诗之“活法”无疑受到吕本中的启发,“诚斋体”的形成与此也不无关联。因此,杨万里摆脱江西诗派樊篱的要求与努力,既是南宋诗歌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时代创作精神启迪的结果,特别是吕本中的先锋作用,当然更是诚斋自身求变求新、对诗歌本体不倦探索的诗学精神使然。
同时,诚斋诗序中又明确提到自己曾经“学五字律于后山”,说明诚斋诗歌也受到后山的影响。陈师道作为江西诗派的“三宗”之一,在江西诗派中有着很高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后山虽然推崇黄庭坚,但后山诗风与黄庭坚有很大区别,尤其是五言诗,其多写亲情和日常生活,感情真挚,用典较少,较黄庭坚写得平易质朴,如其《别三子》、《示三子》等。陈后山有不少抒写飘旅思乡的作品,语言质朴而情感真切,往往能用典型的细节渲染出独特的心理体验,令诚斋很是仰慕。诚斋曰:“谁谓陈三(按:指后山)远,髯张下笔亲。夫何此意合,恐有宿生因。我岂慵开眼,年来寡见人。更烦雕好句,割取楚江春。”(《仲良见和再和谢焉》其二)作为江西诗派之“宗”,陈后山对于诚斋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其学习杜甫“遇物而奇”(《后山诗话》)的创作理念对诚斋影响可谓深远。
事实上,诚斋不少诗作,就明显得后山之长,如《夜雨泊新途》:“乱眼才迷树,回头已湿沙。萧萧打篷急,点点入船斜。此夕初为客,何时却到家。余樽曾卧否,唤取作生涯。”诚斋此诗抒情写景,体味入微,语浅意深,真切感人。尤其“此夕”、“何时”两句更是深得后山神髓而耐人寻味。诚斋五律也明显有学后山五律之痕迹,如《腊夜普明寺睡觉二首》其一:“旅梦忘为客,檐声忽唤愁。亲庭未差远,佛屋不胜秋。只么功名是,如今悟解不。十年行路饱,谁不遣吾休。”全诗不用典故,只是选取日常生活意象进行烘托,抒写腊夜客居佛寺之愁苦以及宦海奔波的艰辛,自然平易,质朴感人,颇有后山神韵。
四、“晚唐异味”之体认
在考查诚斋诗论及诗歌时,不难发现其对唐代诗学理论的回溯,以及对于唐诗审美趣味的趋向。诚斋广泛学习唐人诗歌,其《送彭元忠县丞北归》云:“学诗初学陈后山,霜皮脱尽山骨寒。近来别具一只眼,要踏唐人最上关。”《读唐人及半山诗》又曰:“不分唐人与半山,无端横欲割诗坛。半山便遣能参透,犹有唐人是一关。”诚斋明显对唐诗十分喜爱,以为“诗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黄御史集序》),而尤好晚唐之“异味”。
唐代诗人中又以李白对杨万里诗歌影响极大。诚斋不仅对李白极度向往和崇拜,而且处处模仿和学习。如关于《重九后二日同徐克章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一诗,罗大经《鹤林玉露》云:“余年十许岁时,侍家君竹谷老人谒诚斋,亲闻诚斋诵此诗,且曰:‘老夫此作,自谓仿佛李太白。’”⑲诚斋七言古体、七言歌行等受李白影响尤大,如其《行路难》,既有李白诗歌之风韵,又有诚斋之个性与变化。在诗歌风格上,亦时时表现出李白式的豪雄俊逸之气。刘克庄说:“放翁学力也,似杜甫,诚斋天分也,似李白。”⑳清人汪琬亦云:“诗印频提教外传,入魔入佛总超然。放翁已得眉山髓,不解诚斋学谪仙。”㉑都道出了杨万里与李白诗歌之渊源。
对于晚唐诗歌,诚斋更是旗帜鲜明地表示激赏。《读笠泽丛书三首》其一云:“笠泽诗名千载香,一回一读断人肠。晚唐异味谁同赏,近日诗人轻晚唐”,江西诗人“轻晚唐”,杨万里却高扬起回归唐诗审美特色的旗帜,之所以特别推崇晚唐诗尤其是唐人绝句,钱钟书先生认为,除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等人以外,“晚唐诗人一般都少用古典,而绝句又是五七言诗里最不宜‘繁缛’的体裁,就像温、李、皮、陆等人的绝句也比他们的古体律体来得清空;在讲究‘用事’的王安石的诗里,绝句也比较明净。杨万里显然想把空灵轻快的晚唐绝句作为医救填饱塞满的江西体的药。”㉒诚斋之爱晚唐诗,显然与晚唐诗歌独有的神韵有关。清叶燮认为晚唐诗“极幽艳晚香之韵”(《原诗》),其思致幽密而韵味深长,故诚斋之好唐诗,实则好晚唐之“异味”。其深层原因是欲将晚唐之“异味”来作救治江西顽疾之良药,从而回归风雅诗学之传统。
诚斋所谓“诗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黄御史集序》),是因为晚唐之“工”实为“属联切而不束,词气肆而不荡,婉而庄,丽而不浮”(《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极具浑然圆润之态,隽永闲雅之气,是一种成熟的审美典范,与江西诗派的“锻炼之工”具有本质的不同,其虽无李杜之雄浑外显,却正好体现了“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的儒家诗学传统,这也是晚唐“异味”之所在。“晚唐异味”因“融合功利与审美的双重性征,笔法含蓄、意境深远、温柔敦厚”㉓,而直溯风雅传统。
同时,诚斋之所以学半山,也与其所好“晚唐异味”有关。诚斋曰:“五七字绝句最少,而最难工,虽作者亦难得四句全好者,晚唐人与介甫最工于此。”㉔其《读诗》又云:“船中活计只诗编,读了唐诗读半山。不是老夫朝不食,半山绝句当晚餐。”诚斋对王安石诗歌尤其是七绝的热爱与推崇,较之其他任何诗歌流派及诗人都要多。诚斋之所以“学七字绝句于半山”,“晚乃学唐人绝句”,其由有二:
首先,在五言、七言各种诗体中,七言绝句是最易写得活泼生动的一种。而王安石七绝,尤其晚年之作,风格平淡隽永,语言简练,思致高远,表现灵活自如,与早年以文为诗和雄峻峭厉之风格不同。黄庭坚曾说:“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咏之,便觉沆瀣生牙颊间。”㉕诚斋刻意学习王安石七绝,要矫正江西派瘦劲、奇崛、拗峭的诗风。
其次,王安石的七绝又可直溯唐人。其《答徐子材谈绝句》云:“受业初参且半山,终须投换晚唐间。《国风》此去无多子,关捩挑来只等闲。”参半山,参晚唐,即可直追风雅传统。而半山七绝之精丽、轻细、圆熟,也是深受晚唐诗人影响的,其《悟真院》等诗颇具晚唐诗韵。特别是用绝句怀古、咏史、感时,其议论之纵横疾驰、气势强劲,又远胜中晚唐诸家。
因此,杨万里选择七绝作为摆脱江西束缚,创建自己风格的突破口,其一生诗作,也以七绝为主,七绝是“诚斋体”最重要的载体,最能体现出“晚唐异味”,而能追“《国风》 《小雅》之遗音”。
除此以外,诚斋还学东坡、学香山等等,在遍参诸家,不断学习与探索后,其诗歌艺术取得了长足进步,也渐渐认识到“闭门觅句非诗法”(《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山中物物是诗题”(《寒食雨中同舍约游天竺得十六绝句呈陆务观》),终于体会到“无法无盂也无衣”(《酬阁皂山碧崖道士甘书怀赠》),“至法无法”的自由境界,从而摆脱了江西诗歌创作之窠臼,而达“浏浏焉”“欣如焉”的自由状态,终究成就了独具一格的“诚斋体”。
要之,“诚斋体”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诚斋“忽若有悟”而臻诗歌艺术创作的自由境界,也绝非简单的一时之顿悟,而是一个转益多师,经长期积累,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杨万里诗风多变,缘于对诗歌本体的执着追寻,体现了一代宋儒对诗学真谛的不懈探求及务实通变的理学精神。
注释:
① 方回:《瀛奎律髓汇评》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② 杨万里:《杨万里诗文集》卷80,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4页。
③㉔ 杨万里:《诚斋诗话》,《历代诗话续编》上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9、141页。
④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22页。
⑤ 左丘明:《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15页。
⑥ 陆机:《陆机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页。
⑦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553页。
⑧ 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页。
⑨⑫㉒ 钱钟书:《宋诗选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53、256、254页。
⑩⑰ 张瑞君:《杨万里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7、220页。
⑪ 郭绍虞:《宋诗话考》、莫砺锋:《论杨万里诗风的转变过程》等都有较为翔实可信的阐述。
⑬ 参见张鸣:《诚斋体与理学》,《文学遗产》1987年第3期;王琦珍:《论杨万里诗风转变的契机》,《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莫砺锋:《论杨万里诗风的转变过程》,王水照等编:《首届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250页;张瑞君:《杨万里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216页。
⑭ 陆游:《吕居仁集序》,《渭南文集》卷14,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766页。
⑮ 吕本中:《东莱吕紫微师友杂志》引谢逸语,《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753页。
⑯ 吕本中:《夏均父集序》,《历代诗话续编》上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5页。
⑱ 周汝昌:《杨万里选集·引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4页。
⑲ 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3—184页。
⑳ 刘克庄:《后村诗话》,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6页。
㉑ 汪琬:《读宋人诗》,《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63页。
㉓ 彭维锋:《徘徊于庙堂与禅境之间》,《天中学刊》2005年第3期。
㉕ 参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第372页。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试点学院项目 “杨万里诗论研究”(SD1737)
I206.5
A
(2017)11-0098-07
龙珍华,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430205。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