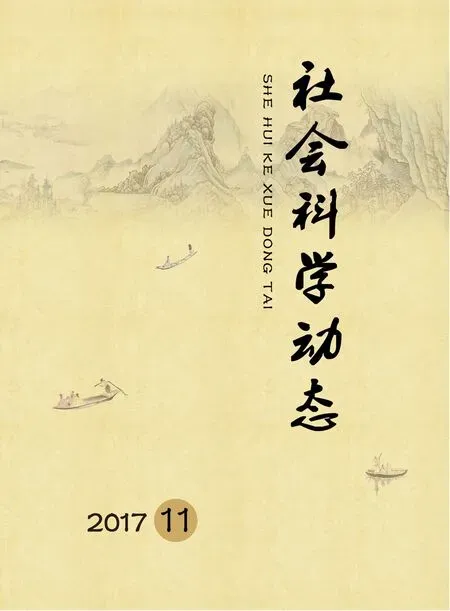总体性社会与即时性治理
——探源“社会底蕴”
门 豪
总体性社会与即时性治理
——探源“社会底蕴”
门 豪
在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内部,长期维系的大一统帝国形态具有典型的结构刚性,形塑出多元融汇的华夏文明与家国同构的宗法制传统。在实际的权力运作与政策执行中,应然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国家与民众的关系充分地浸润于在地场景,促使了结构分化与再生产的产生。地方政府为达政策目的和执行效果而采取的“权宜性”的实践逻辑,带来了行政手段的变通,也带来了“行政过程软化制度刚性”的效果。这为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总体性结构中持续的制度供给及地方治理创新提供了合法性来源。市场嵌入和经济转轨后,由开放促改革的范式概未脱离既有路径,转型社会因循一元化管理与即时性治理互嵌的逻辑,促使 “自上而下”的制度刚性与“自下而上”的地方运作弹性交织与并构。这是“变中之未变”与“恒常在场”,亦即“社会底蕴”。
社会底蕴;总体性社会;社会结构;社会治理
一、引言
当代马克思主义学派新锐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在对数国和地区不同形态的社会经验进行分析后认为,“在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中存在众多异质性的团体、网络及社群,它们为了各自不同的目的而组建,不同成员通过各种联带而结合。虽然这种多元差异可能会营造出论辩与社交的公共领域,但想要达到对国家和经济有效控制的需求,它似乎无法成为构筑内在一致权力的坚实基础……为了得到创新及高效投资,我们需要受获利动机驱使的资本主义厂商的存在。不过唯有权力集中、相对隔绝于民众压力及特殊利益之外的专业化国家机器,才能正确地以有效的技术管制经济”。①当前,无论国别,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关系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理论探讨的前提。这种趋势在利益调整期的转型社会尤为凸显。中国的经济政治改革就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整。②当代中国社会从建国后的国家强势入场,市场、社会几近缺场,逐步过渡到改革后市场局部嵌入,国家持续回应新旧群体紧张及阶层矛盾并解决由此带来的新问题。可以说,分化与整合共存且相互形塑是社会转型发生的背景和基本脉络。③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治理方法不利于长期稳定,反而会带来更多、更复杂的非预期后果。看待转型与治理问题,社会文化及价值伦理应当被纳入分析的过程。以想当然的因果推理达致逻辑自洽来进行决策,只能是纸上谈兵。汤因比认为,文明是人类面对自然挑战的应战方式。当前,我国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新技术革命等多个时代的社会形态同时存在,不同时代的诉求同时发生,这就意味着多元文化的交汇与融合,任何单一文化形态都不可能独立地维持和延续,这也说明了当前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如西方文化缺少与本土适应的要素,传统文化有着同当代核心价值不相容的部分,革命文化又生根于特定的时代基础之上。因此,出现激进民族主义、西方自由主义、功利务实主义等并行交错的文化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④可以说,文化的历时性生长催生出制度,制度的空间延展形塑了特定的地域文化。文化与制度不可分割,两者共同作用形成“社会底蕴”。如果说制度是先验的,那么它必定是在文化修饰之后才得以落地的;如果说文化是结构化了的,那么作为制度“执行者”角色的文化,应与特定的时空情境相契合。
二、何以成为转型社会的“恒常不变”?
杨善华等通过大量田野经验分析,认为“社会底蕴”是指在历史变迁中,中国社会自发保存的那些具有相对稳定特征的“恒常”。它可以表现为意识层面的结构性观念,也可以表现为一些非正式的制度(风俗习惯),或者是与道德伦理相联系的行为规范。利用“生活智慧”、“家本位文化”、“人缘口碑”等考察社会历史进程与现代性变迁之间的互动机制,可以发现深具传统特性的“社会底蕴”并非以一种消极对抗的形式出现,而是不断地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并由此创造出建设性和包容性的面貌。⑤探讨“社会底蕴”,是经由历史反思当下问题的一种方法。
从某一视角出发,借助个案研究方法或实证研究方法来对潜藏于深层社会背景和整体结构中的“社会底蕴”进行发掘,是一条反思当下问题的可行路径。这样我们才能在带有温度的、具体可感的现象之中保持价值理性,认知社会事实发生的可能性与发展的方向与可能,进而把握群体事件的发生规律和演进机制。对“社会底蕴”的探讨,无论是出于“诊断社会”的目的,对积聚的社会症结“开病历”,还是为应然社会建设寻求依据,为理想型建构作政策建议,或是对“小型社会试验”、“干预社会”保持贴合实践的预判而言,都是基础。
地域不同,“社会底蕴”亦相互区别,特别体现在制度选择及其演进路径上。即便制度背景和结构相同或相当的两地,因行动者的长期选择与“自我实现预言”的累积,也会导致不同的地方变异。“社会底蕴”有别于“硬质”的制度和社会结构,它是在二者之上“情感化了的”时空集成。国家可以设定制度形态,框架结构亦可由外力塑造,但具体执行和路径选择,却需要结合特定社会历史以及行动者的感性经验。简言之,外部强制的“力量”与内部认同的“情感”,二者共同作用激发出“社会底蕴”,并且这一过程必须是持续的、稳定的且结构化的社会事实。通常我们容易挖掘“硬质”的社会结构,这是社会的“骨骼”,如政治结构——政党、执政者和民众;经济结构——上层、中产阶层及底层。再就是“软性”的社会文化,这是社会的“肌肉”,如“战斗民族”、“和合中庸”、“彪悍民风”。“社会底蕴”,是社会的“血液”,是不易辨识、最为隐蔽的社会“潜在”,是不易捉摸的流态,更微观而难以察觉,嵌入身体之中。唯以“骨骼”、“肌肉”作参照,对这种流态的考察才有意义。社会人在某一时段的行动中,更多地采用日常的行动视角,而非花费时间考虑结构或规范的束缚。这是实践模式化后的身体无意识,不假思索导致的一种基于当下的权宜性行动逻辑,或曰“生存逻辑”,这是“社会底蕴”微观外化的结果。较之于外部他律性的法律和自我约束的道德,“生存逻辑”是共同体属性因习相生、因习相成的行为规则丛,是行动者身体文化痕迹及内化习俗的再生产。将微观生存逻辑放置到社会背景中考察,可投射出其所在社会的“社会底蕴”。当然,即便在同一时空条件下,由于人们所在阶层等的不同,角色定位和行动空间的差异,“生存逻辑”的不同,导致与之相对应的、作为局部存在的“社会底蕴”也不尽相同。因此并不难理解“社会底蕴”在“同一时空的变身”,其实是身份分化的结果。那么,在现代社会甚至后现代社会,最吊诡的问题是,何为“恒常不变”的“社会底蕴”呢?不难发现,“社会底蕴”多少带有静态的“理想型”色彩。同时,从不同维度切入“生存逻辑”,如微观政治运作、礼物交换、互惠方式甚至“中国式关系”,视角不同映射出的“社会底蕴”亦不同。处在变动现代性中的人,他们的“生存逻辑”相较于传统,会更多地启动、萌生、照亮、烘托“社会底蕴”。可以说,“社会底蕴”是反思现代性的一把标尺。在稳定的小农社会中同样存在“恒常不变”,不过,处于经验世俗的人无法发掘“习以为常”而处于自在状态。因此,“社会底蕴”是一种历时态的跨文化视角,是比较历史社会学的产物。由此看来,“社会底蕴”之于“生存逻辑”,同“场域”与“惯习”二者的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处。
本文使用“总体性社会”和“即时性治理”两个概念来缩小、圈定、绘制“社会底蕴”的图像。秦朝开创了大共同体一元化统治和压抑小同共体的法家传统⑥。自此,书同文,车同轨,“中国”这个概念更多地作为文化称谓出现,其中“天下”观是中国文化最具特色,最具宏大愿景的一面。“天下”意识着眼于道德动力和文化整合,展现出对人类与世界的整体关切。⑦任何制度背后都有一套价值体系在支撑,中国封建官僚及其大一统政府所获得的支持,主要来源于社会习俗和社会价值。费孝通指出,在中国,政权和社会威权是很少相合的。政权是以力致的,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关系,而威权是社会对个人的控制力。⑧“唯一正统”的官方话语与持续的文化营造,对传统社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大一统话语几近等同于一切社会事务开展的背景,这种脉络是“大意识形态”的拓展。“皇权至上”是社会关系、经济生产关系等的前提。儒家作为“标杆”、“正统”与包容性文化的代表,获得了皇权支持并与之相互型构,独居“人间正道”的霸主地位。在文化选择中,“政治合法”成为亚文化进入正统的入场券,皇权将“仁孝悌义”等为代表的话语体系构建成为文化支持系统。在偌大的帝国体系中,讲宗法、重礼制,“小家”和“大国”相连结,家国同构与姻亲连带是典型的关系特征。对皇权正统的绝对服从是个体合法性的外部来源,“大赦天下”、“祭天拜祖”等事务系统和政治架构认同成为日常生活的主线。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种家庭内外均联系紧密的空间,长久维系了庞大的依附性文化系统与社会认同。在这样的文化结构中,从某种程度而言,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差别是极小的,个体是相当同质化的存在。近现代以来,总体性结构及其中国特色“关系”的呈现,概源于此。
当今世界,全球市场化加速,社会利益需求多元,科技信息传媒等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碎片化的风险突发叠合,超出了单一专家系统可以解释和控制的范围⑨,并给每个微型场域带来连锁性的持续影响,如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的全球性危害。这种流动的现代性及其内含的风险,逾越了民族国家的疆域边界。这种变化对现代政府的社会治理来说是一种挑战。与此同时,社会人同样面临着对传统关系结构的认知矛盾与困境。“总体性”承袭下来的身体实践,进入了“高原反应期”,经济独立促使人格的自由分化,家长制转向个人主义,出现了诀别传统的“去依附性”,地域熟人社会严重疏离,信任机制不断更迭与重塑,社会支持网络持续变化。
在西方,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社会,进入了对科学真理唯一性的探索时期。而后现代性,则是对现代社会发展中技术革命引发的贫富分化、教育不平等、环境污染、移民问题等的反思,是对科学、主流和确定性的消解。它质疑宏大叙事及其评价标准。在变动中抽离“恒常”胜于在固化中发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社会底蕴”就是“后现代性”的参照。没有后现代理论的较量和争辩,就无从谈起、无法反思“社会底蕴”。因此,“社会底蕴”是后现代社会自反性的产物。可以说,现代性的科学技术手段,为传统魅惑、扑朔迷离的解构奠定了认知基础。现代性的市场提供了生产和消费空间,使人们自愿服从于“市场社会”、服从于“资本的组织”。社会治理就是在后现代语境下,民族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协同治理。可以说,无论中西,庞大社会系统的有序运行,对社会责任、义务和权力的共识与妥协,不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它还须在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共议共治中达到平衡。
三、“大叙事”传统:总体性结构及其稳态
“社会底蕴”潜在于“世代恒常”与“千年不变”之中,这些要素形塑出生活世界的行动方式、价值信念与日常伦理。通常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结构的“最典型”即差序格局。本文着重于通过对社会权力场的考察,发现“国家—民众”的权力流动和操作机制,探究国家的治理逻辑。于“国”而言,这是体量巨大、利益分殊、跨时段的大国治理线索;于“民”来看,这是大国背景、大历史脉络淬炼出的地域情境中的生存智慧,是生产团结、利益让渡、认同延续且可复制的路径,有别于西方的“社群团结”。“家国一体”形态的制度化过程,呈现出大家庭、大宗族、大社会的资源交换及凝聚形式。
皇权不下县,地方皆自治。以往中国基层社会的治理权基本掌握在宗族、士绅、长老等地方势力手中。国家与这些势力相互依偎,共同治理。在中央及地方所依循的若干治理原则中,只要不突破底限——帝国治理的合法性地位即可⑩,皇权是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对合法性的质疑是任何人均应规避的“雷区”。“合法”是“有效”的来源和保障,治理逻辑无不在这一叙事框架内展开。⑪地方治理的各种建制,均遵循“帝国治理”逻辑并在其支配下有序进行。宗族内开展的婚丧嫁娶等社会再生产活动和无所不包的事务,均仰赖于“族长负责制”,道德伦理、奖惩机制乃至暴力的使用,都由“卡里斯玛”权威掌控。非制度化机制的运用,使得在裁决和判定宗族事务时,依据发生情境来保留“发挥空间”,这样可将族群内的紧张就地消化,社会张力也在权威干预中保持妥协。“人格权威”的非制度化使用建立在长期的认同之上,扎根于共同体意识之中,加上族长在内的全体成员,无一例外地保持着自然嵌入的状态,生而如此,去亦不变。小农经济条件下,个人循规蹈矩屈从于“集体理性”,族间“井水不犯河水”,如遇外侵必“群起抗之”。这种劳动生产水平低下的总体性社群,具备“生产合作”的自然理性,家庭和宗族遵守自然规范,“卡里斯玛”的权威伦理浑然天成。国家治理是基于地域社会之上的“大叙事”。也就是说,“总体性社会”的运行逻辑产生于覆盖广、张力强的“家长制”,在以家庭为社会细胞的层级结构中,横向单一序列的“大家庭权威”蔓延开来,逐渐演化为以“家国同构”为特点的国家整合模式⑫;社群权威星火燎原,不断交织并构成巨大的权力网络,终由皇权统合。乡绅治理的路径,无外乎国家对民间权威的吸纳。由此,“国”、“家”意志,皇权和民意通过“家长制”或“族长制”和合为一,地方行政官作为“委托—代理”关系的制度落实者和规约监督者,将刚性制度软化、正常化、合法化。“帝国治理”模式中的节点,由传统封建时期的“乡绅”逐步演变为建国后的“单位”,再到现今的各类社会组织等。
按照孙立平教授等人的研究,“总体性社会”是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国家对经济及各种社会资源全面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高度重叠,国家政权对社会全面控制。⑬当代中国社会沿袭了“帝国治理”逻辑。社会是在单位体制背景下总体性生成的产物,随着改革持续全面地深入,社会形态不断变化——社会不单是政治属性的社会,也是经济整合的社会,同样存在结社基础上的组织化社会的趋势。⑭这种多元分化甚至分散的社会过程,由经济转轨和职业分工、财富分化所引发,其中市场机制发挥了决定作用。社会系统由单一向复杂的演进方向是不可逆的,社会越是发展,子系统就愈加精细化,运行机构也愈加庞大,“重峦叠嶂”而密不可分。任何人既相对独立,又离不开同外部系统的实时联系。
建国初期,我们认为社会主义道路应当讲求平等,灭私求公。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大量经验表明,计划经济体制抑制了发展的动力。于是我们打开市场,注重保护私人产权,强调自由竞争。效率和公平的双重驱动,促使我们创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政治统合经济,国家介入市场化进程,以国家资源统一调配为特点的后发现代化,为支柱型重工业、国有经济发展提供了优先发展的空间,这是讲求迅速回报、实用主义的市场力量所不能及的。另一方面,市场资源相对流通,农村的生产方式逐渐转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干到户激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城市单位制也渐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模式。总的来看,市场机制极大地刺激了资本流动,以人口集中为特征的城市化迅猛发展。
以政治统合为显著特点的“总体性社会”,是建国后自我优化的发展必然。这为我国迈向工业现代化、市场化和全球化,提供了前期的准备,保障了物质基础的有效供给。可以说,建国后直至改革初期,由大一统的强国家及其话语建构出的“总体性”,奠定了经济持续增长、文化多元一体的结构基础。正是这种总体性惯习,使得市场机制嵌入社会文化领域后,个体表现出对原子化的“过敏”、对“缺少人情味”的理性计算的反感、对“共同体缺位”的不适等问题。
低度粗放的发展模式已不再契合当前的社会情境,我们应从“为了人的发展”的1.0初阶,逐步升级到“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2.0高阶。我国的增量改革,就是强调社会发展参与者是全体大众而非部分精英,社会建设是包括生态环境等在内的全面发展。现阶段我国正从“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引领的发展方式,转变到更重质量、更为优化的“国家、市场、社会”合力、共同参与的发展方式。这更有利于实现以要素推动创新,实现“五位一体”和发展协同治理。21世纪以来,我国各类社会组织勃蓬发展,作为社会力量不断渗入总体性社会,宣示着社会力量作为国家、市场之后的第三方渗入了“总体性”,并初步形成了三角稳定的结构。要理解我国“总体性社会”的嬗变机制,便不能脱离当前民族国家及共同体发展的历史逻辑。
一方面,价值统合功用的总体性继续存在。以价值认同为导向的“价值总体性”构建,是国家发展及整合过程的必然。席卷全球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浪潮,在弱化、消解经济边界的同时,促使国家力量显著扩张,民族国家的重要作用愈发凸显。最直接的表现是,二战以来,为保障国民安全,增强国力,争夺国际话语权,国家间的“军事锦标赛”持续发酵。伴随着无声信息革命的到来,科技武器、军事武装等精密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迅猛。除客观上的军事竞赛以外,面对市场挑战带来的价值认同弱化等“劲敌”,民族国家内的话语营造尤为重要。事实上,没有强力支撑的统合主义必然导致价值分化和缺失、现代民粹弥散以致共同体危机,对多民族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正如波兰尼指出,市场社会必将导致国家话语的边缘地位,由市场支配的社会必然处在纷乱无序的状态。⑮因此,着眼于全球发展趋势与中国市场发育的现实,“总体性”的实质与根源不在于控制,而在于“国家话语在场”,这样人的发展才有保障。“单位制”时期,经济、政治、社会高度叠合,呈现锁闭、垄断的总体性特征,凸显了强国家的力量;而当前“价值总体性”的国家整合形式,建立在开放空间与自由认知之上,以应对国际军事贸易摩擦、全球市场冲击与秩序维系为主要目的。建国后从顶层设计到地方政府行为,再到普通民众的行动参与,始终“铆着一股劲”,为的就是摆脱“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落后状态,达成既定的全面小康目标,实现赶超现代化。⑯并且,在这一国家组织实施的市场发育路径中,具备鲜明特点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的“先进”形态既已形成。这种实然存在的“价值总体性”及其优势必将延续。
另一方面,总体性的民间关系结构及其自组织正在发端。不同于民族国家应对市场、社会双重冲击而建构出的“价值总体性”,关系社会资本是中国民间社会长时间的历史沉淀,“和合大同”的精神追求乃是国人社会关系展开的背景,这为和谐的人际联结奠定了总体性基础。中国人的天地时空观是一种“天下主义”,土地疆域辽阔、人口体量庞大、资源相对贫乏。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中,人们交往致密、讲求“家和”,注重“道德规范”、“礼治宗法”,追求“无讼”。大一统时期的文化格局形塑了当前的关系结构,在“大家庭”中须“识大体”、“重大局”。小农经济条件下的互惠互助与共同体精神,是“大浪淘沙”后的“默会知识”,是民族选择的“文化基因”。费孝通先生八十寿辰时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种“隐藏着”的精神向往,作为文化传承具有稳定性。不过,总的来看,改革以来的社会分化严重、整合不足,自组织程度较低,社区社会资本发育缓慢。目前,探索社会支持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发展路径,是规避“转型陷阱”的现实需要。倪志伟和欧索菲认为,长三角乡镇企业在发展初期,缺失正式制度及法律条文的保护,在自身“合法性”尚未得到官方认可的情况下,非正式的关系纽带、持续稳定的信任系统和契约性质的伙伴结盟,同样起到了规范地区往来、促进生产和贸易合作的作用。这种由企业主导的市场化的转型是自下而上的深层变革,更为根本的是熟人社会关系传统的维存。⑰因此,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总体性的关系社会资本是自我文化支撑的强大内核。对总体性的关系社会资本的构建,既不应强力推行社区参与,也不能在良性互动的探索中止步不前。微观人际关系和权力联结形式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当前社会建设的主体是利益筛选后的高度分化的各类社会组织。社会人的行动有自身特点,这决定了社会建设有别于无缝对接的理想状态。各类社会组织在整合资源、促进群体信息交流、构建符合社会发展特点的“公序良俗”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关系总体性”作为“应然存在”正在逐步发育并将不断完善。
综上,当前“总体性社会”特征已不同于建国后一段时期内的政治统合主义。具备共同体性质的“总体性”,是对全球化挑战的合力应对——没有全球化就无法凸显地方性特点和独特优势。更为重要的是,缺失了民族价值认同的市场经济,丢掉了中国特色也就丧失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行动能力,无法实现良性必要的市场干预。因此,一种基于民族国家层面的共同体意识,是公民社会培育的前提。现阶段包揽一切、包办社会的国家统合形式业已过时,但更需要提防的是市场社会的支配逻辑。
当前这种“总体性社会”,既不能将之简单视为长期的历史传统或计划经济时代社会形态的延续,也不能将其理解为一般意义上西方的民族国家建构。这种“总体性”意涵,会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运行发生变化。它可以承前启后,将历史与现实前后连结,使民族特色“支流”与全球化“总源”相互衬托。汇聚地方社群博弈与国家力量运作整合的“总体性社会”,在“价值总体性”与“文化总体性”两方面延续和继承了历史惯性。
四、市场嵌入、秩序重构与多中轴的历史转向
二战以降,包括第三世界在内的民族国家纷纷独立。全球发展环境稳定、经济形势大好,以市场同形化(isomorphism)为主要表现,国界的划分在实质上并没有阻断全球化进程,反而形成各面向的合作与交流。在这种情况下,以经济发展为动因的新型社会阶层大量出现,复杂的社会系统在独立的国家实体内部精细分化,形成国家、市场、社会三足鼎立,造成传统地域范围的熟人社会网络再难单一支配地方运作。自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开放成为主旋律。“黄金时代”并非单纯的财富累积,更是社会的全面剧变、创新和进步。外部要素纳入社会历史进程,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不再是整合的唯一度量。国家、市场、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治理。
稳定的传统同风险交织,熟人社会网络很难提供稳定的整合形式。在精细分工的行业系统内,问题解决追求高效规范,造成了程式固定和单一化的效果。只顾及大众的普遍一般性,对特殊的群体、利益和需求,全然没有纳入系统可搜寻的方案。这样,多数人的需求通过系统达成了共识,少数人则成为社会的弃儿。在部分而非全体的整合中,某些群体掉了队。市场经济中的公平与效率、民主和自由问题相伴而生,化身为矛盾体。综观我国的增量改革,既遵循了资本市场的私有原则,不断地刺激了财富增长和加速流通,又兼顾了市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给予他们最大的社会支持,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对全体人民的底线保障。⑱当资本运行逻辑无法兜底时,国家成为“公平—效率”问题的最后防线;地方政府托底,抵御市场洪流,保障最底层生存发展权益,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来源之一。⑲
政府与社会功能的高度叠合,是改革以来社会治理面临的结构性难题。建国后,以社会保障、医疗事业、教育事业等为主的关乎基本保障的制度安排,是对特定弱势群体的照顾和政策倾斜。国家在此施行了平均主义方针。但是,政府掌握大量资源的同时,采用单一的公有制形式,不进行成本核算,也不讲求效率,财政来源全部由政府拨款,造成政府财政负担沉重不堪。⑳并且,政府仅凭自身力量无法及时回应个性化、差异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市场化改革后,由于赶超现代化目标的推进,地方政府与市场逻辑合谋,政府一定程度上牵引了市场力量“非正常”地加速发展。㉑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将重点放在了市场的渐进改革与调节过程上,在社会建设领域和社会政策方面则较为缺失。“公司化”渗透到社会各层级,乡镇企业崛起。㉒可以说,在迈向调整期的新阶段,国家大刀阔斧搞活市场,依循既定目标实现赶超,向单一发展模式迈进,经济政策较之于社会政策保持压倒性优势。
市场的本质是竞争,竞争的本质是淘汰。市场机制以个人效用最大化及帕累托最优为追求,无法解决公平与效率原则的矛盾,难以调和个人与社会价值取向的分歧。由于贫富差距大,市场化发展在某些地域过快,结构性失业、环境危机等亟待解决;各界尚未从“富起来”中缓过来,便又迈入了社会建设的制度场域;资本自发运动不会带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全面小康必须依托政府“有形的手”进行调节。资本累积使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多元分散需要回归与整合;经济发展也不等同于社会正义,可能倒逼体制改革以适应经济社会现状。转型之快令人始料未及,大量问题反作用于国家政策,迫使其顺势调整,开展积极的社会建设。㉓国家政策更加侧重社会公平,从向市场化让步逐步调整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路径。此外,反观国家行政逻辑,从“父爱主义式包办”,“有事找政府”的思维惯势,到“谁发展,谁治理”的责任主体理念,再到“多元协同治理”理念的构建,历史发展的中轴及变动,表明看似坚硬的社会存在着“运转真空”,应对可能的风险需要动员一切社会力量以防脆弱体系的崩塌。
由传统血缘、地缘性的资源获得方式过渡到契约、流动的“变迁型社会范式”,这是“结构刚性”的包办政府远不能及的治理范围。因此,应当将专家系统、社会组织等纳入治理主体,以使治理内容、治理方式更为正当可靠,治理效果也将持续可控。国家与社会合为一体以及资源和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国家具有很强的动员与组织能力,但结构却较为僵硬、凝滞。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政府理应退到维护社会公平的位置,以此防止社会完全由市场支配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盛行。单位体制的终结,意味着新的社会机制的填充和社会组织的勃兴。㉔在计划经济时代,发展的诸要素均被纳入单位组织中。市场经济时期,社会闲散人员和自由职业群体的再组织化主要依托于社会组织,包括技术指导、道德教化、规范制定等内容的职业团体建设,成为社会组织化的方向之一。
分而化之,是以为明事实、理思路、解问题;合而共谋,是以为趋共识、成方圆、求发展。正式制度落地到具体的实施环境中,通常会产生各种不适。政策统一性越强,它与各地实际情况的差异就越大,基层政府在执行过程中注入的灵活性就越大。针对“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和改革开放过程中随制度变迁而不断涌现的各类问题,需要平衡市场与社会的固有矛盾,优化发展空间及时序性。此时,地方政府的自主裁量权加大,可及时进行政策论证与出台。在此意义上来说,政策变异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种求同。各地积极探索土地流转、招商引资、开发区扩建等城镇化和城市化建设路径,实现政府统一规划之下的运作模式。规则软化、政策妥协和权力的非正式使用时常发生,而一旦地方走在政策之前,就可能出现发展机制的创新。
然而,伴随着这一制度过程出现的是社会的撕裂。因市场化与资本集中过快,加上原有体制文化颇具“计划保守性”,人们无法适应角色调整,产生对发展逻辑的抗拒。大批体制内职工失业,甚至出现了在巴黎营生的中国东北“站街女”。有学者研究认为,这些群体的生产过程折射出转型期“一代人”的集体焦虑和期盼。㉕年轻的中低端技术工种被城市吸纳,“漂”在城市的边角,“歧视—排斥—反抗”事件层出不穷;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迅速变迁,家庭主妇变为职业女性,男性的“男子汉”气概时常遭遇消解。
经济是“嵌入”社会中的,任何经济制度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社会整合体系。计划经济让位于市场经济,经济转轨表面上只是经济制度的改革,但它实际上意味着原有再分配体制下国民“父爱主义”庇护关系的松动甚至消解。市场机制被简单地等同于“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且经常受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等问题的困扰,不能使资本得到最优配置。市场自发调节与脱嵌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人们对物质财富和金钱消费的盲目追求,弱化了对发展本质和目的的思考,缺失了对价值的理解,使人陷入一种历史虚无主义而无所适从。“不忘初心”的发展,是物质丰盈、精神满足、环境优良、人文法制的全面发展。若市场经济变了味,成为市场的傀儡,会导致“金钱物质本位”的产生。“金钱物质本位”遮蔽了作为整体的与主位的人的意义,造成片面追求极端的客位资本,它是一种自我压榨和发展的收缩。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政府逐步强化市场而自身隐退的过程。政府在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和权力结构的同时,建立了新的制度规则,发挥了重大作用。如果没有政府,要在错综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网络中导入新的运行机制是不可能的。可以说,在改革的全局中,改变的主体是政府,政府放弃大包大揽而收缩权力。随着市场机制的导入,市场要素得以参与资源配置过程,追求平等自由的发展主义。社会建设新领域也不断开启,并在多元系统中共治共谋以应对风险及挑战。
五、即时性治理:后现代源流及实践逻辑
“治大国若烹小鲜”。日常生活中的一整套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设置,并非凭空而起。“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严格遵循着宗法制原则与事本主义的历史逻辑。共同体规则是明确的,所规范的对象没有特殊。这是传统中国的“法”。
人人都在创造,孰人还在聆听?这是一个人人皆“知”、急剧变革的时代。制定标准、订立契约成为了单方所谓的“共识”。以往,变迁中的参照、样板和本体基础,是共同的历史,是“恒常”与“不变”,时代的基础是“礼制秩序”对身体的嵌入,是“自然而生”的社会法,那是一个简单的时代。现在的时代是因标准过多而没有标准的复杂割裂的时代。私利与公益持续地抗衡,预示着公民社会的自我启蒙和权利意识的觉醒。这一方面宣告人们从简单的物质联合进展到了精神联盟阶段,另一方面也警示我们应冷静对待尚未成熟的,甚至可能激进展演的自组织利益,注重权力让渡的渐变光谱和转型规律,避免民粹和“俄式转型”的出现。㉖
特定时空的治理行动同“总体性结构”产生了自反困境——在原有“包办一统”的时代,政府缺乏对公共传统领域的构建,导致社会自组织发展的薄弱,形成“凡事找大政府”的思维惯势,进而陷入路径依赖。㉗这使得政府科层繁冗、治理压力重重。同时适逢转型“青春期”,矛盾问题多发。社会系统精细分化,价值认同松散,统合无序,社会团结浅表无力。在瞬时脱域的网络社会、移动联通的交通社会以及物欲内爆的消费社会,经由政府单方面力量回应“社会何以可能”已经非常困难。问题尚须回归到社会历史传统和后现代语境中去,进一步地来讲,就是要找到“总体性结构”和多元主体间的断层和链接点,即“大叙事”和“小叙事”的社会权力演变问题。
后现代社会走入了分化的极端。与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等大相径庭,后现代性主张不确定性、非中心化、小叙事、差异和分散。治理理论中分权、自治、市场化、网络组织之类的话语,强调“多中心秩序”的构建,与传统“统治”相区别。治理理论与后现代主义如出一辙。现代官僚制的特征是专业化和非人格化,注重权力等级与规章制度,甚至过分刚性以致不能灵活处理日趋复杂的公共事务。治理具有更好的灵活性,表现为可以横向协调伙伴关系。地方治理研究亦不再探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模式,它注重实用、强调行动,认为一切都要视不断变化的环境而定,从一个个具体案例中寻找可行的治理之道,而非构建大而无当的宏观体系。㉘后现代社会生活及其治理范式的特点,便是依靠一次次的具体博弈,而非根据明确稳定的制度安排来解决问题。㉙同上述治理逻辑不谋而合,出于赶超现代化的需要,国家默许了地方分权后的路径创新及与之配套的即时权宜性的社会治理方式。这种历史进路,与建立“长效机制”并非同一逻辑起点。前者是指向实际的绩效与发展成果,侧重治理行动的有效性。而后者主要体现过程正当性、历史一致性,侧重行政规则的订立和执行。
无论是市场还是再分配,在任何经济体制中,主要的、占支配地位的调控机制总是服务于有特权的、有权力的富人的利益,而没有特权的人、无权的人和穷人就不得不依赖于第二位的、补偿性的机制。㉚从学理上看,1949年到1978年我国的权力格局是国家专政。1978年后,我国发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向,国家全能主义受到解构。当前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专政、国家管理之后的新形态,是继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后的第五个现代化。在经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失败后,西方主张以治理替代统治。在这一层面上,中国有着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轨迹。在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中,多元主体间的治理目标不尽相同,多元的治理思维与共识总是相互作用着。即时性治理就是针对利益分配机制与实践过程中不平等、不合理的现象,即时地修正以防止断裂群体产生的治理方式。
制度以证合法,即时确保有效。古代的东西不过是后人的一种语言建构,而现实却是一种正在进行时。这就需要我们给予真正有敏感性的理解且作出一种即时性的反应。因此,对于现实处境以及对它的理解有着一种极为紧迫的需求存在。如社会人“何以违法”的问题,向来是要以情境来界定的,此时此地的违法者,到了彼时彼地,可能就是一位守法者。㉛改革前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身份泾渭分明。㉜当时空情境不断地分化和变化,“社会”变为复数时,与“总体性结构”匹配的一元化管理,变为和自身不相适应的活动。“总体性结构”同时空情境分化的矛盾,正式制度同各地民情的差异,导致了正式制度的实践困境。特别是大量既存制度与现实对接困难的出现,引发了各种权宜性行动与规范再生产。在正式制度与生活领域间,或在正式制度丛内部的冲突中,各种“变通”方式不断涌现,以虚化正式制度与生活领域间的矛盾。合法的制度往往是抽象的,而日常的情理却是具体鲜活的,容易调动情绪并产生共鸣,因此合情合理的“变通”实践有时比制度更有力量、更为正当。㉝
在操作化的行政过程中,组织无法获知下一秒会出现哪些新问题,因此制度之“常”与即时之“变”都是可能的选择参考。在基于当下的问题场景作出即时性的决策预判时,如无法根据既有制度搜寻到具体的应对措施,那么只能采取相应的“权宜性手段”来缩减处理时间,更符合实际地化解事态矛盾。这种“能动”和“行动空间”是在共同体的协商对话、实际参与以及不断操练中催生出的。沟通理性与社区性共识的达成是一种“能力”,而不是“知识”,这正如游泳、驾车等能力不能只依靠理论或理念,还必须经过身体实践,方可习得。㉞因此,当“即时的行动”与制度创新具有同一指向,即行动空间被历时性的互动形态定型化和模式化之时,新的社会机制便可诞生了。在方法论上,这意味着“就事论事”与“僵化教条”都是要竭力避免的,既要防止“去时效”的“现实不在场”,又要防止“去法理”而导致“制度不在场”。㉟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如果无法在已有的制度框架内谈判协调,就会出现机会主义盛行的局面。从我国基层政府的实践来看,对待冲突和纠纷时,一些针对性的事件处理方式带有应急特征,可在短期内较好地发挥作用。但因短期问题的即时解决而忽视了长期的制度建设,则可能产生新的隐患。为避免矛盾激化升级,当制度边缘乃至制度外的行动取代制度内的谈判,即“旧规已破,新规未立”之时,政府曾采取先“默许”实践对规则的突破,再由法律和政策进行事后认可的“合法化”方式。这种“行动”的策略优势在于灵活和适应性,但同时形成了“逆向选择”,鼓励短期行为,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政策的权威性。㊱因而,在转型的利益调整期,“把蛋糕做大”比新机制的出台更为现实和有效。
即时,在现代语言中意为立刻、马上,延伸有最快、最方便的意思,如即时通讯、即时战略等。即时性(或准时化) 生产(Just-In-Time或JIT) 就是在需要的时候按需求量生产所需的产品。它起源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是二战后最重要的生产方式之一。由于市场需求始终处在波动状态,为避免生产过量以及劳动力、设备等资源冗余,企业采用小批量、实时、精细化的生产方式。即时性生产这种灵活的生产组织形式,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快速地调整生产,依靠严密细致的管理手段“彻底排除浪费”。㊲不过“降低库存—暴露问题—解决问题—降低库存”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过程,是理想的生产方式。在工业制造历史的演进中,较之于“福特主义”时代讲求批量、同质化、高效率、大规模制造(massproduction)等特征,当前的消费需求表现为个性差异化、少量精细等,于是生产趋势随即发展到了推崇“匠人精神”的“丰田主义”。
与之相应,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同现代企业在问题处理机制、组织理念和科层结构等方面都具有相似性。在社会治理活动中,因实时变化的现实情境与要素制约,治理策略应当随时空条件、人员参与、组织结构的变化作出相应调整。基层政府须因地而治,制度落地也不可避免地需要不断试错。地方性的法律条文、规章制度及政策实施限定于既定的框架内,保证治理合法。而某些行动看似具有随意性、临时性甚至运动性,其实是内外要素联动的结果。此外,临时行政手段对突发、紧迫性事件具有“救场”作用。在科层体制及制度化的流程之外,“特事特办”可填补原有制度安排可能的疏漏,填补既定行政区域空白,确保政府行为的有效性。简言之,固定的制度化行政体系用以应对、处理常规事务,属常态治理;相应的,在流态与瞬息变化的实践情境中,辅以特殊的“审时度势”,作出非制度化的指令,进而得以契合当下,实现正当有效的即时性治理。
以往事务处理依赖于往日经验、情境和线索,这些都是围绕固定化的叙事展开的,日常生活“大叙事”启发和凝结了个体的应对规律。在后现代社会,“先天变量”多发多变,科学技术产业等强要素推陈更迭使人眩晕,在这样一个变动快速、异质分化的时期,所谓的“当下”、“此时”、“这里”不过是“昙花一现”。后现代社会给人们的只是一种场景经验,它可能是瞬时的偶发,不一定会再现,是决绝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社会经验的。后现代情境中制度对个体行为指引、限定的效用大大缩减。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变的表现是“小叙事”对“大叙事”的取代。时代碎微化导致了总体性的消解,互联网给信息流动和民众表达提供了新空间。㊳凭借以往程式化了的生活经验显得捉襟见肘,人们要依据实时的、基于微观环境感知的大量信息作出反馈,这种周遭信息的特点可类比常人方法学指向的“无尽的索引性”,是一种基于当下多变量的不确定性。常人方法学认为系统和生活世界中的社会行动都是基于情景的、实践的结果,具有索引性、权宜性和反身性等特征,社会结构在“流动”中体现,在先验和环境决定的位置中,人们采取“权宜性行动”,进入“结构—行动”的建构过程。㊴
在这样一种转型文化情境中,“总体性社会”的“国家—民众”关系互动紧密且趋于紧张。大而全的行政结构是效率低下的,容易出现治理虚拟化的趋势,小规模的专才型组织较之于大型通才组织更加高效和创新㊵。因此,政府要把一直以来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分解出去。此外,客观上来看,当前治理行为的准备时间短、矛盾化解周期短,突出考验应变能力和执政水平。并且历史长期存在的中央集权治理模式,又使得人们多少会产生一些特定的习惯性认知偏误,如将政策的具体执行问题放大为政策的总体性问题,这又进一步上升到了政治性的高度。㊶也因此,针对当前的负面事件和绩效建设,应侧重于引导社会治理中的多元参与,疏散过于集中的权力,导入“第三方”中间机构,使多层级、多主体共担风险,消解“剑锋直指”。基于此,应当把行政机构非核心部分适度剥离,推行社会建设,培育与发展社会组织、社会企业,加深“政府—社会”的互动合作。制度的可持续性意味着“路径依赖”的形成,国家法治与社会自治的环境需要长期的建设和培育,这不仅关乎机制创新,更需要制度的可持续。
当前正值转型青春期,在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中出现的“青春痘”、“不舒服”是必然现象。即便存在“马上办”等机构回应亟待解决的各类具体问题,也应当意识到这是一个缓慢调整、摩擦协商的长期“自适应”阶段。以“恰在其时”的情势作参考,预案出台、判断和行动的基点都是“事实的当下”。这是一种无限逼近外部环境的过程,“此时及至彼时”以贴合真实。由于问题具有突发性,在人员规制方面,临时整治小组和专业委员会顺承总体性指派与即时性治理的原则,甚至产出常态化制度。“随叫随到”是政治支配与治理需求结合的产物,体现出强政府及其行政体系的变通。㊷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手段的配合使用,契合了“总体性社会”中“国家”的显性支配逻辑,这种行政过程又正向促进了该机制的合法性。强有力的资源调配传统和能力,使得政府强于市场和社会,独享不容置疑的地位。有学者认为,以政府为主体和主导的治理仍是现阶段的重心,现实可行的目标不是营造“小政府、大社会”,而是要构建问责政府,让责任构成权力的边界。㊸
六、简单的结语
乌托邦无非是早产的真理。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方法并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不仅仅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描述,而是一种总体的批判视野和历史的辩证法。自移植西方教育体制后,认识外在世界及理解自己的方式在模仿中颠倒,主客易位,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生活世界中的意义与价值似乎只能在对方的认识框架中得到自我表述,原本只是外在的西方事实上已经不知不觉成为我们内在组织的一个部分。㊹认识自我与认识他人已成为一个事物的两面,我们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世界体系中的位置,正像身体的“皮肤”一样,化身为结构本身;同时试图在传统脉络中超越既有系统,塑制并传播新的规则,或曰“结构形塑中的结构” (structuring structure)。㊺
以多民族、大一统为特点的传统总体性社会结构,在近代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话语——或外力影响或主观认知建构之下发生了改变。这可以理解为我们取得了举国共识,实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轨战略,成功推动了“先进”或“标准”的现代化建设。伴随着经济领域全面而深入的开放,社会政策和社会结构也在持续地变迁。不同于西方“先发内源型”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轨迹,“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所借鉴的西方社会治理模式并非应然路径,而是要采取适应本土的策略,这是时空条件变异引致的“社会底蕴”。
制度刚性和运作弹性的“社会底蕴”横贯千年,概不外乎大一统和多民族的传统帝国特征使然。大一统格局的确立与维系,导致了社会结构和权力制度的刚性存在,而多民族、多变量与复杂情境实然导致了“因地而制”的运作弹性。当前我国存在着“部分紧张—冲突暴露—即时化解—问题出现”的转型问题机制及治理架构,问题成因看似多发、偶发、突发和不可预测,但在时间维度上却有溯源的脉络,在空间上则以差异化的自然条件、地域人文为依托背景和治理线索。社会发展的历史延续性决定了治理问题在时间顺序上不能早也不能晚,对象覆盖不能多亦不能少。首先应当明确何为“保卫社会”的主体,同时“社会”的所指不能泛化。㊻
即时性治理,可以解读为一种现代政府的治理术,一种积极的社会建设。在“问题出现—成因分析—矛盾化解”过程中,“在地”政府立足于微观的行动视角,问题的“演化—处理”过程体现出主客体间即时贴合的胶着状态。应该说,作为应对方,地方治理的“动作”牵引着问题动向,也就是说,并非社会利益矛盾在单方面“一厢情愿”地作用着,地方的疏导作为“制动”与“熄火”的另一端同样在不停地运动着。㊼
改革的逻辑影响着生活,“变迁”成为国人生命历程的基本节奏。无论是社会结构转型,还是社会机制调整,总是在解决老问题而又形成新问题、转变旧机制而又构成新矛盾的曲折运动中展开。㊽这样,就一次次具体的博弈和治理行动来看,似乎是在无规律地“散打”,但日常问题应对手段的经验化和规律化,进一步作用到了国家制度安排的“应然”过程中去㊾,这是后现代社会即时性治理中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和中央与政府的关系的基本方向。制度安排虽已事先存在,但“自下而上”的运动和反馈过程其实已经作为制度化的外部系统实时地运动着,并且不断地建构和形塑出新的制度安排。无论力量大小,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逆向“社会力”,起到了“半边天”的倒逼效果。改革以来的体制变迁路径,即在保持体制存量的情况下,培育和发展原有体制之外的增量,再通过增量积累形成结构性的变迁动力,促发原有体制的应激性反应,从而实现社会结构的逐步转型。㊿因此,在经长期发展而历史形成的“总体性结构”中,由开放促改革的转型范式,尤其是由市场嵌入而带来的即时性机制,是近年来我国社会治理的鲜明特点。显然,在此阶段所形成的信息对称基础之上的协商对话机制,是各方达成共识从而实现有效治理最为必要的路径依托。
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曾拥有庞大精细的官僚制,伴随它出现的是着周期性的组织失败和运行困境。当前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紧张不断衍生出新的国家治理的复杂生态。即时性治理压缩了治理周期,降低了总体性社会的运行成本。这种政治与行政统一、高度组织化的“行动状态”,体现出总体性社会中国家的“基本能力”,同时也持续地维护着自身合法性的“本能”。这种时刻“待命”的行政模式,问题式反应的即时迅速,是“总体性结构”下高度集成的治理水平与状态的真实反映。不过,面对持续出现的各种问题,地方政府到国家层面的即时出场与切入,并不必然促成社会的内部增能,反而可能加深社会对国家的依赖,造成社会内部分裂或强化基层政府的管控。进一步说,如何调动社会主体有序地“动起来”并协调合作,优化和改善“未启蒙”的社会资本进而凝聚分散的力量,即时降低矛盾的规模效应从而实现“有机团结”,将是今后一段时期“总体性社会”的转型难题。
注释:
① E.O.Wright,Envisioning Real Utopias,Verso,2010,pp.145-148.
② 唐士其:《“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以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
③门豪:《市场嵌入、秩序重构与社会治理——从“结构性抗拒”到“主体性认同”》,《新东方》2016年第4期。
④ 邴正:《从发展社会学的视角看中国的社会转型——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历程回顾与创新》,《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2期。
⑤ 杨善华、孙飞宇:《“社会底蕴”:田野经验与思考》,《社会》2015年第1期。
⑥ 秦晖:《“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上),《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
⑦ 孙向晨:《民族国家、文明国家与天下意识》,《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9期。
⑧ 《费孝通文集》第5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79页。
⑨ 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1期。
⑩ 冯仕政:《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
⑪ 蔡禾:《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对周雪光、冯仕政二文的再思考》,《开放时代》2012年第2期。
⑫ 李友梅、孙立平、沈原:《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页。
⑬ 孙立平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⑭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58—363页。
⑮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199页。
⑯ 杨宏星、赵鼎新:《绩效合法性与中国经济奇迹》,《学海》2013年第3期。
⑰ [美]倪志伟、 [德]欧索菲:《自下而上的变革: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19页。
⑱ 景天魁:《底线公平与社会保障的柔性调节》,《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6期。
⑲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37页。
⑳ 李迎生:《中国社会政策的改革与创新(社会学前沿论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页。
㉑ 人民论坛:《大国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年版,第205—216页。
㉒ 折晓叶:《县域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变化》,《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㉓ 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㉔ 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页。
㉕ 赵晔琴:《身份建构逻辑与群体性差异的表征——基于巴黎东北新移民的实证调查》,《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6期。
㉖ 俞可平:《俄罗斯民主:中国学者的视角》,《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2期。
㉗ 李汉林:《中国单位社会:议论、思考与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117页。
㉘ 郁建兴、刘大志:《治理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2期。
㉙ 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㉚ 冯钢:《转型社会及其治理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㉛赵旭东:《何以违法?——适用中国文化转型的规则与社会》,《河北学刊》2016年第6期。
㉜ 周红云:《社会治理与社会创新》,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页。
㉝ 肖瑛:《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
㉞ 李丁赞:《公民农业与社会重建》,《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84期,2011年9月。
㉟ 竹立家:《转型期国家领导力的全新考验》,《人民论坛》2014年第6期。
㊱ 郑风田、郎晓娟:《转型期社会治理:挑战与对策》,《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4期。
㊲B.B.Flynn,S.Sakakibara,G.Schroeder,Relationship between JIT and TQM:Practices and Performance,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5,38(5),pp.1325-1360.
㊳ 周宪:《时代的碎微化及其反思》,《学术月刊》2014年第12期。
㊴ 刘岳、张玉忠:《常人方法学理论探析》,《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4期。
㊵J.M.Mezias,S.J.Mezias,Resource Partitioning,the Founding of Specialist Firms,and Innovation:The American Feature Film Industry,1912-1929,Organization Science,2000,11(3),pp.306-322.
㊶ 周雪光:《无组织的利益与集体行动》,《社会发展研究》2015年第1期。
㊷ 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㊸ 陈明明:《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意蕴》,《人民论坛》2014年第10期。
㊹ 戴锦华等:《超越“左”与“右”》,《开放时代》2010年第9期。
㊺ 吉尔·伊亚尔、伊万·塞勒尼、艾莉诺·汤斯利:《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后共产主义中欧的阶级形成和精英斗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㊻ 麦克·布洛维:《公共社会学:麦克·布洛维论文精选》,沈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8—74页。
㊼ 禹规娥、杨世华、张翼鹏:《探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140页。
㊽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㊾ 李友梅:《转型社会的研究立场和方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135页。
㊿ 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C912/C916
A
(2017)11-0011-12
门豪,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责任编辑 陈 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