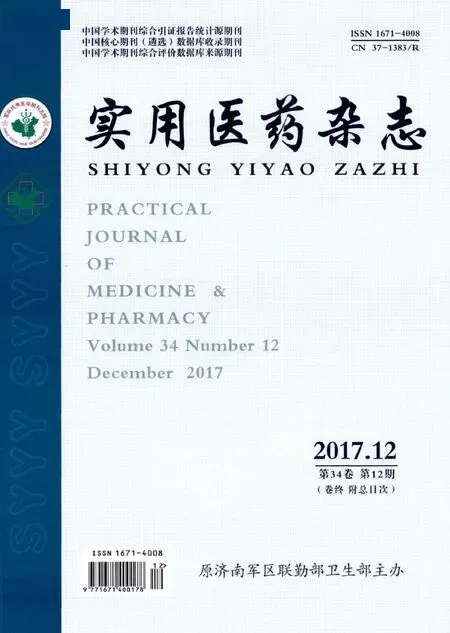血清降钙素原检测对肝衰竭继发性感染的诊断价值*
覃亚勤,韦贞伟,李 芬
细菌、真菌等病原体侵犯机体后,会刺激人体产生降钙素原(procalcition,PCT)、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 超敏 C-反应蛋白 (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HS-CRT)、 脂 多 糖(lipopolysaccharide,LPS)、白介素 2(IL-2)等各种炎症因子和反应蛋白因子。大量研究证明,它们在许多合并细菌和真菌感染的疾病中血浆水平升高,具有诊断价值,有的特异性和灵敏度较高,以PCT、CRP、HS-CRT价值较大,其中不少研究认为PCT甚至优于血常规中性粒细胞计数。肝衰竭是临床上常见的严重疾病,易继发各种感染,PCT在肝衰竭继发感染患者的诊断报道较少,该研究对83例慢性(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检测了PCT,并探讨其诊断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2012年9月1日—2015年3月30日在笔者所在医院住院的慢性肝衰竭和慢加急性肝衰竭为研究对象,病因包括HBV、HCV感染、药物性肝衰竭,所有患者入院前均无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腹膜炎、慢性尿路感染、慢性胆道感染病史。肝衰竭组83例,男62例,女21例;平均年龄48±16岁;其中,继发感染组(A组)52例(包括入院未感染,住院期间继发感染者21例),临床好转和治愈(A1组)23例,恶化自动出院和感染后死亡(A2组)29例,继发的感染包括自发性腹膜炎、肺炎、尿路感染、败血症、胆道感染、脓胸等。无感染组(B组)31例,临床好转和治愈17例,死亡14例。以慢性乙型肝炎和门诊健康体检患者为对照,慢性乙型肝炎组(C组)42例,男30例,女12例,平均年龄(42±15)岁;门诊健康体检组(D 组)31 例,男 19 例,女12例,平均年龄(45±16)岁。肝衰竭诊断符合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和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制订的《肝衰竭诊疗指南(2012版)》。患者诊断为继发感染后按常规给予抗菌药物治疗。
1.2 检测方法 血清PCT采用免疫化学发光法检测。正常值标准:PCT<0.5 ng/ml。患者于入院时、出现典型感染时和出院前采血4 ml由专人负责检测。
1.3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分析采用SPSS 12.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肝衰竭感染组血PCT阳性率 A组PCT阳性率 100%(52/52), 分别与 B 组的 8.8%(3/31)、C 组(0%)、D(0%)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2.2 慢性(慢加急)肝衰竭感染与非感染组PCT检测水平 A组PCT均值明显高于B组[(2.65±0.86)vs (0.27±0.24)ng/ml],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2.3 慢性(慢加急)肝衰竭继发感染后临床好转和治愈患者治疗前后PCT水平 A1组23例患者治疗前 PCT均值明显高于治疗后 [(2.11±0.56)vs(0.75±0.17) ng/ml],两组患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4 慢性(慢加急)肝衰竭继发感染后恶化自动出院和感染后死亡患者治疗前后PCT水平 继发感染后,A2组恶化自动出院和感染后死亡29例,治疗前 PCT均值明显低于治疗后 [(2.54±1.62)vs(4.01±2.26) ng/ml], 两组患者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
3 讨论
3.1 继发感染的原因与结局 肝衰竭是由各种因素引起肝严重损伤的一种综合征,常见的四大死亡原因包括肝性脑病、消化道大出血、肝肾综合征和继发细菌或真菌感染。大量研究表明,60%~80%肝衰竭患者继发腹腔、上下呼吸道、胆道、尿道、肠道甚至盆腔、颅脑等部位的细菌或真菌感染,主要原因是肝衰竭患者肝内库普弗细胞数量减少,功能下降,补体合成明显减少,调理能力下降,体液免疫、细胞免疫紊乱,同时,肠道内细菌过度增殖、易通过黏膜下淋巴管入血或进入腹腔,从而导致自发性腹膜炎、败血症、肺炎等[1]。继发器官细菌或真菌感染后,在临床上,往往存在采样复杂、细菌培养周期长且阳性率低、毒素体内累积多、“炎症因子风暴”等不利因素,导致病情发展更加迅速、治疗难度更加大,预后变得更差,死亡率更高,李显勇等[2]报道确诊自发性腹膜炎的死亡率达60%。因此,及时诊断和处理感染,对缩短治疗疗程、减少医疗费用、提高治疗成功率、减少死亡率等极为重要。
3.2 PCT与肝衰竭继发感染的关系 许多研究表明,降钙素原、肝、肺、肾、脑和胰腺生成,当有严重细菌、真菌、寄生虫感染以及脓毒血症和多脏器功能衰竭时,在细菌毒素和炎性细胞因子刺激下,降钙素原水平快速上升,在严重细菌感染早期(2~3 h后)即可升高,其升高程度与感染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影响降钙素原水平的因素包括被感染器官的大小和类型,细菌种类,炎症的程度和免疫反应状态。但是,自身免疫、过敏和病毒感染时降钙素原不升高,局部有限的细菌感染、轻微的感染和慢性炎症也不会导致降钙素原升高,因此,降钙素原反映了全身炎症反应的活跃程度,可以判断早期细菌感染的存在,对败血症、脓毒血症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并指导临床进行抗菌药物治疗[3]。
经过多年来的研究和实践,降钙素原已经被推荐用于细菌感染性脓毒症的诊断、分层、抗菌药物应用、治疗监测和预后评估[4]。例如,符立贤[5]报道重型肝炎继发细菌感染后PCT、CRP、CA199等大多升高,有助早期识别感染的发生,雷飞飞等报道[6]肝衰竭并发腹膜炎患者的血PCT、HS-CRP均显著高于非继发感染者,且PCT的特异度和灵敏度均高于HS-CRP。表明降钙素原用于诊断肝衰竭继发感染优于HS-CRP,王玉梅等[7]检测56例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降钙素原阳性率为83.92%,明显高于健康组。王治兰[8]报道肝硬化患者合并自发性腹膜炎者的血清和腹水降钙素原水平明显高于无自发性腹膜炎患者,诊断的灵敏度分别为90.3%、96.8%。黄玲等[9]研究表明,肝硬化合并自发性腹膜炎患者PCT、CRP及 PCT+CRP的敏感性分别为 93.3%、90.0%和 96.6%,特异性分别为90.0%、75.0%和95.0%,认为联合检测血清PCT和CRP能够提高早期诊断肝硬化合并自发性腹膜炎的敏感性及特异性。王艳等[10]报道感染组和非感染组、感染好转组与感染加重组之间PCT、WBC和hsCRP值差异有显著性。杨惠安等[11]报道肝衰竭合并感染组血清PCT、CRP水平高于非感染组。该研究慢性(慢加急性)肝衰竭感染组降钙素原阳性率达100%,均值(2.65±0.86)ng/ml分别高于非感染组的 8.8%、0.27±0.24,降钙素原阳性率显著高于慢性肝炎患者和健康对照组,各组间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慢性(慢加急性)肝衰竭继发感染前后的降钙素原阳性率比较差异也有显著性,表明检测血清降钙素原对诊断肝衰竭继发感染有较大价值。
赵蔚等[12]报道重度慢性肝炎并发细菌感染入院第7天与出院前降钙素原值比较有显著差异,说明血清降钙素原水平对重度慢性肝炎并发细菌感染有早期诊断价值。高晓娟等[13]研究表明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组治疗前PCT、ALT、AST、TBil、PTA水平与好转后、CHB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该研究慢性(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中,临床好转和治愈组治疗后降钙素原水平明显下降,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恶化自动出院和感染后死亡组治疗后水平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较治疗前升高,也说明PCT对肝衰竭继发感染早期诊断和疗效判断有价值。
综合上述,血清降钙素原是诊断肝衰竭继发感染的良好指标,对诊断、预后判断、指导抗菌治疗等有较大价值,值得临床医师更深入研究和应用。
参考文献
[1]张志成,张 骏,谭荣欣,等.肝衰竭合并真菌感染临床分析[J].江西医药,2011,46(3):247-249.
[2]李显勇,夏 刚.自发性腹膜炎对慢性肝衰竭预后的影响[J].实用肝脏病杂志,2010,13(5):375-376.
[3]张玉婷,秦爱兰.降钙素原在细菌感染性疾病中的诊断价值[J].苏州大学,2015.
[4]降钙素原急诊临床应用专家共识组.降钙素原(PCT)急诊临床应用的专家共识[J].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2012,21(9):944-948.
[5]符立贤.重型肝炎继发细菌感染的临床特点及疗效分析[J].现代医药卫生,2016,32(24):3840-3842.
[6]雷飞飞,张 韬,汪兴禄,等.降钙素原、超敏C反应蛋白、中性粒细胞比率对肝衰竭自发性腹膜炎的临床诊断价值探讨[J].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2016(2):203-206.
[7]王玉梅,孙丽娟,王善菊.降钙素原C-反应蛋白及病原体检测对下呼吸道感染的诊断价值[J].放射免疫学杂志,2011,24(4):447-449.
[8]王治兰.降钙素原对肝硬化并发自发性腹膜炎的诊断价值[J].中国当代医药,2014,12(23):122-123.
[9]黄 玲,黄 菁,虞 玲,等.血清降钙素原及C-反应蛋白的联合检测在肝硬化合并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诊断中的临床价值[J].国际检验医学杂志,2014,35(23):80-83.
[10]王 艳,甘建和,冯婷婷,等.血清降钙素原检测对肝衰竭继发感染的诊断价值[J]. 江苏医药,2014,40(11):1274-1276.
[11]杨惠安,陈明胜,江晓燕,等.肝衰竭患者血清PCT、CRP检测的临床价值[J]. 福建医药杂志,2013,35(4):79-80.
[12]赵 蔚,王景玲,瞿志军,等.血清降钙素原水平对重度慢性肝炎并发细菌感染的诊断价值[J].山西医科大学学报,2013,44(5):332-334.
[13]高晓娟,余祖江.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外周血降钙素原的动态变化研究[J].现代预防医学,2013,40(11):191-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