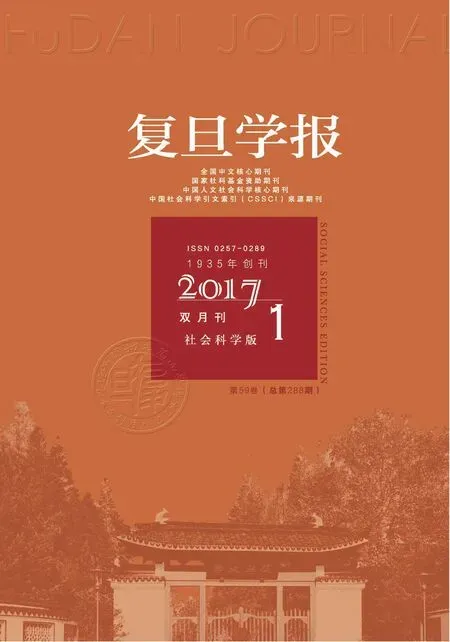两种内在哲学之比较
——西田几多郎与叔本华的对话
[日]板桥勇仁
(立正大学 文学部哲学科,日本)
Yūjin Itabashi
(Rissho University, Tokyo, Japan)
两种内在哲学之比较
——西田几多郎与叔本华的对话
[日]板桥勇仁
(立正大学 文学部哲学科,日本)
本文集中探讨了西田几多郎的“内在”哲学,并试图将其思想放置于叔本华哲学之经纬中予以考察(众所周知,叔本华的意志论具有将康德的批判哲学彻底化的旨趣)。在笔者看来,在西田建立起其大名鼎鼎的“场所逻辑”思想之时,其所给出的一则评论其实已经包含了使得上述思想得以被建立的关键线索。相关论述的文本根据,则是通常被评判为“西田中期作品”的《从动者到见者》一书(1927年出版)。与叔本华哲学遥相呼应的是,西田的哲学立场的真正旨趣,通常被学界把握为对于“康德式的批判主义”的彻底化。对西田而言,这种彻底化进程的实质就在于:关于那些牵涉到经验本性的哲学预设被摒弃得越多,那么这种“彻底化进程”就会被执行得越好。而在这些需要被摒弃的哲学预设之中,有一个预设的内容便是这样的:所谓“独立于客体的认识主体或意识”的确是“实在”的一部分。另一个预设则是这样的:独立于经验的客体亦的确是“实在”的另一部分。而为了与这些流俗意见相对抗,西田建立起了一种“内在”的观点,并经由这种观点将主体或意识视为“场所”——在这种“场所”中,主体和客体都被置于其中,或是被包含于其中。西田的这一评论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场所哲学”不单单是经由东亚的思想资源(或是他本人的宗教体验)而诞生的,其创生同时也已借助了康德哲学的东风。换言之,他比康德本人更为彻底地贯彻了康德式的批判精神,由此才构成了西田本人所说的“彻底的批判主义的立场”。而这种对于批判哲学的彻底化也便构成了西田哲学与叔本华哲学之间的契合点。此外,考虑到叔本华的“内在哲学”是基于“对于生存意志之否定”这一概念的,在笔者看来,西田对内在哲学的彻底化其实也是通过“否定那个不断索求事物之根据的意志本身”才得以实现的。
场所 意识 意志之否定 意志之自由 内在哲学 康德式的批判主义 无
一、 引 言
日本京都学派创始人西田几多郎曾就其“场所”逻辑思想的形成给出过一个评论,而该评论对我们理解该思想的形成来说,具有重要的线索意义。此评论来自于其中期作品《从动者到见者》(1927年出版)。在相关的讨论正式开始之前,笔者想要预先强调的是,西田此后的演进过程,其实就可以被理解为他对于“场所”概念的理解不断加深的过程。而从根本上看,他的哲学立场其实完全可以被归结为所谓的对于“康德式的批判主义”的彻底化——至少对于西田而言,这种彻底化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摒弃那些关于经验的本质的哲学预设,譬如“存在着独立的认识主体或意识”,或“存在着对立于经验的客体”之类的预设。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西田相关评论的内容。他写道:“康德所说的诸如‘自在之物’(德语:Dingansich)之类的超验的实在,是在认知主体之外而自在地存在的。关于此类实在,我可不打算予以讨论……在下相信,沿着康德式的批判主义的路径而正在跋涉的我,其实比康德本人走得更为深远”(日文原文:“私は寧ろカントの批評主義の途を歩みつつあると信ずる”)(NKZ-5:8)。*本文所引用的《西田幾多郎全集》(岩波書店1965~1966年版),缩写为NKZ,后跟卷数以及页码。比如:“NKZ-5:8”的意思就是:西田全集第五卷第八页。对于无法解读日文原文的读者来说,不妨可以参考John W.M. Krummel和Shigenori Nagatom对于西田核心文本的选译。该译本的版本信息是:Place and Dialectic: Two Essays by Nishida Kitarō, Trans. John W. M. Krummel and Shigenori Nagatom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基于这种认识,西田提出了自己的“内在的”立场:根据此立场,主体或意识是需要被视为所谓“面”或“场所”的——而在这种“场所”中,客体也好,存在的事物也罢,都是被“内置于”(日语:於いてある)其中的(参看NKZ-4:322)。在他看来:“即使在康德式的批判哲学里,独断论思想依然被当作出发点来坚持”(NKZ-5:184)。也就是说,“即便是康德,其哲学工作也开始于如下想法,即,认识是一种‘从主体指向客体’的行动,而此想法本身又预设了主、客之间的对立(这里的‘客体’指“物自体”)。而为了反对这一点,我所采纳的理论出发点,将比康德更为深远”(NKZ-4:320-321)。
这一评论清楚地表明,西田的“场所哲学”不仅仅是东亚思想资源或他本人的宗教体验的产物;毋宁说,它是作为一种方法而被提出的。该方法的旨趣,便是要比康德本人更为彻底地贯彻康德式的批判精神。西田把这种方法理解为“彻底的批判主义的立场”(NKZ-5:184),也正是基于这种理论觉悟,他才引入了关于意识的“内在”立场——这里的意识被视为“场所”,而“场所”又被视为主、客的包容者。不过,这里也出现了一个问题:西田的“彻底的批判主义”的“内在”立场,与我们平时所说的“泛意识论”或“唯心论”立场,是否有分别呢?另外,对于被刻画为“场所”的意识而言,“客体”或“存在者”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才“内在于其中”的呢?
本文将集中讨论西田中期思想中的“内在”哲学,并把它与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哲学观念相比较。在芸芸西哲诸贤之中,笔者之所以特别要提到叔本华,则是因为他也试图以一种与西田遥相呼应的方式,将康德式的批判主义彻底化。*有关叔本华对西田早期哲学的影响,见于Yūjin Itabashi,“Realization or Denial of Will: Zen no kenkyū and 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in Kitarō Nishida in der Philosophie des 20. Jahrhunderts, hrg. von Rolf Elberfeld und Yōko Arisaka (Verlag Karl Alber, Freiburg, 2014)261-272.
二、 叔本华哲学中的意志与直接意识
我们的讨论从叔本华开始。众所周知,叔本华哲学受到了康德批判主义的影响。叔本华曾云:“关于在所有可能的经验之外,还有何物存在,吾人哲学将不置一词。毋宁说,我的哲学仅仅提供对于下述问题的解释与阐述:在外部世界中,或在自我意识之中,有什么东西是被直接给予的。……因此,我的哲学便是‘内在的’(至于“内在的”一词在本人著作中的意义,正如该词在康德著述中的意义)”(WII,736)。*本文引用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Band 1 und Band 2),参考了如下英译本:The World as Will and Presentation, Volume 1, Trans. Richard E. Aquila in collaboration with David Carus (Pearson/Longman, 2008). 但是在引用页码的时候,笔者始终引用的是德文版全集(“德文版全集”指的是Arthur Huebscher编辑的七卷本,F.A.Brockhaus出版社1988年出版)。在正文中,“WI”表示该书第一卷,“WII”表示该书第二卷,后面跟着的数字表示页码。在这里,叔本华把康德的“内在性”哲学视为如下两个预设的否弃:一是存在着与认识主体相分离的超验实在;二是存在着先于客体而活动的独立主体。也正是基于这些认识,在叔本华的代表作《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他最终将其“内在”哲学构建成为了一个发端于作为直接意识的“意志(Wille)”的哲学体系。就此,他写道:“意志在自我意识中被直接地认识到,并自在地存在着”(WI,135)。
据叔本华对意志的看法,“意志行为与身体行为,并不是经由因果性之韧带而被联结起来的两个彼此分别的、并被客观地认识到的状态……毋宁说,它们是合二为一的,只是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下被给定而已”(WI,119)。因而,意志实乃统一主、客之活动。叔本华断言正是“在一种主、客界限难以被辨认的直接状态中”,意志宣告了自己的存在(WI,130)。
由上文可看出,叔本华试图消除以下两个假设对象:其一是超越于自我意识的客体,其二是先于客体意识而存在的主体。如之前所考虑的那样,叔本华主张,我们只有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同一个作为意志的直接意识后,才能分出主、客。简言之,在叔本华的内在哲学中,一切皆源自于这个作为意志的直接意识,而绝不能与之分离。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叔本华所说的“意志”既高于主—客区分,亦高于因—果区分。因而,不论是作为世界一部分的身体,还是在主—客关系中呈现出来的整个世界,均为客体化的意志的现象,或者是意志的客体化的现象。不过,有鉴于意志本身并不是现象,叔本华就把它称为“自在之物”。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叔本华并不把“现象”视为关于对象的表征或者为主体所拥有或构建出来的观念。毋宁说,“现象”就是意志的客体化。而在他的术语库中,“表象(Vorstellung)”就是指这种被客体化的意志。从这个角度看,用“表象”来翻译德语中的“Vorstellung”一词才更符合叔本华的原义——而若像学界所通常所做的那样,将其译为“表征”或者“观念”,则有些不妥。这是因为,只有采纳笔者所建议的译法,读者才不会将“Vorstellung”误解为“主体对于客体所具有的印象”之类的意思。
关于上述基于意志论的“表象”理论,叔本华还给出过一番非常有益的补充性说明。在他看来,由意志发出的每一活动皆有其动机,而所谓“动机”,无非即意志呈现自身之机缘(WI,127)。他还说:“在诸多动机中,为何单单是这一动机最终触发了意志呢?此事并无根据可供吾辈追索”(WI,148)。这就意味着:就意志之存在的整体性而言,无根据可谈。意志是“无根据的”(grundlos,WI,127)。*“根据”的德语说法是“Grund”。在德语中,此词兼有“根据”、“基础”、“理由”、“动机”等多重意蕴。也正因为这一点,叔本华说:“意志之每一个别活动均有目的,而意志之整体却是没有目的的。”(WI,196)他还说,作为“无尽的追求”的意志总体来说,所有目的均已缺席(WI,195)。因此,从总体上说,意志从不知晓它所欲求的究竟是什么——就此而言,意志是“盲目的”。
由此看来,叔本华的见解便是:就每一人类的个体 “生命(Leben)”而言,所谓“意志”便是“生存意志(Wille zum Leben)”。生存意志是盲目的,它是对其自身之根据作出无尽之欲求,尽管这样的根据确实并不存在。对人类而言,在这世上仿佛确有目的,确有意志的最终所指,而这也正是人类能够活下去的理由。也正是基于这些认识,人们才具有了意志以统一自身的生活。但是,从总体上看,意志从不知晓它欲求什么,而且,也不存在着意志活动的终极目标,而所谓在“达到目标”后产生的满足感,并不会长久(WI, 365)。因此,痛苦是“无法衡量的,没有尽头的”,而对生命而言,痛苦的存在是具有本质意义的。
三、 意志之否定与内在哲学
如叔本华所写:“单单是由于巨大的不幸和创痛,对于生存意志之自相矛盾性的认识,也会不可阻拦地涌上心头。这样,我们也就迅速悟到了一切挣扎之虚无性(Nichtigkeit)”(WI,466)。他把这一点推及至每个人的生活中(对任何人而言,痛苦的存在均具有本质意义)。叔本华所言及的这种心路转变历程,就是所谓的“意志之否定”。这种转变并不能被刻意求得,而是“天赐”之果(WI,479)。
由此可见,意志对于自身根据无尽追索,“意志之否定”则对这种追索提出质疑。这一质疑之所以发生,乃是因为如下见解已经得到领悟:生存意识在根本上是虚无的,是没有根据的。若套用叔本华在其《充足根据律的四重根》(DerSatzvomzureichendenGrunde)*基于德语“Ground”一词有诸多意义(比如“根由”、“基础”、“理由”、“原因”和“动机”)这一点,“Der Satz vom Grunde”不应译作“理由律(Principle of Reason)”,而应译为“根据律(Principle of Ground)”。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我们便可说:对于生存意志的否定,在实质上便是对于“根据—结果”关系的超越。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否定不能被视为对于某种处于意志之外的基础状态或终极状态的达成——因为倘若我们这么看的话,这种状态就会成为意志的某种根据,而意志却本该是无根据的。最后,对于生存意志之否定,也就是对那不断探问着根据的意志的否定,便成为了这样的一种“转向(Wendung)”活动:该“转向”的初始状态乃是某种欲求着其根由的意志,而该“转向”的结果则是某种“自在存在”的意志——该意志既无所作为,也不通过“根据律”而将自身奠基于任何根据之上。
此外,叔本华还主张说,所谓“意志之否定”便是“作为自在之物的意志所具有的本真的或是真实的自由”之涌现,抑或是“对于自在存在的意志自由的本真的、唯一的直接表达”(WI,355)。据叔本华的观点,“自由(Freiheit)”意味着“独立于根据律”,亦即,一种不对其根据作出欲求的无根据的意志活动。这样一来,对于生存意志之否定,便成为了一种转向活动,这种活动偏离了生存意志,进而转向意志自身——而这里所说的“意志自身”就其本质而言是以自由之方式而活动的,或者说,是以无根据之方式而活动的。这种否定,实际上就是针对生存意志的“弃绝(Aufhebung)”*“Aufhebung”在黑格尔的语境中一般被翻译为“扬弃”,而在叔本华的语境中,我们就暂且将其翻译为“弃绝”。——不过,这种“弃绝”并不针对意志自身。毋宁说,恰恰是通过这种否定,作为“自在之物”的意志自身才得到了实现。*叔本华和西田都思考过意志的直接的觉知。见于拙文《对于意志的否定》(「意志の否定性」),此文收于《叔本华读本》(日文版版本信息为:齋藤智志·高橋陽一郎·板橋勇仁 共編著『ショーペンハウアー読本』,法政大学出版局2007年), 第273~281页。另外还请参看拙著《无底之意志的谱系》(日文版信息:板橋勇仁:『底無き意志の系譜』,法政大学出版局,2016年),尤其是该书第五章。叔本华本人的说法是:“对于生存意志之否定,无论如何都不意味着对于实体的湮灭。”*出自叔本华《附录与补遗(Parerga und Paralipomena)》卷二——这一文本自身收录于叔本华德文全集卷六页 331处。对这一段落的详细分析,见于Koßler, Substantielles Wissen und subjektives Handeln: Dargestellt in einem Vergleich von Hegel und Schopenhauer (Peter Lang, Frankfurt am Main, 1990)201-204。Koßler看出,在对意志加以否定之后,还存留有一些意志的活动。不过,请读者不要误读此话的意思。这并不是说对于生存意志的否定不会对“实体”的存在构成影响——相反,这意味着“意志”本身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种“实体”;同时,就“实体”本身而言,无论在生存意志被否定之前还是在此之后,叔本华均未为其在自己的体系中安排任何位置。
如叔本华所坚称的,对于那种不断求索根据的意志所作出的否定,将把我们引向某种 “天赐之福(Seligkeit)”,引向芸芸众生之生命进程(也就是世间每一个体存在者之生灭进程)之中的“不可剥夺的宁静(unanfechtbare Ruhe)”(WI,464)。*见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Aquila译本的456页。这样的意志处于平和状态之中,而且这样的意志又是自由的。但其平和与自由与其说是源于其自身,还不如说就是在其自身之中的。而对于那试图拥有自己之存在根据的意志(也就是自身缺乏根据的生存意志)而言,这个世界是彻底地为空虚性所充盈的。而只要意志试图避开这种空虚性,那么它就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到痛苦。对于这样的意志而言,从根本上来说,一切皆无。只要意志把空虚性(Nichtigkeit)领会为根据自身的无根据性或者根据之虚无性(即其非存在性),那么这样的意志就会发现,在其所面对的这个世界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是存在的。这也就是说,由于世界本身既无根据用以支撑自身,又无更大的背景用以映衬自身,那么除了这个无根据的世界之外,就不会有任何东西存在。叔本华说:“自由虚无化了那处在现象根据处的(zum Grunde)本质,与此同时,现象自身却还在时间中继续存在。”(WI, 339)这样一来,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对于生存意志之否定,乃是植根于自身的(甚至是显现于现象之中的)意志的自由的‘本真且唯一的直接表达方式’”(WI, 355)。*Herald Schöndorf注意到了叔本华的如下观点:自由会在现象中表达其自身。请参看:Herald Schöndorf, Zum Pradox von Wille und Freiheit bei Schopenhauer. In: Schopenhauer Jahrbuch, 72 (Verlag Waldemar Kramer, Frankfurt am Main, 1991)S.83-89.特别注意该年鉴87。
简言之,根据叔本华的看法,对于那个不断探求着根据的生存意志的否定,吾辈便可意识到所谓“意志”本身也就是“自在之物”。这同时便意味着:对于生存意志的否定,就引发了那作为意志自身之活动的直接意识或直接觉知;这还意味着,这种直接意识(或说得更严格一点,是意志活动的自我觉知与自我实现)其实并没有根据可以超越(或先在于)那作为“自在之物”的意志自身。就此,我们便可理解,为何叔本华哲学被说成是一种“内在哲学”:因为根据他的哲学立场,作为意志的直接意识之外的超验实在性已经全部被弃绝了。
在此基础上,叔本华还对康德版本的内在哲学提出了批判。他写道:“根据康德所言,‘自在之物’本身是与附着于认知之上的任何形式毫无关涉的……然而,康德的错误却在于,在提到这些认识形式的时候,他却偏偏漏掉了‘成为一个为主体而存在的客体’(das Objekt-für-ein-Subjekt-Sein)这一形式。”(WI,206)叔本华还批评说,康德本人实际上已经预设了那为认知主体提供认识质料的“自在之物”的存在,但与此同时,康德却忽略了一点,即这样的“自在之物”其实应当是具有前面所说的“成为一个为主体而存在的客体”这一形式的。在叔本华看来,从上述事实中我们便可推出:根据康德的预设,“自在之物”便成为了凭借它自己而存在(即借由自身的根据而存在)的实体。
叔本华本人的见解则与上面所呈现的康德见解相左。据叔本华的看法,“自在之物”不应该处在所有的认知活动之外,而仅仅是处于下面这些认知活动之外:即具有主—客形式并服从充分根据律的那些认知活动。*鎌田康男研究了叔本华的遗稿和生前出版的作品,并说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叔本华没有把自在之物认作实体。见于鎌田用德语写就的《青年叔本华》一书。版本信息:Yasuo Kamata, Der junge Schopenhauer (Verlag Karl Alber, Freiburg, 1988).因而,只有通过对那不断寻求着根据的意志的否定,我们才可以领会到“意志即‘自在之物’”这一点,并同时领会到:所谓主—客之别,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意志所得到的结果而已。简言之,根据叔本华的意见,对于生存意志的否定,实际上已经标志着对于康德式的批判的内在哲学的彻底化——而关于这种“彻底化”,叔本华本人所给出的具体的执行策略便是:我们必须否弃对于任何独立实在的预设(无论这种“独立实在”是主体还是客体)。而在前文中,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了叔本华本人对于这种“彻底化运作”的描述:在世上芸芸众生的生灭中而寻觅到的平和与自由。
四、 西田对于康德哲学的阐释
与叔本华一样,西田哲学也受到了康德批判哲学的启发。西田几多郎曾以一种富有理论同情的态度,对《纯粹理性批判》中有关“知性之纯粹概念的演绎”的理论进行了阐述。在他的阐释中,“纯粹统觉”被说成是将思维的主观形式与知觉的客观质料统一起来的理智性自觉状态。其原文是:“康德将构成客观识见的东西,视为在作为纯粹统觉的智性自觉中所达成的对于主观形式与客观质料的统一。”(NKZ-4:303)据西田的诠释,康德的相关观点应当是这样的:对于一个客体的识见,并不是以超验性的实在或“自在之物”所具有的“摹本”的形式而被造就的(这里所说的“自在之物”当然是独立于认识主体而存在的);毋宁说,对一个客体的识见,乃是由认知主体所驱动的对于被认知客体的构建活动的产物。此外,在这种构建活动之中,客体的质料只能被给予与感觉到,却不能被创生出来。就此,西田解释道:“在那些被给予构建性思维的东西之中,一定就包含着思维的质料。”(NKZ-4:13)西田还引用了康德在“知性的纯粹概念的演绎”中的知名论述:“这些显像并不是自在之物,而本身只是表象,而这些表象又有其对象。因其对象不再能够被我们直观,故而可以被称为‘非经验性的对象’,亦即‘先验的对象=X’。”*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 109。
凭借对于康德这段话的引用(西田的引用见于NKZ-4:111),西田试图将康德的批判哲学解读为对于如下两个哲学预设的否弃:其一,与认识主体相分离的超验实在是存在的;其二,先于客体的独立主体是存在的。如西田所言:“吾辈不应认为思维形式与知觉质料之间毫无关联。”(NKZ-4:13)也就是说,认识主体与被认识的客体也好,思维的主观形式与知觉的客观质料也罢,它们都不是相互独立的,而只能统一于“作为纯粹统觉的理性自我意识”之中。因而,西田写道:“康德寻求着这种处在智性的自我意识之中的形式与质料的统一。而依在下浅见,康德哲学之本质,便在于此。”(NKZ-4:305)
尽管西田对康德的批判哲学表示赞许,但他却也说过:“即便是康德的哲思,亦开始于如下想法,即把认识看作是一种(从主体指向客体)的行动(日文原文“知るということを作用と考える”);此想法基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这里的“客体”即“自在之物”)。为了反对这一点,在下打算从一个更深、更广的立场出发进行哲思。”(NKZ-4:320-321)根据西田的批评,康德错就错在把自在之物(也就是存在于自身之中的实在)预设为既超越于被认识的客体,又超越于认知主体的东西。诚如西田所言:“倘若‘自在之物’确然在任何一种意义之上皆不为作为主体的吾辈意识所囊括的话,那么,即使将其视为吾辈认知边界上出现的东西,恐怕也是不成的啊。”(NKZ-4:12)简言之,自在之物绝不应是超验的,而必须总是被包容于那对于客体的识见所具有的“内在性”之中。就此,西田坚称:“就康德批判哲学的出发点而言,依然残留着独断论的思想。”(NKZ-5:184)依据西田的见解,认知主体与“自在之物”只能经由彼此而存在,因此,它们实际上构成了同一实在之两面。也就是说,西田试图把康德批判哲学彻底化为这样一种样态:对于任何独立的实在的预设都需要被抛弃——无论这里所说的“独立实在”指的是主体还是作为自在之物的客体。
五、 “作为无的场所”的西田内在哲学
西田不仅试图消除对于意识(即主体)或事物(即客体)之独立存在的预设,而且还试图将这一“消除”进程加以彻底化。而相关的理论后果,便是将意识设定为“面”或是“场所”:在它们之中,所有存在着的事物、所有存在者皆被包摄、被理解,并“恰如其所是”地“内在”于其中。*这一对批判主义的彻底化,也经由西田与新康德主义者(柯亨、李凯尔特与拉斯克等)的思想对话而应运而生。对西田早期哲学至中期哲学的发展的详细分析,见于拙著《西田哲学的逻辑与方法》(法政大学出版局2004年)。该著作还考察了对于“作为无的意识”进行哲学思考或反思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只有经由意识的镜映活动(the mirroring of consciousness)去镜映(mirror)事物,对于事物的识见才可获得。西田本人的相关表述如下:
作为意识的知者(表现为意识)并不是简单地指示出那指向被知者的知识构成形态或认识活动为何。毋宁说,在知者之中,被知者已得到了包摄(日语:知られるものを包むもの)——不仅如此,知者还必须是镜映自身的东西(日语:内に映すもの)。“主客合一”也好,“无主无客”(日语:主も客もない)也罢,其意义都必定无外乎于:……“场所”变成了镜映之镜(日语:映す鏡)。(NKZ-4:222-223)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意识的包裹或镜映活动本身并不是某种先在的、独立的存在。如西田所解释的那样:“意识背后必定是绝对之无(日语:意識の背後は絶対の無でなければならぬ)。”(NKZ-4:232)*可参看前文提到的John W. M. Krummel的英译本,第65页。甚至“主体”自身也是“彻底地内在于(日语:何処までも内在的)”意识(的镜映活动)之中的。(NKZ-4:311)
西田坚称,无论是意识(主体)还是作为实体的存在,都不能独立于“意识的包摄或镜映”而发生。换句话说,意识和存在“内在于”这种包摄活动之中,而这一点也就提示出,“存在”与对于“存在”自身的意识活动其实是一回事,并且也只有当意识活动与关于“存在”自身的事实合一之时,对于“存在”自身的意识活动才可能被实现。在原初的意义上,意识活动与“存在”就是经由彼此并朝向彼此而存有的,它们乃是从不同视角出发而看到的同一个实在。
就此而言,在“存在”背后便是虚无,而意识自身亦就只是“存在”自身。因此,也就有了西田的下述评论:“意识的真实立场只能是‘最后的无的立场’。”(NKZ-4:237)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西田将意识说成是“真无”,或是“最后的无”,其含义并不是说意识不存在——而是说,意识不是以“超越于存在的实体或根据”的方式而存在的。因此,根据这种解读,我们是不能够将西田的学说视为一种泛意识论或唯心论的。*John W. M. Krummel写道:“真无的场所,既不能被还原为实在论,也不能被还原为观念论,或是任何类型的二元论” 。请参看John W.M. Krummel, “Basho, World, and Dialectics,” Place and Dialectic. Two Essays by Nishida Kitarō, trans. John W. M. Krummel and Shigenori Nagatom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12)3-48. 特别是p. 22.同理,西田的“最后之无”的本真立场,亦不能被解读为对于“存在—意识”分解的湮灭,因为即使是这种解读,也会预设在“存在”与“意识”的背景处有着一个既非“存在”又非“意识”的超验状态。*John C. Maraldo指出:在“真无”(也就是西田所说的“绝对无”)之中,“同一性”与“对立性”之间是有着某种内在关系的。他写道:“日本汉字“絶対”,其字面上的意义是打破对立,因而“绝对无”并不是针对任何事物而言的——它是将所有的事物都把握为一的场所,而在这些被把握的事物之中,甚至还包含着对于场所之同一性的否定活动” 。请参看:John C. Maraldo,“Nishida Kitarō: Self, World, and the Nothingness Underlying Distinction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Philosophy, ed. Jay L. Garfield and William Edelgla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367.而西田本人的见解则是这样的:“从真无的立场看来,每一事物均不得不成为镜映着自身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必须是自觉的(日语:一々が自己が自己を映すもの即ち自覚的なもの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NKZ-4:248)“存在”与作为“无”的“意识”本身达到了这样一种认识境界,即所谓“自映(日语:自己を映す)”也好、“自见(日语:自己を見る)”也好,“自觉”也罢,它们实为一体,而且,这里说的“一体”也就是对于存在者的意识所具有的直接表象。换句话说,西田在这里试图表达的,并非一个关于意识的实体的存在,而是一个关于意识的事实的存在,或表述得更好一些:一个“具有意识的”的事件。就此,西田说:“当我们在思考那些[作为先于意识活动的主体或实体的]进行意识活动的活动(日语:意識するもの)的时候,它却不是[真的]是那个进行着意识活动的活动(日语:意識するものではない)。”(NKZ-4:270)*“那个在进行意识活动的意识”的日语表述是“意識する意識”。这个日语表达似乎也可以被英译为“consciousness [as an event of ] being conscious”。
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将意识视为“无”的理论,西田完成了对于康德批判哲学的彻底化。在他看来,在“存在”的背后,——或者更确切些,在“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背后只有虚无,或者说,没有一个支撑“存在”的根据。不过,这样的一个哲学论点,并不蕴含着这样的结论:一个人不能确证一个存在者是否真实存在。毋宁说,这样的想法其实是表达了这样的预设:有一个先于“存在”(或以“存在”根据之形式出现)的实体。而一旦此预设被彻底消除,我们也就容易看明白了:说什么“‘存在’奠基于‘无’”,并不意味着“存在”不可能实存,而只是意味着:“存在”除了其自身之外,不可被归结为任何什么别的根据。*西田的后期哲学中,西田在处理与“历史实在(歴史的実在)”相关的种种关系之中,思虑到了无根据性与目的性之间的内在关联。参看拙著《历史的现实与西田哲学》(法政大学出版局2008年)第三章。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根据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也好,实体与现象之间的关系也罢,只要脱离“存在”的范围去讨论它们,它们便立即具有了超验性。而就这些关系本身而言,它们都不能被看作是达到了一个处在比“存在”本身更深的具有终极奠基性的状态。毋宁说,“存在”是植根于根据自身的虚无的,是植根于“无”自身的。
很明显,“无”不是独立于“存在”的,也不是与“存在”相分离的。正因此,“存在”是在“无” 之中的,或是如西田所说:“‘存在’是内置于‘无’的场所之中的(日语:無の場所に於てある)。”西田之所以把“无”称作“场所”,正是因为在“无的场所”之中,“存在”才如其所是,并与“场所”自身形影不离。又如西田所云:“‘存在’如其所是,也就意味着:当‘存在’如其所是之时,‘存在’便是无(日语:有るものが其儘に有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は、有るが儘に無であると云ふことである。)。”(NKZ-4:247-248)这也就是说,只有在无之中,“存在”才是如其所是的;或是说,存在即“无”。
关于“存在”与作为“无”的“场所”之间的关系,西田有如下表述:
本真的“场所”……是一面自己照亮 [并镜映]自己的镜子(日语:自己自身を照らす鏡)。当诸存在者被置于某个“存在”之中时,我们便可以说:后者拥有前者。而当那些得到彰显的存在者处于一个未得到彰显的“存在”之中的时候,我们便可以说前者是对后者的彰显(或确认)……然而,当诸存在者处于本真之“无”之中的时候,我们却只能说后者[恰如其所是地]镜映了前者。(NKZ-4:226)
在此,西田的意思是:那处在作为“无”的“场所”之中的如其所是的“存在”,乃是对于与那作为“无”的意识的合一状态的实现,而这里所说的这种“无”的意识,又被认为是 “自映”、“自见”与“自觉”。而作为“自觉”的意识,或作为意识活动的意识,其实并不构成“存在”的根据或基础,而是体现为如下的事实,即“存在”是如其所是的。进而,西田写道:“自觉的主体并不独立于,而是彻底地内在于(何処までも内在的)[意识事件的]。”(NKZ-4:311)
六、 叔本华与西田的内在哲学综论
西田几多郎与叔本华这两位哲学家都发展出了一种他们各自的内在哲学。为此,他们都采取了如下的策略:即将康德哲学予以彻底化,并由此消除康德关于独立的主体(意识)和客体(自在之物)的预设。具体而言,西田提出了一种关于“意识活动”的内在哲学,而叔本华则提出了一种“作为意志的无根据直接意识”的内在哲学。
不过,这里读者最好不要将 “内在性”理解为与“超验性”相对峙的一个概念。西田将“意识”视为一种“无的场所”的想法,其实是向我们作出了这样一种提示:我们必须超越根据与结果之间的对峙关系,或是超越实体与现象之间的对峙关系。“存在”与意识之间不是相互独立的,而在它们相互关联的背后,也只有虚无而已。因而,经由西田的“内在”哲学,我们也就超越了“超验性”与“内在性”之间的对峙关系(顺便说一句,这里所说的“超越性”,是以“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关联为出发点的,并最终指向“存在”的终极根据;而“内在性”,则存身于“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关联之中)。
与此同时,我们很难不去比照一下叔本华在其内在哲学之中提出的“意志之否定”这一学说。对叔本华而言,对那种不断探求根据的意志的否定,就是要去超越根据和结果(即现象)之间的对立;而这种否定,最终肯定会导致对于“无根据的意志的实现”(与正是在这种意志之中,主、客严格合一了)。
因而,叔本华对根据与结果之间对峙关系的超越——这或可类比于西田对于“内在性”与“超验性”之间对峙关系的超越——便大体上表达出了“对于那寻求着根据的意志的否定”。就此,西田写道:“从‘无’的立场视之,……万物均必须是自觉的。”(NKZ-4:248)他还断言道,“对于意志之矛盾的超越”(NKZ-4:249)*据西田的观点,作为一种行为的意志,其所具有的根据乃是一个被规定了的场所。见于NKZ-4:248-249。,也就是“对于意志之否定”,便是在某种“见者也是动者”的状态之中实现“自见”(见于NKZ-4:249-250)。因此,再也不可能有任何“实在”藏身于所谓“更深的根基处”,而由此,“自由”(NKZ-4: 246)一词的本真含义也才能够得到落实。简言之,正是通过对于那寻求着根据的意志的否定,我们才被导向自由。而成为“内在的”,也就意味着我们消除了自己“依傍存在之根据”的那种惯有存在方式。由此,新的存在方式便应当是通过自己而存在,或以自己为自己的存在根据。
正如我们所见,在叔本华的哲学中,意志的平和也好,意志的自由也罢,都是通过“对于意志之否定”而在世界中得到实现的。而若我们再换用西田的话语框架,便可这么说:那如其所是的“存在”是植根于“无”的,或者说,除了“无”之外,它也就没有什么别的根据了。换句话说,叔本华笔下的“意志自由”,应被重新认识为:每一个事件就其自身而言都是独特而恰当的,因此,它们并不能被归结于他者,亦不可按照他者的方式来进行把握。不过,关于后面这种理解方式,叔本华本人未曾明确提及。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说,西田关于“意识活动”或“作为‘无’的‘场所’”的内在哲学,在不预设任何对于根据自身的欲求的前提下,设定了自由。换言之,这种哲学向我们展现了一种在不寻觅“任何用以为吾辈奠基的根据”的前提下而出现的“共同在场”的方式。这样一来,即使人们的利益或许彼此冲突,或者说,即使那些作为基础或根据的人生目的的确是因人而异的,人们毕竟还是在生活中彼此照面的,并均内在于如下过程:诸存在者是彼此共在的,而且,在不需要预设根据的前提下彼此邂逅。由此,在这种“无根据地共同在场”的过程中,我们也便可发现“存在”与作为“场所”的意识之间的关系,或者说,那存身于作为“场所”的意识之中的“存在”的内在性。*关于“无根据的共现”的更为详尽的讨论,见于本人英语论文《无为而平和——西田哲学中的和平与无根据性》。相关版本信息为:Yūjin ltabashi,“No Effort, Just Peace, -Peace and its Ground-less-ness in Nishida’s Philosophy,” Poligrafi, number 75/76, Volume 19 (University Press of Primorska and Annales Publishing House, 2014) 27-40.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西田的关于“意识活动”或“无根据地共同在场”的内在哲学,必须是一种“自见”的哲学,或是一种“自觉”的哲学。这种“自觉”并不意味着某种“存在—意识”分界被消灭或被超越的未定状态,而是意味着将我们的意识——也就是“‘如其所是的’对于‘存在’的意识活动”(being- conscious-of-being as it is so)——把握为意识与“存在”之间的关联。
如西田所述:“如其所是的‘存在’,也就意味着,当存在是如其所是的,存在是无。这也便是说,万物皆是一个受限的[‘无’的]影像。”(NKZ-4:247-248)在此,“意识活动”这一事件本身并非是某个未受限定的状态,而是“对于‘存在’的意识活动”,也就是对“存在”的“自觉”或“自限定”。
因此,就西田哲学而言,“意识活动”也好,“作为无的意识”也罢,其自身并不超越或分离于任何关于“存在”与意识的哲学思想或描述。毋宁说,伴随着对于那探求着根据的意志的否定,意识活动在哲学思考中以内在的方式表达了自身、构想了自身、限定了自身。而与西田哲学相比照,在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中,“作为意志的无根据的直接意识所具有的表达性的与构想性的内在性”似乎没有得到充分的阐明。
总之,严格而言,吾辈若要完成对于康德批判哲学的彻底化,只有先去否定那探求着根据的意志活动。同时,这种彻底化亦意味着“意识活动”(being-conscious-of)这一内在性事件的生成与实现,因为从西田的立场上看,正是“批判性的内在哲学”才最终将吾辈引向那植根于“根据之虚无状态”之中的“自见”与“自觉”状态。
[徐英瑾 马塞知远译]
Yūjin Itabashi
(RisshoUniversity,Tokyo,Japan)
[责任编辑 晓 诚]
A Comparison Between Two“Immanent” Philosophies: Dialogue of Nishida and Schopenhauer
This study shall focus on the “immanent” philosophy of Nishida Kitarō, compared with that of Arthur Schopenhauer, who developed the notion of “will” in order to radicalize the Kantian critical philosophy. Nishida made a passing remark that he found an important clue for establishing his own philosophical standpoint through the idea of “place (basho),” i.e., an idea that was first formulated in his 1927 bookFromtheActingtotheSeeing, a work that belongs to his middle period philosophy. His philosophical standpoint always remained nothing other than what he considered as a radicalization of “Kantian criticism,” which included, for Nishida, the abandonment of as many philosophical presumptions as possible regarding the nature of experience. One such presumption would be the reality of an independent cognizant subject or consciousness. Another would be the reality of objects independent of experience. Nishida raises such an “immanent” standpoint of the subject (or consciousness) as “basho” in which both subjects and objects are enclosed. This remark clearly suggests that his philosophy of basho was brought into being not simply through East Asian thinking or through his religious experience, but also by means of pursuing the spirit of Kantian critique further than Kant himself, which Nishida understood as “the standpoint of radical criticism.” Considering Schopenhauer’s “immanent” philosophy based on the notion of “denial of will,” Nishida’s radicalization of immanent critical philosophy is only accomplishable if it is united with the negation of the will probing for a ground.
basho(place); consciousness; denial of will; freedom of will; immanent philosophy; Kantian criticism; nothingness
板桥勇仁,日本立正大学文学部哲学科教授。
⌾ 原文作为参会论文,曾宣读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与《学术月刊》杂志社联合举办的“现代性语境中的翻译与诠释——中日哲学界的对话”工作坊(2015年5月23~24日),会议发起人与组织人为复旦大学徐英瑾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