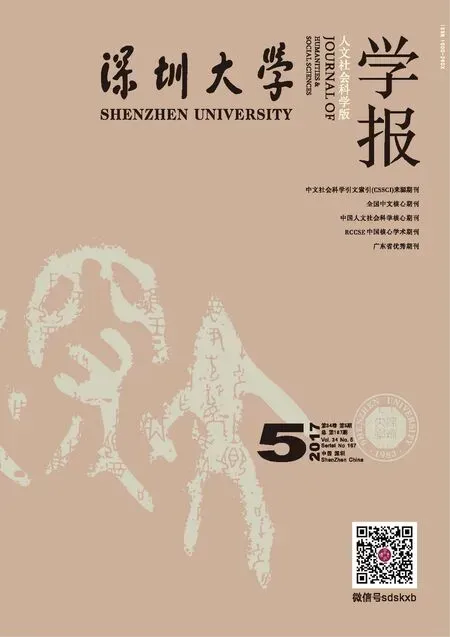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制度选择的“恰适性”逻辑
刘 振,徐立娟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
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制度选择的“恰适性”逻辑
刘 振,徐立娟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
对于基层社会治理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现行讨论中有“互补说”、“替代说”与“冲突说”等三种代表性观点,但这些观点大都忽略了微观治理“场域”的问题,难以解释制度变迁的现象。通过研究C街道物业管理体制变迁从正式制度失灵到非正式制度起效,再到非正式制度的“负外部性”致使正式制度“回归”这样一个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循环性变迁”的历程,我们发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静态结构,而是一个制度安排随着社会情境改变而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而促使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则在于制度安排对于治理场域的“恰适性”。基于此,文章从治理场域中行为主体间关系的角度探寻制度选择的“恰适性”逻辑,将其解构为治理主体组织逻辑的有机统一、社区居民关系结构的合理适用、社区居民对治理主体的组织认同等三个重要特征,以期能为实际应用提供参考与借鉴。
基层社会治理;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恰适性
一、文献回顾和问题提出
基层社会治理直面最复杂的中国。制度作为一种行为主体间的规则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制度有正式制度 (Formal Institution)与非正式制度(Informal Institution)之分,正式制度主要是政府或正式组织有意识地制定,并以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明文规定;非正式制度则是指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过程中自发地形成的,在社会行动主体间不言自明的行为准则。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是一对相应的概念,共同对人们的行为起到规范与约束作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诸多问题可以通过二者的关系去讨论。对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及其实践应用,学界主要有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互补”说。在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中,不乏学者认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正式制度对基层政府治理中的行为主体具有刚性约束,而注重习俗和道德约束效力的非正式制度则有助于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二者在功能上是互补且不可替代的。”[1]同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也是密不可分、相互促进的。对此,有学者指出“非正式制度的安排能够促使正式制度安排的出现,同样,正式制度也为非正式制度的稳定和改进提供了条件”[2]。在此基础上,另有学者强调正式制度应“嵌入”到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土壤之中,相互支持、互为补充[3]。
第二,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替代”说。受到诺斯(Douglass C.North)制度变迁理论关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替代性”论述的启发,有学者认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是一种具有“优劣之分”的可替代关系。具体而言,任何社会都离不开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尤其是在正式制度失去了其本源约束力的时候,非正式制度替代正式制度更是成为可能[4]。究其原因,随着社会改革与变迁,很多正式制度会发生改变,但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因其灵活性却能得以继续。对此,有学者指出“非正式制度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其对正式制度的补充,更重要的是当社会中正式制度缺失或作用薄弱时,非正式制度极有可能直接替代正式制度发挥其社会制约及整合的功能”[5]。
第三,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冲突”说。在基层社会治理尤其是乡村社会的治理中,也有学者认为,由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作用界域不同,二者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6]。持有此观点的学者多数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看做是一对天生的“宿敌”,认为非正式制度对于正式制度起着一种“弱化”、“制约”乃至“挟持”的作用。具体而言,有学者指出,农村社会转型之后,非正式制度以一种新的形势得以延续与发展,并作为一种与正式制度相对应的约束力量对农村治理产生较大影响[7]。同样,有学者借用20世纪90年代初计划生育推行的数据,分析了以宗族为支撑的非正式规范与以国家机器为后盾的正式法律之间的微观冲突机制,提出“当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范冲突时,社会网络的规范约束力会增加正式制度的执行成本,降低其有效性”[8]的观点。
不难看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各有其独特优势,不同学者对于二者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关系也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是否在每个治理场域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都是固定不变的?笔者认为,并非如此。无论“互补说”、“替代说”还是“冲突说”都忽略了制度应用的微观场域。现行关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关系的讨论并不能有效地解释我国基层治理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关系变迁的现象。基于此,本文以C街道社区物业管理体制变迁过程为例,借用社会学制度主义中的“恰适性”概念进行回应与补充。并在此基础上探求基层社会治理制度选择“恰适性”的标准与特征,以期能为实际应用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二、“恰适性”: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关系的新视角
“恰适性”(Appropriateness)概念最早由马奇和奥尔森(James G.March,Johan P.Olsen)提出。 马奇和奥尔森把制度分为建立在理性(rationality)与交换基础之上的聚合式制度和建立在历史、责任与智理(reason)基础之上的整合式制度,进而在一个循环往复的世界中审视制度的变迁[9]。如其所言,“为了证明更多整合式制度的合理性,可能我们必然说服自己相信聚合式制度已然堕落,而权利与理性辩论与行政自主前景光明。与此同时,我们还须承认,不出几十年我们将重新发现整合式制度的缺陷,并再次欣然接受基于自利交换的聚合式制度”[10](P160)。换言之,制度无法摆脱这种“左摇右摆”的周期性宿命,整合式制度与聚合式制度不断经历着周而复始的变迁。面对这样一种“循环性变迁”,我们探寻的则是一种在没有确切结构的世界中祈求确切行为的“恰适性逻辑”[10](P143)。马奇和奥尔森把制度与行为完美地结合了起来,在他们理解下的“恰适性”主要是指组织行为选择对于特定制度的适当性。康贝尔(Cambell)则在此基础上将“恰适性”的概念进一步拓展,他把“恰适性”运用于制度安排对于制度环境适宜性上,提出“某一组织之所以会采用某种特定的制度形式或实践模式,是因为后者在一个更大的文化环境内具有更大的价值”[11]。可以看出,此种定义上的“恰适性”是制度的一种自身状态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发展的属性,是一种制度安排对于环境的适应性。
本文主要是在中观层面展开讨论,一方面强调制度对环境与文化的适应,另一方面也注重制度对行为的激励与约束作用。具体而言,所谓“恰适性”就是制度对其存在的环境和对与制度相关行为主体的恰当性、适应性,是制度与环境和人的和谐有机统一,具有合法性、可行性、协调性等三个特征[12]。笔者认为,基层社会治理中制度安排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治理场域的影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也具有类似整合式制度与聚合式制度的“循环性变迁”现象。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不可能永久独占鳌头,二者也不可能有着固定不变的搭配与组合方式,而是经历着一个周而复始的变迁过程。对此,我们要做的则是在复杂多样的基层社会治理中发现制度选择的“恰适性”逻辑。
三、制度的“循环性变迁”:基层社会治理个案的实践逻辑
C街道(镇)是江苏省Y市(县级市)的城关镇,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2006年10月C镇“撤镇设街”,成立了C街道办事处。作为Y市的中心城区,C街道(镇)具有较多的老旧小区。这些老旧小区是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制”的产物。在那个政府包办年代,小区中的绝大多数事务都由所属单位负责。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单位这个“保姆”也随之消失,致使国家与个人之间缺少了必要的连接体,形成了所谓的“断裂”[13]。众所周知,当时我国的应对策略是大搞社区建设,以“社区制”的形式对此进行弥补和修复。但在很多情况下,“社区”并不能成为“单位”的完全替代,也不能承接单位的所有功能,社区物业管理就是最好的例证。
C街道(镇)经历了单位制改革,不少单位尚且不存,这些单位小区更是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原先隶属于单位的物业管理也被剥离出来。但此时,作为居民自治组织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并没有义务承接此项功能,这也就造成了社区物业管理主体的暂时性缺失,带来了社区物业的混乱与失序。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政府的一项棘手任务。在考虑了社区实际承接能力和市场经济发展成果后,市场承接成了首要选择。2002年Y市政府成立了H物业管理公司,由它专门负责单位制解体后单位的物业管理服务。地处于Y市中心城区的C镇,近乎集中了全市所有的老旧小区,自然成为了H物业公司服务的重点。
(一)正式制度的失灵:物业公司负责阶段(2002-2005)
在单位制时期,社区基本卫生的打扫多数属于志愿性质。有人习惯早起就帮着清扫院子里的卫生;还有不少闲置在家的单位家属,清扫公共卫生打发时间,获得大家的好印象。这并没有形成一定的规章制度和工作规范,干好、干坏全凭大家的一份“良心”。但作为企业,H公司更多的是一种“理性人”的行动逻辑,公司运营遵循的是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市场法则,公司所做的决策、所制定的制度,很大程度上走的是精心设计的“计算途径”。于是,H物业公司对保洁员的工作规范和服务质量也就有了一定的要求。H物业公司逐渐自上而下地制定了《H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企业规章制度——小区保洁员工作制度》、《H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企业规章制度——员工考核制度》等一系列的“正式的”公司管理制度。一位当时的工作人员说:“H物业公司确定了保洁员的工作时间。按节气规定上、下班时间,进出工作时每天必须到所在小区门卫登记签到4次,由各小区物业负责人直接负责。此外,公司规定了对保洁员日、周、月的考核:小区物业负责人必须每天对自己管理区域的保洁人员工作进行考核,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每周六上午物业管理公司对每位保洁人员进行抽查考核,现场进行打分;每月5日下午召开保洁员工作例会,对上月考核情况进行通报,对不足的和需要完善的地方提出改进方法供保洁员参考。”
但H物业公司这样一系列的正式制度并没有得到居民的认可。究其原因,主要是物业费收取所致。作为企业,物业管理公司就要“有利可图”,H物业公司每年向社区居民收取一定的物业管理费用。扣去Y市政府每年给H物业管理公司拨付的补贴,整体上算下来,每年每户居民只要缴纳72块钱的物业管理费。对于一般的家庭这72块钱并不高,而正是这72块钱难“倒”了当时的物业公司。在单位制时期,没有“物业管理”的概念,只是开展一般的保洁和保安工作,这一切成本都是由单位来承担。但总体上说,还算相对成功,居民也都习以为常了。但当物业管理从单位剥离时,社区居民“有偿服务”的物业意识却没有很快地建立起来,甚至多数居民尚不知“物业管理”为何物。所以,当物业交由市场来做的时候,多数居民仍旧认为,物业管理是社区的事、政府的事,与个人无关。此外,在老旧小区的居民多为下岗职工,经济条件相对较差,更是不愿购买物业服务。一位当时的工作人员这样说:“当时我们在收取物业费时,不少社区居民会抱怨:现在连单位都不要我们了,不给我们发工资了,怎么反而让我们向单位交钱了……我们现在下岗了,没钱!”总之,在H物业公司的努力下,虽然各个社区物业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当H物业公司向居民收取物业管理费时,仍旧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不少居民拒绝缴纳。这样久而久之H物业公司无法生存,最终倒闭。之后,Y市和C街道虽又成立或引入了一些物业管理公司,但也都没有得到社区居民的认可,大都因为物业管理费收取困难而相继撤出。
不难看出,社区居民对于物业缴费制度的不认可、不接受,主要原因在于以前“单位包办制”的社会记忆里没有“拿钱找人打扫卫生”的事。诚如诺斯所言:“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结起来的。”[14](P1)过去的记忆都会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或者说,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在H物业公司管理时期,居民对于“无所不包”的单位制的记忆并没有随着单位功能的剥离而消失,人们对缴费才能享受物业服务这种“市场化”的形式心存芥蒂。面对单位制解体带来的物业“失序”,由H物业公司提供有偿物业服务的解决方式,并不符合社区居民建立在“单位制”标准之上的心理预期。这样一来,与单位制的物业管理服务相比,缴纳物业费便没有了合法性机制。最终结果只能是一个个物业公司的撤离,表面上雄心壮志的“正式制度”却也只能以失败告终。
(二)非正式制度的效用:居委会代管阶段(2006-2013)
由于几次物业公司的倒闭和撤出,各老旧小区的基本卫生问题并没有得到改善,大部分社区的物业管理仍旧一片混乱,各种问题层出不穷。2006年“撤镇设街”以后,老旧小区的物业管理工作由C街道负责。社区居委会开始介入社区物业管理,协助物管公司开展社区物业服务,社区物业管理得到了一定的改善。2010年Y市城市管理工作会议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的意见》。文件明确了物业管理工作“条块结合、属地负责”的原则,建立了街道指导、居委会负责的物业管理新体制。进而把物业管理纳入社区管理体系,由各社区居委会具体负责物业管理工作。
城市管理会议之后,C街道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安排,将社区物业的基本保洁、保安、保绿等服务下放到居委会。由居委会负责招募工作人员开展物业服务,物业人员工资由居委会下发。居委会开展物业服务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居委会每年向社区居民收取72元的物业管理费;二是街道按照每百户每年8000元的标准拨付社区居委会的办公经费以及按照每百户每年2000元的标准拨付社区居委会的应急物业维修费用。在此基础上,各社区居民委员会“自负盈亏”。如此一来,社区居委会亦可以看做是街道下属的、没有营业执照的“小物业公司”。这种“小物业公司”既不和居民签署服务合同,也不对服务质量提出明文要求,但它却在物业管理上尤其是物业管理费收取上获得了较大的成功。大部分的社区居民愿意缴纳物业费,甚至不少社区居民志愿参与到物业服务之中。
那么,是什么致使社区居委会开展物业管理的成功?笔者认为,社区居委会物业管理的成功,离不开居委会社区物业管理中“非正式制度”的巧妙运用。社区居委会作为我国法律明文规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无疑是一个“正式组织”。但老旧小区是一个被熟人关系笼罩的共同体,也是非正式制度发育与应用的有效“场域”。因而,在物业管理实际开展过程中,多数社区居委会涉及到“非正式制度”的应用或者是一些正式制度的“非正式化运作”。譬如,C街道各社区的物业管理费多是由居民小组长、社区活动骨干收取,她们在社区中有着较为广泛和牢固的社会关系网。社区居民大都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拒绝缴费。访谈中有社区居民说到:“以前来收物业费的,我们都不认识,脾气都还不小,服务也不行,我们也就不愿意交……现在是我们楼道长H大姐来收钱,几十年的邻居了,钱又不多,一年就72块钱,怎么好意思不给……”此外,老旧小区中有不少的文体娱乐团队(社区自组织),这些社区文体娱乐团队是社区居民日常交流、沟通的平台,也是社区居委会开展活动的抓手。D社区京剧社成员提到:“我们在D京剧社中,社区平时对我们很支持,给我们免费提供场地、购买部分乐器、补贴租服装的费用等等。现在收物业费,社里成员都交钱了,你也就不好意思不交了。”不难看出,居委会是在一个熟人社区,用人情、面子、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在收取物业费。
(三)非正式制度的“负外部性”:正式制度“回归”的呼声(2014-)
虽然,在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场域”中,非正式制度的运用有其必要性与不可或缺性。但是,非正式制度也有不可避免的“负外部性”①。且随着时间的变迁,非正式制度的“负外部性”日益凸显。那么接下来,笔者将对非正式制度给C街道社区居委会工作带来的问题或者说是非正式制度的“负外部性”进行分析和论述。
第一,物业费的收取加重了居委会的负担。虽然居委会是一个社区自治组织,但其“行政化”问题在我国已经成为了普遍的现象。在Y市这座县域城市里,居委会在繁重行政事务的基础上,还要承担老旧小区物业管理的工作,更是加重了居委会的工作负担。M社区C书记说到:“每年物业管理服务工作量巨大,我现在几乎80%的精力放在物业上。在每年的收费时期,工作量猛增,疲惫不堪。而且本来老旧小区物业管理中大大小小的问题就比较多,设施陈旧、不完善、易损坏,维修频次很高。物业设施的损坏也会影响邻居的利益,导致邻里纠纷出现的增加,增大了物业管理的难度。”可见,将非正式制度有效的运营起来,人力、物力、精力投入巨大,加重了居委会原有的工作量,影响了居委会其他工作的开展,有些“喧宾夺主”的嫌疑。
第二,改变居委会“性质”的72块钱带来了居委会和居民的“冲突”。居委会原本是一个没有任何经济功能的居民自治组织,如今却因收费改变了自己的性质,成为了居民心中的“物业公司”——“居民拿钱买服务”的替代品。因而,在部分居民心中居委会就应该是一个万能的服务机构。有社区工作者谈到:“对于居委会收取物业费,居民很不理解,认为居委会收钱了,就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不管是物业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反正社区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做到尽人如意。有一点做不好的,居民就要抱怨,都已经拿过钱了,却什么事情都不给做、也做不好。”这样,无形中造成了居民与社区的冲突,给居委会的日常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第三,物业的利润造成了居委会内部管理“失序”。居委会接管物业服务这一工作不仅加重了居委会工作的负担,带来了居委会和居民的矛盾,而且还造成了居委会内部管理的混乱。每年街道都会根据每个社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各个社区物业费的收取标准。同时,街道也会按照一定的比例以奖励和直接拨款的形式下拨一定的经费到社区账户,这样社区办公经费的多少就与物业管理费收取率直接挂钩。故此,社区物业费的收取成为了社区办公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为了增加社区办公经费和便于其他费用支出,社区物业费成为了居委会内部收入的“灰色地带”,这造成了内部管理的混乱。在开始上报社区内人口和住房面积时,就有部分居委会存在虚假谎报现象,以此增加收入,用于其他开销。甚至有社区出现了贪污的行为。
在这些非正式制度“负外部性”的影响下,不少社区居民和社区工作人员开始抱怨这种“社区管物业”的非正式制度。而此时“单位制”的记忆也已逐渐消退,物业管理公司开始得到居民的承认,成为了近乎无人不知的“名词”。此时,物业公司管物业的呼声再起,一种正式制度回归的趋势油然而生。自2014年起,C街道开始有社区居委会将社区物业重新交由物业公司管理,Y市政府、C街道办事处也出台了相应文件支持物业公司介入社区物业管理,为居民直接提供服务。
四、“恰适性”逻辑:基层社会治理制度选择的内在机理
C街道物业管理体制变迁经历了从正式制度失灵到非正式制度起效、再到非正式制度的“负外部性”致使正式制度“回归”这样一个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循环往复的过程。因而,笔者认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孰优孰劣”(替代说)、“如何组合”(互补说)抑或“弱化制约”(冲突说)等固定不变的静态结构,而是一个制度安排随社会情景改变而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促使这种变化的机制则是在现实社会情境中何种制度关系更恰当、更适宜(恰适说)。换言之,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制度安排遵循着一种“恰适性”逻辑,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关系的设定是一个“恰适性”选择的过程。
那么,面对基层社会治理中复杂多样的社会环境和行为主体,何为“恰适性”逻辑?即怎样确定制度选择的“恰适性”?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更规范地说,它们是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计的一些制约[14](P3)。不论是正式制度抑或非正式制度,都是行为主体间的一种社会关系体系,对主体行为起着规范与制约作用。笔者认为,基层社会治理“场域”可以看作是一种行为主体间的关系网络。一方面行为主体间关系是制度存在的外在环境;另一方面,行为主体间关系又受到制度的规范、制约。因而,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体间关系的角度来讨论基层社会治理制度选择的“恰适性”。总体上来说,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诸多行为主体可以分为治理主体 (基层政府、居委会、物业公司、社区社会组织)和服务对象(即社区居民)两大类②,具有治理主体间关系、服务对象间关系以及治理主体和服务对象间关系这三对关系。从这三对行为主体间关系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基层社会治理制度选择“恰适性”的三个重要特征:
第一,治理主体组织逻辑的有机统一。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基层社会治理中多元参与、各司其职、协商共治也已为常态。但是,基层社会治理中不同治理主体分属不同的领域,具有不同的组织逻辑。对于制度安排的设定,我们应当依据治理主体的组织逻辑,全面考虑治理主体组织间关系的协调发展。譬如,C街道物业管理中,作为企业物业管理公司所奉承的主要是“效率优先”、“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原则,而社区居民委员会则更多的是考虑“人情”、“面子”等“社会人”原则。正因如此,二者对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各有偏好。2006年至2010年之间,C街道也尝试了社区居委会和物业管理公司协同开展物业管理服务,但是由于没有做好前期规划,二者在价值偏好、行为策略等多方面的张力造成了困境重重,最终导致这种组合方式不了了之。当时这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组合模式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治理主体组织逻辑没有做到协调统一。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并不是否定不同治理主体间合作的可能。而是强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合作应认清治理主体间关系背后的组织逻辑,进而合理均衡地设定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作用界域,做到二者的有机统一、良性互动。
第二,社区居民关系结构的合理适用。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服务对象,社区居民间的关系弥漫在基层社会治理场域之中,其间的亲疏远近、长久短暂,是基层社会治理中制度安排的又一重要影响因素。无论是在制度设定层面还是在制度执行层面,能否适用于社区居民的关系结构都影响着制度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譬如,C街道早期的老旧小区多是原先的“单位制”小区,有着“熟人社会”的历史条件。此外,大部分的老旧小区属于完全开放式的小区,居民聊天与互动的机会相对较多,最终构建成了一个社区居民关系紧密、稳定的共同体。在这样的治理场域中,“人情”、“面子”的作用得到很大程度的“放大”,成为非正式制度滋生的土壤,并为其应用奠定了可行性的基础。而在C街道后期的商品房小区中,社区居民多是以各自家庭为中心,少有互动;且多是一些年轻人居住,平时工作较忙、少有闲暇,因而彼此交流甚少,其间居民关系处于一种“原子化”、“碎片化”的状态,从而限制了非正式制度发展的空间,对于契约化、规范化的正式制度更有青睐。因而,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制度选择,应当充分考虑社区居民的关系结构,从而做到合理适用,打牢可行性基础。
第三,社区居民对治理主体的组织认同。基层社会治理可以视为一种治理主体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互动。治理主体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服务对象对治理主体的组织认同,这一关乎制度“合法性”确立的重要因素,更应纳入基层社会治理制度“恰适性”选择的考量范畴。如上文所述,治理主体具有组织逻辑所赋予的制度倾向,所以居民对于不同治理主体具有不同态度,这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居民对于基层社会治理中制度安排的选择倾向。譬如,C街道早期物业管理中物业公司“理性人”的组织逻辑及其契约化的“正式制度”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当时人们心中残留的“单位制”的思维逻辑,同时“熟人社会”的场域特质又更进一步深化了居民对物业公司认同的阻力,因而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物业公司及其所附属的一系列正式制度的“合法性”并没有得到认可,最后只能是以失败告终。相反,社区居委会开展社区工作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其“合法性”基础早已根深蒂固。同时,其“社会人”的组织逻辑和“乡规民约”式的非正式制度,更是适应当时“熟人社会”的场域特质,因而能够得到居民的认可。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商品房住宅小区日渐增多,社区居民对于“物业管理”概念的认识日益加深、对于物业管理规范化的要求日渐提高。致使“居委会管物业”的“非正式制度”的“合法性”逐渐退却,不再得到居民的认可,所以居民对社区物业管理中“正式制度”的呼声再起。
综上,现行讨论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关系的“互补说”、“替代说”与“冲突说”都不能很好地解释基层社会治理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实际应用(至少在C街道的老旧小区这种典型的案例中无法解释)。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有时需要正式制度的刚性制约;有时需要非正式制度的“软制约”;在有些阶段需要二者的互补与相融;在某种“场域”二者却可能会发生抵制与冲突……但影响甚至决定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关系的则是制度安排对于具体治理场域的“恰适性”。对此,文章从治理场域中行为主体间的三对关系来探寻制度选择的“恰适性逻辑”。进而将“恰适性”解构为治理主体组织逻辑的有机统一、社区居民关系结构的合理适用、社区居民对治理主体的组织认同等三个重要特征。但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基层社会治理制度选择“恰适性逻辑”的探究,并非仅有“行为主体间关系”这一条途径。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的视角进行分析、论述。对此,笔者将另文再述。
注:
①所谓负外部性,原本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也称外部成本或外部经济,是指一个人的行为或企业的行为影响了其他人或企业,使之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费用,但后者又无法获得相应补偿的现象。本文主要借指物业管理中“非正式制度”给其他组织或在其他方面造成的无法弥补的损失。
②某种程度上由居民组成的社区自组织,也可以看做是治理主体。因而,笔者并不排除治理主体和服务对象间有部分重合。
[1]李慧凤.制度结构、行为主体与基层政府治理[J].南京社会科学,2014,(2).
[2]崔万田,周晔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探析[J].教学与研究,2006,(8).
[3]杨嵘均.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乡村治理中的互动关系[J].江海学刊,2014,(1).
[4]唐绍新.传统、习俗与非正式制度安排[J].江苏社会科学,2003,(5).
[5]温莹莹.非正式制度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T村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3,(1).
[6]章荣君.乡村治理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解析[J].行政论坛,2015,(3).
[7]高满良.农村治理中的非正式制度分析——对砚山县鲁都克村的个案研究[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2).
[8]彭玉生.当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发生冲突:计划生育与宗族网络[J].社会,2009,(1).
[9]刘晓靖.恰适性制度理论述评:内涵与启示[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2).
[10][美]詹姆斯·G·马奇,[挪]约翰·P·奥尔森.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M].张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11][美]彼得·豪尔,[美]罗斯玛丽·泰勒.政治科学与三个制度主义[J].何俊智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5).
[12]秦国民,高亚林.恰适性: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建设原则[J].中国行政管理,2015,(9).
[13]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13.
[14][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责任编辑:周琍】
The“Appropriateness” Logic of the Institutional Choice in the Practice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LIU Zhen,XU Li-juan
(Soci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chool,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Shanghai 200237)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al system and informal system in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there are three representative views of“complementary theory”,“substitution theory”and“conflict theory”in the current discussion.But these are mostly based on static perspective analysis and ignoring the micro-governance“field”problem.And it is difficult to explain the phenomenon of institutional change.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the C property management system.It is a process from the formal system failure to the informal system,and then to the informal system of“negative external” led to the formal system return,and shows a formal system and informal system“cyclical change”course.It can be seen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mal system and the informal system is not a static structure,but a dynamic process in which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with the changing social scene.And the mechanism that makes this change lies in the“appropriateness”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governance.Based on this,the article explores the“appropriateness logic” of the system sel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ctors in the governance field,and deconstructs it into three characteristics,Which is the organic unity of the logic of the main body of governance,the rational applic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community residents,the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of the community resident.In this paper,we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Grassroots social management;Formal Institution;Informal Institution;Appropriateness
C 913
A
1000-260X(2017)05-0111-07
2017-06-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16ZDA07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差异性均衡权力体系框架下社区社会治理新路径研究”(14BSH011)
刘振,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宜城街道博士后工作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社会治理研究;徐立娟,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博士,华东理工大学-宜城街道博士后工作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解释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