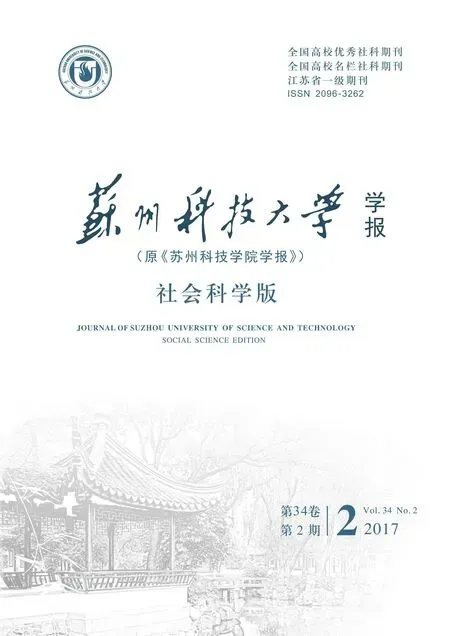论贾植芳“他序”之“真”的意涵*
何 清
(苏州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论贾植芳“他序”之“真”的意涵*
何 清
(苏州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他序”是贾植芳先生晚年留下的重要文字,量多面广,内容丰富,也是他表达对学术研究、学科建设、教书育人等方面思考的重要载体。在那些为他人所作数量可观的序文中,贯穿着贾植芳求真求实的学术理念、思远意深的真知灼见、真情扶助的精神品格,而蕴含其中的“真”,不仅是他衡量评价所序对象的价值尺度,而且彰显着他的学术思想与现实关怀。
贾植芳;“他序”;“真”
贾植芳先生曾笑称自己是“写序专业户”[1]185。在他“由鬼变成人”后,从67岁到87岁(1983—2003年)的20年里,写下了七八十篇序文,数十万字,见诸《劫后文存》《老人老事》《历史的背面》等集子中。这些文字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但它们却是贾植芳先生历经坎坷、饱受磨难之后,在相对稳定、宽松、自由的人生状态下的书写,尽管多是应人所请的“遵命”之作,篇幅或长或短,但内容关涉面广,从中国到外国,从现代到当代,大抵都脱不了“文学”二字。先生的身份是由作家始而教授终,相对而言,后一种身份持续时间更长,蕴含其中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教书育人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文学创作的经历以及因此连带而至所被的长达25年的“文祸”,使得他对文学在实践与理论的层面有着独特、深刻的理解和阐释,使得他的序文成为有着厚重的历史意识、浸透着个人深沉的生命体验、闪耀着灼见真知且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精神的学术引言。它们的存在不仅构成了贾植芳先生学术思想和精神人格的外在表征,而且丰富和发展了相关学科学术研究领域的内涵。
贾植芳先生的序文有“自序”也有“他序”,但真正“序己”的“自序”所占篇数并不多,也只是《〈契诃夫手记〉新版题记》《〈热力〉新版题记》《〈历史的背面〉——关于自选集的自序》《〈给任敏的信(1972—1978)〉——写在前面的话》《〈狱里狱外〉新版题记》《〈解冻时节〉自序》《〈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我的三朋五友〉序》等几篇而已。写作的绝大多数是“序书”“序人”的“他序”,这些“序文的内容涉及颇广,现代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目录学、小说、诗歌、散文创作、通俗文学、传记文学、文学史料学、社会学、政治学诸多领域都涉笔成文,或探寻源流,或梳理支脉,提要勾玄,洞幽见微,既论述各学科在当代的发展,同时又独抒一己之见解,因而往往给人以清晰的整体感和有益的理论启示”[2]。可以说,“他序”构成了贾植芳先生“序文”的主体,也是最能体现他精神境界、学术理路和道德情怀的重要载体。当我重新细读这些序文时,有一个非常明晰而强烈的感受——“存真而序”是贾植芳先生始终坚持的写作原则和价值标准。这份“真”蕴涵了本真、真实、真诚、正气、实在等美好的意义,是贾植芳先生在波诡云谲的社会里长期摸爬滚打后的珍视和坚守,“真”既是他本性的表达,也是他品评人事的重要观照。
其一,贾植芳的“他序”之“真”着意于学术研究中的“真材实料”。由于长期受“左”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文革”后的学术生态存在着虚假、歪曲、隐瞒、粉饰的现象,因此,去伪、去蔽,还原真相,已成为学术界的当务之急。而“真材实料”的所指正是“真知识”和“真相”。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贾植芳认为,就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而言,应该“从清理重灾区入手”[3]。“重灾区”的主要表现为:一是文学史观的狭隘和偏颇,造成许多空白、遗漏的缺陷;二是在此文学史观下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有失客观,甚至存在明显失误。对此,他在1980年代的“他序”中借助不同的研究对象,不断地强调建立尊重历史事实、全面客观地认识和评价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学史观。在他看来,正确的文学史观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前提,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严格尊重历史事实”,“才能真实而完整地描绘出中国现代文学全景和实质,作出真正的历史分析和美学评价”[4]223,也才“符合历史真实的要求”。这在客观上为当时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开展的“平反文学史”“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提供了一份支持。
贾植芳极其重视资料性文献编撰中的真实性,因为在他看来,“真材实料”不仅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得出正确结论的前提,还体现着知识分子的历史认知和责任担当。他指出,在现代文学“生长发展的进程中,总是不断受到政治权力者的猜疑、干预、骚扰和破坏。因此,资料流失、损毁现象严重”[5]132,而资料缺失带来的弊端就是对真相的遮蔽,要想弄明白“真相”,就要“保持历史本身的真实性、严肃性、客观性和完整性,为当代人提供一份真实的史料,为子孙后代留一份真实的历史文献”[5]133,并且认为能否做到这一点关乎对待历史的态度和知识分子本身的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大辞典〉序》中,他在指出现代文学研究工作和资料收集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后,高度肯定了该辞典编撰者的做法:编撰者本着尊重历史事实,对过去因各种原因“受到疏忽或不公正待遇,因而被历史尘沙淹没无着或半被淹没以致评价虚假、失之偏颇或扭歪变形的运动论争、社团流派、作家作品、文艺报刊等类”[6]121,都能通过深入发掘史料,进行整理鉴别、拾遗补缺、校正失误、更易旧说。贾植芳认为这部辞典“足以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三十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风貌”[6]121。他在《〈郁达夫年谱〉序》中认为,作者“通过求真求实求全的资料收辑,厘订和考证工作,用文字力量真实而完整地再现了郁达夫的生活血肉和灵魂”[6]162。可以看出,在贾植芳眼里,无论点、面研究,对材料真实性的要求是必须的。
那么,如何做到编撰的文献“符合历史真实的要求”呢?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序》中就清晰地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尤其对一些历史上“有争议的人和事”,不仅要“取公允的审慎态度,作出尊重客观史实的理性的陈述和评价”,“避免那种直观武断的立论恶习”,还要“能以今天的思想水平、从新的认识层次上,来审视和分析那些复杂万端、纠葛重重的历史上的文学现象”[4]224。在贾植芳的“他序”中,像这样以是否体现“真材实料”对学术研究成果进行评价的序文不在少数。他之所以如此执着于“求真”“求实”,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待历史,是因为他经历过太多的虚假和不实,颠倒和扭曲。他深切地认识到,“历史是不允许想象和假设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同时还要对“既有的史料作出细致科学的鉴别,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因为“确凿的材料可能要比仓促的结论更显得重要切实”,而还历史以本来面貌,“抢救历史是我们这代人应尽的历史责任”[5]151-152。
贾植芳之所以在“辞典”“年谱”“资料汇编”类的“他序”中格外强调“真材实料”的重要性,是因为他深知这类文献具有工具书的特质,而工具书的权威性恰恰来自于它的真实性、全面性和正确性。大凡人们遇有疑惑难明的问题,总是首先想到去查工具书,工具书提供的知识、资料应该是客观的、科学的,它代表的是权威的解释和存在。资料性的工具书是开展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基础,是传之后世、影响深远的,绝不能掺假虚饰、以讹传讹,贻害将来。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出版百种纪念》中针对当时高校现代文学教学资料现状指出,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造成中国现代文学各类文献资料“流失情况严重”,“这就大大地限制了研究课题的开拓和深入,也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5]63。在盛赞该套资料丛书的出版“真是一件功德无量、惠及子孙、泽及中外的历史盛举”的同时,进一步对如何“真实而完整地把30多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面貌显示出来”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不仅应该继续选印那些流传稀少或久已湮没无闻的作家文集和研究文献,也应该选印那些重要作家作品的初刊本,为学术界撰写中国现代文学全史提供充足的原始材料。[5]64
由此可以看出,贾植芳所提到的几个方面在当时都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它清晰地提示着现有文献资料存在的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现代文学“真实和完整”的显示度,因此,解决之道当以资料编撰须遵循“原始”和“全面”为原则。
其二,贾植芳的“他序”之“真”蕴含着知人论世与学科建设的“真知灼见”。这主要体现在贾植芳序文的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上。他在《老人老事》前记中曾说:
这些学术性的序跋文,是以我的人生际遇和历史感受为底蕴与视角的,它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文章,只能说是具有学术性而已。[1]2
从这样的话语中,除了感受到先生一直说的“我不是学问中人”的自谦之外,那句“以我的人生际遇和历史感受为底蕴与视角”的自我概括,却正好道出了他的序文所具有的他人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独特魅力。他曾用“狱里狱外”概括自己的人生,由于他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使他对社会、对历史的认识与感受总会带着一分反思的自觉,这种意识进入文字后,就呈现出一种抵达“历史的背面”所具有的深邃和透彻,表达的是一个独立不迁价值立场的人的个人判断。
这种“真知灼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历史经验洞察深刻的知人论世。在《“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晓风著〈胡风传〉序》中,对胡风的遭遇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审视和解读,从“历史的经验”看,这已不是个人的悲剧,它重复着“知识分子与政治王权的冲突的故事”[7]106,而胡风身上存在的“忠臣心态”又使得这种悲剧的重演多了一分新与旧、历史与现实的复杂缠绕。在《一双明亮的充满智慧的大眼睛——为〈路翎文论集〉而序》中,贾植芳先生个人对于历史的那份沉痛感受清晰可见。看到路翎这样的“难兄难弟”因长期遭受迫害而致精神分裂的惨状,看到那双曾经明亮智慧的大眼睛如今变得暗淡呆滞,那份感同身受的悲愤之情是难以言表的,但他却在这一悲剧的现象里清醒地看出了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时代时个人的局限性。他说:
路翎与胡风一样,在文学领域如同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能所向无敌;可是一离开文学领域进入社会,他们就变得单纯而幼稚,特别对于中国历史社会发展中的黑暗与野蛮,知识分子命运的复杂性与残酷性,都缺乏深刻的认识,所以一旦天塌地裂,他们的精神都会受不了。[8]193
这样深刻的认识无疑是发人深思的。《〈一个探索美的人〉序》[6]102是贾植芳为自己曾经的学生、已经去世的美学家施昌东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所写的序文。该小说除了述及师生之间的关系与牵连,以及作者的人生之路、为人治学、学术成长外,“处处闪烁着真实的光芒”,“它写出了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成长史,力图从一个侧面概括地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的种种风云变幻,以及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苦难道路及其精神上的勇敢探求”。贾植芳认为这部小说还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悲剧是否存在着?”他指出其最大的价值就在于认识了“主人公所追求美与探索美的过程,也正是美在社会生活中被扼杀和被毁灭的过程”,从而“引导读者去向历史的纵深处进行反思”。像这样蕴含深刻且具有哲理意味的表述在贾植芳所写的“他序”中还有很多,经常是在谈论一书时由书及人再由人及事,表面看似随意的文字,实则浸透着贾植芳厚重的历史意识和深沉的生命体验。可以说,那些知人论世的“真知灼见”,源自一个历史的深度参与者和见证者穿透现象后的审视与思考。
二是以开放的视野引领学科专业建设的远见卓识。大学的学科是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平台,贾植芳作为一位资深的教授,不仅始终关注着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而且致力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创建,在给那些名目各异的相关学科研究著作所写的长短不一的序文中,留下了他对学科发展的深远思考和非凡识见。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序》中,贾植芳指出,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建国后出现的独立学科,它的发展受到了“左”的思潮的不断干扰,把政治与学术混为一体,排斥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和艺术特点,同时又从庸俗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复杂的文学现象,严重地影响和破坏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应该以尊重文学发展规律和历史特点的认识与理解来建设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序》中谈到了现代文学的研究、文学史的编写以至选本的编选应该注意的问题,贾植芳指出,“在注意选品的思想艺术质量、社会影响和文学史的地位的同时,也注意到它们的史料价值。就是说,所选对象,不只有范文的意义,也是研究对象,只有这样,才便于考察作家的思想和艺术的变迁和当时的社会影响,因为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取决于它们问世的当时,而不是以后” ,“为了引导学生走向广阔的文学世界,必须从现代文学的整体性和发展性上来认识和研究现代文学的历史面貌”[5]22。由此可以看出,贾植芳总是把研究者的成果置于学科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评价并肯定其研究价值,同时高屋建瓴地以点论面,见微知著。
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创建者之一,贾植芳先后写下了《〈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资料(1928—1949)〉审读意见》《〈比较文学导论〉序》《〈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译文集序》《〈屠格涅夫与中国——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序》《〈新文学作家与外国文化〉序》等数十篇序文,时间跨度达二十多年,借助于这些为不同时期的研究者提供的不同研究对象所写的序文,贾植芳持续地表达着他对于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的深度思考,表达着他对建设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富有前瞻性的意见。早在1983年,他为《比较文学导论》写的序中,就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该学科的历史渊源及其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肯定了“以我为主”地开展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必要性,“以至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而“这门新学科的建立和它所取得的成就,应当以在高等院校开设独立课程,出版专著和发行专门刊物为其标志”[6]61。时至今日,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一如他之所愿,尽皆实现。
从这些例证中不难看出,贾植芳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在文字中总带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这可能就是他身上所带的“历史的经验”的外化。他的思考是深邃的,合于实际的,而人们常说“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句话用来概括贾植芳先生的学术视野也是贴切的。作为一个在“五四”新文化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五四”文学精神的传承者和实践者,他的眼光始终是敏锐的、开放的和看向将来的。他的那些关于为人为学、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精辟论述、真知灼见,对相关学科发展、学术研究、专业教育等都起着一定程度的指导、引领作用,影响绵长而深远。
其三,贾植芳的“他序”之“真”体现了一个长者关怀的“真情实意”。贾植芳所作大量的“他序”,基本都是应人所请,但他对这些序文的写作从不敷衍了事,而是认真查阅资料,精心准备,严谨命笔而成。他深知为学不易,尤其对年轻人更是途路艰辛,他把对他们的关心视为一种责任。在谈到为什么耄耋之年还要答应写序时,他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书系〉总序》中说:
对我们这一代在“五四”精神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识分子来说,凡是有助于社会进步和文化建设,即能促进中国由旧的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大小活动,总是习惯性的卷起袖子。奔上去,自觉地做些什么,即或是为之出生存身,呐喊几声,擂鼓助阵,都当成是一种义不容辞的社会职责。[5]144
他以“为人作序”的方式,真情实意地提点、帮助、扶持、呵护着年轻后学,许多人的学术成长因此而受益匪浅。贾植芳就像鲁迅当年关心爱护文学青年、胡风当年真心扶助像他这样的文学青年一样,对待如今的年轻学人,这也是一种“五四”精神传统的当代传承。
品读贾植芳先生的序文,分明感受到一个长者的慈爱之心与呵护之情,这里有对自己学生的真情,也有对其他人的实意。他的文字因浸润着真诚的情感而有了暖人的温度。《反思的历史 历史的反思——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而序》,是贾植芳应他的老学生范伯群所请为其著作写的序文。他在开篇就说:
苏州大学范伯群教授主持的“七五”重点项目——《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终于完工而且要出版了,他来信要求我为之作序。伯群是我50年代的老学生,1955年“反胡风”时,他和其他同学因我的关系受了不少牵累,而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又是他主持的这个项目的成果鉴定小组的负责人,深知这个项目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因为这两层关系,作序也就成了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就愉快地接受了。[1]174
这段话表明两层意思:一是他用了“要求”而不是“请求”,说明师生关系非同一般,它隐含了先生因“牵累”了学生而怀有的歉疚之情,为其写序是情分所致;二是对学生具有如此“重要价值和意义”的学术成果“终于完工而且要出版”,感到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和愉快,作为老师,为其写序是责任所在。《〈巴金论稿〉序》写于1984年,是贾植芳恢复工作后所写的文字中比较早的专门为研究现代文学的专著所写的序。《巴金论稿》作者陈思和、李辉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在贾先生的引领下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大概对曾“牵累”学生的事心有余悸,表面上以“同志”称呼似乎想拉开一点距离,但却掩饰不住他内心的认同和欣赏,从称赞他们在“治学和做人上的严谨和谦虚”,到对他们研究的“主题和领域是一些巴金研究工作中尚未触及或尚未深入的方面和内容”而具有的开拓性、创新性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并对这样有价值的成果能够出版,“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喜欢”,他非常“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愿意出这一本年轻人写的书”[6]78,内心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序》,是他为90年代的学生宋炳辉的著作写的序。由于作者“成长于中国开放的历史时期,生活在中西文化又重新碰撞和交会的时代环境里,他身上没有旧的历史负担。他能以开放性的文化心态直面历史和未来”。这就使得“炳辉笔下的徐志摩是一个落笔客观实在而又可信的历史人物,因为他写得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就更显示出它的可读性和文学价值”[5]128。实在人做实在事,有了先生对学生人品的了解,才有了先生对学生学术成果的信任,也才有“我相信我们的读书界是会喜欢”这样的断语。不难看出,贾植芳给不同时期的学生写的序文里,都透着一份心灵的亲近,蕴含着浓浓的真情。
在贾植芳先生的序文中,绝大多数是给学生以外的作者写的,它们更能体现先生实意相助的侠义心肠。像《〈余上沅戏剧论文集〉序》《〈艺海一勺〉序》《〈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联”作家〉序》《〈报告文学春秋〉序》《〈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序》《〈人类学导论〉序》《〈文学鉴赏学〉序》《〈鲁迅与高长虹〉序》《为姜云生〈细读自己〉序》《〈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序》,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请他作序的有熟识,有新朋,还有素未谋面者,他总是爽快地应允并认真地写下他对所序著述的意见和评价。对此,他是这样解释的:
但大半是为中青年两代人著译写的序文,目的是起个广告作用,用商业语言说,是为了“以广招徕”。因为这年头,严肃的文艺著译与学术著作,出书尤其不易,为了对他们的劳动成果给以应有的品评,把他们推向文化学术界,我应义不容辞地为他们破土而出摇旗呐喊。[9]
这段话讲得实在,凡是有益于学术研究、有益于学术成长的事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做,用实际的鼓励和肯定表达他扶持相助的心意,这也是他的序文里为什么多是正面评价的缘故,足见一个长者的宽厚慈爱之心。
需要说明的是,贾植芳为人写序并非无原则的捧场,他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总是爱憎分明,有着强烈的个人立场,但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怎么做学问,怎么做人,怎么明事理、辨是非,他都借助序文表达出来,而是否写出了“真”,则始终是他作序时看取的重要标准之一。他说陈思和教授的《巴金传》“写出了一个人的历史真实”[5]125,说晓风的《胡风传》“写了历史的真实”[7]109,说宋炳辉的《徐志摩传》是一种“真实的人生记录”[8]361,说秋石的《萧军与萧红》“写得比较真实可信”[1]221,说孙正荃的《大众美学99》是“对真善美的呼唤”[1]297等,都是以“真”表明了他信守的原则和立场。
纵观贾植芳先生数十年的“他序”写作,“存真而序”的概括切中肯綮。一方面,他是一个满怀赤诚之心的“真人”,他的文字无不体现他对“真”的追求,他以自己的方式肯定、维护着“真”的价值,强调着“真”的存在对做人和做学问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存真的序文又为我们留存下了先生真实的性情、敏锐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境界的见证。从他对“真”的看重,也可看出其中有“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影响。对此,陈思和教授在《我心中的贾植芳先生》中有精辟的阐述:“这是一种尚未定型,同时遭受着各种苦难考验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需要在整个中国进步发展的实践中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这种传统在贾植芳先生身上强烈地体现为两个精神特征:一是怀疑一切权威教宗,要求在人性的范围——就是把‘人’字写端正——检验一切事物的真相;二是要有尽可能开放的视野来看世界,要接受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文化财富,不排除异己,不唯祖宗为绝对之是。”[10]这就从根本上解释了贾植芳先生坚持“存真而序”的深层缘由。
[1]贾植芳.老人老事[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
[2]孙乃修.深沉厚重显卓识[N].人民日报,1992-09-11.
[3]贾植芳.把人字写端正:贾植芳生平自述与人生感悟[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197.
[4]贾植芳.《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序[J].新文学史料,1989(3).
[5]贾植芳.贾植芳文集:理论卷[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6]孙乃修.劫后文存:贾植芳序跋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
[7]贾植芳.不能忘却的纪念:我的朋友们[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8]贾植芳.历史的背面:贾植芳自选集[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9]贾植芳.《劫后文存》前记[M]∥暮年杂笔.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198.
[10]陈思和.耳顺六记[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20.
(责任编辑:袁 茹)
2016-12-29
何 清,男,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67.1
A
2096-3262(2017)02-005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