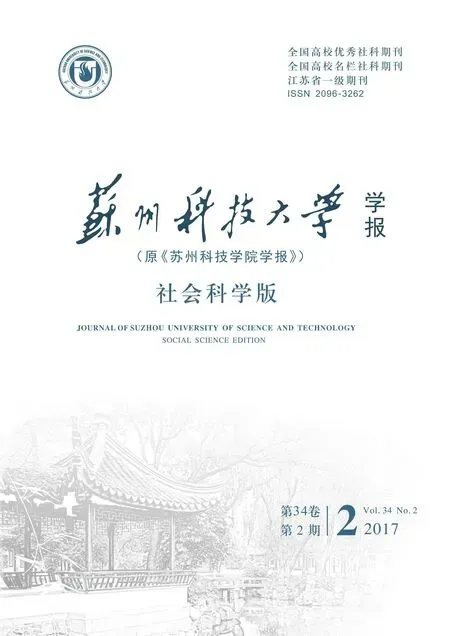明代都邑赋的守成与创变*
王树森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51)
明代都邑赋的守成与创变*
王树森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51)
明代都邑赋创作繁盛,反映出明代城市的政治、经济、军事功能都有重要发展。京都赋在继承汉、晋京都大赋的基础上,又呈现出新的开拓。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对于京都的认识有很大差异,与赋家在处理各种素材时是否为帝王倚重有关,京都赋也因此呈现不同的面貌。明代都邑赋创作与明代文学的复古思潮息息相关。中外交往的扩大为都邑赋提供了宝贵的素材,《朝鲜赋》《交南赋》的出现,使都邑赋的外交职能得到充分体现,也推动了异域赋的创作。
明代;都邑赋;城市功能;复古;异域赋
有明一代,都邑赋创作繁盛。从明初到后期的嘉靖、万历年间,都有赋作问世,直至晚明,还有夏完淳的《燕问》出现。其中尤以成祖永乐年间与明中期成化、弘治年间创作的都邑赋数量最夥,成就最高。从地域分布来讲,华南、东南、中南、西南、中原、华北、西北等地都有不同数量的都邑赋,甚至还产生了以董越《朝鲜赋》、湛若水《交南赋》为代表的异域赋,这种广度是前此各代所不曾有过的;从赋家队伍构成来看,既有馆阁文臣,也有相当数量的中下层文人,非常庞杂;从体制上看,明代都邑赋主要采取的是汉代散体大赋的结构,也有少量的骚体赋,如《张秋赋》,律赋则几乎没有;从内容上看,即便是面对同一对象,不同赋家的观照角度、处理方式都会存在很大差异。明代都邑赋最鲜明的特征是既在题材上、体制上自觉向汉、晋京都大赋的追摹,同时又依据新的时代社会、政治与文化、文学发展的基础,对都邑赋这一传统赋体题材进行开拓,表现出自觉的创变意识。
一、明代都邑赋的城市类型
明代都邑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地域分布广泛,全国几乎所有大的地理区域都有都邑赋出现。这和唐以前都邑赋主要写北方城市而宋以来又渐趋关注南方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现象首先是和明代统一的国势密切相关,其次也说明明代各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均有较大进步,特别是一些此前发展相对滞后的内陆地区,此时的进步尤为明显。
既然明代都邑赋中涉及诸多城市,在地理分布上又很难找到一个相对明显的趋向,那么是否还有一些其它的规律可循呢?其实,如果跳出简单的地理观念束缚,从城市功能的角度出发,会发现明代都邑赋中所写的这些城市大体上可分三种类型,即政治型、商业型、军事型。政治型自不待言,主要是指作为帝都的北京和南京,清代陈元龙所编《历代赋汇》中所收大批《北京赋》和《皇都大一统赋》均针对此类城市。由于下文还要专门对此类京都赋展开探讨,为免重复,此处拟先对围绕其它两类城市所产生的都邑赋作一简单梳理。
首先是商业型城市。元代后期,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残酷压榨,全国经济,尤其是江南遭到了十分严重的破坏。朱元璋甫一建国,便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恢复、经济发展的积极政策。随后的几十年里,粮食产量和官府的赋税均有大幅增加,一些在战乱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商业城市也相继复苏,对外贸易也因为明廷的开放政策而发展迅速。南京、北京、苏州、广州等地都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商业城市。特别是明代中期以后,随着重商思潮的日益深入,全国有愈来愈多的人弃农从商、弃士从商,这给明代商业城市的兴起带来强大动力,从而也使明代都邑赋对于当时城市经济发展盛况的描写较之宋元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的北京、南京、嘉兴甚至太原等地,均以商业繁荣闻名,在明代都邑赋中也有非常直接的反映,像桑悦的《两都赋》、余光的《两京赋》等诸多赋作,其中最有特色的是莫旦的《苏州赋》、黄佐的《粤会赋》。
《苏州赋》[1]开篇即云苏州“拱京师之南畿,据江浙之上游。擅田土之膏腴,饶户口之富稠”。文中,作者对苏州这座江南的重要经济城市的描写极为细腻。写其城建如“列巷通衢、华区锦肆,坊市棋列、桥梁栉比”;写其士女如“远方巨商、它方流妓,千金一笑、万金一箸”;写其货贿如“万国储粟、千艘转输,上供玉食、天下所需”。此外还写到苏州的“家家礼乐,人人诗书”,以及具有浓郁江南水乡特点的风俗民情,难怪作者要感叹:“天上天堂,地下苏杭,天下之通谚也。”除苏州外,广州也是明代十分重要的经贸城市,尤其是在对外贸易方面,其地位更是举足轻重。黄佐《粤会赋》[2]167云其“允矣乐国,四方所届。实泉货之渊薮,夷夏之都会也”。经济的发展给广州城民的生存状态带来极大的改变。他们“富侈相高”,“沉湎而自豪”;他们“因岁时,事娱嬉。逾涧越井,吊古探奇”;他们“清明簪柳”“端午酌蒲”,在“春王初吉”“中秋重阳”等节日里,无不“粲绚冠服”“其乐陶陶”,可见当时广州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之高。
其次是军事型城市。陈正祥先生曾云:“中国城的发展,受政治的影响最大,军事防御次之,商业或交通等的因素,都只是陪衬的。”[3]明朝“尽复汉唐故地”,这固然扭转了两宋贫弱的国势,然而明太祖及其子孙并未完全消灭蒙元势力,实际上只是将其赶出长城以外,而其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存在,依然让明廷不敢轻视。在此后的两百余年间,无论其内部经历怎样的分合,觊觎中原之心一直不死,且屡屡犯边,因而给明代的北部边疆带来极大威胁,促使明廷不得不屯重兵于此。且明代边疆还实行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屯垦”政策,这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历代久为困扰的粮饷调运问题,也使得一大批边镇得到快速发展,著名的“九边”即为其代表。明代都邑赋中有两篇,即曹琏的《朔方形胜赋》与娄奎的《朔方风俗赋》,都是描写当时“九边”之一的宁夏卫(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风光的重要作品。另外张凤翼的《晋国赋》也属此类。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外经济往来的日益扩大,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日益成为明王朝的大患。为消除倭寇给沿海人民带来的灾难,明廷屡屡派重兵进剿,当时福建、广东沿海诸州多已成为抗倭前线,从而使其作为军事重镇的作用愈显重大。这个转变,在明代杨彩的《南澳赋》(广东潮州)、池显方的《大同赋》(福建同安)和严从简的《东南巨镇赋》等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都邑赋中写军事重镇,并非始自明代。早在唐代,张嵩和吕令问等人的《云中古城赋》便已肇其端,但是张、吕诸赋过于粗放(当然,这也可能说明当时的边疆地区的确太过荒凉)。到了明代,上述诸篇写军事重镇的都邑赋就要翔实、细致多了。在这些赋中,赋家除了写其作为军事重镇所不可避免要进行的相关军事活动,如《大同赋》和《东南巨镇赋》中直接写军民的抗倭活动,《南澳赋》中写对当地草寇的剿灭,《晋国赋》中严阵以待的边镇官兵等,但更主要的是写当地的风光和人民的实际生活情状,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朔方形胜赋》[4]中“浚渠溉田,省费万计”两句就鲜明地点出了明代实行屯垦的显著效果,“民杂汉戎”传达了多民族和睦共居的重要信息,一个安定、富足的“塞外江南”在曹琏《朔方形胜赋》与娄奎《朔方风俗赋》中得到了很好的描绘。《南澳赋》中“大国小邦,外趋内附”[5]的中外贸易盛况,《大同赋》中的冠盖、士女、俳优等等,都表明了越是在这种军事重镇,普通百姓对于和平生活的期盼越是强烈。
当然,明代都邑赋中所涉之城市类型,绝非只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三种,至少还有一类,就是风景型城市。这些城市既不像苏杭那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没有边镇那种险要的地理位置,但它们仍然具有一些吸引眼光的优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山水风光、人文古迹,将笔力集中于对这些的描绘,也构成了明代一部分都邑赋的显著特色,如丘濬的《南溟奇甸赋》、陈安的《衡阳八景赋》、韩扬的《荆湖山川人物赋》和徐杜的《郑州揽胜赋》等。《衡阳八景赋》写了衡阳境内很多著名景点,如回雁峰、东洲等;《荆湖山川人物赋》除了对荆湘一带的名山秀水作出描绘,还提到了该区域内众多的历史遗存,这对于增加人们对这些地区的了解是不无裨益的。但总体上看,这些赋作除了丘濬《南溟奇甸赋》因写海南岛的亚热带风光较有特色外,多数赋作的艺术价值和认识价值都很有限,在明代都邑赋中属于别调。特别是有明一代涌现出众多山水散文、游记,流风所及,辞赋中也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山水题材作品,相形之下,这类明代都邑赋就更无优势可言了。
二、各具特色的京都赋
明代产生了一大批以国都为创作对象的京都赋,如金幼孜、杨荣、胡启先均有《皇都大一统赋》;董应举有《皇都赋》;李时勉、盛时泰、黄佐、余光、钱幹都有《北京赋》;顾起元有《帝京赋》;桑悦有《两都赋》。还有莫旦的《大明一统赋》,虽未径以皇都为题,但究其实际内容,也和金、杨等赋相类,亦当计入。*此赋当作于《苏州赋》之后,因为在《苏州赋》中,作者曾借赋中“鲈乡子”之口云:“吾俟夫南山豹变,北海鹏飞,……然后仿吉甫美周室,效封人祝多男。披五经之腹笥,荡百代之言泉。展平生之素志,秉巨笔之如椽。作‘大明一统志’,以颂神功圣德之盖世,鸿图大业之齐天。”由此可推莫旦当时尚未作《大明一统赋》。另外,余光尚有《两京赋》;清代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七收帅机《北京赋》一篇[6]。此外,前举夏完淳《燕问》也可计入。
如此众多的京都赋,时间跨度几近整个明代,这在整个都邑赋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作家队伍的构成差异对京都赋的影响。明代都邑赋家既有身居庙堂的馆阁文臣,也有相当数量的中下层文人,这种庞杂的特点给明代都邑赋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京都赋。众所周知,京都是具有严肃政治意义的城市类型,尽管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功能的不断融合,京都往往也是一个王朝的文化中心或经济中心,但其作为政治中心、天子宸居的特殊地位却是无法代替的。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对于京都的认识必然会有很大差异,赋家在处理各种素材时与是否为帝王倚重有关,京都赋因此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上述诸位京都赋作者,像金幼孜、杨荣等人,都是永乐一朝的重要阁臣,位高权重。《明史·金幼孜传》云:“帝(按:指明成祖)重幼孜文学,所过山川要害,辄命记之,幼孜据鞍起草立就。”[7]4126杨荣在成祖初即位时便“受知”,后来“帝益重之”[7]4138。永乐十八年(1420),金、杨二人“并进文渊阁大学士”[7]4126。稍后的李时勉、陈敬宗等人,以及嘉靖、万历年间的黄佐、顾起元等也都长期任职馆阁,甚见亲任。因而,他们所作的京都赋,风格上总体呈显平正典雅;在取材上,他们多选一些与帝王活动密切相关之事,如对祭祀、讲武、朝贡等加以铺写。李时勉《北京赋》中写皇帝接受朝贺的场面:
乃服衮冕,御帝座。开九重之深宫,受万邦之朝贺,内侯甸而要荒,外殊方而异俗,胥近悦而远来,纷鼓舞而匍匐。方物溢而充庭。奓绚璨而骇瞩,率蹈舞于阶墀,效华封之三祝。[2]158
除此之外,在上述诸赋尤其是早期的金幼孜、杨荣等人的赋中,更是对整个皇城布局及其中的重要建筑的外观、功能等都作了详细交待*明北京皇城的大规模修建,直至永乐十八年(1420)方告成厥功,金幼孜等人都直接参与了此项工作。,特别是其中对于一些文化机构、藏书机关的描写,更是不惜笔墨。如金幼孜《皇都大一统赋》中云:
复有石渠天禄,以蓄图书。玲珑绮钱,照耀文疏。悬牙签之万轴,列缃帙之纷如。宛奎璧之宵映,璨藜灯之夜嘘。瀛洲文学之士,阆苑列仙之儒。备顾问于朝夕,咸钦仰于圣谟。[2]151
杨荣《皇都大一统赋》亦谓:
复有文翰之林,词艺之苑。处严密之清禁,列英华之妙选。优游庙堂之署,出入金銮之殿。擅瀛洲之美誉,承黼扆之清问。[2]152
明代前期诸帝多尚文好学,《明史·李时勉传》载,“(正统)九年,帝视学,时勉进讲《春秋》,辞旨清朗”[8],即可为金幼孜、杨荣之赋做注脚。
然而,正如北宋杨侃《皇畿赋》所云:“至于宫禁之深严,子未闻也。”[2]148上述场景并非任何人都有机会接触到。赋家必须要有极真切的宫廷体验,方能形诸笔墨,若赋家位卑职贱,在作品之中就很难对之进行刻画了,即使有,用的也都是粗笔。因而,虽然同样是京都赋,属于中下层文人的桑悦等人的赋作一般更注意表现一些更为广阔的城市生活画卷。桑悦的《两都赋》于帝王起居很少着意,倒是对诸多带有浓郁市井色彩的城市生活画面作了详细摹写。譬如,在《南都赋》中,他写了南京纺织业的发达,写了“公子王孙”的游艺活动,还写到了“大比之秋”南京科场的群生百态。在《北都赋》中,他用一种几乎是猎奇的眼光写了活跃在北京城内的异邦之人:
按节长安之街,饮马玉河之堤。……或来东夷,或朝西域。置以会同之馆,攭以乌蛮之驿。观其翠发卷茸,绿睛转赤。绮衣并臂,文面穿鼻。露金齿之龂齿咢,摇环耳之琅咋。[9]
盛时泰《北京赋》以大量篇幅来写当时“市肆星罗”的盛况;余光《南京赋》中所写的珍宝、货贿的流通等,这些京都赋展现了北京、南京作为帝都的另外一面气象。
指出赋家队伍构成的差异对此类京都赋的影响,并非是刻意追求畛域分明。实际上,这也根本无法做到,因为具体到每一篇作品,情况是相当复杂的。譬如,黄佐在嘉靖年间曾官翰林,可是他的《北京赋》中除了写皇城内很多与帝王有着密切关系的建筑与活动之外,也细致刻画了当时长安街上人声鼎沸的生动场景和端午节时的君臣欢娱;莫旦只是一个普通举人,一生并未显达,可是,他的《大明一统赋》却极尽典雅。然而,这仍然是我们观察、理解明代京都赋艺术特色的一个重要角度。
三、明代都邑赋复古问题述评
明代文学特别是明代前、中期文学弥漫着一股浓厚的复古空气,当时一些传统文体如诗、文、赋等均走复古之路。《明史·文苑传序》云:
弘、正之间,……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瓠谈艺之士翕然宗之。[10]
针对诗文复古,明人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以秦汉文和盛唐诗作为榜样,而赋则要直承楚骚、汉赋的传统。明人何景明曾云:“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11]胡应麟也说:“骚盛于楚,衰于汉而亡于魏;赋盛于汉,衰于魏而亡于唐。”[12]尽管这种复古引起后人的尖锐批评,如清人即认为“明代文章自何李盛行天下,相率为沿袭剽窃之学,逮嘉、隆以后,其弊益甚”[13],但这种复古思潮的另一面则应当是明人鲜明的“尊体”观念。
具体到明代都邑赋,众所周知,以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为代表的京都赋是汉代大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代都邑赋的典范形态,因而明代都邑赋的复古无疑是以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为学习的榜样。对此,马积高先生曾有过简当的描述:
两汉的作者描述的多为大都、大邑,篇幅一般也比较大;魏晋至隋,题目小、篇幅短的渐多,但大题目的大篇仍不少;至唐而小题、小篇占主导地位,大题、大篇很少;宋元大题目虽较多。但描述多趋于简省,篇幅大的殊少。至明,则又以大题目、大篇为主。成化以后之都邑赋结构尤为庞大。汉以后渐少见的罗列名物,多用奇字、难字的现象又进一步出现。[14]
这段话所包含的最明确的一层意思是:魏晋以降,最能继承汉代京都大赋衣钵者,即为明代都邑赋。
然而,在仔细考察明代都邑赋之后,仍然发现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明代都邑赋并非一开始即完全步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明初金幼孜、杨荣等人的《皇都大一统赋》尽管也是京都题材,却和汉代京都赋有着诸多不同,具体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从体制上看,这些赋没有遵循“述客主以首引”的问答结构;第二,从词采上来看,这些赋大多没有汪洋恣肆的气势,谈不上“极声貌以穷文”[15]。但这些赋都不约而同地舍弃了骈赋、律赋体制,为以后明代都邑赋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成化以后,都邑赋迎来了复古的高潮(这正好与明代诗文复古思潮同时)。这一时期出现了桑悦的《两都赋》、余光的《两京赋》,还有《历代赋汇》所收阙名之《蜀都赋》等。仅从题目上看,这些作者学习的就是汉代京都赋,若论其结构之庞大,比起汉赋有过之而无不及。晚明夏完淳的《燕问》也是模仿唐代柳宗元的《晋问》。黄佐《粤会赋》序云:
佐自幼知读书,十有二而举子业成,乃更学古文、辞赋,尝撰《赵都赋》以拟左思。[2]167
丘濬《南溟奇甸赋》、莫旦《苏州赋》分别设“翰林主人”与“奇一士”、“鲈乡子”与“客”主客问答,其赋的主体结构也如赵逵夫先生所言:
这种以问答对话的形式将整篇文章装进去的方式,……从全篇来说,以问对为框,以赋的描述部分为画面,但这画面不是一个整幅,而是多片拼接成的。[16]
不仅如此,在一些都邑赋中甚至还吸收了七体赋的结构,如《苏州赋》前半部分基本上采用的是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的模式,即散体对话+多片段韵文+散体对话,而到了后半部分,节奏陡然加快,改用七体连续问答结构,一问一答,环环相扣,饶有趣味。《大同赋》的后半部分,也采用了这种结构。以七体写都邑,始于唐代柳宗元的《晋问》,而后北宋都颉《七谈》、南宋孙因《越问》嗣其响,但是将七体结构放在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式的大结构中,明代都邑赋当为首创,这一点应当引起注意。
明代都邑赋的复古,最受争议者不在体制,而在语言。因为汉赋最为人们诟病的即是其语言难懂,汉赋中大量出现的“玮字”*“玮字”是指一种非常怪异、常用汉语中很难见到的字,一般以形容词和名词居多。严重限制了人们对它的亲近,而明代都邑赋规摹汉大赋的一个重点即在其语言。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
首先,毋庸讳言,明代都邑赋特别是成化以后诸赋中出现的大量“玮字”是明人醉心于复古的直接产物。在桑悦等人的赋中,有很多字直接可以从班、张赋中找到,特别是某些表状态的形容词,这很难说不是一种迂腐和倒退。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正如前文所言,明人复古暗含强烈的“尊体”意识,而汉大赋之所以能示人以巨丽之美,很大程度上要靠这种“玮字”,明人既然尊崇汉赋,为了能在艺术风貌上追步之,采取这种做法也未尝不可。其次,由于明代的社会土壤与汉代有着某些相似之处,譬如都是大一统的强大帝国,久已隐没的朝贡体系在明代前、中期又得以重新确立,这些都为“玮字”的重新出现提供了某种相似的外部条件。最后,明代都邑赋中出现的一些语言陌生化的倾向,源于明代社会出现的一些新事物、新气象,未可一概以复古涵盖之。譬如在汉代京都赋中,称外邦异族仍是按古制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其间多有难以坐实之处,但是在明代都邑赋中,这些指称得到明确化、具体化。如莫旦《大明一统赋》中提及“天下一统之外夷”的诸多番邦,只要取《明史》一比参就可明了。黄佐《粤会赋》中提到的诸多异国珍宝,都是当时中外贸易所实有,未可一概斥其虚妄。
四、《朝鲜赋》与《交南赋》——兼谈明代中外交往与都邑赋之关系
明孝宗以后,赋坛出现了两篇异域赋——董越的《朝鲜赋》和湛若水的《交南赋》,这是明代都邑赋的重大突破。因为在此前,无论都邑赋所关注的地理区域怎样广阔,基本上仍限于王朝统治范围之内,而此时出现的《朝鲜赋》和《交南赋》却是以异国为创作对象,这在整个都邑赋发展史上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大事件。 《朝鲜赋》作于弘治元年(1488)董越出使朝鲜归来。《四库全书总目·〈朝鲜赋〉提要》云:
孝宗即位,越以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同刑科给事中王敞使朝鲜,因述所见闻,以作此赋。又用谢灵运《山居赋》例,自为之注。所言与《明史·朝鲜传》皆合,知其信而有征,非凿空也。考越自正月出使,五月还朝,留其地者仅一月有余,而凡其土地之沿革、风俗之变易以及山川、亭馆、人物、畜产,无不详录。[17]
《交南赋》的创作缘由及时间,赋中自序云:“予奉命往封安南国王晭*晭,指黎晭。《明史·安南传》载:“晭,一名滢,(正德)七年受封,多行不义。”与赋序合。详见《明史》第27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313页。,正德七年(1512)二月七日出京,明年正月十七日始达其国。睹民物风俗,黠陋无足异者,怪往时相传过实。托三神参订而卒归之于常,作《交南赋》。”[18]依此序可知亦因湛若水出使而作。
西晋左思《三都赋序》云:
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扬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观土风。见“绿竹猗猗”,则知卫地淇澳之产;见“在其版屋”,则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19]
《朝鲜赋》和《交南赋》的创作初衷,正是要呈现一个真实的异国图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两赋的作者特别是董越用了巨大的心思。《朝鲜赋序》云:
予使朝鲜,经行其地者月余。凡山川风俗人情物态,日有得于周览咨询者,遇夜辄以片楮记之,纳诸巾笥。然得此遗彼者尚多。竣事道辽,息肩公署者,凡七日。乃获参订于同事黄门王君汉英。[2]172
寥寥数语,却能让人深刻感受到赋家创作态度之严肃。
正是有了这种严肃的创作态度,我们才得以一赋而睹一邦。《朝鲜赋》中写到朝鲜民众诸多的生活方式、习惯,以及男女、职业、等级的严格限制;《越南赋》中描绘的越南朝廷待客礼仪,以及因常年多雨而采取的诸多迥异于中土的居住方式等,都极具认识价值。尽管两赋相较,可明显察觉出明廷对于朝鲜和越南的不同态度,《交南赋》的翔实程度也远逊于《朝鲜赋》,但无论如何,两赋的出现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这一点是无法抹杀的。
必须指出,明代赋坛之所以能出现《朝鲜赋》和《交南赋》,决非偶然,主要是因为有适宜其滋生的社会土壤,这个土壤就是明代中外交往的扩大。明代的中外交往远较此前历代广泛、深刻。明代前期,朝贡体系得到恢复和加强,郑和下西洋就是这一时期中外交往的明证。到了后期,虽然这种体系本身开始瓦解,但随着海禁的解除,中外交往的程度却进一步加深,发生了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一次移民浪潮——下南洋,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极其罕见的。中外交往的不断发展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都邑赋作为一种与当下社会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赋体题材,也受沾溉至深。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首先,中外交往的扩大为都邑赋提供了宝贵的素材。按照传统的文化心理,大量异邦外族的归顺是天子“德化”的重要体现。明朝甫一建国,即与周边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明皇帝也年年接受外国朝贡。那些异邦外族除了派遣大量使臣朝贡方物之外,有时甚至由国王亲自司其责。这种盛况往往在都邑赋中得到体现。另外,天子苑囿中的珍禽异兽也多由异邦贡献,这也成了都邑赋的重要内容,和汉代的《两都赋》《二京赋》相比,此时朝贡的象、鹿、虎等都能在《明史》诸本纪中找到,更加真确。而数量众多的外国人的来临,也给北京、南京、苏州、广州等大都会带来了浓郁的异国情调,这在前述诸篇京都赋和写广州、苏州等的都邑赋中都有生动描写。
其次,中外交往的扩大使都邑赋的外交职能得到充分体现。刘师培云:“诗赋之学,亦出于行人之官……盖采风侯邦,本行人之旧典。”[20]赋体文学本来就具有鲜明的外交功用,明代的不少都邑赋就因外交而作。如桑悦《两都赋》后记云:
臣……之京,每见安南、朝鲜进贡陪臣,寻买本朝《两都赋》,市无以应。臣私念我朝圣圣相承,治隆唐虞而反无班孟坚、张平子等颂德之臣,非缺典耶?……(是以)衍成二篇,……传示四方以及万世。[21]
《朝鲜赋》写成以后,在日、韩等国都出现了大量钞本、刻本,也足以证明此赋在外交活动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最后,中外交往的扩大促使出现了一大批描写异国风物的赋作。香港学者饶宗颐在《选堂赋话》中曾云:
湛若水以正德八年正月奉命往封安南王,至其地因撰《交南赋》,以存故实。朱舜水于丁酉三月在越南供役,作《坚确赋》。……明陈乃玉为《噶喇巴赋》,……文载《开吧历代史记》(《南洋学报》第九卷第一辑)。噶喇巴,即今印尼耶加达也。梅县罗芳伯于坤甸东万律撰《游金山赋》,……文虽庸近,自是写实之作。……上举诸赋,皆咏南裔海外邻邦,虽非杰构,亦足为考史之助。[22]
明赋中出现的写异域风光、民俗、物产的作品,若论其贡献,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若论其根源,则终需落实到明代中外交往的大背景中。
[1]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121-124.
[2]陈元龙.历代赋汇[G].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3]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72.
[4]冯福祥,王之臣.[民国]朔方道志:第4册 [M].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0:1465.
[5]陈天资.东里志[Z].王琳乾,校.汕头:饶平地方志办公室,1990:338.
[6]于敏中.日下旧闻考:第1册[Z].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109-112.
[7]明史:第1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明史:第1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4:4423.
[9]马积高,曹大中,常书智.历代词赋总汇:第6册(明代卷)[G].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5318.
[10]明史:第2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4:7307.
[11]吴文治.明诗话全编:第3册[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260.
[12]胡应麟.诗薮·内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6.
[13]谢国桢.黄黎洲学谱[M].2版.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76.
[14]马积高.读《历代赋汇》明代都邑赋[J].中国文学研究,1999(1):39.
[15]刘勰.文心雕龙[M].冰心主人,标点.上海:大中书局,1932:51.
[16]赵逵夫.《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J].文学评论,2003(1):72.
[17]永瑢.四库家藏:史部典籍概览:第2册[G].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526.
[18] 增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增城县志[Z].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779.
[19]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74.
[20] 刘师培.论文杂记[M]∥中国文学讲义.扬州:广陵书社, 2013:192.
[21] 黄宗羲.明文海: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17.
[22] 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16册[G].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469-470.
(责任编辑:袁 茹)
2016-12-05
王树森,男,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唐代诗歌、历代赋学研究。
I207.224
A
2096-3262(2017)02-004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