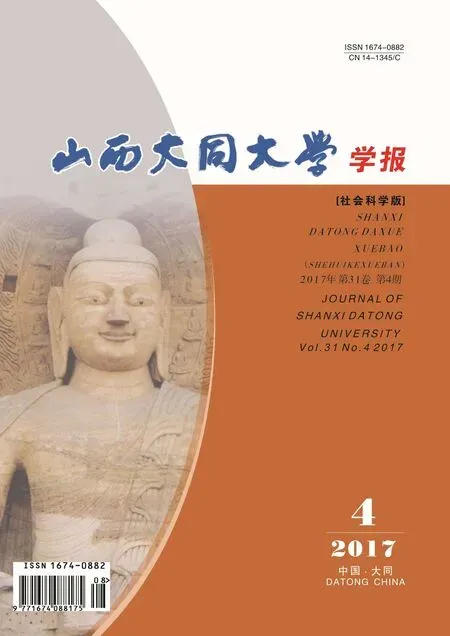《追风筝的人》中阿米尔的“伤”
王 燕
(山西大同大学外国语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追风筝的人》中阿米尔的“伤”
王 燕
(山西大同大学外国语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追风筝的人》是阿富汗裔美籍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处女作。小说展示了20世纪70年代的阿富汗社会,讲述了富贾之子阿米尔与其仆人哈桑的友谊以及阿米尔童年的心理创伤事件。通过深入探讨阿米尔遭受童年创伤前后的心理状态,揭示童年的心理创伤以及父亲带对他人生成长的深刻影响。创伤记忆也是阿米尔敢于在移居美国多年后重回阿富汗实现自我救赎的根源所在。
创伤;记忆;救赎;复原
小说《追风筝的人》于2003年在美国出版。作者卡勒德·胡塞尼以平淡细腻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关于爱与友谊、背叛与救赎故事。小说中生动鲜明的人物刻画、扣人心弦的心理描写,引人入胜的情节安排,饱满真挚的情感抒发,令人感慨万千。因此一出版便受到广泛的关注,之后又翻译为42种语言,全球热销上千万册,创造了销售奇迹,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如今,《追风筝的人》更是作为美国文学的经典之作被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列为新生必读书。与此同时,该小说也开始受到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并从各个角度进行分析。其中,背叛与救赎主题、风筝的隐喻及象征意义、成长小说、离散族群的文化身份认同、战争的残暴与种族歧视等都是研究的热点。本文试图以创伤理论解读主人公阿米尔的心路历程,从而揭示其童年的创伤以及创伤记忆。
一、创伤与“创伤”理论
众所周知,创伤属于心理学范畴。传统创伤理论主要发轫于弗洛伊德的创伤心理学。他认为,当大脑在抵制有害刺激时有可能发生错乱,而这种错乱便是普通的创伤性精神疾病。当有害刺激突如其来令人防不胜防时,人就会感受到巨大的情感冲击。这种冲击又会使受伤者一次次地无意识重复伤害事件,并试图掌控冲击所带来的焦虑、惊骇等情绪。[1](P169)20世纪90年代初,耶鲁大学教授凯西·卡鲁斯将创伤理论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她将“创伤”定义为某些人“对某一突发性的灾难事件的一次极不寻常的经历”。她认为,灾难事件发生后,人们的心理上会推迟出现对该灾难事件的反应,甚至会反复出现幻觉,根本无法得到控制。换句话说,灾难会给人们内心留下创伤,但这种心理创伤并不与灾难事件同时发生,或同步进行,而是出现在灾难事件发生后的某段时间,出现在人们对灾难的回忆中。灾难受害者未来的生活也会因灾难事件在其心理留下的阴影与伤害而受到巨大影响。[2]
小说《追风筝的人》便讲述了这样一个有关心理创伤的故事:生活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富家少爷阿米尔与家仆的儿子哈桑从小一起长大,形影不离。尽管两人身份地位悬殊,但却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友情。然而,这段纯真的友谊却因十二岁的阿米尔亲眼目睹哈桑被强暴却未加干预而蒙上阴影。为了摆脱痛苦的记忆,同时不再承受良心的煎熬和道德的拷问,阿米尔又栽赃哈桑偷东西从而迫使哈桑随其父阿里远走他乡。然而,阿米尔对自己的背叛行为却无法释怀,哈桑像一只顺从的待宰羔羊般被阿塞夫欺辱的画面时常出现在眼前,令其痛苦万分。作者就这样用平实的语言向读者揭示了阿米尔所遭受的童年创伤,讲述了阿米尔内心痛苦的挣扎。
二、阿米尔童年时的心理创伤
小说一开篇,作者胡塞尼以倒叙的方式将我们从2001年的美国旧金山带回到上世纪70年代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小说的主人公阿米尔出身于喀布尔的首富之家,是普什图人,也是精英阶层的代表。而与其一起长大的哈桑,是阿米尔家仆人的儿子,他是哈拉扎人,代表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3](P143)然而两人的共生共存关系并未因为阶级的差异受到影响。直到阿米尔遭受到心理创伤,他的成长道路才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一)创伤事件前——阿米尔无忧无虑的童年在小说中,作者借助阿米尔的口吻向我们讲述了自己12岁前快乐无比的童年时光:阿米尔和哈桑常常一起爬到自家车库旁边的白杨树上,拿一块镜子反射日光来捣蛋。他俩面对面坐在树梢上,光着的小脚丫晃来晃去,裤兜里满满塞着各种好吃的小零嘴儿,有桑果干儿,还有核桃。两个小家伙一边玩着镜子,一边用桑果干儿互相打闹。哈桑会在阿米尔的再三央求下,用弹弓打邻居家的独眼德国牧羊犬,其父阿里得知时常常会责备哈桑,但善良的哈桑却从来不会告阿米尔的状。他们一起去看电影、打扑克、爬山、放风筝,阿米尔朗读故事给尚不识字的哈桑听,在他们经常玩耍的石榴树上刻下自己的名字:“阿米尔和哈桑,喀布尔的统治者”。[4](P3)两个小男孩嬉笑着,打闹着,一天天长大……作者就这样用简单的语言向我们呈现出一幅充满童趣的画面。两个纯真的小男孩,两张稚嫩的笑脸,两个单纯而美好的生命,无忧无虑的童年,一起长大的伙伴。我们似乎已经看到长大后的两个人,互相依存,成为一生的伙伴,一世的兄弟,一辈子的挚爱朋友,彼此的生命里都留下对方深刻的烙印。然而,命运似乎却与他们开了一个玩笑,在阿米尔12岁那年发生的一件事,永远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二)创伤事件——阿米尔童年的“殇”在小说中,作者巧妙地将阿米尔童年快乐的巅峰时刻与童年的结束结合在一起,这种安排充满悬念,张力十足,令读者心理落差极大。喀布尔的冬天是放风筝的季节,放风筝作为阿富汗古老的习俗,十分受孩子们的欢迎。参赛者需要将自己的风筝放飞到天空中,同时还要用自己的风筝线将对手的风筝线割断,而最后一只飞翔在天空中的风筝即为获胜者。而追回那只最后被割断的风筝的人便会被大家不约而同的看做是勇气与智慧的化身,成为大家心目中的英雄。[5](P74)每个孩子早早就开始为放风筝比赛做准备,阿米尔和哈桑当然也不例外。起初,他俩总是亲手制作风筝,后来由于手艺不佳,便由阿米尔的父亲带他们去喀布尔最著名的风筝匠人处去买风筝。阿米尔12岁的那年冬天,放风筝比赛即将在阿米尔家所在的街区举行。阿米尔心里明白,在强壮而勇敢的父亲眼里,阿米尔一点不像自己的儿子,也不像个男孩子,不喜欢踢足球,相反只喜欢埋头读书和安静地写故事。他是胆小怯懦的,并不是父亲心中期望的“儿子”的样子。因此,这次比赛对阿米尔非常重要,它是让父亲对自己刮目相看、彻底改观的唯一途径。于是阿米尔暗下决心,立志要在风筝比赛中拔得头筹。风筝比赛如约而至,望着在自家阳台上观看比赛的父亲,阿米尔既紧张又兴奋。阿米尔这次并没让父亲失望,在比赛的最后关头,他如愿割断了那只蓝色风筝,获得比赛的冠军。就在阿米尔收风筝线时,哈桑上场了。作为追风筝的高手,他为阿米尔追到了那只梦寐以求的蓝色风筝,却在后巷和曾经有过节的恶少阿塞夫狭路相逢。后者提出只要哈桑交出风筝便可放他一马,然而,为了保护阿米尔的胜利果实,哈桑甘愿选择自己受辱,他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一样被阿塞夫强暴了。这一切都被躲在巷口的阿米尔目睹了,但他却并未加以制止。事实上,阿米尔的内心也曾经有过挣扎,他也想像哈桑曾经无数次奋不顾身替自己解围一样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制止阿塞夫,救出哈桑,然而他并未这么做。一方面,是他的怯懦的性格使然,他害怕阿塞夫伤害到自己,也害怕失去那只能够赢回父亲的心的蓝色风筝。另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他认同阿塞夫的种族主义观念,认为哈桑是低贱的哈扎拉人,是在某些利益面前可以舍弃的“车”。为了能够保住蓝色风筝这个“帅”,阿米尔沉默了,背叛了忠诚的哈桑。
至此,在短短的一天之内,阿米尔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别人眼里,他是风筝大赛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在自己心中,他却是个十足的胆小鬼、懦夫。如此这般,从云端到谷底,情感的落差一落千丈。由于这件事情的刺激突如其来,阿米尔没有丝毫防备,因此,对他产生了巨大的情感冲击。同时,在该事件的刺激下,阿米尔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提前结束,纯真的童年也夭折了。[6](P66)这件事情也变成了阿米尔童年挥之不去的“殇”,成为他日后成长道路上挥之不去的痛。同时,也正是由于“殇”的存在,阿米尔才会在多年之后,有勇气面对自己昔日的过错,百转千回地踏上自己的精神救赎之旅。
(三)创伤事件后——阿米尔的创伤记忆心理创伤是创伤理论中最基本的概念。它是指某一事件或灾难给受害者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害。[7]该灾难性的刺激发生后,阿米尔受到了心理创伤,开始体会到延迟出现的各种刺激反应,后巷发生的那一幕不断在眼前重演,那只斜倚在角落里的蓝色风筝和哈桑被扯掉的棕色灯芯绒裤子就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像来自过去的幽灵般缠着他,令他无法释怀。以至于在以后的岁月里,阿米尔都感到无所适从,他无法面对哈桑,更惧怕看到哈桑,每次与哈桑相见,当日后巷所发生的一切便会立刻出现在眼前。除了该事件本身令他难以接受之外,刺激发生时,阿米尔转头跑掉的处理方式也令他难以接受。事实上,心理创伤的程度除了受灾难事件本身影响外,受害者对事件的暴露程度,受害者当时的主观反应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8](P17-26)面对哈桑一如既往的照顾,阿米尔选择了逃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尽可能地减少与哈桑接触的机会。然而,创伤记忆是如此深刻,根本无法轻易抹平;道德的拷问是如此严厉,让阿米尔终于不能承受。于是,阿米尔开始想办法将哈桑从他的生命中彻底抽离。阿米尔13岁的生日很快来临,父亲为他筹备了盛大的生日派对,受邀参加派对的客人当中,居然有当日对哈桑施暴的阿塞夫和他的帮凶,看到站在父母中间,朝着自己咧嘴笑的阿塞夫,阿米尔顿时觉得头晕目眩,听到父亲对阿塞夫亲切的称呼更令阿米尔难过异常。阿米尔终于无法忍受,向门外的空地跑去……事实上,阿米尔与灾难施暴者阿塞夫的重逢,意味着现实强迫他再一次重温该刺激性事件,痛苦的记忆再一次将阿米尔吞噬,他受到了创伤后精神障碍的困扰。为了能够摆脱内心痛苦的煎熬,阿米尔诬赖哈桑偷了自己的手表。因为他知道,在正直果敢的父亲看来,偷盗是罪无可恕的。在阿米尔的设计下,哈桑随父亲阿里搬离了阿米尔家,远走异乡。阿米尔的这一举动,其实是他为了能够摆脱创伤记忆的折磨,摆脱道德拷问而启动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时光荏苒,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阿米尔与父亲移居美国,然而这段创伤的记忆却无法褪去,相反他却一直生活在痛苦和自责中。在美国,阿米尔遇到了同是来自阿富汗的姑娘索拉雅,并对她一见倾心。索拉雅开诚布公地将自己曾经不光彩的过去告知了阿米尔,并且得到了阿米尔的谅解。然而,在内心深处,阿米尔期待有朝一日自己能够有勇气向妻子坦诚自己过去曾经犯下的罪行,并且获得妻子的宽恕,从而解开自己身体和灵魂上的双重枷锁,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生活。这一刻,阿米尔等了15年。夫妻二人结婚15年却没有孩子,在收养孩子这件事上也一直不愿意松口。而对于没有孩子这一事实,阿米尔心中也有他自己的解读:也许在某个地方,我对某个人,做的某件事,否定了我做父亲的权利。以此作为对我的惩罚,对我的报复。[4](P204)由此可见,来自于阿米尔童年时代的刺激,在他的心理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和深刻的伤害,而这种心理阴影和伤害持续发生作用,使阿米尔成年后的生活也受到影响。
三、父亲与阿米尔童年创伤的关系
(一)父子关系的疏离 阿米尔出生后几天,他的母亲便去世了。阿米尔从小由父亲独自抚养,按道理,这样的父子关系本应该非常牢靠。然而,作者勾画出来的图景却并非如此。父亲是喀布尔赫赫有名的商人,也是阿米尔心中真正的男子汉,是他所崇拜的英雄式人物。也许是因为阿米尔的出生导致了父亲深爱的母亲的死亡,父亲对阿米尔的要求非常严苛,在父亲眼中,阿米尔却胆怯软弱,不具备男孩子应有的勇气。父亲曾经对自己多年的好友拉辛汗抱怨,如果不是亲眼见到妻子生下阿米尔,他怎么也不会相信阿米尔是自己的儿子。父亲对阿米尔的种种不满与鄙夷,令阿米尔对深受父亲喜爱的哈桑非常厌恶,充满敌意。他认为哈桑是自己的仆人,是下贱的哈扎拉人,不配得到父亲的喜爱。这一切让阿米尔焦虑异常,唯恐失去父亲的爱,不自觉地陷入与哈桑争夺父亲的关爱的漩涡中。因此,一年一度的风筝比赛是阿米尔重新赢回父亲的唯一筹码。在遭遇后巷发生的事情时,阿米尔内心也有过挣扎,但是对于12岁的孩子来讲,父亲的爱是他必须要争取的,而哈桑就成了为此必须付出的代价。疏离的父子关系让阿米尔在遇到后巷事件刺激时,在搭救哈桑和修复破碎的父子关系之间本能地选择了后者,同时,这件事成为阿米尔童年永久的创伤,成为他一生的隐痛。
(二)父子关系的和谐 到了80年代,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后,阿米尔先随父亲移居巴基斯坦,然后又移民美国。阿米尔心中十分庆幸,美国对于他而言是埋葬过去、重新开始的地方。相比于阿富汗的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生灵涂炭,美国充满了美好的希望:交通便利,物产丰富,生活平静而优越,更为重要的是没有了哈桑——这个父爱的争夺者。[9](P130-135)而对于父亲而言,美国却是极其无奈的选择,是彻底的失去。由于阿富汗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弥漫的种族主义,父亲无法认回自己的私生子哈桑,又为了让身边唯一的儿子阿米尔免受战乱之苦,他们来到了美国。在美国,父亲不再是那个出生于名门望族,几乎能呼风唤雨的富商,不再是主流社会的一员,不再是精英阶层,他成了来自阿富汗的难民,成了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在失去往日的光辉岁月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阶层。[6](P66)父亲在加油站辛苦工作,为了能维持一家的生计终日奔波,双手布满老茧。然而,父亲却仍有自己的骄傲,宁肯周末去跳蚤市场摆摊,也不愿接收免费的食品救济券,用自己的辛勤劳作撑起这个家。阿米尔就这样与父亲相依为命,父子关系回归和谐。父亲去世后,阿米尔从父亲的好友拉辛汗处得知哈桑竟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父亲隐瞒此事的行为令阿米尔在惊愕之余,更加愤怒不已。父亲是有罪的,自己又何尝是清白的呢?面对折磨了自己二十几年的创伤记忆,阿米尔必须回到阿富汗,找到哈桑的儿子索拉博,从而真正完成灵魂的救赎。为了救出索拉博,不占任何优势的阿米尔勇敢地面对他心理创伤始作俑者阿塞夫,被他打得遍体鳞伤,但阿米尔却大笑着,完成了自我救赎的同时,心理创伤也得到复原。
综上所述,童年的创伤给阿米尔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和伤害,对他成长心理产生了持续的影响,数十年来阿米尔始终深陷在在创伤记忆中,即使自己一路拼搏,成为一名作家却无法开始真正地幸福生活。童年时父子关系的疏离是阿米尔遭遇童年创伤事件的主要诱因之一,而父子关系在美国的重新构建也是阿米尔最终能够有勇气踏上自我救赎之旅,追求创伤后复原的心理动力。
[1]杨晓.新兴“创伤文学”理论对创伤小说的成功诠释——评米歇尔·巴勒夫《美国创伤小说的实质》[J].外国文学研究,2013(01):169.
[2]Caruth,Cathy.Trauma:Explorations in Memory[M].Baltimore&London:The John Hopkins UP,1995.
[3]Algoo-Baksh,Stella.Ghosts of the Past[J].Canadian Literature,2005(Spring):143.
[4]Hosseini,Khaled.The Kite Runner.New York:Riverhead Books by Penguin,2007.
[5]郑素华.《追风筝的人》主人阿米尔的人格成长——从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角度解读阿米尔的三重人格[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1):74.
[6]Pearson,Geraldine S.The Kite Runner Book Review[J].Journal of Child&Adolescent Psychiatric Nursing,2007(01):66.
[7]Caruth,Cathy.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 History[M].Baltimore&London:The John Hopkins UP,1996.
[8]Pfefferbaum,Betty.Aspects of Exposure in Childhood Trauma:The Stressor Criterion[J].Acute Reactions to Trauma and Psychotherapy:A multidisciplinary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2005(E.Carden&K.Croyle):17-26.
[9]王慧敏,荆蓁.身份流散下的精神守望与追寻——论《追风筝的人的流散主题与身份建构》[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6(02):130-135.
On Amir’s Childhood Trauma inThe Kite Runner
WANG 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xi Datong University,Datong Shanxi,037009)
The Kite Runneris a haunting and quite extraordinary first novel by Khaled Hosseini.It’s a touching and memorable story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wo boys,Amir and Hassa,of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and ethnic backgrounds.The brutal assault against Hassan is witnessed by Amir,who did not intervene.And this event haunts Amir like a ghost throughout his life as a childhood trauma,makes him suffer from the traumatic memory.Meanwhile,the father-son relationship has a quite close connection with his trauma and his redemption.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mir’s childhood trauma,and his father’s influence on the traumatic event.
trauma;memory;redemption;recovery
I712.84
A
〔责任编辑 裴兴荣〕
1674-0882(2017)04-0070-04
2017-04-25
王 燕(1978-),女,山西大同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英美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