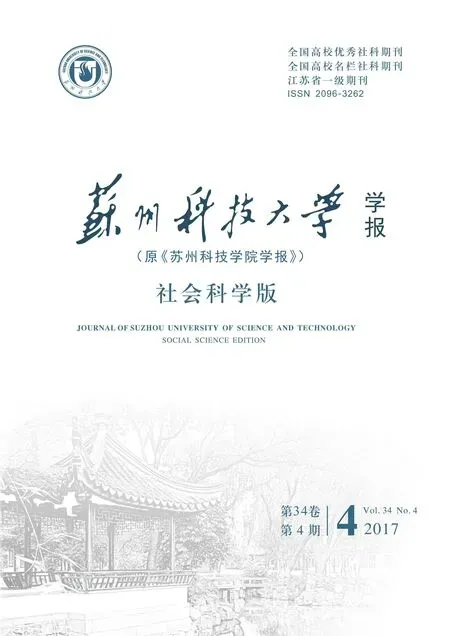试论张爱玲对丁玲创作精神的承续
——以《沉香屑 第一炉香》和《梦珂》为考察中心
陈娇华
(苏州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试论张爱玲对丁玲创作精神的承续
——以《沉香屑 第一炉香》和《梦珂》为考察中心
陈娇华
(苏州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丁玲的创作精神对张爱玲有明显的影响,尤其表现在《第一炉香》对《梦珂》在情节模式、内涵意蕴及艺术表现等方面的承续。两篇处女作都以出走与沉沦作为情节模式,以性别关怀和存在叩问为内涵意蕴,以女性心理刻画和隐性叙述为艺术表现手法。这既是张爱玲喜爱丁玲早期作品并深受其影响所致,也是她们在关注和思考女性人生命运和生存境遇方面前后相承的结果,更与她们对文学创作艺术性的执著追求有关。然而,由于她们身世经历、个性气质、文学修养、创作意图等不同,两篇作品的相异性也很显然,正是这种相异性决定了她们日后创作的不同发展趋向。
张爱玲;丁玲;女性文学;第一炉香;梦珂
众所周知,张爱玲的文学渊源主要是旧派小说和西洋文学,她对“五四”新文艺则无甚好感[1]。在谈到40年代最时髦的冲淡文章时,她说:“因为一倡百和,从者太多,有时候难免有点滥调,但比洋八股到底是一大进步。”[2]97她给夏志清的信中也说:“根本中国新文艺我喜欢的少得几乎没有。”[3]事实上,“五四”新文学也是张爱玲创作的重要文学渊源之一。她读过老舍、沈从文、钱钟书等人的作品,也读过陈衡哲、冰心、丁玲等女作家的作品。相较而言,她对丁玲创作比较关注,曾经想研究丁玲早期小说,并难得地对之表达过好感,认为“丁玲的初期作品是好的”[2]91,觉得“宋淇最注重她以都市为背景的早期小说,大概觉得较近她的本质”[3]181,这其实也是张爱玲本人对丁玲早期小说的一个看法。尽管夏志清扬张贬丁,认为“张、丁二人的才华、成就实有天壤之别,以张爱玲这样的大天才去花时间研究丁玲,实在是说不通的”[3]183,但毋庸置疑,张爱玲确实关注过丁玲创作,且她的作品有着抹不去的受丁玲影响的印迹。笔者拟从情节模式、内涵意蕴及艺术表现等方面,探讨《沉香屑 第一炉香》(以下简称“《第一炉香》”)对《梦珂》创作精神的承续。
一、情节模式:出走与沉沦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许找不出两篇像《第一炉香》与《梦珂》这样在情节模式上如此相像的作品。《梦珂》写的是少女梦珂离开湖南老家到上海求学,因在学校声援被男教员侮辱的女模特而被迫辍学,寄居姑母家。在姑母家中,喜欢上一位表哥,但表哥并不爱她,只是想玩弄她。于是,她离开姑母家到社会上自谋出路,最后在某剧社声色犬马的生活中沉沦下去。《第一炉香》写的是少女葛薇龙因上海战争爆发随父母到香港求学,但父母后来要回上海,薇龙不愿中断学业跟着回去,就寄居香港姑母家。在姑母家里,薇龙遇到了浪荡子乔琪(又叫乔琪乔)并爱上他,而乔琪并不爱她。薇龙知道乔琪不爱她,却无法抗拒他的诱惑,最后还是嫁给他。从此“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了给梁太太与乔琪乔,整天忙着,不是替乔琪乔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4]160。可见,两篇作品讲述的都是“出走与沉沦”的故事:女学生离家出走到大都市求学,中间因某种变故被迫寄居姑母家,并爱上姑母家或出入姑母家的某个男性,最后离开姑母家或是在姑母家沉沦下去。
两篇作品不仅人物身份及人物之间的关系具有相似性:梦珂和薇龙都是女学生,都寄居在姑母家中(《梦珂》中是堂姑母),且情节的转捩点和结局也大体相似。《梦珂》中的梦珂离开充满虚伪、丑恶的姑母家后,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回老家去;二是留在上海做工或读书或当看护,但都被她否定,最后进入某剧社。刚进入剧社,她看不惯某些演员的轻浮狎昵举动,警惕自己不要“变成妓女似的在这儿任那些毫不尊重的眼光去观赏”[5]39,为此“骇得晕倒”,这些都表明她潜意识中有过本能的反感和抗拒。但最后还是委屈自己,“继续到这纯肉感的社会里去”[5]40。《第一炉香》中的薇龙也是如此。离开姑母家,她可以选择出去做事或者回上海的家,但都被否定,最后留在姑母家沦为娼妓。刚到姑母家时,她觉得只要自己“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4]123。后来事情发展超出她的能力控制,身不由己地沦为姑母钓人的诱饵,特别是遇到浪荡子乔琪后,情不自禁地爱上他。乔琪虽喜欢她却不愿娶她,薇龙一度想回上海以示反抗,甚至为此病倒。即便这个时候,她还可以出去找事做,但都放弃了,最后嫁给乔琪,彻底沦为娼妓。
两篇作品如此相似,究其原因:首先,这与张爱玲喜爱丁玲早期作品并深受其影响有关。任何创造都是从模仿开始,张爱玲创作也不例外。丁玲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女作家,她的作品必会对后代女性写作产生影响。张爱玲一度喜爱丁玲作品。1936年,16岁的她在专门为丁玲小说集《在黑暗中》写的评论中认为:“丁玲是最惹人爱好的女作家。她所作的《母亲》和《丁玲自选集》都能给人顶深的印象。”[6]1974年,身处美国多年的张爱玲依然对丁玲小说保持着兴趣,准备对其进行研究,且托夏志清等好友帮忙查找和影印丁玲小说,这些“足以见出她对丁玲创作的某种认同和看重”[7]。因此,尽管张爱玲说过“根本中国新文艺我喜欢的少得几乎没有”[3],但不容置疑的是,包括丁玲《梦珂》等早期作品在内的新文学作品确实对其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次,“娜拉出走”时代思潮的影响也是重要原因。1918年6月《新青年》“易卜生专号”刊登胡适和罗家伦合译的《娜拉》全剧,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和文学界刮起一股强劲的“娜拉风”。“娜拉出走”成为“五四”以来新文学创作的重要话题,影响一直持续到三四十年代,涌现胡适《终身大事》、鲁迅《伤逝》、丁玲《梦珂》、白薇《炸弹与征鸟》、曹禺《日出》、巴金《寒夜》等书写“娜拉出走”式的作品。而张爱玲本身先后有出走父亲家和离开母亲家的类似经历,“娜拉出走”的情节模式必然会影响和沉潜到其潜意识深处,并不时外化在作品中,形成“娜拉出走”的情节模式原型。事实上,除《第一炉香》的薇龙出走外,张爱玲后来许多作品也出现这一情节模式,如《倾城之恋》中的流苏出走(逃离白家),《封锁》中的吴翠远出走(意念中的逃离“好人”),以及《小团圆》中蕊秋的出走(逃离夫家)等。因此,《第一炉香》与《梦珂》情节模式的相似既是作者无意识中“出走”情结的艺术外现,也是后者影响所致,是后者与张爱玲潜意识中的原型情节模式的暗合。最后,也是两位作家相类似的求学求职人生经历及其对女性情感命运深切关注导致的结果。丁玲和张爱玲都有过一段类似于笔下女性的求学求职经历,可以说两部作品都源自她们各自相似的一段人生经历。张爱玲曾离开上海到香港求学,丁玲离开湖南老家到上海求学。而且由于性别本能因素,两人都比较关注女性的生活情感和命运遭遇,她们笔下出现相似的“娜拉出走与堕落”情节模式自在情理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两位作家家庭身世、生活经历和个性气质不同,其作品情节模式的相异性也是显然。如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女性形象的性格心理及叙述者的情感态度,特别是情节故事的最后发展走向等有着显著不同。梦珂虽然最终选择委屈自己,隐忍着沉沦到“纯肉感的社会里去”,“忍受非常无礼的侮辱”,即沦落为男性中心社会消费和把玩的商品,但她始终是清醒中带着不甘和悲愤。这从结尾叙述者的语气和腔调中不难感受到。而沦为娼妓的薇龙对自身处境虽然也很清醒,但清醒中流露一种无奈与悲怆,这从结尾她与街头娼妓的自比中不难看出,她说:“她们是不得已的,我是自愿的!”[4]162因此,如果说梦珂的沉沦更多是由社会的挤压和逼迫所致,蕴含着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愤怒揭批和反抗;那么薇龙的堕落则更多出于人物的主动选择,她的消沉和萎靡体现了作者对人性弱点和“雾数”的清醒而深刻的彻悟。人是虚弱和卑怯的,人有时做不了自己的主!两篇作品情节最后发展的不同走向,既源于创作者不同的价值取向,也预示着她们日后创作的不同发展路向。
二、内涵意蕴:性别关怀与存在叩问
《梦珂》和《第一炉香》分别是丁玲和张爱玲的处女作,一开始便都显示出对女性爱情婚姻和人生命运的深切关注与思考。丁玲随后创作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暑假中》,与《梦珂》结集为《在黑暗中》。这些作品通过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的女性在黑暗现实中内心充满的性苦闷、痛苦、迷惘来表达个性解放的时代主题,体现了作者对女性个体生命和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注与思考。张爱玲随后创作的《沉香屑 第二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同样以言情模式关注女性婚姻情感和爱情心理上的痛苦与纠结。李欧梵指出:“张爱玲的绝大多数小说是围绕着婚姻和家庭人际关系的整个模式的……婆婆和儿媳妇间的矛盾,亲戚间的诡计,还有那更重要的男性用情不专。”[8]因此,张爱玲小说也是以书写女性的爱情婚姻情感故事来探讨女性的生命情感和生存境遇。可以说,《第一炉香》承续着《梦珂》的创作精神,也是由女性的爱情婚姻情感故事引发对于女性个体生存境遇和生命价值的终极追问与探索。
(一)对女性生存境遇和人生命运的关注
《梦珂》和《第一炉香》都体现了女作家出于性别意识对女性个体生存境遇和人生命运的关注,对迈出校门、走向社会的女学生职业与出路问题的探索。主人公都是女学生,内里精神气韵一脉相承。她们孤傲、纯真,不满周围生存环境,与之进行过抗争,但最终都放弃、沉沦。梦珂先是在学校声援女模特反抗男教员侮辱,维护女性人格和尊严,结果被迫辍学。在姑母家,她虽然一度被表哥晓淞外表迷惑,喜欢上他,但看穿他的虚伪、猥琐后,勇敢地选择离开,自谋生路。即使进入剧社,她的“晕倒”和“痛哭”仍彰显其沉沦前的犹豫和挣扎。薇龙也是如此。刚进入姑母家她就警示自己,要“行得正,立得正”。嫁给乔琪前,也闹着要“回去,愿意做一个新的人”[4]155,并为此大病一场。这些也体现了薇龙堕落前的惶惑与挣扎,但最终都放弃、妥协了。她们的沉沦经历展现了当时女学生由孤傲、纯真走向麻木、堕落的不幸命运遭遇,揭示了女性个体生存境遇的艰难及其沉沦的深层原因。一方面,女性的沉沦是由她们的生存困境决定的。“五四”个性解放的时代思潮唤起了沉睡中的女性,使她们迈出家门,走上社会;但社会并未给她们提供广阔的生存空间,也未给她们创造自由宽松的工作条件,她们不是成为女结婚员重回家庭相夫教子,就是走上社会成为花瓶式摆设或女职员,后者不仅工资低、工作环境恶劣,且诱惑和陷阱无处不在。梦珂和薇龙不愿成为清贫、困窘的女职员:一个进入“纯肉感的”剧社沉沦下去,一个堕入名为婚姻实则卖淫的娼妓生活中。可见,现代中国女性解放前进的步履之艰难、沉滞!另一方面,也与女性自身性格、人性的缺陷和“雾数”有关。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女性自身的虚荣心及人性的缺陷导致了她们的沉沦堕落。梦珂的沉沦除了社会逼迫外,如因声援被侮辱女模特而被迫辍学,姨母催婚使她不愿回家等。其实,这也与其虚荣心有关。她寄居姑母家,受表姊妹们奢华风气影响,追求物质享受,把父亲辛苦攒来的三百元买了貂皮大氅。自然地,她最后不愿选择清贫、艰苦的做工或看护生涯,也不会回去,而只能沉沦于演艺圈的声色犬马之中。特别是薇龙,进入姑母家的当天晚上,那满壁橱的绚丽衣服就给了她堕落暗示,她自己也意识到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人没什么区别,但还是陶醉其中不能自拔,沦为替姑母钓人的诱饵。就是嫁给乔琪前,她也有自救机会,去上海重新生活或出去找事做,但都放弃了。可以说,正是人性的贪欲和卑怯把薇龙一步步推进“无边的恐怖”。总之,《梦珂》和《第一炉香》不仅揭示了现代女性个体生存的艰难、困境,更进一步思考和探讨了现代女学生的职业化问题,关注她们的人生命运和生命价值。这些问题是从“五四”时期《洛绮思的问题》《海滨故人》等开启,经过《梦珂》《绮霞》等深化拓展,在《第一炉香》《半生缘》《结婚十年》等作品中得到承续发展,也是至今女性文学仍在思考和探讨的沉重话题,体现了女作家们鲜明的性别意识和性别立场。
(二)对女性爱情婚姻的关注与思考
《梦珂》和《第一炉香》对女性爱情婚姻的关注与思考也存在影响和承续关系。其一,女主人公都追求真挚爱情。青年男女追求爱情自由、婚恋自主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爱情自由、婚恋自主、性苦闷等成为个性解放的重要表征。梦珂不高兴姨母索婚,不愿回老家而寄居姑母家,喜欢上表哥晓淞,但表哥游戏感情的态度使梦珂的爱情梦幻灭。为了不愿见到那些虚伪、猥琐的人,她离开姑母家。这些都体现梦珂对纯洁真挚爱情的追求和对虚伪感情游戏的反抗。而她后来因“内在的冲动和需要”[5]36进入某剧社,沉沦到纯肉感社会游戏人生,这既是走投无路的无奈选择,也是对真挚情感绝望后的消极反抗,从反面印证了她对真挚爱情的追求。由此不难理解《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因追求不到灵肉合一现代爱情的莎菲的宁可一人“悄悄的活下来,悄悄的死去”[5]78的孤绝选择。薇龙一开始也是追求真挚爱情的,她爱上卢兆麟,但卢不久入了梁太太圈套,薇龙只好放弃,转而爱上浪荡子乔琪。初次见面,她便不可救药地爱上他。乔琪却说:“我不能答应你结婚,我也不能答应你爱,我只能答应你快乐。”[4]146明知得不到真爱,却无法抗拒他所引起的她那“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最后还是嫁给他。这是薇龙对真爱追求失望后的无奈之举,也是她遵循内在生命激情而做出的放弃自主意志的选择,更是作者勘破现实情感真相后的有意而为。如果说梦珂对真挚爱情的追求还停留在情感精神层面,薇龙则已深入个体生命内在的欲望层面。张爱玲承续丁玲关注女性情感生命的创作精神,深掘女性个体内在的生命欲念,写出了她们在自己情欲面前的卑微和无力。其二,两篇作品都强调爱情对于婚姻的重要性,认为没有爱情的婚姻实质等于卖淫。《梦珂》借梦珂与表嫂的谈话指出:旧式婚姻中的女子,嫁人也等于卖淫;而新式恋爱若只是为了金钱、名位,也是一样的。[5]28可见,丁玲对爱情之于婚姻重要性的强调,这种现代爱情观在她后来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得到强调和深化。如果说《梦珂》是从正面对这种观点进行强调,那么《第一炉香》则是从反面印证这一观点。薇龙深爱乔琪,可他只答应给她快乐,不能给她爱和婚姻,薇龙还是嫁给他。这样一来,她的未来便成了“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4]161。婚姻本是给人以情感温暖和现世安稳的,薇龙的无爱婚姻却将她推入黑暗的深渊,里面尽是恐怖和荒凉。薇龙对于无爱婚姻的清醒意识及由此而滋生的恐怖和荒凉感,显示张爱玲沿着丁玲对女性婚姻情感关系探索的创作路子,并向前掘入婚姻情感关系中个体的生命和存在体验,这是作者苍凉人生哲学和对于现世千疮百孔情感凄怆体验的艺术呈现。其三,两篇作品都对爱情婚姻中的男性持不信任态度。如果说晓淞对梦珂纯朴、真挚爱情的游戏玩弄,主要是为了促成梦珂离开姑母家,走上社会,有利于揭批黑暗现实和女性生存困境;那么,乔琪对薇龙爱情的背叛和亵渎,特别是薇龙婚后名为妻子实为娼妓的处境,则体现了作者对现实婚姻情爱关系及男性缺乏责任感和担当精神的清醒认识,流露出作者洞彻人性缺陷和“雾数”后的无奈与绝望。总之,这些爱情婚姻关系的处理既体现了女作家对于社会、人生及男性的清醒认识,也是她们自身情感心路历程的折射,体现她们内心对于理想爱情婚姻的追求和向往。
(三)对女性被商品化和物化命运的反抗与书写
《梦珂》和《第一炉香》还体现了女作家对女性被商品化和物化命运的反抗与书写。传统社会中的女性是“养在深闺人未识”,而“五四”后中国女性开始迈出家门,走向社会;但现代社会并未为女性提供广阔自由的发展空间。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左右,随着现代社会和城市的发展,刚摆脱传统束缚的女性不仅成为所谓新派男人欲望追逐的目标,还面临着被商品化和物化。梦珂和薇龙开始都警惕和反抗这种命运,但最终都妥协、放弃,沦为供男人消遣和把玩的商品。梦珂刚到上海不久,就警惕、反感那些“挤眉弄眼的男子”[5]16,在学校声援女模特反抗教员侮辱,她力避和反抗沦为男性消遣和泄欲的物品。没想到在姑母家,她不期然成为表哥消遣和猥亵的猎物,“表哥坐在一个矮凳上看梦珂穿衣……眼光便深深的落在这腿上,好像另外还看见了一些别的东西”[5]17,梦珂只好逃离。然而为了谋生,最终在某剧社,不得不忍受像“妓女似的在这儿任那些毫不尊重的眼光去观览”,沦为“空前绝后的初现银幕的女明星,以希望能够从她身上,得到各人所以捧的欲望的满足”[5]40。孤傲纯真的梦珂最终沦为男性社会消费和赏玩的物品。如果说梦珂的反抗和沉沦带着强烈的愤怒和绝望,那么薇龙的挣扎和堕落则无疑显得无奈与凄怆。薇龙刚到姑母家,也警示自己要“行得正,立得正”,抗拒来自司徒协金刚石手镯的诱惑,但梁府骄奢淫逸的生活及乔琪的魅惑使她迷失了自己,沦落为姑母的钓人诱饵和乔琪的挣钱工具,彻底被商品化和物化,最终只能在那些“琐碎的小东西”上找到暂时的慰藉和安稳。而沉醉于物品中的薇龙反过来也为这些物品所淹没,难以再生出反抗。人的渺小、生存的卑贱、人性的虚弱就在这些琐碎堆积的物品中得以凸显。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丁玲对女性商品化命运的书写具有揭批和反抗黑暗现实的意义,那么张爱玲对女性被物化命运的书写则显然超越了现实层面,直指女性个体的生存困境和人性缺陷,其形而上的人性探索与存在叩问意蕴昭然若揭。
因此,正如论者所言:丁玲是将女性生存的终极生命归属定格于现时存在,但不否定间歇性的形而上虚无;而张爱玲将终极生命归属定格于永恒的虚无,同时亦执着于世俗的存在。这种对终极价值和生命归属的思索和在创作中的渗透,使她们的作品不局限于政治学意义上的反封建主题,也不拘泥于社会学上的女性解放主题,而是抹去一切人为的面具和文明的遮掩,直指女性的生命存在实质和灵魂存在方式,作品于是显得切实而又格外的深刻,两人也在最深层的精神意义上形成了内在的沟通和相互比照的可能性。[9]
三、艺术表现:女性心理刻画与隐性叙述
如前所言,张爱玲曾专门为丁玲小说集《在黑暗中》写评论,虽然张爱玲对《梦珂》评价不高,但认为《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细腻的心理描写、强烈的个性、颓废美丽的生活,都写得极好”[6]。可见,张爱玲对丁玲作品阅读认真、细致,评论中肯、到位。这些评论丁玲小说的视角和话语必然会在她自己的创作中得到强化,形成张爱玲对丁玲创作上的延续关系。
(一)对女性情感心理的深刻发掘与细腻描写
丁玲以细腻、真实的心理描写写出了梦珂沉沦的过程。最初,梦珂与表哥们一起聊天、下棋时,对自己被赏玩和被消遣的处境缺乏意识,只全神贯注于自己的棋子,根本“没留心到对面还有一双眼睛在审视她纤长的手指”[5]15-16。而在剧社,对被观赏和被消遣处境的清醒意识把她“骇痴了”。那些人当着她的面品评她的容貌,像商议生意一样,气愤、羞惭使得她“不知应如何说话和动作了”[5]38。到最后,梦珂“见惯了,慢慢的可以不怕,可以从容,使她的隐忍力更加强烈,更加伟大,能使她忍受非常非礼的侮辱了”[5]40。可见,丁玲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把梦珂由纯真、懵懂的少女蜕变为麻木、颓废的演艺女郎的具体过程切实地书写出来,使得读者不由得去追究梦珂沉沦背后的深层原因:为什么一个纯真、孤傲的女学生会沦落为一个麻木、消沉的依靠姿色来生活的演艺女郎?张爱玲也细致地刻画了薇龙堕落的人性内因。与丁玲直接刻画不同,张爱玲以动作、言语、梦境及意象等进行间接刻画。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打成一片”,人物的“每一个举动,每一缕思维,每一段对话,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10]421。薇龙住进姑母家当晚,那满壁橱华服使她感觉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人没什么区别,梦中的她在一件件试穿,那种清凉柔滑感觉背后透露了薇龙潜意识的堕落欲念。后来请客宴上,身着磁青旗袍的薇龙,被乔琪撩拨得感觉自己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4]135,身不由己地爱上他。到最后,乔琪告诉她不可能给她爱和婚姻,她感觉“天完全黑了,整个的世界像一张灰色的圣诞卡,一切都影影绰绰的,真正存在的只有一朵一朵顶大的象牙红,简单、原始的、碗口大、桶口大”[4]158。明知前路是深渊,但无法遏制的内心欲念使她还是嫁给了他。薇龙的堕落印证了人性的卑弱,人在自己欲望面前的无力与渺小!事实上,丁玲和张爱玲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擅长刻画女性心理的作家,特别是女性情欲心理,这在她们后来各自的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和《金锁记》中不难看到。对此,夏志清认为,丁玲早期作品“大胆地以女性观点及自传手法来探索生命的意义”,“流露着一个生活在罪恶都市中的热情女郎的性苦闷与无可奈何的烦躁”[11]203。而张爱玲“对于人和人之间的微妙复杂的关系,把握得十分稳定”。《传奇》里的人“是地道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11]286。可见,这些心理刻画特征在她们各自的处女作里已初显迹象。不过,《第一炉香》中的女性情欲心理刻画尽管不如后来的《少帅》《怨女》等作品中那么大胆和赤裸,而是显得隐晦、含蓄,但与丁玲《梦珂》中的女性心理描写相比,已是前进多了,显得相当的大胆和深刻。
(二)隐性叙述的运用
两篇作品都运用了隐性叙述,即在作品故事背后存在一个客观、冷静的女性隐含叙述者,她在冷静、理性地审视整个故事发展及其中的男女,形成复调结构,丰富了作品的内涵意蕴。《梦珂》中,晓淞以诗歌挑逗梦珂,羞得梦珂先是用双手遮脸不敢抬头,继而“轻飘的跑走了”,而表哥倒在软椅上,“得意的称许起自己的智慧,自己审美的方法,并深深的玩味那被自己感动的那颗处女的心。这欣赏,这趣味,都是一种‘高尚’的,细腻的享乐”[5]25。这段叙述揭露了表哥对梦珂的把玩和戏弄,并为自己的游戏和玩弄手段得意。但细读后不难发现,在表哥的把玩和游戏背后还存在一个更隐匿的隐含叙述者对表哥玩弄感情游戏的观看、冷讽和玩味。这样一来,既调侃和消解了表哥的游戏和玩弄意味,又不着痕迹地揭批了表哥对待感情的游戏和不负责任态度。反讽结构背后透露了作者对玩弄女性、缺乏责任心和担当的陈腐男性观念的批判,使得女性沉沦背后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得以凸显。还有,梦珂离开姑母家踏进社会,作者先以情绪愤激的文字否定几种可供选择的职业道路,也否定了回家这条路。接着写道:“几天后吧,这女子出现在那拥挤的马路上,在许多穿尖头鞋围丝围巾的小男人,拖大裤脚的上海女人中跑着……”[5]34如果说前面那段情绪激烈的议论容易使作者与笔下人物间的距离缩短,那么后面“这女子”叙述的出现则又拉开了距离,隐现着故事背后的隐含叙述者,显示作者对于人物命运的关注和同情,及对黑暗与不合理现实的批判。因此,隐性叙述的灵活运用,一方面便于作者感同身受地发泄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愤懑情绪,揭示女性个体生存的艰难与困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作者超拔于故事层面,对情节故事及人物处境做更深层次的反思和审视,构成复调结构,丰富作品的内涵意蕴。相形之下,《第一炉香》的隐含叙述者有些变动不居,时而与显在叙述者合二为一,时而与人物混同一起,显得比较隐蔽。整个作品套在“点一炉香”的故事讲述中,这个讲故事的人就是显在叙述者,中间薇龙的香港故事就是她讲述的,直到结尾香烧完故事也结束了。而隐性叙述者则隐匿在故事中,她不期然地现身,超拔故事层面之上,对人物的生存、命运及人性予以冷漠、理性的审视和启悟。如薇龙与乔琪的情事败露后,她闹着要回上海,姑母劝说她:“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回不去了。”薇龙道:“我知道我变了。从前的我,我就不大喜欢,现在的我,我更不喜欢。我回去,愿意做一个新的人。”[4]155姑母听后沉默一会,在薇龙额角上吻一下就走了。接着隐含叙述者出场:“她这充满了天主教的戏剧化氛围的举动,似乎没有给予薇龙任何影响。薇龙依旧把两只手插在鬓发里,出着神,脸上带着一点笑,可是眼睛却是死的。”[4]155表面上,薇龙似乎没被姑母说动,还是要回去,但事实上,“眼睛却是死的”泄露了她潜意识中不愿回去的欲念。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已被奢华浮靡生活麻痹心灵的薇龙注定回不去了,她做不了自己的主,只能沦为姑母和乔琪的诱饵和工具。在这里,隐性叙述者超拔情节之外揭示了人物内在的欲念及人性的虚弱注定其做不了自己的主人,人成了自己欲念的奴隶。这是从人性的内在层面揭示女性堕落的深层内因,从而使作品超越了故事现实层面而深掘到人性、生命和存在境域,丰富和深化了作品的内涵意蕴。还有隐含叙述者与人物混同一起的情形,如生了一场病的薇龙,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不愿意回去,不回去就只有嫁给乔琪。“乔琪一天不爱她,她一天在他的势力下。她明明知道乔琪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浪子,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他引起的她那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她躺在床上,看着窗子外面的天。中午的太阳煌煌地照着,天却是金属品的冷冷的白色,像刀子一般割痛了眼睛。秋深了,一只鸟向山巅飞去,黑鸟在白天上,飞到顶高,像在刀口上刮了一刮似的,惨叫了一声,翻到山那边去了。”[4]157前面两句是人物视角叙述,后三句则跳出人物视角,转换成隐性叙述者叙述,以通感手法描写太阳、黑鸟和山巅,处处暗示的却是人物的生存处境、命运及人性的虚弱和“雾数”。正如论者所言,这种叙述视角的转换运用,不可避免地使“作者对笔下的人物在怜悯、同情中裹着冷漠的外壳,在冷漠的外壳之外却又无处不让你感到隐隐的温暖”,这是一种“精神上俯视的超然态度”[12]。
(三)消沉、萎靡及颓废的情感基调
丁玲的包括《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内的早期小说历来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女性情感和生活的写照,流露出鲜明的感伤、颓丧、消沉,乃至厌世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夏志清就认为丁玲早期作品流露一种“颓丧、虚无主义的情绪”[11]204。而张爱玲的早期小说也被傅雷批评:“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都为男女问题这恶梦所苦。恶梦中老是霪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灰暗,肮脏,窒息的腐烂的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假如作者的视线改换一下角度的话,也许会摆脱那种淡漠的贫血的感伤情调。”[10]431这种感伤、颓丧、消沉及萎靡的情绪/情调自然也流贯在《梦珂》和《第一炉香》中。这里,不说梦珂和薇龙最终沉沦堕落的命运,单是作品对人物内心情感、心绪及人与人之间情感纠缠的刻画等,无不流露出感伤和消沉的情绪色彩。《梦珂》中梦珂与表嫂关于爱情与婚姻的谈话,晓淞与伍太太的风流情事,剧社男女演员的打情骂俏等,都呈现一种消沉、萎靡和颓废的情绪色彩;而《第一炉香》中的感伤、颓废及萎靡情调更其显然。主仆间的争风吃醋,乔琪与睨儿的偷腥,乔琪与薇龙的情事,以及姑母与卢兆麟、乔琪及司徒协等人的风流韵事,可谓将丁玲作品中那股萎靡、消沉和颓废情绪发挥到极致。丁玲曾说自己“因为寂寞,对社会不满,自己生活无出路”而从事创作,并且那时自己“是一个很会发牢骚的人,所以《在黑暗中》,不觉的染上了一层感伤”[13]。张爱玲也说自己不喜欢壮烈的力,而喜欢苍凉的美,因为“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乏人性”[14]。可以说,流贯在她们作品中的这种感伤、消沉和颓丧的情绪是其所处时代社会情绪和作家个人审美情趣等影响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的本质就是表现这些感伤、消沉和颓废等情绪的,因为它们更切近于人性本质。人性中有高昂乐观的情绪,也有感伤低徊的情绪,而后者似乎更接近人性常态,更切合人内心的情绪状态及其渴望。正是这种感伤、颓废和消沉情绪,增强了《梦珂》和《第一炉香》的审美感染力,使其内涵意蕴超越了对现实层面的揭批,深入对生命个体的人生命运、生存境遇及幽微人性等视域的探索与叩问;也即作品在社会历史内涵之外,在意蕴结构深层,寄寓一种深切的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慨叹与追问。
综上所述,丁玲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二代女作家,她的创作对后代女作家构成强劲而深远的影响,张爱玲创作所受的影响及其对丁玲创作精神的延续只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因此,《第一炉香》与《梦珂》在题材情节、主题意蕴及艺术表现等方面极具相似性。这既有两位女作家出于自觉的性别意识对女性人生命运和生存境遇深切关注与思考的因素,又与她们对文学创作艺术性的执著追求有关。丁玲包括《梦珂》在内的早期作品属于自我表现的产物,作家内心寂寞、苦闷,不满社会,又无人倾诉,只好发抒为文。这种观念较接近于郁达夫一切小说均是作者“自叙传”的创作观,追求自我情感表现的真实,而不是为了任何外在社会目的。张爱玲虽然对那种通篇“我我我”的身边文学比较反感,但她也承认“写小说的间或把自己的经验用进去,是常有的事”,而“作家的个性渗入书中主角的,也是几乎不可避免的”[15]。两篇作品可谓都渗透着她们对于艺术性的独创和开拓的追求,如深刻的心理描写、多视角叙述、新旧文字的揉和及新旧意境的交错等。然而,由于两人身世经历、个性气质、文学修养及创作意图等的不同,特别是人生观和文学观的相异性,两篇作品的相异性也很显然,如作家创作的情感态度,一个热情参与(梦珂帮模特抱不平),一个是冷观世事(薇龙冷观梁府丫鬟争风吃醋)。特别是《第一炉香》讲故事的传统形式和腔调的选择,模糊和冲淡了其性别和社会抗争,情感调子回环往复,陷入传统窠臼,结尾饶有韵味。而丁玲则是一往无前地西化,从结构、思想、形象到语言、形式等,彻底反传统而新文学化。梦珂成为在现实社会无处容身被迫沉沦的“娜拉”形象,具有揭示女性悲剧性困境及现实黑暗的作用。张爱玲则通过薇龙形象的塑造,倾向于揭示女性自身人性的虚弱和贪欲导致其选择堕落,这是人的自由意志的自我放弃,较少外力胁迫。两篇作品的这些不同性决定了两位作家日后创作的不同发展趋向:一个朝向社会,关注女性的社会人生发展,将女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相结合,拓展了创作的题材视域和意涵境界,创作了《母亲》《一九三〇春在上海》《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一个则退回身边,始终注目女性内囿的情感与婚姻生活,深掘人性内里,探寻旧式家庭和都市社会里女性被物化和商品化的必然命运,创作了《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不过,她们创作的内在精神依然在延续和发展,值得深入探究。这已是另一篇文章探讨的话题,留待后续。
[1]金宏达.《传奇》集评茶会记[C]∥回望张爱玲:昨夜月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79.
[2]金宏达.女作家聚会谈[C]∥回望张爱玲:昨夜月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3]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C].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184.
[4]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7[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
[5]丁玲.丁玲全集:3[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6]张爱玲.张爱玲散文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496.
[7]王艳芳.千山独行:张爱玲的情感与交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72.
[8]李欧梵.苍凉与世故[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51.
[9]吴晖湘.激越的与苍凉的:丁玲、张爱玲创作文本的歧异[J].齐鲁学刊,2000(3):63-65.
[10]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M]∥张爱玲.张爱玲文集:4.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1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2]万燕.女性的精神:有关或无关乎张爱玲[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69.
[13]丁玲.丁玲全集:7[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5-16.
[14]张爱玲.自己的文章[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6:136.
[15]张爱玲.红楼梦魇[M].台北:台湾皇冠出版社,1995:197.
(责任编辑:袁 茹)
2017-08-18
陈娇华,女,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7.65
A
2096-3262(2017)06-003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