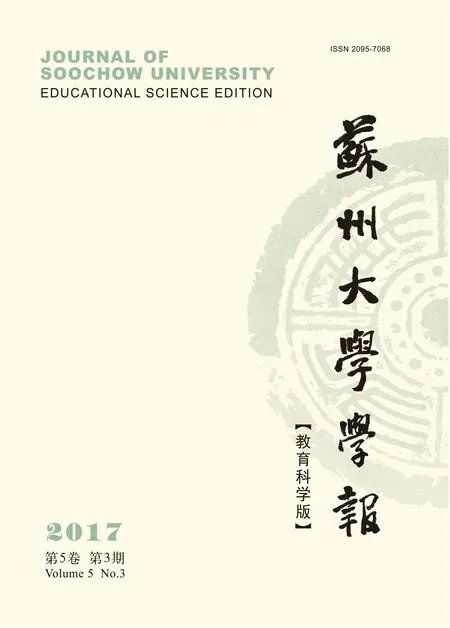学校民族志与教育政策研究:从陌路到相逢
张 东 辉
学校民族志与教育政策研究:从陌路到相逢
张 东 辉
(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872)
长期以来,教育政策研究依赖的是量化的研究方法,把科学性狭义地等同于教育实验和数据分析,把实证单一地等同于大样本的调查。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政策研究掀起了对理性—技术主义研究取向的种种反思和批判,转向了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视域。政策研究的后实证主义转向(价值的转向、文化的转向及语言的转向)与学校民族志的学术传统(关注情境、探究个体、寻求“地方性知识”和反思自我)不谋而合,从陌路走向相逢。具体来说,学校民族志有助于政策制定者界定“真正的”政策问题、自下而上地了解政策的发生机制,推动微观层面的学校变革。
学校民族志;教育政策研究;教育人类学;研究范式
作为实践取向和问题导向的学科,教育政策研究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教育研究和发展的重要方向,是联系教育科学和教育实践的必不可少的中介,也最为教育决策部门关注。一般来说,教育政策研究依赖的是大样本的调查和量化分析,而民族志(ethnography,亦译成人种志)作为一种研究取向起源于人类学,是对“人以及人的文化进行详细地、动态地、情境化描绘的一种方法,探究的是特定文化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1]25。长久以来,学校民族志与教育政策研究泾渭分明、各不相干,似乎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不能为政策制定者或政策研究者采纳。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政策研究掀起了对理性—技术主义研究取向的种种反思和批判,转向了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视域。在这样的转向中,教育政策研究与学校民族志开始从陌路走向相逢。本文从学校民族志与教育政策研究各自的学术传统、研究理路以及新近的发展出发,结合学校民族志的具体案例讨论民族志如何应用于教育政策研究。
一、学校民族志的研究理路
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人类学家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儿童早期经历与文化人格的养成,但是真正系统的学校民族志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2]在以美国学者斯宾德勒(Spindler)、奥格布(Ogbu)和沃尔考特(Wolcott)为代表的一批教育人类学家的推动下,学校民族志得以发展起来。从研究理路来看,学校民族志秉承了后实证主义的学术传统,与主张技术至上、寻求普遍规律和客观真理的经验实证主义大相径庭。不论是基于后现代主义架构的现象学—诠释学、建构主义和符号互动理论,还是当代批评与解构理论乃至于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的理论思潮,都影响了学校民族志的研究取向。具体而言,学校民族志的研究理路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关注情境
教育人类学者认为人类有效的学习是日常文化生活的结果,学校教育不仅仅包括知识的传授,而且意味着根植于特定社会和文化当中的学校组织对个体进行社会化和濡化,使其接受该文化的信条,预备其接受特定的社会角色,适应该社会的需要。[3]1学校民族志研究的最大特性是对于教育所处的社会—文化情境格外关注,这里“情境”(context)的含义非常宽泛,不仅仅指简单的物质生活环境,还包括语言、认知模式、共享价值、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等。民族志学者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与全貌性的描述,把学校、学生及教师放置于更加宽广、全面的社会人口结构和生态背景来考察,如社区与学校之间的互动模式,特定社会或群体的价值、信仰及文化观念,社会权力机制和意识形态等,从而获得对教育问题整体性的了解。建构主义和符号互动理论都强调:任何行为只有在一定的情境之中才能确切地表示出其意义,使用文化的整体架构作为诠释资料主要的组织或概念工具使学校民族志可以超越简单的变量分析,从整体上把握学校教育是如何发生的,揭示出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相互依存的关系。
(二)探究个体
袁同凯认为:学校民族志经历了从微观民族志到宏观民族志的发展过程,微观民族志专注于范围较小的单位或组织,考察课堂或学校当中行动者(如学生、教师和学校管理者等)的互动、交往模式、语言运用、课程设计、师生关系与规训等,宏观民族志则试图在文化、生态社会结构及权力机制等宏观系统下研究学校教育问题。[2]然而,不论是微观民族志还是宏观民族志,都坚持“以小见大”的研究取向,强调从个体人物、事件及日常行为当中发现意义,根据一个或几个关键报导人(key informant)提供的信息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所谓“个案”一般指的是“有界限的系统”(bounded system),但是学校民族志研究中的个案不同于实验心理学中的“个案”,目的不是追求代表性或从单个个体扩展开来推广研究结论,而是意在呈现个体的“特殊性”,希望透过个体提供的丰富脉络,深入了解行动者意向,探究包涵在其中的复杂关系及人际互动的参照架构,对个体及其所处社区作深入详实的描述、诠释及理解。[4]84在写作方式上,学校民族志推崇格尔茨(Geertz)提出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写作手法,即把微观个体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作详尽的描述,研究普通人如何创造与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其目的是探究人们习以为常、浑然不觉的实践惯性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秩序,使巨观的“文化脉络”在微观议题中得以凸显。
(三)寻求“地方性知识”
早期民族志发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对世界上比较“原始”、“落后”民族的异文化所持有的兴趣,然而这种兴趣带来的是西方学者从自身的文化镜片出发的叙述。[2]对此,后现代学校民族志试图打破长期以来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注重聆听不同人群,特别是社会边缘人或弱势群体的声音,不仅仅在认知层面“了解”对方,而且需要通过亲身参与到被研究者的生活世界来“体验”对方的视角,获取“内部人知识”(insider’s knowledge)和“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地方性知识“根植于基层社会的知识体系之中,是当地人对其周围文化现象的主位阐释,是经过长期历史积淀的地方性知识和日常生活的合理化常识”[2]。一些学校民族志学者,如奥格布,就是通过揭示这些底层人的“生存常识”或“民间成功理论”来发现学校场域中隐含的文化、性别、阶层和种族等因素,表达社会边缘群体长期以来被压制的声音。近年来,沿袭批判主义的分析视角,学校民族志日益关注学校中存在的多元文化与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考察存在于社会之中的权力关系和文化冲突是如何在日常教学活动和师生互动中渗透和呈现的,意在揭示隐藏在教与学、教育制度、教育规则背后的文化机制,这种研究取向能帮助研究者更深入地剖析学校教育是如何嵌入于社会主流政治系统,并对少数群体(minorities)和弱势群体造成压迫,从而叩问社会公平与正义。
(四)反思自我
不同于科学理性主义对于“主观—客观”“事实—价值”秉持的二分法,学校民族志研究遵循的是现象学的解释主义,认为研究不是对固定不变的“客观事实”的了解,而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双方共同建构、共同理解的过程,即研究者本人的角色和立场参与到对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的影响,研究者不再是价值中立。陈向明认为:阐释学中的“阐释”不是对某个“客观实在”的事物的直接观察或即时辨认,而是通过研究者的阐释把该物“作为某物”的结果,“理解”是在研究者的阐释意图与解释对象之间的一个循环互动。[1]36符号互动论也认为:任何人都是诠释者、界定者和符号使用者,在不断地与他人进行沟通磋商的过程中,得到“互为主体性”的了解。因此,民族志研究特别强调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承认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凭借言语和行为等符号参与到意义建构这一复杂的交互过程中,达成相互理解,取得共识。在这样的前提假设之下,学校民族志不追求对客观规律的描述或构建“普世标准”的理论,而是着重主观描述、意义建构以及反思自身。
二、教育政策研究的后实证主义转向
政策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领域,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美国政府职能的扩张而发展出的“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联邦政府的大型公共政策被视为一种强有力的干预手段,可以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随着公共教育事务在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重要性的突显,教育政策研究逐渐成为学者和决策者共同关注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在这种对公共政策的理解和期望之下,教育政策研究秉承的是社会科学中占支配地位的实证—经验主义(empirical-positivist)研究取向。一般来说,政策制定者想要迅速地获取明确、清楚的信息,简单易行的解决办法,而民族志研究提供的是广泛、深厚的描述。教育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既没时间或耐心去读学校民族志研究所提供的长篇的、具体的细节,也没兴趣去关心学校民族志研究者所提出的“与政策无关”的理论解释或现实批判。而且,教育政策研究者常常以样本量、因果关系、成本效益等量化标准去衡量学校民族志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批评民族志研究结论不具有代表性、可推广性,提出的仅仅是“泛泛而谈的关系”,缺乏现实操作性。民族志与教育政策研究在学术传统上似乎存在很大的冲突或本质上的“不相容”。
近年来,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影响,政策研究者开始反思其“实证—经验”取向和理性主义的“目标—手段”范式。由于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决策所需信息不充分、决策成本高昂,难以形成统一的决策评估,决策中的事实和价值之间难以区分等原因,理性模式在现实的政策制定中被认为过于理想化,并不符合政策的现实,实际决策很少以合乎逻辑的、综合、目标明确的方式作出。[5]127-130因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政策研究,包括教育政策研究,掀起了对理性—技术主义政策研究取向的种种反思和批判,转向了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视域。曾荣光把这种政策研究转向称为“阐释转向”(interpretive turn),具体来讲包括四个层面的转向:组织研究的转向、争辩与游说的转向、价值的转向和语言的转向。[6]本文从价值的转向、文化的转向和语言的转向三个方面分析政策研究的新进展,认为正是在这些转向中,民族志与政策研究开始从陌路走向相逢。
(一)价值的转向
80年代以来的政策研究者越来越意识到一些看似价值中立的政策争议背后实质上是由不同价值及理论倾向的“框架”所构成。政策不仅仅是政府单向的指令或代表公众对公共问题的一致诉求,而是反映了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和各种相对抗的社会需求之间的妥协和折衷。价值取向对于所有的公共政策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教育政策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教育的目的总是多元的、可辩论的、模糊的,在教育政策确立过程中,各种力量、团体和行动者以多种参与的方式进行争论,对问题界定、政策议程、备选方案等阶段施加影响,从而将各种对教育的价值追求带入政策过程。因而政策研究不仅应该根据问题本身来分析行动方案,即“我们应当做什么”,也应对政策过程中的价值涉入进行质疑和分析,即“什么是好的”和“我们必须相信什么”,以探究那些根植于政策脉络的价值、信念、观感与取态。[6]
(二)文化的转向
在政策研究的新进展中,传统的理性主义政策模式受到批判,新兴的政策理论流派(如新制度主义、公共理性选择等)批评传统政治学局限于正式的政府机构和制度,如国会、官僚体系、联邦制,各级政府的职能部门等,忽视了非正式的制度文化和微观层面组织的能动性。制度文化指的是行动者所共享的一系列概念、原则、规范和策略等,这些默认的规则会影响组织中的个体如何行动或决策,如哪些行动是允许的,哪些行动是被禁止的以及结果是如何被评估或报告的。[7]21在这样的制度文化约束之下,组织行为是由其所处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形塑而成的,是更广范围内的文化规范的反映。这里的文化意指有关政治制度的一系列社会建构的假设,以特定的符号、语言、迷思、仪式等表达出来,这些假设虽然存在于主观世界,却为政策行动者共享,并影响着他们的日常行为和结果。因而新近的政策研究转向从微观层面的个体能动性出发来研究政策执行过程,考察政策行动者或组织与制度环境、“不成文”的文化规范之间的互动,即“政策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哪些政策得以执行,哪些政策没有得以执行,为什么”。
(三)语言的转向
长期以来,政策执行者如家长、教师和校长被排斥在政策制定过程之外,也并非政策研究的中心。政策研究多以政策制定者、政府权威机构所颁布的政策声明、政策文件、政策指令以至法令为重点考察对象,认为政策是政治系统的输出,政策文本作为“一种经由书写形式加以固定化的话语”是官方的、唯一正确的表述方式,具有合法性、约束力和强制性。然而近年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使政策研究者不再把政策文本看作由简单的词汇、语法、修辞等语言要素组成,而是“对社会行动作出有效规训和监控的一系列政策陈述”[6]。英国教育政策研究专家斯蒂芬·鲍尔(Stephan Ball)进一步推动了“政策话语”理论框架的发展,他认为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它由社会结构所决定,承载着权力与权力关系,反映了言说者在社会权力关系网络中所处的地位。在话语理论下,政策文本是蕴含着权力技术的社会制度,反映了政策制定者如何为建构有利于自身的政策立场而进行的语言游戏。[8]语言转向的政策研究尤其关注政策是如何被社会主流群体制定并对边缘群体进行压制和排斥的,呼吁边缘群体的声音在政策中给予表达,质问“谁制定的政策”,“政策有利于哪些群体,不利于哪些群体”一类的问题。
三、学校民族志的新视角:教育政策研究的重心转移
(一)从“伪”问题到“真”问题
一般来说,教育政策力图解决的问题是社会广泛关注的,政策研究者试图从影响学校的若干变量中寻找解决方案,然而问题症结往往并非如研究者预想的那样显而易见。大量政策失败的事实证明:预先设计好的问题常常是“伪”问题、外来的问题、不相关的问题。这种情况下,政策研究仅仅依靠发放问卷做量化分析是不够的,而是需要借助民族志研究者的视角,即在没有明确的研究设计和研究问题指引下进入“田野”,经过长期深入的参与性观察之后获得“内部人的知识”,逐渐发现“有意义的问题”“相关的问题”。对政策问题的有效界定,不仅仅需要了解学校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更有必要体察与该政策问题有关的正式与非正式机构、制度、经济结构、文化、信仰和价值观等。只有这样,才能捕捉到真正的问题。
(二)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
传统对政策执行的研究聚焦于上令下达和具体人、财、物的资源配置,把政策客体看作是被动接受政策的一方。然而事实上,政策执行常常不是完全的理性执行,而是参与各方依据各自的利益和出发点有选择地执行,执行过程充满了象征性和仪式性。学校民族志研究把学校各方参与者看作是具有能动性的个体,尊重来自不同文化、阶层的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特别是那些长期以来被边缘化、失语的文化群体的声音。政策执行正是需要借助学校民族志了解不同行动者解读世界的方式,只有把政策对象的世界和视角呈现出来,才能真正地了解政策的全过程,达到政策中不同行动者之间的有效沟通。
(三)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
传统的政策研究致力于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往往在研究结论处列举一系列的政策建议。然而,不考虑社会文化背景而一厢情愿提出的政策建议必然是空洞的、无根据的、立不住脚的。学校民族志以“日常生活的深描”为己任,不是通过发表自上而下的政策建议来推动学校变革,而是透过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即鼓励实践者参与到积极的研究工作中来,将研究结果应用到对制度和行为的改变上,自下而上地发生变革。教师是学校发生变革的中坚力量,行动研究鼓励教师对自己的实践进行批判性反思,使教师在研究中获得“赋权”,追求自由、自主和解放,最终采取相应的行动来改变现状。[9]如果说教育政策研究的目的是促进学校、教师和学生在政策实施的终端发生实质的变革,学校民族志之行动研究正是理想的研究取径。
四、学校民族志在教育政策研究中的应用
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人类学家活跃在印第安人的教育问题研究领域,为印第安人学校撰写历史和教材,帮助双语学校使用印第安人的语言教学。60年代,民权运动唤醒了社会边缘群体对自身文化权利的意识,引起了美国主流社会对少数族裔(如黑人和新移民)社区及文化的重视,美国公立学校的低效和“白人文化中心主义”倾向招致民众的广泛批评,教育者、政策制定者开始针对黑人、西班牙裔学生、本土印第安人以及新移民学生的学业成就、学校适应、文化融入等问题寻求新的解决方案。面对学校里大量处境不利、家庭文化背景与主流社会差异很大的少数群体儿童,基于简单因果关系的政策方案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大量的经费投入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政策后果,美国的教育政策制定者不得不进行范式转移,从以往单纯的行为主义量化研究转向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寻求新的解释。
近年来,随着政策研究的后实证主义转向,各国学者积极探索开展学校民族志研究,为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发展贡献了独特的视角和诊断方案。如布拉德利·列文森(Bradley Levinson)编著的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 Policy Across Americas[10]展现了美洲各主要国家的民族志学者如何参与该国教育政策研究并推动政策变革,论述了民族志运用于政策研究时存在的问题、前景及趋势。随后,沃尔福德(Geoffrey Walford)编著了Investigating Educational Policy Through Ethnography[11]一书,里面收集了将民族志方法运用于具体教育政策研究的案例,包括对教育“成功”的政策话语分析,多语政策在日常教育实践中的反映,信息技术教育的政策意旨在学校和家庭中的影响等。具体来看,学校民族志在教育政策研究中的应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传统政策研究构成有益的补充
以少数民族教育为例,传统的政策研究倾向于从经济落后或家庭文化资本不足去解释少数民族学生为什么学业失败,并试图通过设立寄宿学校、采取同化教育等办法来解决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然而这种“简单粗暴”的政策方案被认为是“惩罚受害者”的做法,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常常引起少数民族学生和家长的反感。究其原因,正是由于政策研究者对少数民族文化缺乏了解所致。
美国学者菲利普斯(S. Philips)在其著名的民族志研究The Invisible Culture:Communication in Classroom and Community on the Warm Springs Indian Reservation中挑战既有的思维框架,基于对印第安学生与白人教师在课堂上的细致观察,发现印第安学生的语言交流模式是参与式的、不排斥他人的,学校中的白人老师倡导的却是竞争、优秀和个人中心主义。[12]由于学校没有认识到印第安学生特有的认知方式、交流方式、激励方式和读写方式并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法,导致大量的印第安学生无法在白人文化主导的学校里获得成功。又如Jinting Wu通过对贵州两个苗族、侗族农村学校的民族志研究对中国的“素质教育”政策内涵提出质疑。素质教育这一概念反映的是教育政策制定者对进步、现代化和以人为本等价值观的追求,落实到学校实践中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创新性思维等,但这与苗族和侗族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强调集体歌舞(如侗族大歌)、群体认同感等特征是不和谐的,因而素质教育政策的实施进一步边缘化了农村少数民族学生和教师在教育改革中的文化身份。[13]
大量的民族志研究从文化层面探讨少数民族教育问题,以令人信服的一手资料和独到的文化视角,将熟悉的事物、现象变得陌生,以叩问的方式审视和批评主流社会的文化中心主义,构建新的价值体系,剥离出教育政策的本质问题。民族志学者提出的“文化解决方案”已经为很多西方教育政策制定者采纳。
(二)帮助政策制定者自下而上地了解政策发生的微观机制
以往,很多政策研究者只关注政策是如何制定出来的,忽视了政策执行的环节。随着近年来政策研究的新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策执行本身也是一个文化现象,受制于不断变化的标准、价值观以及具体的情境。民族志研究在分析政策执行方面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学校作为一个比其他社会组织功能更齐全的组织,其内部的微观政治过程提供了政策重新融入情境的环境,这种重新融入与其说是“执行政策”,不如说是“再造政策”。[14]从多元的视角看待政策,尤其是从最接近教室的一方(即教师和学生)看待政策正是民族志学者力图呈现的。
李书磊撰写的《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是中国大陆第一本教育民族志,本书以河北省丰宁县胡麻营乡的一所乡村希望小学为调查对象,通过对学校以及教师们日常生活的描写,可以看到乡村学校与乡村生活的隔绝、课堂中文化传承与村落生活的断裂、乡村教师的生活困境以及与村落之间的隔膜等。作者没有采取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策研究范式去合理化这所乡村小学,而是从普通村民、社会底层小人物的视角出发去看待它,发现乡村学校处处散发着国家行政的色彩,是村落中的“国家”,与村民生活实际需要格格不入,因而乡村学校受到村民的抵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15]通过对具体学校情境下的各个群体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民族志研究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了解政策如何在现实的学校场域中发挥作用,监督政策实施效果(包括政策预期的结果以及未预期到的结果),推动学校变革。
五、总结
本文探讨的是学校民族志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范式能否为教育政策服务以及如何为教育政策服务。一方面,以质疑人们习以为常的知识体系和概念模式为起点,学校民族志研究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重新界定政策问题,拓展看问题的方式,使研究视野不仅仅局限在学校场所里看得见的、可量化的变量,而且揭示出学校、家庭、社区、文化等各因素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另一方面,通过与社会变革和社会行动结合起来,学校民族志研究可以帮助行政部门和政府机构了解政策在具体学校场域里的执行情况,表达社会底层的“受害者”和“失利者”的声音,为教师赋权,促进学校实践者反思,从而推动学校实现真正变革。与此同时,教育政策研究也不应该仅仅处理所谓的“实际问题”,而是完全可以并且需要拓展视野,成为“启迪”的研究。尽管政策领域里权宜之计和实用性是重要的考量,但是在对问题没有充分、深入的研究之前就仓促下结论和草率行动,不了解“地方性知识”,不具备“局内人的文化”,只能使长期的效益让位给短期的效果,导致政策朝令夕改。
毋庸讳言,学校民族志方法不能适用于所有的教育政策研究。如果研究者试图探讨可量化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或期望通过大样本的数据来验证理论假设,那么他们需要处理的信息必然是“硬的”,量化的方法也就更适用。然而,即使量化研究者也需要对所研究情境(如文化和社会情境)有基本的把握和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对数据结果进行合适的解释。无视社会和文化情境的数据是平面的,无法比较的,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如埃沃哈特(Everhart)所言,不做民族志研究的学者也需要具有民族志的视角(ethnographic lens without being ethnographers)[16]。教育政策更是需要情境化的参照,脱离具体情境空谈教育政策是毫无意义的。笔者认为,随着政策研究的后实证主义取向日益受到重视,学校民族志的方法在教育政策研究中必将占据一席之地。
[1]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2]袁同凯,温馨.现代西方学校教育民族志研究及其新近发展趋势[J].民族研究,2014,(5).
[3]Kelly D. Introduction:a discursion on ethnography[M]// Liu Judith,Ross H A,Kelly D. The ethnographic eye:interpretive studies of education in China[M]. New York:Falmer Press,2000.
[4]潘慧玲.教育研究的取径:概念与应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5]谢明. 政策分析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曾荣光.理解教育政策的意义[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1,(1).
[7]Heck R H. Studying educational and social policy:theoretical concepts and research methods[M]. Mahwah,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2004.
[8]Ball S J. What is policy? 21 years later:reflections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policy research[J]. Discourse: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2015,(3).
[9]Gardinier M P. Agents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the pivotal role of teachers in Albanian educational reform and democratization[J].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2012,(4).
[10]Levinson B,Cade S L,Padawer A,et al. 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 policy across the Americas[M]. Westport,Conn:Praeger,2002.
[11]Walford G. Investigating educational policy through ethnography[M]. London:Elsevier Science,2003.
[12]Philips S U. The invisible culture:communication in classroom and community on the Warm Springs Indian Reservation[M]. New York:Longman,1983.
[13]Wu Jinting. Governing Suzhi and curriculum reform in rural ethnic China:viewpoints from the Miao and Dong communities in Qiandongnan[J]. Curriculum Inquiry,2012,(5).
[14]林小英.理解教育政策:现象、问题和价值[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4).
[15]李书磊.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16]Everhart R B. 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al policy:love and marriage or strange bedfellows[J].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1976,(3).
[责任编辑:罗雯瑶]
School 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al Policy: From Strangers to Encounters
ZHANG Dong-hui
( School of Edu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
For a long time, studies on education policies rely on quantitative researches, in which scientific researches are narrowly considered equal to experiments and data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earches are simply regarded as investigation on large samples. However, since the 1980s, self-examination and criticism about techno-rational orientation have risen in the research of public policies, and people turned to the post-positivist orientation. The choice of the latter ( which means changes in values, cultures, and languages ) coincides with the academic tradition in school ethnography ( which focuses on surroundings, exploring individuals, pursuing more knowledge about the region, and self-examination ). More precisely, the ethnography assists policy makers in identifying“true”problem in policies, and getting to know the occurring mechanism from bottom to top to promote reforms in micro level.
school ethnography; educational policy studies;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paradigm
G40-032
A
2095-7068(2017)03-0054-07
2017-01-20
10.19563/j.cnki.sdjk.2017.03.008
张东辉(1976— ),女,吉林榆树人,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教育、教育人类学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校内科研基金“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大学的讨论与中国高等教育走出去的路径分析”(项目编号:16XNB01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