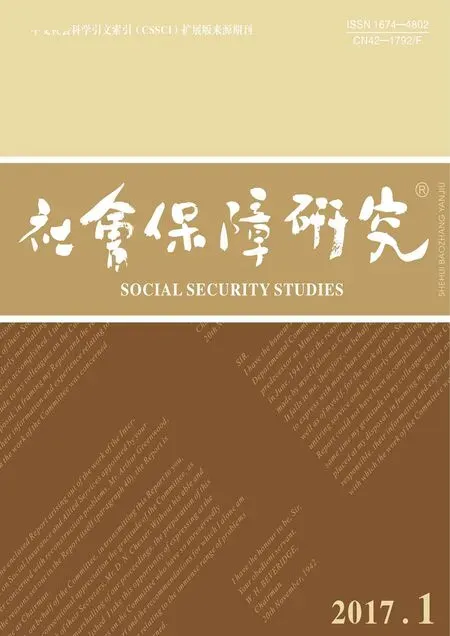长期护理保险的家庭溢出效应研究综述及对我国的启示
吕璧如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广东深圳,518060)
长期护理保险的家庭溢出效应研究综述及对我国的启示
吕璧如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广东深圳,518060)
家庭成员与老年人的护理选择有着复杂及重要的交互作用。本文回顾和梳理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长期护理保险家庭溢出效应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作为我国构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参考,最后提出促进国内长期护理保险的建议。
长期护理保险;非正式护理;正式护理;家庭;溢出效应
一、引言
长期护理保险已在很多发达国家举办,除了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外,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的规模一直很小,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家庭成员作为非正式护理的供给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多重原因驱使我国人口结构正迅速发生变化,老龄化是其中特别显著的特征,我国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口数亦迅速增加,预测到2020年将突破4600万,*数据来源于《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14)》。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同时导致了劳动力供给宏观上的减少,进而不可避免地造成家庭成员的护理成本上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护理供给会大幅下降,寻找相应的替代手段,满足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的护理需求,是刻不容缓必须正视的问题。长期护理保险作为老年护理需求风险的转移工具,推动其社会化和市场化,通过家庭之外的手段来解决长期护理需求的巨大缺口,已被中央高层重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要“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长期护理保险作为一项制度,其推行会引起社会经济主体行为和经济变量行为的改变,对社会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评估这些行为,针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采用不同的长期护理保险模式,是需要先行解决的问题。本文集中跟踪了长期护理保险与家庭成员行为交互作用的研究结果,并据此提出一些对建立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议。
二、长期护理保险家庭溢出效应的理论模型
与发达国家人口结构变化几乎同步,对长期护理保险的研究也是最近20多年才兴起的。针对现实中购买长期护理保险的人很少,一些人做了一些感性上的分析,认为子女的家庭非正式护理(informal care)替代了护理机构的正式护理(formal care),*正式护理包括基于社区的居家护理、基于社区的家庭外护理、机构护理等形式,由签订合同的人提供护理服务,并根据雇佣合同得到固定收入。其中基于社区的护理一般由护理人员提供上门服务和日托服务,也称为居家护理; 机构护理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的护理服务,表现为养老院、护理院等形式。非正式护理则是由配偶、成年子女或其他亲戚、朋友、邻居等与被护理者已经存在某种社会关系的人提供的非支付性、无组织的家庭护理。认为子女的非正式护理抑制了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而后,随着家庭结构与观念的变化,父母可能不想增加子女的负担或想维持各自的独立性,子女的非正式护理成为正式护理的补充,两者成正向互补关系。
Pauly(1990)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模型来解释这一现象,其模型是建立在如下的假设基础上的,决策者是有支付能力的、理性的风险厌恶个人,决策环境是信息充分的竞争性市场,决策目标是终身期望效用最大化。构造了了如下的期望效用函数(EU):
(1)

(2)

依据以上简单的效用函数,从最简单的无配偶,从而也就无继承人的个人决策开始,并一步一步地放松这一假设,分析了离异家庭、有配偶和有遗产继承以及国家公共政策影响的情况下,即使在精算公平的保费下,由于家庭护理质量及慢性病发生概率等因素,购买长期护理保险都会使得效用水平降低,在有附加保费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有经济能力的人不愿购买这类保险。[1]
在Pauly(1990)模型中,长期护理保险和遗产数量完全由父母决定,子女只是被动地接受,在模型中是外生变量。Zweifel和Strüwe(1996)认为父母的遗产存量和长期护理保险不仅取决于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决策,而且取决于同子女博弈的结果,这一结论是通过委托-代理模型得出的。
作为代理人的子女在父母离世时获得的财富是一随机变量





s表示储蓄的累积存量。相应地,父母的效用函数为:

在子女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满足的情况下,父母进行自身效用最大化决策,分别讨论了只有遗产和只有长期护理保险的最优激励结果,以及遗产和长期护理保险同时存在的优化问题,其结论是,父母通过对风险分担和子女在长期护理方面存在的道德风险的权衡,优化策略是购买较少的长期护理保险,因此在现有的遗产状况下,长期护理保险规模是较小的,特别是在主要工业化国家是如此。[2]
Courbage和Zweifel(2011)认为道德风险不仅为子女所独有,父母也存在道德风险,委托-代理模型不足以刻画这种情况,引入了静态非合作博弈模型。他们假定父母与子女同时做出决策、并都具有期望效用函数、父母将其财富在死亡后全部赠与子女(利他动机),与前面两个模型不同的是,长期护理保险的保费和赔偿金进入了父母和子女的效用函数之中,就他们各自的效用函数分别对子女护理的努力以及保险保障水平,求一阶、二阶和混合(偏)导数,得到父母与子女的反应曲线,设定两条能够相交的反应曲线,交点即为纳什均衡(如图1)。
外生变量的变化影响反应曲线的位置,从而导致均衡点的移动。Courbage和Zweifel的分析有如下结论:(1)父母初始财富多,均衡为(子女护理努力提高,长期护理保险保障低),非正式护理与正式护理为替代关系;(2)长期护理保险保障补贴,得到与(1)相同的结果;(3)父母健康状况差,对子女护理努力影响效果难以确定,但是长期护理保险保障水平会上升;(4)子女的机会成本增加,子女护理努力小的概率增加,长期护理保险保障水平不变;(5)子女继承预期增加,子女护理努力小的概率降低,长期护理保险保障水平降低(非正式护理与正式护理为替代关系);(6)提高了初始较低的遗产份额,子女护理努力小的概率降低,长期护理保险保障水平不变。[3]

图1 父母与子女的反应曲线
Costa-Font和Courbage(2015)把非正式护理作为模型的外生变量,通过比较静态分析,考察了非正式护理与政府支持对长期护理保险需求的挤出效应,并用欧洲的一些数据验证其模型导出的结论正确性。[4]很重要的是,他们把以前对利他主义因素的处理方法引入了模型之中(vandenBergetal.,2005),[5]从而使得模型更接近现实,结论也更有说服力。其基本模型为父母的期望效用:


最优保险水平由期望效用函数的一阶条件得到

一阶条件分别对子女护理努力程度和政府支持强度求导,得到如下结论:非正式护理与政府支持对长期护理保险存在挤出效应,即它们的增加将导致长期护理保险需求的下降。在考虑家庭内的道德风险时,通过适当改变父母的期望效用函数,重复上面的过程,得出长期护理保险随着政府支持和非正式护理的增加而增加。
三、实证研究
(一)事前家庭溢出效应
虽然家庭成员为失能老人提供显著程度的非正式护理(Cantor,1989),实证研究对于家庭相关因素(例如是否有配偶或子女、是否有遗产等)是否影响老年人购买长期护理保险的检验结果却不一。Mellor(2001)使用美国Study of Asset and Health Dynamics(AHEAD)和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PSID)两个数据库,发现家庭非正式护理者的存在与长期护理保险的购买没有关系;[6]Sloan和Norton(1997)使用1993年AHEAD以及1992年和1994年两轮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HRS)的数据,发现遗产并非购买长期护理保险的考虑因素。[7]
部分美国与欧盟的实证研究支持家庭成员提供的非正式护理与长期护理保险为反向替代关系。Brown(2006) 使用1993年AHEAD数据,发现父母的遗产分配与成年子女的非正式护理呈正向关系,间接为Zweifel和Struwe(1996)的模型假设提供实证支持;[8]Brown等(2012)使用RAND American Life Panel近3000个家计单位的网上问卷调查数据,发现当父母较能得到家庭成员的免费非正式护理时,其倾向不购买长期护理保险;[9]Van Houtven等(2015)使用1996年到2010年八轮HRS的数据,发现有同住子女、在岗配偶的老年人较不会购买长期护理保险,因为同住子女或在岗配偶为潜在的非正式护理供给者;[10]Lockwood(2016)使用1998年到2008年六轮HRS的数据,发现遗产馈赠动机越强烈的单身65岁以上老人,越倾向增加储蓄以及越不倾向购买长期护理保险;[11]Costa-Font(2010)、Costa-Font和Courbage(2015)使用Special Eurobarometer中的283个欧盟区数据,也发现家庭护理与长期护理保险的购买呈反向替代关系。[12][4]
两篇国外的实证研究对父母因对子女的利他动机而购买长期护理保险的理论假设提供支持。Courbage和Roudaut(2008)使用Survey of Health,Ageing,and Retirement in Europe(SHARE)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法国父母为了不想增加成年子女的负担或者为了保全遗产(利他动机),倾向购买长期护理保险以满足相应的护理需求;[13]Sperber等(2014)采用8组美国波士顿、夏洛特与芝加哥焦点小组访谈(focus group)资料,发现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与改变,父母对成年子女的非正式护理偏好减弱,而是购买长期护理保险,让父母与子女各自都能维持独立自主。[14]
在国内,关于长期护理保险的实证研究多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Xu和Zweifel(2014)使用2012年10月在上海地区所做的500份有效回复问卷进行分析,发现若子女可以提供较多的非正式护理,父母较不会购买长期护理保险;[15]丁志宏、魏海伟(2016)利用《2010 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个人问卷(城市部分)》10069份数据,发现有偶老人或子女数量多的老人较愿意购买长期护理保险,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16]
(二)事后家庭溢出效应
一般长期护理保险以两种形式供给:政府强制性投保与私人自主性承保。关于事后家庭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长期护理保险对非正式护理的挤出效应与家庭成员的行为反应上。 Courbage和Roudaut(2010)使用SHARE中412个单身60岁以上法国老人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长期护理保险若对居家日常活动的协助服务给予保险理赔,将使老人接受到更少的非正式护理;[17]Tsutsui等(2014)针对日本2000年全面实施长期护理社会保险前后的非正式护理者进行问卷调查,得到611份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女儿及媳妇对老人的肢体活动护理显著降低,而肢体活动护理正是日本长期护理社会保险的主要保障项目,同时,家庭非正式护理者的孝道感降低,尤以媳妇降低最多;[18]Coe等(2015)使用1996年到2010年八轮HRS的数据,发现长期护理保险的保障使非正式护理的供给降低,同时,父母若有购买长期护理保险,成年子女不会与父母同住或住在父母附近,而且子女较有可能从事全职工作。[19]
在国内,关于长期护理保险事后家庭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基本上是欠缺的,只有Xu和Zweifel(2014)的上海地区问卷调查分析,且其问卷关于长期护理保险为假设性问题,填答问卷者不见得已有购买长期护理保险,Xu和Zweifel发现若父母有较高的护理保障,子女倾向于提供较少的非正式护理。[15]
四、评论及对我国实践的启示
(一)对已有研究的评价
理论研究是针对长期护理保险购买量少这一事实展开和发展起来的。考虑了遗产、家庭初始财富数量、非正式护理的供给、政府支持力度、父母和子女的道德风险等因素对长期护理保险需求的影响,得到了若干结论,应该说这些结论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是基本成立的,但是除了少数情况之外,很多时候实证检验却难以与之吻合。其原因在于:第一,理论模型进行了高度抽象和简化,例如在所有模型中对长期护理保险市场都做了竞争性假设,这一假设条件太强,在现实中往往不能满足;第二,效用函数中没有考虑不同财富水平对风险厌恶程度的影响,例如Pratt(1964)认为,个人愿意在财富增加时承担更多的风险(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而Arrow(1965)的结论是,当个人变得更加富有时,他们会购买较多的安全资产,降低承担风险的比例(递增的相对风险厌恶)。这是长期护理保险需求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目前的理论模型中没有考虑;第三,正式护理行业的规范与否,护理服务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护理服务的标准化等,直观上都对长期护理保险需求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另外,同一般商品不同,护理商品带有很大的情感色彩,子女的护理可能会给父母带来更大的满足;第四,不同种族、不同国度文化价值的差异,导致对正式护理和非正式护理接受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别,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即使家庭护理供给很少,父母也不愿意到养老院等机构获得护理服务;第五,分割的劳动市场和劳动技能不同,使得子女提供非正式护理的实际成本与机会成本可能存在较大差距,激励父母和子女不同的经济行为,间接影响到长期护理保险需求。
(二)对我国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启示
商业性的长期护理保险在我国已经走过了十几个年头,2017年北京石景山等地开始强制性的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理论研究伴随着实践的推进而兴起,国内的研究先后有人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赵曼、韩丽,2015;鲁於、杨翠迎,2016;仙蜜花、胡瑞宁,2017),[20][21][22]对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必要性没有异议,主要基于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对采取商业保险、强制性(社会)保险还是二者的混合出现分歧,与此相一致,在筹资上也有三种意见:个人负担、个人集体(企业)和国家三方负担、集体与国家负担。实践进展的缓慢部分反映了理论研究没有取得有效突破,因此,是时候重新检讨我国构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三个基本问题:
首先,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到底有多紧迫,这是所有理论和实践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到目前为止,尚没有看到权威的研究问世。我们不能用需要护理的总人数规模作为支撑证据,因为长期护理保险需要个人有支付能力,没有支付能力的长期护理需求,只能通过完善现有的社会救助制度来提供。显然,信息不对称也不是得出必须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充分条件。
其次,如果证明必须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那么就要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每种制度的具体模式可能产生的微观效应,选取最有效率的制度,扭曲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稀缺资源配置是不可取的模式。本文跟踪的就是这方面的研究,国内较少今后有待加强。从政策上来看,现在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强制性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破坏了市场机制,很难保证有效率,是不可取的。
第三,从家庭来看,长期护理保险只是提供了一种护理成本转移方式,这种转移方式的发展需要有完善的正式护理服务市场,因此,在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之前,先要建设好规范的正式护理服务市场制度。
[1]Pauly,M.V.The Rational Nonpurchase of Long-Term Care Insuranc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0,98(1):153-168.
[2]Zweifel P.,and W.Strüwe.1996.Long-Term Care Insurance and Bequests as Instruments for Shaping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JournalofRiskandUncertainty,1996,12:65-76.
[3]Courbage,C.,and P.Zweifel.Two-Sided Intergenerational Moral Hazard,Long-Term Care Insurance,and Nursing Home Use.JournalofRiskandUncertainty,2011,43(1):65-80.
[4]Costa-Font,J.,and C.Courbage.Crowding out of Long-Term Care Insurance:Evidence from European Expectations Data.HealthEconomics,2015,24(Suppl.1):74-88.
[5]Van den Berg,B.,H.Bleichrodt,and L.Eeckhoudt.The Economic Value of Informal Care:A Study of Informal Caregivers' and Patients' Willingness to Pay and Willingness to Accept for Informal Care.Health Economics,2005,14(4):363-376.
[6]Mellor,J.M.Long-Term Care and Nursing Home Coverage:Are Adult Children Substitutes for Insurance Policies?JournalofHealthEconomics,2001,20:527-547.
[7]Sloan,F.A.,and E.C.Norton.Adverse Selection,Bequests,Crowding out,and Private Demand for Insurance:Evidence from the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Market.JournalofRiskandUncertainty,1997,15(3):201-219.
[8]Brown,M.Informal Care and the Division of End-of-Life Transfers.TheJournalofHumanResources,2006,41(1):191-219.
[9]Brown,J.R.,G.S.Goda,and K.McGarry.Long-Term Care Insurance Demand Limited by Beliefs about Needs,Concerns about Insurers,and Care Available from Family.HealthAffairs,2012,31(6):1294-1302.
[10]Van Houtven,C.H.,N.B.Coe,and R.T.Konetzka.Family Structure and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Purchase.HealthEconomics,2015,24(Suppl.1):58-73.
[11]Lockwood,L.M.Incidental Bequests:Bequest Motives and the Choice to Self-Insure Late-Life Risks.NBER working paper #20745,2016.
[12]Costa-Font,J.Family Ties and the Crowding out of Long-Term Care Insurance.OxfordReviewofEconomicPolicy,2010,26(4):671-712.
[13]Courbage C.,and N.Roudaut.Empirical Evidence of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Purchase in France.TheGenevaPapersonRiskandInsurance-IssuesandPractice,2008,33(4):645-656.
[14]Sperber,N.R.,C.I.Voils,N.B.Coe,R.T.Konetzka,J.Boles,and C.H.Van Houtven.How Can Adult Children Influence Parents'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Purchase Decisions?TheGerontologist,2014,00(00):1-9.
[15]Xu,X.,and P.Zweifel.Bilateral Intergenerational Moral Hazard: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a.TheGenevaPapersonRiskandInsurance-IssuesandPractice,2014,39:651-667.
[16]丁志宏、魏海伟:《中国城市老人购买长期护理保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载《人口研究》,2016(6)。
[17]Courbage C.,and N.Roudaut.Informal Care,Insurance,and Intra-Family Moral Hazard.Working Paper Series of the Geneva Association #369,2010.
[18]Tsutsui,T.,N.Muramatus,and S.Higashino.Changes in Perceived Filial Obligation Norms among Coresident Family Caregivers in Japan.TheGerontologist,2014,54(5):797-807.
[19]Coe,N.B.,G.S.Goda,and C.H.Van Houtven.Family Spillovers of Long-Term Care Insurance.NBER working paper #21483,2015.
[20]赵曼、韩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选择:一个研究综述》,载《中国人口科学》,2015(1)。
[21]鲁於、杨翠迎:《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构建研究回顾与评述》,载《社会保障研究》, 2016(4)。
[22]仙蜜花、胡瑞宁:《高龄农民工养老津贴制度探析》,载《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7(1)。
(责任编辑:D)
Implications from Research on Family Spillovers of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LV Biru
There are complex and important interactions between family members and long-term care decisions of elder people.This paper reviews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the family spillovers of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for the government’s reference to building up a long-term care system.Finally,some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that prompt more domestic studies on long-term care.
long-term care insurance,informal care,formal care,family,spill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