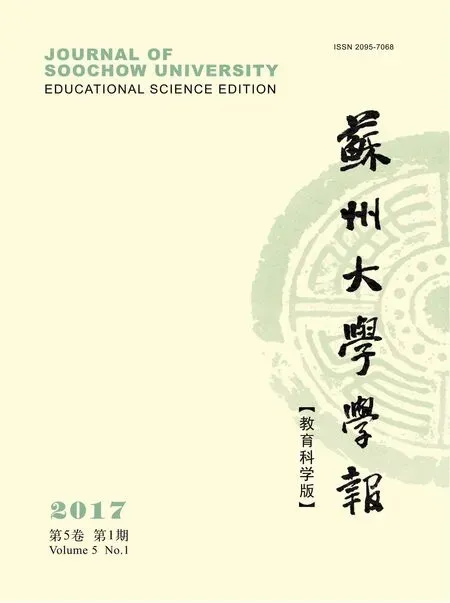埃里克森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理论新探
陈 永 胜
(浙江师范大学 心理研究所,浙江 金华 321004)
埃里克森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理论新探
陈 永 胜
(浙江师范大学 心理研究所,浙江 金华 321004)
埃里克森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理论立足生命全程,完整勾勒了个体宗教心理的发展阶段,强调社会文化在个体宗教心理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运用典型个案揭示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的内在动力。其完善了个体宗教心理毕生发展的阶段划分理论,深化了学界对于个体宗教心理发展原理的认识。但其关于个体宗教心理发展阶段的假设缺少实证支撑,有关个体宗教心理发展规律的解释仍然具有偏颇。
埃里克森;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理论
在《现代西方宗教心理学理论流派》(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中,笔者着重从身份认同角度,剖析了埃里克森的宗教心理学思想。根据“中国特色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研究”的需要,本文将着眼于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理论的视角,对埃里克森的宗教心理学思想进行新的探讨,以期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理论奠定基础。
一、埃里克森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理论的形成背景
埃里克森(Eric Homburger Erikson)祖籍丹麦,1902年生于德国,1994年卒于美国。有人评价埃里克森是一个“走钢索的人”①在笔者看来,“走钢索”的评价虽有夸张成分,但对理解埃里克森的成长背景大有裨益。[1]200,这主要是因为在埃里克森的一生中,尤其是童年期和青少年期,他曾经历过严重的心理冲突或认同危机。
埃里克森童年期的认同危机,主要来自于姓名变更、同伴评价和信仰冲突。埃里克森出生时,母亲卡拉·亚伯拉罕森(Karla Abrahamsen)给他登记的姓名为埃里克·萨洛蒙森(Erik Salomonsen),后因母亲改嫁,埃里克·萨洛蒙森被更名为埃里克·杭伯格(Erik Homburger)。这次姓名变更的原因,年幼的埃里克森并不清楚,他一直把继父杭伯格医生看成是亲生父亲,不过在埃里克森的记忆里,好像自己并不属于这个家庭。在寺庙学校,同学们嘲笑他是北欧人;在语法学校,伙伴们讥讽他是犹太人。在犹太教中,埃里克森则是一个高大、金发、蓝眼睛的异教徒。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埃里克森童年生活中认同危机的重要节点。
埃里克森青少年期的认同危机,主要来自于人生道路的选择困境。继父杭伯格希望埃里克森继承自己的事业,为将来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做好学业上的准备。但是埃里克森青少年时期的兴趣却集中在美术领域。18岁从预科学校毕业,埃里克森并没有选择继续深造,而是从德国的卡尔斯鲁厄出发,游历欧洲中部达1年之久;回国后,埃里克森在卡尔斯鲁厄和慕尼黑的艺术学校进行了短期学习,接着又踏上了去法国和意大利的游历之路。通过这种放荡不羁的游历生活,埃里克森逐渐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适合以绘画为生。那么,什么样的职业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呢?埃里克森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几十年后,埃里克森将自己在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困扰概括为“同一性危机”。
埃里克森的生活在25岁后出现了转机。一位在奥地利相识的朋友邀请埃里克森到维也纳的一所小型私立学校任教,在这里他结识了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安娜注意到埃里克森对儿童的敏感性①这或许预示了埃里克森后来对儿童研究的兴趣。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Erik_Erikson.,便鼓励他去维也纳精神分析研究所学习精神分析,从此便成为“可以进入弗洛伊德家族圈内并直接受训的学生。于是埃里克森再次成为养子”②米切尔和布莱特称埃里克森“再次成为养子”,显然针对的是其早年的继子身份。[2]168。1931年,埃里克森与加拿大舞蹈艺术家琼·莫厄特·塞森(Joan Mowat Serson)结婚,其间他皈依了基督教。1933年,埃里克森获得了维也纳精神分析研究所颁发的结业证书,这是他一生仅有的学术文凭。后来,由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埃里克森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移居美国(到美国后又生一女)。
在美国,埃里克森成为波士顿地区第一位儿童精神分析人士,后在哈佛、耶鲁等大学任职,探讨儿童的自我意识发展问题。1939年,埃里克森加入美国国籍。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埃里克森曾花费大量时间参与儿童文化人类学的考察,考察的结果发表在1950年出版的《童年与社会》(Childhood and Society)一书中。20世纪50年代,埃里克森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堪萨斯等地任教,60年代返回哈佛大学专事人类发展问题研究,直到1970年在该校退休。
埃里克森涉及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的论著除了《童年与社会》外,还包括《青年路德:精神分析与历史的一项研究》(Young Man Luther: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1958)、《顿悟与责任:关于精神分析见解伦理含义的演讲》(Insight and Responsibility:Lectures on the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Psychoanalytic Insight,1964)、《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Identity:Youth and Crisis,1968)、《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Gandbi’s Truth:on the Origins of Militant Nonviolence,1969)、《玩具与推理:仪式化经验中的阶段性》(Toys and Reasons:Stages in the Ritualization of Experience,1977)等。
依笔者之见,埃里克森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理论的学术思想来源主要包括弗洛伊德的心理性欲发展阶段说、沃尔夫(C. F.Wolff,1733—1794)的“渐成论”和以米德(M.Mead,1901—1978)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观点。作为新精神分析学派的重要代表性人物,埃里克森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与经典精神分析存在潜移默化的渊源。根据性本能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具体表现,弗洛伊德把儿童少年的心理性欲发展划分为口唇期、肛门期、前生殖期、潜伏期和青春期5个阶段。弗洛伊德认为,口唇期流露出较早的快感和偏见;肛门期以排泄为快乐;前生殖器期出现男孩的恋母情结;潜伏期相对平静,性发展处于停滞或退化状态;青春期容易产生性冲动,并且有可能导致与成人的抵触情绪。弗洛伊德的上述主张,在埃里克森提出的个体宗教心理发展阶段假设的前5个阶段得到不同程度反映。沃尔夫是胚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最早提出了“渐成论”。依据这一理论,胎儿在子宫中成长时,各器官系统相继出现并占据优势,通过复杂的生理过程整合,最终成为一个机能健全的婴儿。在埃里克森看来,一个人自我意识的发展如同个体胚胎期一样,也是这样一种渐进的有机融合过程。通过生理、心理、社会一系列对立力量的相互平衡,自我意识按照一定的顺序向前发展,其发展趋向贯穿于人生全过程。一个人宗教心理的发展,同样遵循着这种“渐成论”的发展模式。米德作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大众媒体频繁亮相的文化人类学代表性人物,非常重视特定文化对个体人格形成的重要作用。她认为,不同人类群体之间(包括男女性别之间)不同的心理活动和行为举止,并不是由各自不同的生理结构决定的,而与他们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这种文化决定论的思想,“构成了埃里克森创造的背景,他由此对社会环境中的个人发展提出了丰富而结构化的精神分析阐述”③米切尔和布莱特的这一分析非常准确。埃里克森对社会文化的重视程度,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专门阐述。[2]169。
二、埃里克森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理论的主要特点
依笔者之见,埃里克森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理论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立足生命全程完整勾勒个体宗教心理的发展阶段
在埃里克森看来,如同一个普通人的心理社会性发展是围绕生理、心理、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一样,个体的宗教心理也是从低级向高级,分成8个阶段向前发展的。
在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婴儿期(0—2岁),婴儿面对的问题是“我可以信任这个世界吗”,其心理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为基本信任对信任缺乏。埃里克森指出:“由于受到不合时宜的刺激或由于长期发作的忿怒和疲乏,婴儿对自己和对他人的最初信任产生了动摇……‘善良’和‘邪恶’开始进入婴儿的世界。”①这段论述是埃里克森在阐述婴儿期发展模型的第Ⅰ阶段和第Ⅱ阶段时提到的。[3]68在埃里克森看来,婴儿“对牙齿咬东西的快感,对母亲抽回奶头的忿怒,以及由于自己的忿怒毫无作用而引起更大的忿怒导致婴儿体验了虐待狂和受虐待狂的严重混乱状态,从而给婴儿留下了这样一个总印象:即,很久以前,有人毁坏了他与母亲的合作。这种可怕的印象,犹如《圣经》中传说的那样,因为偷食禁果而惹怒了上帝,地球上第一批人永远丧失了可以毫不费力地随意取用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的权利”②从婴儿生理发育过程中的内在冲突,联系到与母亲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与宗教传说中人类早期的邪恶起源联系起来,这便是埃里克森探讨婴儿期个体宗教心理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路径。[3]69。在婴儿期的成功解决方案中,基本的美德是希望。埃里克森认为,希望是在强烈愿望获得中的持久信仰,婴儿“做什么才有意义,这是由父母信仰所培育起来的;儿童对希望的泛化意义,将及时使其转化成为一种成熟的信仰,一种既不需要证据也不需要世界是值得信任的理由的信心”[4]153。
在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儿童早期(2—4岁),儿童面对的问题是“我是怎样的”,其心理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为自主对羞愧。埃里克森指出:“这个阶段,父母和孩子间的相互调节关系又面临着严重的考验。如果采用太严格或太早的训练来形成外界控制,不许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思和选择来逐渐控制他的肠部和其它器官的话,则他对自己身体的内部和外部会感到无所适从(如害怕体内的粪便,好象它们是身上的恶魔),他不得不借助倒退和假前进来寻求满足和控制。”③此段引用中的“象”字,按照新版《现代汉语词典》的规范使用应为“像”字。[3]72埃里克森还指出,这一阶段“其它可能出现的‘横向偏移’模式……即利用粪便作为攻击人的炮弹。其表现形式可能为过分地排除粪便或积蓄粪便。这种尝试在成年人中也是有的,他们将粪便作为亵渎神灵的东西来使用”④埃里克森在这里把幼儿自主排便训练中遇到的困境,与恶魔、神灵联系起来,借以说明此阶段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的特点。[3]72。关于这一阶段至关重要的美德,埃里克森认为是意志品质,这种品质为日常生活(包括宗教领域)中的接受或选择奠定了基础。
在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游戏期(4—7岁),幼儿面对的问题是“我的运动和行为是怎样的”,其心理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为主动对内疚。埃里克森强调,此阶段的危险是超越受禁欲望和嫉妒竞争的一种深刻持久的内疚,或许在惊恐、不可控制的攻击行为中表现出来。一旦幼儿的幻想受到压抑,愤怒遭到否认,便有可能产生限制性抑制和不能容忍的道德正义。埃里克森指出,这一阶段至关重要的美德“目的性”的发展,源自于幼儿游戏的“媒介现实”背景。在假装的简化世界里,幼儿通过过去的失败去操作,并且自然形成了可实现目标的未来。埃里克森使用具体案例来证明他的观点。“一个女孩,在她的游戏桌上反映出对某些她不知道的事情的觉察……她构造了一堆废墟,场景的中心放着一个女孩。这意味着‘一个女孩被献祭给众神以后又不可思议地活了过来’。这些例子并不牵涉到如何解释孩子在无意识情况下的行动,它仅表明,这些场景是接近孩子生活的。”⑤使用具体案例(既包括生活中的实例,也包括临床中的个案)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埃里克森建构理论的重要方法。[3]89-90
在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即学龄期(7—12岁),学龄儿童面对的问题是“我可以使自己进入他人的世界吗”,其心理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为勤奋对自卑。埃里克森认为,这一阶段是“在社会意义上最具决定性的阶段”⑥埃里克森把学龄期看作“在社会意义上最具决定性的阶段”,显然受到了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影响。[5]111。因为此时的儿童超越即时家庭圈,学习使用成人世界的实践工具和器皿,因而发展了勤奋感。当儿童不能在努力中成功或目标本身模糊时,便会出现不胜任感或自卑感。在师生互动特别是参与社会的日常宗教仪式活动中,儿童关注细节与合作的能力得到发展。通过熟练教师、合作伙伴和理想榜样的熏陶,成长中的儿童“逐渐成为环绕文化技术的一名称职参与者”①埃里克森这里所说的“文化技术”既包括古老的文化传统,也包括现代的科学技术。[4]123-124。
在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的第五个阶段,即青少年期(12—18岁),青少年面对的问题是“我是谁”,“我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心理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为角色认同对角色混乱。在埃里克森看来,这一阶段的青少年面临着把儿童时期习得的自我品质及知识,与个人视野中朦胧显现的成人角色联系起来的问题。青少年需要心理社会能力的“延期偿付”,以便为今后的成人角色扮演提供机会。青少年的心理带有意识形态特点,因为致力于某些信仰或教义的青少年,发现了内部的一致性和对罪恶的某种界定。通过仪式被确认为某一宗教传统的成员之后,青少年便对这一新的、更大的群体承诺了忠诚。忠诚具有两重性,其危险在于局外人的攻击,这种攻击有可能影响局内人的价值认同。因此,在某些青少年中会导致认同破碎,呈现出一种狂热的崇拜体验和失去自我的神秘幻想。
在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的第六个阶段,即成年早期(18—25岁),刚刚成熟的成年人面对的问题是“我能够得到爱吗”,其心理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为亲密对孤独。埃里克森发现,在成年早期的生活中,性别之间决定性的生物学差异,最终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危机和化解,并且会按照他们典型的爱和关照模式,形成两性持久的两极分化。这些模式在生育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中得到最明显的反映,同时也出现在宗教所采取的共同形式中。埃里克森认为,男性是在允许内疚行为自由的逻辑中寻求宗教信仰确认的,女性则是随宗教信仰本身(在新的一代中建立信任和培养希望),也就是在她们能够做什么的逻辑中找到宗教信仰的。因此,“爱是减轻分离功能中固有对抗、永远忠诚的相互关系……是伦理关怀的基础”②在爱中体现着忠诚,这是埃里克森判断该阶段宗教美德的标准。[4]129-130。
在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的第七个阶段,即成年中期或中年期(25—50岁),中年人面对的问题是“我能够使自己的人生有价值吗”,其心理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为繁衍对停滞。埃里克森指出,繁衍的核心在于安排和指导下一代,这里包括直接养育自己的后代以及社会生产力、创造力的延续两层含义。中年期的美德是关怀,这是一种基本的特质,并且是各种自我特质的成功保持。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够确保繁衍,人们只能说所有的制度都渴望成功的道德。甚至宣布放弃生理上生殖功能的修道院宗教传统的冲动,也显示了对于关怀更深刻理解的一种努力,因为它投射了一种超人的能量,这种能量必须“足够强大,以便指导(或者至少免除)男性克服自由繁殖后代的倾向”③“超人能量”是埃里克森对宗教专职人士自我控制力的神学表述。[4]131。
在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的第八个阶段,即成年晚期或老年期(50岁—死亡),老年人面对的问题是“对于我的存在而言,它是怎样的”,其心理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为自我整合对厌恶和失望。按照埃里克森的说法,具有自我整合的老年人知道,“个人的生命不过是仅仅一个生命周期与仅仅一段历史的偶然巧合,而且对他来说,一切人类整合的成败与他所参加的一种整合方式也是密不可分的”④这段话是埃里克森将个体成长与社会发展有机融为一体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论述。[5]125。缺乏或丧失这种自我成长的自我整合,往往表现为厌恶和失望。这种厌恶和失望没有与有意义的生命远见相结合,只不过是个人对自己的鄙视。因此,一个有意义的老年期,要在最终衰老之前,能够为赋予生命周期以必不可缺的前景需要服务。此时所采取的形式,是对以死亡为归宿的生命的积极关注,这种积极关注又可称为“智慧”。“智慧的本质不是一种个体的成就,而是在相当程度上通过有活力的宗教或哲学传统所提供的。”⑤“智慧”也是埃里克森对老年期宗教美德的概括。[4]140
(二)强调社会文化在个体宗教心理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关于社会文化在个体宗教心理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埃里克森是在对北美印第安人的田野考察中找到证据并对其加以系统阐发的。
埃里克森首先考察的是美国南达科他州的苏族(Sioux)印第安人。南达科他州的苏族印第安人以狩猎为生,他们规模最大、最崇高的宗教仪式为太阳舞。太阳舞每年夏季举行两期,4天一期。此时,野牛肥壮,野果成熟,牧草茂盛。作为仪式开始的斋宴,表达的是对野牛神的敬意;接下来是丰收和婚娶仪式,这些仪式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仪式相似;随后是作战与狩猎游戏,此类游戏着重表现人与人之间相互竞争的荣耀,以及相互之间的依存和友爱;最后要完成相互自残的仪式。这是人们履行在一年中关键时刻许下誓言的时刻。埃里克森描述道:“这时节目达到了高潮。只见男人们用带勾的针穿进他们胸部和背部的肌肉,用长长的皮条把针的另一端绑在太阳柱上,然后他们盯着太阳,缓缓地向后跳跃,直到肌肉被撕裂,胸口被撕开为止。这样,他们成了当年最优秀的人物。他们通过忍受的痛苦来祈求继续获得太阳与野牛神灵的赐福,保佑他们民族的繁衍与兴旺。”①这段描述来自“超自然”的举例。[3]141-142埃里克森强调,这种为了祈求神灵赐福,把自己胸部肌肉撕裂的特别英勇的行为,只是世界上无数种表示赎罪和奉献的一种形式。每一种文明必须具有某种神秘信仰的习俗和某种荒诞规范的礼仪,这样才能使少数现象获得理解,并承认有这样一个灵魂拯救的事实。
埃里克森考察的另一个样板是生活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尤罗克(Yurok)印第安人。尤罗克印第安人以捕鱼和采集橡果为生。他们的生活环境或社会文化,塑造了这一原始部落独特的宗教信仰和禁忌习俗。尤罗克印第安人居住在狭窄、多山和森林密布的河谷以及河流通往太平洋的沿岸地区。这里没有东西南北,只有上游和下游。尤罗克印第安人讲究的是“清白”而非“强壮”。“清白”包括避免不纯洁的接触和污染。如果男性渔民同妇女发生了性行为或者和一些妇女睡在同一间屋子后,这些男性渔民就必须通过流汗屋子的“考验”(即必须通过圣火仪式,汗流浃背地穿过一个非常狭小的出口),然后还要到河口去游泳,这样才能结束“道德净化”的过程。埃里克森意味深长地指出,“尤罗克人的上帝是一位非常强壮的、到处漫游的人,他的无法无天的行为危及了整个世界。他的儿子说服他离开这个世界,最后,他答应做一个善良的神。但当他冒险沿着海岸来到一个杳无人迹的神秘地方时,他发现了鳐鱼女巫躺在海滩上,诱人地叉开她的双腿(尤罗克印第安人传说,鳐鱼看上去非常像一个‘女人的肚子’)。他不能抵抗这个女巫的诱惑,但当他进入她的肚子时……女巫用双腿把他夹住,并把他拐走了。这个传说足以表明,昏乱和无节制的色欲会把人引向神秘的灾难。在这个由失足的上帝过分谨慎的后代建立起来的、以戒律约束的尤罗克人世界里,一个聪明的男人要避免受一个不道德的女人、或者受一个错误的时间和地点的欺骗——这里所谓的‘欺骗’是指它将危及他作为一个经济上有独立财产的人而存在,他就必须学会避免这种诱惑而成为一个‘清白’的、有‘辨别能力’的人”②这段论述是埃里克森在叙述尤罗克儿童训练问题时引发出来的。[3]176。
总之,贯穿埃里克森理论的核心主题是“个人与文化的相互渗透:个体的心灵是在特定文化背景的要求、价值观和判断中产生和形成的,而个体在生活中努力寻找意义和连续性的努力又影响了文化和历史的变化”③米切尔和布莱克对埃里克森理论核心主题的概括可谓入木三分。[2]170。
(三)运用典型个案揭示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的内在动力
为了具体地阐明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的内在动力问题,埃里克森花费了很大精力,深入探讨西方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Luther)青年时代的成长历程,以及东方宗教领袖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K.Gandhi)的心路历程,试图通过这两个典型宗教人(the homo religious)的个案研究,揭示“蕴含在心理社会危机中的动力学关系”④埃里克森动力学的侧重点在于心理和社会层面。[6]387。
埃里克森对路德心理社会危机的探讨主要侧重于其青年时代。在埃里克森看来,路德走上僧侣之路并非偶然,而是他面对与父亲持久性认同危机的无奈选择。路德去当僧侣,与父亲的愿望相反,这似乎意味着对父亲的一种无声反抗;路德选择否定性身份认同,代表着他遭遇雷击时对圣安娜的承诺;修道院僧侣生活的超然有序,显然有助于缓解路德的自我认同危机。然而,进入修道院后,路德发现,自己与上帝的认同危机居然超过了与父亲的认同危机。因此,即使对于上帝,他也表现出了一种“强迫性亵渎神灵的矛盾心理”⑤在《青年路德:精神分析与历史的一项研究》中,埃里克森对此有详尽的描述。[4]29。当路德从奥古斯丁修道院被派到威登伯格修道院时,他遇到了心地仁慈的大主教约翰·斯托皮茨(John Staupitz)。斯托皮茨引导路德领悟信任感的重要性,并耐心地帮助路德转变对上帝的态度。埃里克森据此分析到,路德中断学业到修道院隐修,这是路德在处理个人与父亲心理社会危机方面的消极认同;路德从斯托皮茨那里获得的宗教教诲,则是路德在处理个人与上帝心理社会危机方面的积极认同;从消极认同向积极认同转变,无疑是路德后来能够成为一名宗教改革家的内在动力。
埃里克森对甘地心理社会危机的探讨则贯穿其整个人生。在对甘地青少年期成长经历的考察中,埃里克森发现,甘地受母亲的影响非常深刻。甘地的母亲目不识丁,虔诚仁爱,深情告诫外出求学的儿子不得食荤,不要酗酒,这些都成为甘地后来成长的动力。甘地受父亲的影响较为复杂。他和父亲的关系,“类似圣经中子对父和父对子的主题”①埃里克森在考察甘地的心理社会危机时,经常不自觉地流露出个人基督教的背景;巧合的是,甘地在汲取印度古老宗教传统的营养时,也喜欢与西方的宗教加以对比。[7]97。埃里克森指出,甘地对养育自己、长期生病的父亲怀有依恋,但对父亲13岁便让自己成亲一事又决不能宽恕。这种心理社会危机是推动甘地青少年时期思想成熟的动力。甘地在南非工作时遇到的种族歧视,铸成他成年后立志成为一名改革者的强大动力。甘地1915年返回印度后,在争取民族独立、推为政治领袖的宗教实践中,创造了绝食等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方式,从而使甘地表现出一种宗教现实主义者的独特品格,即通过某种成熟的活动过程进行有效实践,并力求从印度古老的宗教文化中汲取营养。总之,正如埃里克森所指出的,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背后蕴含的深刻心理矛盾,是推动甘地勇敢地探寻“人类生存真正力量”的不竭动力。②埃里克森这里所说的“真正力量”,显然是指传统宗教的精神力量。[6]392
三、埃里克森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理论的历史地位
埃里克森的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理论具有哪些历史贡献呢?在本人看来,以下两个方面的历史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一是完善了个体宗教心理毕生发展的阶段划分理论。在霍尔的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理论中,着重探讨的是青少年期个体宗教心理的发展特点;至于霍尔有关儿童期和老年期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特点的阐述,主要是为了相关年龄阶段的衔接或延续,因而显得较为单薄甚至肤浅。埃里克森的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理论,以沃尔夫的“渐成论”为生物学根基,以弗洛伊德的心理性欲发展阶段说为扬弃之框架,以米德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思想为重点突破方向,全面超越了霍尔的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理论,成为西方从个体宗教心理角度系统阐述发展特点及其规律的重量级人物。正如伍尔夫所评论的:“无论他的作品可能具有什么缺点,或者无论它需要怎样的纠正和补充,它将长久地保持必要的阅读。”③这是伍尔夫对于埃里克森历史贡献的最后评说。[6]413
二是深化了学界对于个体宗教心理发展原理的认识。什么是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的动力?哪些因素对个体宗教心理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对于这些问题,埃里克森之前的研究者虽然具有或多或少零散的论述,但围绕一个人的生命周期,进行系统的、创造性的、跨文化视角探究的学者,笔者认为只有埃里克森!埃里克森关于婴儿信仰是由母亲信仰培育起来的论断,关于心理社会危机是推动个体宗教心理发展动力的阐述,关于个体的心灵是在特定文化背景的要求、价值观和判断中产生和形成的,而个体在生活中努力寻找意义和连续性的努力又影响了文化和历史变化的思想,至今仍显现着真理的光辉。笔者以为,当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思考中国文化背景下个体宗教心理发生、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理论时,我们切切不能忽略埃里克森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理论中蕴含的某些积极因素,而这也正是该理论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一定活力的价值所在。
关于埃里克森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理论的历史局限,笔者认为下述两个方面比较突出。
其一,关于个体宗教心理发展阶段的假设缺少实证支撑。埃里克森关于个体宗教心理发展八个阶段的划分,是从其世俗性的个体生命周期理论推演而来的,并试图借助路德、甘地这样典型的“宗教人”个案,对该理论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然而,在以实证为基础的西方主流宗教心理学中,没有可测量、可重复、可检验的数据支持的假设,往往会引来非议。正因为如此,有人批评埃里克森的个体宗教心理发展阶段理论是“一种解释性心理学,而不是科学心理学”(J. J. Fitzpatrick,1976)④类似的批评较多,这里仅引用了其中一例。[8]。此外,还有人将批评的锋芒指向埃里克森关于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的某一具体阶段的特征概括,例如科特(J. Kotre,1984)指出,繁衍的主要成分开始于成年早期,但埃里克森把它分配到成年中期,而且对于像路德、甘地这样的“宗教人”来说,“繁衍可能在某些生活中导致真正的破坏性……成为一种潜在的邪恶”⑤科特的批评侧重于埃里克森关于“繁衍”释义的生理层面。[6]407。
其二,有关个体宗教心理发展规律的解释仍然具有偏颇。埃里克森认为个体的宗教心理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这种发展受到生理成熟、社会文化和教育训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解释从方向上来看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具体的阐述中仍然存在不少漏洞乃至偏颇。我国学者孙名之早在1998年翻译埃里克森的著作《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时,便在中文版译序中尖锐地指出:“他的理论深处仍然保持着弗洛伊德理论中的生物学化观点……个人的成长与社会的进化原来是两个独立且平行的系统……个人既没有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制度也只是以心理社会产物为基础的一些上层建筑。”①在心理学界,一些已故著名心理学家(如潘菽、高觉敷、朱智贤等),大多持有像孙名之先生这样的见解。[5]7-8这些一针见血的批评,至今仍然是我们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辩证看待埃里克森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理论是非功过的警世箴言。
[1]熊宏哲.西方心理学大师的故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斯蒂芬·A.米切尔,玛格丽特·J.布莱克. 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现代精神分析思想史[M].陈祉研,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3]埃里克森.童年与社会[M].罗一静,等编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4]Erikson E H. Insight and responsibility:lectures on the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psychoanalytic[M]. New York:W. W. Norton,1964.
[5]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M].孙名之,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6]Wulff D M. Psychology of religion:classic and contemporary(2nd ed.)[M].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Inc.,1997.
[7]埃里克森.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M].吕文江,田嵩燕,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8]Fitzpatrick J J. Some problematic features of Eric H. Erikson’s psychohistory[J]. The Psychohistory Review,1976,5(3).
[责任编辑:杨雅婕]
A New Exploration about Erikson’s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Individual Religious Psychology
CHEN Yong-sheng
(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China )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rikson’s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individual religious psychology are mainly display in a complete outline based on the entire life for development stages of individual religious psychology, an emphasis on culture’s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dividual development of religious psychology, and a revealing of the inner dynamics of the individual development of religious psychology through cases. It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includes that this theory perfected the stage division about life-span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religious psychology, and deepened the understanding of development principle of individual religious psychology. Its historical limitation includes that this theory lacked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presumption of development stages of individual religious psychology, and did not entirely explain the law regard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religious psychology.
Erikson; individual religious psychology; development theory
陈永胜(1952— ),男,山东济宁人,硕士,浙江师范大学心理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宗教与社区心理学、学校心理健康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2BZJ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B84-0
A
2095-7068(2017)01-0074-07
2016-04-12
10.19563/j.cnki.sdjk.2017.0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