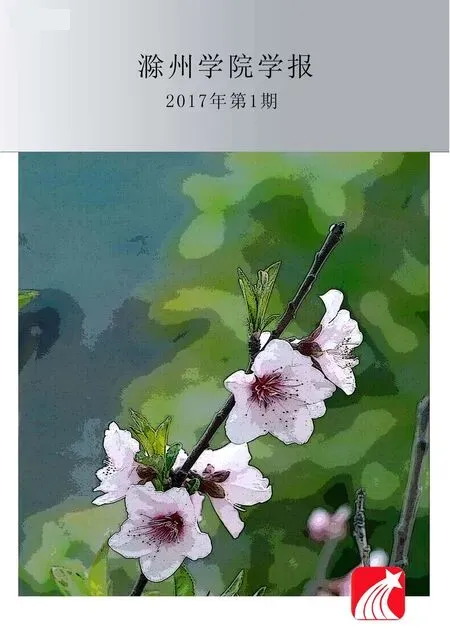从《儒林外史》看吴敬梓的教育思想
苏 立
从《儒林外史》看吴敬梓的教育思想
苏 立
《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小说,也是一部教育学专著,从《儒林外史》中可以看出吴敬梓丰富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想,归纳起来主要有:反对科举制,期待教育改革;重视人格教育,呼唤道德建设;主张养教并重,重视教育与生产协调发展;主张教育助政,渴望文武全才;重视实业教育,主张教育多元化。
儒林外史;吴敬梓;教育思想
《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小说。但是,笔者最近研究发现,在这部书里,也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吴敬梓通过一个个人物形象和他们的语言讨论了一系列教育问题,比如:科举取士问题;学子的出路问题;登科者的道德建设问题;教育与生产的关系问题;教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排除单一的科举教育内容,实现教育内容多元化的问题等等,通过登场人物的谈话和思考,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可以说《儒林外史》也是一部教育学专著。总体概括起来,从《儒林外史》看吴敬梓的教育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反对科举制,期待教育改革
《儒林外史》强烈地批判封建科举制,揭露主试不学无术,蔑视应试者愚蠢无知;批判考试买卖贿赂,猜试赌题,死记硬背,找人替考等种种问题。从吴敬梓的身世看,他深知走科举之路的希望渺茫,渴望除了科举制以外还有很多成才之路,期待教育改革。他首先推出了王冕,这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形象。王冕家里很穷,没有钱进学堂读书,边放牛边学习,边练习画画,天文、地理、经史,无一不通。他鄙视功名利禄, 安贫乐道,孝敬母亲, 与人友善, 是一个儒家贤者的风范。他批判八股取士制度说:“这个法却定不好, 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 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1]12与其他儒林人格堕落的士子们相比,王冕是吴敬梓心中的成功教育的理想形象。在其他很多章节也透露出了吴敬梓的这种思想。在第二回“王孝廉村学识同科周蒙师暮年登上第”中,周进的姊丈金有余来看他劝道:“老舅莫怪我说你:这读书求功名的事料想也是难了!人生世上难得的是这碗现成饭只管稂不稂莠不莠的到几时?我如今同了几个大本钱的人到省城去买卖,差一个记帐的人,你不如同我们去走走;你又孤身一人在客伙内还是少了你吃的、穿的?”。[1]24他反对科举制考试内容方面的局限。鲁编修认为做八股文的举业才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1]115的读书人的正道。迟衡山则与鲁编修不同,他认为“这举业二字原是无凭的”“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1]345反对学而优则仕,批判那些有学问的人取得功名之后,贪污腐化,主张学问与功名分开。用迟衡山的话说: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若是两样都要讲,弄到后来,一样也做不成。”[1]500
《儒林外史》主题之深刻伟大,在于它的‘反体制’思想,是对过度膨胀的体制及其造成的儒林整体堕落,日趋丑陋的沉痛反思。[2]
二、重视人格教育,呼唤道德建设
《儒林外史》着墨于写在科举制度驱使下士人们专营举业、贪图名利、图富弃道、色胆包天的种种丑行,他们灵魂被腐蚀,人格遭扭曲,沉沦为儒林丑类。“儒家传统人格的失落和儒林人格的堕落是吴敬梓剖析人物现状反思探索人格理想的动因。”[3]
王德、王仁受贿二百两银子,在妹妹还没有断气之前就做主把行贿的小妾扶正了;严贡生赖人家的猪、房产、家产、船钱;举人王惠上任首先想到的是讨要人情、地方特产;秀才匡超人私动官印,篡改文书,勇做抢手,撒谎未娶,再攀高枝。这些儒生玷污了《儒林外史》的前三十二回,各个道德败坏。书中列举了犬儒们道德沦丧的种种恶行,表达了吴敬梓对人格教育的担心。同时,书中也列举了杜少卿、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等正面形象,抒发了吴敬梓人格教育的理想。他们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遵规守道, 崇尚礼乐,实行兵农, 诚实守信,侠义助人,主持正义,但是,他们却被世人看做是呆子、狂人,不入主流。他们虽无力挽狂澜之力,却能洁身自好,比如:匡太公临终嘱咐儿子:我一生是个无用的人……将来读读书,会上进一层也不可知,但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1]178
归纳起来,吴敬梓的人格教育理想有: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有独立思想、重修身立德,重节操、重品行,博学多才,孝敬父母,知恩图报,讲究信义。
吴敬梓师德教育也有自己的见解。用蘧太守的话说:“不瞒二位贤侄说,我只得这一个孙子,自小娇养惯了。我每常见这些教书的先生也不见有甚么学问,一味装模做样,动不动就是打骂。”[1]92批判了教师的无知无法无德。可以说,《儒林外史》是一部极好的道德教育的教科书。
三、主张养教并重,重视教育与生产协调发展
吴敬梓主张养教并重,重视教育与生产协调发展的思想在书中有所体现。他在“慎思堂”中巧妙地设置了的金笺对联,这幅对联写得好:“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1]234读书和耕田并不矛盾,读书也好耕田也好,学好便好。读书,生产,礼教应并重。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描绘了嘉靖和萧云仙这两个主张养教并重,重视教育与生产协调发展的人物。嘉靖重视富民行礼,在问策时咨询庄绍光:百姓不能温饱,士大夫不行礼乐。教养之事,何事为先?庄绍光解答他的提问便把富民行礼之事,做了十策。这些策略在萧云仙的实践中得到了落实。萧云仙优先发展生产,在此基础上发展教育。重视教育与生产协调发展。他 “出榜招集流民”“开垦田地”“亲自指点百姓兴修水利”、骑马劝农。他想 “百姓们的日子有的过了”“只是这班小孩子……怎得有个先生教他们识字便好。”,于是,请来常州读书人沈大年,把孩子们“都养在学堂里读书”“和他分庭抗礼,以示优待”。 卧闲草堂本评者评论说:“萧云仙在青枫城能养能教,又能宣上德而达下情,乃是有体有用之才”。《儒林外史评》评论说:“既有以养之,必思所以教之,坐言起行,方不愧儒者。”
四、主张教育助政,渴望文武全才
吴敬梓在书中,也提到了他对教育目的的态度。首先,由于他接受了当时一些进步思想家如颜元、李塨等人的影响,在教育的目的就是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上,他同意统治者制定的教育目的的本没有错处,不能有益于政治的教育是应当被反对的。[4]
从《儒林外史》的故事描写里可以看出吴敬梓主张教育助政,渴望文武全才。迟衡山认为士人应该“替朝廷做些正经事”: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1]345杜少卿说得更具体“宰相须用读书人,将帅亦须用读书人”。敏轩认为,教育培养的人才,应当是文武全才,既要能做宰相,又要能当将帅。做为宰相,要懂得发展经济,使百姓解决“温饱”,丰衣足食,率先垂范,能行礼乐。做为将帅,要能保持稳定,平定叛乱,剿灭逆贼,维护朝廷的体统。杜少卿、敏轩、萧云仙等人物是教育助政的代表,他们文武全才,心系百姓,施政有道。相反象南昌太守王惠、马二先生等人物则是吴敬梓批判、鞭挞的对象。他们做举业,谋官位,却无助时政,无能治理一方,“件件都是虚应故事”以致“盗贼横行”,不求安民良法,执念雪花白银。王惠的县衙里经常响起是算盘声、板子声。还有一些士人心理素质差、生存能力低下,为了科举,成了呆子傻子。周进60岁还未进学,到省城看贡院一头撞在号板上,悲恐晕厥过去。得到捐助,高贵的膝盖跪向了他一向瞧不起的商人。未考取之后教学的差事也丢了,最后只得靠给商人记账维持生计。范进家里穷困潦倒,时常断粮,在得到捷报之时,跌了一跤,不省人事,醒来疯了。倪老爹只读死书,做了37年的秀才,毫无养家糊口的能力,六个孩子,死了一个,卖了四个,最后一个还过继给了别人。这样的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不是文武全才的精英而是愚昧无知的低能儿。
五、重视实业教育,主张教育多元化
《儒林外史》中讲述了祭泰伯祠、萧云仙重农桑、市井四大奇人的故事,抒发了吴敬梓主张发展实业教育、主张教育多元化的思想。
在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凶闹捷报” 中,周学道和童生的会话:“求大老爷面试。”学道和颜道:“你的文字已在这里了,又面试些甚么?”那童生道:“童生诗、词、歌、赋都会,求大老爷出题面试。”学道变了脸道:“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况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么?看你这样务名而不务实,那正务自然荒废,都是些粗心浮气的话,看不得了!左右的!赶了出去!”一声吩咐过了,两旁走过几个如狼似虎的公人,把那童生叉著膊子,一路跟头,叉到大门外。[1]30吴敬梓很同情那个童生。周学道甚至把诗词歌赋都看成了杂学。敏轩在《儒林外史》中批判了以四书、五经作为教育内容的同时,还十分重视某些有裨实用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认为这些学问也是“士人”所应该了解的。小说中的一些正面人物都通晓天文、地理、工、虞、水、火之学,而且还努力付诸实际。
鲁编修和娄三公子谈论杨志执中时说:“老世兄,似你这等所为,怕不是自古及今的贤公子,就是信陵君、春申君,也不过如此。但这样的人,盗虚声者多,有实学者少。我老实说:他若果有学问,为甚么不中了去?只做这两句诗,当得甚么?[1]106虞育德“不耐烦做时文”,重视有裨实用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某些社会科学;王冕“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虞华轩精通“一切兵、农、礼、乐、工、虞、水、火之事”;杜少卿“祖上几十代行医”;虞育德也准备教儿子在“读书之余”“学个医”。这些都是吴敬梓心中理想人物。吴敬梓在教育内容方面,反对八股举业,提倡有裨实用的实际学问。倪老爹说: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的重。[1] 258迟衡山说:“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1]345通过这些人物的语言,表达了吴敬梓重视实学,渴望实现教育内容与实际联系、实现教育内容的多元化的思想。“从历史发展进程看,职业教育是由实业教育演变而来。因此,这部小说中的一些实业教育的缩影及小说中所描述的一些人物对实业教育的探索对中国发展职业教育有一些借鉴意义。”[5]
另外,吴敬梓也有男女平等的教育思想。在第十一回“鲁小姐制义难新郎杨司训相府荐贤士”中描写:鲁编修无儿便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就请先生给她启蒙,熟读《四书》《五经》;十一二岁讲书读文,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他做“破题”“破承”“起讲”“题比”“中比”成篇。送先生束脩,那先生督课,同男子一样。这小姐资性又高,记心又好,到此时,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记得三千余篇;自己的文章,理真法老,花团锦簇。鲁编修每常叹道:“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士都中来了!”[1] 115他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对女子学无所用的惋惜之情,溢于笔端。
[1] 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金盾出版社,2003.
[2] 鲍鹏山.《儒林外史》的反体制思想[J].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1(3):85.
[3] 黄伟.从《儒林外史》看吴敬梓的人格理想[J].惠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44.
[4] 陈斐,张蕾.从教育目的看《儒林外史》中的教育危机[J].现代妇女(下旬),2014(3):26.
[5] 杨影,郑小琴 .《儒林外史》中的实业教育探索对我国发展职业教育的启示[J].江西科技学院学报,2015(2):9.
责任编辑:刘海涛
Wu Jingzi's Education Thought fromTheScholars
Su Li
TheScholarsis a satirical novel, but also an education book. fromTheScholars, Wu Jingzi's educational thoughts can be seen mainly including: be agains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pay attention to personality education and moral construction; stres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education and production; advocate the education service for civil and military; attach importance to industrial education and diversified education.
TheScholars; Wu Jingzi; educational thought
G40-092
A
1673-1794(2017)01-0001-03
苏立,青岛科技大学传播与动漫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文学与新闻传播(山东 青岛 266000)。
2015-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