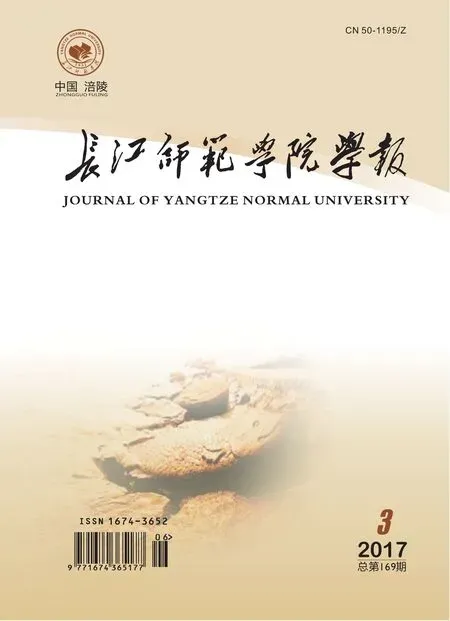民国时期的家庭形态的嬗变与中国现代小说
——以吴组缃的破产小说为例
吕洁宇
(曲靖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民国时期的家庭形态的嬗变与中国现代小说
——以吴组缃的破产小说为例
吕洁宇
(曲靖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20世纪30年代,中国遭遇的经济危机给当时的家庭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吴组缃的破产小说对其进行了客观的描写。他通过对皖南农村家庭的书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现状和家庭形态的变化。经济破产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农村女性不得不谋求经济独立,社会经济的变化加快了封建宗法制的崩溃,也对家庭伦理和亲情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传统的家庭形态在外界环境的刺激下正发生着重要的改变。
吴组缃;破产小说;家庭书写;家庭形态
吴组缃的小说量少而质优,他曾说他的小说“取材方面,大多写内地农村,其中又以反映农村破产时期动态的居多。”[1]从1931年至1935年,中国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在这期间,他创作了《小花的生日》《栀子花》《黄昏》《官官的补品》《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等大量破产题材的小说。而这些作品几乎都以家庭为主要叙述场景,通过对家庭的书写向我们展现了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衰败。一直以来,学界对吴组缃的破产小说都较为关注,严家炎肯定了他的写实风格和剖析精神,丁帆则将吴组缃定位为社会剖析派乡土小说家,认为他的小说“通过异常冷峻客观的描写来展示农村社会畸变、衰败和丑恶的图景”[2],作品中的风物描写和语言都带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同时很多学者也关注到了他作品中的革命反抗精神,认为其作品具有“左翼”文学的色彩。吴组缃的小说多专注于20世纪30年代破产家庭的生活,通过家庭形态的变化反映了时代的变迁,但极少有人从家庭入手来考察作品[3],从而忽略了吴组缃作品中最基本的书写场景。我们通过吴组缃对家庭的描绘可以看到民众在黑暗社会中的挣扎与绝望,更明晰地了解20世纪30年代家庭形态的变化。
一
吴组缃的破产小说“对全般社会进行了缩影式的描绘”[4]。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战乱严重扰乱了社会的稳定,经济危机影响了中国的贸易,连年的旱涝灾害致使农作物产量低下,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的压迫等因素都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农村经济并导致了大量资本的破产,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很多报纸都对当时农村的衰败予以了描述,诚如国民党政府在报告书中供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其描写农民则谓“成千累万,泥首军前,鹄面鸠形,僵卧道右”,有人写道:“江苏农民,早已由天堂而入地狱。”[5]吴组缃的家乡皖南也难逃厄运,店铺倒闭,工人失业,乡民生活窘迫。吴组缃在《栀子花》《官官的补品》《黄昏》等小说都详细交代了当时的社会情形和家庭的变故。《栀子花》通过祥发的视角叙述了当时农村的衰败境况:“古旧的破屋子,倒塌的墙和狭隘崎岖的石路,鸦片馆,小赌摊,褴褛的男人和女人,大家都戴着一个沉郁忧愁的脸,谈着关于粮食涨跌,土匪兵灾的事……村里,镇上,以及邻近许多地方,近来每年都有许多店关上门,贴上 ‘召顶’的字条。”《天下太平》通过王小福的生活境遇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他升做 ‘伴作’时,村里镇上早盛行着既漂亮又便宜的竹布和花洋布,娘的纺纱织布的工作已不能维持下去,而一个 ‘伴作’照规例每年只支得10多元薪资,最好的年头也不过勉强支20多元。这工钱除了做一两件不可省的衣服外,仅仅只够得补贴娘花用。”可见,大量的外国商品占领了中国市场,民族经济在外来资本的挤压中纷纷破产,致使像王小福这一类以传统手工业经济为生的店员大量失业。吴组缃的小说将社会的变迁与家庭的兴衰融合到了一起,客观地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状况。
20世纪30年代社会经济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农村家庭的生活,大量小康之家坠入困顿,工人失业,佃农无力承担租金以致生存艰难。吴组缃的家乡——安徽“是个地瘠民贫的省份,失业问题要较重于任何省份”[6],在遭遇了经济危机以后,农村经济每况愈下。据1930年11月的统计,“浙江省贫困无以为计的达二百九十一万七千九百六十八人,而安徽较浙江贫困殊多,即使不超过二百九十万,但无论如何总不会较下于浙江。”而后几年的情形只会愈发恶劣。在吴组缃所描写的皖南乡村,大部分家庭中的男性都在店铺中当佣工,当遭遇破产,大量的男性劳动者失去了工作,陷入了经济困境的家庭不得不依靠女性做工来维持生计,因而女性被迫成为了家庭经济的主要贡献者。吴组缃破产小说中的家庭模式基本都是如此。在《栀子花》中,“祥发失业后,只靠着妻做女红所赚的钱来敷衍日子,想尽了路头谋生意,都毫无结果。”《小花的生日》里的小花爸爸歇了生意回家已经快有5个月了,“如今一家四口子,都靠她十个指头替人家洗点衣服,做点女红来维持”。《天下太平》里的小福子失业之后,一家人的生活顿时落入贫困,他春天尚可上山去挖野货,到了夏天,有时“成天找不到一点事做,是完全寄生在妻和娘甚至孩子的身上了”,他也自责:“自己堂堂一个壮年男子,如今是完全变成一个寄生者。”迫于生存的压迫,妻子只好去卖奶水来换取全家的吃食。吴组缃笔下的女性已经开始通过劳动来获得经济的独立。但是,这种转变是被逼迫而不得已的艰难之举,她们大多只能从事简单的商业劳动,通过卖奶水,洗衣服来获取微薄的报酬。虽然她们还不能通过劳动来完全改变家庭的困境,但是她们已经摆脱了对男性的依赖,生存的危机促使农村妇女在自我解放的路上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
妇女独立一直是思想文化解放的重要内容,而经济独立是妇女解放的重要条件。在“五四”倡导妇女解放的思想潮流中,有很多进步报刊都十分关注妇女经济独立问题,它们刊登了不少相关文章,阐释了妇女经济独立的重要性。李达在《女子解放论》里指点也:“女子的地位,常随经济的变化为转移。女子也是 ‘人,就当为生产者。’”女子“果能有此经济独立的能力,则婚姻的结合,以爱而不以利,男子自然承认女子的价值,真正改变态度,抛弃特权,男女间一切不平等的道德与条件,也可以无形消灭了。”[7]茅盾也认为:“经济不独立,是妇女地位、人格、低落的原因,是妇女被压制的原因。所以妇女运动的第一句motto(座右铭)便是经济独立。”[8]由于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的破坏,很多女性不再仅仅需要依赖家庭才得以存活,她们得以走出家庭进行生产劳动。到了二三十年代,女性拥有工作已成为极其普遍的社会现象,女性已经能够通过参加社会工作获得经济独立,“据1930年工商部统计,江、浙、皖、赣、鄂、鲁、桂、闽9省28市女工共有37万多,占全部工人总数46.4%。”[9]可见已有大部分女性走出了家庭,但是其劳动创造的经济价值不大,为数众多的女性工人所从事的都是体力劳动,只靠劳力而不需要技巧和知识就可胜任。当然这一数据统计主要是针对城市妇女,对农村妇女而言,情况就不同了。由于当时农村思想闭塞,很多家庭仍保留着传统的劳动分工,在安徽合肥的农村,农妇每日的操作便是“烧锅,煮饭,带孩子,以及补缀破碎衣服等事。畜养家畜,也是她们的专责,可是她们所照应的只是猪、鸡、鹅、鸭等。”[10]可见当时妇女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屋内,吴组缃的家乡——茂林的情况应该也是如此。而到了破产时期,情况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农村经济还没有走到破产的境地时,农妇们的奴隶生活也还能勉强支持下去。可是现在的情形已完全不同,就连奴隶生活都不能继续了。”[11]大量男性逃亡到城市谋生计,留守在农村里的妇女就陷入了绝境。在吴组缃的破产小说里,女性在家里主要承担养育子女和简单的家务劳动,遭遇破产之后,迫于生存的压力,女性必须想尽办法求生存,甚至连王小福(《天下太平》)年迈的母亲都到街上卖油条换得几个铜板,可见,吴组缃笔下的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独立,但是这种独立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女性受压迫的现状。首先,这种经济独立伴随着经济衰败而产生,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她们的经济地位也随时都有丧失的可能。其次,经济独立与职业获得是等同的,“五四”时其人们“把妇女获得职业看成是妇女摆脱家庭约束,实行经济自立,成为自食其力者的必要手段。”[12]而吴组缃笔下女性的工作只局限于简单的生产活动,缺乏稳定性,还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并且她们的工作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家庭衰败的现状。因此,经济压力是促使农村妇女寻求独立的外因,而在当时动荡的社会时局中,要想让女性真正的获得独立,必须改变衰败的社会现状,而这则必须依靠一次彻底的社会变革。在吴组缃后来的作品中,这一思想逐渐得以展露。
二
吴组缃不仅仅展现了小家庭形态的改变,也触及到了封建统治最根本的维系——宗法制,吴组缃在《一千八百担》中描写了宋氏子孙对1 800担粮食的算计,他们想独占甚至瓜分这份共同财产,对物资的争夺超越了伦理亲情,这也意味着这个大家族失去了维系。茅盾认为这部小说“很有力地刻画出了崩坏中的封建社会的侧影”,宗族的解体也预示了封建社会解体的命运。
宗法制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将有亲情和血缘关系的组群联系到了一起,它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组织细胞,建构了封建社会严密的制度等级。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封建的婚姻家族制度和观念开始削弱,西方家庭文化逐渐进入中国,但同时由于旧有社会经济基础没有改变,旧式封建家庭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着,它与小家庭制度一起构成了这时期家庭状况的两重性。总的来说,此时宗族家庭的存在形态已经没落了。1930年,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主编的《统计月报》(11、12月合刊)上公布了卜凯对1921-1925年安徽等7省16处2 640户的家庭成员情况的统计数据[13]:农家平均人口为5.65人,其中安徽南部的农家平均人口为5.53人,一个家庭中夫妻及子女占到家庭成员的77%。另外,余华林将金陵大学农学系、清华大学等多个机构的调查资料予以整合,对这40年来的家庭变化情况进行了统计,得出的结论是:“20世纪10-20年代的调查表明平均家庭规模为5人左右,多者至6.43人。而30-40年代的家庭规模则又有所减小,其算术平均数多为4人左右。”[14]这也说明传统的宗族家庭的构建方式已经没落,小家庭已成为多数,家庭组成也更为简单。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宗法制并不会如此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其家族观念仍根深蒂固地存在着。1927年6月《时事新报·学灯》编辑部在该报刊登了一次社会学问卷,其中一类问题是关于对大小家庭制及祖宗祭祀的看法,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人认为祖宗祭祀制度殆将淘汰,但祖宗纪念的原则不可丢,在当时中国,宗祠和宗谱仍具相当之势力。”[15]可见,即使宗族制的存在形态遭到了破坏,但它的精神内核仍影响着民众的家庭观念。当时的宗族家庭形态已经开始向小家庭转变,它们按照小家庭的模式进行生产创造,但同时又保留着封建宗族制的精神维系,它处于一个混合的状态。
“自给自足的农业是血缘家族存在的经济基础,家风和家法是维系中国家族制度的最重要因素。”[16]在20世纪30年代的皖南乡村,自然经济已经解体,宗族家庭已不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有着自己独立的经济活动。在《一千八百担》中,宋氏家族的子孙们都拥有独立的产业,他们处于小家庭的组织模式中,与整个大家族的利益联系微乎其微,失去了维系家族存在的重要基础。同时,族人的家族荣誉感和参与精神也便逐渐丧失,宗族制家庭赖以存在的纲常伦理也逐渐瓦解,正如宗族老人鑫樵老所说:“从前姓宋的走出一个人来,都是像模像样,有貌有礼的。那时候词堂里每月三小祭,每年二大祭。子孙走进来,按辈分,坐的坐,站的站:尊卑有次,长幼有序。老辈子不开口,小辈子那个敢哼一口气?而今是个什么样子?简直是个放牛场了!敏斋,这个家法,我说,还是要整顿的……”[17]鑫樵老的脑中还保留着50多年前宗族的模样,从他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民国时期宗族统治的急剧衰落。即便如此,现在宋氏家族仍保留着宗族的躯壳,他们有血缘联系和少量的共同财产,但它的维系力已经很微弱了。1 800担粮食是家族的共同财产,用以维系整个家族事务的正常运行。此时年青的宗族子孙早已摆脱了封建家庭的束缚,进入了城市;老一辈族人心念着整个家族,却已无力挽回大局;中年族人拥有着社会大权,却全然抛弃了团体的精神和宗族的共同利益,只想着为自己筹谋,连身为族长的柏堂都意欲中饱私囊。一个庞大的家族体系已经近于崩溃。他们在祠堂里谈论着瓜分粮食并为此发生了争斗,祠堂作为宗族权力的象征也失去了它的威严。在相互的争夺中,最后的一点精神维系也丧失殆尽。因此,宋氏家族是所有封建大家族的一个缩影,宗族在乡村虽然还存在,但是它的衰败已经是不可避免。整顿家风也只能是鑫樵老的一个梦想,因为时代的变革终会将宗族制淘汰,吴组缃所描写的宋氏家族会议也成为了它崩溃之前最后的一点记忆。
三
经济衰败对家庭的影响不仅仅表现为物质的困窘,同时也表现为对原有的家庭关系的冲击。经济问题导致了各种家庭问题增多,矛盾激化。生存的压力甚至逼迫人冲破了道德的底线,亲情伦理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代际冲突在此时表现得极为明显。吴组缃的《樊家铺》写了一个处于焦急和痛苦中的女人弑母的故事,吴组缃自己坦言:“此稿特别为美国读者所看重。但在国内或因写了杀人放火,觉得内容不健康,故不为论者道及。”[18]可见,这篇文章的内容确实与中国的传统伦理观相冲突。“弑母”是对中国传统伦理的背叛,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少有的,但吴组缃之所以会描写这一情节,也是有着深刻的文化原因的。由于长久以来的礼教束缚,子女的命运都由父母掌握,因而对父母须保持绝对的服从。随着民国法制的健全,子女也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同时,由于思想解放中“反封建”口号的提出,“人们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曾经严重桎梏人们思想的封建道德和伦理观念。而以家长专制为主要特征的封建孝道伦理,因为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极为紧密,首先受到人们的强烈质疑和批判。”[19]这些因素都冲击了传统的伦理关系,长久以来对纲常伦理的过度强调极大地压制了人的正常需求,而线子嫂的例子可以视为传统封建家庭本身固有矛盾的爆发。另外,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也为悲剧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此篇为中心故事铺开了一个颇广阔的社会背景,写了多方面的社会形态。丢开了这个环境背景,此篇题旨就没有什么意义了。”[20]社会时局的动荡和经济的衰败让本来繁荣的樊家铺变得一片死寂,生活艰难的线子嫂又恰逢丈夫被抓,走投无路的她为救丈夫杀母取财,吴组缃通过这一场景展现了线子嫂在身处困境之中的不得已而为之,生存的危机是她走向犯罪的根本原因。再者,线子嫂处于一个畸形的家庭关系中,亲情关系的淡漠也是促使她反目的一个原因。线子嫂在刚出生后就被送去当童养媳,与母亲感情疏远,对丈夫的依赖则成为了她感情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母亲认为“嫁出去的女,泼出门的水”,沉重的家庭负担让她对女儿的事情无能为力,而女儿线子嫂则因为母亲的不肯相助而心中充满了忿恨。因而,当得知丈夫有生命危险时,亲情和爱情在线子嫂的感情天平中轻重立判,她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母亲的对立面。《樊家铺》以一种较为极端的方式表现了传统伦理关系在社会经济恶化中的崩溃。可见,传统的家庭观念已经不能再适应社会的发展了,长久隐匿在伦理道德之下的各种矛盾得以爆发,一种新的家庭观念正在形成。
随着大家庭的解体和家庭关系的简化,夫妻关系逐渐凸显而成为了家庭关系的核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公民独立自主意识的增强,妻子对丈夫的依赖逐渐减弱,夫妻关系也逐渐趋于平等。但这也意味着以前隐秘的冲突现在变得公开化,夫妻矛盾也随之变得更加尖锐。
在封建家庭中,男性一直拥有着家庭的主导权,妇女是男性的私有物品,可以被任意支配,妇女只能忍气吞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导致大量男性失去了工作,他们只能依靠女性的劳动来维持生活,这给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男性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男性的挫败感和女性地位的上升逐渐地形成了对立,激化了夫妻矛盾。小花爸爸(《小花的生日》)在失业之后,“每天枯坐在屋里,看妻的愁眉怨眼,听小孩子的大哭小叫,和体味着亲戚本家们底讥笑与蔑视底辛味。他原是一个生性刚强高傲的人,在这种生活底紧压之下,一腔悲愤,就只有向美容和大花身上找岔儿发泄。”为了小花能有衣服御寒,三太太约了人在小花家里打牌,期间富少爷的举动却让美容遭遇了丈夫疯狂的殴打,妻子忍不住道出了委屈:“你死起两块铁脸在家里闲住五六个月,躺倒睡,伸手吃,你几曾给我个半文钱!我辛辛苦苦地一天做到晚,几个钱来养你们一家饿瘪鬼!”《黄昏》中的松寿针匠被辞退,“在家里住闲,碍了媳妇的眼,媳妇就借题目天天哭闹。说丈夫没出息,说他白顶了个男人头。”《天下太平》里的小福子失业后,看到娘和孩子很辛苦,“偶尔在无意中自言自语地说一两句自己谴责或是对娘和孩子表示惭愧和罪疚的话。话刚说出口,妻就免不得要抢白他”。可见,由于传统家庭劳动关系的被打破,男性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当他试图用以前的家庭模式来重建自己的威信时,自然遭遇了女性的反抗,而这也使得处于生活困境中的夫妻关系变得更加脆弱不堪。经济的衰败让女性的家庭地位有了上升的可能,但是这种上升是在相对滞后的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发生的,大多带有屈辱性意味。因而妇女地位的提高仅仅是经济地位的提升还不够,还有赖于整个社会文化的转换,二者缺一不可。
四
吴组缃向我们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巨大的家庭变化,农村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独立、家庭组织形态的变化以及家庭关系的变化都反映了当时的农村家庭已经处于了一个弃旧换新的阶段,城市中新的家庭观念已经开始在农村萌芽,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新式家庭的雏形。但这种形态却是极其不稳定的,特别是当它被经济衰败等诸多社会因素所刺激时,它便显得格外脆弱,广大被迫寻求解放的女性最终还是会在痛苦的生活中尝试到失败的艰辛。相对于“五四”时期娜拉之类的女性,吴组缃笔下的女性向前又迈出了巨大的一步,他们开始获得了经济的独立,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种被迫的独立并不能从根本上让女性获得解放,因而要想真正改变女性的地位必须要依靠社会的变革。“家庭变革决不能摆脱社会变革的大背景而独立进行,家庭变革发生的根本动因是社会构成、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社会观念和社会文化特征的变化。”[21]随着认知的不断深化,吴组缃也觉察到了自己“纯客观”写作的局限性,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创作方向,《子夜》“用一种振起向上的精神和态度”来“宣示着下层阶级的兴起”[22],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于是便有了《一千八百担》中农民暴动的情节,他“以昂扬之情歌颂了被压迫人民的崛起与胜利前途,对压迫阶级及其统治势力的走向崩溃灭亡,则投以痛快的嘲笑”,在作品中他表现出了对社会革命的极大支持,在对进步思想和创作艺术的自觉追求中,吴组缃逐渐由单纯的社会剖析转向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之路。
[1]吴组缃.吴组缃小说散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
[2] 丁帆.论“社会剖析派”的乡土小说[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78-83.
[3]袁红涛.“宗族史”与“社会史”的衔接:论《一千八百担》的叙事意识[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4] 杜显志,薛传芝.论“社会剖析派” [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5(3):101-105.
[5]青士.我国农村破产之状态及其原因 [J].北辰杂志,1932(10).
[6]公度.中国失业概况及救济方法[J].安徽建设,1930(24).
[7]李达.女子解放论[M]//张岱年,等.回读百年: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第一卷).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831.
[8]茅盾.家庭服务与经济独立[M]//茅盾,等.茅盾谈人生.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105.
[9]孙利霞.民国时期家庭关系的变化[J].今日南国(理论创新版),2008(12):206-207.
[10] 晓天.合肥农村妇女[J].女声,1935(16).
[11]陈碧云.农村破产与农村妇女[J].东方杂志,1935(5).
[12]陈文联.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潮[D].湖南师范大学,2002.
[13][15]邓伟志.近代中国家庭的变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05、134.
[14][21]余华林.中国现代家庭文化嬗变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2002.
[16]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下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794.
[17]中国现代文学馆.吴组缃文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32.
[18][20]吴组缃.关于《樊家铺》的时代背景[M]//.苑外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30、131.
[19]张艳.我国农村老年保障制度变迁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2.
[22] 吴组缃.评《子夜》[M]//苑外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94.
[责任编辑:志 洪]
I206.7
A
1674-3652(2017)03-0086-05
2017-02-27
吕洁宇,女,湖北长阳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思想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