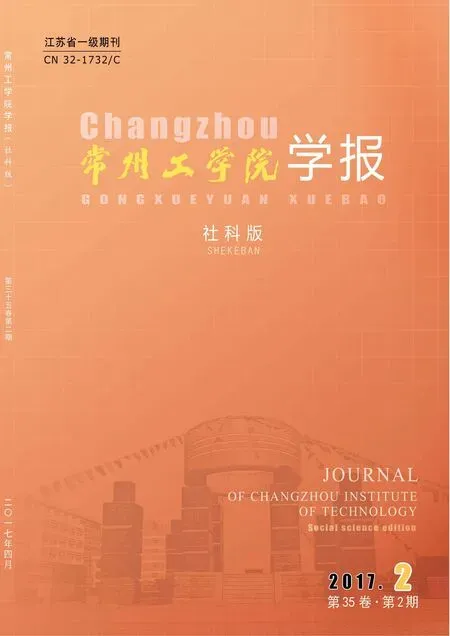现实与想象
——《去中国的小船》中的中国形象
方宏蕾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401331)
现实与想象
——《去中国的小船》中的中国形象
方宏蕾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401331)
村上春树在《去中国的小船》中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浸润着极大的主观情感因素,他站在民族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表现出对中国人鄙夷俯视的同时,又受日本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对异域中国进行了乌托邦式的遐想。
《去中国的小船》;中国形象;西方视野;诗化想象
比较文学形象学是从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理论发展而来的,由卡雷最先提出,经基亚、巴柔、莫哈丰富完善而形成的一套研究理论。比较文学形象学主要以某国某民族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异族形象为研究对象,并以形象背后的文化差异与时代需要为评价标准,寻找和研究隐藏在异国异族形象背后的注视者的自我形象,以及由异国异族形象折射出的注视者的自我民族意识、价值观和生活观等。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形象不只限于人物,还包括器物、景观、观念、词汇等。受生活环境和个人经历影响,村上春树在创作中表现出对中国的极大关注,《且听风吟》《去中国的小船》《寻羊冒险记》《天黑之后》《1Q84》等作品都涉及中国元素。《去中国的小船》是村上春树早期的一部短篇小说,发表于1980年,主要讲述主人公与其所遇到的三个中国人之间的故事。目前,学界有关这部短篇小说的论文大多从象征、隐喻及作者的中国观等方面对中国形象进行分析,而站在比较文学形象学角度,从村上春树个人与中国的关系及其所处日本社会文化角度对文本中的中国形象进行研究的论文不多。
一、 主观视域下的灰暗色调
村上春树早年的生活环境为他了解和描写中国形象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丰富的素材。村上春树早年生活于日本神户,从幼年开始就与中国人有过直接接触,他自称“我生活的周围一直有中国人,中国情结对我而言是很自然的”[1]18。他还坦言《去中国的小船》这篇小说“就是根据小时——在神户的时候——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2]241。可见,作者相关文学创作的第一手材料正来源于他与中国人的直接接触。
但是,村上春树对中国的认识及感情态度则更多地受到父辈经验的影响。他曾经向记者披露,二战前其父亲本是一名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大学生,战争爆发后,还在读书的他却应征入伍被派往中国战场,从此经历了另一番完全不同的人生,这段在中国的参战经历也成为他记忆中永远难以抹去的伤痕。父亲的此种创伤终其一生也无法摆脱,并深深地影响着村上春树对中国的情感甚至他的人生选择,他说:“因为父亲的悲伤也是我心中的垒块。父亲一生没有走出这种伤痛,这也是我始终没有要孩子的原因。”[3]123对于父亲在中国战场具体经历了什么,村上春树并没有明说,我们也不得而知,总之那是一段充满伤痛的经历。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我们也能依稀找到一些类似的伤痛叙述线索,“我共有三个叔父,一个死于上海郊区——战败第三天踩响了自己埋下的地雷”[4]4,这是其另一部自传性作品《且听风吟》中主人公的自述。可见,父辈对中国的伤痛体验已经渗透进村上春树的创作中。我们暂且不讨论村上春树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看法,可以肯定的是,战争在某种程度上的确给其父辈带来了伤痛的记忆,而这些伤痛的发生又与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父辈的这种抑郁情感极大地影响着村上春树对周围中国人的看法,这种情感的延伸,导致“中国之于村上不仅仅是他的国家历史的一部分,他的家族经历的一部分,也是他的人生理解的一部分”[3]124。在小说文本中,则呈现为一组具有灰暗色调的“我”与中国人的故事。
小说回忆了主人公认识的三个中国人:小学时一次模拟考试的监考老师,大学时一起做兼职的女孩,二十八岁时重逢的高中男同学。巧合的是,与他们每一个人相遇时,“我”都正好处于人生中某种灰暗情绪的笼罩下。当“我”还是一个不太独立的小学生时,因为某种差错被指定独自去对“我”来说是天涯海角的中国人小学参加一场模拟考试,“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前往那里,在这种情况下遇见了那位中国老师;与中国女孩相遇时,“我”只身一人在东京求学,并且与女朋友正进行着煎熬的异地恋,距离和时间的空白考验着我们相互理解的程度,在东京“我”几乎没有可以交心的朋友,大学生活相对单调无味,“我”处在一种空虚烦闷的状态中;而与那位中国同学“重逢时我二十八,结婚都六年了。六年里我埋葬了三只猫,也焚烧了几个希望,将几个痛苦用厚毛衣包起来埋进土里”[5]21。这也是在一种人生极为迷茫彷徨的时刻。总之,在“我”的记忆里,中国人总是和某种不愉快的情境联系在一起,“我”与中国人的交往总是笼罩在某种灰暗抑郁的色调之下。
二、西方视野下的鄙夷俯视
通过对文本的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在村上春树的笔下,中国老师是一个谦卑、谨慎、友善、富有说教意味的形象。考试那天,这位老师先进行了自我介绍并仔细讲解了考试规则,然后给大家讲了很多中日两个邻居应友好相处的道理,并要求我们不要在教室桌椅上乱涂乱画,要互相尊重等,俨然一个循循善诱的教导者姿态。中国女孩则是一个具有紧迫感、沉默寡言、神经质、自卑、胆怯、受管束的弱者形象。女孩干起活来非常积极,认真,卖力。她容易因为一点点小差错就惊慌失措,不停自责,并演变成巨大的精神危机。可见,这个中国女孩极度缺乏安全感。在与中国女孩的进一步交流中,“我”了解到她的家庭并不是很幸福,且家教管束严格。这种家庭背景使女孩并没有远大的抱负和高层次生活追求,她只希望将来能生活得安稳。因此,她的职业目标只是当一个翻译。而“我”的那位高中同学则是一个圆滑精明、做作不自然的、被生活磨损的、疲于奔命的中国人形象。他年龄与“我”相仿,虽然看似“一副精明能干的派头”[5]21,但从衣着、五官、面部表情各个方面都给人“磨损”的感觉。他干着向同胞推销百科事典的行当,下一步也许改成向中国人卖平安保险或者墓地。从这里可以领会作者的言外之意,即在“我”的眼里,这位曾经学习成绩不错又不缺女孩追的优等生同学,现在好像混得并不怎么样,甚至比“我”还差一些。
总之,村上春树通过第一人称视角所观察和表述的这三个中国人形象都是正面的,但又是处于弱势的。这种形象塑造与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及村上春树所受的西方文化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19世纪中叶,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日本打破闭关锁国的局面,受西方现代化科技文明的刺激和影响,日本人认识到古老东亚文化的落后状态,因此他们致力于学习西方,“脱亚入欧”。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从此更是自恃其经济强势和文明程度,急欲割断与东亚的联系,而将自身完全看作是西方的一部分,甚至“以亚洲的先知自居,用西方人看待东方的眼光来看待亚洲其他国家”[6]43。他们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为了彰显自我优势、抬高自身价值,以俯视的眼光将中国人与贫穷、懦弱、狡猾、失业、犯罪等负面因素联系在一起,极大地歪曲中国形象,将其置于一种被异化的“他者”地位。另外,村上春树所受的教育也是偏西式的,他从小就热衷于阅读外国文学,尤其“喜欢读英美原版小说”[7]373,并且深受美国影响,“作品中人物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全面美国化”[6]196。因此,村上春树并没有超越民族主义甚至站在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上,他塑造的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形象,即按照日本社会的模式和话语来建构中国人形象。在对中国人的弱势形象进行塑造的同时,以达到强化自我,彰显其日本民族优越感的目的。
这也可以进一步解释文本中的“我”为什么总是在人生中比较黯淡的时刻遇见中国人。一方面,这里暗含着自我与他者的一种不平等的对话关系。也就是说“我”只有在一个特定的处于弱势状态的前提下,才开始与中国人进行对话和互动。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弱势形象是对“我”的糟糕际遇的一种陪衬,在这种对比中“我”找到了自我存在的优越感和自信心。
三、基于日本文化传统的诗化想象
与对中国人形象意识形态化的刻板描述相反,“我”对中国文化风物的想象则是乌托邦式的。也就是说村上春树对中国这个异国形象的塑造偏离了当时日本社会的主流话语,他采用了一种不同于主流意识的、合乎自我理想和想象的话语对“中国”这个他者形象进行塑造,从而超越了当时日本社会对中国的集体想象,表现了其对本国社会现实的不满。这种对异邦中国和现实中国人的截然不同的形象塑造,呈现出巨大的反差和矛盾。
通过“我”对所遇到的几个中国人的叙述可以看出,在“我”的注视和观察下,这些中国人的处境并不是很乐观,他们属于社会弱势群体,生存的压力迫使他们谨小慎微,谦卑顺从,他们都是弱者,是被同情的对象,但是“我”为什么还会憧憬中国,还会期待那开往中国的小船?“我”为什么对中国展开了“灿烂生辉的屋顶”“绿接天际的草原”的乌托邦式想象?为什么“我读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书,从《史记》到《西行漫记》。我想更多一些了解中国”[5]29?
这种愿望和憧憬与日本的社会文化传统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在明治维新(1868—1873)之前,中国文化是日本人极力推崇和学习的典范,大量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在日本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日本文字中存在的大量汉字,以及日本文学中的汉诗,公元七、八世纪日本模仿中国唐朝都城长安建造奈良等,都足以说明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很深。因此,在传统日本人尤其是日本文人的心目中,中国曾经是他们崇拜和向往的理想国度。由东方传统文化所建构的异域中国,是传统日本文人共同享有的文化乌托邦。
而从明治时代开始,极力效仿西欧近代文明的日本逐渐建构起其大帝国的形象和地位,帝国文化的控制力也随之上升。日本制定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扩张政策,随后通过甲午战争正式侵入中国大陆。清朝统治末期,落后腐朽的中国暴露在日本文人面前,他们心目中理想、光辉的古典中国形象在灰暗残败的现实图景面前顷刻间土崩瓦解。因而他们“由对汉语经典文本中的古代中国的仰视转为对现实中近代中国的审视”[6]16。
到了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造成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的脱节,甚至导致“人的异化和主体的丧失”,日本文人普遍感觉精神和心灵家园的丢失。而这些日本知识分子大多自幼就受到中国古典诗文的熏陶,儒道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已深入骨髓。因此,面对现代社会快速消费文化的冲击,他们掀起了一股怀旧思潮,对中国表现出强烈的“异国趣味”,此时他们遥想中的异域中国,实际上正是日本文人心灵乌托邦的象征,他们也欲借此古老而熟悉的东方传统文化来对抗陌生汹涌的西方文化。东方与西方的冲撞,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使“日本作家看待中国的视角在文本与现实之间逡巡,游移于俯仰之间”[6]37,而这种表述中国的模式延续下来并影响到其后的作家。
村上春树出生于战后,中日两国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没有理由对其产生必然的影响。但是作为现代日本作家群体里的一员,村上春树并没有摆脱日本社会集体意识的桎梏,他对中国的观点和看法依旧是日本本土社会文化的产物。因此,村上春树对现实中中国人的俯视与对遥远中国的诗化想象,正是传统日本文人从“对古代中国的顶礼膜拜,到对近现代中国的蔑视欺辱,再到对当代中国的矛盾心态”[3]119的总体特征之体现。
四、结语
村上春树在《去中国的小船》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及故事情节的设置都包含着其个人主观情感因素。他从现实中对中国人的主观认识出发,尤其是在其父辈精神创伤的影响下,将整部作品置于一种灰暗阴郁的基调之下。村上春树所受的西式教育,使其对西方文化及思维模式推崇至极,加上日本近代以来“脱亚入欧”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西方中心主义和日本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深深的印记。为了抬高自我,彰显日本民族优越性,他塑造了一系列弱势的中国人形象,并对其进行了意识形态化的刻板描述。但是,村上春树身上又保留了部分日本传统文人共有的东方古典汉民族文化熏陶,在对现实中的中国人进行俯视鄙夷的同时,又产生了对异域中国文化风物的诗化般遐想。
[1]杨炳菁.后现代语境中的村上春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2]林少华.为了灵魂的自由:村上春树的文学世界[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
[3]尚一鸥.村上春树小说艺术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4]村上春树.且听风吟[M].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5]村上春树.去中国的小船[M]. 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6]李雁南.在文本与现实之间:近现代日本作家笔下的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7]杨国华.日本当代文学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责任编辑:赵 青
10.3969/j.issn.1673-0887.2017.02.010
2016-08-17
方宏蕾(1987— ),女,硕士研究生。
I106.4
A
1673-0887(2017)02-004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