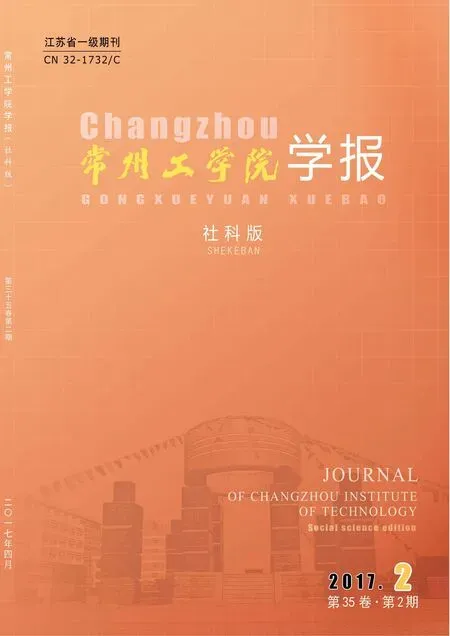欲望征逐的悲剧人生
——解读“潘金莲书写”的一种角度
李曙冬
(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苏盐城224002)
欲望征逐的悲剧人生
——解读“潘金莲书写”的一种角度
李曙冬
(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苏盐城224002)
李碧华常因女性身份而被当作女权主义者解读,然而她所要解构的恐怕不只是男性中心话语。她的戏仿小说对经典文学形象(如潘金莲)、历史事件(帝王将相)或传统文化(京剧表演)重新书写的意图令人玩味。多元文化语境为文学评论提供了更多剖析角度,也给了读者更多阅读体验。文章试将研究注意力转向整体文本体验,从宗教、心理学等层面,探讨作者赋予人物形象更多欲望元素的意义,重新构想文本创作对传统文化的多重表达。
李碧华;多元文化;欲望;叙述;世情关怀
一、“欲望”的意义
现代心理学普遍认为人的所有行为从动机发起,动机出于需要或需求,一般分为生理需要、社会性需要或物质需要、精神文化需要,又有食欲(自己保存欲)、性欲(保存种族欲)、游戏欲(自由欲)三欲的区分。佛学对人的需要、需求、动机意义上的欲,大致分为三欲、四食、五欲诸说,“三欲,谓饮食欲、睡眠欲、情欲,属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四食,谓四种食物。指养育和维持生命所需的食物。五欲,指对财、色、饮食、名、睡眠的需要和欲望。六食,谓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各有其欲望或所需。包括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和爱的需要等。十一欲,为性欲的种种表现”①。由此可见,虽然人类的欲望需求是多方面的,但是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生存的欲望;二是匮乏性的生理需求(物质生活的追求);三是感官和内心快乐的情绪需求(情感世界的满足);四是被尊重、被爱的社会性感情需求(个人的社会价值的实现)。
无论是从现代心理学分析,还是从传统佛教分析,“欲”都代表了精神生活的动能,是人生的一切希望、意义和价值所在。但是,一切苦难和罪恶也因“欲”而生。本文探讨的主要是性属不善的贪欲和属善的善法欲。贪欲,意指对世间的食、色、睡、声及钱财、名位等的执着迷恋和非份追逐。贪求这些东西的欲望,佛学称为“人欲”,或曰“人性”。世情包裹的贪欲无非“情欲”“爱欲(占有欲)”“物欲(权欲)”的追寻,而一切有关“人性”的行为似乎需要给予更多的探询和关怀。这一点在李碧华的文本创作中颇为突出,最具代表性的莫如对潘金莲女性形象的重新书写和对历史事件的另类想象。
二、欲奴潘金莲
人的原罪和情欲密不可分,情欲不能获得满足,人类会感到极其痛苦。一旦情欲获得满足,人类会产生巨大的快乐。因此,人只要活着总是要追求自身情欲的满足。正因为情欲使人快乐无比,又使人痛苦不堪,既能使人获得幸福又能使人陷入罪恶,它才能对人的生活构成巨大的诱惑,同时又产生强大的威胁。所以,人们对潘金莲的企慕和诅咒的本质就在于对自身情欲的矛盾态度——迷恋又害怕。
施耐庵先生在潘金莲身上集中了情欲、乱伦、通奸、谋杀等诸多激烈元素,光华灼灼,自动吸粉。这样一个沉湎肉欲的女人在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中有着更为精彩的演出。《金瓶梅》从封建伦理道德角度对人物行为进行否定,从人性本能驱使出发对人物行为给予同情。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虽然客观上赋予了潘金莲更多层次的审美内涵,但是也更加让人省思:为什么中国人在“欲”的话题上会如此扭曲、如此变态、如此压抑?文学史上的“潘金莲”总是由男性来塑造,不论是从“万恶淫为首”的道德信条出发否定她,还是从祸害男人的角度丑化她,不论是从反抗束缚人性的封建伦理道德立场肯定她,还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同情她,总而言之,这些男性作家似乎都在潜意识中集体回避了造成潘金莲悲剧的最自然原因,人的本能欲望与社会伦理道德的激烈冲突——情欲的征逐。
在《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李碧华立意写一个市井美女的故事,一个大户人家长得风流标致、力求自保的妾,并非天生就是“勾搭汉子”“鸩杀亲夫”的恶人,只不过是阴差阳错地嫁于性无能的武大郎,亢扬的情欲无法满足,她才循着人的本能走到“谋杀亲夫”的一步。在李碧华创造的前世今生里,大家都在关心“九转轮回”的潘金莲去了哪里?她将演出什么样的“今生今世”?今生的潘金莲是孤儿,出生在大陆,有了新的名字单玉莲,有了新的身份——芭蕾舞演员,亭亭玉立,貌美鲜妍。她又逢着了形形色色的男人,这些男人仿若前生的记忆符号,逼迫着(或可曰引导着)今生的单玉莲走上了冥冥之中安排好的路。“潘金莲”像是被诅咒过的不祥人,得不到幸福,更得不到她渴慕的男人。有论者认为这就是人类无法抗拒的“命运”。如果说宋代的潘金莲或有可怜之处,那么现代的单玉莲则是自导自演了一切,悲情苦果也必须由自己承担。无论是宋代的潘金莲还是今生的单玉莲,她们的目的都一样,都是为了追求情欲的满足。异度空间里,两个女人都知道自己要什么,“要”的感觉是强烈炙热的。所不同的是,宋代的潘金莲囿于封建礼法不是自由身,而今生的单玉莲是自由身,能够为自己的婚嫁做主,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男人,但是她出卖了自己。单玉莲的贪婪物欲促成了自己无爱的婚姻,嫁给了自己不爱的香港商人武汝大,武汝大给单玉莲提供了她想要的一切物质生活,对她百般呵护与宠爱,唯独难以满足她亢扬的情欲。单玉莲欲望的眼睛无视丈夫对她全心全意的爱,欲壑难填的她最终走向了纵情声色的不归路。茨威格说过,当一切欲望满足之后便是对爱情的考验。对于单玉莲来讲,这种考验是致命的。起初,单玉莲为了报答武汝大救她出苦海,也曾决心收敛艳光好好对待这个有趣的矮男人,可是日子久了便会不满足,便会有更多的诉求。单玉莲出卖爱情婚姻换取的优渥生活并不能笼络她很久,她开始嫌丈夫蠢,开始觉得委屈,“他对她太好了,千依百顺,生活因而平平无奇”。“为什么同在一爿店里,自己的男人,蠢相得像个肚满肠肥的相扑手?”②单玉莲流连夜店,艳羡着都市男女的堕落夜生活,开始感叹寂寞,艳羡他人情浓,及至遇到放荡不羁的设计师Simon,爱(武龙)而不得的单玉莲在强大情欲的驱使下和Simon缠绵在一起。在Simon充斥情欲的幽暗寓所,在元朗百年传承的古朴书房,他们无所顾忌地享受身体的快乐。背德的欢愉益发增添情欲游戏的危险和刺激,耽溺情欲的单玉莲为此粉身碎骨在所不惜,彻底堕入了情欲征逐的深渊。旧社会纵有千般不是,害了潘金莲的性命,香港的花花世界一样吞噬人命。情欲的大门一旦敞开,堕入其中的男女就身不由己,一再重演自己的角色。在貌似时光错置的前世今生里,一对无媒男女的疯狂苟合似乎有了足够浪漫的理由,或者说,因着“前世”的“淫”的铺垫,使得今生“奸夫淫妇”的剧情不需浓墨重彩就可以一丝不挂地上演。李碧华这一点点“前世今生”的遮羞布实在是遮不住当下社会都市男女情感生活的苍白和身体游戏的荒唐。“她是欲的奴。他是治奴的药。她肯为他做任何不堪的事。此一刻,她只盼望天长地久。”③在李碧华看来,女人可以勇敢表达自己的爱,追求自己的爱。但如何获得这些“欲”的满足则是故事如何往下演的关键。现代人为生计奔波劳碌,爱情变成脆弱的奢侈品,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李碧华那么迷恋于深藏旧文本记忆中的事和物,不仅投射了她对现世爱情和文明进程的失望,也传达了现代人自身的无奈,以及以放弃追寻“永恒”来抗衡现实无奈的决绝。李碧华不动声色地将人物放在多角恋爱关系中奋力搏杀,写人物追寻在前世今生的爱恨纠缠,写人物久被压抑的情欲爆发时的惊涛骇浪,用讽刺嘲弄的口吻书写人性的自私猥琐、阴暗毒辣,不无残忍地裸露出纯真恋情破碎后不值一文的真相,唯有情欲的彻底宣泄才是真实的、热辣的。李碧华形容现代社会中许多美丽聪明、有心机的女人都是潘金莲的心态:要一个体贴多金的武大郎丈夫;要一个英俊潇洒懂得情趣的西门庆情人;再要一个打虎英雄做贴身保镖。由此看来,《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不但是探讨女性情欲交汇与矛盾的作品,也揭示了女人对理想男人近乎乌托邦的诉求。李碧华对女性情欲的抒写朴素深刻又幽微动人,而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的卫道士们的反性和道德优越感在自然的人性面前土崩瓦解。
三、权欲操纵的微渺生命
欲望人生不外乎权欲、物欲和情欲的征服满足。《诱僧》可被视为一部有关情欲与政治的寓言,也可以说是一部摇曳多姿、香艳刺激的唐朝野史。藤井省三认为《诱僧》“书写的是权力、恋爱、出家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圣与俗两种个人意识相克的故事”④。历史总是惊人相似,也许人生也是千篇一律地惊人相似,《诱僧》或可说讲述了一则权欲争夺践踏无辜人生的故事。大将军石彦生智勇双全、英姿飒爽,被秦王李世民和十九公主红萼同时看中。李世民的部将霍达游说石彦生参与兵变。石彦生忠于太子却又爱惜苍生,为了减少生灵涂炭,答应帮助霍达,但其结果却是促成了一场兄弟相残的血腥屠杀,自己也落下了不忠不义的罪名,成为李世民通缉的朝廷要犯。在强权的逼迫下,石彦生的母亲为了成全儿子的名节自刎于霍达的剑下;公主红萼美艳动人、泼辣任性,却也甘愿放弃荣华,倾心追随。石彦生从最初的抗拒红萼到最后接受红萼缔结鸳盟,经历了巨大的人生变化——从正统的武将生涯走到了家破人亡。等他想通一切打开心结,却又失去了红萼,人生顿时又陷入一无所有。石彦生内心一场人神交战最终却弄得落花流水。在皇权的压迫下,在名利的诱惑下,在情欲的纠缠下,石彦生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官位和美人(面貌酷似红萼公主的青绶夫人),遁入空门。在失控的大环境中,石彦生丧失了可依傍的理想,一切行为也都没有了支撑,甚至完全放弃了个人选择和反思能力。文本将历史的荒谬性和小人物的悲哀刻画得淋漓尽致。李小良指出《诱僧》“延续了李碧华一贯对中国大陆极权的批评……是她重复‘历史都不是真相’的意念”⑤。借皇帝集权指涉中央集权,未尝不可,但笔者认为《诱僧》更加强调了历史空间下“人”的卑微渺小,“历史都不是真相。一场场权力斗争的游戏,欲避无从。世情在变,他们的命运也随之而变,怎会有‘自己’?只觉得失是非一场空”⑥。石彦生和随属本是避身佛门的戴罪之人,为解口腹之欲下山玩乐,却惹祸上身。石彦生不但被同袍出卖,还在这次厮杀中失去了心爱的女人,万念俱灰。身为佛门子弟,轻易心动,随意破戒,扰乱清规,就无法避免地要承受“心动”带来的苦难,这是对亵渎信仰的责罚。石彦生在失去一切后才领悟,“人那么壮大,权位、生死、爱恨、名利……却动摇它。权位、生死、爱恨、名利……那么壮大,时间却消磨它。——时间最壮大吗?不,是‘心’。当心空无一物,它便无边无涯”⑦。石彦生痛彻心扉地悟到了世情之变。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一种需求得到满足,又会产生新的需求,可是这种变异不定的欲求,必然不会得到充分的满足,必定会使自身永远陷于需求难以实现的痛苦之中。人都希望美好生活能够保持恒常不变,但是保持恒常不变的愿望与变化不居的现实之间就有矛盾,矛盾得不到解决就如同深陷绝境中。佛教所说“诸法无我”,也就是石彦生所想到的“他们的命运随之而变,怎会有自己?”。最后,他对“心”的摒弃则达到了佛教“涅槃寂静”的境界。“涅槃寂静”是佛教的最终理想,也是《诱僧》的最终理想。石彦生以权力欲望为入口,悟到了人生欲望的无穷和由此产生的痛苦,于是自动放弃一切欲望追求。石彦生悟出人的欲望乃是人生痛苦的根源,只有放弃心中的欲念才能真正达到解脱的境地。
如果说《诱僧》中的石彦生是因为坚持真相而陷于权力、爱情与出家的矛盾中,《秦俑》中的蒙天放则是因为忠诚于秦始皇而两次失去了情人冬儿。蒙天放回首前尘、感怀今生“不断地有战争,内忧外患,不断地有运动,波谲云诡。一切的权力斗争,都是血腥而惨烈的”⑧。李碧华在此充分抒发自己对权力争斗的政治暗指。神秘的欲望在后台指导人物亦步亦趋地表演,而人性悲剧与社会悲剧在前台轰轰烈烈地上演。《生死桥》里,唐怀玉对功名充满渴望之情,汹涌澎湃。“怀玉”亦暗指了他的欲望之心“怀欲”。他在北京弃学从艺,立志在上海踏出天下,不但赔尽自尊还失去了双眼。丹丹追随怀玉来到上海,发现心上人另有所爱不惜自毁报复,然而她费尽心机还是惨遭失败。不管是怀玉,还是丹丹,他们身上都透出一股飞蛾扑火的狠劲,这种令人生畏的生命力是悲剧精神的显现,也是无休止的欲望征逐(对爱的占有欲)。《川岛芳子》中,如果说权欲是芳子不幸人生的始作俑者,那么,她对权欲无法克制的渴望就是幕后掌控者。《霸王别姬》中,李碧华将政治、爱情、性别杂糅在一起,将传统的感情放在现代的处境中考证。因着荒谬的时代(“文革”)更能表现荒谬的人性,要么同流合污,要么玉石俱焚,此外别无选择。所以,在这种环境的逼迫下,人性中最为隐蔽的“恶”才会一点点地被压榨出来,人类精神的两面性才会逐渐显露。“文革”的“互相揭发和批斗”逼迫每个人都必须通过对别人的斗争来表明自己的清白,并以此获得一个可以自我保全的政治身份,这种精神上的煎熬折磨比肉体上的摧残更让人感到绝望。由此也将程蝶衣、段小楼和菊仙三人的“人性”和“人欲”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三个人近乎疯狂的互相揭发中,我们看到人类的理性与智慧消失了,人还原为最初的自私残忍的动物。面对死亡的考验,生存的欲望压倒一切。在这里最让人心酸落泪的是,在正典中顺理成章的一切,在现实中却变成随时都会被粗暴打断的一盘棋。看着由真正的女性来替代程蝶衣表演虞姬,那是一种不需要苦苦挣扎就可以开始的自然表演,那是程蝶衣历经血泪挣扎才成就的艺术表演,却在历史前进的车轮中被无情地碾压和否定。程蝶衣半生的付出和牺牲瞬间变得一文不值、毫无意义。面对这样血肉模糊的人生悲剧,程蝶衣的精神世界轰然倒塌,他只有放弃毕生的求索向现实妥协,回到男性的世界苟活。程蝶衣的一生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湮灭在历史洪流中,面对历史时空的愚弄,程蝶衣如何活得下去?李碧华以现实的丑陋和卑贱来反衬名伶们在舞台上的华美和高贵,真是极大嘲讽。
李碧华的视野跳出了两性间的较量,投入了人性对抗和历史对抗的广阔背景中。在她的笔下,“历史”与“人性”形成一种镜像关系,互为参照,而“人性”和“欲望”也成了李碧华极力描写的关键词。欲望、人性和历史构成了李碧华小说的三个写作维度,我们始体悟,每个活生生的人都会有各种层次的需要,而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反抗压抑的本能,“人的意志、个人的意志永远不可能实现自己完全的、绝对的自由和解放。但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在这种反抗中实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⑨。李碧华以当下的欲望人生串演经典文本,以古人之心对照现实人心,表达了她对混乱人生湮灭在欲望世界的极度失望。小说文本不单嘲弄爱情的腐烂溃败,更是借“爱情”在人世间的起承转合,展览了被欲望驱逐推动的无涯慌乱的人生。李碧华的作品常常因为她的女性身份而被当作女权主义文本解读,然而作者所要解构的恐怕不只是所谓的男性中心话语,而是对猥琐人性的深层解剖,对淡漠人生的微凉嘲讽,对堂皇历史的彻底颠覆和对政治大话的极度质疑。欲望的世界里,积淀千万年的人类文明无声无息地崩毁在强权争夺中,文明记忆毫无怜惜地被践踏、被掠夺,卑微湮灭。始惊觉,“人”的被牺牲、被放弃、被欺骗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欲望的世界很残酷,世俗的情怀却还一厢情愿地保留着一份可笑的诗意追求。李碧华极力避免正面描写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在穿越时空的变换中写出了欲望世界里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人性的淡漠。宗教偶像破灭了,政治偶像也破灭了,但无论是经典神话、英雄神话的瓦解,还是宗教偶像、政治偶像的倒塌,这一切都不如人类文明的崩溃能产生这么大的震动和破坏,带来这么大的伤害和反思。在面对人生的断壁残垣后,我们不得不恐慌于人类文明在欲望世界里的堕落和消失。
注释:
①陈兵:《佛教的人生欲望观》,《兰州学刊》,2007年第3期,第1-5页。
②③李碧华:《潘金莲之前世今生》,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102-103页,第123页。
④藤井省三:《李碧华小说中的个人意识问题》,陈国球:《文学香港与李碧华》,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年,第107页。
⑤王宏志、李小良、陈清侨:《否想香港》,台北:麦田出版社,1997年,第222页。
⑥⑦李碧华:《诱僧》,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221-225页,第270页。
⑧李碧华:《秦俑》,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133页。
⑨王富仁:《中国文学的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353页。
责任编辑:庄亚华
10.3969/j.issn.1673-0887.2017.02.005
2017-02-22
李曙冬,女,讲师。
盐城师范学院校级课题(61141061080)
I206
A
1673-0887(2017)02-0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