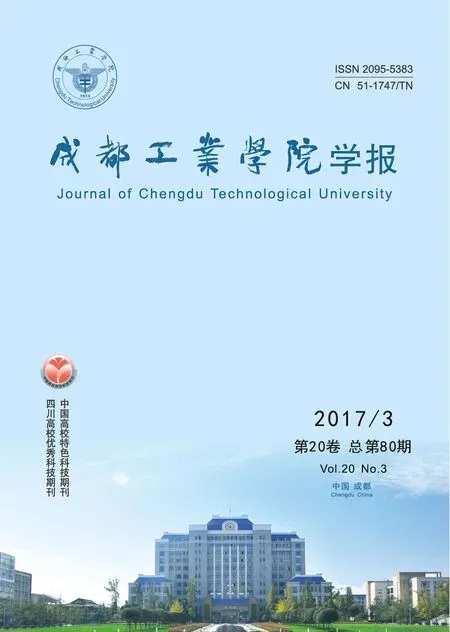劳伦斯在《菊花的清香》中的创伤书写
丁华良
(内江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四川 内江 641112)
劳伦斯在《菊花的清香》中的创伤书写
丁华良
(内江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四川 内江 641112)
创伤是劳伦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在短篇小说《菊花的清香》中,劳伦斯运用固定式内聚焦、记忆闪回与重复、延宕等叙事技术,书写了在工业主义蹂躏下的生态创伤和家庭创伤,记录了女主人公伊丽莎白面对创伤和接受创伤的艰难过程,表达出现代人治愈创伤和超越创伤的可能与希望。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创伤代表的是现代人的集体创伤无意识,生态和家庭创伤是二十世纪社会创伤的一个缩影。
《菊花的清香》;创伤书写;叙事技术
“创伤”源自希腊语,指“伤口”,特别指“刺破或撕裂的皮肤的皮肤。”[1]20《现代汉语词典》将“创伤”释义为“身体受伤的地方;比喻物质或精神遭受的破坏或伤害。”[2]196所以“创伤”既指在身体方面有形的伤或伤痕,又指在心理、精神方面无形的伤或伤痛。对创伤学的大规模研究主要开始于弗洛伊德,并以两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作为催化剂而发展。弗洛伊德、荣格、朱迪思·赫尔曼以及中国学者施琪嘉等的创伤研究成果对医学领域的创伤研究和创伤复原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学意义上的“创伤”是以医学意义上的创伤研究成果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如李桂容所言:“对于文学性创伤来说,医学性创伤是元创伤,是文学性创伤的原型和根基。对医学性创伤来说,文学性创伤是医学性创伤的文学表现,是医学性创伤的生动变形和扩展。”[1]17同时,弗洛伊德、拉康、柯里奇立等从历史、哲学、心理学等角度对创伤的研究则给文学性创伤研究带来了巨大影响。所以,文学作品中的文学性创伤是在医学、心理学创伤基础上的自由变体和艺术变化。创伤研究也就成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视角和研究方法,它有助于读者从纵深层次理解作品的艺术内涵。
作者劳伦斯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矿工家庭,非常熟悉底层劳动者的生存遭遇,切身体会到工业发展和机器文明对自然环境和人们精神的侵蚀与毒害。矿工们日夜劳累,风险极高,然而收入微博,生活贫困。他们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矿区糟糕的生存环境给年幼的劳伦斯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畸形的家庭关系、痛苦的婚恋经历、常年的海外漂泊让他感受到人生的痛苦与不幸。再加上他常年体弱多病,还得时时刻刻与“人类最大的创伤源”——死亡作斗争。所以,创伤成为劳伦斯一生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他将自己体验到的人生磨难、对人生的深刻领悟生动而敏锐地化作创伤性的文学表达。应该说,他的每一个作品既是他人生经历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书写创伤、见证创伤的有效手段,更是他战胜创伤、治愈创伤的必然途径。
短篇小说《菊花的清香》取材于劳伦斯婶母的真实遭遇,生动叙述了一个普通的矿工家庭的悲剧故事。作品以等待为线索,记录了矿工妻子待夫归来的心路历程,由起先的猜测埋怨,到后来的焦虑担忧;由惊悉丈夫遇难噩耗时的哀伤焦虑,到面对丈夫遗体时的恐惧无助,最后猛然发现自己必须独自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勇敢地面对未来的生活。《菊花的清香》是劳伦斯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学术界已经从生态解读、心理分析、象征意义、女性批评、原型批评、主题思想、叙事艺术等方面对该作品做了深刻的阐释,而鲜有从创伤视角对该作品的解读。由此,笔者认为,对《菊花的清香》进行创伤研究可以深化我们对作品主题的理解,也为我们解读劳伦斯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
1 生态创伤:工业化的缩影
劳伦斯所处的时代正值英国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人们对工业革命充满了乐观情绪,对战胜自然充满了坚定信心。工业发展对能源的需求量巨增,所以英国的煤矿开采业得到迅猛发展,乡村变成矿区,农民沦为矿工。煤矿开采破坏了生态平衡,加剧了生态恶化。条件恶劣、污染严重、矿难频繁,这些都是煤矿工业快速发展导致的恶果。见证了家乡遭受到的生态创伤,敏锐地感受到工业文明对大自然的破坏作用,劳伦斯曾经这样愤慨道:“我认为英格兰真正的悲剧是丑陋所形成的悲剧。乡间多么美啊,人造的英格兰却丑得出奇。”[3]172在《菊花的清香》的开头段落,作者采用照相式的全知视角,为读者生动展示了机械文明与大自然之间的冲突,客观记录了由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恶化、生态创伤。昔日的绿水青山如今变成了毫无生气的矿区,矿坑坑口随处可见,烟囱高高耸立,树叶枯萎落下,火车头喷出的浓烟笼罩在杂草、葡萄藤和菊花上,原本休闲自在的马、鸟、鸡群等被满载货物的机车轰鸣声惊吓得四处逃窜。通过对这些集中在矿区意象的并置,读者看到的是一副被工业化严重破坏的自然画面,感受到的是因过度开采所引起的生态创伤,强化的是工业化与大自然之间的尖锐对立。
2 家庭创伤:夫妻关系的物化
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最早提出了“物化”概念。他认为,“物化”是商品结构的本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了物性的特征和以此方式获得了一种‘魔影般的对象化’,而恰恰是这种对象化以严格的、似乎完全封闭的和现实的固有规律性掩盖着自己的基本本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4]78作为人类伦理关系中最亲密无间的夫妻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被高度物化。在《菊花的清香》中,妻子伊丽莎白只是将自己的婚姻和对丈夫的感情“魔影般的对象化”为面包和先令,把丈夫视作为家里的经济来源,而非爱的对象。像其他矿工家庭一样,沃尔特家里异常贫穷,屋里黑暗、潮湿、狭窄。在矿井的工作艰辛、条件恶劣、风险极高,但即便如此,沃尔特依然不能获得妻子的同情和理解。相反,“态度傲慢”且“容貌漂亮”的妻子十分厌恶每天回家满身煤灰和泥巴的丈夫,她只是将丈夫看作为家里生活来源和物质增加的工具而已。夫妻之间缺乏对彼此的了解和情感上的沟通,导致隔阂越来越深,离得越来越远,最终成为“两个孤立的人”。[5]20当老太太来告诉伊丽莎白沃尔特遭遇矿难噩耗时,她的第一本能反应竟然是“他死了吗?”当老太太正沉浸在悲痛之中时,作为妻子的伊丽莎白“却在忙着想别的事。如果他丧了命,她能靠微博的抚恤金和她自己挣的一点点钱维持生计吗?她飞快地计算了一下。”妻子的内心是极具矛盾的。丈夫的死亡会断了家庭的经济来源,但是与其是丈夫受伤,还不如是丈夫死去。因为如果他只是受伤,“看护他会是十分麻烦的。”[5]13所以当后来确定丈夫死了之后,“这倒使伊丽莎白放了心。”[5]15丈夫的死至少省去了看护的麻烦和他继续把钱财糟蹋在喝酒上的可能了。在丈夫尸体被抬回来之前,伊丽莎白做了一些准备,她“拿来那块红色的旧桌布和另外一块旧布,把它们铺在地上,这样就省得用她那块地毯了。”[5]15-16为了节约,妻子连一块地毯都舍不得为已经死去的丈夫铺在冰冷的地上。夫妻关系如此冷漠,死去的丈夫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还没有一块地毯有价值。在擦洗丈夫遗体时,伊丽莎白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夫妻之间的隔阂,她“想和他取得某种联系。然而她无法做到。她被赶出来了。与他是无法沟通的。”[5]19身前如此,死后也是如此。本来应该是亲密无暇的夫妻之间却没有了任何心灵和情感上的交流,他们“在生活中曾经互相拒绝接受对方。”[5]21究其根由,这样的家庭状态主要是源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夫妻关系的物化,他们把对方仅仅看作为一个生存对象,而非情感对象。
3 心理创伤:创伤症候及复原
美国著名精神病学教授赫尔曼在《创伤与康复》一书中这样说道:“心理创伤的痛苦源于无力感。在受创当时,受创者笼罩在无法抵抗的力量下而感到无助。创伤事件摧毁了人们得以正常生活的安全感,世间的人和事不再可以掌控,也失去关联性与合理性。”[6]29根据这一观点,创伤事件会造成人们对一些基本人际关系的否定和怀疑,会粉碎借由此建立和维系与他人关系所架构起来的自我。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灾难,天灾、人祸、意外等都可能成为创伤源,而死亡是人类最大的创伤源。在《菊花的清香》中,妻子伊丽莎白所经历的创伤是多维和复杂的,既有由于家庭贫穷而产生的焦虑、因丈夫挥霍钱财、酗酒成性的埋怨,也有与周边环境以及自己丈夫疏远的孤独,更有对丈夫死亡的恐惧、对未来生活的迷惘与无助。
3.1 心理创伤症候
3.1.1 焦虑
下班时间丈夫沃尔特并没有按时回家,妻子心生埋怨,认为丈夫肯定是像往常一样,溜到酒店喝酒去了。妻子在家里焦急等待丈夫的回家,“房间里显得特别空空荡荡,充满了等待的紧张气氛……这时,她的怒气里又夹杂着几分担忧。”酗酒对于一个经济本来就十分困难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种挥霍,所以,妻子对丈夫的这种浪费钱财的行为的焦急和愤怒便是情理之中的反应。丈夫迟迟不归,妻子开始焦虑起来,只好外出寻找。在去酒店路上时,她凭女人的直觉感到情况不妙,但是她还是勉强安慰自己“她多傻啊,竟会以为他出了什么事!”[5]9通过与矿工里格利谈话以后,她就“已经肯定发生了灾难”,但是当听到提升机下矿井去寻找丈夫的声音时,她依然在坚持自欺欺人地认为“这只不过是九点钟值班的安全检查员下矿井去了。”[5]12在丈夫的尸体被工友抬回来之前,她在家里“紧张不安地等待着。”[5]14由此可见,焦虑、烦躁不安始终贯穿于妻子伊丽莎白的内心活动当中,让她时时刻刻感受不到任何的平静与安全。
3.1.2 恐惧与无助
虽然伊丽莎白只是将丈夫“魔影般的对象化”为家里的经济来源,但她还是不敢立刻接受丈夫死亡的事实。当沃尔特的母亲来告诉她噩耗的时候,她的本能反应是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未来生活的无助。所以,明明知道丈夫已经死了,她还是在问句中用“伤”这个字来回避“死”,“他——他伤得很重吗?”[5]14当工友来家里亲口告诉她沃尔特已经死亡的消息时,她“吓得直往后退缩。”[5]15面对丈夫的尸体,她“感到畏惧,心里怀着深不可测的恐惧。”在为丈夫擦拭身体的过程中,伊丽莎白“无力地倒在地上……她被巨大的恐怖和疲乏支配着:她是多么力不从心啊。”丈夫死了,未来的生活咋办?此时此刻,她甚至感到“腹中的婴儿也成了一个跟她莫不相干的重担。”这个恐惧既来自于对未来经济上的担忧,更让她感觉到“人类的灵魂是多么的孤独。”[5]19丈夫的死亡最终让他们夫妻之间彻底分离开来,导致他们之间“隔得那么远,使她恐惧得几乎支持不住了—那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空间。”[5]22让她感受到的是“生活掩盖下的、绝对的、完全的孤独。”[5]20
3.2 创伤复原
根据赫尔曼的观点,心理创伤的核心体验是“自主权的丧失和与他人感情联系的中断。”[6]124所以,治愈创伤的目标就是恢复患者的自主权和建立新联系。而要实现这个治愈目标,就必须帮助患者理性认识自己所经历的创伤,让创伤转化为过去的一段历史,建立起新的人际关系和生活软环境,就是要“哀悼被创伤毁坏的旧我……重建一个全新的自我”[6]186,集聚力量,面向未来。
3.2.1 哀悼“旧我”
赫尔曼指出,只有完成了对那个过去被创伤毁灭掉的旧我的哀悼,才能建立起一个崭新的自我。哀悼是“为在创伤事件中失去的东西进行哀悼,是以健全的心智、健全的情感机能过滤创伤,检查自己在创伤事件中的责任,使自己的心灵得到救赎,把创伤经历化为历史的心路历程。哀悼的过程是获得新的力量的过程。哀悼是为了救赎,哀悼是为了忘却,哀悼是为了开始新的生活。”[1]39所以,通过哀悼,创伤患者才能逐步恢复对事物和对自我的辨别与整合能力,才能完成对创伤事件的重构和解读,使创伤仅仅成为一段人生经历,以帮助患者从恐惧和无助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彻底破解创伤的意义,释放患者的情绪,恢复对生活的信心。因此,哀悼的本质就是把“创伤化为积极力量的途径和必要心理过程。”[1]40
擦洗完尸体,面对丈夫,伊丽莎白的头脑是“冷静的、超然的”,她在开始探索“我是谁?我一直在干什么”的问题,她在开始审视那个过去被创伤毁灭的“旧我”。死亡彻底解决了夫妻矛盾,也让他们永世分离。她在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以及与丈夫在黑暗中的争斗,她开始认识到她错误地把丈夫“说成他实际上并不是的那种人”,[5]20她现在终于明白了“她曾经拒绝接受那个真正的他。”[5]21面对尸体,伊丽莎白心里充满了惭愧、自责和内疚。她逐步意识到是她自己误解了丈夫,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愧对死去的丈夫。她开始对丈夫充满悲伤和怜悯,为丈夫死前所遭受的折磨、为自己不能施以帮助、为自己不能给丈夫任何补偿而“痛苦得全身僵硬。”[5]21伊丽莎白在极度的丧夫之痛后认清了生命的本质,消减了创伤所引起的伤痛。最后,伊丽莎白对生活的屈服、对死亡的妥协标志着她对过去创伤哀悼的完成。
3.2.2 重建自我
创伤复原的标志是重建自我。在创伤中,自我被毁灭,信念被动摇,患者体验到的是无助和孤立。要彻底治愈创伤,回到正常的生活状态,患者就必须在完成对创伤的哀悼后,重建自我。只有探索出新的生活意义,重新获得自主权,建立起一个崭新的自我之后,才能创造出新的力量,开始新的生活,面向未来。在小说中,妻子伊丽莎白正是在这样的心理矛盾和心理调节中,冷静面对,理性分析,勇敢接受创伤,积极寻求应对创伤的心理能量,最后超越创伤,实现了创伤的复原。
当得知丈夫矿难噩耗后,伊丽莎白难掩丧夫之痛,而是迅速地从悲伤中冷静下来,自觉地承担起对家庭和对孩子们的责任。“这是什么时候,怎容得她这样多愁善感?她又考虑起孩子们来,无论如何,他们就全靠她了。照顾他们就是她的责任。”[5]13得知儿子死去,老太太放声痛苦,但伊丽莎白却尽力阻止老太太的哭泣,“别闹醒了孩子们。”[5]15当尸体被抬回来之后,伊丽莎白不得已从丈夫死亡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第一反应是“振作精神”,[5]16因为这个时候她已经意识到必须要面对现实,要做好善后工作,才能肩负起抚养孩子们的责任。所以,她并没有急于告诉孩子们他们的父亲已经死去,而是温柔地哄劝他们安心睡觉。
在擦洗完丈夫的尸体并给他穿上衣服后,善后工作基本完成。这个时候她已经意识到她需要面对的不是这具躺在地上的遗体,而是未来她们一家人的生活。死亡是沃尔特逃避生活、逃避现实的手段,却不是伊丽莎白逃避的借口,她得勇敢地承担起抚养孩子、照顾老人的重任。不管他们夫妻之间有多少误解或隔阂,逝者已逝,生者坚强,生活还得继续,“她知道自己对生活屈服了,因为生活是她现在的主宰。”[5]22弗洛伊德在“追忆、复述和克服”中这样说道:“患者必须有勇气集中注意力面对自己的病……坚强的毅力必须成为他性格的组成部分,成为他未来有价值的生活赖以存在的基础。妥协之路就是这么走出来的。”[1]35很显然,弗洛伊德所说的“病”就是伊丽莎白所经历的创伤,她对生活的妥协和屈服表明她已经找到自我生命的价值,集聚了足够的勇气和毅力接受生活,面对未来。
妻子伊丽莎白在面对丈夫遗体时对过去的追忆和反思过程其实就是自我疗伤的过程。她逐步理解自己的心理感受,能够开始理性地看待整个创伤事件,最后才能够从创伤中走出来,建立起面对生活的勇气和对未来的信心,这标志着伊丽莎白创伤的复原。
4 创伤叙事技术
在《菊花的清香》中,劳伦斯充分运用多种叙事技术来辅助表达创伤主题,宣泄自己的悲愤与哀伤。这些叙事技术不是单独出现,而是相互合作共同作用。
4.1 固定式内聚焦
根据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对叙述聚焦的分类,《菊花的清香》采用的是零聚焦和固定式内聚焦相结合,以固定式内聚焦叙事为主导的叙述模式。零聚焦展示的是工业化蹂躏下的生态创伤,固定式内聚焦揭示的是妻子伊丽莎白体验创伤与修复创伤的艰难历程。
聚焦的核心在于视点的限制,而“零聚焦”就是用“居高的视点,即上帝的视点传发故事”,[7]109其视点不受任何限制,并且对于叙述者而言,没有看不见或感受不到的任何东西。所以,在《菊花的清香》的开头段落,叙述者就是以上帝般的眼光来审视一切,刻画出一幅幅因工业发展所导致的生态创伤画面。
固定式内聚焦是这篇小说占主导的聚焦叙事模式,它是从特定人物的眼光展开叙述,包含有固定式、不定式和多重式三种聚焦类型。小说就是以伊丽莎白为聚焦人物,从伊丽莎白的视点展开,以她的待夫归来为线索,呈现出她复杂的内心活动和心理创伤。这种聚焦方法既可以增加叙事的可信度,又可以带领读者深入人物内心,切身体会到人物的内心感受。伊丽莎白所经历的痛苦和创伤就是在等待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起伏和得到强化的。久等丈夫未归,她由埋怨到愤怒;外出寻夫未果,她由焦虑到害怕;面对丈夫遗体,她由恐惧迷惘到冷静超然。复杂的情绪、痛苦的经历、极度的创伤等内心体验一一通过伊丽莎白的视角、通过她的内心独白立体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4.2 记忆闪回与重复
从修辞角度来说,闪回就是沟通手段当中的重复,其目的是强化表现力,加强表达效果。记忆闪回打破了常规的时空感,而创伤事件闪回的过程就是创伤暴露的过程。从审美机制上,在创伤叙事过程中,对创伤事件、创伤景象和创伤源的不断闪回和重复可以不断加深印象,强化创伤效果。在小说中,丈夫一次次醉酒的场景已经在妻子的心里烙下深深印痕,成为挥之不去的记忆。丈夫没有按时下班回家,她的第一本能反应就是他溜到酒店酗酒去了,因为在上一周内,他已经有两次是喝醉之后被抬回家的。
作为贯穿整个小说的中心意象,“菊花”代表的是他们过去的美好时光。在他们相识、结婚、孩子出生的时候菊花盛开,香气怡人。可是现在“菊花”对于伊丽莎白来说,更多的是引起创伤记忆的一个“扳机点”,因为这些菊花一次次见证了伊丽莎白的伤心体验。“他第一次喝得烂醉,别人把他送回家来的时候,他的纽扣眼里也插着棕色的菊花。”[5]7菊花对于伊丽莎白而言,便意味着伤心的回忆和痛苦的家庭婚姻生活。每一次回忆就是创伤经历的再体验。丈夫醉酒之后不省人事的记忆始终困扰着妻子,丈夫的酗酒成性、挥霍无度对贫困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除此之外,小说对矿工沃尔特的死亡并没有做直接描述,而是通过工友的讲述、矿区经历的重复来还原了沃尔特死亡的细节与真相,很好地强化了死亡创伤的效果。工友是这样道出关于沃尔特死亡的细节的:“它(石头)塌在他的背后。他正在采掘面底下,塌下的石头没有碰着他,却把他堵在里面啦。他似乎是被闷死的。”[5]15关于沃尔特死亡的场景在后来经理对沃尔特死亡过程的重复中得到了强化和巩固。很显然,这种重复增添了恐怖的气氛和体现了人在死亡面前的脆弱,“(石头)恰好落在他的身后,把他堵在里边。不到四英尺的空隙……像只捕鼠笼那样把他关在里面。”[5]17借助于这种报告沃尔特死亡的过程,作品生动再现了沃尔特在死亡面前的孤立绝望和矿工们的悲惨命运,同时强化了死亡对死者家属伊丽莎白的心理创伤,而这种被重复的死亡场景必定会成为伊丽莎白的意识深处永恒的记忆。
4.3 延宕:拉长叙事时长
作为一种后现代叙事的主要方法,延宕在创伤叙事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延宕,作者可以自由地拉长叙事时长,设置悬念,在适当的时候揭开谜底。在整个被拉长的叙事过程中,谜底的揭示要经过叙事者、被叙事者、隐含读者和真实读者的互动参与,反复推敲研判,才能最终得出结论。在通常性的叙述中,读者通过叙述者之口就可以直接获得思想,而在延宕性的叙述进程中,读者需要积极地投入到对结论和思想的等待或探寻之中。
在《菊花的清香》中,矿工沃尔特就似一个无处不在的影子,但却始终没有以正面形象出场。唯一的一次出现在读者面前就是以被工友抬回家的遗体形式。读者对于这个至关重要的人物的完整了解就只有从侧面获得,通过其他人物视角、通过其他人物对他所做的片断描述。小说情节紧紧围绕沃尔特迟迟没有回家这个谜面展开。通过妻子伊丽莎白与父亲、与孩子们的谈话读者得知,沃尔特一定是如同往常一样下班后直接溜到酒店喝酒去了。可是通过一番打听和寻找,读者和伊丽莎白对沃尔特却产生了一丝担忧。经过焦急、漫长的等待,通过沃尔特母亲来提前透露、工友来告知噩耗等悬念设置,一直到最后沃尔特的尸体被抬回家中谜底才最终得以揭开,证实了沃尔特的死亡。通过延宕的使用,读者能够更好地融入到对作品的阅读和理解进程中,能够与伊丽莎白感同身受,切身感受到等待的绝望和死亡的恐惧,以及现代人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生存困境。通过延宕,读者感受到的是强化的创伤意味和悲剧张力。
5 结论
劳伦斯作品的创伤主题具有相当的社会厚度和心理深度,记录的是过度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创伤和生态创伤,体现的是作者对现代人命运的深刻同情和心理的亲切关怀。《菊花的清香》通过讲述一个普通矿工家庭的悲剧故事,运用固定式内聚焦、记忆闪回与重复、延宕等叙事技术,揭示了女主人公伊丽莎白所体验的心理创伤及其复原的艰难历程。待夫归来和为夫善后就是她面对创伤、接受创伤和治疗创伤的过程。在遭受焦虑、恐惧和无助的困扰之后,伊丽莎白能够冷静理性地认识和接受创伤,完成对过去“旧我”的哀悼,重新建立起崭新的自我,集聚力量,勇敢地面对未来。伊丽莎白的心理创伤代表的是在工业主义蹂躏下现代人的集体创伤无意识,其家庭创伤是20世纪初社会创伤的一个缩影。在对英国工业文明深刻考察的基础上,劳伦斯通过创伤书写,努力探索工业文明与自然、人性的复杂关系,竭力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和对自身命运的关注,积极寻求对抗工业主义和拯救人类的方法,表达出用伊丽莎白式的创伤复原模式来构建理想和谐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美好期待。
[1]李桂荣.创伤叙事:安东尼·伯吉斯创伤文学作品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2]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劳伦斯.劳伦斯书信选[M].哈里·莫尔,编.刘宪之,乔长森,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
[4]李忠尚.“新马克思主义”析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5]D.H.劳伦斯.菊花的清香[M]//冯季度,选编.文美惠,黑马,译.骑马出走的女人:劳伦斯中短篇小说选.上海:三联书店,2014.
[6]朱迪思·赫尔曼.创伤与复原[M].施宏达,陈文琪,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7]谭君强.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OnLawrence’sTraumaWritinginOdourofChrysanthemums
DING Hualia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 Neijiang 641112,China)
Trauma is an important theme in D. H. Lawrence’s writing. InOdourofChrysanthemums, using such techniques as fixed internal focalization, memory falshback and repetition, afterwardness, Lawrence narrates the ecological and familial trauma under the industrialization, records the difficult process how Elizabeth faces and accepts trauma, and conveys the possibility and hope for modern people to cure and transcend trauma. Characters’ psychological trauma in the story 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modern people’s collective trauma unconsciousness, the ecological and familial trauma is the microcosm of social trauma in the 20th century.
OdourofChrysanthemums; trauma writing; narrative technique
10.13542/j.cnki.51-1747/tn.2017.03.022
2017-03-02
丁华良(1978—),男,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电子邮箱:113905285@qq.com。
I106.4
:
:2095-5383(2017)03-00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