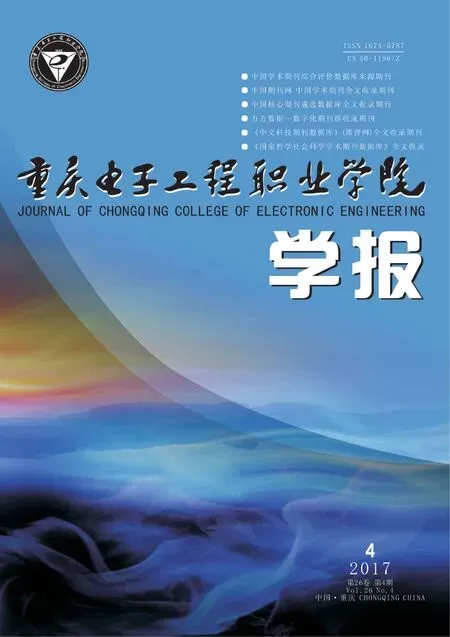危险驾驶行为刑行界分问题研究
王 菁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危险驾驶行为刑行界分问题研究
王 菁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危险驾驶行为罪与非罪的边界相对模糊,仅从形式上满足构成要件不能合理地对危险驾驶行为进行刑行界分。从质量差异说的理论出发,运用刑法总则第十三条“但书”和刑法分则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危险驾驶罪的规定,结合危险驾驶行为、危险驾驶人主观罪过为主要方面并综合情节来考量罪量,从而判断危险驾驶行为是否达到可罚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以此认定犯罪。危险驾驶行为定罪实质上是一个衡量社会危害程度的过程,需要借助个案主客观方面全面综合地判断。
危险驾驶行为;危险驾驶罪;刑行界分;罪量
1 问题的提出
2017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试行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中关于危险驾驶罪规定:对于醉酒驾驶机动的被告,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车辆行驶道路、行车速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准确定罪量刑。对于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于刑事处罚。从中看出,危险驾驶罪尤其是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不再一律入刑,行为人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作为定罪需要考虑的要件之一,同时围绕机动车、驾驶人各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认定,符合了可罚性的社会危害程度才能予以定罪量刑。罪量因素成为危险驾驶行为定罪与否的关键点。刑法中的罪量延续到行政不法领域,大量尚未达到刑事可罚性的行为由行政法加以规制,罪量的分衡使得刑行之间的界限模糊,造成危险驾驶行为的行政不法与刑事犯罪难以界分。危险驾驶行为触及的法律不同,对是否构罪、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社会评价都有差之千里的区别,因此,危险驾驶行为的刑行界分有一定的必要性。
2 危险驾驶行为刑行界分的理论依据
刑行界分的理论围绕质的差异说、量的差异说、质量差异说展开。
2.1 质的差异说
质的差异说沿袭自然法个人本位的思想,由此延伸了自体恶理论、文化规范理论、法益侵害理论等。质的差异说认为刑事犯罪与行政不法的区别在于两者的本质不同,刑事犯罪要求法益受到侵害,有强烈的社会伦理谴责性。行政不法的着眼点在于规范的不遵守。在侵害后果上,刑事犯罪侵犯的是实际利益,而行政不法造成的不是既得利益的损失,是应有更大福利的损失。沃夫在此基础上认为刑事不法造成的是一种个人损失,而违反行政法的行为造成的是国家的损失,这种损失不具有实质的内容,是一种特殊拟制的损失[1]。
2.2 量的差异说
社会国家的产生动摇了质的差异说,由于质的差异说注重个体的损害,社会的发展使得行政主体调整的范围逐渐扩大,将个体融入到整体当中,对社会利益的侵害同时也是对个体的侵害,两者的相互交融的过程,以法益侵害作为标准不能合理地区分刑事犯罪与行政不法。量的差异说认为刑事犯罪与行政不法在本质上都是对法益的侵害不存在实质的不同,行政不法在不法程度上轻于刑事犯罪。行政法规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增强,违反行政规定的行为不再只具有形式上的违法性,也会直接损害国家管理和社会秩序,并最终影响到对个人利益的保护。
2.3 质量差异说
质量差异说结合了质的差异说与量的差异说,认为刑事犯罪与行政不法既有本质的不同,又存在量的差异。质与量的不同表现在不同的领域当中。传统类型犯罪行为之间的区别是质的区别,例如故意杀人、绑架、抢劫,因为这类犯罪涉及刑法的核心领域,是对个人及社会共同体最为重要的价值,受到绝对性的保护。这种排他性的保护使得行政法不在其中,社会危害性的有无便是区分二者的标准。对于处于刑法边缘区域的犯罪行为与行政不法之间是不法程度的差别,这类犯罪集中在社会管理类型,行政法与刑法通常都享有管辖的权力,社会危害性的有无不能担当重任,需要依赖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大小来加以判断。
2.4 质量差异说的提倡
质的差异说从法的目的、侵害后果的角度,对刑事犯罪与行政不法进行了泾渭分明的划分,保护了个人的合法权益,避免了行政权力的扩张。但是,无论是自体恶理论、文化伦理理论还是法益侵害理论,依靠不稳定性和转变性的伦理作为分割点,本身是不现实的。而且,个人法益与社会法益在大部分情况下是不能分离的,这个前提不复存在。量的差异说重在研究刑法与行政法的联系,忽视了两法保护对象的侧重方面的差异。质量差异说主张的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等刑事犯罪行为以违法类型的类别作为区分,在妨害公共安全、扰乱经济秩序等方面以量作为区分标准是恰当的。危险驾驶行为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范畴,根据质量差异说的观点,涉及公共安全的边缘领域的区分在于量,定量标准的本质属性就是法益侵害的程度,法益侵害性小的行为由行政法调整,法益侵害性大的行为则由刑法规制。法益侵害程度是危险驾驶行为刑行界分的标准。
3 危险驾驶行为刑行界分的法律依据
从我国现行立法来看,我国立法模式采取的是既定性又定量,立法者不仅对行为犯罪类型化作出规定,划分刑法否定性评价与行政不法状况,而且以行为可罚性社会危害程度为边界,将刑事犯罪与行政不法加以区分。这样的立法模式决定了涉及刑事犯罪既要看行为的质,又要重视量的分析。
3.1 刑法总则第十三条“但书”
刑法第十三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体现了我国刑法对犯罪行为认定的量化判断。“情节显著轻微”是情状性规定,“危害不大”是结果性规定,两者侧重方面不同,但本质上是相同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说明行为有社会危害性,只是程度不高丧失了可罚性。《刑法》第十三条“但书”的设置,将罪量因素引入刑法规定中,在罪量上通过限制社会危害性需要达到刑罚处罚的程度来排除行政违法行为,将犯罪限定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2]。这样一来,大量轻微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被排除在犯罪圈之外,限制了我国刑法的处罚范围,从而罪量作为刑事犯罪与行政违法的区分点。
以“但书”为规范根据,区分达到刑事可罚性的刑事犯罪和仅需行政处罚的行政不法的行为。对满足“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条件的违法行为,仅认定行政不法。对排除“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且符合刑法分则具体条文规定的,具有刑事可罚性,属于刑事犯罪。即便刑法分则对危害性大小没有做具体规定,“但书”所涵摄的罪量要素也应当作为判断行为是否构罪的依据。
3.2 刑法分则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
刑法分则第一百三十三条危险驾驶罪部分行为设置了“情节严重”,与第十三条但书“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相互照应,显示了我国罪量因素渗透到各个罪名中,将罪量表述得更具体。“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外化到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中,但是这不代表《刑法》第十三条“但书”的作用退化,因为还存在着醉驾、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驾驶的行为没有罪量的规定,这些行为仍然受到“但书”的指导。危险驾驶罪中的危险驾驶行为既有行为本身的要求,又有对行为量化程度的要求。
首先,从罪质上来说,危险驾驶罪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类罪,危险驾驶罪侵犯的是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财产安全,不特定要求危险驾驶行为的危险或可能带来的后果是不确定的,不受行为人主观预期和控制所能决定。危险驾驶行为指的是驾驶员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这一行为涵摄了四个要素——驾驶人、道路、驾驶、机动车。危险驾驶罪主体不要求特殊身份,不论行为人是否取得驾驶证,只要年满16周岁、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的自然人即可。在校车、旅客运输超员超速型和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型危险驾驶行为中,车辆所有人和管理人也是本罪主体,考虑到从事载客运输和危化品运输一般由专门的公司统一进行管理,车辆所有人和管理人对危险行为的发生往往存在管理上的疏忽,纳入危险行为主体有利于从根本上减少事故的发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危险驾驶罪中的道路的定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场所”,凡是具有一定公共属性的道路都被纳入到此范围当中。驾驶行为要满足机动车发动起来后形成的位移,单纯发动引擎不属于驾驶的范围之内。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的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
再者,从罪量上来说,对追逐驾驶型危险驾驶入罪标准要求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比如,校车、旅客运输严重超员超速,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型危险驾驶要求危害公共安全,对醉驾型危险驾驶则没有提出具体要求。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醉驾型危险驾驶行为既属于抽象危险犯,又没有明确的量度要求,只要具备醉酒且危险驾驶即可认定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危险驾驶罪成立。危险驾驶罪的性质是抽象危险犯,这意味着立法者对危险驾驶中的危险采取预先假定,一般情况下只要醉酒后仍驾驶机动车,便满足了抽象的类型化危险性。但是,危险驾驶行为之所以被刑法所规制,是因为其本身有侵犯公共安全的可能性,而且一旦发生事故,造成不特定或者多数人法益受损的危害后果是严重的。危险驾驶罪的前提是设定了公共安全法益受到侵害的可能性,倘若根本没有法益侵害的可能性,即便行为人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也不能以危险驾驶罪定罪[3]。
4 危险驾驶行为刑行界分标准
危险驾驶违法行为相对危险驾驶罪或具有较轻的法益侵害性,或欠缺高度的刑事可责性,两者在违法性的量上存在差异。量的区别主要从主观罪过、客观行为和情节三方面论述。
4.1 危险驾驶行为主观罪过
行政违法性质的危险驾驶行为在主观上没有特别的限制,行为人不论是故意还是过失都不影响对危险驾驶行为的认定。但是,构罪的危险驾驶行为在主观心态上的要求更为严格。理论上,危险驾驶罪有故意说、过失说和故意过失说。故意说认为,行为人明知危险驾驶会发生实际危险,仍希望或放任这种危险状态的发生。过失说认为,行为人饮酒是故意行为,但对结果的发生应是一种过失的态度。并认为故意说的缺陷在于,故意包含认识和意志两方面的内容,即行为人不仅有饮酒后开车对公共交通安全存在隐患的认识,更要有明知危险仍酒后驾驶,不顾他人的安危和公共安全的意志。故意过失说,危险驾驶罪既可以有故意的主观心态又可以有过失的主观心态[4]。笔者认同故意说。过失说的论点不能成立,行为人主观上只要能够认识到自己处于不能安全驾驶的状态,仍然采取驾驶的行为,满足了故意中的认识要素,不要求对危险后果产生认识。过失犯要求要产生一定的结果且法律有明确规定,但危险驾驶行为只要出现危险状态不要求结果的发生[5]。而且,过失犯的成立与《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相冲突,《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四款认为车辆所有人、管理人对超员超速和违规运输危化品危险驾驶负有直接责任的,按照对驾驶人的规定处罚。实际上是驾驶人和车辆所有人、管理人之间成立共犯,但是,过失犯缺乏意思联络没有共犯的余地,如果认定危险驾驶罪的主观心态是过失,不能合理地解释第四款的规定。故意过失说表面协调了两种观点,但是故意和过失心态的可责性不同,承担的刑事责任也是不同的,在本条文中并没有对责任大小的区别性规定。因此,危险驾驶罪中的危险驾驶行为主观罪过为故意。如果行为人对驾驶行为只是抱有过失的心态,如食用了一定量的荔枝,即使此时行为人酒精含量达到80mg/100ml,也不能认定行为人危险驾驶罪。
4.2 危险驾驶具体行为辨析
行政违法性质的危险驾驶行为主要由《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种类多样,包括无证驾驶、驾驶拼装机动车、违规停放等行为。危险驾驶罪中的危险驾驶行为只限于情节严重的追逐驾驶、醉酒驾驶、校车或旅客运输车辆超速或超载,违反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四种情形的行为。危险驾驶行为的刑行界分范围限定在这四种行为类型中。
4.2.1 追逐竞驶型
追逐竞驶,强调两车相互追赶,竞相行使,在行驶过程中有特定的对象或者目标且双方或一方形成竞争状态。表现方式主要有随意追逐、频繁并线、突然并线等。有学者认为,追逐竞驶包括超速行驶和常速行驶,在超速行驶中即使只有一辆车也应视为追逐竞驶。前半句是正确的,追逐竞驶一般伴随着高速行驶,但却不以高速行驶为前提,单纯的高速驾驶或者超速驾驶,没有其他情节不构成本罪。后半句中一方确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追逐竞驶不需要驾驶者之间事先要有意思联络,但是需要行为人单方面将他人设定为目标追逐竞驶,如果行为人只是单纯的超速行驶,没有“竞”的状态,不应认定追逐竞驶行为。
4.2.2 醉酒驾驶型
酒精对人的神经起到麻醉作用,使大脑处于麻痹状态,四肢不受控制,判断能力和控制能力同时下降。醉酒的判断标准有客观判断和主观判断之说,前者以一般人为标准,统一设定酒精含量值,当驾驶人体内的酒精含量等于或高于这个数值时,驾驶人便处于醉酒状态。后者则根据个人对酒精的耐受值不同采取区别判断。我国采取客观标准,对一般人来讲,当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80mg/100ml的时候,驾驶员往往不能控制机动车的正常行驶,对交通状况也不能有正确的认识。这一客观标准也是危险驾驶行为刑行界分的判断标准之一。但是,酒精含量标准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行为人的危险性,不能全面概括危险驾驶行为达到了严重的社会危害程度。
4.2.3 超员超载型
超员超速型危险驾驶行为中,针对的对象是校车和从事旅客运输的车辆,需要界定校车和从事旅客运输的车辆。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校车安全管理条例》,校车指的是取得使用许可,用于接送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上下学的7座以上的载客汽车。校车的范围被限缩到针对中小学学生7座以上的专用校车的原因在于中小学生由于身体尚在成长阶段,相对高中生、大学生在校车事故中极易受到伤害,一旦发生事故,这类群体由于体质的原因,伤亡比例往往更高。旅客运输,根据交通运输部颁布的《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是指用客车运送旅客、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具有商业性质的道路客运活动,包括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等。在这一界定中,有两个问题需要考究。一是,校车的范围是否作扩大解释?二是,不具有营运资质的车辆是否属于旅客运输?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校车无需扩大解释。尽管,现实生活中适用校车的不只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高中生、大学生、教师职工都是乘坐校车的主体,其他主体的法益也应受到平等保护。考虑到校车超员超速入刑为保护的法益,不应当扩大使用校车的主体范围。对于这类非义务教育的学生、老师乘坐校车出现超员超速可以用旅客运输超员超速进行规制。旅客运输分为营利性旅客运输和非营利性旅客运输,对旅客运输不进行限制解释为营利性旅客运输即可解决这类问题。不具有营运资质的车辆从事运输活动也应当按照本罪论处。缺乏相应资质从事运输活动本身是行政不法行为,又满足超员超速,危险性明显高于普通旅客运输超员超速,以“举轻以明重”的原则入罪。
4.2.4 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型
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不同于一般的运输事故,往往会衍生出燃烧、爆炸、泄漏等严重的后果,并且对道路安全造成影响大、危害大的后果。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三条的规定:“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危险化学品的管理包括生产、使用、销售、运输、储存和废弃六个环节。危险驾驶罪针对运输环节,但并不惩罚非法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行为,而是旨在针对合法但违规运输的行为。涉及安全运输危险化学品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剧毒化学品购买和公路运输许可证管理办法》等。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的要求运输许可并办理登记、驾驶人员、装卸人员和押运人员取得从业资格,车辆要求悬挂警戒标志等。违反这些规定则有构成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型危险驾驶罪的可能。
4.3 危险驾驶行为刑行界分情节要求
对情节的把握,应当结合犯罪的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进行综合全面的考量。其中,反映犯罪主观方面的情节除了主观罪过还包括犯罪的动机、目的、是否有预谋。反映犯罪客观方面的情节除了行为,还包括危害结果、犯罪时间和地点等。
4.3.1 追逐竞驶型
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要求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主观上判断驾驶人的动机是否恶劣,是否为了寻求刺激、发泄情绪,是否有预谋而为之以及参与的人数多少。客观上,结合驾驶人追逐竞驶的路段、时间,以及行为自身和导致的后果。尽管危险驾驶罪属于抽象危险犯,不要求造成一定的后果,但是后果的严重与否影响对情节的判断。具体而言,行为人炫耀车技、宣泄情绪、多人多次参与追逐竞驶、驾驶时速超过规定时速50%、车辆密集路段、上下班高峰期和驾驶人无证驾驶、酒后驾驶等情形,根据个案综合衡量行为人的追逐驾驶情节。
4.3.2 醉酒型
醉酒驾驶的行为由于欠缺立法上的情节规定,在其纳入刑法典之初便引发醉酒达到客观标准时能否一律入罪的争论。醉酒后行为人的控制能力减弱是无可争议的,只是个人承受酒精的程度不同,表现出的行为危险性大小不同,但改变不了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本身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正因为如此,一般情况下只要有醉酒后危险驾驶的行为即认定达到构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但是,这不代表醉酒型危险驾驶行为不受任何情节的限制,并列的危险驾驶罪不法行为定型,四种不法行为定型从属于危险驾驶罪这一个罪名,适用同一法定刑,表明立法对四种不法行为定型是同样的否定性评价。醉酒型危险驾驶的不法程度应与其余三种行为的不法程度基本相当。同样受到危害性大小的约束。对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但满足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应当排除危险驾驶罪的成立。比如,行为人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为了将机动车从一个车位移动到另一个车位,停车场有公共性的特性,但人流量毕竟是有限的,加之移动车位的速度较小,此时行为人即便达到醉酒的客观标准,也不能因此判断其构成危险驾驶罪。
4.3.3 超员超速型
刑法对超员超载没有规定标准,结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二条:“客运车辆超额载客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超过额定乘员20%的,处500元以上2 000元以下罚款。”可知,超过额定乘员的20%作为严重程度的分界点。第九十九条:“机动车超速行驶的以超速50%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200元以上2 000元以下的罚款。”超过时速的50%为严重超速的分界点。超员超速的比例参考行政法律的基础上,应当根据实践制定属于刑事判断的标准,刑事的标准显高于行政法上的标准。超载时还要考虑到车辆的规格,大型客车、中型客车和小型客车的标准应当分别而论。大型客车(根据《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大型载客汽车是车长大于等于6 000mm或者乘坐人数大于等于20人的载客汽车)载客量大,自身的车重更重,行驶过程中的可控性更差,一旦发生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更大。小型客车的灵活性较好,相较大中型客车在同比例超载人数时的控制能力更好,因此,大中小型客车应当按照比例由低至高安排。超速的认定也不能仅仅依靠固定的时速值,不同路段对时速的要求不同,盘山公路、陡坡路段、桥梁路段、连续下坡、连续转弯等情形分别而论。这种比例标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给司法人员裁判的依据,但不能作为全部情节认定标准,还要综合行驶的路段、时间等因素。
4.3.4 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型
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危险驾驶要求危及交通安全,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一旦发生,将造成不同于一般车辆运输的巨大的人身财产损失,对道路公共安全存在严重威胁。在判断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是否危及公共安全时,以危险驾驶行为本身情况,根据一般社会经验进行判断。具体而言,所运输的危险化学品的性质、数量,运输的时间、道路和违规运输的程度以及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等,对这些客观评价要素进行分析后,结合驾驶人主观罪过、动机、目的等主观因素来认定。
社会危害性大小的标准很难具体化,因为个案情况不同,需要司法人员实质判断分析。无论四种类型中哪一类型,从主观、客观到情节,从驾驶人、车辆到路况,主要围绕驾驶人主观罪过、动机,驾驶路段、驾驶时间段以及其他违法驾驶的情形,综合认定罪量。
[1]王莹.论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分野及对我国行政处罚法与刑事立法界限混淆的反思[J].河北法学,2008(10):26-33.
[2]梁根林.刑事法网:扩张与限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9.
[3]何荣功,罗继洲.也论抽象危险犯的构造与刑法“但书”之关系———以危险驾驶罪为引例[J].法学评论,2013(5):48-53.
[4]谢望原,何龙.“醉驾型”危险驾驶罪若干问题探究[J].法商研究,2013(4):105-116.
[5] 黎宏.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477.
责任编辑 周斯韵
Studies on the Difference of Dangerous Driving Behavior in the Criminal Law and the Administrative Law
WANG Jing
(Law School of 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Jiangsu 215000,China)
The boundary of dangerous driving behavior is relatively fuzzy,so it can not only reasonably judge the quality of dangerous driving behavior just meeting the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in form.Starting from the theory of quality differences,use the regulation of dangerous driving crime of the article 13 in the general criminal law and one of the article 133 in the clause criminal law,and combining with the driver’s dangerous behavior and subjective fault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dangerous driving behavior can reach the level of the extent of social harmfulness punishable as a crime or not.Convicting the dangerous driving behavior is a process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social harm in essence,needed cases to comprehensively judge.
dangerous driving behavior;sin of dangerous driving behavior;the boundary of dangerous driving behavior;criminal factors
D924.3
A
1674-5787(2017)04-0011-06
10.13887/j.cnki.jccee.2017(4).4
2016-05-18
王菁(1991—),女,山东淄博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