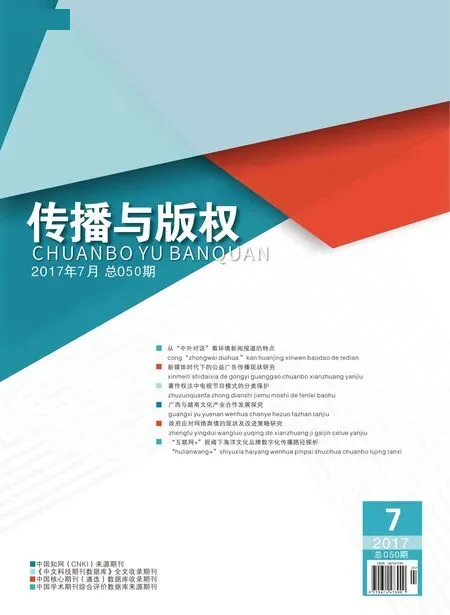浅析现当代中国教会书刊出版历史
周晓薇
浅析现当代中国教会书刊出版历史
周晓薇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以及改革开放的进程,人们的思想逐渐解放,国内文化及出版界对教会的认识和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与更新,相关研究和出版也逐渐兴盛。对新中国成立后和改革开放至今国内教会书刊出版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介绍,并分析每一时期三自爱国运动与非官方出版的书刊的文化特征与精神属性,亦探讨进入数字出版时期后我国教会出版方面取得的成绩与所需要面对的挑战。
教会书刊;出版;三自爱国运动;数字出版
[作 者]周晓薇,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教会书刊出版事业进行了诸多的研究和探讨,但对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至今的基督教属灵书刊的出版状况却鲜有人问津,几乎没有较为正规和详尽的学术文献呈现。因此,笔者将对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教会书刊的出版历史进行简要的回顾与论述,特别针对三自爱国运动和当时历史背景下社会文化对我国教会出版的影响进行分析,着重介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基督教书刊;并探讨进入21世纪后,近十多年来我国教会出版事业所取得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以期为今后相关出版发行和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对中国教会书刊出版发行的起步发展时期
(一)三自爱国运动对中国教会书刊出版发行起步发展时期的影响
1950年7月28日,在吴耀宗的倡导下,我国基督教界的40名知名人士联合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一文(后称三自宣言),提出中国教会要脱离近百年来“洋教”的形象和海外基督教团体的控制,即中国教会将不再从属于任何国外的基督教组织和罗马教廷,真正开始实现“自治”“自传”“自养”——于是,轰轰烈烈的三自爱国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1-2]。
在三自爱国运动初期,吴耀宗就提出了关于基督教属灵出版的一些设想和建议,在其1951年发表的《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新阶段》一文中就曾指出:“中国基督教是从西方传来的,中国的宣教人才大半是受过西方神学训练的,中国基督教的读物,大半是西方著述的译本,中国的信徒必须脱离西方神学,创造中国教会自己的神学系统;这样中国才能把耶稣的真精神,表现在新中国的环境里。”[2]
(二)社会文化对中国教会书刊出版发行起步发展时期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唯物主义在中国社会全面并深入宣传。在此背景环境下,中国基督教团体和教会人士纷纷开始进行思想改造,加强认识与学习时政功课与相关文件精神,正常的宗教活动与学术出版研究均受到影响[2]。
“文化侵略论”一直是新中国刚成立后学术界对基督教的总体态度和基调,其中影响至深的主要是将基督教定义为:帝国主义麻醉中国人民的一种精神鸦片,无论是传教、办医院、建学校、办报纸和刊物等,都是其文化侵略的方法和措施[3]。虽然现在看来这种评价在当时有其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也影响了此阶段相关的研究和学术出版。
而香港和台湾地区则分别出版了有关于中国基督教的通史性著作是1965年香港周仁孚所著的《基督教与中国》和1968年台湾基督教学者杨富森的《中国基督教史》[4]。
二、中国教会书刊出版发行的过渡发展时期
(一)三自爱国运动对中国教会书刊出版发行过渡发展时期的影响
1979—1998年是三自爱国运动的第二个阶段,该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坚持并深化“三自”原则,从“自办教会”逐步向“办好教会”转变,由实现“自治”“自养”“自传”过渡为以“治好”“养好”“传好”为主要方针政策[5],而对文字出版工作的重视和复兴亦由此开始。
作为我国基督教出版的主要书籍——《圣经》,自1980年便开始印刷发行;新编赞美诗也是发行量比较大的书籍,自1983年至今出版累计已达915万册[5]。除了两大传统基督教出版物外,还出版了种类繁多的教会书刊,其中新书有35种,印数达到了187万册;1992—1996年间,各地教会共出版新书有130多种,发行总量达到1000多万册[5]。
1982年和1989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先后编印了《回忆吴耀宗先生》和《吴耀宗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后来又在1995年编印了《吴耀宗生平与思想探讨》,但鉴于编者地位的特殊性,其学术性的意义和价值不高[4]。除了吴耀宗外,中国基督教协会还出版了德国学者所著的《赵紫宸的神学思想》(1999年)。
值得一提的是,创刊于1945年的《天风》杂志,自1980年复刊以来,便成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简称两会)主办的专业性宗教学术期刊。该刊充分体现了三自原则,是中国基督教两会宣传基督教文化、探讨学术问题、引导三自教会及其信徒属灵生命的重要纸质媒介,并为海内外华人提供了很多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的相关信息。
(二)社会文化对中国教会书刊出版发行过渡发展时期的影响
1.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教会书刊出版。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历史文化遗留问题和政治环境影响等因素,导致引领当时基督教出版界的总体意识形态为:捍卫无神论,批判基督教的迷信虚伪。198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日本作家幸德秋水所著《基督何许人也——基督抹煞论》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6]。此外,还有霍尔巴赫的《袖珍神学》、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罗素的《宗教与科学》和《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等都是当时同类型的出版物[6]。
而对中国基督教史的出版则呈现出从单纯研究反洋教运动,发展为探索其历史的各个方面,并能作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的巨大转变。当时学界所聚焦和关注的热点是义和团运动及其教案的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1981年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该书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在大陆地区的首部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专著,不但详细论述了1540—1949年间由传教士参与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教育活动和医疗慈善事业,更有所侧重的分析了几大教案[1]。
2.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教会书刊出版。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国外文化的逐步开放与接受,出版物市场特别是我国基督教书刊出版的变革发展,表明了社会和文艺出版界对基督教作为西方文明重要源头的认同,亦肯定了其将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于是,大批量的西方文学作品和学术著述,开始以“本土化”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这种本土化,实际上是将西方现代观念与本土经验相结合的产物,是将“文化”取代“政治”,继而促发了当时所谓的新一轮启蒙运动的文学出版革命。在这场运动中,“走向未来”编委起到了非常关键的推动作用,其在1986年发行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以及同属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宗教与世界丛书”,其中更包含了《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基督教思想》《论神圣》《科学与宗教》等多部颇具影响力的基督教学术著作[6]。
但是,当时中国社会及出版界对于基督教的认识尚处于萌芽阶段,因对先进科学文化的急需和渴求,基督教出版也都偏向于对社会功用与实用性的开发以及普世人文价值的研究,而有关各宗教的比较和基督教与现代科学也是比较常见的出版物选题。
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出版的基督教书刊才开始关注并探讨中国社会与基督教文化之间关系的作品,其中又以刘小枫所著的《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为新启蒙运动的学术代表作。正如刘小枫[7]本人在该书的修订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序言中所说:“不断在欧洲小说和哲学中寻找某种东西,心中挂念的仍然是相当含糊的‘中国问题’。”关于这个所谓的“中国问题”,刘小枫给出了既尖锐又独特的视角,并且在内容的丰富和思想的深刻性上在当时整个中国出版界也算独树一帜。但纵观全书,哲学性的形而上学思想和儒释道精神的解读超过了对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诠释,且其中对基督教信仰的认识仍存在很大的争议,甚至误区。因此,或许该书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再解读具有深远意义,但并不能将其作为纯粹的基督教出版物。
综上所述,就整个80年代出版而言,关于中国基督教史的、有价值的研究性作品并不多见,究其原因是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整体思维方式和观念的转变则为未来该方向书刊作品的出版提供了有利条件。
3.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教会书刊出版。从20世纪90年代起,对中国基督教的通史性研究亦取得了重大进展。不仅能突破以往的局限,参阅和借鉴国内外论著,对于史料的论述和评价也更为翔实与客观。例如:199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顾卫民所著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便为其中一例佳作。有评论指出[8]:本书的作者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摆脱了长期以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支配,从固有的学术研究局限中挣脱出来……能秉持理性而客观的原则对史料进行叙述与判断,是具有很高可读性与参考价值的基督教通史类书籍。
以区域性划分基督教在华发展史的研究成果与作品亦不断涌现,是本时期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另一大特色[8]。其中又以研究基督教对沿海各省和西南少数民族的影响居多,发展出许多关于我国福建省、上海市、云南傈僳族和石门坎地区为代表的中国基督教区域发展史作品。属于此类型的代表出版物有陈支年、李少明的《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苗族社会》(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姚民权的《上海基督教史(1843—1949)》(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94年)[8]。
此外,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中国基督教的研究成果迅速增长,研究领域和对象渐趋多元化与完整化,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学艺术的研究也由80年代开始建立后经过十年间的发展有了真正深入的发掘和研究[4]。
而将20世纪80至90年代底总体划分为中国基督教书刊出版的过渡发展时期的主要原因是:(1)当时三自爱国运动正处于转型阶段,“两会”对相关基督教书刊出版的方针政策也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2)因着整个中国社会正处于大众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转型过渡时期,中国社会和文艺出版界对作为外来事物的,且在中国处于新兴状态的基督教,还需要一个逐渐接纳和认识的过程。
三、中国教会书刊出版发行的蓬勃发展时期
(一)三自爱国运动对中国教会书刊出版发行蓬勃发展时期的影响
1998年底济南会议的召开,确定了以“加强神学思想建设”为标志的决议,并宣告了三自爱国运动前两阶段的结束与第三阶段的正式开始[9]。自此,我国基督教出版发行事业迎来了新的春天。
随着基督教书刊出版发行的蓬勃发展,在2008年10月举行的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发行工作会议上,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秘书长徐晓鸿牧师就表示:“在中国日益发展进步的大好环境下,中国基督教的出版发行事业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故此,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合法经营,自觉抵制非法出版物;二是服务至上,甘做传扬福音的好使者;三是科学化管理,即在新兴媒体和网络的大力发展与覆盖之际,基督徒应尽快转变观念,不断学习和创新,使用先进的科学管理技术和手段,让“发行人”成为生命之粮智慧的“传递人”[10]。
另外,新时期三自教会的新领导人,关于丁光训的个人文集和纪念文集的出版发行也受到重视。
(二)社会文化对中国教会书刊出版发行蓬勃发展时期的影响
根据基督教文字出版所传播的文化内容,大致可以将基督教书刊出版分为宗教类福音类和世俗科学类两大部分,前者主要面对下层社会进行传播宣讲,后者的读者群则主要是中上层的知识分子[11]。从历史的总趋势来看,两者一直是双管齐下、紧密结合的。
而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已趋于稳定,相应的对精神文明的需求则越来越高。对于西方文化,特别是对宗教信仰方面的学习热情也随着有关政策的开放而逐渐高涨起来。因此,不同于20世纪流行的科学与信仰类选题,我国现阶段对基督教书刊出版的首要任务是宣扬福音和辅导信徒成长,当下基督教书刊出版的关注点也更集中于福音慕道与初信造就,灵命进深与释经解经类作品。
在通史性书籍出版方面,不仅于2004年再版了王治心1940年完成的《中国基督教史纲》(中国古籍出版社),还有姚民权、罗伟虹合著的《中国基督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等多部历史巨著。《中国基督教史纲》更被誉为是中国学者所撰写的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影响力最大的中国基督教通史作品[4]。
相对来说,对于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有了更为宽广和细致的研究划分,在医疗、文字、妇女、基督教政策等各领域都不乏举足轻重的作品出版。而对外国传教士的研究方向也已经由宏观转向个案探讨,从单纯的负面批判发展为客观评论;在相关教案的研究的视角及方法上也有了不少突破和进展[4]。中国本土家庭教会及相关人物的作品也逐渐增多,例如倪柝声、王明道、宋尚节等传道人生平的介绍以及他们本人所著的讲道集、属灵作品等也都已成为21世纪国内基督教出版界的畅销书。
但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即有关1949年后的基督教在我国的发展与建设的著作却一直并不多见,甚至成为现今基督教出版的一项空白。研究中国基督教内部的资料则更为罕见,大多数书刊更多围绕着基督教与社会、政治、文化等外围方面展开。
引进国外的基督教经典著作也成为新世纪我国基督教出版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此类基督教出版物可以历史时代大致划分为:早期教父类、宗教改革类、中世纪欧洲教会史和清教徒系列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宗教文化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发行的“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丛书,属于该系列的有《基督教早期文献选集》《教父及中世纪证道集》《中世纪灵修文学选集》《奥古斯丁选集》及《基督教要义》等书籍,以及三联书店的“基督教经典译丛”,属于此译丛的有《基督教要义》《回到正统》《教会史》《论基督教信仰》及《圣徒永恒的安息》等作品。
通过对基督教经典著作的引进和出版,可以帮助读者更透彻的理解基督信仰,体会其深邃的内涵,使信徒的属灵生命得到丰富和提升。相对于20世纪80、90年代的同类型作品,现今我国对基督教文化经典的引进出版,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有了大幅的提高,对作品的文化精神也有了更为细致和深入的挖掘;出版界对基督信仰本身也有了更为全面和正确的认识,在尽可能保留和传递作品自身精神的同时,为迎合当下中国社会和读者的阅读水平,也做了多次多人反复的审读校对以及相应的修订、注解。
目前,在国内市场上比较热门的一类基督教出版物是关于婚恋交往的。如果按照内容分类,其品种又可细分为单身预备、恋爱交往、婚前辅导、夫妻相处以及家庭建造等。这类书刊中比较受读者欢迎的作者有袁大同、刘志雄、提姆·凯乐和珀尔夫妇,后者所著的“帮助者”三部曲系列和戴比·琼斯的《清心等候的女人》都是现今畅销的基督教婚恋类书籍。而儿童读物、青少年读物、青春期教育以及亲子教育类书籍也随之应运而生,逐渐成为国内出版物市场上的广受大众青睐的品种。
另外,标志着中国基督教书刊出版发行进入蓬勃发展时期的另一标志是名人效应以及书刊的品牌效应愈发突显明,在国内比较受读者欢迎的基督徒作家有C·S路易斯、杨腓力、加尔文、马丁·路德、巴刻等;国内在基督教出版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出版社及工作坊有中信出版社、三联书店、陶土书房、橡树出版等。
近年来,互联网和计算机通讯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促发了数字出版的诞生和流行,促发了出版观念的革新。除了官方色彩的基督教杂志意外,《海外校园》《举目》《橄榄枝》《杏花》等基督教杂志也以微信、微博等互联网工具为依托,搭建了新的数字出版平台,拓宽和发展了更为广阔的基督教出版空间。
四、结语
研究近代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就离不开基督教所从事的文字出版。
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基督教对中国社会文化、经济的方面的影响力也逐渐突显,并体现出积极的作用;其书刊出版将逐步同教育、医疗并列成为基督教会宣传教义、参与社会的重要手段。并且,今后中国基督教对区域史、宗派史、教育史等相关性的研究也会逐渐开放,并形成新的出版增长点。因此,出版社在引进国外基督教经典作品的同时,更应该不断追求门类齐全、品种繁多的出版路线,打造自有品牌和特色化的出版精品。
随着数字化出版日新月异的发展,如今的基督教出版也不应拘泥于传统出版框架的局限,需要拓展思路和模式,积极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利润增长点,实现从单一纸质媒体出版向综合性网络资源库出版的转变和过渡。
[1]谢明.当代中国基督教传播方式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0.
[2]金圣民.当代中国基督教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1.
[3]陶亚飞,杨卫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J].史学月刊,2010(10):5-21.
[4]陈建明.激扬文字 广传福音 近代基督教在华文字事工[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5]中国宗教编辑部.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韩文藻先生谈我国基督教书刊的出版和发行工作[J].中国宗教,1998(3):16.
[6]游冠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教文字出版事工之回顾与展望[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90c9590100 lxv9.html.
[7]刘小枫.拯救与逍遥[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8]陶飞亚,杨卫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J].史学月刊,2010(10):5-21.
[9]中国宗教编辑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50年的成就与启示[J].中国宗教,2000(5):26-31.
[10]华炎山.中国基督教两会2008年出版工作会议在汉召开[EB/OL].http://www.hbmzw.gov.cn/zwdt/tpxw/24862.htm.
[11]邹振环.近百年间上海基督教文字出版及其影响[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27-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