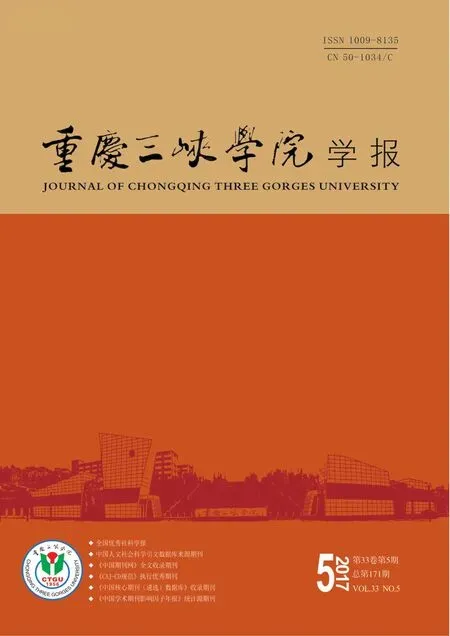当代上海市井小说的家庭叙事:从传统到现代
张艳虹
当代上海市井小说的家庭叙事:从传统到现代
张艳虹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241)
当代上海市井小说以微观的视角呈现特定的生活空间的体验与经历。这些不可复制的细节展现出的生动、真实与具体,不同于宏大叙事。弄堂里的家庭叙事和生活细节是个体的历史,弄堂里的生活图景、“流言”以及情感叙事都是上海市井生活中最具生命力的事物,让城市染上了感性色彩,具备了生命的温度。
市井;弄堂;流言;情感叙事
当代上海市井小说固然缺乏大场景和宏大叙事,总是“螺蛳壳里做道场”,但从另一面看则“有着市民文化不拘不束、日常世俗和宽容”[1]58,能在虚弱和狭小的空间中寻找意义与滋味,以平实日常上海之形象与辉煌发展的上海形成映照。家庭叙事构成平实日常的上海,其所描绘的市井生活不断地以现代之物破坏精致整一的古典美学想象,又使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获得成为审美对象的可能性,呈现出城市之下具体个体的历史和生活图景。
一、弄堂镜像:市井小说中的生态景观
弄堂伴随着上海发展的历史,代表上海的特征。从早期的老式石库门、新式石库门弄堂到新式里弄、花园里弄,再到中国弄堂、外国弄堂等等,上海的弄堂千姿百态,里面的生活包罗万象。原来的弄堂构成一般多是二、三十幢房子,规模小的可能只有几幢。随着城市的扩张、人口的增加,石库门越建越多,新式石库门规模少则几十幢,多的上百幢甚至是几百幢。随着石库门规模扩大,房子数量增多,弄堂也相应地复杂起来,有总弄,还有支弄。在20世纪50年代,上海弄堂总数有9 000多条,弄堂里的住宅超过20万幢,占当时上海所有住房的60%,容纳了70%的居民。上海弄堂的发展承载着这座城市的生活气息,有着普通人的童年回忆,凝聚起城市的个性基因。透过弄堂看到的上海大众,是日常生活中最广大的群体,维系着社会的稳定。市井的精髓便在这个群体之中。这是上海市民生活的天地,藏污纳垢、宁静又嘈杂,弄堂早已与上海居民融为一体,蕴藏着上海的市井文化。
1937年,夏衍创作了三幕戏剧《上海屋檐下》,把普通的石库门拦腰斩开,展示出一个细致的横截面,真实的日常生活空间便展现在舞台上。人们可以看到灶披间、自来水龙头,看到亭子间窗口挂着的淘箩、小孩的尿布,也看到客堂间的写字台,用作衣橱的玻璃书橱以及天井里的破旧家具、小煤炉、饭桌等等。住在阁楼上的老报账、沦落风尘的施小宝、失业的洋行职员黄家楣、小学教师赵振宇以及二房东林志成和杨彩玉。这些不同身份的人和家庭拥挤在这狭小的空间中,没有宏大的理想与伟大的事业,各种破旧的、杂乱的家什所传递的是生活的种种不易与逼仄。即使是在大时代即将到来之前,我们所看到的也只是实实在在生活中的算计与努力的挣扎。我们很难厘清,到底是世侩算计的一面支撑助长着这种建筑格局的扩张,亦或是这种建筑空间的格局塑造了城市的特性①。城市记忆通过建筑、叙述、日常的交往,存在于主流传播系统之外,在生活之中默默存在并互相传递。“生活在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里的人创造了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的诗意和美。”[2]4在生活中坚守的坚实的价值理念,通过交往与实践,使之成为日常生活情境中延续和发展的实践性能量。文化始终保持着动态的流转,经过记忆筛选留下的东西恰好反映了人们内心的期待。
到1990年代后,作家们更倾向于在文学中挖掘“上海”特色。弄堂成为文化的想象标志出现在各类作品之中。程乃珊的《蓝屋》《女儿经》《金融家》,王安忆的《文革轶事》《长恨歌》,王晓玉的《紫藤花园》,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都在文化和市场上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对于精致的、细微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回忆与想象,与城市发展的宏大图景似乎是背道而驰,但是其内在却又有着相通之处。旧上海图景中的弄堂、石库门及其所对应的日常生活的方式与做派,描绘出了在当时与众不同的“上海叙述”,并满足了全球化趋势下对日常生活的想象。这正如罗兹•墨菲所说的“就在这个城市,胜于其他任何地方,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扩张主义的西方和因袭传统的、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效率低的、闭关自守的中国——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3]5。在上个世纪末的怀旧情绪中,“重返石库门”成为极具象征性的符号和体验,俨然成为了欲望、梦想和市场意识形态的符号。
相似的空间所产生的文化具有在地性和独特性。这种物质规训带来相似的共同记忆,一些相似的东西被保留了下来。比如对时光流逝的眷恋、新旧观念的冲突、纯真岁月的追忆、风俗的体验等等。这些主题一直在各种场合反复出现,又各有侧重,丰富着市井弄堂的内容。程乃珊的叙述中弄堂是高门大户,是有厨房、卫生间、保姆间的高档公寓。每天的菜金两元,要六菜一汤,二大荤,二小荤;陈丹燕的书写比起程乃珊更多写家常。相较之下,王安忆的弄堂更世俗,是日常生活中的絮絮叨叨,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弄堂景色才是真景色”[4]。弄堂生活成了集体的想象。“一个伟大的城市所依靠的城市居民对他们的城市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感情,最终必须通过一种共同享有的认同意识将全体城市居民凝聚在一起。”[5]242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有街道、有弄堂。社会认同、家庭位置被框定于其中,生活的往来既是进入这个关系网,同时也意味着社会归宿感。家庭与外部环境的边界被模糊了,通过模糊的处理,虚化了家庭的存在,以弄堂生活的组成部分的形象出现。弄堂的生活在这种关系的不断叙述强化中被浪漫化了。
如果说,作为城市的上海象征着欲望、现代性、变化、速度,那么弄堂就是躁动的反面,是城市中最安静、闲淡但又最丰富曲折的一面。城市外部的环境在不断地改变,但这个封闭小环境内的变化总要慢几拍。城市的变化是如此之迅速,街道上几乎时时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一代人的记忆几乎都无法复制。因此,关于一座城市的记忆竟然变得如此不确定,甚至是隐晦的,不可触摸的。关于城市的乡愁就变成对于城市这一段历史的回忆,所有人都试图找出相似的、可分享的记忆来。从邻里间的绰号到嬉闹,弄堂的记忆通过互惠和共享机制得以维持,这种家庭之间的互通有无,具有了经济和象征的意义。这些叙述来自于被袒露的生活。这些形象是记忆的拷贝,被一次次重复利用,并在其中找到了归属感。即便是卫慧、棉棉,这些曾走在文学欲望表达最前沿的作家,她们文本中涉及到“弄堂”时,也表现出出乎意料的柔软。
历史的隔绝与记忆的模糊,种种在过去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人、物、事件以及物品逐渐离开了生活,并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下得到不同的阐释与解读,或被赋予了审美的想象,或被曲解,再现出一个个弄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种种家长里短展现出独特的市井意味。当个体的经历被凸显的同时,一旦相似的经历得到呼应,那么那些相通、相似的内容便显得弥足珍贵,尤其这些记忆和印记随着时间的流逝只留下了那些美好的部分。但在现实中,艰辛的物质条件并不能创造出田园诗般的家庭环境,生活本身的残酷与乏味依然尖锐。
二、流言记事:市井小说中的世俗精神
弄堂的世俗生活图景所形成的叙述惯性常常是琐碎、细腻且铺陈的,在“声”与“色”的统一中,谱写生活的韵味。王安忆的“平安里”、程乃珊的“蓝屋”、王晓玉的“永安里”,看似安静的弄堂其实波涛汹涌,“这里都是一条条小弄堂,每一幢石库门老房子里人多得要死,从我们这个石库门进出的,就有二十多户人家哩”[6]76。每个家庭各自曲折起落、兴衰散合,奠定了城市的基调。弄堂里的人物众生相展示不同的风土人情。有的人家有过显赫的家族历史,之后家道破落,屈居弄堂之中,如《天香》《长街行》;有的是心心念念“上支角”,要住进弄堂做真正的上海人,如《点绛唇》;有的是被生活空间挤压到无以复加,一心要离开弄堂的,如《初夜》。随着时间的推移,弄堂中的流动渐渐频繁起来,拆迁,进入新房,离婚生病。家庭是弄堂的构成,弄堂又成为了家庭的衍生,从弄堂里搬进搬出揭示着人物地位变迁、荣辱得失、命运沉浮。
一般普通人住的弄堂都以“里”来命名,内部的人员构成复杂,一个小阁楼里可以住到七八户人家,人们在狭小密集、拥挤嘈杂的弄堂里生活是透明的,身处其中,秘密是无处遁形的。家庭隐身于弄堂之中,弄堂空间的窄小拥塞,曲折拐弯,造就了特定的环境气氛,事无大小,全都要算得仔仔细细、妥妥贴贴。你来我往的人情似恰到好处不多不少的,细碎到馄饨是按只计算,这就是生活的艺术。弄堂生活看似简单,无外乎一日三餐,左邻右舍、鸡毛蒜皮、家长里短、喜怒哀乐,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弄堂的生活顿时就有了热气腾腾的感觉。
家庭与弄堂、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混杂,流言和隐私成为弄堂里的共同话题,弄堂的世界是一个“流言的世界(或者按照字面意思,‘漂流的词语’)。在一个如此沉迷私人生活,如此拒绝有意义的公众生活观念,如此凝神于世俗享乐的礼仪的矫揉造作的城市中,流言是上海居民交流和互相联系的媒介。实际上,由于缺乏发达的公共空间,他们拥有并且用以界定他们的社区和文化的正是流言蜚语”[7]。“它们可说是上海弄堂的精神性质的东西。上海的弄堂如果能够说话,说出来的一定是流言。它们是上海弄堂的思想,昼里夜里都在传播。”[4]流言以“家长里短”的形式成为弄堂日常的重要组成部分。闲言碎语、家长里短中既有俗世里的热闹与好奇,同时也有着被隐藏的关切与相濡以沫的亲昵。各种复杂的情绪构成了弄堂生活的基底,上海市井的智慧便在于这种现实之中。国家大事、社会变革固然重要,但其影响总要经过层层传递才会落实,只有身边这些触手可及的事情,才有生活气息,左右着生活的节奏与情绪。
弄堂里各道各处的灶头间、后门口、晒台上、弄堂拐弯抹角处,七嘴八舌地打听,以此消耗时光。在这些家长里短的叙述中,市井生活姿态真实显现,小市民的好奇心理浮现在人们的面前,结局在大幕揭晓前才最有吸引力。于是,大家耐心地等待着下一个流言的诞生。流言并不仅仅只是待在弄堂里面,随着空间的转移,也悄无声息地转移到工人新村中,弄堂里的人们即使集体搬迁了,但依然维系着彼此之间的联系和默契。张怡微在《你所不知道的夜晚》中将弄堂里的生活移植到了新村之中,除了空间位置的变化,家庭生活似乎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张家姆妈、黄家伯伯、苏州阿婆,新村里人与人的称呼依然保留着弄堂的习惯,公共厨房的空间格局使得女人们在淘米拣菜时,依然保持着闲言碎语的生活日常。
流言常常是和女性相关的。女性是上海家庭的主心骨,也是弄堂的主角,每条弄堂里面都有自己的弄堂之花,她们身上具有鲜明的文化的烙印,成为弄堂文化景观的亮色和传奇。王琦瑶、大妹妹、梅瑞莫不如此。她们或大起大落、今昔对比,或是安稳度日,相夫教子,无论怎样变化,都有着市井弄堂的文化底色与心理结构。人物间关系的亲疏、相互之间的分分合合,似乎极少有什么实质性的利害冲突或者是非恩怨在起作用。可能是今天多用了一点酱油,也或者是说者无心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但在平凡得几乎会忽略过去的现象背后,是邻里之间不惊心动魄却意味深长的生存较量,是一种只有内行才明白的委婉曲折对比。这是特定的历史和地域环境中的文化传统和教育才形成的相应的价值尺度、知识结构和心理动机体系。它一旦形成就深沉、隐蔽而稳固地起作用。这些人物或可恶、或自私、或懦弱、或善良,但是市井中成长的小家碧玉都有着浓浓的地域色彩。张怡微说:“故事很不新鲜,说的是上海,又仿佛是上海的背面——一个眼看着‘上海’生活的小圈子。有平淡的流逝,也有流逝中的五味杂陈。这种感觉就仿佛觉得日子好像是过不完的,遥遥无期,明天是今天的延续。”[8]1-2
弄堂的历史就是城市发展的历史,看似安静的弄堂其实波涛汹涌,家家都在较劲挣扎,每个家庭的曲折起落、兴衰散合成为弄堂的背景,家庭的变化敏锐地反映出社会整体的动荡、转型,与城市走过的历程相通,导致人物家庭离合变化的社会因素,同样左右着城市的变迁。一个人物,一个家庭,一条弄堂的兴衰,就是这个城市,这个社会的历史缩影。弄堂里的历史叙事和生活细节是个体的历史,通过微观的视角,讲述个人或特殊群体“不可复制的时代体验、生命经历和面对历史时的姿态,展现小人物的命运在历史洪流中的跌宕沉浮,使文字涉及的历史同时能成为个人心灵的历史”[9]。生活的世界是普通民众社会实践的追求意义,市井文化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世界中滋长与完善。市井生活内蕴的反本质主义,是通过异质并存、藏污纳垢的空间构造实现的。它甚至不单纯是一种一心过日子的平民态度,市井生活的文化逻辑恰恰在于并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资源能够独掌局面。那些“流言”与焦躁既是生活中最具生命力的事物,也让弄堂染上了感性色彩,具备了生命的温度,凝结成了复杂微妙的情感。
三、情欲浮动:市井小说中的情感形式
狭小的居住空间是家庭的隐痛。1981年《上海文学》发表了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描绘了一家人因为生存空间的挤压所产生的纠纷。在想象弄堂美好生活的同时,对于生存空间的焦虑弥漫着整个时代,叶辛的《孽债》、夏商的《东岸纪事》、周嘉宁的《天空晴朗朗》,对这样的居住环境有过真实的描绘。在弄堂的想象之下,并非都是琐屑精致,更多的时候,内部的生活与空间是局促与窘迫的。空间的拓展是对于人的重新解放。家庭具有不同于公共领域的经济和道德标准,象征着安全、和睦、舒适与温暖。“家”的独立代表着“独立时代”“自由也现代”“后上海主义生活”,甚至是海德格尔式的“人,诗意地居住”[10]。“家”的空间开始施展力量,它成为家庭为之奋斗的目标,塑造着家庭内部关系。幸福与位置有关,幸福与面积有关,婚姻与空间的捆绑更为密切。家庭,它的使命、目标、原则,都紧紧地缠绕着空间展开。
石库门中亭子间体现了市井生活中对于空间运用的极致,在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挑高两米,六七平方,也能搭出一片小天地,另有乾坤。亭子间是城市边缘人的栖身之处,三教九流,艺术家、诗人、卖艺者乃至风月人物,演绎着各自不同的生活。梁实秋在《住一楼一底房的悲哀》说:“别看一楼一底,这期间还有不少的曲折。”程乃珊的《亭子间》里住着一位“布满白癜风的老妇,一口的糯苏州话,手上香烟不离”;周天籁的《亭子间嫂嫂》是影响最大的“亭子间”之一,这部小说在《东方日报》上刊载,风靡一时。弄堂成为海派文化的图腾,“无数信息密码都藏在亭子间里”。
王安忆的《文革轶事》写于1993年。这篇小说虽然用了“文革”这样刺眼的名字,但那场浩劫却只是提供了人物活动的背景。张思叶家颇有根基,可父亲被关进牛棚,哥哥从文员贬为三班倒的工人,一个姐姐划清界限去了外地,平日在家里活动的都是女人:张思叶、嫂子胡迪菁、胡迪菁的两个女儿大妹小妹、大学毕业前途无着的张思蕊,还有一个很少出场的母亲。一家人住在一栋三层小楼上,但是第二层被贴了封条,居住空间不免紧张,会客吃饭全靠一个亭子间。这家人生活的变化,从工人赵志国与张思叶结婚做了上门女婿开始。赵志国相貌堂堂,却是工薪家庭出身,无钱买房,只能栖身张家。张思叶长相一般,毕竟是大家小姐,难得她放下架子,对赵志国一往情深,但后者似乎总提不起精神,倒是与同是小户人家出身的嫂子胡迪菁颇有默契。一家人常在亭子间相聚,甚至自办舞会,竟也其乐融融。赵志国被簇拥于一群女人之间,难免有贾宝玉的感觉,但是也有意料之中的麻烦,正处于人生困惑期的张思蕊偷偷地爱上了他。张思叶被安排到安徽农场劳动,赵志国不得不直面张思蕊满含哀怨的进攻,种种窘况中,他与胡迪菁产生了微妙的情愫。张思蕊一气之下去了东北,胡迪菁也拒绝了赵志国的苦恋。张父从牛棚放出,二楼被封的房子还给张家,张思叶也从安徽回到上海,一家人眼看苦尽甘来,却因为房间分配问题发生纠纷。胡迪菁为抢得主动,将偷藏的张思蕊的情书交给张思叶。绝望的张思叶决定去外地工作,而遭到背叛的赵志国也心灰意懒,夫妻俩痛哭一场,一起离开。
从以上故事梗概,便知王安忆有意演绎政治身份的微妙冲突。表面看来,一切都因为“文革”,“他们彼此都受到了欺负,这欺负是深到骨头里去,痛到心肺里去”[11]500。只有“文革”这场浩劫能解释这种无缘由的伤害。但是亭子间所发生的一切,又似乎有浩劫不能直接解释的地方。赵志国与胡迪菁分明是两个外来人,因为有这层身份认同,彼此有一种莫名的同情,但也正因为同是外来人,又不免暗自较劲。他们是亭子间的主宰者,在这个既逼仄又开放,最具生活气息的空间里,他们挑起话题,活跃气氛,留心观察,试图掌控一切。他们对上海包括那个摩登的、浮华的老上海如数家珍(虽然有些只是道听途说),将那种布尔乔亚式的怀旧气氛带入了亭子间。但是这种气氛只是幻影,一旦开始生存条件的争夺,亭子间的浪漫与温情便荡然无存。对于这一点,胡迪菁看得最明白。早在亭子间的“派对”如火如荼之际,她便察觉到一种危险,亭子间变得越来越重要,与她的人生都有了联系,这是凡事都带着目的的她所不能接受的。
亭子间里的聚会是一个安慰,也是一个发泄,并且已成为一个固定的日程,没有它每天下午干什么呢?午后的时间漫长而愁闷。自从来了个赵志国,这聚会的意义就远不止这些了。胡迪菁对自己说,事情和原先一样,没有任何改变。可她越对自己说,自己就越不相信。胡迪菁的世故与精明,加上她涉猎各类戏文和好莱坞情话,使她对人情世事具有极强的预知能力,事情还未发生就好像已在她眼前演过。有时候,这些画面还会出现在她的梦境里,真的一样,她不由惊出一身冷汗。[11]447
这种亭子间的“派对”是上海市井文化饶有风情的一面,它能够很自然地被解读为一种生气勃勃的民间精神,一种在逆境中仍能保持精致生活的乐观态度。当然,如果持批判的态度,也可以将之划入“上海怀旧”的范畴。但这显然不是王安忆的意图所在。这个小小的亭子间,同时展示了诱惑与危险。它既是标示地位的正房之外的飞地,又最终跳不出提防与算计;它既让人享受平等的幻觉,却又随时激发身份的冲突;它既滋养了日常生活,又破坏了它。胡迪菁完全不能允许自己被亭子间的温情收买,她比赵志国要彻底得多。后者确实有种贾宝玉似的悲凉心态,他时时刻刻觉得自己是个外人(而且是“逆袭”的外人),他对妻子的冷淡,与其说是厌恶妻子本人,不如说是厌恶自己的外人身份。亭子间是能够让他如鱼得水的地方,但是他在亭子间爱上了出身相当的胡迪菁,却似乎他之所以享受这个地方,可能还是因为它是某种“外”。那些在大房间里出生的女儿们不懂得珍惜,她们看待自己的心比看待这个城市要重得多,她们纷纷离去,或是因为爱,或是因为恨。她们还没有真正进入日常生活,她们在亭子间的幽怨,表明她们并不理解亭子间那种狂欢化的气氛。只有两个外人能够主宰这亭子间,他们似乎更配得上这三层小楼——但是,他们越是能够主宰亭子间,就越是表明自己不属于这三层小楼,因为这种主宰所依靠的生存智慧,这栋楼里的人本不需要。亭子间只是人们落拓时的栖身之所,当一切恢复秩序时,他们应该远离它,只有当他们占据了二楼朝南的大房间时,才算是在上海站稳了脚跟,才算是把生活攥在自己手里。上海市井生活最幽深的一种面相,就从这内与外的辨证中渐次展开。
家庭是安居的意象,“向往拥有一个温暖安定的家庭,爱情是幸福,是生活的主流,是产生力量的源泉”[12]189。当代上海市井小说中的家庭叙事内蕴着现代人不安稳的体验,流动与迁徙始终蕴含于其中。家庭是对城市变迁的顺应和抵抗,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市扩张,大量的人群涌入城市,丰富了城市的构成;另一方面,这种扩张以及伴随而来的城市变革,又使居民的安定感日益稀薄。这使得家庭叙事总是以一种动荡的景观出场。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固然令人神往,而身居其中的人们每日感受不间断的拆除、重整、新建、融入与分离,喧嚣就在安居之中。我们可以将家庭叙事视为一种后退之中的涌出,不断被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逼退,却又总是在这种变化暂停的瞬间涌现出来。它本身又始终在寻求确定的空间。
在市井小说之中,家庭成为个体观照城市的视角,在城市的发展之中,有的家庭呈现出因变化缓慢而日益凸显的衰败景象,更多的是因变化太快而不断扩大的情感空洞。家庭叙事提供的是将城市的物理和社会的层面通过文学文本的形式呈现,寻求以文学之眼来观看社会,在这种表达与叙述中,赋予城市“想象”的意义。而在这想象之中,“市井”的一面始终作为城市地域性的灵魂与根基存在。但是另一方面,上海的文学叙述不应该也不可能仅仅停留在上海的海派想象中裹足不前。这一面向始终与现代化的城市想象相伴随,既推动着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又填补着城市文化的空间。
[1]杨扬.兴废之际——2007年的上海文学[M]//浮光与掠影:新世纪以来的上海文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2] 钱谷融.代序:对人的信心,对诗意的追求[M]//钱谷融论文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 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4] 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5] 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6] 孙侃.上海之刺[J].上海文学,2012(4):75-82.
[7] 张旭东.现代性的寓言:王安忆与上海怀旧[J].中国学术,2000(3):122-161.
[8] 张怡微.你所不知道的夜晚[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9] 谢有顺,周会凌.历史碎片中的生命凝思——读袁敏的《重返1976》[J].文艺争鸣,2010(15):98-102.
[10]王晓明.从建筑到广告——最近十五年上海城市空间的变化[G].热风学术:第一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1] 王安忆.文革轶事[M]//王安忆自选集之三:香港的情与爱.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12] 陈祖恩,叶斌,李天纲,等.上海通史·当代政治[M]//熊月之.上海通史:第1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郑宗荣)
①张济顺在《论上海里弄》(《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382)指出,里弄中的社会生活功能的健全其实是社会生态不平衡的表现。弄堂中固然提供了较为便捷的消费生活,但这种低层次的水平更多地加剧了逐小利、短视的市井生态。
On Family Narratives of Contemporary Shanghai Marketplace Novels: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ZHANG Yanhong
In a marketplace novel, individuals or special groups enter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space and show the experience in a specific living space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The vivid, real and specific, shown in the details which are not reproduced, are different from grand narratives. The family narratives and the details of life in the alley are the history of the individual. Life scenes, gossip, and emotional forms in the alleys are the most vital things in the streets of Shanghai, bringing emotional colors and temperature of life to the city.
marketplace family; alley; gossip; Emotional narratives
I206.7
A
1009-8135(2017)05-0083-06
2017-06-22
张艳虹(1979—),女,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