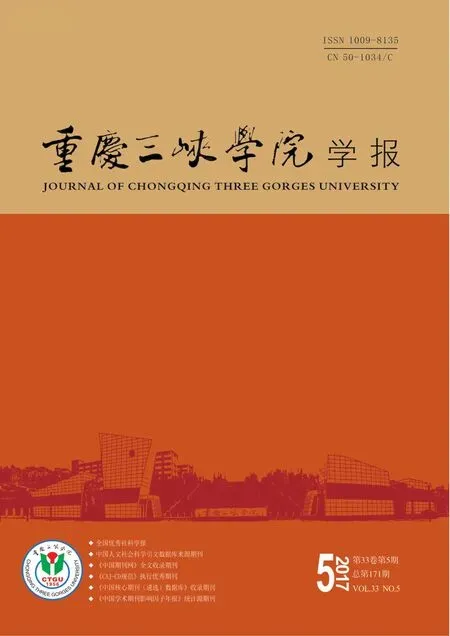论白居易谪居忠州期间的人生心态
李 俊 滕 峥
论白居易谪居忠州期间的人生心态
李 俊 滕 峥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重庆 404020)
白居易在忠州刺史任上,堪称勤于政事,但对于一向“外服儒风”有更大政治抱负的诗人来说,仍有沦落天涯的弃掷感;白居易忠州期间种树栽花之举,可视为诗人在遭遇现实挤压之后对“内宗梵行”人生理念的践行;此间的饮酒、优游之举,其实也是诗人超越眼前苦难、避祸全身的人生策略。
政事治理;种树栽花;饮酒优游;儒风;梵行;人生心态
陆游论及白居易谪居忠州一事,以“可怜”二字概括之。其《老学庵笔记》云:“忠州在峡路,与万州最号穷陋,岂复有为郡之乐?白乐天诗乃云:‘唯有绿樽红烛下,暂时不似在忠州。’又云:‘今夜酒醺罗绮暖,被君融尽玉壶冰。’以今观之,忠州那得此光景耶?当是不堪司马闲冷,骤易刺史,故亦见其乐尔。可怜哉!”[1]68
与陆游不同,黄庭坚则直言白居易忠州之任为“最暇豫有声”,其《四贤阁记》说:“乐天由江州司马除刺史,为稍迁,故为郡最暇豫有声耳”[2]2。
有“可怜”“暇豫”等说法,可见白居易刺史忠州期间复杂的人生心态。
一、“天教抛掷在深山”——白居易忠州政事治理与人生心态
从治绩上来看,白居易应该算得上勤于政事。其《征秋税毕题郡南亭》《代州民问》《答州民》《早祭风伯因怀李十一舍人》等诗便相关政事。按《新唐书》载,忠州为下等之州,人口稀少,政事简松,民风亦淳朴,所以治理起来颇为轻松。《征秋税毕题郡南亭》便是这样一首描写诗人轻松理政的诗,诗曰:“且喜赋敛毕,幸闻闾井安。岂伊循良化,赖此丰登年。案牍既简少,池馆亦情闲。秋雨檐果落,夕钟林鸟远。南亭日潇洒,偃卧恣疏顽。”[3]878-879尽管政务简松,得心应手,但白居易并没有因此掉以轻心,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代州民问》曰:“官职家乡都忘却,谁人会得使君心?”《答州民》也说:“宦情斗擞随尘去,乡思销磨逐日无。”所以,尽管贬官低微,并兼乡思沉重,但白居易总是想多为百姓做一些有益的事情,“龙昌寺底开山路,巴子台前种柳林”(《代州民问》)。“唯拟腾腾作闲事,遮渠不道使君愚。”(《答州民》)[3]1476《早祭风伯因怀李十一舍人》一诗则写了自己一大早便遵循朝廷的典章制度祭祀风神、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之事,其诗曰:“远郡虽褊陋,时祀奉朝经。夙兴祭风伯,天气晓冥冥。导骑与从吏,引我出东坰。”[3]862而《东坡种花二首》之二则将种花种树与治理州郡的经验相联系,其诗曰:“养树既如此,养民亦何殊?将欲茂枝叶,必先救根株。云何救根株?劝农均赋租。云何茂枝叶?省事宽刑书。移此为郡政,庶几氓俗苏。”[3]870尽管州小事疏,但白居易的治理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初到忠州赠李六(景俭)》一诗备言这种困难:此地之中,吏人桀骜、奸猾,“吏人生梗都如鹿”;市井狭小,“市井疏芜只抵村”;绝少平地,交通不便,“一只兰船当驿路,百层石磴上州门”,“更无平地堪行处,虚受朱轮五马恩”[3]1432。另外,还有语言上的不通,“安可施政教,尚不通语言”(《征秋税毕题郡南亭》)[3]878。
虽说刺史忠州,已然处江湖之远,但较之无所事事居于闲散职务的江州司马来说,毕竟还能事实上专治一郡,也当视为实现其“治平”理想的一个有效途径。但对于“外宗儒风”“欲以生平所贮,仰酬恩造”的白居易来说,忠州之地还是备显偏远、蛮荒,如《初到忠州登东楼寄万州杨八(归厚)使君》所说:“山束邑居窄,峡牵气候偏。林峦少平地,雾雨多阴天。隐隐煮盐火,漠漠烧畬烟。”虽然“我怀巴东守”,但这并非“本是关西贤”的诗人施展政治抱负的地方。有此一念,故类似“平生已不浅,流落重相怜。水梗漂万里,笼禽囚五年”[3]849诗句中表达的流落、漂泊、羁縻之感便贯穿于整个忠州刺史任上。其在忠州所作《京使回累得南省诸公书因以长句诗寄谢萧五(佑)刘二元八(宗简)吴十一(上矩)韦大(处厚)陆郎中崔二十二(韶)牛二(僧孺)李七(宗闵)庾三十二(敬休)李六(景俭)李十(渤)杨三(嗣复)樊大(宗师)杨十二(巨源)员外》《冬至夜》等诗也表达了这种被弃掷而生发的流落、漂泊感受。前者谓:“雪压泥埋未死身,每劳存问愧交亲。浮萍飘泊三千里,列宿参差十五人。禁月落时君待漏,畬烟深处我行春。瘴乡得老犹为幸,岂敢伤嗟白发新。”[3]1439后者曰:“老去襟怀常濩落,病来须鬓转苍浪。心灰不及炉中火,鬓雪多于砌下霜。三峡南宾城最远,一年冬至夜偏长。今宵始觉房栊冷,坐索寒衣䛏孟光。”[3]1461表达类似情感的诗还有《木莲树……三绝句云》,其三有句“天教抛掷在深山”[3]4917,盖因此句深刻抒写了那个时代遭遇贬谪命运官宦的弃掷感,所以,竟然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共鸣,故“咸传于都下,好事者喧然模写”[4]4352。
白居易谪居忠州期间的漂泊、羁縻、流落等诸多悲凉感受,当视为他虽处江湖之远,却不改初衷地对于理想人格的执着坚守,如《新唐书》所说:“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5]4353但久处逆境,白居易并非一味愤懑于当世,而是适时调节心情以自洽于当下,然后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这种调适自洽以待来日的心态,其实在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被贬江州时便已然产生了。其《与元九书》云:“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6]326故较之柳宗元、刘禹锡等,白居易显然更善于调适自己的心情以超越眼前的悲苦,亦如《新唐书》所说:“居易被遇宪宗时,事无不言,湔剔抉摩,多见听可,然为当路所忌,遂摈斥,所蕴不能施,乃放意文酒……暮节惑浮屠道尤甚。”[5]4304写诗、饮酒,乃至种花、种树,既而赏花、优游、唱答并深谙于佛理,当是白居易超越眼前悲苦的有效途径。故其忠州所作诗歌,关于饮酒、种花、赏花、种树、佛理之篇多矣。
二、“种杏栽桃拟待花”——白居易忠州赏花弄树与人生心态
白居易谪居蛮荒之中,之所以表现出更多赏花弄树雅兴并因此有诗记其事,除开老庄思想(如白居易《君子不器赋》所言:“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6]68)的影响外,更重要的便是佛家思想使然。尽管白居易对于唐代僧徒日众、佛寺日多以至于影响到社会生产颇有微词,但白居易还是颇重视佛家学说对于辅助王化、净化社会风气、养成个人修为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故其元和初年所作《策林》第六十七条说佛教:“大抵以禅定为根,以慈忍为本,以报应为枝,以斋戒为业。夫然,亦可以诱掖人心,辅助王化。”[6]1589《策林》第十一条也说:“夫欲使人情俭朴,时俗清和,莫先于体黄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宽简,务俭素,不眩聪察,不役智能而已。”[6]1380基于上述认识,对于白居易来说,佛家理义便不惟一种认识宇宙人生的全新途径,更是一种人生态度,或者根本就是一种人生实践方式,所以白居易在元和七年所作《和梦游春诗一百韵》中宣称自己“外服儒风,内宗梵行”[3]1130。故当白居易来到忠州之后,虽倍感“天教抛掷在深山”的痛苦,却懂得借助平生信奉的释、老思想调节自己的人生与心情,以期超越苦难,再待来日。因此,其忠州所著诗歌中,便不乏关于信佛、礼佛题材的作品。《和李澧州题韦开州经藏诗》曰:“既悟莲花藏,须遗贝叶书。菩提无处所,文字本空虚。观指非知月,忘筌是得鱼。闻君登彼岸,舍筏复如何?”[3]1448不拘于形式,不拘于文字,亦不拘于现实的种种苦难,并从这种苦难中超越出来,方能得到自在的人生。至于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放下的人生态度,对此,白居易忠州诗另有一首《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韵多叙贬官已来出处之意》说得非常明白,诗曰:“谏诤知无补,迁移分所当。不堪匡圣主,只合事空王。龙象投新社,鹓鸾失故行。沈吟辞北阙,诱引向西方。便住双林寺,仍开一草堂。平治行道路,安置坐禅床。”正是因为现实中谏诤无门,匡扶圣主无路,“外服儒风”的人生取向行不通,故只有改弦易辙“内宗梵行”,这才有了白居易心宗西方佛教祖庭,结堂当地双林寺之举,故此诗又说:“唯拟捐尘事,将何答宠光?有期追永远(晋时永、远二法师,曾居此寺),无政继龚黄。”[3]1433-1434谪居忠州期间,白居易造访的寺庙还有开元寺,《留题开元寺上方》即写了自己多次往来其中、流连忘返之事。诗曰:“东寺台阁好,上方风景清。数来犹未厌,长别岂无情?恋水多临坐,辞花剩绕行。最怜新岸柳,手种未全成。”[3]1481
佛教是一个非常重视自然的宗教,不仅自然界中诸多的山川河流、花草树木是佛教教义体系中重要的象征意象,而且自然界也是佛教徒悟道证性的重要场所。所以,经常见到建立在山林之中体现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佛教寺庙,也听闻过佛陀菩提树下修行的相关经历,以及以心传心拈花微笑的布道方式。总之,如佛教主张的“大地众生,皆有佛性”“情与无情,同圆种智”一样,在佛家教义之中,一花一木皆有佛性,山山水水都可体性,所以亲近自然,皈依自然,优游于山水,寄情于草木,不惟可以借天地灵气洗涤胸中抑郁,而且可以超越现实苦难。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白居易谪居忠州之时为何偏好种花植树,就有理可循了。其《种桃杏》曰:“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路远谁能念乡曲,年深兼欲忘京华。忠州且作三年计,种杏栽桃拟待花。”[3]1443诗歌之中,海角、天涯与乡曲、京华相对呈现,前者是谪居的现实,后者是基于“外服儒风”理念的人生理想,当理念被现实摧毁,理想被现实挤压,只能谪居僻荒之后,白居易为自己作了一个贬谪忠州三年的打算。三年之中,其欲为之事不是悲天怆地的呼号与沉沦,也不是做无谓的挣扎,而是“种杏栽桃拟待花”。种杏栽桃之谓,即亲近自然,皈依自然,从而用“心安”来超越眼前的苦难。白居易是这样计划的,而且也是这样实践的。尽管他在忠州并没有呆到三年,但栽花种树之事却并没落下,《喜山石榴花开(去年自庐山移来)》诗曰:“忠州州里今日花,庐山山头去年树。已怜根损斩新栽,还喜花开依旧数。”[3]1472又有《东坡种花》诗,先写买树苗、花种,继而种之,“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杏梅”。也写花开之后置身鲜花丛中的怡然自得:“花枝荫我头,花蕊落我怀。独酌复独咏,不觉月平西。巴俗不爱花,竟春无人来。唯此醉太守,尽日不能回。”还写自己修理花圃:“每日领僮仆,荷锄仍决渠。剗土壅其本,引泉溉其枯。”[3]869-870也有《东涧种柳》诗云:“野性爱栽植,植柳水中坻。乘春持斧斫,裁截而树之……富贵本非望,功名须待时。不种东溪柳,端坐欲何为?”[3]876-877种柳东涧,正是诗人体性于物,超越现实悲苦的举动。白居易不仅自己种树栽花,也喜欢漫步忠州山野之间,观花赏树,自得其乐,因此有《桐花》《木莲树三绝句》《画木莲花图寄元郎中》《别桥上竹》等诗。除诗歌之外,白居易另有流传广远、脍炙人口的散文《荔枝图序》。
白居易忠州期间的种花栽木,赏花弄树,从个人意趣上讲,正是其现实人生遭到挤压之后亲近自然、皈依自然践行“内宗梵行”人生理念的具体体现。当然,白居易之咏花,不惟关于遭遇逆境之后更加笃信的佛家教义,从白居易与笔下鲜花之间吟咏主体与吟咏对象这一主客体关系的构成上来看,花之自开自落,树之春荣冬枯,亦与白居易遭遇贬谪不幸之后的落寞寡合、自惬自洽情怀相关。另外,白氏钟情于桐花木莲、翠竹荔枝,一方面乃地理固然,如《荔枝图序》所说“荔枝生巴峡”,为白居易所历他处无有之物;木莲花亦然,“生巴峡山谷间,巴民亦呼为黄心树。大者高五丈,涉冬不凋。身如青杨,有白文,叶如桂厚大”[6]369-370(《木莲花诗序》)。虽然白居易家乡也有桐花,但家乡的桐花却与巴峡桐花大不相同,在白居易家乡新郑,“春令有常候,清明桐始发”,而巴峡“桐花开十月”[3]861(《桐花》)。所以,白居易之咏荔枝、木莲、桐花者,应该有异地风物的新奇心情在内。另一方面,白氏之咏花木,当与中唐时期审美意趣的转向亦且有关。中唐是盛唐衰败的直接产物,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转折点,这之后的中国古代社会,由汉人主导的开拓进取、大气磅礴的宏大业绩与气象几近于无。这也导致了民族审美旨趣发生了转折,盛唐文学中那种恢宏的气势、宏富的辞章,渐次被精致小巧、色彩淡雅所代替,包括白居易忠州有关花木的诗歌正是这种美学风潮变迁的产物。
三、“闷取藤枝引酒尝”——白居易忠州饮酒优游与人生心态
除了钟情于自然及自然中的花草树木,白居易在忠州调适自己心情的另一途径则是喝酒、优游[7]。白居易晚年归居洛下,曾经写有《醉吟先生传》一文,内中说自己“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并言自己在“醉吟相仍若循环然”状态中,“繇是得以梦身世,云富贵,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古所谓得全于酒者”[6]1981,1983。白居易此语,说明饮酒有两个目的,其一是迷醉自己,以超脱相关于身世、富贵的诸多人生烦忧与苦难;其二则是避祸全身的目的,所谓“得全”是也。其实以饮酒方式避祸,古已有之,故叶梦得说:“晋人多言饮酒有至于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唯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流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饮者未必剧饮,酣者未必真醉也。”[8]434-435对照《醉吟先生传》中白居易关于自己为何饮酒的说辞、忠州期间执着于栽花种树以及分寄荔枝、胡麻饼给万州刺史杨归厚这样的小事来看,白居易此间的自洽自适还是卓有成效的。
不过,毕竟其人生理念是“外服儒风,内宗梵行”,梵行、儒风的矛盾还是必然存在的,有此矛盾,故有“天教抛掷在深山”的悲愤。但对于有过直言诤谏、忤怒人君并终为宵小诽谤贬谪天涯人生经历的白居易来说,专注于悲愤,不仅对身体的健康没有任何好处,而且悲愤之下的不当言行也极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其危险性甚至大于阮籍、嵇康们所处的时代,因为较之西晋司马氏打击异己较为单一的政治恐怖,掺杂了朋党之争、藩镇割据、宦官乱政等各种要素在内的中唐政局则更为诡谲多变,更为复杂危险。以白居易当时正谪居其间的忠州为例,先后有过刘晏受诏就死以及裴延龄布局李吉甫复仇陆贽的事件。对于有过遭人怨谤并正处贬谪生涯的白居易来说,他知道在险恶的政治背景中即使是些微的言行不周,便可能引火烧身。《蚊蟆》喻指这个道理,诗曰:“斯物颇微细,中人初甚轻。如有肤受谮,久则疮痏成……么虫何足道,潜喻儆人情。”[3]879谨言慎行、避祸全身便是最好的选择,所以诸如赏花、优游、喝酒等便是公余的消遣方式,也是其避祸全身、超越现实苦难的有效途径。
除赏花、喜树等相关题材诗歌之外,白居易忠州任上也不乏饮酒、优游的诗歌。其《东楼醉》诗曰:“天涯深峡无人地,岁暮穷阴欲夜天。不向东楼时一醉,如何拟过二三年?”[3]1459治地僻远蛮荒,人稀事少,并非自己理想的政治舞台,郁积不能发,唯有以醉打发时光,其《招萧处士》曰:“东郊萧处士,聊可与开眉。能饮满杯酒,善饮长句诗。”[3]856在“所逢非所思”的峡内,公务之余,招不求闻达、自处自怡的萧处士,对饮联吟,可看出诗人面对苦难处境、黑暗现实的自洽情怀。另有《花下对酒二首》之二曰:“况吾头半白,把镜非不见。何必花下杯,更待他人劝。”[3]863忠州之中,蹉跎岁月,也见郁积,故自醉以解忧。又《东楼招客夜饮》曰:“莫辞数数醉东楼,除醉无因破得愁。唯有绿樽红烛下,暂时不似在忠州。”[3]1460谪居忠州非白居易所期,又不便牢骚太盛,于是只有绿樽红烛之下,寻醉而已。
白居易忠州寻醉,较之他处,也别有一番地域风情在里边。《郡中春宴因赠诸客》曰:“薰草席铺座,藤枝酒注樽。中庭无平地,高下随所陈。蛮鼓声坎坎,巴女舞蹲蹲。使君居上头,掩口语众宾。”[3]873《春至》曰:“闲拈蕉叶题诗咏,闷取藤枝引酒尝。”[3]1467《三月三日》曰:“画堂三月初三日,絮扑窗纱燕拂檐。莲子数杯尝冷酒,柘枝一曲试春衫。”[3]2504《九日登巴台》曰:“黍香酒初熟,菊暖花未开。闲听竹枝曲,浅酌茱萸杯。”[3]859首先从饮酒的方式上看,采用了忠州之地特有的“咂酒”法,上述诗中“藤枝”“柘枝”即此之谓也。所谓咂酒,按《忠州直隶州志》记载:“咂酒以稻谷粟米和曲药贮瓦坛内酿酒,逾月馨香,不可名状,以竹管插坛内,沃热水泡之,饮者呼吸承之以管……此酒即郫筒酒之遗。”按白居易诗来看,喝酒的管子并非竹管,而是“藤枝”“柘枝”,藤为引藤,引藤“产引藤山,大如指,中空,可吸酒”[9]60-61。其次,佐酒的果品、物什也极具三峡地域特色。其《荔枝楼对酒》曰:“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欲摘一枝倾一盏,西楼无客共谁尝?”[3]1477按白居易《荔枝图序》曰:“荔枝生巴峡间,树形团团如帷盖……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6]364-365荔枝本为气候暖和的巴峡以及岭南等地所特有之物,为气候相对寒冷的北方所无,兼之保鲜时间短,故非帝王之家,对居于长安中的其他各色人等,吃上荔枝,近乎奢望。杜牧《过华清宫》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即云此。贬谪忠州,本来为白居易之不幸,但亲临忠州,其荔枝楼中佐酒之物可为荔枝,却是白居易之幸了。
另外,白居易忠州饮酒,也多有流行此间的巴渝舞与竹枝词助兴,所谓“蛮鼓声坎坎,巴女舞蹲蹲”(《郡中春宴因赠诸客》)[3]1467,“楚袖萧条舞,巴弦趣数弹”(《留北客》)[3]1451。所谓“巴童巫女竹枝歌,懊恼何人怨恨多”(《听竹枝赠李侍御》)[3]1445,“蕃草席铺枫叶岸,《竹枝》歌送菊花杯”(《九日题涂溪》)[3]1449。本地流行的竹枝词甚至也影响了白居易的创作,白氏流传至今的诗歌中,便有专以《竹枝词》为题的诗歌四首。只不过,流淌在白居易《竹枝词》中的仍然是谪居此间难以排遣的愁绪与哀怨,所谓“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3]1463。
余 论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无论是白居易忠州刺史任上的政事治理,还是公务之余的种花植树、礼佛赋诗、饮酒优游诸事,在表面的超越之下,到底还是多了一些哀怨。这种哀怨,究其根本,基于其“外服儒风”的人生理念对比于贬谪蛮荒的现实使然。由此看来,尽管在人生走向低谷之时,基于“内宗梵行”理念的饮酒、优游、赏花植树到底还是败北于内心儒风的蠕动、滋长。所以,尽管如《岁晚》诗所说:“去国固非乐,归乡未必欢。何须自生苦,舍易求其难?”[3]883但当其与兄弟白行简登临郡之南山时,想到的却是遥远的长安边上的骊山。《和行简望郡南山》曰:“反照前山云树明,从君苦道似华清。试听肠断巴猿叫,早晚骊山有此声?”[3]1456所以当宪宗暴亡的消息传来,白居易竟然深为悲戚,其《奉酬李相公见示绝句》云:“碧油幢下捧新诗,荣贱虽殊共一悲。涕泪满襟君莫怪,甘泉侍从最多时。”[3]1471白居易悲宪宗之崩,确有源自真心的痛楚,因为当年正是宪宗皇帝将其擢升为翰林学士的,所以对于白居易来说,宪宗对他有知遇之恩。不过,白居易之悲,也未必没有一己之私的打算,因为他本来打算忠州三年量移期满,能够依制被先前慧眼识他的唐宪宗重新召回京城的,但唐宪宗一日归西,自己重回天子脚下也将变得遥遥无期了。
令白居易没有想到的是,穆宗即位之后,元和十四年(819)冬,便传来自己被召回京城并拜司门员外郎的消息。当此之时,白居易喜不自胜,作《初除尚书郎脱刺史绯》诗云:“亲宾相贺问何如,服色恩光尽反初。头白喜抛黄草峡,眼明惊拆紫泥书。”[3]1480不过,当其真的要离开忠州时,却有了诸多不舍。《别种东坡花树两绝》云:“二年留滞在江城,草树禽鱼尽有情。”[3]1482《留题开元寺上方》亦云:“数来尤未厌,长别岂无情。恋水多临坐,辞花剩绕行。”[3]1481离开忠州之后,白居易依然恋恋不舍。《发白狗峡次黄牛峡登高寺却望忠州》云:“北归虽引领,南望亦回头……时时大开口,自笑忆忠州。”[3]1483在诸多不舍之中,白居易离开了忠州,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京城。
[1]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M].李建雄,刘德权,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 吴友篪.忠州直隶州志:卷二[M].道光六年刻本.
[3]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 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 谢思炜.白居易文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7]陈婧.白居易的咏陶诗研究[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3(2):55-58+66.
[8] 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9] 吴友篪.忠州直隶州志:卷四[M].道光六年刻本.
(责任编辑:李朝平)
Research on the Life Attitude of Bai Juyi Exiled in Zhongzhou
LI Jun
When Bai Juyi was appointed the governor of Zhongzhou, he was absorbed in government affairs, but for a poet with greater political ambition, he also had a sense of being abandoned. He was getting interested in gardening when living in Zhongzhou,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an implement of his philosophy of life – Confucianism outside and Buddhism inside when he suffered oppression. His behaviours such as drinking, traveling were his life strategies so as to avoid sufferings and to preserve himself.
government affairs; gardening; drinking and traveling; Confucianism outside and Buddhism inside; life attitude
I022
A
1009-8135(2017)05-0008-06
2017-05-18
李 俊(1971—),男,重庆开州人,文学博士,重庆三峡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区域文学与文化。滕 峥(1992—),女,安徽当涂人,重庆三峡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重庆市社会科学基金博士项目“长江三峡文学地理研究”(2015BS10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