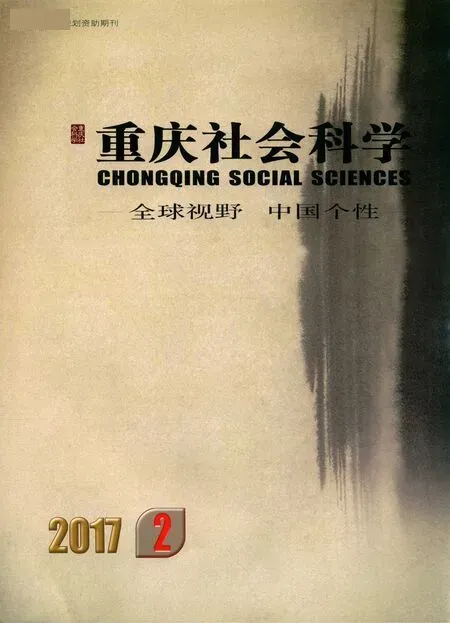文化集体记忆载体与变迁:自一个节庆分析*
赵 将 翟光勇
文化集体记忆载体与变迁:自一个节庆分析*
赵 将 翟光勇
集体记忆是凝聚民族共识和增强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凉山彝族火把节的记忆经历了口头传统、书面传统、影视记录等记忆载体的变迁。大众媒介通过重大事件的集中报道,在塑造、唤醒和保存彝族火把节集体记忆时处于核心地位。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解决新媒体传播带来的“数字化遗忘”和“碎片化”记忆,解决族群流散中的集体记忆危机,增强和重构彝族民族集体记忆,是人们需要面对和思考的课题。
历史文化 文化传承 凉山彝族火把节
涂尔干认为“集体欢腾”是人类社会文化创造和传承的“温床”,部落和族群在节日仪式、庆祝舞蹈时聚集在一起,是集体成员文化共享与记忆延续的有利时机。[1]但是在欢腾期以外的时间段,族群和部落的凝聚、认同靠什么维持?这是涂尔干理论的困境之处。涂尔干学派第二代成员、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把记忆研究从心理学领域引到社会学领域,创造性地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他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在一个社会中有多少群体和机构,就有多少集体记忆。”[2]从另一个维度来说,每个民族的集体记忆都需要得到在时空被界定的“同一民族”的支持。在族群内部,个体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中的位置来进行回忆,群体的集体记忆通过个体的记忆来唤醒和实现,并且在每个个体的记忆之中体现自身。
一、研究缘起:集体记忆框架下的火把节文化
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正是为了解决“涂尔干的理论困境”提出的。哈布瓦赫认为“存在于欢腾时期和日常生活时期之间的明显空白,事实上是由集体记忆填充和维持着的。这种集体记忆以各种典礼性、仪式性的英雄壮举的形式出现,并且在诗人和史诗性的诗歌中得到纪念,它们使记忆在除此之外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的常规实践中保持鲜活。”[3]集体记忆像是一个中介变量。一方面,民族通过节日庆典纪念那些对民族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另一方面,民族的集体记忆也被这些节日庆典所固化和强化。
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提到两种不同的社会实践,即体化实践和刻写实践。[4]民族节庆因其广泛的参与性和现场性是一种体化实践。在这种活动中,族群和部落成员只有亲身在场参与节庆具体活动,才能传达信息。凉山彝族火把节中的各种习俗活动是彝族民众集体记忆的结果。火把节在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前后举办,历时三天,分为“祭火、庆火、送火”三部分。在三天之中,彝族民众会穿着节日盛装,相约在火把广场举办选美、斗牛、斗羊、赛马、爬竿、朵洛荷、跳达体舞等活动,热闹非凡。火把节作为民族节庆文化,承载着彝族民众敬火尚火、祭祀祖先、祈求丰收、驱灾纳福的民本愿望和朴素理想。火把节是“眼睛”的节日,有“东方狂欢节”的美誉,是彝族最为盛大的民族节庆活动。而火也成为彝族人精神领域的文化象征符号,承载着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成为彝族团结和民族凝聚的力量之源。
地域性、周期性的节庆活动和独特仪式,是展示“火文化”、建构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和民族历史博物馆、文化遗迹、民族歌曲和文本记录一样,一个民族的文化和记忆只有经过这些载体才能继承和流传下来。诺拉形象地称这些文化载体为“记忆的场”。“一个民族如果缺乏共同记忆,必然无法建立深层次的认同和团结。这是每个民族都必然珍惜自己的共同历史传说或祖先故事的文化原因”。[5]在这种定期重复举办的节庆活动中,彝族民众既保持了与传统文化“记忆通道”的连续性,也借助集体记忆和共同历史保持着族群的凝聚和认同。
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是一种建构的概念,民族的过去和记忆主要由现实的关注所形塑,即“现在中心观”,也就是集体记忆的现实性。[6]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将民族定义为一种基于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民族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民族是被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不过民族成员彼此之间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7]彝族民众通过参与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民族共同记忆,将本民族的过去和现在“勾连”成绵延不绝的统一体,也在节庆活动中建构着“民族想象”和“身份坐标”。
二、历时性视角:火把节传播形式和记忆载体的发展与嬗变
集体记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其传承需要文化载体。而记忆方式和记忆载体的变化对记录功能有着本质的影响。本文通过历时性地考察彝族火把节的口头传统、书面传统、影像记录等传播载体和呈现形式,来透视民族节庆文化集体记忆的承载发展与嬗变。
(一)口头传统与记忆
媒介环境学派用四个特征鲜明的传播时代构想历史,它们分别是口语时代、书写时代、印刷时代、电子时代。口头传统的涵义鲜活而富有弹性,具有灵活性的特征。哈罗德·伊尼斯认为: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倚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8]而口头传统达到了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的理想境界。在利用民族主义方面,口语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它可以对更多的人发生作用,是一个更加有效的工具,文盲状况不再是严重的障碍。[9]
口头传统强调的是记忆和训练。[10]记忆术对口头传统的传播是必不可少的。[11]传统社会节庆集体记忆的传播主要依靠口头叙述和面对面的人际交流。口语传播使得集体记忆代代相传,言语的习俗则构成了集体记忆最基本、最稳定的框架。千百年来,彝族的历史总是以口头叙述的方式流传。火把节的传说也不例外。彝族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通过面对面的人际交流可以了解火把节的历史渊源和神话故事,也可以在世代口述中沿袭火把节的传统仪式和节日内涵。而在重大庆典时刻,人们共同走向火把场,这种集聚让更大范围的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成为可能。彝族民众亲身参与节日的经历成为彝族个体的“自传记忆”,加强了参与者之间的纽带联系。蓝天白云下,彝族的青年女子跳着优美的朵洛荷舞、唱着朵哈经;年轻的男子或在摔跤场上展示身手,或是在马背上飞速驰骋;富有才艺的彝族人在场上展示高亢的阿都高腔;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则通过“吟诵”的方式讲述着古老彝族的社会发展、历史变迁史。通过火把节的集聚,彝族群体成员的集体记忆被间接激发出来。一方面人们在一起分享信息、沟通情感,获得身体和心灵的愉悦;另一方面,通过既定的纪念仪式和庆祝活动,把彝族的文化观念、火把节的文化记忆传递给每一位彝族群众。年复一年的“仪式重演”对于塑造社群记忆,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口语传播的便利性对民族集体记忆来说是天然的优势,但口语记忆的天生缺陷是在人际传播间极易造成民族文化的 “结构性失忆”。在经意或不经意间,节庆文化的集体记忆产生“部分流失”。访谈中,阿力莫尔呷说:“其实,这个火把节原来的内涵,只有那些比较老的人才知道嘛。现在他们都不给那些青年人讲嘛。不给青年人讲这火把节的来源、这些火把节仪式有什么作用、它意味着什么。然后现在的青年人越来越不知道这个火把节是为什么过的。只知道点火把、杀鸡、吃鸡肉这些嘛。越来越不隆重了。”访谈中,青年人黄聪哈说:“我们现在因为要读书,有时候不会在家里。特别是在火把节传统知识这些方面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因为父母没跟我说,我也就不知道火把节的缘由。现在我们都大了,只知道去‘耍’。像我们这样的,对火把节的了解就很少了。”因此,书面传播因其文本性和永久储存性,成为集体记忆的另一种方式。
(二)书面传统与记忆
文字的出现使记载和储存成为可能,是人类传播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纸和印刷术始终对空间感兴趣。[12]书面传统借用文字来保持其准确性。[13]扬·阿斯曼认为:文字是被作为存储的媒介物而非交流的媒介物发明出来的。[14]彝族是中华民族中为数不多的既有民族语言、又有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之一。彝族文字叫古彝文,又叫毕摩文。古彝文主要是由彝族的仪式祭司——毕摩传承的,毕摩是一种专门职业和身份符号,这种身份是世袭的。访谈中,黄聪哈说:“但是现在我们这里会写彝族文字的越来越少了。我们彝族的法师叫做‘毕摩’,他们全部会写、会看。这是一个很好的传承我们彝族文化的方式。”普通的彝族民众认识的彝文相对较少,因此毕摩是彝族文化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借助传统仪式和文字传播,民族的文化记忆再次被激起和唤醒,书写文明作为一种“流动的文本”又重新获得生命。保罗·康纳顿认为:从口头文化到书面文化的过渡,是从体化实践到刻写实践的过渡。用文字传递的任何记述,被不可改变地固定下来。这种固定性给文化创新带来了动力。2014年普格县火文化研究会会长毛小兵出版个人诗歌集《火把节的火把》;中国彝族现代诗歌资料馆与普格县火文化研究会发起面向全国的“火把杯”火把文化体裁原创诗歌(体裁:新诗、散文诗、传统诗词)和论文大赛征稿赛事。赛事以大西南彝区“火把文化”为题材,收到了一大批原始古朴、清秀自然的文学作品,并以特刊专辑《火把魂》刊名推出。从古彝文的记载到当代关于火把节诗歌、文学作品的集结出版,书写文明的记录和表意功能对节庆文化的记忆产生了重要影响:书写文化使得记忆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记忆作为一种符号表征实现了“自由流通”。从时间上看,关于火把节的集体记忆保存和传播得到延长;从空间上看,则把民族记忆和文化向外拓展,实现了跨文化、跨族群、跨部落的传播。
(三)影像记录与记忆
电子媒介时代,技术革新使得真实记录和电子保存成为可能。图片和视频资料不仅可以对历史文化、传统仪式、庆祝活动进行写实、客观记录,其本身承载的信息还可以被 “二次再现”。
德国学者约恩·吕森在谈及新兴媒介、图像符号对记忆方式所造成的改变时说道:“在公共文化场景中,集体记忆已经被大量的活动影像及其图片资料所覆盖,结果是那些由文字记载而产生的意识形式——首先是那些保持距离的理性的意识形态可能会很快失去作用,尤其失去政治的影响。”[15]借助影像资料,族群关于过去的历史回忆再次被唤醒,使得每个民族个体都能形成对于族群的集体认同。这是一种新的“叙事策略”,民族成员在直观生动的 “影视再现”中建构过去和集体记忆。
摄影术是视角本位的传播。[16]举办火把节期间,摄影爱好者齐聚彝族聚居区,用镜头记录下精彩赛事和精彩瞬间。国际火把节的时候会举办摄影采风活动和摄影展,展示魅力凉山、彝族风情,形成了一批文化作品。既有选美冠军、民众点火把的照片,又有朵洛荷舞蹈、赛马、摔跤比赛、围着篝火跳达体舞的视频。这种具有现实主义记叙风格的作品,以其独特的形式满足了受众对节庆活动的欣赏和感知。2014年5月,中国首部彝族神话电影《支格阿鲁》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CCTV6)首播。支格阿鲁是彝族公认的英雄祖先,千百年来关于支格阿鲁的神话传说一直在彝族聚居地流传。电影故事情节采自彝文古典长诗《勒俄特依》,影片利用虚拟、动画和大量特效,让逝去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得以再现。无论是服装、化妆,还是道具都保持了彝族原汁原味的风格特色,完整讲述了火把节的英雄史诗传说。该影片先后参加了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的影展,并在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获评“民族电影展优秀展映影片”。
2007年6月,第五届凉山彝族国际火把节在西昌举行。中央电视台《探索与发现》栏目组走进凉山,拍摄火把节专题纪录片《彝寨狂欢:凉山彝族自治州火把节》。在彝人的心目中,火是工具,火是历法,火是武器,火也是图腾。毛小兵先生主创的光影作品《寻找取火人》《火舞者》先后在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四川广播电台、凉山电视台播出。纪录片影像对真实场景进行了模拟和深层意义的传递,它根据民俗专家的口述、故事现场的重新建构、节庆文化的史料搜集与整理,将历史传说变成“公共历史事件”,让族群成员达成文化共识并唤起族群的集体记忆。
(四)博物馆与记忆
博物馆是人类征集、收藏、陈列、展示历史物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实体场所,“物性”是博物馆的特征。博物馆根据时间顺序或者类别属性将民族传统的“物件”摆放在不同位置,附以文字、音频、视频解说,借助物品形成一个可以被实现、被理解以及可传递的认知空间,使参观博物馆的人们能够体会到遇见历史、保存记忆、对抗遗忘的快乐。这些残存的民族历史“碎片”既直观地展示了民族的灿烂文化和历史谱系,也通过“博物馆叙事”的方式来串联民族文化的记忆。
过去世界不可还原,过去文化的记忆却可以通过博物馆得以“重建”。在关于博物馆传播与集体记忆的研究中,伊丽莎白·亚克尔认为“博物馆展览正在成为一种新的交流和传播类型,搜集到的东西、呈现的故事和将它传递给公众的方式能够保留或者遗忘人类的某一部分文化,形成记忆,并且决定了什么是历史性的文化象征。”[17]而在全球范围内,博物馆作为群体生活秩序的认知空间,起到了“规范有用知识和构筑具有民族国家群体意义的集体身份”的作用。[18]
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坐落在西昌市泸山上,其中“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文学艺术”两个陈列序厅对彝族火把节的节庆文化均有所展示。它集知识性、趣味性和教育性于一体。博物馆是免费开放的,这能让彝族民众在参观博物馆中熟悉本民族历史,重唤节庆文化的集体记忆。凉山州政府还可以利用融媒时代的数字化工具和电子媒介,建立数字化博物馆。这种网络化的博物馆集声音、图片、文字、视频于一体,可以全方位地展现文物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这样的展览方式既符合新时代受众获取信息的潮流,也有利于传播彝族火把节典型文化,加深和巩固族群的集体记忆。
三、新闻报道:唤醒和重构节庆文化的集体记忆
近年来,传播学和记忆研究实现了学科融合,从传播学的视角研究集体记忆逐渐进入学界的视线。刘国强认为:意义的生产和传播绝大多数时候是通过大众传媒来进行的,他们通过截取历史素材,以种种方式重新建构集体记忆。[19]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大众媒体与民族认同的关系进行了深刻论述。他将印刷文字的传播、资本主义商业与宗教世界观的没落用以解释作为调解的国家认同历史化趋势的形成。大众媒体,特别是新闻报道,在塑造想象的民族共同体中的作用重大,在民族形成和记忆共享过程中处于核心位置。[20]美国学者卡罗琳·凯奇认为:媒介塑造集体记忆有两种叙事方式:一是通过对重大事件的报道,使人们通过媒体了解到无法亲身经历但可以“目击”的媒体事件,以实现社会认同;二是通过多种形式,媒体将历史进行再现,选择性地进行报道,扮演着“公共历史学家”的角色。[21]大众媒介通过影像、符号和文本使得民族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顺利整合,连接起民族的集体记忆。
重大事件以及节庆典礼作为国家和民族自身历史的重现和传承,记者和新闻媒体对周期性节庆活动的集中报道有利于唤醒族群的集体记忆,凝聚民族认同。访谈中,吉各要日说道:“我觉得这个媒介帮助了我们,媒体是民族文化传播的载体嘛。假如没有媒介帮助、没有媒介传播和新闻报道的话,就没有外地的人了解、喜欢过火把节了,更不可能有这么多外地人每年暑假来凉山过火把节了。因为媒介的缘故,彝族火把节传播速度变得快了,传播范围也广了,火把节也就比较出名了。媒体的传播调动了我们彝族同胞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热情。别人都开始重视我们的文化,我们自己为什么不重视呢?我们会更加的重视,也就更加的积极了。”
每年举办火把节的时候,举办地都汇集了县级、市级、省级甚至国家级、世界级的媒体。新闻作品通过对重大节庆事件的“深描”和“选择性报道”,利用“议程设置”的方法、“新闻框架”的范式,对节庆内容进行现场报道或深度挖掘。访谈时,阿基尔拉说:“媒体介入更多的是宣传火把节,提高火把节的知名度,通过媒体、通过电视、网络啊等等,然后向外界宣传火把节的盛况。2015年普格火把节你没有参加,我当时去参加了。当时四川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都来了,有的还进行实况转播了。”2015年8月8日上午,第七届中国·凉山彝族国际火把节在西昌火把广场开幕。开幕式吸引了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四川日报》、四川卫视、四川广播电台、《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旅游卫视、香港《大公报》、香港《文汇报》、新浪、腾讯等40余家媒体和网站进行采访报道。成都电视台和凉山电视台还直播了开幕式实况,中国凉山彝州新闻网、凉山广播电视无线凉山、火把节专题官网及“五彩凉山”微信、“微凉山”微博、今日头条“大凉山”、“掌上凉山”客户端、“凉山广电全媒体”微信进行现场视频直播。①宋明 杨尚琳 阿支布哈 刘晓嵩:《第七届中国·凉山彝族国际火把节隆重开幕》,http://old.lszxc.cn/news/201588155324.html,2015年 8月 8日。媒体的集中报道会产生强大的传播效果,火把节的“个体想象”被聚合成“集体想象”,过去关于火把节的记忆和亲身经历被媒体重新召唤出来、达成共识。访谈中,伙补么尔歪说道:“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少数民族嘛,经过这么多媒体传播后,感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我们彝族,知道了我们民族的文化,还是很高兴的。毕竟火把节是彝族的文化,它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用媒体传播到世界上去,让大家都能看到火把节这种文化。看到现场有人来拍摄,看到电视台和网上都播放火把节的现场情况时,作为一个彝族人,我很高兴的嘛。”新闻报道在塑造族群意识、界定族群身份的同时,也强化了族群集体记忆的基础和过程。
四、现实反思:新媒体传播和“族群流散”带来的集体记忆危机
(一)新媒体传播带来的集体记忆危机
大众媒介在族群集体记忆的建构中日渐处于核心的地位。而新媒体技术、数字化技术的突飞猛进,给族群的记忆结构、集体记忆传播带来了技术性的变革,可能引发族群集体记忆的“数字化遗忘”和“记忆碎片化”。融媒时期的集体记忆危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新媒体作为一种数字化、可移动、超文本的传播方式,促使“自产自销”的受众形成新的记忆文化,有可能会引发“数字化遗忘”。[22]电子媒介的储存和影像再现功能,使得民族成员即使不参加族群节庆活动,也可以很容易地重温精彩的节日活动实景,这样势必造成社会遗忘了本该留存的东西,比如节庆时候的特殊仪式、民族图腾、宗教信仰等。节庆文化的集体记忆越来越依赖于外部的“符号储存系统”,而对族群自传性回忆和身体记忆的依赖性越来越小。[23]访谈中,阿里子且说:“因为现在有光碟嘛,没看到开幕式、火把节内容我可以买一份光碟看嘛。以前没有媒体的时候,大家都很珍惜这一年只有一次的节日,过的时候也很隆重,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的。但是现在大家可能是过来找同伴玩的,不是来看这些节目,过节日了。”
传播手段的现代发展造就产生了更加逼真的效果,同时也造就了更大的虚幻。[24]融媒时代多元化、多角度的呈现方式,让人们了解到彝族节庆文化的绚丽多彩和深刻的民族记忆。但在网络传播的过程中,彝族文化之精髓无形中被消解殆尽,最后沦为机械复制时代的作品,成为“象征的符号文化”,使得内涵丰富的火把节文化变得“荧屏化”和“脸谱化”。[25]四十岁的赵长友(彝族)是普格中学的教师。访谈时,他说道:“来拍的记者,他们只会拍好看的镜头,漂亮的、内容精彩的等等。播出去之后就像那些综艺频道一样,就只是好看的。只是看到火把节的‘盛况’,更多的是渲染火把节的这种激情,节日气氛。”
此外,“超媒体”的多元性、交互性、平等性和即时性特点带人们走进了 “大众书写”的时代,“去中心化”的话语结构颠覆了传统记忆中的权力结构。大众书写的碎片化、快餐化和娱乐化的特点,使民族节庆文化的记忆愈发容易“在不断地生产与不断地消费之间被逐渐消融”。[26]这是融媒时代集体记忆的“碎片化”危机,也是人们必须要思考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族群流散中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作为人类社会的产物,与人类社会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传统社会因为生产力的相对落后、经济发展缓慢、信息流畅性滞后,族群大多依附于土地进行生产生活。传统农耕社会人员流动性不强、社会成员组成结构相对完整,这有助于集体记忆的唤醒和保存。
王明坷强调:“离散族裔历史失忆与认同变迁常发生在移民情境之中。”[27]新的发展时期,因为传播的便捷、市场经济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彝族民众被卷入到城市进行务工。外出务工的机会让彝族人接触了外界的文化,增加了彝族民众的经济收入,但也造成了火把节期间的“族群流散”,在无形中影响着其传统的过节方式。因为火把节的放假时间通常和工作时间冲突,更多外出务工的人员失去了回家过节的机会。访谈中,阿力莫尔呷说:“他们在外面打工的,大部分都是三四月份去,九十月份回来嘛。但是火把节正好在6月,他们大多数在过火把节的时候都回不来嘛。有的就不回来了,不过火把节了。他们对火把节有些淡忘了那种,回来的时候不怎么重视了。”吉各要日说:“比如去年过火把节的时候,有很多人就没有回来,因为外地的老板有的不知道火把节。如果工程没做完的话,他们就不放人回来,去年我大哥也没有回来。我嫂子带着两个孩子和我们家一起过的节日。”同时,因为彝族民众教育观念的改善,使得青少年受教育的机会显著增加,越来越多的彝族青年离开家乡,到各类高校接受高等教育。这两类群体离散程度较高,分布相对分散,火把节期间他们成了流散在异乡的彝族人。访谈中,赵长友(彝族)说道:“因为每年火把节的时候,我们彝族家里会有祭祖活动,一般来说,家里人都要参加。但实际上彝族小孩到外面读书,肯定不能为了火把节专门回来,这种祭祖、祭祀活动只能通过他最近穿的衣服来替代。”如何在他们中间通过举行民族节庆的活动唤醒“共同历史”意识和集体记忆成为现实问题。
五、新时期增强和构建民族集体记忆的建议和思考
纵观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我们不难看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观念、国族集体记忆总是特定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理空间的文明产物。因此,在新的媒介社会和历史时期必须立足于时代发展的现实和现状,找到“时代轴心”、“记忆之困”,尝试对民族集体记忆的保存和书写多些更有效的思考。
文化自信是浸润在特定文化传统中的特定主体对其文化的内在体验和认同,集体记忆则是传统文化向文化自信转换的中介和桥梁。[28]对于彝族火把节文化来说,增强和建构民族的集体记忆首先是要唤醒彝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调动彝族民众保存火把节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和紧迫感。
一种新的媒介意味着一种新的传播和书写方式。当代是新媒体时代,也是媒介融合时代。民族集体记忆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更多的机会。文化是不同于别物的东西,对于集体记忆的重塑和书写不能停于表面、浅尝辄止。为了应对新媒体的挑战,在传播火把节的文化时,无论是学者还是新闻传播者,对民族记忆传播和研究要做到“深度挖掘”“潜心梳理”“系统研究”。要扮演彝族火把节文化集体记忆和传播“主人翁”的角色。赵长友(彝族)说道:“媒体采访可以多一些‘人文关怀’的采访。因为现在多数记者看到的火把节是由政府组织的,比如普格县和西昌市的火把节。他们更多的是把火把节的客观现状或者事实情况进行报道、描述、展示。那么记者能不能去不同的地方,经济发达或者经济条件不好的地方看看?对普通彝族家庭里过火把节各种活动的场景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记录,看看普通村里人三天火把节是怎么过的。不要只是看到火把节的‘盛况’,只是渲染火把节的节日激情和节日气氛。”
集体记忆的形成是个能动的过程,具有主动设计性、自觉引导性和走向可预测性等特点,增强民族集体记忆要引导彝族民众和国家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彰显彝族火把节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要重新建构彝族传统文化的记忆之场,促进彝族优秀传统文化“再登场”。[29]当地政府在增强民族集体记忆中担任重要的角色,在2017年凉山彝族自治州《政府工作报告》中,启动实施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办好旅游节庆活动(火把节)成为2017年重点工作之一。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还应组织专家和学者对彝族火把节文化精心整理,包括火把节传说和诗歌、节日仪式研究、毕摩苏尼文化、活动场所的修复和保存等等,保护好这些民族的文化遗产。同时,要鼓励有条件的彝族群众变外出务工为自主创业。利用新媒体客户平台、商业网站发展彝族服饰、彝族绘画等手工艺品产业,让原本流散在全国各地的彝族群众能“留守乡土”。减少因“族群流散”带来的记忆缺失。要以延续族群中的火把节文化集体记忆为出发点,加强新时期的彝族民众,特别是彝族青少年对民族文化仪式和符号背后内涵的深刻认识。利用电视媒体和宣传报道培养广大彝族民众文化自觉意识,加强彝族民众对本民族文字和语言的把控能力,让火把节文化的集体记忆找到口头传播或文字书写的载体。每年举办火把节的时候,既要注重媒体宣传,扩大影响,又要保持民族特色,防止民族文化流于舞台化、庸俗化和脸谱化。要重视火把节文化记忆的传承与保护。在大型火把节演出的过程中,要使节目在形式上紧跟时代审美,在精神记忆上做到“尊重历史”和“回归传统”。尊重彝族民众在火把节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警惕火把节从乡村迁往城市的过程中造成的普通彝族民众身份的“边缘化”问题,致使普通彝族民众沦为自己民族节日的看客和“他者”。只有政府积极作为,民众充分自觉,尊重民族文化发展,经济和文化协同共进,才能使得彝族集体记忆的增强和重构成为可能。
总之,集体记忆是凝聚民族共识和增强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凉山彝族火把节的记忆经历了口头传统、书面传统、影视记录等记忆载体的变迁。大众媒介通过重大事件的集中报道,在塑造、唤醒和保存彝族火把节集体记忆时处于核心地位。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解决新媒体传播带来的“数字化遗忘”和“碎片化”记忆,解决族群流散中的集体记忆危机,增强和重构彝族民族集体记忆,是人们需要面对和思考的课题。
[1][3][6](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 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3~45 页
[2][20][22]陈振华:《集体记忆研究的传播学取向》,《国际新闻界》2016 年第 4 期,第 109~126 页
[4](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1页
[5]燕海鸣:《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 3期,第 10~14页
[7](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页
[8][9][10][11][12][13][16][24](加) 哈德罗·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53、65、7、93、62、88、65、66 页
[14](德)扬·阿斯曼 王霄兵:《有文字和无文字的社会:对记忆的记录及其发展》,《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73页
[15](德)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綦甲福 来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页
[17]Yakel,Elizabeth.Museums,Management,Media and Memory:Lessons from the Enola Gay Exhibitio.Libraries&Culture,2000,35(2):pp.281~304.
[18]徐贲:《全球化、博物馆和民族国家》,《文艺研究》2005年第5期,第44页
[19]刘国强:《当代传媒形塑集体记忆的方式探析》,《社会科学辑刊》2009 年第 2 期,第 70~74 页
[21]Kitch,Carolyn.Twentieth-century Tales:Newsmagazines and American Memory.Journalism&Communication Monographs,1999,1(2):pp.120~155.
[23]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80页
[25]吕晓英:《网络传媒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发展》,《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0期,第 117~120 页
[26]王蜜:《文化记忆:兴起逻辑、基本维度和媒介制约》,《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6期,第8~17页
[27]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5页
[28][29]王蜜:《集体记忆的重建与文化自信的生成》,《阅江学刊》2017 年第 1 期,第 33~39 页
Carriers and Changes of Cultural Collective Memory:an Analysis of a Festival
Zhao Jiang Zhai Guangyong
Collective memor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the cohesion of national consensu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national identity.The memory of the Torch Festival of the Yi people in Liangshan has experienced the change of the memory carrier,such as oral tradition,written tradition,film and television record.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how to solve the “digital oblivion” and “fragmentation” memory brought by the new media,how to solve the crisis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ethnic diaspora,and how to enhance and reconstruct Yi nationality collective memory,these need people to face and think about.
historical culture,cultural heritage,Torch Festival of the Yi people in Liangshan
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2
*该标题为《重庆社会科学》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新闻传播视角下的凉山彝族火把节集体记忆研究——兼论火把节记忆载体的发展与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