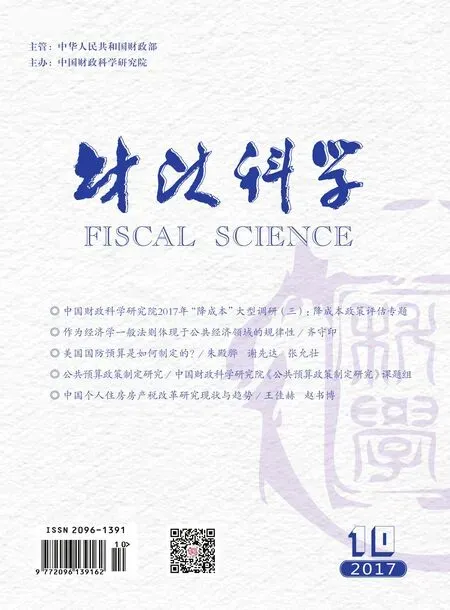PPP的十个问题研究
何 杰
PPP的十个问题研究
何 杰
2013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正式提出PPP模式,旨在管控政府债务、防范债务风险、促进公共物品供给提质增效。经过多年发展,PPP政策体系不断健全,项目落地成果丰硕,但仍存在很多未决争议。本文从财税和金融视角,辨析PPP“十大关系”,划分推进阶段,展望发展未来。
PPP 政府债务 十大关系
2011-2013年,审计署开展了三次政府性债务审计。审计结果发现,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政府性债务总额为30.27万亿元,较2010年末和2012年末分别增长73.27%和9.02%,其中:中央政府债务为12.38万亿元,较2010年末和2012年末增长83.30%和4.19%;地方政府债务为17.89万亿元,较2010年末和2012年末增长66.93%和12.62%。从数据上来看,2010年至2013年6月,中央债务增长趋缓,地方债务增速较高,带动全国政府债务较快增长,而且地方政府存在违规举债、变相举债、债务管理不透明,容易积累风险“堰塞湖”。在此背景下,2013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首提PPP概念和基本原理,旨在减少和控制政府债务规模,调动社会资本积极性,提高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
一、正本清源:PPP应有之义
英国1992年实施的“私人融资计划”(PFI),是PPP的早期实践,此后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得到快速发展。尤其是在2000年由联合国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框架中,PPP被认为是保障经济社会公平发展的最佳模式。
我国的PPP“孕于审计止于债务”,是分税制后的重大财政改革,涉及财政体制、政府债务和投融资管理,蕴含全新的政府投融资哲学。PPP要求政府和社会资本全生命周期深度合作,讲求精诚合作、损益共担和激励兼容,关键是要保持财政支出、银行信贷、风险分担和产出绩效“四大平衡”:财政支出和银行信贷是资金来源,风险分担是“隐性收益”,产出绩效是“显性收益”;财政支出和银行信贷加总是项目投资总额,比例关系均有条文约束,两者“此消彼长”,但都折射出风险分担比例;财政支出、银行信贷和风险分担是产出绩效的基础,产出绩效内含于三者比例关系中。
二、隐忍生发:PPP成长历程
从2013年提出到现在,PPP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总体来看,可归结为三大阶段,在质疑中破土而出,在逆流中茁壮成长,在协作中勃勃生机。
一是不忘初心,坚定启航。2014年初,调研施工央企、金融机构和平台公司等,对PPP项目多数持观望和质疑态度,“周期长、收益低”是主流意见。究其原因,传统的政信和基础设施项目,金融机构和施工企业习惯于政府兜底和信用背书,对项目实质风险缺乏识别、定价和转移能力,风控逻辑和完整体系尚未形成,更不愿意探索实践。
二是国家战略加速推进。财政部第一批22个示范项目的推出,引起社会资本较大关注;2015年第二批和2016第三批示范项目推出,“退库机制”的建立完善,促进PPP示范项目建设常态化和健康化。2016年3月4日,中国PPP基金正式成立,建立了PPP事业推进“国家队”,推动引领PPP发展方向。201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PPP项目建设进入国家意志。
三是矢志不渝,成绩喜人。《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第7期季报》披露,截至2017年6月末,全国入库项目13554个,累计投资额16.3万亿元,已签约落地项目2021个、投资额3.3万亿元,落地率34.2%。示范项目“捷报频频”,财政部示范项目700个,累计投资额1.7万亿元,已签约落地项目495个、投资额1.2万亿元,落地率71.0%。其中,第一批22个、第二批162个已百分之一百落地;第三批516个示范项目,落地率60.6%。
三、激辩争锋:PPP十大关系
发达国家PPP起步较早,实践期限较长,交易模式清晰,数据基础扎实。相比之下,我国PPP的正式起步在2014年,数据积累薄弱,理论建设滞后,存在很多空白地带。本文结合个人思考和实践,对一些争议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关系
经典理论认为,公共物品、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导致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宏观调控弥补市场不足;部门利益、官僚主义和有限认知等因素导致政府失灵,需要政府放权让位于市场。PPP是政府和市场结合的重要纽带和载体,“有理有利有节”是合作的基本原则,行为边界的划定兼具科学性和艺术性,政府“抓大放小、制定规则、维护公平”,社会资本“民生保障、高效运转、成本管控”,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扬长避短,相得益彰,才能协同推进PPP项目。
(二)“国际经验”和“以我为主”的关系
PPP项目支出规定,“每一年度全部PPP项目需要从预算中安排的支出责任,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应当不超过10%。省级财政部门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确定具体比例,并报财政部备案,同时对外公布”。《财政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2587号建议的答复》(财金函〔2017〕85号)指出,10%的红线,是在参考借鉴国际通行标准(6%-7%)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城镇化发展实际需要,经过反复论证最终确定的“上限”。
我国城乡和区域发展非均衡度较高,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欠账较多”,需要长期限资金大规模持续投入,对当地政府投融资能力是“大考”。特别是,监管部门债务管控不断升级,金融同业业务逐渐萎缩,机构配置久期偏好3年以内,导致资金市场利率中枢上移,公司债和企业债等品种续发难度增大,加剧了欠发达地区资金链紧张情况,可能带来潜在区域性公共风险。因此,在全国政府债务额度一定的前提下,可考虑政府债务额度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适度倾斜,并在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中给予一定安排。
(三)政府负担和政府负债的关系
债务融资的理论依据是代际公平,即“爸爸掏钱儿子也掏钱”;负担支出是即期消费,即“当期有钱当期花”。一方面,可行性缺口补助和政府付费等支出责任,在可承受范围内是政府负担,归类为或有负债,达到触发条件和“阈值”成为政府负债;另一方面,政府负债是负有直接偿付责任,具备内在增长和刚性兑付属性。两者分水岭是政府承受度,财政可承受是负担,过度透支形成负债。严把10%的支出红线,着眼于控制政府负债增长总量、速度和节奏。除此之外,采取“开明渠、堵暗道”,放开政府一般债和专项债,分别纳入公共财政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提高政府债务透明度;禁止变相举债和违规担保,规范地方政府违规举债行为,防止债务风险隐性积累。
(四)资产付费和服务付费的关系
传统的资产付费模式,政府支出主要考核工程施工进度,与公共物品供给质量和数量无关,导致社会资本存在施工导向、成本失控及工程质量纠纷等问题。PPP模式“孕于审计止于债务”,政府支付采取“见货付款,钱货两清”模式,且付费数额与绩效考核高度挂钩,在PPP项目的公共物品未提供之前,政府不存在付费义务。因此,资产付费属于传统模式,服务和绩效付费才是PPP的付费依据。
(五)PPP和特许经营的关系
PPP强调“共建、共享、共担、共治”的契约精神,政府和社会资本全生命周期深度捆绑,构建平等协作、互利共赢和“白头偕老”的“夫妻关系”,风雨同舟共同完成公共物品供给。特许经营是政府部门授权社会资本垄断性或排他性经营权,社会资本负责公共物品生产与供给全过程,政府参与度很低,双方是“父子关系”或“主仆关系”。政府和社会资本从属关系不同,决定了双方地位和权利义务差别。
(六)政府购买和政府付费的关系
1999年《招投标法》正式出台,规定一定规模标准的工程建设项目,必须采取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方式组织实施,内容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加入WTO后,为与国际接轨,2002年《政府采购法》正式出台,要求集中采购目录以内或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五种采购方式。2014年,《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4〕214号)正式发布,对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招投标法要求规模范围外的工程建设项目,采取竞争性磋商方式进行。
从促进公共产品供给提质增效目的来看,PPP可以看做拉长版政府购买服务。从PPP项目涉及阶段拆分来看,PPP项目包含工程建设和运营服务。工程建设应当走招投标程序;运营服务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因此必须采用专门的法规体系。
(七)预算周期和项目周期的关系
财政预算从年度预算管理,到实施中期财政规划(三年),体现了年度平衡财政思想到周期平衡的重大转变,同时债务和调入资金的使用,操作上也是在向功能财政过渡。PPP项目周期为10-30年,政府付费和可行性缺口补助支出,纳入当年财政预算和中期财政规划,但对于3年以上的项目支出,其保障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靠性存在不确定性,仅靠现有保障层次,很难让投资者安心,需要法律规范、管理制度、政府信誉三位一体组合的“稳定安全阀”。
(八)资本金和项目贷款比例的关系
可融性是PPP项目落地的关键,核心是资本金比例和结构设计。从数字计算来看,资本金是投资总额与项目贷款的差额,银行信贷政策和项目审批标准,是“两评一案”设计主要参照和核心指标。实际操作中,有些地方政府“一毛不拔”,要求社会资本全额承担资本金;有些项目资本金比例“拍脑袋”决策,导致项目很难融资落地。从实际出发,金融机构、施工单位和运营商组建投标联合体如能各安其分、各司其职、各尽其责,采取表外基金融资模式,资金安排和工程阶段紧密相连,则对项目实施保障程度较高。
(九)项目收益和投资收益的关系
PPP项目以有一定现金流准公益性项目为主,民生属性十分突出,公共物品供给价格受到政府严格管控,因此项目总体收益在5%-7%之间,盈利但不暴利。但是,投资收益是社会资本取得的回报,通过结构化设计、政府(及其出资代表)让渡(或放弃)分红权,可以取得有吸引力的收益比例。以某地“BOT+特许经营”新建污水处理厂为例,项目期限为30年(含建设期),总投资1.4亿元,市政府授权区环保局以前期费用入股占比30%,社会资本以现金出资占比70%,项目总体年化收益为5.6%,但政府通过放弃分红权,促使社会资本投资收益达到7%-8%。因此,PPP项目投资收益可以通过产品设计和结构创新得到提高。
(十)资产证券化和项目退出的关系
PPP项目资产证券化,本质是收益权或收费权证券化,收入来源和还款安排高度依赖企业经营治理情况,很难实现真实出表和破产隔离。具体操作层面,资产证券化前提是基础资产没有权利瑕疵,而项目融资已将收益权质押给银行,因此首先要进行解质押操作;为保障企业日常运营,通常将考虑企业运营成本后的现金流入池;为获得较高信用评级,通常要求1.2倍甚至更高覆盖倍数,从而企业通过证券化回笼资金约为总额的6-7折。资金用途层面,债权人偿付顺序优先于公司股东,回笼资金首先要偿付银行贷款,余下资金数量较为有限;如果用于回购政府持有项目公司股权,则会造成政府“缺席”,不能再称为PPP项目;如果用于回购社会资本股权,一方面额度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如果社会资本抽离,项目公司运营存在难度。因此,资产证券化只是项目公司盘活存量、优化融资结构重要工具,并不能实现退出安排。
资本市场多元化退出路径日渐明晰。公开上市方面,云南水务从2011年成立,到2015年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为PPP项目打包上市指明了方向;并购重组方面,2017年5月,东旭蓝天3.4亿元收购星景生态(专注环保行业PPP项目)100%股权,为PPP项目并购推出提供了样板;资产交易方式,2017年2月底天金所PPP交易平台挂牌,3月初上海联交所“PPP资产交易中心”挂牌成立,为PPP项目股权和债权交易流转提供支持服务,有利于PPP项目有效转让和“真实退出”。
四、引领潮流:PPP发展方向
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防风险”和“经济去杠杆”是重要关键词,提出“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从源头约束政府举债融资行为,需要政府转变理念,加快盘活存量资产,更好利用股权融资工具。
现金为王,盘活存量快速发展。第一批和第二批示范项目均已落地,未来2-3年,预计PPP项目将迎来证券化浪潮。2016年12月,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推进传统基础设施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相关工作的通知》,鼓励对建成正常运营2年以上、有稳定现金流的基础设施项目,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截至目前,发改委体系已经有供热、污水及高速公路共5单证券化产品发行成功。2017年5月,财政部《关于规范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资产证券化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公共服务领域推进资产证券化,鼓励具有稳定现金流的收益权和合同债权作为基础资产开展证券化,探索建成运营2年后项目公司股权分红权证券化,同时,优先支持水务、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市场化程度较高、公共服务需求稳定、现金流可预测性较强的行业开展资产证券化。
资产为王,并购重组激发活力。PPP项目进入正常运营期,项目公司收入稳定,成为优质“现金奶牛”,随着注册制和退市制度不断完善,缺乏业绩支撑和转型企业对此类资产并购需求强烈,目前已有企业开始积极布局,着手研究收购PPP项目公司;从现有PPP项目投资分布看,在污水、垃圾、供热、环保等领域,已经涌现专业化大集团,并购重组是未来业绩扩张的重要途径;对城投公司而言,“背靠政府要钱花”已成为历史,专注特定行业,整合特色资源,做实企业资产,集团化运作,市场化运营,完善治理结构,提升治理水平,成为“城市运营服务商”。
Research on ten issues of PPP
He Jie
In 2013,the national fiscal work conference formally put forward the PPP model,aiming at controlling government debt,preventing debt risk and promot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public goods.After years of development,the PPP policy system has been improved and the project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outstanding disputes.This pape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e and taxtion,discriminates the"ten relationships"of PPP,divides the promotion stage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PP;Government Debt;The Ten Relations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部
邢荷生)
F812.7
A
2096-1391(2017)10-01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