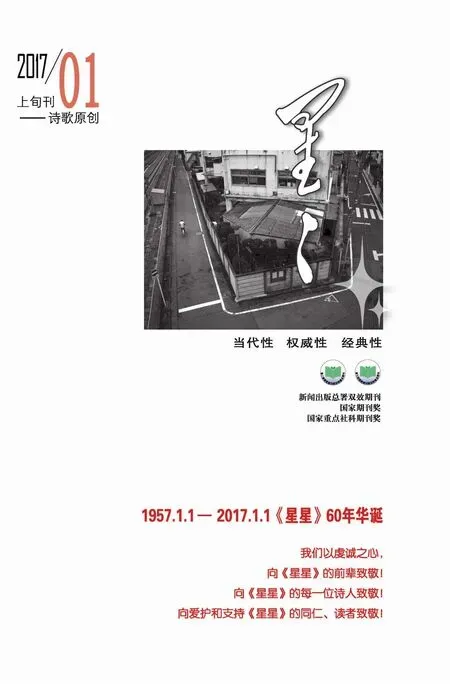采煤者说(组诗)
老 井
采煤者说(组诗)
老 井
救 赎
第一次下井,在八百米地心深处关掉矿灯
便遭遇到史上最强的黑暗
我的眼睛看不到脚尖,左手看不到右手
浑身的器官都看不见
他们的躯体,遍体上下没有铜钱大的一块亮点
沿着前方30°倾斜的工作面上行
在陷于黑暗和低洼时对自己的一次提升行为
闷热无风的空间,二百米的上山爬过
矿灯下,淌出的一身晶亮大汗是救赎的光点
瘫软在风量充足的巷道内
肺部的风箱拉得吧嗒、吧嗒地作响,我竭力张大嘴
想一口把地心黑暗以及其中
包裹的煤层岩块、钢轨矿车一口吞下
收 拢
乌黑的巷道、乌黑的地心、乌黑的矿工
电车头开过
明亮的灯光划亮多少
蛰居若干个地质年代的面孔
铁棚逐渐弯曲,岩层一声不语
悸动的煤层,拼命地把戳进体内的钢轨往外推
“今天必须咽下这块万吨的大炭才能下班”。
高大的综采机满脸惆怅地
对低矮的皮带运输机说
“冰川纪、石炭纪、侏罗纪,
草履虫、三叶草、古森林”。矿长和总工程师
刚谈过神秘深邃的地心压力
抬头便看见栖身的巷道正缓缓地收拢
浅与深
锄头带起的是地表的浅
铁镐咬住的是八百米地心深处的深
所以刨煤时必须要用更大的力气
你一镐我一镐地继续往前赶
地心的长城被我们一砖一瓦地拆下
这块是恐龙肉,那块是棕熊骨
这片是凝固的海浪,那片是上冻的狼嚎
这堆是夏商的宫殿,那堆是秦汉的老墙
乌黑的煤体中,岁月的表情模糊不清
你一镐我一镐地继续往前赶
这一镐离诞生更远,那一镐只会距死亡更近
我们的劳作比黄土低下
比庙堂更高,八百米深处两个中年男人
半裸的躯体上,汗水夹带着爱恨情仇
轰轰烈烈地淌下。体内的行星正一粒一粒地
透过毛孔往外挤
大地的补丁
卡车奔忙,推土机轰鸣
这一片沉陷的低洼被用矸石填平
有人掏出大地的骨头和内脏
去敷补上它肌肤上的创伤
一场新的地壳运动过后
这堆拒绝炭化的大地骨骼铺成了坎坷的大路
岁月的零部件被扔得到处都是
大地的骨骼随随便便地被烈日冻凝
被霜花熏烤,微风吹过
还能嗅到其中残余的炸药味,在夜深人静时
随便拿起那块石子放在耳畔
都能谛听到其中传来的匆匆脚步声
这一堆被遗弃的矸石表面已经
长满杂草,野花
浅绿的毛发从青灰色的身躯中钻出
像是石块的灵魂已经萌芽
石块的爱情已经开花、春风吹过
一片姹紫嫣红,一片郁郁葱葱
石块们从梦里挤出几瓣地球的童年
停产的小煤窑
钢铁的井架上爬满青藤,有些许的蓝花
点缀。花香自由地在井筒内产卵
阳光的皮尺拉断,也无法量出它的深度
沉寂的小煤窑,在停产前已给怀胎亿年的大地
做了多次野蛮的剖腹产,但还没摘取干净
还有许多星宿般的小煤层
在地心深处闪耀。停产的小煤窑
这座工业的废墟
独自地承受着原野料峭的敌意
一个干涸的井筒,想把周围的乡镇大楼
沉陷湖,庄稼地一口吞下
地心的迷惘
操纵综掘机
竭力地在地心深处劈开岩层,因为心存敬畏
我才能看见瓦斯、一氧化碳惊骇的脸
因为看见瓦斯、一氧化碳的阴险
综掘机的脚步立刻变得像是灌了铅
我轻轻点动开关,合金钢的刀头
在离煤壁尺把远的地方停下
只是用冰冷的目光向四周斜视
此时它离地面八百米,离矸石山顶一千米
离山顶洞穴十万八千里
离一亿年前的原始森林不到一米
目前,我分不清自己是
冰冷的钢轨,还是乌黑的煤炭
抑或是亿万年前就盘踞在沼池底部的
那群吞食荒凉的草履虫。深夜两点
我暂时迷失方向,像是陷进钢铁纹路里的螺丝钉
工友们笑着将我从座位上拧出来
继续操纵庞大的机器剖开大地苦胆里的结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