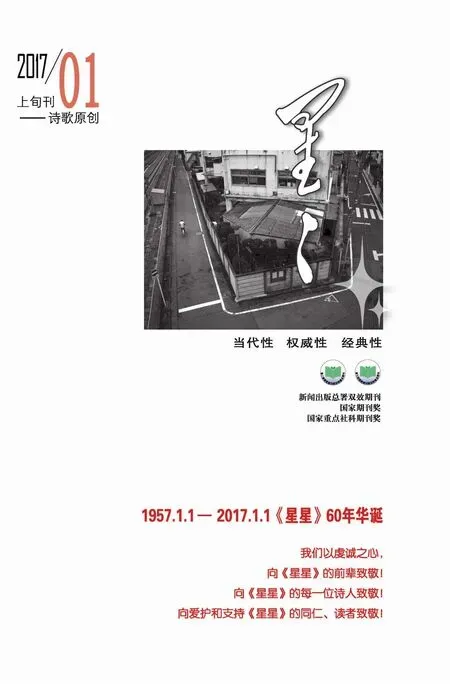挑一只红日装在锈迹斑斑的龙头上(组诗)
蓝 喉
挑一只红日装在锈迹斑斑的龙头上(组诗)
蓝 喉
修车匠
他小心地抓紧后轮,像扶起摩天轮。
又像刚凿出花岗岩石磨。
他吸尽了落日的浑圆
用一节麦秸蘸着滴进车轴。
暮色将加速轮子的转动。他能把圆推为直线
也能把身后的长巷滚成铁环。
请允许他挑一只红日装在锈迹斑斑的龙头上
代替他十八岁的听觉。
白苹果
我捧起蜷缩垃圾箱一角的白苹果
围着火堆取暖的白苹果
湖面漂浮的白苹果
被倒塌的小学校砸烂的白苹果。
我从街头,小巷,十字路口,摘下满怀满桌的白苹果。
曾经,我拿来果腹,冲淡口腔的异味
往往唤醒浩瀚的饥饿。
是啊,饥饿。
我晓得它们慌乱无措的饥饿。
它们献上仅有的一缕血
又交出白皙的骨头,皮肤。
这一场难以喂饱的饥饿却发动另一场更无垠的饥饿。
我剖开它们,搬空的四壁上
山坡放羊的白色理想簌簌发抖
抱紧着不忍放手。
它们越白
越无法在人世隐身。
领着浑身泥垢的妹妹,在街头卖艺的白苹果
地下通道伸出脏手乞讨的白苹果
变作装满积雪灯笼的白苹果
一次次,在红日下和我狭路相逢。
枯 井
等待流水明年从地下四十多米涌来,
无比虔诚和垂直地把孩子们
从漆黑里还给母亲紧攥的掌心,
把坠井的星星送还天空,把怒放的白菊花
运抵嚎哭的鲍墟乡中孟尝村。
让一次次垂下
却绝望而返的吊桶
坚信流水必来,请把这绒布玩具娃娃永埋地底
见证流水涌来的时刻。那时刻
沁凉不可禁的井水才可替他大悲大哭。
而现在是2016年的深秋,华北平原上的枯井
像六岁男童赵梓聪的爷爷泪腺干枯的眼窝,
安静而恐怖的眼窝,
八十台挖掘机难以掘尽死亡的眼窝。
疯人院
疯人院门外,红砖水塔荒废多年,塔顶芦苇
折断天空。一个消防栓铺开巨大的混凝土地面,
刚刷的红漆撕开孤独和羞耻。院中再无余物。
他们的眼神轻软,蜷曲于空荡荡的眼眶,
这个早春细微的波澜也能卷尽其中所有。
黑咔叽老头一动不动,他想挤进年轻时曾痴迷的雕像。
“要变须从额头开始”,几十年来,
他一直琢磨如何先变成汉白玉。
牡丹花棉袄中年胖女人,母豹般咆哮,猛烈跺脚,
欲借土遁远离此地。他们相互提醒为我让路,
凝视我从锁孔进来,又从锁孔出去。
他们祈求的空间比身体废掉的空间要小,
恐惧和冥想比庭院还大,对此他们似有悔意。
白云恍惚,斜靠着水塔,仿佛红砖尚有余温。
快递员之死
秋风,这锉骨的力,弑父的力,摆动钟锤的力,
驱动马路不断地卷上快递车的轮毂。前方,
地址已在等待中作废,而落日依然遥远。他太累了,
躺在马路边,合上眼睑就是给自己拉上棺盖。
街上猝死的他和两个男孩的父亲难以重合,
快递员和服装厂工人难以重合,户口薄中
三十九岁的他和死亡证明上的他难以重合。
早春祝福的他和秋风中不祥的他,
难以重合。他们分属于马路的两边:一个人
不可能同时出现在马路的两边,也不可能
同时踏上出发和回家的路。我不知道凌晨几点
他从马路对面跑过来,脱下橘红上衣,
换上蓝厂服。也不知道深夜何时他拧熄电瓶车
又爬过天桥跨上一辆旧自行车。在秋风的空棺中,
死亡把他们焊在一起,无非证明
活着就是潜在的死亡。落日,他的黄金棺,
正在晚霞的烈焰中焚尽。
女孩小忠
我写下小忠,你就来到纸上。
立在我的灯下,
薄薄的,
圆珠笔墨水一样淡。
你八岁的年纪像被揉起扔掉的纸团。
你不说话,我听见
窗外有鸟鸣,
纸的褶皱里有鸟鸣。
我只能
让你立在纸上立在
象形字之间。小忠,我只有
白纸和无力的长句子。
如果我再找不到一张洁白的纸
我答应一定把你的名字
擦得干干净净
假装它也没有来过。
其实不必
写下连绵的长句子
把小忠迎到案头。
每个人身上都可以搀出一个小忠。
正如我走过乡村的小池塘,
必有孤独可供映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