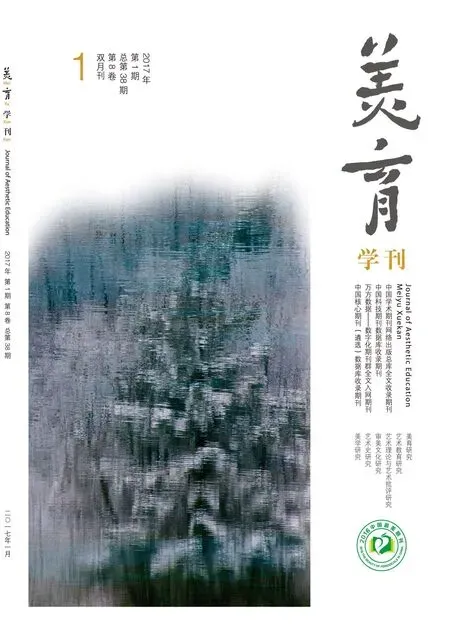中国现代“美学三慧”之人生艺术化思想比较
王广州
(安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中国现代“美学三慧”之人生艺术化思想比较
王广州
(安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朱光潜、宗白华与方东美同出一时一地,其各自的人生艺术化思想对“生”与“情”作出了富有个性的阐发,涉及人生、生活、生命与情趣、同情、情调三组相对应的主题,而且同中有异,异中见同,相映成趣。同时,三人也用各自的主张回应了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实践论、想象论与存在论三条探讨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的路径。
朱光潜;宗白华;方东美;人生艺术化;比较
中国近现代以来,关于人生艺术化问题的探讨者可谓甚众,较有影响的也不下十数人。其中朱光潜与宗白华的人生艺术化思想最为纯粹与显著,而方东美的人生艺术化思想则最为独特却稍为隐晦。由于这三人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生成长于同一地区(安徽安庆),所以有论者化用方东美一篇论文的标题将他们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学三慧”。[1]3朱光潜与宗白华同年生而又同年逝,方东美较二者仅仅晚生两年;朱光潜与方东美皆生于安庆桐城,并于1912年和1913年相继进入由晚清桐城派大师吴汝伦创办的桐城中学就读,直到晚年二人分处海峡两岸而仍有书信与诗文往来;宗白华与方东美早年都曾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方东美的重要论文《哲学三慧》首次发表于宗白华主编的《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上,并被后者高度评价。[2]173三人在青年时期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回国后不约而同地走上了美学与哲学研究的道路,方东美与宗白华曾在20世纪40年代的国立中央大学共事,朱光潜与宗白华则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北京大学共事,在相同的工作领域中思考着诸多共同的思想主题。
此三人同为从安庆走出的思想人物,行迹上有很多相似与叠合之处,这种物理事实对于有索引癖的学者来说,好像很有可以玩味和挖掘的地方。但是总体来说,这一切与其说是地域使然,不如说是时代使然。美育与人生艺术化命题的提出及其话语生产,在三人那里本身就是对时代问题的各自回应。目前关于人生艺术化思想的研究,主要是以人物个案为主,因此往往着重探析各家之特点,而有意无意地忽略或无视各家之共点;实际上,在缺少比较的维度后,在分述各家之特点时反易误入自说自话、漫无归落的倾向中。本文意在比较三人的人生艺术化思想的具体构成,总其同而析其异,并就其思想对时代问题的回应范式揭示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的三条典型路径。
一、“生”与“情”:思想内涵之异同
“人生艺术化”,此一命题称谓已经大致道出该命题本身的精义,似乎并无太多理论操作的余地了。所以严格说来,三人皆未建成某种完备的人生艺术化理论,非其不欲,诚其实难。例如宗白华在1920年就明白无误地说:“我久已抱了一个野心,想积极地去研究这个‘科学人生观与艺术人生观’的问题”,但最后只是写了一篇两三千字的《新人生观问题的我见》,于是“很是抱歉”,“所说的实在太简略了”,而期之未来。[3]208不过后来也并没有践行,原因倒不在于缺乏他自己所谓的“科学与艺术的基础知识”,而在于这命题本身只是个过于实在的主张而已。情形在朱光潜与方东美那里大致相近。朱光潜在《谈美》的最后一章谈到“人生的艺术化”问题时,也只是说要“提议约略说明艺术和人生的关系”。[4]91方东美时常将哲学与艺术视为中国与希腊文化体系的枢纽,但他还是倾向于认为哲学才是“民族文化生活之中枢”。[5]125由此,就在三人那里形成了一个关于该命题的相同的话语存在形态,即散论式。宗白华的观点主要散见于《青年烦闷的解救法》(1920)、《怎样使我们的生活丰富》(1920)、《新人生观问题的我见》(1920)、《艺术生活——艺术生活与同情》(1921)、《席勒的人文思想》(1935)、《〈美育〉等编辑后语》(1940)、《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1946)等文中;朱光潜的观点散见于《给青年的十二封信》(1929)中的《谈情与理》《谈摆脱》及附录的《无言之美》,《谈修养》(1942)中的《谈美感教育》及附录的《消除烦闷与超脱现实》《看戏与演戏——两种人生理想》等文中;方东美的观点则散见于《生命悲剧之二重奏》(1936)、《生命情调与美感》(1936)、《哲学三慧》(1937)、《诗与生命》(1973)等文中。
就存在形态而言,三人的观点是零散分布于各个年代的作品(主要是单篇文章)中,时间跨度从十余年到三十多年不等。不过,综观之下,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三人各自的,乃至共同的某些核心主张,它们与该命题中的两个关键词“人生”和“艺术”相关,质言之,就是三人的思想都围绕着“生”与“情”两大主题而展开(传统艺术观常常落实到情感的维度),同中而又有异。首先,“生”意味着人生、生活、生命,这是三人都曾明确言说的对象,不过宗白华与朱光潜多言“人生”与“生活”,而少言“生命”。反之,方东美则主要言说“生命”,极少言说“人生”与“生活”。这一点仅从上述三人文章的标题中已可见一斑,而具体行文之中更为明显。这三个词在其他语言如英语或德语中一个单词就可以表示,但是由于汉语词汇的丰富性与含混性,它们互有联系但是又互分互立。“生活”具有物质的意味,“人生”具有精神的意味,而“生命”则具有哲学的意味。对宗白华和朱光潜来说,无论是前者的“艺术人生观”,还是后者的“人生的艺术化”,其要旨都在一种较高尚优雅的精神追求,但最终都还是诉诸具体现实的形而下生活本身。所以对他们二人而言,人生与生活两个概念可以看作是一体。宗白华的这个判断也同样是朱光潜思想的前提:“‘生活’等于‘人生经验的全体’。生活即是经验。”[3]191而方东美言所必称的“生命”具有强烈的形而上色彩。我们尤需注意的是,方东美的生命概念并不单纯地指个体的生命,而是一个既包含个体生命同时又超越它的普遍生命。关于普遍生命的存在、特征以及个体生命与它的关系,方东美做了简明的哲学设定。首先,“天为大生,万物资始,地为广生,万物咸亨,合此天地生生之大德,遂成宇宙”。其次,“宇宙乃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是生生不已、新新相续的创造领域”,“其中生气盎然充满,旁通统贯,毫无窒碍,我们立足宇宙之中,与天地广大和谐,与旁人同情感应,与物物均调浃合,所以无一处不能顺此普遍生命,而与之全体同流”。[6]82-83从言说路径看,方东美的“普遍生命”可说是黑格尔“绝对精神”概念的翻版,同时又完美地杂糅了中国上古易经与西方现代哲学家柏格森的学说,三相凑泊,赋予其丰富的哲学内涵。
其次,“情”在三人那里也各有所主,在朱光潜是“情趣”,在宗白华乃“同情”,在方东美则为“情调”。情趣、趣味、愉悦等等是人生艺术化命题的应有之义,三人之中朱光潜最为大力标举,指出“人生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它本身个体在世界之中“物我交感共鸣的结果。景物变动不居,情趣亦自生生不息”,“在这种生生不息的情趣中,我们可以见出生命的造化。把这种生命流露于语言文字,就是好文章;把它流露于言行风采,就是美满的生命史,”总而言之,“情趣愈丰富,生活也就愈美满”。[4]92-97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朱光潜继续推演与丰富其情趣说的逻辑内涵,在他看来,生活有情趣,便不“俗滥”,不苟且,生命便不“机械化”,反而能够“彻底认真,不让一尘一芥妨碍整个生命的和谐”;这种风度既艺术的,也是道德的,所以朱光潜说“我们主张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主张对于人生的严肃主义。”[4]92-97有趣的是,很少关注人生艺术化之情趣愉悦维度的宗白华与方东美在偶尔言及情趣愉悦时,几乎不约而同地持有和朱光潜相同的逻辑。例如宗白华在说当我们把世界上无论美丑的存在现象都看作艺术品一样时,忧苦烦闷就都烟消云散了,我们的“心中就得着一种安慰,一种宁静,一种精神界的愉乐”。[3]179不过宗白华强调“愉乐”不是“娱乐”,更“不是娱乐主义、个人主义,乃是求人格的尽量发挥,自我的充分表现,以促进人格上的进化。”[3]194所以宗白华的艺术人生观也绝不是轻浮乃至轻佻的消费主义追求,而是着眼于生活与情绪的调节,精神与人格的完善,也许此他才较少言及情趣和愉悦,以免引起误导。同样,方东美在论及古希腊人“从心而欲的悲剧”精神时,认为希腊人的生命精神“着重幸福的结局、愉快的后感”。但他也指出这种幸福和愉快并不“佻巧、一味求乐”,而是要“将实际生活中所经历的酸辛苦楚都点化了,饰之以幻美,始能超越艰难、陶铸乐趣,以显耀人生的胜利”。[5]26
“情”在朱光潜是情趣,是人生艺术化的目的。相较而言,“情”在宗白华主要是“同情”,是艺术人生观的方法。在宗白华看来,情绪感觉属于人类的主观世界,本来就参差万态,不易一致,而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情感完全不一致,却又是社会的缺憾与危机”。于是宗白华首先从社会学的观点界定同情的价值,把它作为社会结合、协作、维系与进化的动力和途径。而艺术也就起源于“人类社会‘同情心’的向外扩张到大宇宙自然里去”,且又可以反哺社会,“真能结合人类情绪感觉的一致”,是社会的黏合剂。所以,宗白华说“艺术的生活就是同情的生活”,是“我们拿社会同情的眼光,运用到全宇宙里,觉得全宇宙就是一个大同情的社会组织,什么星呀,月呀,云呀,水呀,禽兽呀,草木呀,都是一个同情社会中间的眷属”,这时就会产生“极高的美感”,而整个自然与世界“就是一个纯洁的高尚的美术世界”了。[3]316-319在这里宗白华把作为见之于社会界和艺术界之方法的同情看作是一种“空想”,其本质是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内省或反照”或“比例对照”(Aualogie)。[3]206同情起于空想,而能“入于创造”。所以,“所谓艺术生活者,就是现实生活以外一个空想的同情的创造的生活而已。”[3]319
“情”在方东美那里被具体化为“情调”,是生命状态的表征。方东美自谓平生最服膺并多次引用的一句谚语是“乾坤一戏场”,此乾坤即世界、宇宙,亦即人类社会存在与活动的空间。方东美借鉴恩斯特·卡西尔的符号学说,把空间视为各民族文化的基本符号,认为通过考察一个民族的空间观念就可以理解其民族文化的形态、内容与性质。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生命就是存在于宇宙这个空间中的,“生命凭恃宇宙,宇宙衣被人生,宇宙定位而心灵得养,心灵缘虑而宇宙谐和,智慧之积所以称宇宙之名理也,意绪之流所以畅人生之美感也。”这种人生美感是宇宙之中的“生命诗戏”,而又“常系于生命情调,而生命情调又规模其民族所托身之宇宙,斯三者如神之于影,影之于形,盖交相感应,得其一即可推知其余者也。”[5]88-93据此方东美在《生命情调与美感》一文中比较了三种宇宙空间观:古希腊宇宙为“有限之形体”,近现代西方宇宙为“无穷之系统”,它们都属于“科学之理境”;而中国的宇宙则为“艺术之意境”。前两者虽有有限与无穷之别,但却都遵循科学的法则,其民族文化生活在哲学、艺术与典章制度各个层面上的最高造诣都离不开科学,所以方东美将希腊人与欧洲人的生命情调类型定格为“科学家”。而中国人则舍科学而取艺术,“体质寓于形迹,体统寄于玄象,势用融于神思”,“播艺术之神思以经纶宇宙,故其宇宙之景象顿显芳菲蓊勃之意境”,所以中国人的生命情调类型是持有“多系于艺术表情之神思”的宇宙观的儒道二家,[5]101他们把宇宙感性地把握为一个空灵的艺术境界。
此外,“情”的问题还牵涉到另一对立面,即“理”。方东美在将希腊、欧洲的“科学型”与中国的“艺术型”相比较时,就已经暗含了他在《生命悲剧之二重奏》《科学哲学与人生》与《哲学三慧》中所论述的“理”与“情”的区分。具体而言,方东美认为情理本是一体而非两截的,“情由理生,理自情出,因为情理本是不可分割的全体”,“宇宙自身便是情理的连续体,人生实质便是情理的集团。”但是人生与世界确实又是分立的,所以情境与理境也就随之分立,“生命以情胜,宇宙以理彰。生命是有情之天下,其实质为不断的、创进的欲望与冲动;宇宙是有法之天下,其结构为整秩的、条贯的事理与色相”,但最终“有法之天下与有情之天下是互相贯串的”[7]。这种情理如一的生命理想的典型案例,在方东美看来总能处于艺术意境中的中国人当然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古希腊人。同样,他们“拿艺术心眼同情地透视宇宙人生”,“情之所钟,理必应之;理之所注,情必随之;情理圆融,物我无间”,[5]57,81天人合德,融汇于普遍生命的大化流行。这样一来,方东美对希腊民族文化特征和生命情调的判断似乎与上述《生命情调与美感》中“科学型”(即“理”型)的观点有所矛盾,这或许是因为他分别强调了希腊文化精神的两个不同侧面。这种生命理想的反例就是近代欧洲在经历了文艺复兴时代之后,它的“宇宙人生之美化”[5]80的精神失落了,它的文化开始走偏,情境告退而理境方滋,从天人合一走向了天人对敌和天人交战。[6]81-82这表现为欧洲人“每好划分主宾、离析身心、范形有别”,“理或远注,情又内亏,实情与真理两相剌谬,宇宙与生命彼此乖违”,“情理异趣,物我参差”,陷入虚无主义的生命悲剧。[5]32,81所以,方东美把理智称为现代欧洲的“鬼胎”和“魔法”。[5]55,67这几乎可谓是现代中国较具先驱性的启蒙现代性批判。
朱光潜在他的人生艺术化思想中也参入了情理之辨。首先,朱光潜也认为人是一种有机体,情感与理性是其固有之天性,既不易拆开,也不宜浪费或压抑,那样只会造成精神的损耗或残废。但是朱光潜认为美感教育或人生的艺术化其实就是“叫人创造艺术,欣赏艺术与自然,在人生世相中寻出丰富的兴趣”,故而其本质“是一种情感教育”。[8] 227-228因此,在此领域中朱光潜强调情胜于理,“有了感情,这个世界便另是一个世界,而这个人生便另是一个人生”;反之,理智的生活是狭隘、冷酷、刻薄的,如果理智暴涨横行,那么“不特人生趣味剥削无余,而道德亦必流为下品”,所以“理胜于情的生活和文化都不是理想的”,“我们试想生活中无美术、无宗教(我是指宗教的狂热情感与坚决信仰)、无爱情,还有什么意义?”[8] 47-49显然,朱光潜在对情与理的褒贬抑扬上与方东美的均衡二者的态度有所不同,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朱光潜是站在美育与人生艺术化的立场上讲他的话的,重情自有其可辩护性。而方东美是在另一个更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发言的,是想从古代思想历史中寻找一种可以补缺时弊的文化理想形态,理路与朱光潜有所不同,这种态度上的差异也就可以存而不究。
二、时态与型范:思想气质之异同
上文提到朱、宗、方三人的人生艺术化思想是他们对时代问题的各自回应之产物。从时间看,宗白华的思考最早,始于1920年,而朱光潜次之,始于20年代末期,方东美最迟,始于30年代中后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在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冲击之后,又继以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失败,而日本不断挑衅,最终悍然入侵,如此混乱的时局导致文化方面尤其是青年们人心惶惶、精神失落而苦闷,一派颓顿。面对此种时代病与青春病,宗白华与朱光潜的反应最为直接,就是以人生艺术化的方案来为青年除烦、解闷,进而为时代与国族把脉、找路。
为此,宗白华在1920年三四月份一气写了《青年烦闷的解救法》《怎样使我们的生活丰富》《新人生观问题的我见》三篇文章。希望青年们尝试建立“艺术的人生观”,首先运用“唯美的眼光”,把社会与生活中的各种无论美丑的现象都当作一种艺术品去看待,这样就能在平凡乃至丑陋中见出美,心中得到安慰、宁静和愉悦,一切忧愁与苦闷、无聊与烦恼就都排遣掉了。但这还只是消极的、静观的一步,仅仅丰富了对外经验,还要以积极奋勇的行动在世界中遍历一切既有与变数,把生活当作艺术品去创造,这样人生的内在经验也丰富了。在这一取径上,朱光潜和宗白华是极为相似的,他在《谈情与理》《谈摆脱》《谈美感教育》《消除烦闷与超脱现实》《看戏与演戏——两种人生理想》等文章中以朋友身份与青年娓娓交谈。朱光潜也要求人生的艺术化要在欣赏与创造两个层面形成合力,首先是艺术式地欣赏,从人生与生活中得到情趣与享受;其次他尤其强调人生本身就是广义的艺术,会生活的人就是艺术家,每个人的生活与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而完整、和谐、本色的生活或生命史就是一种令人惊叹的艺术杰作。[4]92-95朱光潜把这称为人生艺术化的另一层含义,即人生的严肃主义,从而与情趣主义完美合璧。
在那个风声鹤唳、刀兵四起的时代中期冀用人生艺术化的方法来解除苦闷、调剂生活、创造生命,这种务虚的路子看起来显然是极为不合时宜的,宗白华与朱光潜对此其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宗白华在1935年的《席勒的人文思想》一文中认为席勒美育思想的主旨就是“将生活变为艺术”,以实现其文化理想,但是“这个理想在现在看来似乎迂阔不近时势”。[2]115而在《谈美》的“开场话”中,朱光潜也承认在那个危急存亡的年代中,“谈美!这话太突如其来了!”[4]7谈美,甚至主张人生艺术化,看起来这实在太违时太矫情了。相反,时局已然如此,朱光潜认为“现在谈美,正因为时机实在是太紧迫了”,“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大半是由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4]7较之朱光潜,宗白华则稍显谨慎与犹疑,不过他也说“徒然提倡实用,不注重精神人格的培养,在这国家危急的时候,流弊也很大。”[2]261而精神人格培养的重要途径就是美育或人生艺术化,所以“向着这个理想去努力,也不是不可能的,况且古代也不是没有实现过。”[2]115如此,他们二人才抱一种“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的心态,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勉开人生艺术化之言路。
与宗、朱人生艺术化思想的逆势“早熟”形成有趣对照,我们可以稍稍提及他们的同代人梁漱溟人生艺术化思想的“晚出”。梁漱溟早在1927年就做过以“人心与人生”为主题的讲演,30年代又在山东讲过一次,但是由于“九一八”事件和“七七事变”,中国的形势日益严峻,所以他认为“懂人生问题这种没有时间性的研究写作之业”就“延宕下来”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这一“延宕”就是近半个世纪,直达1984年才出版同名著作,在其中梁漱溟的人生艺术化思想才得以呈现。[9]梁漱溟人生艺术化思想的晚出,当然是应景的、入世的,而宗、朱二人思想的早熟同样是另一种应景与入世,区别在于策略的不同。
方东美身处同样的时态之中,不像宗、朱那样对当时国家民族命运与社会人心道德耿耿于怀,他一直保持一种冷静的哲学家的心境,其思考与写作超越了一时一地的国家与民族问题,直入一种类似于梁漱溟所谓的“没有时间性的研究写作之业”中去。这个没有时间性,也没有空间性的“业”就是感性文化状态中的人的生命理想。*由于方东美的论述范围几乎囊括了人类东西方文化的历史与现实,所以仅就人类的范围而言,他的论题可以说是没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方东美的人生艺术化思想是他的文化哲学的有机构件,也是他的“宇宙蓝图建筑术”的一个方法。他的“哲学三慧”(古希腊、近现代欧洲与古代中国)其实是文化三型,不过我们看到其中的西方世界是古今完整的,而中国只是半截中国,有古而无今,这表明方东美在无意识中认为从文化上看中国没有现代史。方东美所以探讨文化类型与生命理想问题,实是出于对人自身的忧虑。
方东美认为当时的工业化时代“是一个突变的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科学与技术支配了人的社会生活,以致人类“几乎无一处不成问题”,都成了“问题人物”,[10]于是宇宙与人生也就不能相合相应,人类再也“寻不着安身立命之所”,[5]28“与他们的住所扞格不入,备感疏离。”[6]65所以方东美怀着一种浓烈的文化乡愁向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寻求智慧与资源,在那里他发现了理想的生命模式:人类与宇宙的普遍生命浑然一体,浩然同流,生机无限,“足以陶铸众美,超拔俗流,进而振奋雄奇才情,高标美妙价值,据以放旷慧眼,摒除偏执,创造浩荡诗境,迈往真、善、美、纯与不朽的远景。”[6]382此时方东美的“宇宙蓝图建筑术”已经完全实现,此时的人已经进入生命的最高境界,是方东美念兹在兹的“大人”了,这个人同时也是真人、善人和美人。
合而观之,我们看到在朱光潜与宗白华的人生艺术化思想中都同时包含艺术式的欣赏与艺术式的创造,朱光潜更多的是强调把人生与生活当作艺术品一样去创造,使之成器,故而其人生艺术化思想是人间的,具实践论气质;宗白华更多的是强调唯美的、空想的静观态度,故而其人生艺术化思想是艺境的,具想象论气质。而方东美从文化类型出发,以和谐圆融的生命情调修复现代性社会状况下人在世界中的生存感受,形成美感境界,故而其人生艺术化思想是宇宙的,具存在论气质。
三、结 语
中国现代的人生艺术化思想的园地中,朱光潜、宗白华与方东美可算是三朵美丽的花,朱光潜热烈,宗白华雅洁,方东美素淡。他们的人生艺术化思想追求不俗,而又气质各异。其中朱光潜与宗白华的人生艺术化思想是显学,论述已丰;而方东美的人生艺术化思想则通常不为人所论及,至多到他的生命美学而止步,我们捅破层纸,把它纳入到这个人生艺术化学术史来探讨,并打破一般的独立个案研究的模式,与朱、宗的思想相比较,形成以三人为模范的三种人生艺术化的言说路径,从而为中国现代的人生艺术化思想研究提供一点讨论。
[1] 陈继法.朱光潜的美学——及其悲剧命运与悲剧精神[M].台北:台湾晓园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
[2] 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
[3] 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1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
[4]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2.
[5] 方东美.生生之德[M].北京:中华书局,2013.
[6] 蒋国保,周亚洲.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方东美新儒学论著辑要[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7] 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M].北京:中华书局,2013:22-24.
[8]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2.
[9] 王广州.从艺术到礼乐:论梁漱溟的审美教育思想[J].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1(6):11-16.
[10] 方东美.方东美先生演讲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3:174,192.
(责任编辑:紫 嫣)
A Comparison of the Thoughts of the Three Sages in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s on Artistic Life
WANG Guang-zho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011, China)
Zhu Guangqian, Zong Baihua and Fang Dongmei, three contemporary aesthetes of a same place, came up with differing views of artistic life that touched on aspects such as life, tastes, compassion and sentiments. Yet their differences were not without similarities. The three of them dealt with the problems of their epochs each in his own fashion, resulting in three approaches to exploring ideas of modern Chinese artistic life — the practical, the imaginative and the existential.
Zhu Guangqian; Zong Baihua; Fang Dongmei; artistic life; comparison
2016-11-2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在家”问题研究》(15YJC720023)、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散文与在家:黑格尔美学中的现代性问题研究》(SK2015A381)的阶段性成果。
王广州(1976—),男,江苏东海人,文学博士,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
B83-0
A
2095-0012(2017)01-00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