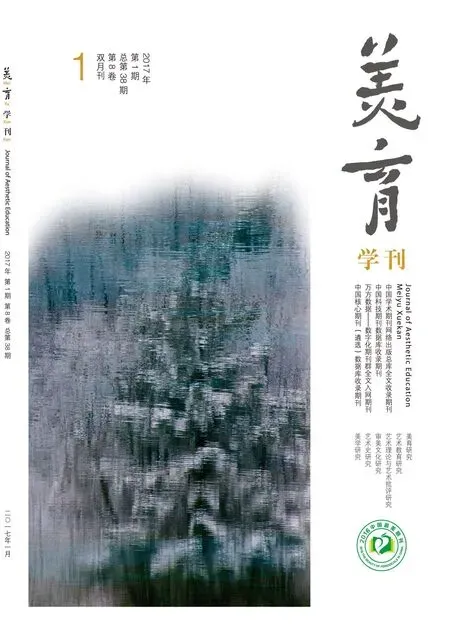个体正义、城邦正义与诗的正义
——论《理想国》中的诗与正义
殷明明
(1.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2.合肥学院 中文系,安徽 合肥 230000)
个体正义、城邦正义与诗的正义
——论《理想国》中的诗与正义
殷明明1,2
(1.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2.合肥学院 中文系,安徽 合肥 230000)
对“正义”的诉求贯穿着《理想国》,在其中柏拉图坚信任何事物只有符合“正义”时,才是善和美的,诗亦不能例外。诗的正义在于能够陶冶和协调人的灵魂,造就正义的个体,而一个理想城邦就是一个由正义的个体组成的正义的城邦。这使他否定了诗的自主性,弱化了其审美价值和娱乐功能,以其伦理政治意义和教育功能为中心。
《理想国》;个体正义;城邦正义;诗的正义
柏拉图对于艺术的态度今天看来过于保守和苛刻,若完全按照柏拉图的意见实行艺术审查则艺术难免窒息。但在批评柏拉图艺术观念偏颇的同时,同样应细查柏拉图做出如此极端论断时的文化逻辑,因为柏拉图并不缺乏审美能力,只是他没有从审美的角度,而是从人性与社会的整体和谐的角度来设定艺术的位置,在文化分裂、人欲膨胀的当下,回顾他对诗与正义关系的理解并非没有益处。
一、理解柏拉图诗学的前提
理解柏拉图诗学的文化逻辑,首先应当明确柏拉图的文化身份,柏拉图涉猎极广,涉及政治学、伦理学、形而上学、诗学等各个方面,诗在其中并没有处于中心地位,他更为关心的是政治哲学问题。
所以《理想国》中当阿得曼托斯询问苏格拉底诗人具体应该怎样创作时,苏格拉底以政治家的气魄回答道:“你我都不是作为诗人而是作为城邦的缔造者在这里发言的。缔造者应当知道,诗人应该按照什么路子写作他们的故事,不许他写出不合规范的东西,但不要求自己动手写作。”[1]73-74因此理解他的诗学,就有必要先了解柏拉图的政治观点。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一样,对作为雅典政治基本形式的民主政体和时而出现的僭主政体都不予支持。他所认可的是王政或贵族政体,因为他坚信城邦应当由那些道德和知识中的精英,也就是那些“知道”的人来治理。但他所处的雅典已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政局频变,僭主政治与民主政治交替,精英统治早已成为历史,他那有着强烈的复古倾向和理想主义色彩的政见并不受当时的民众和统治者欢迎。由于缺少机会和失望,出身政治世家的柏拉图没能过多地介入雅典的现实政治,在叙拉古的政治实践则以失败告终,只能退而在学园致力于培养未来的政治家。因而他的论述是在一种政治焦虑中做出的,大多是对现实政治问题的回应,而不仅仅是一种形而上的玄想。
柏拉图关于诗的观点,同样有着强烈的复古色彩。相对于城邦时代的传统艺术观念,智者学派对于艺术形式因素和娱乐功能的强调才是当时的新见解。这并不是说艺术的形式因素和娱乐功能在此时才出现,它们从来就存在,只是一般不受到哲学家们的重视,未受到理论关注。智者学派则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雕塑)是对真实的人体的模仿,它们给观看者以快乐,但却没有任何实用目的。
美是通过视听给人以愉悦的东西。
画家只有在通过许多色彩和形状创造一个形体或形式时,才给眼睛以愉悦。创造人和神的雕像给视觉以愉悦。[2]139-140
《理想国》没有接纳这种时尚的感官主义,柏拉图反潮流地将艺术在城邦形成和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作为艺术价值的典范。城邦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模式,在西方历史中只存在于希腊地区,而且存在时间不过几百年。根据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说法,城邦和现代国家不同,它并不建筑在领土概念之上,而是建筑在一种政治认同感之上。[3]122
艺术则在构成与强化这种认同感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希腊人日常生活设施简单,最堂皇的建筑是公共建筑,神庙就是最雄伟的一种,其间供奉着城邦各自的保护神。神庙并非一开始就有的,最初的宗教仪式在露天举行,“到了公元前8世纪左右,随着城邦时代的到来,人们开始在圣地建造神庙”[4]52。通过庄重的建筑和伟岸的神像,城邦确立了各自的标志,强化了城邦的凝聚力,所以“神庙也就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建筑,而且也是城邦的标志,是国家意识的体现。神庙越多越豪华,则表明国家愈强盛愈蒙神宠,也就愈能增强公民的爱国心和自豪感”[4]52-53,这也是为何随着城邦制的发展,神庙数量亦不断增多,“公元前7世纪大约有三十九座,公元前6世纪已有八十八座”[4]53。各种艺术手段和贵重材料都被用来装饰神庙,最好的艺术家也服务于神庙,米隆、菲狄亚斯都是如此。
同时,以神庙为中心形成了城邦公共活动空间,各种仪式、庆典都围绕着它进行,而这些仪式庆典又包含着音乐、戏剧等艺术形式,“在这些活动中,由仪式所带来的共同的敬畏和共同的希望,通过人们共同的关注,将团体中的不同个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而形成一种社会伦理控制的巨大力量”[4]45。
艺术除了用于宗教,还被用在各种纪念性事务上,如神话、史诗,保存和延续各个城邦的起源,为城邦公民提供了集体记忆。造型艺术也如此,“纪念性雕刻也是希腊雕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既用以庆祝战场上告捷奏凯的胜利,也用以表彰运动场上竞技夺魁的青年,就是两城之间缔结的条约,希腊人也将之铭碑勒石,以志纪念。”[5]
可见,在城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艺术有助于形成和加强各个城邦的凝聚力,有益于公民和城邦构成和谐的共同体。但随着城邦的繁荣和文化的分化,人们日益关注艺术的形式美,智者学派对于艺术形式因素和娱乐功能的重视正是对这种潮流的概括。但这种新思想却为柏拉图所反对,他顽固地反对将艺术的意义建筑在感官愉悦之上,依然坚持艺术必须是一种有益于城邦的活动,否则他宁可放弃艺术。
二、个体正义和诗的正义
作为一部政治哲学著作,《理想国》虽然讨论了艺术方面的问题,但它的核心议题并非艺术,而是城邦政治。一个理想的城邦,在柏拉图看来,应当是由“正义”的个体构成的“正义”的城邦。艺术在这个理想国中首先是一种教育手段,柏拉图希望能够延续艺术在城邦形成和鼎盛时代所发挥的陶冶和凝聚作用,培养出“正义”的个体。
柏拉图的“正义”不完全是现代政治或法律意义上的“正义”,它更多的是一种伦理原则,是一种德性,用现代的学科分类来说,“正义”既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伦理概念。对于城邦,正义是一种政治秩序;对于个体,正义是灵魂秩序。柏拉图把人格分为三个部分:理性、激情和欲望。三者等级分明,理性是其中高贵的部分,欲望是其中低贱的部分,激情则摇摆于两者之间。理性和欲望之间存在着矛盾,激情可能服从于理性,也可能服从于欲望。所以“正义”带来的和谐并非三者的绝对平等,而是三者按比例分布,它必须是理性占主导地位,能够协调激情,实现对欲望的控制,就是他所言的:“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自身内的各种品质在自身内各起各的作用,那他就也是正义的。”[1]169
这种以“正义”为中心的伦理观决定了柏拉图的艺术观和他艺术观的功利性质。对此柏拉图毫不掩饰,他直言道:“我们一定先要找出正义是什么,正义对正义的持有者有什么好处,不论别人是否认为他是正义的。弄清楚这个以后,我们才能在关于人的说法上取得一致意见,即,哪些故事应当讲,又怎样去讲。”[1]94
因此,柏拉图最关注的不是艺术自身如何的美或精彩,而是关注艺术对公民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符合柏拉图哲学的逻辑,他在《理想国》开篇不久就提出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任何技艺都不是为它本身的,而只是为它的对象服务的”[1]24。艺术也不能例外,艺术对人格的各个部分都可以产生作用,它既可以促进人的理性及勇气,又可以滋长人的非理性、懦弱、狂暴等恶劣情绪。所以对艺术的调控非常重要。只有当艺术有益于个体正义时,它才能被理想国接受,反之,再精彩的艺术也要被驱逐。具体而言,艺术必须能够不断强化理性的力量,而绝不能增长了欲望的力量,那样的结果将是欲望联合了激情,压制了理性。
从这一立场出发,柏拉图首先反对的是有不道德内容的艺术。柏拉图指责荷马以及其他艺术家们把神和英雄写得充满了贪婪、傲慢、好色、残暴、好斗、放纵等恶劣品性,可以说是具有了人类所有的道德缺陷,甚至比人类的更加极端。他认为当艺术的感染能力和这样不道德的内容结合在一起时,将是一剂可怕的毒药。这会为人们提供了反面典型和自我安慰的借口,当人们有了类似的恶行时,人们会说连神都是如此。他在列举了荷马一些描写地狱恐怖的诗句后说:“如果我们删去这些诗句,我们请求荷马不要见怪。我们并不否认这些是人们所喜欢听的好诗。但是愈是好诗,我们就愈不放心人们去听,这些儿童和成年人应该要自由,应该怕做奴隶,而不应该怕死。”[1]84他如此评断诗歌原因就在于不道德的内容通过艺术的魅力将给予公民以坏的指导,腐蚀他们的灵魂。因此柏拉图强调:“神是善的原因,而不是一切事物之因。”[1]76对于那些描写了神的恶行的作品,柏拉图认为不仅丑恶而且虚假。[1]72
柏拉图反对的第二种艺术是激起欲望的艺术。绘画迎合了人的观看欲,这在柏拉图看来是一种拙劣的模仿,是对视觉错误的利用,将会扰乱人的心智。戏剧同样是人性弱点的需求,柏拉图认为人时刻都应当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戏剧恰好相反,它模仿人的欲望,并以激起人的欲望为目的,“舞台演出时诗人是在满足和迎合我们心灵那个(在我们自己遭到不幸时被强行压抑的)本性渴望痛哭流涕以求发泄的部分”[1]405。在这样的状态中得到的快乐,柏拉图认为是一种可耻的享受,会削弱人高贵的理性而滋养低贱的情感。
这也是为什么柏拉图尤其强调面向儿童和青少年的艺术应当严加审查。柏拉图基本上认为所有城邦公民都不应受到不良艺术的影响,特别是面向儿童的艺术必须完全优美高尚。柏拉图认为儿童缺乏识别能力,“年轻人分辨不出什么是寓言,什么不是寓言”[1]73,他们最容易受陶冶,因此只有最严格的艺术,才能保证他们心灵的健康成长。那些少儿不宜的故事,如天神弑父的故事,并非一概不能讲述,但必须严格限定受众和宣讲条件,“只能许可极少数人听,并秘密宣誓,先行献牲,然后听讲,而且献的牲还不是一只猪,而是一种难以弄到的庞然大物。为的是使能听到这种故事的人尽可能的少”[1]72。
只有那些歌颂神明、好人和美德的艺术才能被柏拉图接受。因为柏拉图认为人的天性善于模仿,连续的模仿会形成习惯,习惯则是一种“第二天性”,会影响人的心灵和言行。所以柏拉图坚信,艺术必须符合伦理的准则,必须由伦理加以指导乃至强迫,在《法篇》中他同样强调:
真正的立法家会进行劝告,劝告无效就强迫,拥有诗人天赋的人必须创作他们应该创作的东西,用高尚精美的诗句来再现好人,用适当的节奏来再现好人的心怀,用优美的旋律来再现好人的节制,这些人是纯粹的,高尚的,简言之,是善的。[6]407
这在当时并非是孤立的看法,就像阿里斯托芬的《蛙》中埃斯库罗斯指出的,“教训孩子的是老师,教训成人的是诗人,所以我们必须说有益的话”[7]446。他的对手欧里庇德斯也不得不承认,艺术家的意义在于“因为我们才智过人,能好言规劝,把他们训练成更好的公民”[7]444。
三、个体正义、城邦正义和诗的正义
通过艺术实现个体正义并不是柏拉图诗学逻辑的终点,他的诗学的逻辑是:诗的正义——个体正义——城邦正义。换言之,柏拉图的诗学服从于他的伦理学,而他的伦理学服从于他的政治学。
在古典思想家那里,政治和伦理并无本质区别。在中国,人们已经普遍认同古代中国政治的伦理意味。在古典希腊同样如此,柏拉图指出,正义的个体与正义的城邦有相同的内部构造,他相信仅就正义的概念而论,一个正义的个人和一个正义的国家并无质的差异,有的只是量的区别。[1]57而且两者密不可分,只有正义的个体才能组成正义的城邦,也只有正义的城邦才能捍卫个体的正义。这就形成了伦理以政治为目的,政治以伦理为内容的复杂关系。
这种思想,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脉相承,他们都坚信城邦是最高的善,个体的善只有依赖于城邦才能实现,只有神祇或野兽才可能不属于任何城邦。“人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3]7,所以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开篇就写道:“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社会社团(城市社团)。”[3]3
现代学者们也相信,古典思想家们“把国家设想为一个道德共同体,并且作为其后果,从一个伦理的视点来看待它的研究对象”[8]14。泰勒明确指出:“根据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观点,在道德和政治之间,除方便的区分外,没有区别。公正的法则,对阶层和城邦和对个人是一样的。不过我们必须补充说,这些法则首先是个人道德的法则;政治建立在伦理学上,而不是伦理学建立在政治上。《理想国篇》中提出的并最后在其结尾中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严格的伦理问题。”[9]麦金太尔也讲:“实际上柏拉图的道德学说和政治学说紧密地相互依存着,缺少一方,另一方就没有逻辑上的完整性。”[10]
对于古典思想,不仅艺术,伦理问题亦并非自足,它以政治为其规定性。这也是为什么《尼各马科伦理学》在开篇不久便指出政治是最高的善,是所有学科的最终目的。[11]对此,罗斯解释道:“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关于社会的,他的政治学是关于伦理的,在《伦理学》中,他没有忘记个体的人是基本的社会成员,在《政治学》他也没有忘记国家的善的生活仅仅存在于其公民的善的生活中。”[12]
艺术最令柏拉图不安的地方,不在于艺术是一种拙劣的摹仿,是“影子的影子”。柏拉图并不一概反对不真实,他承认为了城邦利益,城邦的保卫者可以说谎。在他看来,艺术更危险的地方是艺术确实有影响和塑造人心灵的能力,却没有将这种能力使用在“正义”之上,当荷马诗篇中有符合他正义观的地方,他也赞赏荷马。
四、柏拉图诗学正义论的局限和意义
塔塔科维兹正确指出,在柏拉图的思想体系中,艺术根本没有自主地位[2]165。的确,柏拉图没有轻视艺术,他明白艺术有极大的影响人灵魂的能力,但他决不孤立地思考艺术,艺术只是城邦文化的一部分,并不享有特权。在柏拉图看来,单纯形式美的意义是贫乏的,艺术不可能因自身的美而美,只能因善或者说因实现了正义而美。柏拉图诗学中那些极端保守的观点,并非由于他的无知或缺乏审美能力,而是因为《理想国》中的他始终以城邦缔造者的身份在思考,为了城邦正义他宁可舍弃那些危险的美,为了理性的坚强他宁可放弃情感的丰富。
这并非无可指摘,柏拉图严苛的艺术审查没有给艺术发展留下太多空间,他对个体的辨识能力也过于缺乏信心,对艺术与理性、情感的关系的理解也过于简化。与柏拉图认为那些有着怜悯、恐惧等内容的艺术会迎合、滋长人灵魂中这些低劣成分,因而与应严格禁止的观点不同,亚里士多德便认为即使是表现了怜悯、恐惧等内容的艺术也有着积极的伦理意义。亚里士多德指出对这些情绪的激发能使之得以合适的疏导,不仅不会有害于人的理性,反而会平衡人的内在状态,有益于人格的和谐。
但是,柏拉图诗学正义论的基本立场所具有的强烈现实感依然有其重要意义。当代社会已然是一个不缺乏美的艺术的时代,从城市景观到衣服饰品,从剧场戏院到电视电脑,各种形式的美充斥于其中,如韦尔施所言:“这股潮流长久以来不仅改变了城市的中心,而且影响到了市郊和乡野。差不多每一块铺路石、所有的门户把手和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没有逃过这场审美化的大勃兴。”[13]4-5
这的确是一种进步,人类的感性需要由此获得极大的解放和满足,艺术挣脱了伦理和政治的束缚,仿佛获得了全面的胜利,人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美好艺术的世界之中,“古老的审美化工程之大功告成,是它先前的辩护者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一切都变美了”[13]166。
但艺术的这种胜利不是没有代价,如果把这些具有美的外形的人工制品都称之为艺术的话,那么意味着艺术被简化为感性形式,这无疑是对艺术的一种贬低,是柏拉图绝对无法接受的,恰如杜威指出的:“‘形式’并不是‘艺术的’和‘审美的’因素的特有的属性或创造,它们只是任何事物借以满足使人愉快的认识的要求的符号。”[14]所以韦尔施在描述了当代社会现实日益审美化的同时,毅然指出:“无论如何,没有人敢说当今的审美化肯定是成功的。”[13]111
科林伍德就认为,这些仅仅具有形式美的艺术,意在激起某种情感,但不是将其导入现实,而是“作为本身有价值的某种东西加以享受”[14]80,将其释放在虚拟情景中。他进一步指出,在可能被激起的各种情感中,情欲是最容易被利用的,这就导致了各种激起情欲的娱乐艺术的泛滥。从柏拉图诗学来看,这完全是一种“非正义”的艺术。如果现实中充实的仅仅是这样的艺术,那么的确是艺术的悲哀。科林伍德就相信,一味迎合人欲望的艺术将导致人们沉溺于虚拟的空间之中,减弱人们对实际生活有益的情感能量,使人厌倦现实生活,最终导致“完全丧失了对实际事务、对日常生计和社会义务都是必要的工作和兴趣和能力”[15]98。
按照柏拉图的正义论诗学,情况可能比科林伍德所描述的更糟糕,非正义的艺术在燃起各种情感之后将会影响现实,造就的将是一些非正义的个体,最终出现的是非正义的城邦。当然,这有些夸大了艺术的作用,柏拉图也没有认为艺术是实现正义的唯一手段,在他的教育体系中,数学、几何学等学问对实现正义同样重要,其中最重要的则是辩证法。
今天重温柏拉图对诗与正义关系的理解,并不是要在当下复制他的观点,这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即使在城邦时代,他的观点也仅仅是一种观点,他对民主政体的反对和对贵族政体的怀念在当时并不受欢迎,连他自己都承认他所描述的理想国只是一个存在于天上的原型。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都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城邦政治的命运,柏拉图写作《理想国》时,雅典已经衰败;亚里士多德写下《政治学》时,雅典已经败于马其顿王国。他们的著作,已经是对希腊城邦政治的总结和批判,更多的是留给后世的文化遗产。
重要的是柏拉图思考诗学问题时所具有的视野和责任感,他的诗学固然因掺杂着政治焦虑而显得僵化,但其中凝结的是他对人的灵魂以及人赖以存在的社群的深沉关怀,这种使命感使他以一种更高意义上的诗人自居,在其最后一部著作《法篇》中他就认为,摹仿了最优美最高尚生活的城邦才是真正的悲剧,城邦的立法者是真正的诗人[6]576。为此他可以克制自己的审美冲动,不惜抨击他青年时代曾倾心的艺术和他所敬爱的荷马。毕竟,人类的任何一种行为和产品,都只有在其有益于个体和群体发展时,才有充分的合理性。为了人和城邦的正义,对诗进行一定程度的审查,甚至做出一些伟大的放弃,无损于诗的尊严。
[1]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 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M].杨力,耿幼壮,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4] 吴晓群.古代希腊仪式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5] 里本特.希腊艺术手册[M].李本正,范景中,译.杭州:中国美术出版社,1989:5.
[6] 柏拉图.法篇[C]//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7] 阿里斯托芬.蛙[C]//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8] 巴克.希腊政治理论[M].卢华萍,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4.
[9] 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M].谢随之,苗力田,徐鹏,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378.
[10] 麦金太尔.伦理学简史[M].龚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85.
[11]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4-5.
[12] 罗斯.亚里士多德[M].王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06.
[13] 尔施.重构美学[M].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14] 杜威.经验与自然[C]//当代美学.李普曼,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76.
[15] 科林伍德.艺术原理[M].王至元,陈华中,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紫 嫣)
Individual Justice, Justice of the Polis and Poetic Justice: Justice and PoeticsinTheRepublic
YIN Ming-ming1,2
(1.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fei University, Hefei 230000, China)
Justice is a core concept inTheRepublicin which Plato deems that all things, including poetry, must correspond with justice to be good and beautiful. Poetic justice makes for upright individuals by virtue of tempering and coordinating the human soul and an ideal polis is a just polis composed of upright individuals. This leads Plato to deny the autonomy of poetry, downplay its aesthetic and recreational value and give a central place to its ethical, political and instructive function.
TheRepublic; individual justice; justice of the polis; poetic justice
2016-09-22
殷明明(1980— ),男,安徽黄山人,文学博士,合肥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西方文论、欧美文学研究。
I106
A
2095-0012(2017)01-008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