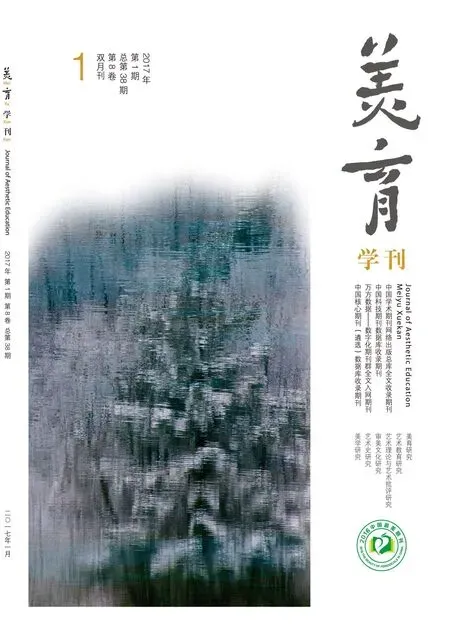热恋自然
——威廉·莫里斯的生态美育学启示
张 锐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热恋自然
——威廉·莫里斯的生态美育学启示
张 锐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19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艺术家威廉·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中构建了一个爱美的乌托邦。莫里斯的美育观集中体现在人类与自然的热恋关系上。乌托邦民众在森林中野营,与自然畅意游戏,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莫里斯突破了自康德以来的静观美学, 主张积极的参与美学,通过创造性的手工劳动来创造艺术和美。乌托邦民众热爱地球,将地球视为情之所依的恋人,将生命融入恋人季节更迭的节奏。与现代生态美学中的“家园意识”和“四方游戏说”异曲同工。莫里斯并非全然“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者,他在强调自然审美属性的同时,关注艺术的道德属性以及教育意义,期待乌托邦民众师法自然,热爱自然,通过与自然亲密无间的恋爱,熏染出向善的气质和审美趣味,从根本上克服人类的异化,恢复人之为人的完整性。
威廉·莫里斯;生态美育学;热恋自然
“热恋自然”是一种充满浪漫和诗情的境界,人与自然不仅和谐共处,而且亲密无间。这种境界一直徘徊于诗人与哲人的想象当中,无人能述说人类终将如何与自然热恋。150多年前,英国杰出的思想家威廉·莫里斯(1834—1896)在自然与生活之美中找到了人类与自然的浪漫之路,并深入细致地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向人们解读这种诗意。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中勾画了如此爱美的乌有乡民众。他们对美的追求不仅表现在服饰、建筑以及日常生活的细节上,更显现于居民的气质和容貌。莫里斯的诗意解读丰富了生态美学的研究,尤其是他的教育思想对现代美育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都有一定的启示。
一、“热恋自然”美育思想的形成
莫里斯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是大英帝国的巅峰时期。工业革命的急速推进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环境,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使人们日益异化。面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人类的异化,英国的文学界作出了积极回应。其中最突出的是以狄更斯小说为代表的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以及以华兹华斯、拜伦和雪莱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美学界自席勒以来就敏锐地意识到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朱光潜分析了马克思和席勒对于人类异化问题的相异之处:“面对异化,席勒将‘完整人格’或 ‘优美心灵’作为最高理想,马克思把病源诊断为私有制,把私有制的消灭定为唯一的根本治疗方法。而席勒把病源诊断为人心腐化,于是就把审美教育定为治疗社会的方剂。”[1]莫里斯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观点,在肯定消灭私有制这一前提下,莫里斯同时发出了热恋自然、回归艺术生活的呼声。在莫里斯构建的乌托邦社会中,手工劳动本身就是创造美的艺术,就是生活的最大报酬。在手工劳动中,人类走出异化,实现了自己的全面发展,恢复了人自身的完整性。
(一)莫里斯对转型时期教育体制的解构与重建
面对日益严重的人类异化问题,莫里斯在他的小说中对现存的教育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提出现存教育的全部理论不过是“必须把一些知识灌输给儿童,即使用苦刑的方法来达到目的也在所不惜”[2]80。而结果是“多数人所得到的仅仅是少得可怜的不很正确的知识,人们硬要把这种知识塞给刚刚知道生活艺术的人,不管他们喜欢不喜欢,也不管他们是否有这种要求。同时,这种知识还由那些对知识漠不关心的人再三加以咀嚼消化,以便灌输给别的对知识漠不关心的人”[2]79。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的教育就是一场“苦刑”,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师和学生,对知识本身都是“漠不关心”的,他们关心的只是这些所谓的“不很正确的知识”带来的一切功利价值和金钱。莫里斯指出教育的极端功利化和庸俗化加剧了人类的异化。因此,在乌有乡中,莫里斯彻底解构了现存教育体制。
(二)对“教育”和“学校”概念的解构
乌有乡中的民众完全不能理解“school(学校)”究竟为何物,“我”理所当然地解释为学校是一种教育制度。当他们再次对“educate(教育)”这个词表现出无知时,我略带轻蔑地说:“教育就是一种教育年轻人的制度。”[2]35“为什么不连老人也加以教导呢?”[2]35当地人对“我”的诘问同时也是对现存教育体制的拷问。现存的教育是分裂的,在现存的教育体制内、学期与假期、教室与户外、学龄与非学龄、老师和学生的二元对立加剧了人的异化。莫里斯对存在千年的学校教育进行了深刻剖析。他甚至摈弃“学校”“教育”等习以为常的字眼,仅以“路边的孩子”专章来探讨教育问题。莫里斯并未刻意将教育分裂成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也没有将不同年龄的孩子按年级划分,而是让不同年龄的孩子们一起生活、学习,相互激发。教育本身应该是个整体,孩子的成长过程与学校的所谓教育过程不可能泾渭分明。这种教育没有教材,也没有学科分类,而是将人囊括于自然的大美之中,与林木、鸟兽一起沐浴雨露风霜,亲身参与四季的更迭,热恋自然,熏染出真善美的性情。这是对现代教育较彻底的解构。
(三)森林教育概念的重建
莫里斯有破有立,他的教育观集中体现在《艺术与劳动》这篇演讲的开头,“合理愉快的工作, 美丽的环境和无忧无虑的休闲才是教育最核心的部分(Education means reasonable, pleasant work, and beautiful surroundings, and unanxious leisure, these are essential parts of it)”[3]。换言之,教育不过是人们在美好的环境中愉悦的劳作和无忧无虑的休闲。在乌有乡,孩子们和成人的教育就是在美好的夏日去森林中野营,教育也同样发生在晒干草的田野和宁静的小溪边。“‘无论我们的孩子有没有一种教导制度’,都在进行学习,这里你找不到一个不会游泳的,他们每一个人都会骑着林中小马到处跑,他们全都会做饭做菜,年纪大一点的孩子会割草,许多孩子都会用稻草盖屋顶,都会一些零星的木工活,他们也会经营商业。”[2]35这就是乌有乡的教育,这些手工劳动是乌有乡中老少拥有良好审美趣味的源泉。莫里斯对森林中的野营作了详尽的描述:
这座肯辛顿森林虽然充满罗曼蒂克气氛,但并不孤寂荒凉。我们遇到许多人群, 或来或往,或在森林边缘漫游。在这些人群中有许多儿童,年龄从六岁,八岁,到十六岁,十七岁不等。在我看来,他们是他们的种族特别优良的标本。他们显然是在尽情享受着生活的乐趣,有的在那些搭在草地上的小帐篷附近荡来荡去,有些帐篷旁边生着火堆,火堆上悬着锅子,像吉普赛人那样。[2]33
夏日附近乡间各地的孩子成群结队地在森林中野营数周,以此为家。同时,莫里斯提到众多成人也去更大的森林野营。那些“漫游”“荡来荡去”的孩子一定是无比愉悦地发现和探索森林之美。在乌有乡,教育本身就是林间最天真原始的游戏。他们不仅用眼睛,而且用身体,用心去热恋自然。这种游戏的心境逍遥且诗意,正合海德格尔的“四方游戏说”。
(四)莫里斯的“恋爱说”
“海德格尔的‘四方游戏说’指的是人与自然如‘婚礼’一般的‘亲密性’关系,作为与真理同格的美就在这种‘亲密性’关系中得以自行植入,走向人类审美的生存。”[4]正如乌有乡中深谙历史的老者喊出的那样:“新时代的精神,我们时代的精神,就是热爱尘世生活,强烈地,充满了骄傲地爱人类所居住的这个地球的外壳和表面,正如情人对他所爱恋的女子的美好肉体所发生的那种爱一样,这就是时代的新精神。”[2]163无论是海氏的“婚礼”和“亲密性”,还是莫里斯的“爱恋的女子美好的肉体”都表明,他们的对自然的热恋不是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而是深深地被地球的外壳和表面、地球上的万物之美所倾倒而自发的本能的爱恋,热恋中的自然与人类相互栖息,更加尽善尽美。正如莫里斯反复强调乌有乡民众都拥有出众的容貌。自然与人类都在热恋中趋向完美。
海德格尔著名的壶之例证说得绝妙,“壶的物性,不在制造壶之原料,也不在壶的具体的有用性,而在壶之赠品即倾注物中成其本质。在赠品之中有泉,在泉中有岩石,在岩石中有大地的浑然蛰伏。这大地又承受着天空的雨露。在泉水中,天空与大地联姻,在酒中也有这种联姻。酒由葡萄的果实酿成,果实由大地的滋养和天空的阳光所生成。在水之赠品中,在酒之赠品中总是栖息着天空与大地。”[5]
如果将乌有乡众人比之于壶,那么人的形貌及趣味即为壶之赠品,乌有乡中人之形貌已大大改良,仿佛是优良品种的标本。爱伦是乌有乡人类之美的化身,试看“我”第一次看到如仙子的爱伦,“当我们走进一间很漂亮的茅草屋,壁上饰着雕刻的嵌板,干净无比,可是房中的主要的装饰却是一个年轻的女人。”[2]184因为天地自然之美已经在人的外壳和体内栖息。人与景相互栖息,互为装饰。中国自古有“为悦己者容”的雅俗,乌有乡的男女无不为“悦己者容”,更因“悦己者”而容。这里的“悦己者”就是自然。这是全人类的情人与热恋对象。哈蒙德老人发出了由衷的感慨:“现在组成人类的男女至少都是自由幸福的,生气勃勃的,往往身体也很健美,周围全是他们自己所创造的美好的东西,大自然跟人类接触以后变得更好,而不是变得更坏了。”[2]164莫里斯特别提到母亲和女人的美,再也不是娇柔易逝的,而是一种接近真理的永恒之美,母亲们再也不用焦虑孩子的未来,人人都生活在与天地神人的惬意游戏之中。在乌有乡中,人创造的手工之物是大自然及天地万物的映射,不仅原料本身来自于大自然,穿在身上的织物,所用之器皿,都映射天地万物之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五)森林教育所体现的“家园意识”
在莫里斯看来,森林是人类的家园,人在森林中能够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人类如同森林中的动植物一样自然成长,遵循自然的节奏,倾听自然的声音,关心自然如同关心自己。整个小说中弥漫着一种浓浓的“家园意识”。
莫里斯对森林的热恋源于莫里斯童年嬉戏的埃平(Epping)森林。莫里斯的传记中多处提到这片森林,这是给莫里斯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带来无数灵感的处所。 “他生活在这片野生鸟兽活跃的森林,这对一个酷爱户外生活的小男孩来说简直是天堂。在这里,莫里斯与他的兄弟们赤脚漫游,或者骑着他们的小马驹穿越森林。”[6]7莫里斯一生挚爱着埃平森林,这些茂密的灌木,即使晴空万里,在它幽深的树荫下,也会感受到深沉的庄严和神秘。这片充满诗意和神性的埃平森林成为莫里斯终身魂牵梦绕、难以割舍的爱恋。传记作者这样评论道:“难以估量这片森林对莫里斯这种敏感而浪漫天性起了多大的作用, 或者说对他一生对地球和自然之美起到了多大的激发作用。”[6]13森林成为他终身情感所依的家园,与现代城市人茫然失其所在的“无家可归”的落寞感形成鲜明对比。人唯有回归自然中才能拥有家园。乌有乡的每个人都热爱和珍惜自己的家园,那种与自然水乳交融之美体现了强烈的家园意识。
森林寄托了莫里斯自身的无限乡愁,森林是自然中物种最丰富、层次最分明的地理形态。森林不仅是指以乔木为主的植物群落,更包括动物和微生物,以及所有林间的地质和地貌。森林的美学意义早已被发现,但森林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然陌生而遥远。而对于莫里斯和乌有乡的民众来说,这是他们熟悉的地方,是与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场所。这里的松涛、燕雀和小马驹都很容易被识别,能带给他们愉悦的体验,他们的记忆中充满了情感。所有的生物都给他们以个性的温馨,森林中的他们感到了自在和惬意。“在这里,人们会热心地讨论天气啦,干草的收获啦,最近落成的房子啦,某种鸟儿太多,某种鸟儿太少啦等等,而且他们在讨论这些东西的时候,不是空泛地,依照惯例地随便谈谈,而是具有——我敢说——真正的兴趣。”[2]212乌有乡民众对森林的感同身受来自他们与活生生的森林动植物同呼吸、共命运。正如罗尔斯顿所说: “我们开始可能把森林想作可以俯视的风景。但是森林是需要进入的, 不是用来看的。一个人是否能够在停靠路边时体验森林或从电视上体验森林是令人怀疑的。森林冲击我们的各种感官: 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甚至是味觉。视觉经验是关键的,但是没有哪个森林离开了松树和野玫瑰的气味能够充分被体验。”[7]正如恋爱的世界里,我们不仅是用眼睛,而且用尽我们所有的感官,去进入,去触摸,去碰撞。
(六)圆融通透的教育模式恢复人类的完整性
莫里斯的教育观圆融通透,打破了教育时空的隔阂,重塑教育时间的连续性和空间的完整性。消除了体脑劳动的隔阂,弥合了德智体美劳及各科教育的鸿沟,在游戏中恢复了教育的完整性。首先,莫里斯的教育观打破了教育的时空隔阂。现代的教育总把教育框定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仿佛学校教育的终结就是整个教育历程的终结,教育是封闭的,缺乏开放性。当无限焦虑的现代父母将孩子受教育的年龄无限提前催长时,莫里斯借哈蒙德之口语重心长地说:“we can afford to give ourselves time to grow.我们应该慢慢成长。”[2]118乌有乡从不把教育框定在一个时间段,我们所有的生活劳绩都是教育。乌有乡无论是百岁老人还是黄口小儿都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莫里斯认为教育必须遵循自然的节奏,人的生长如同自然万物,需要时间和等待。其次:打破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界限,弥合了德智体美劳等分课程教育的鸿沟。分裂的“学校教育”永成历史。在森林里,我们既是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也是陶冶一种上善若水的品格,既是愉悦的劳作,也是对身体肌肉、皮肤及整个骨骼的锻炼。在这里清洁工可以写戏剧,历史学家也可以当纺织工人。再次,所有的教育不再是冷冰冰的、漠不关心的教育,这里高扬着感性的力量。真正的学习都来自兴趣和热爱。所有的学习都是自发与本能的,正如植物的生长需要雨露一样,人对知识和技能的获取是人类自我成长的自然自发过程。教育再也不是一种“苦刑”。
现代教育看似一个整体,却是各种碎片化的分割组成的一个机械、松散的整体,缺乏内在统一性和有机生动性。莫里斯消解各种差异及分裂之后,人的感性呼之欲出。在乌有乡中,所有人都热切地表达他们对自然万物的爱恋。孩子们如同动植物一样, 拥有足够的时间去发展他们的各种感觉系统,在完整有机的教育之中,人类恢复了各自的完整性。
二、莫里斯对现代美育学的启示
(一)艺术到底是什么?
关于艺术是什么?莫里斯的回答颇有新意。“艺术就像我们吃的面包,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8]它平凡得如食物与空气,栖息于我们的身体内,当它存在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当它不在的时候,我们却无法生存。它已然成为我们生命的本能,它是我们身体无法分割的一部分。关于如何发展艺术,莫里斯提到:“我现在所谈到的这种艺术,或者应该称为工作的乐趣,看来几乎是从人们的本能中自发产生出来的。这种本能就是希望把自己手里正在做的工作做好,希望能够做出优良的产品,这样工作了一个时期之后,心中似乎就产生了一种对于美的渴望——他们一旦开始了这方面的活动,艺术便开始发展起来了。”[2]165手工劳动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而且每一件物品都精雕细琢,代代相传。艺术就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与劳动之中,存在于我们将房子建得更精致,存在于我们的衣着更得体美丽。所以,劳动的场面总是那么美好,人们穿着美丽精致的刺绣和天鹅绒服饰去劳作,人们劳动时体态是无比优雅的,参与劳动的男男女女们的肤色是那么健康美好。连堆满干草的草地也美如“郁金香花坛”。[2]192对于莫里斯来说,“艺术更关乎生命。通过艺术地生活,人的生命可以从劳动的愉悦中获得意义,可以融入过去与未来,融入社会和大自然,也就可以实现超越,融入无限”。[9]
现代美育大部分从艺术品欣赏入手来提高人的审美判断和鉴赏力,美育基本沦为艺术美学。莫里斯几乎摈弃了被现代美育无比推崇的历代艺术精品,而直接转向自然。莫里斯认为作为自然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对人类审美趣味的培养起了更直接、更本源的作用。自然本身就是一切美之源泉,也是人类的终极理想之境。艺术不再是奢侈品,不再是属于少数人享受的所谓艺术品。在乌有乡已经没有所谓的“艺术品”:“一句话,我们所采取的补救方法就是进行过去所谓艺术品的生产,我们现在没有艺术品这个名称,因为艺术已经成为每一个生产者的劳动的必需组成部分了。”[2]165
在莫里斯看来,任何一部艺术作品本身都是部分的、片面的、瞬间的。是人作为主体与被作为客体的艺术品相孤立。与艺术品相比,自然物是没有框架的。在自然中,人既是欣赏者也是被欣赏者,即是参与者,也是被参与的对象。人永远是自然景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完整性是人回归自然的依托。
(二)艺术更美还是自然更美?
现代美育学对自然美的忽视源于席勒, 虽然席勒自称:“我所研究的理论依据主要是来自康德提出的原理。”[10]2但正如彭锋提出的那样:“席勒的思想代表了西方美学关于审美教育功用的一般观点,但它显然是对康德思想的庸俗化发展, 尤其是掩盖了康德关于自然美的深刻洞见。”[11]席勒在《席勒美学信简》的第三封信中提到:“人之所以是人,正是因为他不会停滞在自然创造他的那个阶段,而是他可以通过理性来指导自然赋予自己行动的能力,可以重温自然带领他走的路程, 可以将必需的自然产物转变为自由的产物, 可以把必需的物质升华成精神的法则。”[10]6席勒认为自然和自然之物与人类最理想的自由状态是相背离的,自然被认为是粗鄙的, 急需人类通过崇高的理性去努力摆脱的状态。最终让人变得自由的是艺术。在席勒的世界中,艺术美显然高于自然美。
受席勒的影响,美育学绝大部分是关心艺术的,很少关心自然美,因此席勒所谓的美育主要是指艺术教育。在席勒那里,美主要指艺术美而非自然美。莫里斯却热切地讴歌自然之美。在莫里斯的观念中,自然是全美的,他并没有发现自然本身任何丑的东西,只有庸俗之徒的粗制滥造之物及机器制造的刻板物品才是丑的。虽然莫里斯很少提到“艺术”或“审美”这样的字眼,但乌有乡的民众在服饰、建筑和日常生活细节上处处彰显很高的审美趣味。可见,与自然的热恋已使艺术融入他们的血脉中。
(三)美育是静观美学还是参与美学?
英语“艺术”(art)这个词的拉丁词源是“技能”(skill),直到17世纪,“art”一词才与绘画、雕塑等联系在一起。所以在英国18世纪初的技工讲习会用的是 “School of Arts”。这个内涵大大突破了席勒对于艺术及审美的理解。正如莫里斯揭示的那样:艺术的真正源泉是劳动,特别是那种愉悦的创造性劳动。而这种愉悦的手工劳动是人与朴素的自然直接接触。杜威对此作了更细致的分析,“在英语中,我们没有哪个词能够精确地包含‘艺术的’和‘审美的’这两个词所指明的含义。‘艺术的’主要是指创作行为, 而‘审美的’主要指感知以及欣赏的行为。一个术语的缺失,就能指明‘审美的’和‘艺术的’的结合过程是不幸的。”[12]
当代美育学继承康德以来的静观美学,偏向审美感知和欣赏,人类作为主体对作为客体的艺术品的玩味和欣赏。在静观美学视野中,自然只是作为消极的客体,而不是一种积极的参与者。而莫里斯主张与自然恋爱,融入社会去从事创造性劳动,这是一种积极的参与美学,它并非停留在经院式的玄想和高雅艺术品的欣赏中,它不仅是美的欣赏更是美的创造过程。整个参与过程既是审美的,也是艺术的。两者交融在一起。正如柏林特所言, “所有这些情形给人的审美感觉并非无利害的静观,而是身体的全部参与,感官融入自然界之中并获得一种不平凡的整体体验,敏锐的感官意识的参与,并且随着同化的知识的理解而加强,这些情形就会成为黑暗世界里的曙光,成为被习惯和漠然变得迟钝的生命里的亮点。”[13]
(四)莫里斯“热恋自然”的思想源泉
莫里斯的思想深深植根于马克思的唯物实践论。因此,莫里斯美育观不仅突破了单纯的认识论,是唯物的,而且是实践的,是一种积极的参与美学。作为积极的社会主义者,莫里斯突破了傲慢的“人类中心主义”,相信乌托邦必将走向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亲,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杜卫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理论与美育的关系做了精辟的分析,正如其中提到的那样:“一切旨在全面开发受教育者各种潜能的教育思想,总是把美育置于相当重要的地位。”[14]
作为诗人,莫里斯深受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雪莱和拜伦等的影响, 他们对自然的热爱甚至崇拜给莫里斯很大的精神养分。莫里斯和其他浪漫主义诗人一样崇尚自然,在自然美中获取灵感。正如著名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George Brandes)在他的名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提到:“英国诗人都是大自然的观察者、爱好者和崇拜者,自然主义在英国如此强大,以致不论是柯勒律治的浪漫的超自然主义,华兹华斯的英国国教的正统正义,雪莱的无神论精神主义,拜伦的自由主义,还是司各特对以往时代的缅怀,无一不为它所渗透。它影响了每个作家的个人信仰和文学倾向。”[15]莫里斯也不例外。
文艺复兴之后,拉斐尔成为一种范式,艺术界急需回到拉斐尔之前,重新观察自然和生活。1848年, 伦敦皇家学会的7个学生组成了一个秘密社团, 名为前拉斐尔兄弟会,他们绘画,“他们先于法国印象派几十年就开始在户外自然光下创作。”[16]作为前拉斐尔学派第二代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莫里斯的装修设计、彩绘玻璃和家具制作是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花架、布料,还是彩色玻璃的设计,莫里斯多取材于森林中的植物和花鸟。这些都打破了取材中世纪和人与社会的风格。拓展了艺术的领域和风格。“拉斐尔前派只有一条原则,每事每物都要从最细微的细节着手, 从自然, 只从自然中来。”[17]莫里斯充满律动的花卉设计灵感显然源于自然。
莫里斯思想同时也是对当时英国手工艺发展的状况及学校教育状况作出的具体回应。在莫里斯生活的年代,英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在这个过程中, 学校教育几乎不起作用,主要是学徒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技术人员的成长主要靠个人之间、师徒之间的技能和经验的传授,依靠自己的摸索和自身经验的积累。《工业化时期英国教育变迁的历史研究》这本书中提到一个重要事实:“在西方1875年左右,西方经济中应用的技术多发端于并非科学家的人,而且这些人几乎没受过什么科学训练。必须感谢能工巧匠和普通工匠的杰出的发明和事实构成他们的科学基础。”[18]83这个事实多少道出当时英国学校教育的无奈和无能。其次,森林教育在英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该书还提到当时英国最古老、最大和最有名的现代中学哈克尼学校。在它的日程表中可以看到“每日18:00~19:00,一年有6个月学习地理、考古学及统计学,另外6个月野外活动。在19:00~20:00,一年中有8个月学习历史,另外4个月野外活动。学校经常远足学习自然。”[18]43
三、结 语
莫里斯那富于律动的墙纸设计,深深影响了后世装饰艺术的发展,而这些装饰艺术往往只聚焦于作品的表面装饰效果,剥离题材主体的情绪或叙事内涵,因此莫里斯屡屡被认为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者。笔者对此不能完全苟同,莫里斯从未忽视美的道德属性,他也并不机械地强调艺术的教化功用。正如他自己充满律动的花卉和藤叶一样,莫里斯希望能寻找到拥有自然生命力的道德与审美,将它内化于人类的外壳与血脉之中。使热恋中的人类从善如流、美如神话。百年之后,他对自然的挚爱依然深深地打动我们。
[1]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483.
[2] 莫里斯.乌有乡消息[M].黄嘉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3] MORRIS W. Art and Labor[Z]. London: Penguin,1993:114.
[4] 曾繁仁.当代生态美学观的基本范畴[J].文艺研究,2007(4):17.
[5] 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12.
[6] MACKAIL J W.The Life of William Morris[M].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mp,1911.
[7] 柏林特.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的多维视角[M].刘悦笛,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166.
[8] MORRIS W. 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lliam Morris[M]. London: Longmans,1915: 29-31.
[9] 殷企平.艺术地生活:莫里斯的文化观[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2):46.
[10] 席勒.席勒美学信简[M].高燕,李金伟,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
[11] 彭锋.完美的自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60.
[12] 杜威.艺术即经验[M].高建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6.
[13] 柏林特.环境美学[M].张敏,周雨,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155.
[14] 杜卫.美育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7.
[15]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英国的自然主义[M].徐式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6-7.
[16] 法辛.艺术通史[M].杨凌峰,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294.
[17] 蒋孔阳.19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英法美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00:100.
[18] 李立国.工业化时期英国教育变迁的历史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紫 嫣)
An Ardent Love of Nature: Enlightenment of William Morris for an Ecological Aesthetics Education
ZHANG R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William Morris, an outstanding artist and socialist, portrays an art-conscious nation in his utopian fictionNewsfromNowhere. He hopes to be in love with nature. During their everlasting sweet courtship, human beings go summer camping in the forest and enjoy the great fun of life in nature. Morris abandons the conventional Kantian contemplative aesthetics for an engagement aesthetics. While emphasizing the aesthetic property of nature, Morris never neglects its moral attributes. He hopes that all the people in Utopia could fall in love with and learn from nature, thus nurturing kindness and a good aesthetic taste. As a result, human beings will finally overcome alienation and realize their wholeness.
William Morris; ecological aesthetics education; be in love with nature
2016-09-29
张锐(1982—),女,江西贵溪人,硕士,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美育学、英美文学研究。
G40-014
A
2095-0012(2017)01-005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