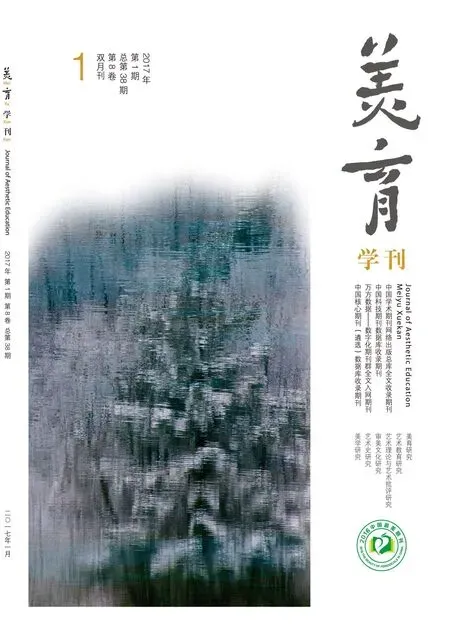古今之争与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美学之衰落
张 颖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编辑部,北京 100029)
古今之争与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美学之衰落
张 颖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编辑部,北京 100029)
在17世纪末的法国,受意大利知识界的影响,几乎所有的饱学之士都卷入了一场规模盛大的论争。这场论争史称“古今之争”(Querelles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随着分裂的加深和公开化,王家学院出现两个阵营:崇古派与厚今派。这场文人战争牵涉诸多复杂问题,甚至卷入私人恩怨。因此,后世对之历来褒贬不一,甚至对其研究价值亦无定论。现通过追溯古今之争法国战场(尤其是第一阶段)的始末,阐述两派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尝试解释古典主义美学之衰落与这场文人战争的关联,并认为它是17、18世纪交替时期法国古典主义文化衰败的表征之一。
古今之争;古典主义;美学;法国
在17世纪至18世纪,围绕着古今何者更具优越性的问题,欧洲知识分子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史称“古今之争”(Querelles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它最先爆发于17世纪初的意大利,主要发生在法国和英国,在其他欧洲国家也有回响。这场文人间的战争声势浩大,在17世纪末达到高潮,掀动了整个欧洲知识界。在法国,当时饱学之士几乎都被卷入古今之争,王家学院随之分裂为两个阵营:崇古派(les anciens)与厚今派(les modernes)。参与者写诗赋文、唇枪舌剑,蔚为一时之盛。一种观点认为,两派都是古典主义者,只不过前者“自觉是家道中落的后嗣”,后者“自觉是青出于蓝的嫡派”,从而尖锐对立;[1]另一种观点认为,崇今派已经分裂出古典阵营,而属于现代派,是启蒙者的前身。至少就古典主义美学的特征——规范、严整、简练、明晰、崇尚理性[2]——而言,厚今派并未有所违背,他们其实仅只反对古典题材和古代作家的独尊地位,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古今之争是古典主义的内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关于古今之争的历史,自古至今有很多种写法。其中,伊波利特·希格(Hippolyte Rigault)的《古今之争的历史》(Histoiredelaquerelledesanciensetdesmodernes)*Cf. M. Hippolyte Rigault, Histoire de 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Paris: Librairie de L. Hachette et Cie,1856.于19世纪中叶面世。该书以史为主,以论为辅,其史料功夫细致扎实,为这段历史的研究留下很好的文献参考。希格把古今之争分为两个主战场(英法)、三个阶段,亦被后来不少研究者沿用。本文以该书提供的材料及评价为准,梳理古今之争法国战事的主要情况,阐述两派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从而尝试解释古典主义美学之衰落与这场文人战争的关联。
一、法国战况始末
根据希格的记载,古今之争最初在意大利知识界爆发。1620年,意大利诗人、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塔索尼(Alessandro Tassoni,1565—1635)的《杂见》(Penséesdiverses)面世,引起轩然大波。塔索尼在书中做了一番古今对比,得出的结论是:今人在各个领域皆胜过古人,这些领域不单包括科学、工业、农业,还包括文学、艺术、辩才、诗歌和绘画。[1]75据迪拉博斯基(Tiraboschi)说,该书“惹怒了当时的大部分作家,他们发现书中对荷马的诗句与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进行了激烈的贬责,同时对文学的效用做出明确的质疑,上述种种令他们大为光火,仿佛塔索尼是在向所有学科和全体学者宣战”[1]72。文人战争拉开帷幕。
很快,塔索尼的著作被让·博杜安(Jean Baudoin,1590—1650)译介到法国。这位译者于1634年入选法兰西学院(Academie francaise),成为第一批“四十把交椅”之一。塔索尼作品的译介,点燃了蛰伏在法国知识界的、与意大利类似的矛盾。1635年,博杜安的法兰西学院同僚、黎世留手下的五人(悲剧)创作班子成员布瓦洛贝尔(Boisrobert)在法兰西学院大会发表演讲,抨击古典文学,攻击荷马。这是法国厚今派第一次发动攻势。
不过,在希格看来,首战的爆发并非出自一个慧眼独具、洞察先机的伟大心灵,而只是一次偶发事件,一场蝴蝶效应。布瓦洛贝尔的观点并不出自敏锐而深刻的哲学思想,他只不过意在提出一个“简单的趣味问题”,却无意间点燃了一场将持续至少上百年的战争。[1]76-77
第二位出场的厚今派成员是德马雷·德·圣-索尔兰(Desmarets de Saint-Sorlin,1595—1676),他也是黎世留五人创作班子成员。这是一位中年皈依的坚定的天主教徒,曾建言国王出动一支十四万人军队根除异端。与布瓦洛贝尔不同,他之所以反对因袭模仿古代诗歌,主要出自他的宗教狂热。古代诗歌是异教诗歌,而今人应当写作基督教诗歌。在他看来,异教诗人无论具有多高的天资,都无法像基督徒诗人那样伟大,因为魔鬼栖居在他们身上并唤起他们的错误,而居住在基督徒诗人体内的却是圣灵,圣灵将他们带向真理[1]107。他本人践行了这个观念,创作出一些基督教主题诗歌,如《克洛维斯》(Cloris,1657)、《抹大拉的玛丽亚》(Marie-Magdeleine,1669)。
崇古派领袖布瓦洛于1674年发表诗体理论著作《诗的艺术》(Artpoetique),在该书第三章里针锋相对地批评了德马雷。他坚决维护神话作为诗歌的主要题材。几年后,高乃依在一场事件中发表了对崇古派有利的意见。他力主神话入诗,除了像布瓦洛那样指出神话的审美价值,还相当机智地运用自己的创作经验进行说理。他提出,自己在写作诗歌时并不把那些异教神奉若神灵,而是根据异教徒的信仰来描写他们的言语;对于那些不以基督教真理为基础的错误的诗歌神性,他主张大可不必严厉驱逐,因为它们可以用在不严肃的诗歌上,比方说爱情抑或其他快事。[1]99
在古今派交战的这一回合里,局面激烈而紧张。应该说,厚今派的德马雷并没有太占优势,也没有掀起太大风浪。1675年,德马雷自知时日无多,在一首诗里呼唤道:“佩罗,去捍卫那正在呼唤你的法兰西吧;/跟我一道打败这群逆贼,/这伙敌人虚弱不堪又死不悔改,/宁肯选择拉丁作品也不要我们的歌唱……”[1]113
德马雷把佩罗当成自己的继承人,而在佩罗公开加入厚今派阵营之前,另有两位学者站出来发声。首先一位是博乌尔斯神父(Dominique Bouhours,1628—1702)。他思维细腻而敏捷,善发新见。在其主要作品《阿里斯特与欧也尼的谈话》(Entretiensd′Aristeetd′Eugene,1671)里,博乌尔斯神父为厚今派的其他人贡献了新的思路。
表面看来,阿里斯特和欧也尼的对谈彬彬有礼,不温不火,并不像其他厚今派那样充满攻击性和侵略感。不过,他们的谈吐中虽尽力避免进行古今对比,但最终仍难掩今胜于古的优越之处。欧也尼说道:“希腊人和罗马人如此珍视自己国家的荣耀,以至于人们完全没法跟他们辩论,不然就会被翻脸,就会跟世界上最勇敢、最有才华的人们结下梁子。对我而言,由于我并不喜欢为自己树敌,所以宁愿向希腊人和罗马人让步,并真心实意地承认,跟古希腊和古意大利的价值比起来,所有国家在英雄方面都是贫瘠的。”这段话看似恭维古人,但若细细品味,说它是对崇古派的影射之词,说他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恐怕也不牵强。阿里斯特也不否认希腊罗马的精神之美,但不失时机地补充了“当今的精神之美”,它们存在于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英格兰人以及莫斯科人那里;到处都有才识,而这其中,唯有法兰西才具备最完美的才识(bel esprit),“这要么出于气候方面,要么是我们的秉性对此有所推助”。他还说,一个国家的粗野或机敏,可能是此一时彼一时。“上个世纪对意大利来说是教义和礼貌的世纪……本世纪对法国而言,有如上个世纪之于意大利;人们说,世界上的全部才智和全部科学现如今皆备于我们,还说,跟法国人比起来,其他所有地方的人都是野蛮人……”[1]118-120这仿佛是在说,文明的接力棒从希腊、罗马,到意大利,如今传到了法国。话语间颇有些当仁不让的意思,虽未抑古而扬今,却着实是在颂今。
再有一位是大名鼎鼎的丰特奈尔。据说他本人“相当机智、非常有野心同时却又极端冷漠”[1]121-122。他之所以站到厚今派阵营里,可能部分地出于年轻人出人头地的愿望。他宣称,在趣味方面,一切皆真,一切皆假。[1]124丰特奈尔的参战作品主要是《死人对话新篇》(NouveauxdialoguesdesMorts,1683)。这篇对话让苏格拉底、蒙田等不同时代的名人汇聚一堂,拟设了他们的言论,并把作者自己的看法隐藏其中,具有强烈的讽喻色彩。比如这段对话,Erasistrate说:“我承认现代人是比我们更高明的物理学家,他们甚至认识自然,然而他们不是比我们更高明的医生……我们看到这里天天都出现更多的死人。”Harvey回答道:“对人认识得更多,却治愈得更差,这真是咄咄怪事。既然如此为何要耗费时间去完善人体科学呢?弃之一旁岂非更好。”[1]126这段话还触及古今之争的一个重要话题:科学知识的进步问题。
丰特奈尔的《死人对话新篇》是佩罗的《路易大帝的世纪》(LesiècledeLouisleGrand)的前奏。[1]1291674年,由于夏尔·佩罗的兄长皮埃尔·佩罗在攻击古希腊诗歌时犯了两点错误,被拉辛抓住后大做文章:“奉劝那些先生(按:指厚今派)不要再如此轻易地在古人作品上做决定。既然他们处心积虑要谴责欧里庇得斯,但像他那样的人至少经得起他们的检验。”[1]133其实,就总体而言,崇今派阵营的古典学水平远不及以渊博著称的崇古派,于是在这场复杂而多反复的战争里,古典知识上的硬伤屡屡成为崇今派受嘲弄和批评的契机。
古今之争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在1687年1月27日。当天,法兰西学院院士齐聚一堂,庆祝国王路易十四身体康复。崇古派领袖布瓦洛在场。聚会中程,身为国王营造总管的佩罗起身宣读了一首诗,即《路易大帝的世纪》。它的开头一段很有名:
美好的古代总是令人肃然起敬,
但我却从来不相信它值得崇拜。
我看古人时并不屈膝拜倒:
他们确实伟大,但同我们一样是人;
不必担心有失公允,
路易的世纪足堪媲美美好的奥古斯都世纪。[1]141
这段诗常被引用。它诗意浅白,反倒具有直接的力量。为路易十四唱赞歌,本是王家学术机构的职责所在。尽管如此,在这样的公开、重大而严肃的场合,借颂今为由而断然否弃对古人的崇拜,是前所未有的——之前的古今交火,大多发生在书面上,或者属于暗地里的小动作。这不啻为咄咄逼人的宣战。
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在佩罗所诵读的诗句里,列举了不少可与古人成就相媲美的今人,独不见布瓦洛的名字。这一公然的举动令盛名久负的布瓦洛相当不舒服。更加令布瓦洛愤怒的是,在他眼中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些古人作品,被佩罗拿来与今人平起平坐。后来,佩罗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不无暗爽地记载道,在自己发表这场演讲期间,坐在扶手椅中的布瓦洛焦躁地晃来晃去,显得极不耐烦、如坐针毡。布瓦洛的崇古派战友于埃(Pierre Daniel Huet,1630—1721)回忆道,布瓦洛在演讲行将结束前愤然起身离席,叫嚷着“这场演讲实乃学院之耻”[1]146。不过,整个演讲过程并无其他院士打断或表示异议。更有甚者,在演讲结束时,听众全体报以掌声。院士们的反应加重了布瓦洛的不安:局面似乎在倒向厚今派。进展到这个阶段,事情变得相当戏剧化。
布瓦洛尽管耿耿于怀,却一直没有做出公开正式的回应,只在几封私人信件里说了些不怎么理智的气话。*可能是布瓦洛的讽刺诗伤人太多,也可能出于妒忌或文人相轻等种种原因,布瓦洛在法兰西学院里拥护者并不多。他在致Brossette的信中曾说道,学院里只有“两三位”有良好趣味的院士。其实,学院里的崇古派除了布瓦洛和拉辛,至少还有波絮埃、费内隆、弗雷谢尔、于埃等等。布瓦洛口出此言,恐怕是气昏了头,或者有所夸张(M. Hippolyte Rigault, Histoire de 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p. 152)。不过,学院里厚今派的势力于此可见一斑。当然,法兰西学院的分裂已是昭彰。1687年,丰特奈尔出版《占卜史》,指出古代异教神使乃是基督教僧侣设置的骗局,抨击了轻信古典的愚昧心灵,此书不啻为对崇古派的又一次打击。*参见J. S. 布朗伯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6卷 大不列颠和俄国的崛起(1688—172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23页。1691年5月15日,丰特奈尔入选学院。这一事件无疑为风头正劲的厚今派又添了一把柴。曾被布瓦洛嘲弄过的拉沃神父(abbe Lavau),在谈话中将丰特奈尔与西塞罗并提,这让崇古派相当不满。又过去两年,崇古派的一位重要成员入选学院,他就是以写作《品格论》(Caractere)闻名的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ere,1645—1696)。拉布吕耶尔是布瓦洛的崇拜者,也迅速加入了辩论。
崇古派是一群信而好古的学问家,精通古希腊语、拉丁语,其中不少人是古代文献的翻译者,比如布瓦洛(翻译朗吉努斯)、隆热皮埃尔(Longepierre)、达西耶(Dacier)夫妇(翻译贺拉斯)等。面对厚今派咄咄逼人的架势,他们一开始并无实质性的还击,所做的往往不外乎讽刺(梅纳日[Menage])或斥骂(布瓦洛、达西耶)而已。在佩罗公开宣读《路易大帝的世纪》后,有人匿名写了一首拉丁文讽刺诗(据说出自梅纳日之手,但他本人否认这一说法)。诗中写道:
亲爱的萨贝勒斯,你的好友佩罗
做了一首诗,取名为《世纪》,
他在里面信誓旦旦、大放厥词。
说什么勒布伦比阿佩利斯懂得多,
说什么我们的哇哇怪叫比西塞罗说得妙,
说什么我们的拙劣诗人比玛戎还强。
多么暗淡而无脑的《世纪》啊![1]210
佩罗把这首诗译成法文,礼貌而强硬地指出这种辱骂“超出了文人之间所允许的自由”[1]212。他早就不无得意地预言过这个局面:“我们在愉快的争论里乐此不疲/这争论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我们将一直摆出各种理由,/他们将一直说着辱骂之词。”[1]193当然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比如崇古派里的隆热皮埃尔男爵就是例外。在他的《谈谈古人》(Discourssurlesanciens)里言辞是礼貌有加的。然而,除了无节制地赞美古人完美无瑕,他并未贡献出有益的论据。在崇古派占下风、局面僵持的时刻,出现了一位引人注目的调停者德·卡利耶尔(de Callière)。他的《古今之战的诗史》(Histoirepoetiquedelaguerredesanciensetdesmodernes,1688)*Cf. Francois de Callieres, Histoire poetique de la guerre, nouvelement declaree entre les anciens et les modernes, Geneve: Slatkine reprints,1971.以佩罗《路易大帝的世纪》演讲后学院分裂为对立的两派为由头,由真入假,杜撰了真假一炉、古今一体的精彩故事:信息女神在巴纳斯山播下警告,命令那些居住在此圣山上的最负盛名的古人和今人像法兰西学院那样分成两大阵营作战。荷马任希腊诗歌统帅,维吉尔为拉丁诗歌统帅,狄摩西尼率领希腊演说家,西塞罗统领拉丁演说家;在今人里,统领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文坛的将领分别是高乃依、塔索、塞万提斯。该书风趣活泼,引人入胜,广受公众的欢迎。其写法后来被斯威夫特借鉴,于是有了英国战场的标志性成果《书籍之战》*中译本可参见乔纳森·斯威夫特《书籍之战》,见《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李春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第195-220页。文中对崇今派的讽刺力度,几乎让法国崇古派里的任何一位难以望其项背。比如“作者序”里的这段话:“有种头脑,只有一层浮沫可供撇去。有这种大脑的人需慎重收集起这种浮沫,并小心经营这点积蓄,但首先要谨防它们受到更智慧的人的攻击,因为那会令它们全部飞散,主人却找不来新的补给。无知的聪明是一种奶油,一夜之间膨胀而起,一只灵巧的手即可以把它搅成泡沫;然而,一旦撇去浮沫,下面露出来的只配丢去喂猪。”见上书第196页。。故事的结尾表达了平息战争的愿望:阿波罗下令停止互骂,以人人封赏的方式缔造了新的和平。卡利耶尔的著作受到古今两派(除佩罗外)的一致欢迎,使得他本人在发表次年即获得法兰西学院的席位。这是崇古派第一次以活泼机敏的方式得到辩护。[1]213-215
崇古派的更加理性的意见发表在于埃与佩罗的通信里。佩罗曾把自己的《古今对观》寄给于埃,请他做出坦率而无偏见的评断。于埃回了一封长信,在必要的恭维后,毫不客气地一一指摘书中的错误。比如,他认为佩罗是由于错解了《奥德赛》里诗句的意思,才会指责荷马把基克拉迪群岛放到热带,于是尖刻地嘲笑并批评道:“这就好像是指责夏普兰先生搞不清布尔日或波尔多的位置……荷马的用语根本不是您所说的意思……”[1]218-219佩罗没有回信。可以想象,知识硬伤令他羞赧。
法兰西学院院士们的激烈争执,在法国知识阶层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知识人全体发生了自上而下的分裂。有些流亡海外的法国博学之士发表了意见。不少报刊也卷入进来。当时参与古今之争的法国报刊主要有《学人杂志》(Journaldessavant)、《风流信使》(Mercuregalant)、《特雷乌回忆录》(MemoiresdeTrevoux)等。《学人杂志》曾拥护崇古派,后保持中立。《风流信使》则与丰特奈尔、佩罗交好。耶稣会掌控下的《特雷乌回忆录》与布瓦洛势同水火。*关于古今之争期间报刊上讨论的情况,可参见M. Hippolyte Rigault, Histoire de 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pp. 223-233。总体上讲,社会舆论倾向于同情和支持厚今派。另外,知识女性也大多站在厚今派一边,唯有少数几位女性例外,如赛维涅夫人、孔蒂公主等等。至于原因,受教育程度可能是重要方面。就像崇古派人士时常愤愤不平的说辞那样,为厚今派鼓掌助威的观众往往缺乏古代知识,未加深究便贸然藐视古人和古典学。*参见M. Hippolyte Rigault, Histoire de 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pp. 240-241。希格还补充说,女性是天生的厚今派,因为她们既不通拉丁文亦不通希腊文,即便在女性沙龙地位较高的17世纪里,她们一般是通过阅读古代作品的节译本来了解古典学的。Cf. M. Hippolyte Rigault, Histoire de 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p. 242.
崇古派向来不善于处理舆论。面对女性们的不支持,布瓦洛的反应乃是写出第十首讽刺诗(Satire X)加以嘲弄。此举大大加重了来自女性读者的敌意。在有权势的女性们的干预下,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新交椅并未如布瓦洛所愿地留给德·米摩尔(de Mimeure),而是被推给了德·圣-奥莱尔(de Saint-Aulaire)。这个事件令布瓦洛气恼不已。[1]245善于审时度势的佩罗利用了这一戏剧性事件,在1694年发表了《为女人一辩》(Apologiedesfemmes),不失时机地揶揄布瓦洛:“难道你不知道女人们的礼貌生而伴有诚挚吗?”这巧妙而狠辣的一击,为佩罗的崇古派拉拢了更多的拥护者。[1]248
正是在同一年,正当崇古派的名声跌至谷底的时候,布瓦洛终于醒悟,以他所擅长的方式发表了《有关朗吉努斯的反思》(RéflexionscritiquessurLongin,1694),不理情面地指陈佩罗曾经做出的知识错误。他认为造成误判的原因是佩罗不通古文字,只能够读古代作品的译本,而译本难免有讹误。
事态进展到难以收拾的局面时,佩罗和布瓦洛的共同朋友们开始出面调停。佩罗把自己的《为女人一辩》寄给了已届八十高龄的大阿尔诺。这位宗教领袖彼时正在布鲁塞尔流亡,但仍密切关注着法国文坛局势。他在回信中指出,布瓦洛的讽刺并无过错,因为它既未攻击婚姻,亦未侮辱女性尊严,非但如此,那些段落反是优美的讽刺诗篇;更重要的是,讽刺诗作为一种文体,是文学性的,因此在“真”的问题上拥有某些豁免权,如果我们像对待哲学论文那样对待它就是不合适的。大阿尔诺表达了希望二人和解的愿望。[1]2581694年8月4日,也就是大阿尔诺去世前四天,布瓦洛和佩罗握手言和,论战至此告一段落。然而,它只是某些领域获得了暂时的平息。战火很快烧到英国,又在下个世纪初的法国再掀风浪:18世纪初,围绕着《伊利亚特》译本是否可以改写为散文体的问题,达西耶夫人和剧作家乌达尔笔战几个回合,崇古派和厚今派又各自捍卫观点,这次纷争相对第一次的声势较小,最终在费内隆的干预下止息。
二、主要参战人物及其论题
在第一部分里,我们按照古今之争法国战场(第一阶段)的主线,简述了这场事件的爆发、进展和(暂时)收尾。以下我们将围绕该事件的三位主要人物,更加详细地讨论其论题和论证方法。
(一)德马雷
德马雷是第一位有意识、有系统地向崇古派发起挑战的法国学者。他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为后来的厚今派提供了思路。
第一,基督教诗歌的优越性。1673年,他的诗歌《克洛维斯》再版,他增写了一篇开场白,强调唯有基督教主题适用于英雄诗歌。他态度坚决地说:“某些作者试图掩盖自己的狡猾,狡辩道,正是出于对宗教的尊重,他们才不愿在诗歌中处理宗教,还说那种胆敢将虚构混同于宗教的纯粹真实的做法是相当鲁莽的;然而,他们妄称尊重宗教,实为蔑视和憎恨宗教,他们难以自禁地在自己的诗歌和不信教的言语中流露出这一点。当人爱一样东西时,必不会保持这样的沉默;而是会带着与这样东西相配的重视和尊敬去谈论它。”[1]97
德马雷代表着法国崇今派中因反异教而反对古代文化的一类观点。这类观点与基督教的反异教传统紧密关联,也与当时错综复杂的宗教局面有关系。在同一历史时期,基督教教会同样坚决反对神话题材戏剧,也可归入这个传统。
那么,德马雷对于非基督教题材的态度果真是寸步不让的吗?希格发现,其实德马雷的立场原本留有余地,他只不过提倡基督教题材在英雄史诗里享有特权,高于异教史诗、遣兴诗和爱情诗而已。后来,随着论争的延伸,他的观念才推向了极端。[1]99
第二,法语的高贵性。法国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至少可以上溯到16世纪以七星诗社为代表的民族语言运动。经过上百年的雅化过程,法语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官方化,并在文学、艺术、科学语言里得到应用,但并未完全取代拉丁文的至高地位。1680年,法兰西学院内部发生了争执,这场争执被法语捍卫者称作“法语声誉”问题或“法语的无上卓越”问题[1]101。问题的焦点是:凯旋门上的铭文应该沿用拉丁文还是改用法文。大部分院士主张改用法文,比如财政大臣柯尔贝尔和夏尔·佩罗。另一派院士则不主张放弃拉丁文这种“拥有凯撒和奥古斯都之不朽性的语言”[1]102。佩罗认为,拉丁诗歌已被遗弃在深夜里,声望和体面荡然无存。对方一派则歌颂拉丁缪斯,用拉丁语诗句说道:人称龙沙为“法语之父”,而他那些粗野的喧哗刺痛了我们那敏感的耳朵;巴黎对马莱伯吝于赞美……[1]103在布瓦洛等人的力争下,这场争执的结局是崇古派取得了胜利。
早在这场争执发生的十年前,即1670年,德马雷即发表了《论判断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诗人》(Traitépourjugerlespoetesgrecs,latinsetfrancais),除了旗帜鲜明地主张今人诗歌高于古代诗歌外,还触及古今之争的另一个话题:语言问题,具体而言是法语的地位问题。因此可以说,他预见到了语言问题将是古今争论的焦点。按德马雷的看法,今天的法语是活的语言,它直接感染今人的心灵,由此产生出种种优点;古人的语言已经无可救药地死去,唯留造作的虚浮。他说:“我们说着一种语言,比起那个从坟墓里拽出来的悲戚的拉丁语,它更加高贵、更加优美。我们不靠诸神,不靠变形,也不靠那些著名的作品,而往往是通过崭新的事物来感染人们的心灵”,“龙沙只有在模仿那些古代的浮夸时,才会败坏他那高雅的天资”,“马莱伯的艺术教会我们优雅地歌唱,而不假装出博学者的放诞……”在德马雷看来,维吉尔的诗歌是贫瘠的,奥维德虽有才智却欠缺精致[1]108-109。就其丰富、灵活、和谐而言,法语远远高出拉丁语和希腊语。[1]104
第三,进步观。德马雷的进步观受培根和笛卡尔派思想家们的影响:虽说古代值得尊敬,但却比不上后来的时代那样幸福、博学、丰富、豪华,“那才是真正完熟的老境”。它就像世界之秋,拥有了丰富的果实和收获能够判断和利用所有发明创造、经验与错误;而古代呢,只不过是年轻而质朴的时代,就像世纪之春,只开出一些花朵。谁愿意那世界之春同我们的秋天做对照呢?那就好像是愿意把人的初季媲美于我们国王的奢华花园。[1]105-106他的基本论据是,自然乃是上帝的作品,因而是完美的;文学、艺术与科学是人的作品,所以需要一个走向完美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从不完美向更加完美的进步:“自然在任何时间都生产完美的作品:在任何时间都存在着美的身体、美的树木、美的花朵。海洋,河流,星辰的出现与隐没,自创世以来就同样的美;但人的作品就另当别论了:它们一开始是不完美的,一点一点臻于完美。上帝的作品从创世以来就是完美的,而人的发明创造则不断被纠正,根据上帝赋予他们的天赋,越往后进行纠正的人就越幸运、越完美”[1]106,“诗歌是人的一项发明,自然不曾为之提供摹本。人必须发明一些方式,把字词以某种尺度排列成诗句,然后根据或简单或庄重的主题做出多种多样的诗歌,作出英雄诗歌以再现人们的伟大事迹。”[1]107这种将作者与作品分而论之的方式,其实对于证明“今胜古”而言十分便捷,在另一方面也颇合今天的世界在环境美学上的“自然全美”观念。
第四,攻击荷马。法国厚今派的一个主要策略,是攻击西方“诗歌之父”荷马。这个惯例是由德马雷开创的。希格说,德马雷“猜中了现代战略的主要原则:在侵略战争中,必须迅速直捣都城。在对古代的攻击里,他给后继者树立了榜样:直奔《伊利亚特》,它是整个古代的要塞和要冲”[1]109。
综上所述,德马雷提出了不少颇具启发性的论点,它们在后来的辩论中被更多的人展开和深化。作为总结评价,希格认为他虽然“模糊地预见到自然力的永恒性这一观念”,“预感到基督教文学的丰沃性,向最广泛的崇古派下了战书”,因而在当时称得上“是厚今一派的真正关键的人物”,然而,“他缺少分寸,不知轻重,虽有些最天才、最正确的见解,却因条理不清而有所损害,又因傲慢自大而闹了笑话”,加之“他没什么学识,几乎对艺术陌生,从而无法把自己的种种观念普遍化,仅把观点局限在诗歌,尤其是英雄诗歌上”。正是出于上述原因,尽管他早发先声,却往往不被视作厚今派的第一人——人们把这项荣誉给了佩罗。[1]112
(二)佩罗
佩罗在《路易大帝的世纪》里,用自然力之永恒性挑战崇古派的历史衰微观:
在这个广袤宇宙的未可测知的围墙里,
上千的新世界已经被发现,
还有新的太阳,当夜幕降临时,
还有众多星辰[1]142……
……
塑造心灵,有如塑造身体,
自然在任何时代做着同样的努力。
它的存在永恒不变,
而它用于制造一切的这种自如之力
并不会干涸竭尽。
今天的我们所看见的当日星辰,
绝非环绕着更加璀璨的光芒;
春天里的紫红玫瑰,
绝非多加了一层鲜艳的肉粉。
我们苗圃里的百合与茉莉
带有耀眼的釉色,
白色的光芒并不逊于以往;
温柔的夜莺曾经用它的新曲
令我们的祖先迷醉,
而在黄金世纪里,
夜莺唤醒在我们的树林里沉睡的回声,
两种声音乃是同样的悦耳动听。
无限的力量用同一只手
在任何时代制造出类似的天才。[1]143-144
《路易大帝的世纪》是一份宣言。他的说理著作是1797年出齐的洋洋四卷本《古今对观》(Parallèlesdesanciensetdesmodernes)。这套书采用对话体,从科学、医学、哲学、音乐、文学、辩术等各个方面比较了古今成就。书中既充满风趣的机智、尖锐的意见,也不乏偏执的成见,以及轻率的话语。希格评价它“精神自由、出人意表、敢于冒险”,认为里面的辩论不仅属于夏尔·佩罗,也来自德马雷、丰特奈尔、皮埃尔·佩罗的观念,因而可以代表厚今派的主要思想。[1]206
在佩罗的论证里,有三条论据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个论据基于对人类理性的信心。佩罗相信,要想判断所有的文学问题,只要拥有自然的趣味、通常的教育、心灵的文雅就足够了,而并不需要特殊的教育,以及更加精致的、比常人更加练达的趣味。[1]178在这一点上,佩罗显然受到笛卡尔及其知识圈子的影响,尤其是笛卡尔“怀疑-检验”方法的影响。佩罗明确宣称,希望把笛卡尔带入哲学里的自由应用到对心灵作品的检验中去,摆脱文学权威的束缚,就像笛卡尔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那样。[1]179提出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为了降低古代作品评价者的准入门槛,尤其是为崇今派确立资格。因为总体而言,崇古派里不乏古典知识的渊博之士,加之当时法国的经院式教育,给文艺批评规定了不少严格的规矩。然而,倘若仅以理性为准绳而做出的独立判断是可靠的,并足以令人信服,那么,古典学就无法享有特权,而很多不以古典学见长的厚今派人士也可以放心涉足了。
第二个论据基于对自然之永恒性的信心。创造不应以古今分高下,首创者并不更加伟大。他甚至举例说道,第一位造船者无非模仿了贝壳类动物,如果古代创造者比今天的创造者更伟大,岂不是贝壳类动物最伟大?若论熟练程度,今人具备更充分的认识和更悠久的习惯,自当比作为初学者的古人高明。他的持论依据是,作品与作者可以分而观之;而自然的产品是永恒不变的(树木在今天所结的果子与古时相同,人的观念古今同一)。乍看起来,颇有些中国人董仲舒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意思。不过,有意思的是,二者的观念正好走在相反的方向上:董仲舒的话旨在说明统治之道的纲常稳定性,从而常被保守派引以为(政治)守旧的依据;而佩罗则希望扭转西方自古代以来的社会衰落论,把近代人提升到与古代人平等的地位,从而为近代的创新寻求根本支撑。在他看来,就像大自然年年都会出产大批量的中品和差品的葡萄酒,但也会有品质上佳者,任何时代也都有也会有平庸的普通人,却也不乏卓越的天才。[1]179-180因此,“当我们在做古今对比时,所针对的并不是它们的纯自然天赋的卓越性,那些天赋在任何时代的杰出人士身上都是相同的,都具有相同的力量,我们的古今对比仅仅针对他们的作品之美,针对他们对于艺术和科学所具有的知识,那是依时代不同而千差万别的。因为,由于科学和艺术无非是一堆反思、规范、规则,那么,诗歌作者有理由主张这堆必然随着日积月累而增多的东西更加伟大,并走在所有时代的最前列……”[1]181
第三条论据基于对自然科学的信心。比如他认为,古人粗知七大行星和其他一些醒目的星星,今人还认识了一些卫星和众多新发现的小星星;古人粗知灵魂的激情,但今人还了解与之相伴生的无限多的微妙病症和状况;从而,“我可以让你看到我进一步把所有激情依次重新结合在一起,使你相信,在我们的作者的作品里,在他们的道德论著里,在他们的悲剧里,在他们的小说和雄辩篇章里,都存在着成千上万的细微感触,那是古人所不及的”[1]186。总而言之,今人相对于具备更多的几何学、透视法、解剖学等领域的知识,加之掌握了更加完善的工具,又在技巧理论上取得了更多的进展,因此会出现比古人更加伟大的雕塑家、画家、建筑家。佩罗在《古今对观》结尾处充满感慨地说:“读一读法国和英国出版的杂志,看一眼这些伟大王国的研究院所出版的书籍,这样就会深信不疑地认为,自然科学在过去二十或三十年内所作出的发现,比整个古代在学术上的发现还要多。我认为自己很幸运地得以指导我们所享受的幸福,我承认这一点;纵览过去的所有时代,目睹一切事物的诞生和进步,这是莫大的快乐,但是那些在我们的时代尚未获得新的增长和光泽的东西则另当别论。我们的时代差不多已经达到完美的巅峰。自从过去的若干年前以来,进步的速度一直缓慢得多,看上去几乎难以察觉——正如夏至日点临近白昼似乎不再延长一样——很可能没有多少东西会使我们需要对未来的后代表示羡慕,一想到此便会有一种欣悦之感。”*转引自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第四章“退步论:古代与现代”,范祥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
然而,佩罗的论证并不严密,也不乏自相矛盾之处。在第一条论据里,一个可想而知的隐患是,知识的去精英化难免造成知识精度的下降。在第二条论据里,他把作家和作品分开讨论的做法,即便论证出自然的作品持久而永恒,却也会妨碍把这一条论据引向对古人价值的判定;况且这条原则并没有贯彻始终。崇古派的于埃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1]217。就这条论据而言,佩罗的方式不如德马雷的方式明智:如前文所述,后者断言上帝的作品(即自然)是无往而不美的,而人的作品(包括文学、艺术、科学)则有待于逐渐趋向更完美,这样做一劳永逸、干净利落,令反面意见的反驳无从下手;而佩罗的方式则给自己制造了麻烦。
遭到更多人指摘的是第三条论据。人们认为他把科学和艺术混为一谈,把科学的进步作为艺术进步的原因。比如,希格就批评佩罗只知工巧而不懂趣味,只看质料而忽视思想[1]185-186。说到底,佩罗之所以产生如此误解,是其用科学标准来评价艺术问题所致。希格认为,佩罗的问题在于没有能够区分两种艺术:一种艺术,其臻于完美需要时间,而另一种艺术则从开端时就能够是完美的。[1]186我们如果将前一种“art”译作“技艺”“工艺”或“技术”,或者广义之“艺”,希格的意思就很明白了。这种“art”的近亲是科学。科学的发展过程是从无知到有知,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对于科学而言十分重要。今天的我们站在历史的下游向上回溯,能够看得比较明白:艺术史不是凭借经验积累而发展的历史,在艺术上,后发性不等于优越性,后出现的艺术不一定比先前的更高明。佩罗混淆科学与艺术的性质,放在他那个时代的背景下也是可以理解的;与其说是个错误,不如说是时代的思维特色。在17世纪的法国,尽管科学有了相当新异和突破性的进展,尽管科学的观念,如实验、机械论等,已经大大改变了知识精英们的思维方式,但学科领域的界线与今天相比是相当模糊的(类似地,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那么多科学艺术无所不能、璀璨有如繁星的全才,亦可部分地归于知识分界模糊,博学者们一通而百通),科学成就也颇为有限(在《古今对观》中,佩罗只看到了舰船相对于渔船的进步、卢浮宫相对于茅屋的进步等等,当然,这些足以令其感慨不已了)。
在谈到古今诗歌对比的时候,佩罗接续了前述德马雷与布瓦洛的争论,即作为题材,基督教和神话两者之中何者更应该入诗。但他更改了讨论的重点。他先指出,有两类装饰可以为诗歌灌注生气、美化描写,一类是各个国度所共有的、自然的装饰,比如情感、激情、话语等,另一类是只属于某些地域的装饰,如古人诗歌中的众神,又如基督教诗歌中的魔鬼与天使,它们是人为的装饰。后一类装饰尽管会带来美化效果,但它们并不属于诗歌的本质。比方说,我们完全可以把古人诗句中的异教神置换为基督教的天使。因此,古人对神话的利用并没有什么高明,至少不比今人使用宗教题材更为高明。既然旨在美化装饰,故而他也同等地不反对布瓦洛所提倡的寓言入诗。
另外,布瓦洛还曾表示,把基督教人物掺入诗歌这样的想象力游戏是大不敬的(详见下文)。对此,佩罗有一套成熟而理智的看法:“诗歌在被用于游戏时,它是一种心智游戏;但当涉及重要题材时,它就不再是心智游戏,而等同于那些演说、颂词、布道里的伟大雄辩术。我们不能说大卫和所罗门的诗歌是一种纯粹的心智游戏,亲爱的主席,您不会乐意以此称呼《伊利亚特》或《埃涅阿斯纪》的。所以,确实存在相当严肃的诗歌作品,在那里放入天使和魔鬼完全不会有失体面。由于我们相信,上帝之所以把这些鬼神放入人类行为,要么是为了诱惑他们,要么是为了拯救他们,那么,鉴于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懂得的种种原因,诗人难道不能够遵循诗歌的特权把它们彰显出来,令它们变得具体形象吗?”[1]198-199
就总体而言,佩罗确实是一位灵活机智的辩手。当时,《古今对观》第一卷的出版令崇古派震怒,他们纷纷指责厚今派只不过是一帮妒忌者。在《古今对观》第二卷序言里,佩罗风趣地回应了“妒忌说”:巴黎的文人有两种,一种文人认为古代作家尽管娴熟精雅,却犯了些今人没有犯过的错,他们赞扬同行的作品,认为它们与那些模范同样优美,甚至往往比大部分模范更加正确;另有一些文人,他们宣称古人不可模仿,远不可追,从而鄙视同行的作品,一旦遇到就从言辞和文字上加以诋毁。“他们在开始时直截了当地宣布我们是无趣味、无权威的人。到了今天则又指责我们妒忌;明天大概就会说我们顽固不化了吧。”[1]193这一类俏皮话举重若轻,有亲和力,它们时常令崇古派的古板面孔显得颇为滑稽,为厚今派赢得了不少来自女性支持者和报刊舆论支持。
不过,俏皮与机智只适合于作为锦上添花的技巧,只有在进行单方面阐述或单个回合的辩论时,它们的作用才会比较有效地发挥出来。然而,如果面临复杂的学术问题,需要多方深入论证时,系统性、知识性的缺乏很容易暴露无遗。佩罗式的轻盈巧辩,尚需厚重的古典学知识来支撑,才可能无往不胜。尤其是,崇古派提出的一个严肃指责,令以佩罗为代表的厚今派不得不认真面对:“厚今派不懂希腊文,也不懂拉丁文;他们靠译本来判断作者;他们注定会做出糟糕的判断。”[1]194
(三)布瓦洛
厚今派的德马雷提出了神话应否入诗的问题。布瓦洛在其《诗的艺术》第三章里用了四十多行诗(第194行—第237行)提出反驳,力求论证神话入诗的合理性及神话题材的优越性。
古典主义美学注重文艺的教化功能,认为写诗的目的在于劝谕人、教育人,使之乐意接受某个道理;唯有使用令人愉快而可信的内容,诗歌方可达到劝谕的效果,这就是“寓教于乐”。贺拉斯在《诗艺》里曾经指出过的这条创作原则:“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4]作为贺拉斯诗学的继承者,布瓦洛也主张写诗作文首先要讲究“情理”/“理性”(“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5]5。这是《诗的艺术》的总体立场。
按照这个线索,在神话题材之合法性的问题上,我们猜想布瓦洛的论证逻辑会是这样的:诗歌应当实现教育劝服的目的,为此应当具有令人愉快的效果,而神话正是令人愉快的,所以可作为诗歌题材。然而我们发现,布瓦洛在这个部分并未怎么提到诗歌的教化目的,而是纵情谈论“诗情”、诗味。他指出,神话之所以具有令人愉悦的功能,乃是由于它的虚构性。神话故事“装饰、美化、提高、放大着一切事物”,化抽象为具象,变平凡的现实为瑰丽的想象,变“抽象的品质”为性格鲜明的“神祇”;它们令“一切都有了灵魂、智慧、实体和面容”,所以诗歌才会那样引人入胜、令人着迷。布瓦洛没有就此引导到“寓教于乐”的大题目上去,话语间倒更看重诗歌本身的审美价值:“若没有这些装饰,诗句便平淡无奇,/诗情也死灭无余,或者是奄奄一息,/诗人也不是诗人,只是羞怯的文匠,/是冰冷的史作者,写的无味而荒唐。”[5]40-42这里似乎不见其“教”,仅见其“乐”。当然,“理性”作为一个大前提贯彻在《诗的艺术》全书里,在神话题材这个具体问题上是不言而喻、无须再提的。但布瓦洛向来不惮于重复贺拉斯说过的话。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布瓦洛在写下这些作为反驳意见的诗行时,心情难免有些急切。他珍视古希腊罗马的神话史诗传统,衷心热爱那些美妙的寓言故事,因此急于驳倒德马雷,捍卫神话题材的合法性,满腹的道理不吐不快,表达时却略失轻重。比如这几句诗:
并不是说我赞成在基督教题材里
作者也能狂妄地崇偶像乱拜神祇。
我是说,如果他写非教的游戏画图,
也丢开古代神话,竟不敢寓言什九,
竟不让潘神吹笛,让巴克剪断生命,
不敢在水晶宫里不知写虾将蟹兵,
不敢让那老伽隆用他催命的渡船
同样把牧竖、君王渡向阴阳河彼岸;
这岂非空守教条,愚蠢地自惊自警,
无一点妙文奇趣而想受读者欢迎?
进一步他们将不许画*参考当页译者小注可推知,原文此处似乎漏掉了“贤明之神”。参见布瓦洛《诗的艺术(修订本)》,任典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不让那特密斯神蒙着眼、提着小称,
不许写战争之神用铁的头颅相触,
不许写光阴之神飞逝着提着漏壶;
并从一切文章里,借口于卫教为怀,
把寓言一概排除,诋之谓偶像崇拜。[5]42-45
连续的排比修辞仿佛为言辞布下鼓点密集的声音背景,显出责备驳斥的咄咄气势,布瓦洛的急切与激动溢于言表。诗中一系列的“不许”“不让”“不敢”,是布瓦洛相当怕见的诗坛景象。进一步看,神话既然如此令人愉悦,若借以“载道”,宣扬基督教的教义,岂不方便?一百年前,意大利诗人塔索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1575)就是这样做的。但布瓦洛坚决反对把神话掺入基督教文学。他说:“基督教徒信仰里的那些骇人的神秘/绝对不能产生出令人愉快的东西。/福音书从各方面教人的只有一条:/人生要刻苦修行,作恶就恶有恶报;/你们胆敢拿虚构来向《圣经》里掺杂,/反使《圣经》的真理看起来好像神话。”[5]43也就是说,神话题材与基督教义相混,势必伤害宗教的严肃性。布瓦洛的观点至此似乎较清楚了:受詹森派教义影响,他主张美善分离;由基督教信仰来教人明辨是非,而充满想象力的神话令人产生审美愉悦。
由上可见,布瓦洛坚信虚构和想象是诗歌及文学的生命,它们所带来的愉悦感是诗歌的魅力所在,从而主张师法古代诗歌,以神话为主要题材,反对以基督教义入诗,反对以宗教教条取代审美乐趣。用今天的眼光看,布瓦洛的文艺观似乎比德马雷更为宽宏,至少他并未像德马雷那样,以“宗教正确性”作为一种专断的美学标准*希格也在书中评判道,德马雷混淆了宗教与文艺,后者不求“真”而求“美”;造就更伟大的诗人者,并非观念之真,而是“情感之真、想象之美、激情之热烈、语言之光辉”。(M. Hippolyte Rigault, Histoire de 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p. 108)。这个说法恐怕有些苛责前人。希格身处19世纪,那个时候的浪漫派已经标举了“为艺术而艺术”;但在17世纪,审美尚无自主地位,因此德马雷在标准上以宗教代审美,倒也不足为奇。不过,希格还提到德马雷的论据在他的时代重燃。。但他对德马雷的诘难却不大令人信服:在西方文学史上,优秀的基督教文学并不鲜见。
布瓦洛的鲜明主张,在另一方面体现出异教诗歌与基督教诗歌在当时的激烈较量。关于基督教义可否及如何入诗,或者说可否及如何作为文学主题,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希格认为,在基督教里,地狱比天堂更具诗性,因为唯有地狱向种种激情开放,这就是为什么撒旦乃是《失乐园》的真正主角。基督教的天堂是完美的统一体,各品级的天使异名而同类,它们只被上帝的思想激活,被上帝的意愿驱遣。说到底,在天堂里只有一个人物,那就是永恒的上帝。这个上帝是纯粹心灵,其非物质性使得诗人难以下笔为之着色或施加想象力。[3]94
三、古典主义美学的内在矛盾
综上可以看出,这场文人战争牵涉诸多复杂问题,甚至卷入私人恩怨。因此,后世对之历来褒贬不一,甚至对其研究价值亦无定论*科林·麦奎兰在《早期现代美学》第一章“古与今”中对其持肯定态度,他认为这场发生在前美学时期的论战辅助了人们将艺术与哲学归拢一处,从而对于我们了解美学的生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J. Collin McQuillan, Early Modern Aesthetics, London/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2016, Chapter 1)。否定其价值者亦大有人在,具体可参见拙文《克朗茨的笛卡尔美学论及其命运》(待刊)。。如果我们持一种连续性的历史观,则无论我们相信历史的演进道路是前进还是后退,皆会倾向于认为历史现象或事件事出有因,至少在时间上能够分出“前”因与“后”果。那样的话,就古今之争在时间链条中所处的位置而言,它上承古典主义美学,下启启蒙运动,其与二者的关联应在可探讨的范围之内。故而笔者尝试提出,它是17、18世纪交替时期古典主义文化衰败的表征之一。
通过梳理这场古今之争的过程,分析主要人物的主要论题,我们看到,这场争论有一个总题,那就是:古与今何者更为优越?参与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论点切入这个总题。他们提出的分论题涉足宗教问题(基督教与异教)、进步问题(文学、艺术、科学的进步)、语言问题(法语与拉丁语、古希腊语)等等五花八门的领域。在讨论古典传统对西方文学史的影响时,海厄特将古今之争的论题进一步扩展,做了如下清晰而充分的描述:“问题是这样的:现代作家是否应该推崇和模仿古代伟大的希腊语和拉丁语作家?或者古典的鉴赏标准是否已被超越和取代?我们是否必须追随古人的脚步并试图效法他们,以达到他们的水准为最大愿望?或者我们能否自信地期待超过他们?这个问题的范围还可以大大扩展。在科学、艺术以及整体文明上,我们取得的进步是否已经超越了希腊人和罗马人呢?或者我们是否在某些领域领先他们,但在另一些领域落后呢?或者我们是否在所有方面都不如他们,我们是半开化的野蛮人,只是享受着真正文明人类所创作的艺术?”[6]这一连串的问题提示我们,或许可以把那场喧扰的战争理解为一种自我身份的焦虑,理解为当代人对当代文化之品质的矛盾性反思:古希腊人和罗马人是光荣的,我们当代法国人是否同样光荣?
这样的反思,最深刻地纠缠着法兰西学院的知识精英,他们肩负着知识传承的重要责任。这个责任的首要任务,在于权衡和断定怎样的文化最值得推崇,最能够为当代、为自己的民族国家带来益处。他们面临两种文化:古代文化和当代文化。前者被封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完美样板,后者拥有丰富的成果,呈现出繁荣的态势。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进行鉴赏对照时,发现当代文化并不输于古代文化,甚至可能在一些地方有所超越。比如佩罗说过:“古人是卓越的,这一点不可否认;但今人不遑多让,甚至在很多地方更加出色。”可见他身为厚今派却并不一味贬低古人,而只是更看重今人的优胜之处。按希格的话说,佩罗仰慕古人,只不过并非古人的崇拜者;他称颂古人,但并不夸赞古人的所有作品,而是有所拣选,有所批判。[1]177,180这种对待古人的态度,在厚今派里相当有代表性。
然而,他们为何会为这样的问题所纠缠甚至争执不休呢?路易十四时代难道不是一个古典主义美学趣味笼罩下的大一统时代吗?推崇并仿效古代文化,难道不正是一切古典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吗?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古典主义美学内部发生了分裂。
夏尔·佩罗不认为古人作品都是神圣而完美的,因此断然反对给年轻人灌输古代文化。他说:“有那么一些人,把这种偏见灌输给年轻人的心灵、置入他们的行为,这些身披黑色长袍、头戴方形无边软帽的人,建议年轻人去读古人作品,不单把它们说成是举世之珍,还将之标举为美的观念,如果年轻人终于能够模仿那些神圣的摹本,便送上预先备好的冠冕。他们就靠这个糊口。”[1]192夏尔·佩罗的这段话并非理论话语,但看似寻常却很有代表性。其兄长皮埃尔也说过类似的话。1678年,皮埃尔·佩罗以书面形式说道:“我认为,我们在当下仍能看到的对古代作家的伟大反驳,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作品问世于一个精神既粗俗又无学识的时代;就因为有些作品确实优秀,其他同时代作品难以匹敌,它们就激起了较高的评价,这评价强烈渗透到那个时代的精神之中,它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从父辈传给孩子,从师辈传给学生,乃是由于,作为年轻人,孩子和学生是盲目服从的,而他们的父辈和师辈向他们信誓旦旦地说那些作品是神圣而不可模仿的。”[1]131他们所忧心的是年轻人的教育问题:应该教什么?由谁来教?换言之:应该将怎样的文化传承下去?这是在任何时代都至关重要的课题。或许正是在这里,透露出厚今派对古典学权威的真正不满。
从伏尔泰《哲学词典》里,我们可以发现他对佩罗兄弟的呼应:“我们对当代已经过分为人熟悉的伟大成果态度冷漠,古希腊人却对微小的成就十分赞赏。这正是我们的时代对古代具有极大优越性的又一明证。法国的布瓦洛和英国的坦普尔骑士执意不承认这种优越性。这一古人和今人之争至少在哲学领域里已经得到了解决。今天,在文明开化的国家里,没有人再用古代哲学家的论述来教育青年了。”[7]按此说法,厚今派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成功,至少牢牢掌握了教育的方向。
于是不少研究者指出,古今之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乃是反权威。认识到这一点,难免会将古今之争与文艺体制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把古今之争视作学院派里的在野派对学院权威的不满的集中爆发,视作一场文化权力争夺战。不过,这样的解释尚欠确切,容易引起误解,甚至可能掩盖问题的实质。以布瓦洛为例,他在成为文坛领袖之前,也曾是与拉辛等同道一起反对沙普兰权威的年轻人。在这种通常意义上的反权威,所关涉的是同质文化内部的权力分配问题:在野派希望夺取文化领导权和稀缺资源,取代现有权威而成为新的权威。这种代际更替并不更改文化的性质与方向。如果说厚今派确实也反权威,则这种反对与革新的诉求是更为激烈也更为根本的。他们希望弃拉丁语而起用法语,弃异教神话而起用基督教题材,用当今科学之昌明来彰显古代文明之粗陋,这些方案都有志于把异质文化传统扭转为以当代法兰西文化为主导。
换言之,需要在更深广的意义上理解古今之争中的反权威现象。厚今派成员的攻讦之辞,无论出于怎样的私意,在整体上看或就客观效果而论,都在进行着对文化方向的争夺。这种争夺恐怕折射出文化总体的深度病症。那么,法国古典主义美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竟会在其知识精英内部发生这样严重的分裂和根本性的纷争?
这里需强调的是,17世纪法国的古典主义美学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官方美学,是国家政策的附属性产物。这种美学先天地带有一种潜在的错位:它在体制和内容上是古典主义的,在诉求上则是民族主义的。古典主义在内容上要求尊古、复古,在体制上要求规范化、模式化、典型化。民族主义的强国诉求,则包括着眼于当代现实的战略考虑,比如,它需要诗歌与绘画来歌颂国王的战功与伟绩,需要提升民族语言的地位,从而在外交上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它还需要吸纳最新的科学发明,以服务于可能的国防需求,等等。可以说,这种古典主义追求的是一种旨在提高法兰西民族文明、增强法国综合国力的“当代法国古典”。
在这个矛盾的词汇下,透露出两种相当异质的指导思想:一是体制所严格要求的限制与管控;一是文化艺术科学创新所必须的自由意识。这两者显然难以长期共容,势必发生碰撞。而此消而彼长的结果,将决定法国文化品质的历史走向:或则管制扼杀创作,或则自由冲破规矩。正如希格曾经指出的那样,布瓦洛之于文学界,有如路易十四之于最高法院;法王的治下一直涌动着暴力的或无声的政治反抗,而布瓦洛的文学管控也长期面临着一股反对力量。*参见M. Hippolyte Rigault, Histoire de 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p. 150。丑化路易十四形象的事情在当时并不少见,英国崇古派主力乔纳森·斯威夫特就曾在一首颂扬威廉三世的诗歌里把路易十四贬低为“贪得无厌的暴君”。参见彼得·伯克《制造路易十四》,郝名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十章“反面形象”。
所以,古今之争中两派的尖锐对立,或许正反映出现代文明初始阶段的阵痛。我们可以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把古今之争看作是已然逝去、余韵犹存的古代异教文化与基督教现代之间的冲突,也可以引入一个阶级视角,就像布克哈特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所启示的那样,认为它体现了上升期的资产阶级对封建文明的抵抗。新兴的资产者集宗教信徒与渴望世俗成功者于一身,他们的文化精英(这一点在佩罗兄弟身上很典型)更加重视获得文化的广泛受众的支持,更加有意识地针对公众进行写作,于是坚持使用法语,并力求语法浅白、内容通俗。进而我们难免会想到,他们的作品或许是启蒙著作的雏形。
在路易十四去世之后的奥尔良公爵摄政时期(1715—1723年),二十岁的伏尔泰与已逾花甲之年的丰特奈尔曾在苏利馆(Hotel de Sully)沙龙畅叙。伏尔泰赞后者为路易十四时代最多才多艺之人。[8]确实,厚今派与启蒙思想家之间,在精神特质上有诸多相似之处:反叛精神,敢于向现有的权威挑战,推崇理性,讴歌科学。不同之处在于,厚今派身处法国绝对君主制的强盛期,分化自一个高层的文化共同体,着眼于文化上的除旧布新,但所倡导的新文化仍属于旧体制;启蒙者们则处身绝对君主制摇摇欲坠的阶段,其所谋求的思想革命更彻底地带有政治革命诉求,立足于科学理性来鲜明而激烈地反君权、反神权。厚今派和启蒙思想家都深知舆论造势之道,他们较自觉地保持着集体观念、活动的一致性,重视较广泛受众的反应,充分利用各种传播渠道来为自己争取支持。厚今派的笔战在书信和出版物上,也出现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除了这些媒介,启蒙思想家还利用了图书馆和咖啡馆等舆论阵地。
从这个角度看,古今之争的那段历史,或许可以解释为古典主义美学崩溃、启蒙美学萌芽的二项对立时期。法国17世纪的古典主义美学内蕴着自身的反对力量。它本该是一种权威化、规范化的美学,以古典美学为样本,在各种艺术领域设定权威以作为法则的代表。而新成果的诞生,往往出自具有批判和怀疑精神的头脑。层出不穷的新的文化成就,与笛卡尔的彻底怀疑精神走在同一条道路上。启蒙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倚赖理性,信任人人皆生而有之的基本判断力,就像圣·艾弗蒙(Saint Evremond,1610—1703)说的那样:“荷马的诗永远会是杰作,但不能永远是模范。它们培养成我们的判断力,而判断力是处理现实事物的准绳。”[9]
确实,在古今之争的喧嚣里,某些重要的东西被动摇了。就此而言,它确实称得上启蒙运动的先声。从文化权威的倒掉,到神权与君主制的松动,这之间的复杂转变,并不是古今之争一事所能尽显。但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看到,古今之争与启蒙运动之间的相关性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历史延续论。
[1] 吕健忠,李奭学. 西方文学史[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213.
[2] 刘意青,罗经国. 古代至十八世纪欧洲文学[M]//李赋宁. 欧洲文学史:第1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94.
[3] RIGAULT M Hippolyte. Histoire de 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M].Paris: Librairie de L. Hachette et Cie,1856.
[4] 贺拉斯.诗艺[G]//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55.
[5] 布瓦洛.诗的艺术(修订本)[M].任典,译.第2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6] 海厄特.古典传统:希腊—罗马对西方文学的影响[M].王晨,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221.
[7]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M].吴模信,沈怀杰,蒋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497.
[8] 杜兰.伏尔泰时代[M].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23.
[9] 艾弗蒙.论对古代作家的模仿[G]//高建平,丁国旗.西方文论经典:第2卷·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456.
(责任编辑:刘 晨)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Moderns and the Decline of French Classical Aesthetic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ZHANG Ying
(Literature&ArtStudiesEditorial Department,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100029,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France, influenced by the the quarrel between"ancients and moderns" (Querelles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As the division deepened and went public, the Royal Academy broke into two camps : those for the ancients and those for the moderns. This literary war involved many complex issues, even personal strife. Therefore, subsequent ages have disagreed about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this dispute and even about its research value. Now by tracing the whole story of the battle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 at the French front (especially the first stage) and the views of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s of the two camps, we hope to explai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is literary war and the decline of classical aesthetics and establish it as one of the signs of the decline of French classicism at the turn of the 18thcentury.
controversy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moderns; classicism; aesthetics; France
2016-12-1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方美学史1~2卷》(14JJD720022)的阶段性成果;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法国存在主义艺术理论研究》(14DA02)的阶段性成果。
张颖(1979—),女,山东淄博人,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社副编审,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近现代法国美学研究。
B83
A
2095-0012(2017)01-00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