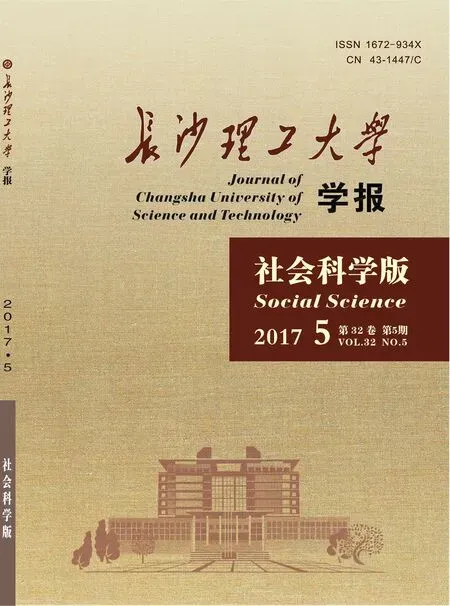徐悲鸿在印度国际大学若干史实的辨正
刘开生,胡玲玲
(长沙理工大学,湖南 长沙 410004)
徐悲鸿在印度国际大学若干史实的辨正
刘开生,胡玲玲
(长沙理工大学,湖南 长沙 410004)
1939—1940年期间,徐悲鸿应泰戈尔之邀赴印度国际大学进行为期近一年的访问、讲学,许多文献对此有所介绍,但其中有的涉及的一些重要史实,如徐悲鸿到国际大学的时间,在国际大学期间徐悲鸿在谁家吃饭,以及徐悲鸿在印度举办两次画展的时间都是错误的。文章根据确切资料对这些错误史实做了厘清,以期为徐悲鸿研究提供一些基础史实。
中印文化交流;徐悲鸿;泰戈尔;谭云山;阿密达瓦·巴塔查理亚
Abstract:During 1939 to 1940,Xu Beihong was invited by Tagore to visit The Visva-Bharati University Of India,and to give lectures there for nearly a year.Many documents have introduced this event.However,some important historical facts,such as Xu's arrival time,the home responsible for his meal,the exact date of Xu's two art exhibitions in India,etc.,are wrong.This article aims at clarifying the right from the wrong based on precise historical facts,to offer some basic historical facts for the research about Xu.
Key words:Sino-Indian cultural exchange;Xu Beihong;Tagore;Tan Yunshan;Amitava Bhattacharya
1939-1940年间,徐悲鸿应泰戈尔之邀赴印度国际大学进行了为期近一年的访问、讲学,这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也是徐悲鸿整个艺术生涯中创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很多作品对此都有记载和介绍。但是,有些介绍徐悲鸿生平和他学术活动的著作(有的应该说还是权威著作),其介绍中涉及的几个重要史实却是错误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此提出辨正,恢复其历史本来面目。
一、徐悲鸿到国际大学的时间
在徐悲鸿夫人廖静文的畅销著作《徐悲鸿一生 我的回忆》(以下简称《廖著》)一书中写道:“一九四〇年春,悲鸿应印度诗哲泰戈尔之邀,赴印度国际大学讲学。”[1]而在《泰戈尔与中国》①一书中收入的印度画家阿密达瓦·巴塔查理亚的《1924年以来的中印画家交往拾遗》(以下简称《阿文》)一文中也写道,“徐悲鸿1940年代初应罗宾德拉纳特(按:即泰戈尔)之邀到达圣地尼克坦。”[2]这两部都堪称权威的著作,都说徐悲鸿是1940年初到国际大学的,但这个时间完全是错误的。
在徐悲鸿的前夫人蒋碧微的回忆录《我与悲鸿 蒋碧微回忆录》中则是这样写的:“徐先生在民国二十八年远赴印度,开画展,并为印度诗人泰戈尔画了一幅素描像……”[3]。民国二十八年即1939年。此时,虽然她与徐悲鸿已处于分居状态,但她仍然是徐悲鸿名义上的夫人,还非常关注着徐悲鸿的动向,因此,她的记忆应该是准确的。事实上,《美术研究》杂志1980年第4期登载的“徐悲鸿年表”,其记载为“1939年,经新加坡,举行筹赈画展(三月)。抵印度,于12月,在印度国际大学举办中国近代画展”[4]。薛克翘编写的《中印文化交流史话》一书则介绍得更为详细:“1938年八九月间,徐悲鸿接到诗人泰戈尔的邀请,10月即带上一批作品自重庆奔香港,1939年1月到新加坡、又在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等地举办画展,辗转达一年之久,约于冬季到达印度,12月在印度国际大学举办中国近代画展。”[5]这里的12月,当然是1939年的12月。
作家傅宁军为写作《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一书远赴印度对徐悲鸿在印度的活动做过详细的调查了解,对徐悲鸿到达印度的时间和情况有精确的描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八日下午,新加坡码头海风浩畅,徐悲鸿与送行的友人握手道别,登上经缅甸仰光赴印度加尔各答的一艘邮轮。当他抵达加尔各答时,谭云山已赶到码头迎接。”[6]徐悲鸿抵达圣地尼克坦的精确时间,写在他给友人的信中:“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六日上午12时少3分。”[6]从11月8日离开新加坡码头,到抵达圣地尼克坦为什么用了将近一个月?这是因为除了邮轮要在仰光可能停留外,到加尔各答码头上后也有麻烦。傅宁军告诉我们:“英国人管辖之下的加尔各答海关,对华人艺术家并不友好。傲慢的海关官员扔过来一大堆英文表格,说徐悲鸿那七八个装满古今中外画作的画箱,全都得打开,每一幅画都得点验、登记、估价、交保(否则照估价预缴关税50%,将来离开印度时未卖出发还,再扣除手续费20%),他才不管你是到印度来干什么的。
不知是真的无知,还是故意找碴,英籍海关官员居然拿出一枚铜印,要在徐悲鸿带去的每一幅画上,戳一记海关的蓝色印章。气质文雅的徐悲鸿大为光火,“那舅子的关税,真不是东西!”,他的宜兴话,外国人听不懂。谭云山赶紧用英文说明,人家就是不理。双方僵持不下,幸亏泰戈尔迅速派人前来交涉,海关对泰戈尔不敢不尊重,答应印戳改盖在画的标签上,总算保住了这批艺术品的完美。徐悲鸿后来说,他带的画太多,来不及一一清点,海关逐件地盖戳,帮他弄清随身携带的画作有六百几十几幅。
在加尔各答与英籍官员周旋,徐悲鸿根本无暇浏览这座印度第二大城市的风光,天天耗在海关。耽误了八天,徐悲鸿才从海关来到加尔各答火车站[6]。
由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确确凿凿认定徐悲鸿到国际大学的时间是1939末,而不是上述著作所说的1940年。
二、在国际大学,徐悲鸿在谁家吃饭?
《廖著》中说,徐悲鸿在国际大学期间是在钱达家中吃饭。她写道:“钱达先生的夫人也是一位著名画家。他们夫妇殷勤好客,悲鸿每天都在他们家中就餐。”[1]钱达先生当时是泰戈尔的秘书,与谭云山一家关系很密切。他的夫人是一位画家,他们夫妇殷勤好客,这都不错。徐悲鸿有时到他家吃饭也是可能的,但说他“每天”都在他们家就餐,于情于理,都是完全不可能的。不知道作者这样写,有什么根据。
于情,徐悲鸿与谭云山两人个人关系非常好,他肯定会叫徐悲鸿在他自己家中吃饭,吃中国饭菜,而不会让徐悲鸿去吃他完全不适应的印度饭菜。徐悲鸿与谭云山认识时间很长,他们两人都是中印学会的发起人,早在中印学会筹备期间,就有很多交往。泰戈尔邀请徐悲鸿到国际大学访问讲学,也是谭云山提议的。邀请函发出之后,与徐悲鸿之间的联系、安排,都是由谭云山负责的,直至徐悲鸿抵达印度,如前所述,也是谭云山专程到加尔各答去迎接的。两人这样的关系,谭云山怎么可能将他推出门去,安排他到钱达家中去吃印度饭菜呢?
于理,谭云山是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作为院长,谭云山将中国学院办成了中印两国学者交流的重要基地,为培养两国文化研究的人才和深入开展研究提供必要的条件,学院可为来交流的学者提供住宿条件,谭云山自己的家则作为公共食堂,使外来学者无食宿之忧,因此,来到中国学院的人都感受到他照顾的温暖。既然外来学者来到中国学院都在这个“公共食堂”吃饭,当时,印度的物质生活相当贫乏,对徐悲鸿,谭云山当然更不会将他推到钱达家中,而是对他关心备至,将他的吃住都安排在自己的家里,尽最大努力为他创造尽可能好的生活和创作环境。
事实也的确如此。2005年8月间大型电视纪录片《徐悲鸿》摄制组在印度拍摄期间也访问了国际大学,还访问过现在仍在印度居住的谭云山的小女儿谭元,他们记述,“谭元……与我们聊起她的父亲谭云山与徐悲鸿、泰戈尔的关系,一边介绍、一边拿出她珍藏的许多老照片,讲述他们相互之间的友谊。…… 徐悲鸿来圣蒂尼克坦时,每天都是在谭云山家吃饭,仿佛是谭家的老客人”[8]。傅宁军到印度调查时也访问过谭云山的大儿子、著名学者谭中。谭中告诉他,“徐悲鸿先生在圣地尼克坦期间,在我家吃饭”[6]。深圳大学有个印度研究中心,在他们编辑印刷的《谭云山中印友谊馆》中有一篇徐悲鸿绘《谭云山》肖像的文章,其中写道:“在深圳大学谭云山中印友谊馆中,收藏着大量珍贵文物。其中,徐悲鸿绘赠谭云山及其妻子陈乃蔚的作品尤为珍贵。赠给谭云山的是国画《谭云山》肖像,赠给陈乃蔚的是素描《观音像》。这两幅作品,饱含着徐悲鸿和谭云山夫妇的深情厚谊。徐悲鸿……长住在泰戈尔国际大学谭云山家里。作为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竭尽地主之谊,从各个方面帮助支持徐悲鸿。”[7]这里没有专门提到吃饭的问题,但既然是长住在谭云山家,难道会安排到另一个人家中吃饭?
由以上材料可以确定,徐悲鸿在印度期间是在谭云山家吃饭,而不是在钱达家中吃饭的。当然钱达作为泰戈尔的秘书,夫人又是画家,有时请他到家中吃饭也是非常合情理的。钱达在印度独立后曾先后担任外交部、房产部的副部长及手工业局局长等职务,20世纪50年代曾率领印度友好代表团访问中国,也许期间曾与廖静文见面,提起过徐悲鸿到他家吃饭的事,廖静文则误以为徐悲鸿是一直在钱达家中吃饭。
三、徐悲鸿在印度举办两次画展的时间
徐悲鸿在印度期间,分别在国际大学和加尔各答举办了两次画展。关于这两次画展的时间,《阿文》是这样介绍的:“1940年末,罗宾德拉纳特在加尔各答和圣地尼克坦为徐悲鸿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画展,得到印度文化界的热烈反应。”[2]也就是说,两次画展都是在1940年末举行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一书是这样记述的:“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四日,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圣地尼克坦的国际大学隆重举办徐悲鸿画展。这是印度第一个中国现代著名画家的画展。”[6]②这里的记述指明,在国际大学举行的徐悲鸿画展是在1939年末举行的,也就是说,徐悲鸿一到国际大学就举行了画展,它与1940年在加尔各答举行的徐悲鸿画展在时间上相隔了差不多整整一年。画展举行的时间明确到了年、月和日,当然是可信的。前述“徐悲鸿年表”和薛克翘的著作也与这一记述一致。
在徐悲鸿国际大学画展后不久的1940年2月17日,圣雄甘地访问国际大学,泰戈尔在他的家院为甘地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席间泰戈尔将徐悲鸿介绍给甘地,并建议他为徐悲鸿举办画展。会见中,“在拥挤喧嚷的人群中,徐悲鸿拿出速写本,用短短几分钟为甘地画了一幅速写像。甘地看了非常高兴,在这张画上签了名。当晚,徐悲鸿记下与甘地相逢的过程,他写道:‘今天于印度整个灵魂共同生活,深感荣幸’”[6]。正是在这一年的年底举行的印度国民大会期间,由甘地而不是泰戈尔在加尔各答为徐悲鸿举行了他的第二次画展。按《泰戈尔作品鉴赏辞典》中附录的泰戈尔简明年谱,1940年泰戈尔已在病中,且9月病情加重,被送到加尔各答就医,并于次年8月去世。所以,虽然此时可能他也人在加尔各答,但也无力为徐悲鸿举办画展了。
在《廖著》中也提到徐悲鸿在国际大学的画展。她说,“画展先后在圣蒂尼克坦和加尔各答两地举行”,没有提到两次画展的具体时间。但她提到甘地1940年2月17日访问圣地尼克坦,“泰戈尔先生亲自将悲鸿介绍给甘地先生,并建议举办徐悲鸿画展,以敦睦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甘地先生表示赞许”。然后说,“举办悲鸿画展的准备工作很快就绪了”[1]。这里虽然没有说到徐悲鸿国际大学画展的具体日期,但既然是“准备工作很快就绪了”,那么也可以确定有一次画展的展出日期是在年初。由此可以确定,《阿文》中指两次画展都是1940年末举行的是有误的。
顺便指出,《美术研究》登载的徐悲鸿年表中说,“徐悲鸿1940年2月在加尔各答举行作品展览”[4]也是错误的。如前所述,1940年2月甘地到访圣地尼克坦,徐悲鸿为甘地画了速写像,并在速写像上面写了“廿九年二月十七日下午三时半悲鸿”的字样。年表作者可能以为这个画像是徐悲鸿在加尔各答举行画展时为甘地画的,因而搞错了展览的时间。
四、结语
本文对某些介绍徐悲鸿的生平和他的学术活动的著作中涉及的有些重要错误史实做了厘清。徐悲鸿是我国著名艺术家,他的生平事迹受到我国广大群众的关注,他的作品受到我国广大群众的喜爱。一些作品或文章对他的介绍存在某些史实错误虽然并不会对徐悲鸿本人的伟大有影响,也不会对广大人民群众对他的喜爱和尊敬有影响,但历史毕竟不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娘,我们应该尊重历史的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还是有其价值的。
[注释]
① 《泰戈尔与中国》为中英文双语版,查英文原文为“Xu Beihong came to Santiniketan towards the end of 1939 at‘Rabindranath’s invitation.”不知是否翻译之误。
② 实际上这并不是印度第一个中国现代著名画家的画展,此前中国画家高剑父在印度举行过画展。
[1]廖静文.徐悲鸿一生 我的回忆[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2][印]阿密达瓦·巴塔查理亚.1924年以来的中印画家交往拾遗[A]//泰戈尔与中国[M].北京:中国编译出版社,2011.
[3]蒋碧微.我与悲鸿 蒋碧微回忆录[M].长沙:岳麓书社,1986.
[4]冯法祀.徐悲鸿年表[J].美术研究,1980(4).
[5]薛克翘.中印文化交流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6]傅宁军.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7]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谭云山中印友谊馆[M].(自印)深圳.
[8]苏伊.印度速写[N].无锡新周刊数字报,2015-12-02.
Correction of Some Historical Facts of Xu Beihong in Visva-Bharati University Of India
LIU Kai-sheng,HU Ling-ling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angsha,Hunan 410004,China)
K825.72
A
1672-934X(2017)05-0153-04
10.16573/j.cnki.1672-934x.2017.05.024
2017-07-15
刘开生(1944-),男,湖南耒阳人,教授,主要从事文史研究;胡玲玲(1942-),女,湖南汝城人,教授,主要从事高教管理工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