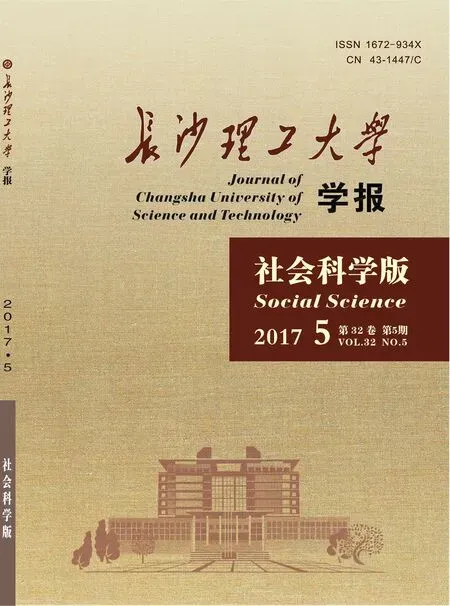“楼梯上”的境遇:1990年代诗歌想象维度的转换
张凯成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楼梯上”的境遇:1990年代诗歌想象维度的转换
张凯成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1990年代诗歌的想象力立足于1990年代初期的“断裂”语境,与其后社会转型的语境之中,呈现出了内在的转换历程。朱朱的《楼梯上》所营构的“楼梯上”的悖论,与臧棣的《在楼梯上》所呈现的“在楼梯上”的突围,构成了一种对位的联系,二者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1990年代诗歌想象维度的内在变化,即由抒情想象逐步转向了叙事想象,转变本身有其积极的意义。
1990年代诗歌;想象力;抒情想象;叙事想象
Abstract:The poetry imagination in 1990s is based on the"break"context in early 1990s,and on later social transformation context,which shows the internal conversion process.The paradox of"on the stairs"in Zhu Zhu's On The Stairs,and the breakout in Zang Di's On The Stairs constitute a counterpoint,both of which,to a certain extent,reflect the internal changes of the dimensions of 1990s poetic imagination;that is,the lyrical imagination has gradually shifted into the narrative imagination.As a matter of fact,the transformation itself has its positive meaning.
Key words:poetry in 1990s;imagination;lyric imagination;narrative imagination
谈论1990年代诗歌的想象力,首先离不开的是其所处的具体历史语境。从根本上说,诗歌想象力与时代境遇、历史发展、社会心理变迁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联系,如耿占春所言,“想象作为一种永恒的美和自由的精神力量,与现实世界抗衡而又遥相呼应,它既高出于现实而又与生活平行地发展着”[1]。因此,1990年代诗歌的诗学想象建基于特有的“现实世界”之中,二者之间呈现出“平行式”的发展轨迹。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诗评界对1990年代诗歌的历史语境保持了清醒的认知,这其中既包括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等人所认识到的1990年代初期诗歌写作语境的“断裂”状况,①又不乏耿占春、孙文波、姜涛等人对1990年代诗歌与外部语境之间关系的价值指认。②正是在1990年代初期的语境“断裂”与其后的社会转型中,1990年代诗歌的想象力呈现出了内在的转换历程。笔者藉此作为本文写作的重点,试图对1990年代诗歌想象维度的发展做出可行性的思考。
一
历时层面来看,1990年代初期的诗歌写作与1980年代中后期诗歌(尤其是“第三代诗”)之间既保持了相对的延续,又努力摆脱着后者的“影响焦虑”。此时期诗歌的想象力正处于“失序化”的社会语境之中,时代的“剧变”带给大多数诗人以巨大的心理伤痛,他们需要在调整“创伤”心理的同时,通过具体的写作来宣告自我之于诗歌本体的坚守,而变化了的社会环境又以其强大的掣肘力制造着诗歌写作的不可能性。诗人朱朱的《楼梯上》(1991年)大致呈现出了此一时期诗人们基本的心理状态:
此刻楼梯上的男人数不胜数/上楼,黑暗中已有肖邦。/下楼,在人群中孤寂地死亡。③
张桃洲认为这首诗“形象地勾画了当时诗歌界乃至整个文学界、知识界所处的一种令人尴尬的‘楼梯上’的处境”[2],笔者看来,这种“尴尬的‘楼梯上’的处境”不仅直接隐喻了1990年代初期诗人们的真实心态,更表达出了一种群体性的时代困境——诗中数不胜数的“男人”陷入了一种“楼梯上”的悖论,即游走于“上楼”与“下楼”状态之中的迷茫与无助。此外,朱朱在诗中还表现出了他对诗歌写作前景的自我预判——“黑暗中的隐没”与“人群中的死亡”这样一组带有明确价值判断性质的短语,不无诡谲地说出了他对诗歌发展形势的基本态度,即相较于“人群中孤寂地死亡”,对已有的“黑暗中的肖邦”的朝向更有其相对的合理性。可以说,1990年代初期的诗人们大都卷入了“楼梯上”的悖论语境中,他们把“抒情想象”作为摆脱现实焦虑的主要方式,努力建构出诗歌写作的可能性。当然,这里的“抒情”相较于1980年代诗歌的“抒情”有着较大的被动性,诗人们更多地用它来描摹“断裂”的时代语境,他们在加速内心与现实对接的同时,提供着社会转型期诗歌写作的方向。
随着社会语境的不断变迁,诗人们渐趋走出了1990年代初期“楼梯上”的心态,其想象力也逐步挣脱了“抒情”的性质,而更多地融入了富于判断力和综合性的叙事思维。诗人臧棣在1990年代中期(1995年)写出《在楼梯上》一诗:
电梯已停开。接早班的小姐/曾说她不能理解任何玩笑:包括爱情/我刚刚翻越院门。我的左脚腕/在落地时扭了一下:这像是/要加深我对一种经历的记忆//楼梯昏暗。因为每层的灯泡/都已烧坏。没有人负责更换/或者即使有人在他家的门前/换上新的。但不超过一星期/灯泡就会失踪,带着它的新鲜的光明//电灯开关还在。在幽暗中/它还有一小部分面孔流露出来/像是这座居民楼的良心/或是有关它的良心的隐喻/一种多余的动作把在开关上的//酣睡的灰尘抱到/我右手食指的小床上。突然间/黝黑的指纹:似乎能对付一切/加入有一张天堂的传票需要凭按/完全可以不用殷红的印泥//我坐在十五层的一级楼梯上/感到整座大楼就像黑夜的一个鸟巢/像是有巨大的翅膀婆娑我的困倦/在那里,没有任何阴影能够存活/幽灵和我挤靠在一起,呼吸着寂静和往事[3]
诗中所描写的“在楼梯上”的场景有其悖论性的前提,即由“停开的电梯”造成的被动性的“置入”,但“置入”本身又包含着诗人自我的主动意识。诗中的“我”置于由“接早班的小姐”“楼梯”“灯泡”“电灯开关”等生活元素所组构的空间中,臧棣通过复杂关系的审视型构出了现代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状态,“叙事想象”成为其写作此诗的内驱力,政治、道德、日常等诸多社会因素大都熔铸在叙事性的想象空间之中,想象的本源意义(即柯尔律治所认为的巨大的“调和力”④)也由此呈现出来。就写作观念来说,臧棣提倡诗歌写作与社会现实、日常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他看来,“每一个时代的诗歌写作,其实都是处理它所面对(经常是有意选择)的其自身的诗歌史的问题”[4]。因此,《在楼梯上》的第二节和第三节通过对常见社会问题的描写,便同时指出的是1990年代诗歌自身所存在的基本问题。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在楼梯上》一诗中所出现的道德下滑、良心隐失等现象与1990年代初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无关系。当市场经济体制以国家制度的形式最终确立,经济话语便逐渐占据了社会权力话语的中心,这同时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发生,使得诗歌写作被迫置入到更为复杂的话语场中,诗人们则不得不直面由经济权力形成的时代“巨兽”的广泛影响。谭五昌认识到市场经济发展与诗歌写作之间的“反比”关系:“市场经济……培养了人们的实用主义人生观与价值观,对于人们的现实生存确实带来了诸多的好处与利益,但对于诗歌(不是指媚俗意义上的诗歌)来说则无异是一场精神的灾难……诗歌在大众眼里成为一种累赘的精神负担,而诗人,则仿佛成为堂吉诃德式的‘向风车挑战’的怪物。”[5]立足于如此的社会语境,1990年代中后期的诗人们在写作中体察到了社会生活的诸多变化,其诗学想象也随之出现了新的适应性调整。整体来说,对特定历史境遇中“自我”的强调,成为此时期诗学想象的重要方向,诗人以“自我”对抗着社会语境所带来的各种“统治性威胁”,并藉此获得了更多的写作“自由”,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自由不仅受到各种统治者的威胁,而且更多地受着一切我们认为我们所控制的东西的支配和对其依赖性的威胁。能够解脱、获得自由的方式只能是自我认识”[6]。在1990年代中后期诗歌写作中,叙事想象占据了更多的诗学空间,诗人们不再被动地适应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写作语境的转变,而是能以积极的姿态降低转变本身所带来的影响,并以之作为探寻写作可能性的出发点,寻求着对现有写作困境的突破。“叙事”的加入及“声音”的多样性使诗歌包容力不断加深,叙事想象逐渐成为此时期诗歌写作的思维主体。
还需强调的是,笔者在此并非有意制造《楼梯上》与《在楼梯上》之间的互文关系,而是试图以“楼梯”作为二者之间的关联点,在可控的关系读解中发掘出1990年代诗歌想象维度的内在变化。抛开诗人的个体差异性,当窥探各自所处的不同写作语境时,我们可以发觉朱朱《楼梯上》与臧棣《在楼梯上》之间的“对位”联系,二者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1990年代诗歌想象维度的演变历程,即由“楼梯上”的困境所形成的抒情想象,转变为“在楼梯上”的突围过程中所依凭的叙事想象,这里的“在”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主动性的置入,最终指向的是叙事性想象思维的形成。
二
1990年代初期诗歌的想象力建基于社会转型期的历史语境之上,陈超曾将此时期诗歌的想象类型归纳为“颂体调性的农耕式庆典诗歌”与“迷恋于‘能指滑动’,‘消解历史深度和价值关怀’的中国式‘后现代’写作”,他同时指出了此两种想象模式所带来的“价值迷惑”性[7](P11)。可以说,“断裂”的时代语境造成了诗人们普遍的写作压力与思想悖谬,随着压力和悖谬的不断加深,他们并未找到接纳时代的合理方式,于是在心理层面形成了一种“楼梯上”的悖论——普遍的迷茫、尴尬与焦灼。面对“转变”的社会现实,此时期诗歌的想象力被迫表征出了一种“由热情向着冷静,由纷乱向着理性的诗的自我调整”[8]。因此,1990年代初期诗歌的想象力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运思手段,诗人们在“断裂”的社会语境中通过“抒情想象”来完成自我对社会、时代以及诗歌本身的被动指认。
1990年代初期诗歌的想象力致力于诗人内心与变幻现实之间的平面化展示,处于心态调试期的诗人们大都将抒情想象作为诗歌写作的基本手法,藉此探寻着诗歌写作的可能性。如西川在“秋天的大幕沉重地落下”的时代语境中,以一种“老了”的抒情心态去接受“一系列游戏的结束”与“动物一样死亡”,其内心正面临着“楼梯上”的悖论,因为“要他收获已不可能,/要他脱身已不可能”(《一个人老了》)。此时的西川尽管还未形成对“历史强行进入”的明确体认,但“老了”一词诠释出了“历史”扭曲内心的可能。王家新对社会转变有着清醒的认知,他在《转变》一诗的开端便以“季节在一夜间/彻底转变/你还没有来得及准备/风已扑面而来”的抒情性表达宣告着“转变”的来临。面对突如其来的社会转型,诗中的“你”被迫陷入了迷茫与无助的境遇——“你一下子就老了/衰竭,面目全非”,诗的结尾(“是到了在风中坚持/或彻底放弃的时候了”)正凸显出了此时期诗人们所持有的抉择式心态。欧阳江河将“马”作为“浪漫世界的最后高蹈”与“冷兵器时代的热烈风景”,它面临着成为“不能入土的种子”与“非马”的可能。诗句“马如此优美而危险的躯体/需要另一个躯体来保持/和背叛。马和马的替身/双双在大地上奔跑”中,“马”在现时代的语境中已无法通过本真的躯体来保持自我,它不得不与“马的替身”共同奔走于此时的“大地”,并且随时有可能被后者所取代。面对如此的境遇,“马”最终走向了自戕——“马的影子透过复制的纵深,/两腰迭出,四蹄突破前额,/由此形成了时间上的错视和重围。/马奔向爱和末日,奉献神髓。”(《马》)孙文波的《回旋》直面了“断裂”的时代语境,“石头像流水一样融化”“歌唱的鸟伤了喉咙和翅膀”等诗句正是对“断裂”语境的抒情想象。尽管诗人最终发出“失败呵失败,消失呵消失”的哀叹,但他依然保持着对未知的追问——“当精神追逐着精神,还有谁,/能够使融化的石头重新复原?/使鸟儿在此振翅和歌唱?/没有了。我们灵魂的狂喜又怎样选择?”。孙文波的追问不仅成为其坚持写作独立性心态的关键,而且也回应了张曙光在面对“带有道德气味的历史”的恐惧时,所表达的“重新翻回那一页”“重新/聚拢香气,追回美好的时日”(《尤利西斯》)的愿望。西渡在《残冬里的自画像》一诗中表现出了他面对复杂社会语境时的“相反的心境”,诗句“而悲伤作为一种情景,在我们身体里最幽暗的部位/正和外面暮色里降雪的氛围吻合”正昭示出诗人试图抵达内心世界与外部氛围相互“吻合”的努力,他将“转变”了的语境作为一种存在“前提”,其所着力思考的是“怎样献身给生活”。于是,在面对“结束是不可能的”与“开始时不可能的”这一相互悖离的社会语境时,西渡保持了相对乐观的心态,其内心所形成的是“一种即将复活的希望开始被淫雨淋着”的坦然。整体上来说,面对“楼梯上”的悖论,1990年代初期的诗人们在进行抒情想象的同时,努力重构着内心世界与现实语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除上述诗歌外,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欧阳江河的《傍晚穿过广场》、于坚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钟鸣的《石头》、肖开愚的《下雨——纪念克鲁泡特金》、翟永明的《我策马扬鞭》、郑单衣的《在我们中间》等诗歌也体现出了突破“楼梯上”悖论的可能。
1990年代初期诗歌的想象力建基于“楼梯上”的悖论之上,更多地作为“旁观者”进入到诗歌写作中。这一方面得因于1980年代中后期诗歌想象中所存在的无序、混乱等问题尚未解决,有着“承继”关系的1990年代初期诗歌在想象力层面自然带有不可避免的焦虑性。另一方面(最为关键的是),此时期诗歌的想象力受制于“断裂”的语境,诗人的内心与外部语境形成了相互的“压力”,极易制造出写作的困境,抒情因素的大量存在成为摆脱困境的重要表现。换个角度说,1990年代初期诗歌的想象力更多地拘囿于抒情性的凝滞空间中,这不仅造成了想象的模式化与解构性,而且极大地限制了其处理社会问题的效力。随着社会语境的不断变迁,尤其当诗歌想象力置入经济体制改革、文化制度转变等复杂的“社会场”时,其自身便走向了重构。这些社会因素的增加也使得1990年代诗歌的想象力不再掣肘于初期单质化的抒情循环,继而走向了陈超所说的“用抒情消灭抒情”,⑤诗人们在写作中逐步加入了较多的叙事因素。
三
基于1993年后先锋诗歌所表现出的“想象力向度的重大嬗变和自我更新”,陈超将此时期诗歌的诗学想象概括为“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并指出这一概念在诗歌功能与诗歌本体意义层面的双重理解[7](P11-22)。联系到1990年代中后期特定的诗学语境,“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提出有其重要的诗学价值所在。然而,尽管陈超指出了该命题所处理的“具体的生存、历史、文化、语言和个体生命中的问题”的复杂性,但笔者以为,这些诗学问题在不同历史阶段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并且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关键程度也各自相异,因此“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便带有较大的时段特性。张桃洲看到了“历史想象力”所带有的“止于包容力或异质性、抽象的历史意识或宽泛的文化情怀等层面”的批评局限[9]。姜涛则意识到“个人化历史想象力”所受到的1990年代初“对于乌托邦话语、宏大叙事等的反动以及个人对历史的担当意识”这一历史前提的牵绊,他同时指出了,“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动如此剧烈,要进入这一‘巨兽’体内,把握多方面绽开的矛盾,对于认识、感受能力与知识储备的要求,以及对语言诗体方面创造性的要求,与90年代初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的基本事实[10]。可以说,面对变动中的社会语境,1990年代中后期诗歌的想象力发生了内在的转换。
整体上说,1990年代中后期诗歌的想象力与社会现实之间处于相互扭结的状态中。随着叙事性因素的不断加入,此时的诗歌写作逐步回应了姜涛对1990年代诗歌“综合能力”的吁求。⑥与初期所面对的“楼梯上”悖论不同,1990年代中后期的诗歌写作更多地表现为“在楼梯上”的突围,即诗人们经历了1990年代初期的思想“震荡期”后,更为主动地去适应转型期的社会历史语境,他们在处理复杂的诗学问题时能够形成富含自我判断力与独立性的叙事想象。较之于“楼梯上”的被动处境,“在楼梯上”有着主动性的表达,这同时使其想象力能够形成自主的集聚,最终构筑起了新的想象思维。如张曙光的《小丑的花格外衣》中,一方面,以“俄狄浦斯王”“阿伽门农”“维纳斯”“海伦”等为代表的历史,与以“精神分析”“原子弹”“焚化炉”“艾滋病”等为代表的现实相互盘诘;另一方面,由虚无的历史(“历史只是/一堆肮脏的文字,在时间的风雨中变得模糊”)所凝构的生命之“轻”,与以荒诞的现实所形成的生存之“重”不断纠葛,诗人不得不在无序的生存征象中寻找宿命中的自我。叙事想象在诗人找寻自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不仅认识到了复杂的现实处境,而且最终能够由对处境的认知抵达对“我”的智性判断——“我的一生也许是一场辉煌的失败”。即便生存本身有着失败的命定性,诗人仍以“当面对着命运和胜者——/我来了,我胜了,或我征服/但胜者何胜,而败者何败——”的宣言式表达抵抗着既定的命运。陈东东的《下降》一诗则直陈了由异化、变形的经济现象所导致的生存悲剧,诗中的“他”作为“身份中混合和末世子孙和/大经济新生儿灼痛的血”的代表,面对的是由“煤气厂”“不锈钢巨罐”“铁烟囱”带来的对“田野”“绿色”“乡村”的致命伤害。他将其敏感的神经融汇到叙事想象中,由此深入地触及到了社会的生存隐症,并试图以批判性的姿态获得对理想化生存现实的精神认同。
臧棣的《菠菜》一诗将“日常”置入“政治学”的审美空间中,如张桃洲所言:“菠菜之类普通事物进入诗写的范围……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较为密集地出现,体现了这一时期诗歌的某种变化,表明诗歌开始放弃关于超拔、伟岸和庄严事物的宏大叙事,转向对身边的切近的琐屑事物的书写。”[11]臧棣通过对“菠菜”这一日常存在物的静态书写,实践着“不纯”的诗学,诗句“菠菜的美丽是脆弱的:/当我们面对一个只有五十平方米的/标准空间时,鲜明的菠菜/是最脆弱的政治”正从现实的介入性角度描绘出日常的政治性,强化着“文本现实与文本外或‘泛文本’意义上的现实的相互指涉性”[12]。而在西渡的《一个钟表匠人的记忆》中,由“钟表匠”这一特定的意义价值体所承载的记忆回环于“世界的快”与“我的慢”之间,这种记忆通过时间的绵延,体现出了经由精神性的“卡里斯马”抵达经验性的荒谬现实之间的嬗变过程,诗人以叙事想象建构出“红色的夏天”“阳台”“钟表”“海洛因”等多维的时空镜像。正如臧棣所说:“钟表匠的记忆不是被动地接受历史给他的印象,而是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他用他的记忆来对抗历史给个人造成的普遍的压力。……钟表匠的记忆还对这首诗所触及的历史经验起着细节的润色作用,使它们变得具体而生动。”[13]
除此之外,西川的《致敬》、欧阳江河的《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于坚的《〇档案》、肖开愚的《动物园》、孙文波的《祖国之书,或其他》、吕德安的《死亡组诗》、朱朱的《一个中年诗人的画像》、桑克的《雪的教育》、姜涛的《慢跑者》等诗歌也都是诗人运用叙事想象来进行写作的典型,这些诗歌文本构筑了1990年代中后期诗歌想象力的基本景观。值得肯定的是,此时期的诗学想象跳出了初期“楼梯上”的悖论,通过“在楼梯上”的突围抵达了新的写作空间,并由此形成了1990年代诗歌想象力维度的内在转换。叙事因素的融入极大地增强了诗歌文本处理社会问题的有效性和包容力,不断触及着王家新所意识到的诗歌本有的艺术认知力:“而在今天,诗歌的‘胃口’还必须更为强大,它不仅能够消化辛普森所说的‘煤、鞋子、铀、月亮和诗’,而且还必须消化‘红旗下的蛋’,后殖民语境以及此起彼伏的房地产公司!”[14]
综上所述,正是在1990年代特有的从“楼梯上”到“在楼梯上”的诗学语境中,1990年代诗歌的想象力发生了由抒情想象到叙事想象的转变。这种转变呈现出了积极的意义,它一方面促使1990年代诗歌写作由初期的失序与震荡,逐步转向中后期的秩序重建与思想的稳固性;另一方面,这也使得1990年代诗歌逐步挣脱了抒情性的“轻”,转而走向了叙事性的“重”,并在由群体性的抒情向个人化的叙事转变的过程中表现出显在的优越性。
[注释]
① 欧阳江河认为:“对我们这一代诗人的写作来说,1989年并非从头开始,但似乎比从头开始还要困难。一个重要的结果是,在我们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了。”(《’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载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1990年代备忘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82页。)西川指出:“对所有诗人来讲,1989年都是一个重要的年头……青年们的自恋心态和幼稚的个人英雄主义被打碎了,带给人们一种无助的疲惫感;它一下子报废了许多貌似强大的‘反抗’诗歌和貌似洒脱的‘生活流’诗歌。诗人们明白,诗歌作为一场运动结束了。”(《答鲍夏兰、鲁索四问》,载《让蒙面人说话》,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268页。)王家新谈到:“从大体上看,1989年标志着一个实验主义诗歌的结束,诗歌进入沉默或是试图对其自身的生存与死亡有所承担。”(《回答四十四个问题》,载闵正道编《中国诗选(第1辑)》,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17页。)
② 耿占春曾阐述到“也许我们时代的诗歌将开始进入一场诗学和社会学的漫长的争吵”的可能性;(《一场诗学与社会学的内在争论》,载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1990年代备忘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268-277页。)孙文波认为:“诗歌的确已经不再是单纯地反映人类情感或审美趣味的工具,而成为了对人类综合经验:情感、道德、语言,甚至是人类对于诗歌本体的技术合理性的结构性落实。”(《我理解的90年代:个人写作、叙事及其他》,载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1990年代备忘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5页。)姜涛则指出了1990年代诗歌写作表现出的“综合能力”。(《叙述中的当代诗歌》,载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1990年代备忘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289-297页。)
③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选诗歌均引自张桃洲编《中国新诗总系1989—2000》,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④ 柯尔律治认为:“(想象)这种力量,首先为意志与理解力所推动,受着它们的虽则温和而难于觉察却永不放松的控制,在使相反的、不调和的性质平衡或和谐中显示出自己来……(《文学生涯》,载刘若端编《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69页。)
⑤ 此为陈超对他在解读郑单衣《昏迷》组诗时所面临批评困境的概括性指认,他指出:“……近来的《昏迷》组诗,像一团彼此缠绕冲撞的线条,不过这线条是画在一个圆球上,像埃舍尔的怪圈。评论遇到了难题,你很难理清诗人的基本意向,他扩大了我们的茫然,扩大了诗歌的载力。你也可以说郑单衣还是抒情,但这种抒情显然缺乏我们习惯的特征。能不能说他是用抒情消灭抒情?”(《当前诗歌的三个走向》,载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1990年代备忘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313页。)
⑥ 姜涛认为:“宽泛地来讲,‘90年代诗歌’摆脱了以纯诗理想为代表的种种青春性偏执,在与历史现实的多维纠葛中显示出清新的综合能力:由单一的抒情性独白到叙事性、戏剧性因素的纷纷到场,由线性的美学趣味到对异质经验的包容,由对写作“不及物”性的迷恋到对时代生活的再度掘进,诗歌写作的认识尺度和伦理尺度重新被尊重……”(《叙述中的当代诗歌》,载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1990年代备忘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292页。)
[1]耿占春.新诗的创造性想象[A]//耿占春.改变世界与改变语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7-8.
[2]张桃洲.众语杂生与未竟的转型:1990年代诗歌综论[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92-102.
[3]臧棣.在楼梯上[A]//臧棣.燕园纪事[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178-179.
[4]臧棣.人怎样通过诗歌说话[J].北京文学,1997(7):71-88.
[5]谭五昌.诗意的放逐与重建[M].北京:昆仑出版社,2013:28.
[6][德]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M].薛华,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132.
[7]陈超.先锋诗歌20年:想象力维度的转换[A]//陈超.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8]谢冕.中国循环——结束或开始[A]//闵正道编.中国诗选(第1辑)[M].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292.
[9]张桃洲.陈超与中国当代诗歌批评[A]//谢冕,孙玉石,洪子诚,编.新诗评论2016年(总第二十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9.
[10]姜涛.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在当代精神史的构造中[A]//谢冕,孙玉石,洪子诚,编.新诗评论2016年(总第二十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1-46.[11]张桃洲.日常生活的政治——从臧棣的"菠菜"看中国20世纪90年代诗歌趋向[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22-26.
[12]唐晓渡.90年代先锋诗的几个问题[J].山花,1998(8):79-85.
[13]臧棣.记忆的诗歌叙事学——细读西渡的《一个钟表匠人的记忆》[J].诗探索,2002(Z1):54-73.
[14]王家新.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关于当代诗学[J].诗探索,1996(1):1-13.
Circumstances on the"Stairs":The Transformation of Poetic Imagination Dimension in the 1990s
ZHANG Kai-cheng
(College of Literature,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I207.25
A
1672-934X(2017)05-0100-07
10.16573/j.cnki.1672-934x.2017.05.015
2017-07-15
张凯成(1990-),男,河北邯郸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