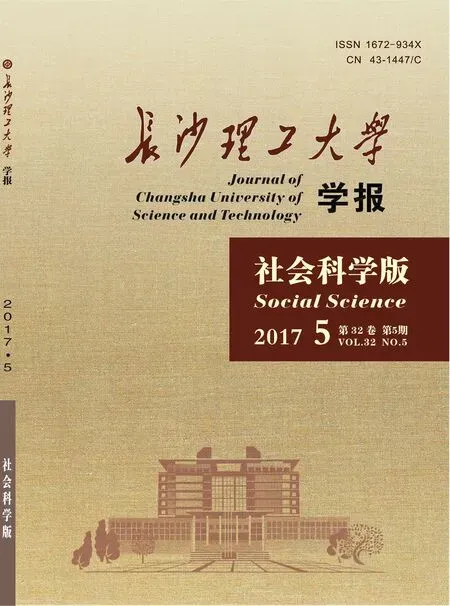对女性本质的探究及面向赛博格的思考
齐磊磊,叶宇彤
(华南理工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641)
对女性本质的探究及面向赛博格的思考
齐磊磊,叶宇彤
(华南理工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641)
西方传统的人的本质理论实际上是一种以男性为主导的人的本质模式,通常忽视对女性本质的探讨。女权主义对此提出批判,并对女性本质进行探究。在赛博格社会,哈拉维怀疑、批判女性本质,主张赛博格打破传统二元论、模糊性别界限,人人都是赛博格。但哈拉维忽略了另一种可能:赛博格技术的介入将建构女性本质,为女性本质的展开和实现提供可能。在赛博格社会,劳动将成为女性本质,成为女性获得生存、地位和发展的最后堡垒。
女性本质;赛博格;人的本质
Abstract:Human essence in western tradition is actually a kind of male-dominated model,usually ignoring exploring female essence.Feminism criticizes this tradition,and explores the female essence.In cyborg society,Haraway doubts and criticizes the female essence,and advocates that the Cyborg break up the traditional dualism and blur the gender boundary,and that everyone is Cyborg.But Haraway neglects another possibility that the involvement of Cyborg technology will construct the female essence and provide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realization of the female essence.In Cyborg society,working will become the female essence,and the last fortress for women to get survival,status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female essence;Cyborg;human essence
马克思首先明确提出人的本质命题: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劳动或实践是人的本质。相对于人的本质,女性是否具有女性本质?对于女性本质的疑问源于女性幼年成长中家庭、学校、社会所告知的“女孩要有女孩的样子”,源于各种社会媒介所呈现出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女性形象,源于恋爱、结婚、生育中女性的心理体验与扮演的角色,源于高科技与多元主义冲击下女性对自我意识、自我本质、自我价值认同的反思。“生态女性主义者假设女性的本质不同于男性;女性的特殊性在于与自然的密切联系。”[1]对于女性本质的思考要追溯到传统哲学家对人性的思考、女权主义对父权制和二元论的批判及对女性本质的探究。同时也要将其放在赛博格的背景下进一步研究,因为技术赋予女性更多力量,“揭开女性本质,需要技术介入”[2]。技术的介入为女性本质的展开和实现创造了可能性和条件。
一、什么是女性本质?
女性本质是在引入性别后,从人的本质派生而来的概念,因此在探究女性本质的含义之前,需先厘清人的本质的含义。实际上,“人性和人的本质在历史上经常是不作区分的,这造成了许多理论上的混乱”[3]。因此需分清人的属性、人性和人的本质这三个含义相近的概念。黄楠森教授认为:“人的属性是表层的东西,属于存在的范围;而人性和人的本质则是更深层次的东西,属于本质的范围,它们也是人的属性,但相比其他属性,它们能表现人之所以为人而根本区别于其他动物;人性和人的本质是人的根本的属性,人性是人的许多根本属性,而人的本质则是人的最根本的属性,人的本质只能有一个。”[3]比如食与性不是人的本质,而只是人的属性;而理性、感性也不是人的本质,都只是诸多人性之一。
对于如何考察最根本的人的本质问题,黄楠森教授主张从人的本性、人的地位和人的发展来研究人的本质问题。“通过人的存在揭示人的本质和规律性,人的本质问题也就是从本质上讲人是什么的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即从本身讲,从人和他的条件的关系来讲,从人的将来发展来讲。”[3]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流派代表人物阿莉森·贾格尔(Alison M.Jaggar)认为,“任何人的本质理论的核心必然是一个关于人类能力、需求、愿望和目的的概念。一个关于人的本质理论要求我们从人们实际表达出来的无数的需要和愿望中分离出‘真正的’或基础的或必不可少的需要和愿望,而且在那些关于基本需求和愿望的观念与人类繁荣和幸福的观念之间似乎存在紧密的联系。”[4](P28)对于如何考察人的本质,贾格尔认为人的本质是与人类繁荣幸福相关的真正的,基本的能力、需求及愿望相关。女性本质是从性别切入的角度谈女性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根据对人的本质的定义,可将女性本质定义为:女性本质是女性最根本的属性,它不是表层的属性,而是更深层次的属性。比如生殖、性就不构成女性的本质。考察女性本质问题,也应从女性的本性、女性地位、女性的发展,从与人类繁荣幸福相关的女性真正的,基本的能力、需求及愿望来研究。
二、女性:被贬低、质疑具有理性本质
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的西方哲学深受二元思想的影响,美国后现代女性主义学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也认为西方传统哲学充斥着对立二元论。这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二分法,将男/女、理性/情感、文化/自然、客观/主观、工作/家庭等等对立起来。“这种二元性的划分一直延续至今,并影响了我们的认识方式和科学。在一种隐喻的方式中,这一系列二元性中的前者,往往与男性相联系,而后者则与女性相联系”[5],前者是主要的,后者是次要的,前者主导、支配着后者。这种二元论是一种将女性、自然、动物当作他者对待的符号暴力,助成了其对他们实行统治的逻辑和实践。“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传统西方认识论中的二元结构是不合理的,因为这种二元结构将男性与理性、社会等同,将女性与情感、自然等同。”[1]这种思维模式下的西方传统哲学中的人的本质理论,实际上是一种以男性为主的人的本质理论。“欧洲哲学史上对人之本质的探究,其基本进路是与肯定男性、贬低女性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对人之本质的探究就是建立在对男性作为理性人的肯定、对女性作为理性人的否定的基础之上的。‘理性’实际上是在人之本质探究中被性别化、男权化了的一个哲学范畴。”[6]
理性是人的本质,这种观点由来已久,并且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处于首要地位。柏拉图认为灵魂是人性中更高的成分,躯体是较低的成分。他将灵魂分为肉欲、理性和精神三个部分,认为人性中的这三个成分应保持完美和谐,但理性应当居支配地位,控制精神和肉欲。在《费德罗篇》中,他把灵魂比作由一匹白马(精神)和一匹黑马(肉欲)拉的马车,并由一个驾车人(理性)驾驭着车子。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是包括理性的一组功能,是活的事物的“形式”,这个形式是表示使某种属性成为它所属事物的根本性质的那种东西。亚里士多德没有严格地遵循柏拉图的三分法,他将灵魂分为理性和非理性两部分,前者支配着后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将理性作为最根本的人性,即人的本质。实际上,以理性为人的本质的传统思想贬低、甚至质疑女性具有理性能力。“亚里士多德在妇女问题上是保守的,他认为妇女虽然是人,但是在理性上天生就不同于男性,不太适合理性思维,比较适合生儿育女和操劳家务。”[7]中世纪的思想家也认为女性的理性能力低于男性。“柏拉图许多讨论的对象是男性,而不是女性,他认为总的来说男人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胜过妇女。”[7]现代哲学家像康德、休谟、卢梭、黑格尔等都对女性具有充分理性能力产生质疑[4](P51)。总之,西方传统的人的本质理论,带有一种男性偏见,贬低、否定女性具有理性本质,忽视了对女性本质的探讨。
三、女权主义的回应
西方传统的人的本质理论,由于忽视、贬低女性受到了女权主义极大的批判。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也就是说是男人、社会使她成为第二性。社会把第一性给与了男人,男人是主要者,女人是次要者。”[8]20世纪60年代,这种女性从属理论开始传播开来,被人们视为科学发现的新起点。在这种背景下,当代女权主义对西方传统以男性为主的人的本质模式提出了批判并对女性本质进行了探究。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女性具有完整理性的潜能,主张只有人的本质,这种人的本质是没有性别区分的。受二元论的影响,自由主义认为理性是一种“心智”的能力。不管是亚里士多德、中世纪的思想家,还是一些现代哲学家都质疑女性具有充分理性能力。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反对这种观点,“主张女性具有完全理性的潜能,因为女性与男性一样具有完全的道德责任,女性通常没有意识到这个潜能的事实是因她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并且被限制在家庭范围内”[4](P51)。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认为男性和女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存在男性本质或女性本质这样的事情。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人的本质理论存在的问题是鼓吹二元论、忽视身体、赋予了人的头脑过多的价值,充斥着男性偏见。关于人的本质,激进女权主义内部有不同的观点。早期的激进女权主义者追求“两性同体”的人性理想,主张废除性别角色,消除性别角色之间的差异,认为女性可以甩掉社会强加给自己的本质,自由选择自己未来的本质。但也有些激进女权主义者则认为人的本质的理想通过两性同体无法实现,这个理想应发展女性天生的特殊能力。当代激进女权主义者主张女性不是天生的,是父权制创造了男性和女性,普遍赞美女性气质,否认男性化的女性是本体论的基础,认为那些专属于女性的特征是最有价值的特征,女性的生殖功能、女性不同于男性的心理特征具有特殊的价值。激进女权主义存在的问题是不先考虑阶级结构,而是考虑性/性别结构及其生成关系,即男性在性方面对女性的构造,这使其可能沦为一种生物决定论的立场,而且激进女权主义对于父权制概念的强调掩盖了不同社会以及相同社会不同阶级、人种、民族背景下女性的差异。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认为男性和女性的差别是可以减少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继承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观点,即人的本质是通过人类、社会、自然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被历史创造的。不同于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固定的,人的本质不是生物决定的结果,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自由主义认为女性本质上不能区别于男性,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人不是抽象的、无性别,认为两性之间的差别是可以减少的,女性本质是她们生存的社会关系形成的,改变这种关系就能改变女性的本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认为要优先考虑社会对女性本质的影响,却常常忽略了性或性别的因素。
激进女权主义和生态女权主义提出女性具备一些令人类赞美的有价值的特性,比如关怀、母性、照顾、细心、温柔,具备不同于男性的心理特征、需求,“女权主义者察觉到了女性这种内在的力量和灵魂,可以想象的是母亲与胚胎或母亲与婴儿之间的天生的生理联系,所产生的那些心理特征一直是与女性联系在一起的,无论在古代的传统还是在现代的行为科学上”[4](P138)。在激进女权主义和生态女权主义看来,母性是一种潜在的能力,是一种印刻在每一个女性基因上的能力。“当我们开始把我们自己定义为一个女人的时候,最直接的特性是母亲与孩子的养育关系中最相同的特性:同情、直觉、适应能力,把成长的意识看作是一种过程而不是目标、创造力、保护他人的感情,以及既有理智又有感情的反应能力。”[4](P142)马克思非常注重劳动在人的本质中的作用,他在提出人的本质命题中强调了“劳动或实践是人的本质”。黄楠森教授也认为,人的本质是劳动能力或物质生产的能力,他在《人学的足迹》一书中强调,“人的本质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使用人自己创造的工具改造物质世界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的形成和发挥产生多种多样的人性,产生人和人类社会”[3]。因此可以将母性、关怀、同情、劳动视为女性的本性,但不能将这些女性的本性视为普遍适用女性的本质。我们承认每个女性都有自由选择和创造自己本质的权利,法国哲学家萨特认为,“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有关于我们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没有普遍适用的真理,主张每一个人都必须创造他的或她的本质”。激进女权主义和生态女权主义眼中的女性特征带有很浓的生物学、感性色彩,“生态女性主义者只是在生物学基础上探讨女性的特征,而没有在人类学的意义上,或者说从本质的意义上揭示出女性的特质,她们只是在感性的意义上探讨女性的本质、力量和美德”[1]。对女性本质的考察,除了考虑女性本性,还应从社会中女性地位、女性发展来考察。
四、基于赛博格技术对女性本质的思考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按照哈拉维的观点,当代世界就是一个赛博格社会(Cyborg Society)。因为一些增强生活功能的辅助器材如手机、电脑、眼镜已成为当代社会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在苏建华看来,“Cyborg Society可能代表两种意义:其一是指社会中住着cyborg的公民,其二就是指整个社会结构就是cyborg。”[9]哈拉维承认赛博格技术虽然在开始的发展阶段会强化父权统治,但她相信赛博格技术之后的发展将会反过来推翻父权统治,有利于女性的解放。也就是说,赛博格技术将赋予女性更多力量,为女性本质的展开和实现创造可能。
(一)赛博格
赛博格(Cyborg)是人与机器融合之后形成的半人半机器的新物种。这个概念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航空和航天局的两个科学家曼弗雷德·克林斯(Manfred Clynes)和内森·克兰(Nathan Kline)提出的,赛博格(Cyborg)是英文“控制论”(cybernetic)和“有机体”(organism)的组合。他们提出这个概念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技术手段对空间旅行人员的身体性能进行增强,“赛博格有意引入外来成分扩展有机体自我调节功能以适应新环境”[10],通过运用药物和外科手术的方法可以使人类在外层严酷的环境条件下生存。科幻电影中充满赛博格,比如《银翼杀手》中的瑞秋,《攻壳机动队1995》中的草薙素子,《蜘蛛侠》中的大反派“章鱼博士”。日本NHK电视台于2005年拍摄的纪录片《改变人类的赛博技术》详细介绍了自21世纪以来赛博格技术的最新发展情况:美国和日本等国家都对赛博格技术的研究开发投入了巨大的资金,美国人希望通过赛博格技术把士兵的作战能力提高到极限程度。赛博格技术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弥补人体的残疾,在这个阶段赛博格技术的典型代表有机械眼、机械手臂、机器人外衣。随着赛博格技术进一步发展,研究者发现,一旦人脑和机械相连,大脑和技术共同进化,由机械传来的感觉将使大脑发生变化,欣然接受、适应久了大脑就会把机械当成自己的东西,机械可以有意识地调节大脑,通过脑机接口,大脑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机械,同时赛博格技术也可以实现电脑对大脑的控制。
哈拉维对赛博格概念进行了扩展,用它描述目前人与技术、机械融合的状态。“赛博格是一种控制有机体,一种机器和有机体的混种,一种社会现实的造物,也是一种科幻小说的造物。”[11](P149)她认为赛博格有两个组成成分,“其组成成分首先包括我们自己以及其他未经我们选择的高科技形式的有机造物,它们成为信息系统、文本和人体功率学控制下的劳动、需求和繁殖系统。赛博格的第二个必要成分是机器,同样成为通信系统、文本和根据人体功率学设计的自动装置”[11](P1)。在哈拉维看来,随着高科技地应用普及,现代社会人人都是赛博格。“到20世纪晚期,我们的时代成为一个神话的时代,我们都是怪物凯米拉,都是机器和有机体的理论化与组装的混种,我们就是赛博格。”[11](P150)也就是说,我们都是技术实体的一部分,人与机器的界线已经消失。这尤其体现在现代医学领域,现代医学充满赛博格,充满着有机体和机器之间的结合,戴义肢、心脏起搏器、人工耳蜗的人无疑可视为赛博格。
(二)女性本质在赛博格社会展开和实现的可能
哈拉维在她1985年发表的《赛博格宣言:科学、技术和20世纪末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一文中提出了“赛博格女权主义”。在这篇文章中,哈拉维是怀疑、批判女性本质。哈拉维坚持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即性别是社会建构的,因此,“不能提供本质团结的信念基础。身为‘女性’并不意味着就能天生把女人绑在一起,甚至没有‘身为’女性这样一个状态,它本身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范畴,是从有争议的性别科学话语和其他社会实践中建构出来的。性别、种族或阶级意识是家长制、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些矛盾的社会现实的可怕历史经验强加给我们的一种成果”[11](P155)。哈拉维认为赛博格打破传统二元论,模糊性别界限,女人本质的象征系统瓦解了。在哈拉维看来,20世纪晚期美国的科学技术打破了人类与动物、有机体与机器、身体与非身体的界限,赛博格社会是一个中心主义瓦解的世界,赛博格隐喻着二元对立范畴的模糊,依托性别、种族的身份划分不再构成根本。“随着这个星球上的人们之间的关系网络变得前所未有的多重、丰富和复杂,男人的家庭和女人的本质的象征系统崩解了。”[11](P160)赛博格社会的主体是一个非本质、多元、没有清楚边界、冲突的主体。
实际上,哈拉维对女性本质的批判代表了当代西方哲学中的一种去中心化思潮,这种思潮强烈批判了“本质”这种观念。但反讽的是,“非中心化思潮自身内部隐含着难以克服的理论矛盾。一方面,它拒绝形而上学对基础、中心和根据的寻求,另一方面,它又肯定、确立新的基础和中心”[12]。诸如德里达对差别的迷恋和哈拉维对赛博格的执着。其实,哈拉维对女性本质的批判是着眼于她想要寻求一种赛博格政治神话,一种跨越界线立足于亲近性、结盟的政治神话,来取代生态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等传统女权主义那种寻求本质认同的政治联合。“赛博格女权主义者(cyborg feminists)必须指出,‘我们’再也不想要任何自然的统合基质,而且没有任何建构是整体的。”[11](P157)张君玫教授在《后殖民的赛博格:哈洛威和史碧华克的批判书写》一书中提到,对于哈拉维来说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去质疑‘认同’或‘同一’(identity)的思考方式,并以立基于共同处境或亲近性的结盟(coalition)关系来取代容易僵化的‘认同’”[12]。所以说,哈拉维从政治联合的向度解构女性本质,但她忽略了女性本质在赛博格背景建构、展开、实现的可能。实际上,从赛博格背景下女性的处境来看,劳动将成为女性本质。
根据哈拉维的观点,在赛博格社会,将出现一种女性化的趋势。“由于机器人学和相关技术导致‘发达’国家的男性的失业,并恶化了未能在第三世界的‘发展’中产生男性就业机会,而随着办公自动化在劳动力剩余的国家中也成为主导,工作的女性化随之加强了。”[11](P168)哈拉维认为这是一种以女性为首的新经济模式。“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中,白人男性近来变得容易长期失业,而女性失业的速度没有男性那么快。家事经济是一种工作的重组,这种工作在广义上具有先前属于女性工作的特点,即字面上只能由女性完成的工作,而今工作被重新定义为女性化了,无论实际从事这些工作的是男人或女人。女性化意味着变得极其脆弱。”[11](P166)这种女性化趋势意味着女性相比男性更具有劳动力优势,哈拉维认为女性是科技为本的产业尤其电子业偏好的劳动力。但是,哈拉维还看到在赛博格社会贫穷的女性化伴随着福利国家的解体,以及家事经济的盛行,不稳定的工作环境使很多女性的生活都要环绕电子业相关的就业机会,置身于这样的处境,为了获得稳定的就业机会,女性的劳动本性进一步被激发了出来。
在赛博格社会,女性的实际情况是,“她们被整合进一个生产/繁殖以及被称作统治信息学的通讯世界体系”[11](P163)。也就是说,世界被翻译成一个编码的通讯世界,而有机体都变成了通讯装置。“微电子技术介入下的转变:劳动转化为机器人学和文字处理;性转化为基因工程和生殖技术;心智转化为人工智能和决策程序。”[11](P165)人类的繁殖无需通过女性生殖,基因工程和生殖技术下是赛博格的生产、复制,机器人取代女性承担照顾家人的角色,小孩由育儿中心抚养,女性逐渐远离传统家庭,成为集成电路中的女性。在这种背景下,女性的生育、养育功能将被高科技取代,那些曾受到人类赞美的女性本性如母性、关怀、同情在这个浓缩为C3I:指挥—控制—沟通—指挥的编码世界,似乎都失去了往日备受赞美的光环与价值。由此可见,在赛博格社会,女性传统的母性、关怀、同情本性发展的空间很小,而劳动本性随着家事经济的盛行将成为女性的本质。在家事经济中女性被提高的劳动优势和地位,以及围绕电子业相关就业机会的生活,都使女性的劳动本性被进一步强化、成为符合女性真正的、基本的需求与愿望的本质。
[1]易显飞.“技术-性别-自然生态”问题探究——以生态女性主义的视域[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5-19.
[2]余乃忠,易显飞.论女性本质的技术介入[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5(5):83-87.
[3]黄楠森.人学的足迹[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12.[4][美]阿莉森·贾格尔.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M].孟鑫,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5]刘兵,曹南燕.女性主义与科学史[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4):44-51,80.
[6]王宏伟.女权主义哲学与人之本质探究批判[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77-83,160.
[7][美]莱斯列·斯蒂芬森,大卫·哈贝曼.世界十大人性哲学[M].施忠连,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99.[8][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939.
[9]苏建华.赛博格与全球脑对人类与社会的冲击[J].网络社会学通讯期刊,2001(17).
[10]Clynes M,Kline N.Cyborgs and Space[J].Astronautics,1960(9):27.
[11]Haraway D J.Simians,cyborgs,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M].New York:Routledge,1991.
[12]智河.当代西方哲学中的非中心化思潮[J].哲学动态,1991(6):38-41.
Inquiry into Female Essence and an Opinion in the Case of Cyborg
QI Lei-lei,YE Yu-tong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Guangdong 510641,China)
N031
A
1672-934X(2017)05-0058-06
10.16573/j.cnki.1672-934x.2017.05.009
2017-06-28
华南理工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XZD06)
齐磊磊(1978-),女,山东临淄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科学哲学研究;叶宇彤(1991-)女,福建寿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女性主义哲学。